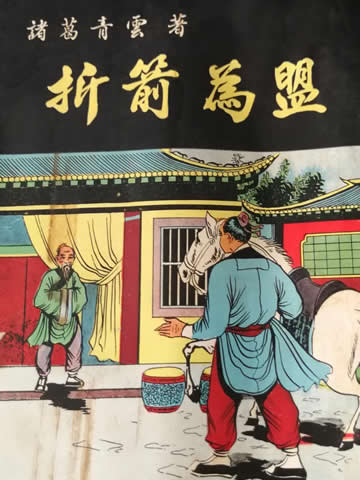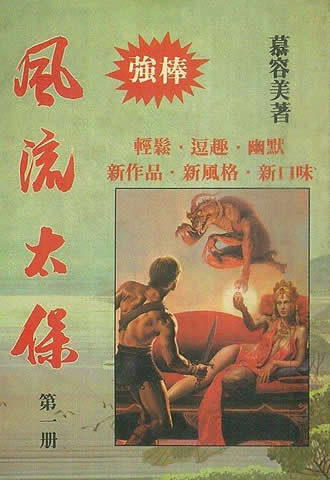“祁家堡”的风浪已成往事,而连串下来的日子却是平淡又悠闲的,好像江湖上的变幻烟霞,诡异风雨,全在这一阶段里安静隐寂了,辰光是那样的恬宜,像小河流水般自然安详。
甚至燕铁衣亲赴杭州去主持当地“青龙社”堂口的一次例会,也是抱着游山玩水的心情去的,非常轻松愉快。
他独个儿办完了正事,又坚辞了“青龙社”在杭州城的“大首脑”“抗山肩”陶昂的陪侍,孤家寡人,无拘无束的在杭城游历了三天。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无论当地的风光如何明媚秀丽,幽迷撩人,燕铁衣也认为差不多看够了!观赏景色,他认为有如品尝美点佳肴,浅试即止,最能引人回味,等到看腻了,也就伤了脾胃,再难寻思怀忆。
于是,和来时一样,他又单人匹马离开了杭州,转向“楚角岭”。
天气有些燠热,在清晨出了杭城,到如今已近午时,却是越走越觉得炎燥,阳光当头,火辣辣的,像在烤着大地,他的内衫已被汗水湿透了。
这是一条蜿蜒于田野丘峦中的大道,在如火的烈日照耀下,除了远处偶有一片荒林外,住户人家也都错落掩隐于岭脚山腰之间,稀稀疏疏,间距很远,要找处歇马、打尖的地方,可真不容易。
阳光下的大地是起伏辽阔的,闪幻着青与黄为主的色调,迢遥的景色中浮动着淡淡的气氲,将景物非常轻微的扭曲,带一点凛凛的,热浪却散发得更炙热了。
燕铁衣抹着汗水,一面策骑前奔,一边游目四顾,想找个合适的所在停下来休息一会,避避日火,他坐下的马匹,也湿漉漉的毛汗黏贴了。
他自己带得有干粮、水囊,但他不到必要时却不愿面对这些——一顿新鲜可口的现煮食物,一壶香醇的酒、或者一杯清凉的饮水,不比他自己携带的冷硬干粮,同晒热了的囊中水要享受得多?
眼前并非特殊情势,又不是身处险地绝境,他犯不上如此委屈自己,因此,他一程一程地赶下去,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解决他饮食的地方。
天气真热,对这条路与周围的地理环境他又不熟,就这么一路朝下赶,走了二十余里地,犹不见一家酒栈、一家路店,甚至连一户适合打尖的住家也没有。
大道上静荡荡的,冷清清的,南来北往,只有他一人一骑;阳光底下的寂静是很奇异的,白昼喧哗,这里竟这样的幽静,叫人心中另有一股落寞不安的感受,但燕铁衣十分明白这种情景的发生——烈日照晒下,什么人愿意受着曝脱一层皮的折磨赶路?一般客商行旅,除非有急事的,大多会挑拣凉快的辰光上道!
叹了口气,他终于放弃了好好享受一顿午膳的希望,目光巡视,他勉强选中了路左边一座山岗上的几株大树下,作为他打尖的场地;那是离他最近的荫凉处,并不太合理想,却也只好将就凑合。
掉转马头,他奔离了大道,经过一条荒草蔓生的窄径后,他抛镫牵马上岗——从树下到岗顶那一株树阴处,居然连条窄径也没有了。
燕铁衣有些后悔,也有些懊丧,他一面吃力地扯着马往岗顶攀,一边回想着这几天在杭城时的口腹享受,可口的菜肴,精美的细点,各色各类香醇的名酒,还有各般各式风味绝佳的清凉汤羹,而如今,只不过短短的半日功夫,几十里路之隔,他就必须啃着干硬的粗食,饮带着怪味的皮囊中水,人生的际遇,真是变幻无定啊!
来到那几棵枝叶蓊郁,互为纠缠的树阴底下,他丢掉马,取了干粮同水囊,无精打采地走到树根盘结的阴凉深处,坐下,先拨开囊塞,喝了几口水,然后,他长长吁了口气,抹掉唇角的水渍;大热天,水总是好东西,虽说比不上清凉沁脾的果冻冷露,至少要比干着喉咙要强上许多。
朝树干上一靠,他的视线随着往四周浏览,正当他乏味的要将目光收回之际,却蓦地被远处一宗事物吸引住了!
在岗子后面,地形凹陷,凹陷的地势中,生满了又密又长的马尾草,再过去,就是一片疏林子,林前,有七、八个人影在晃动!
那地方,距离燕铁衣现在的位置,约有四五十丈之遥。
大热天,毒日头之下,杳无人迹的荒野山林中,这七、八个人冒着酷暑在干啥?
习惯上的本能反应,使燕铁衣警惕注意起来,他料得出其中的古怪意味,也感受得到这眼前的情况有些特异!必有些不寻常的事要发生,或是已经开始发生了!
那七、八个人在移走,在晃动,唔!有两个人分别站开,站到较高又较隐秘的地势上,模样显然是在把风,接着,林子里人影又闪,也不知道从哪里又钻出两个人来,不!三个人,这两个人尚挟持着一个人,被挟持者似是加上了五花大绑,虽在用力挣扎扭动,但却无济于事,左右挟持他的两个人正在粗暴的拖拽拉扯,将他!将他推向一棵枝节突兀的大树下。
另一个人手臂挥动,老天,一根绳索抛过那棵大树横伸的枝丫搭垂下来,这搭垂下来的一头业已打好了一个套结——刚能缠绕人脖子的套结,另一端,已被那人捆绑在树干上。
不消说,一幕惨剧就要发生了,他们是要活活吊死那个人!
悬挂吊绳的那株大树,本来并无特殊的地方,然而,只是多了这么一根绳子,看上去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棵树似在陡然间变得阴森,变得玄异,变得邪恶可怖起来,树干粗糙,瘰沥斑结,枝丫伸展突兀得何其怪诞,仿佛一个奇形的,多手多臂又似欲舞欲腾,暗里狞笑的巫魔!
这是桩大麻烦——人命总是大麻烦。
燕铁衣咽了口唾液,心里十分犹豫,却有更多的懊恼——他不希望自己管闲事,惹麻烦,同时,他恨自己的运气,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偏偏就在这种地方遇上了这么一桩事?
他已经有够多的烦恼,够多的事情,够多的忧虑了,扰他心神的俗务冗杂之事不少,他不愿意又蹚进一湾不相干的混水中。
可是——
他叹了口气,他就具有天生不能忍受“遗憾”的个性;那个人是谁?要吊死他的人又是谁?他犯了什么过失必须以生命偿付?最重要的,他究竟是否该死?
如果那人是十恶不赦,罪无可逭,吊死也就吊死他娘的,但,如果他不该死,他是个好人,甚至他是一个在恶势力胁迫之下的无辜牺牲者,那么!这“见死不放”的罪过可就大了,大得会令他终生不安!
要弄清这个疑团,要免除他的“遗憾”,就只有一个法子——上前问个明白,不过,他也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江湖中人,最忌在“上事”之际为人窥破或阻挠,这“上事”的内容不管是寻仇、械斗、劫夺、私刑或谈斤两,甚至只是印证武功,都不容事外人加以干扰,否则,那是一场莫须有的梁子要结!
设若那不幸的人值得一救,结梁子也就结吧,但是,如果那家伙罪大恶极,真个该死呢?这梁子却未免结得有些笑话,有些荒谬了。
燕铁衣苦恼得很,他一时决定不下要不要去冒这个险?
问题是——无论那人该死与否,只要他一旦现身,便即是一场麻烦,若是救了一个无辜者,这场麻烦惹得尚值,但那人假使死有余辜,这场麻烦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难过了。
值与不值的机会是各占一半。
唯一的法子,只有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有其他变通的方式,至少,目前没有。
燕铁衣不禁又诅咒起自己的运道来,为什么非要今天启程?为什么不早点打尖?迟点打尖?为什么偏又挑上了这个地方?种种因素,只有稍有一项变异,便碰不上眼前这桩麻烦!
突然,他怔忡了——不错,事事全这样凑巧,全配合得如此严密,莫非!莫非是冥冥中有此安排?天意如此?
冥冥中的定数该有神意的,而神意的因果,总不会去叫他救一个不应被救的歹人吧?
深深吸了口气,他聚集目力,全神贯注的向那边注视——就在这时,有一阵疾劲山风卷拂,那被强力挟持到吊人树下的仁兄头发立披散飘扬,乖乖,怎的却这么长法?而且,在阳光下闪泛的发色,居然是那种淡淡的棕红色?
猛地一愣,燕铁衣已经意识到那个不幸者是个女子,而难怪在左右两名挟持者的体魄比照下,身躯竟是如此窈窕纤细。
女人,天爷,是一个女人!
这一个个牛高马大的男子汉,却为何要对一个女人下此毒手?更这般郑重其事,如临大敌!
距离太远,燕铁衣看不清那些人的五官面容,但他可以体会到施暴者的决心同愤恨,也能揣摸出那不幸者的怨毒与不甘。
现在,他们已将那个女人硬推上一截显然是临时锯下来作为刑台的树桩上,女人挣扎得更厉害了,她在尖声叫喊,不,是咒骂;有四个人紧按着她,另外一人已将横枝上垂挂的绳扣套进了她的脖子。
那女人似是极度的悲愤,极度的怨恨,她拼命反抗,头颅也在奋力摇晃,棕红色的长发在阳光的反映下,闪闪泛出一种奇异的光彩!
围在她身体左右的四个大男人死死抓按着她,而那个将绳扣套入她脖颈的人,更恶狠狠地把她的一头长发揪紧,一圈又一圈的缠上了绳索。
在吊人树几步之外,正对着将要受吊的那个女人,是默默站立着的另三个人,他们似乎是这群人的首领,他们都没有动作,只是目注这一场惨剧的发展,当然,他们十分明白,发展的结果将与他们预料中的相同。
很糊,很细微的,风声带过来尖厉的诅咒声与凶恶的叱骂声。
燕铁衣知道,他必须马上决定是否干预此事了,一切的过程演变与后果责任全在他的一念之间,他要不要阻止他们?要不要问个明白?要不要留下遗憾?
情势已经紧迫得到了最后关头。
救,或是不救?只有这唯一的机会。
男人,总有几分英雄色彩的自负,而一个女子在遭到危难之际,似乎更容易引起异性的同情,现在,燕铁衣不禁自嘲地耸耸双肩。
那边,那些人的动作要比燕铁衣预料中的快得多,就当他刚刚下定决心要前往干预此事的一刹那,只见那女子足下的一截木桩突的被人踢飞,那女子的身体往下一坠,又猛地被套在脖颈上的绳索吊紧,微微一弹,就开始晃摆起来。
燕铁衣在震惊之下,身形立腾——他已经有很久的时间没有耗过这么大的力气奔掠了,以至看起来他的飞越之势便有如一抹流光,连闪连翻,足不沾地,瞬息间便到了吊人树的侧方!
几声惊呼尚未发出,燕铁衣已凌空暴旋,寒芒眩映中,索断人落,他翻身接住了从半空中掉下来的人体,匆匆一瞥,果然正是个女人。
迅速将那女子平放地下,燕铁衣猛力扯断套在她脖颈上的绳索,然后,以熟练的手法与技巧,连连为对方搓揉推拿起来。
这时,四周那些仁兄们,好像方才定下心神来,明白了这是怎么回子事,几声叱吼起处,两条大汉手抡朴刀,又凶又狠地扑上来猛劈燕铁衣。
燕铁衣一面在为那女子活血提气,上身不动,两腿猝然飞起倒弹,“铿锵”两声,两柄朴刀已随着两声怪叫滴溜溜抛上了半空!
那两个进袭者齐齐痛抚着手腕,却又悍不畏死的再一次赤拳冲上!
燕铁衣仍然是原来的姿势,直待那两条大汉从左右侧饿虎扑羊似的袭到,他的右脚才“刷”声竖弹,人们只是看见他的一脚扬起,冲来的两条大汉已闷哼连声,打着跟头翻滚倒地!
当然,燕铁衣那飞扬的一脚,其过程业已经过了两次的横击,由于快得离奇,传摄入人们瞳孔中的影像,便仅是两击之后归复于静态中的动作而已。
紧接着,叱喝连声,其余的五、六个汉子全已手抄家伙,打算一拥而上,但是,当他们正在群情愤激,待要围攻燕铁衣的瞬息,一个冷漠僵硬的口音已重重响起:“慢着。”
听到这两个字,那些待要扑袭上来的汉子们方才停止了动作,而燕铁衣也就更是放心大胆的低下头去,嘴对嘴的替地下晕厥过去的那个女子度起气来。
脸对着脸,鼻子贴着鼻子,燕铁衣一边以自己的丹田之气重复吹渡入那女子的喉腔中,一边双手在对方的心房部位用力按摩,以协助这受难者的心脏机能尽快恢复。
四周,静悄悄的。
唯一的声音,便是燕铁衣在深深吸气后又深深渡气的音响,那种音响有点古怪,好像是一个人在耗力之后的嘘嘘重喘,又似是害哮喘症者病发时的呻吟。
良久——
轻微的,压在燕铁衣身子下的那个女人,睫毛开始颤动了,而直到现在,燕铁衣方始发觉这女人的睫毛又弯又密又长,轻轻眨目,有如两排垂柳。
于是,那女子艰辛又沉缓地睁开了眼睛——一双虽然迷茫、怔忡、痛苦,却依然妩媚莹澈的丹凤眼。
就这样,她与燕铁衣眼朝着眼,鼻子贴着鼻子,脸颊黏着脸颊的彼此注视着,燕铁衣不能说话,也无法打手势,只有用眼神向她解释示意。
那女子先是一阵愤怒,又是一阵惊异,接着,她逐渐变得颖悟与了解,她的双瞳中的意蕴非常明显易懂;后来,她的目光透露着温柔、友善,更一再向燕铁衣传示了她的感激——这是个聪明的女人。
又过了一阵,她主动地转开脸去,脱离了燕铁衣的嘴唇,声音是微弱又嘶哑的,她道:“够了吧?”
站起身来,燕铁衣搓搓手,道:“这要问你,是不是觉得顺畅些了?”
那女人又缓缓将面庞转了过来,深深凝视着燕铁衣,而燕铁衣也第一次如此清楚的将她看得这般真切——天,这是一个多么美艳妖娆,荡人心魄的女人!她的双眉弯弯挑起,形成如两抹新月似的美妙弧度,挺直端秀的鼻子下,是一张丰润的、小巧的、能在勾动中令人魂迷的嘴唇——虽然现在失去血色,也一样的诱惑甜蜜;最令人不能忘怀的是她的一双眼睛,那是一双凤眼,是一双晶莹澄澈,黑亮得宛如墨玉的一双眼,而那双眼的深处,却透着炽烈的、火焰般闪耀的光芒,看上去是那么狂野、那么大胆、又那么倔强、流露着一股熊熊的、残暴的炙热,她的左边唇角上有一颗黑痣,大小如豆,这一颗黑痣衬托得好,使她更美、更艳,也更悍野了。
这不只是个女人而已,这还是一个可以害死许多人,迷狂多少人的女人。
她大约有二十三、四岁的年纪,这个年纪对她来说,正是成熟得恰好,魅力到达巅峰的年纪,似一团火。
纵然是刚自鬼门关上捡回了一条命,纵然她刚遭受到如此残酷的心身打击与折磨,但是!她憔悴的气色,孱弱的形容,却丝毫掩隐不了她的美色,反而更增添了一份楚楚怜人的韵致。
燕铁衣在看她,她也注视着燕铁衣。
像是微微叹息,她挣扎着蠕动了一下,轻幽幽地道:“谢谢你,朋友。”
燕铁衣笑笑,道:“不客气,哦,容我替你解绑!”
然而,燕铁衣尚不及动手,背后,那个冷硬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只怕没这么方便吧?”
燕铁衣眨眨眼,缓缓转过身来,他的背后,那三个人一字并排,说话的,是当中那个面色铁青,形态严峻冷削的人物,这人右边的一位,却是玉面朱唇,生像俊逸,而且神韵之间,与中间的说话人颇有相似之处,看样子,他们似是同胞兄弟;左边的一个,身材短小,却是环眼狮鼻,充满了一副剽悍之气,三个人卓立如山,气度沉稳,一看即知乃是这帮人的首领头脑。
另外七条大汉,早已环伺四周,形成了包围阵势,那七个人,嗯!竟是一式的兵刃——朴刀。
微微颔首,燕铁衣和气地道:“阻挠了各位的清兴,实在抱歉,这里,我先向各位赔罪。”
面色铁青的那人冷冷一哼,道:“看情形,阁下亦是江湖同道?”
燕铁衣笑道:“只在道上跑跑龙套,凑合着混碗饭吃!”
那人双目光芒肃杀,严酷地道:“既是一路中人,阁下当知道如此插手、拦事便与故意挑衅启端无异!”
燕铁衣忙道:“我确实没有这个意思,我想,这中间只怕是点误会!”
俊俏的青年人厉声接口道:“还在强词狡辩?我们与你素不相识,且无可言,我们在此解决我们的一桩怨隙,和你毫无相干,你却突如其来坏了我们的事,更不分青红皂白打伤了我们两个友人,这不是挑衅是什么?还会有什么误会?”
燕铁衣心平气和地道:“这位兄台请暂息雷霆之怒,我与各位,确是毫无怨隙,现在之前,也并不相识,但是,我偶尔经过此处,眼见各位正以酷厉之刑吊杀那位姑娘,一时心有不忍,方才冒昧施救;上天有好生之德,蝼蚁尚且贪生,不论那位姑娘犯了何等过失,好歹也是人命一条,大家有甚过节,何妨另以他法解决?动辄残命,未免有干天和,我身处局外,却不能见死不救!”
俊俏的年轻人上下打量了燕铁衣一阵,以一种轻蔑的态度道:“你不能见死不放?我问你,你是以什么身份,什么立场说这句话?”
笑笑,燕铁衣道:“就算是一个心怀恻隐的善意之人吧,我想替各位做个鲁仲连!”
那人勃然色变,怒叱道:“放屁,你是什么东西?你又知道此事的什么前因后果?懵懂糊涂,一派无知,居然也大言不惭要来这里做鲁仲连?你今天破坏了我们的计划,搅乱了我们的行动,就是找碴,既要找碴,拿出本事来!”
燕铁衣赔笑道:“兄台何苦如此气恼?大家有话好说,一动不如一静,我的确并无架梁之意,充其量,只是有心化解这场纷争,问一个事由内情。”
年轻人愤怒地道:“你配?”
摆摆手,那面色铁青的人踏前一步,目注燕铁衣,缓缓地道:“阁下年纪甚轻,但身手不凡,想亦是武林中的少年俊彦,后起之秀,初生之犊,素来不畏虎狼,敢问尊姓大名?师承何处?”
燕铁衣拱手道:“谬奖了,谬奖了,倒要先请教各位的贵姓大名?”
铁青的脸上浮起了一抹冷笑,那人道:“我是‘石虎’贺修,右边的一位乃是舍弟‘玉虎’贺弘,左边的这位,是我的拜兄‘红绸飞云’花川,那七位,号称‘七刀拢月’皆是金兰之交。”
恍然大悟,燕铁衣道:“原来各位都是‘八环聚义’的兄弟伙,难怪声势如此不凡了!”
所谓“八环聚义”乃是由八组相交深厚的挚友结义金兰,拜成兄弟,这八组人或是单一,或是数人,每一组表示一环,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力量,他们不是帮会,也非派别,却是另外结成的坚强势力,这“八环聚义”在武林中颇具声威,也有实际的分量,不是容易招惹的对象。
“石虎”贺修深沉地道:“你既知我‘八环聚义’,可见江湖情势亦极熟悉,此番你拦下此事,当也明白要还我们一个公道吧?”
燕铁衣拱手道:“我尽可能向各位讨个颜面,希望能以化解此事!”
“玉虎”贺弘道:“这算什么话?你就用这个方式来还我们所要的‘公道’么?”
燕铁衣苦笑道:“贺兄,你先别生气,大家心平气和,慢慢商酌不好么?我不是喜欢惹是生非的人,尤其不愿与各位结怨!”
贺弘傲气凌人地道:“谅你也招惹不起‘八环聚义’!”
叹了口气,燕铁衣道:“老实说,惹不惹得起是另一回事,我不愿与各位结怨的主要原因,是‘八环聚义’在江湖上侠名久著,平时急公好义,方正不苟,算得上是一批白道好汉,这样的人物,我一向钦佩,又哪里希望得罪呢?”
贺弘冷笑道:“说得好,但你实则却已得罪了!”
燕铁衣忙道:“贺兄请莫误会,我的本心却出自善意,乃是要替各位消弭纷争,化解戾气,试图救下一条生命……”
“石虎”贺修冷森地道:“但是,你可知道这条生命值不值得救?”
燕铁衣一派诚挚之状,道:“值与不值,正想请教,尚祈点明一二,以开茅塞,以解疑惑!”
贺弘大喝:“你连一丝半点的内情也不知道,就莽里莽气的胡乱插手搅和,你简直糊涂透顶,糊涂人,糊涂心,糊涂脑筋,闯下的糊涂祸!”
这似乎像在骂儿子一样,非但毫无忌惮,更且张狂之极,燕铁衣不禁大大起了反感,可是,他不到逼不得已,委实不愿结仇,况且此事的争端始之于己,他也就只好强行压制着自己的火气,硬硬忍了下来。
贺修向他乃弟抛去一个眼色,较为缓和地道:“你突如其来的破坏了我们的行动,实是一桩天大的错误,姑不论你是否会与我们‘八环聚义’生怨,就只这个女人,你也救错了!”
燕铁衣皱着眉道:“各位与那位姑娘骨子里有什么怨隙,我是的确不明白,所以才一再向各位请教,希望能以垂告此事详情;各位和我,同是江湖中人,各位固然行侠尚义,英名远播,而我呢?虽然谈不上‘侠义’二字,但至少也有颗悲天悯人的心,因此,见到这场血糊淋漓的凄惨局面,便不由自主横插进来,冀图替各位调停调停,更想弄弄清楚其中缘由,并明白一下此举的是非得失!”
贺弘忍不住又吼了起来:“你是闲着没事,寿星公吊颈,嫌命长啦?”
燕铁衣低喟一声,摇头道:“贺家二爷,你这股子肝火,也未免太旺了点吧?”
瞋目扬眉,贺弘厉声道:“不错,你又待如何?对待你这种冒失鲁莽的后生晚辈,不识自身为何物的无知小子,你还想得到什么颜色?”
燕铁衣道:“叫嚣谩骂,就不是解决事体的道理了!”
“石虎”贺修轻轻摆手道:“这位朋友,你的耐性不错,就凭这一点,我便将此事发生的来龙去脉,同你做个说明,同时,只怕你也会因为你的贸然之举而后悔不已!”
燕铁衣平静地道:“希望尚不至于这般令人懊恼;贺兄,我这厢洗耳恭听了。”
贺修缓慢又沉稳地道:“首先,你认为我们‘八环聚义’在道上的声誉如何?作风如何?”
燕铁衣道:“自然是堂皇刚正,节义可风的。”
点点头,贺修道:“我们也不是自我标榜,‘八环聚义’如何的替天行道,大义凛然虽说尚不敢言,至少,锄恶扶弱,惩奸恤贫的零星义举,我们却自来不后于人,就凭我们一贯的宗旨,一贯的行为,你想想,我们岂会无缘无故的以如此酷刑吊死一个女子?”
燕铁衣忙道:“照说,当然是不会的!”
贺弘寒着脸道:“既知不会,你横插一腿又是什么意思!”
燕铁衣容忍着道:“起先我也不知道在这里要吊人的是你们各位,何况彼此间又素不相识!”
轻咳一声,贺修又道:“此事暂且不谈,朋友,你应该知晓,除非是一个罪无可逭,死有余辜的人,我们才会以此手法加以惩治,只要还有半点婉转的余地,我们也不愿,也不忍做得这般决绝!”
燕铁衣颔首道:“相信是这样!”
往燕铁衣身后的那个女子一指,贺修道:“你晓得那贱人是谁?”
回头端详了一下,燕铁衣又接触到地下那个女人的眼睛——那双墨玉般莹亮,古潭般深邃,但却宛似在瞳仁中燃烧着赤红火焰般的眼睛,那是一双狂热的,几可融化一切的眼睛,仿佛魔鬼的咒语!
转过脸来,燕铁衣摇摇头道:“我不认识她是谁,方才之前,我也从未见过她,但是,她长得非常美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突然狂笑如啸,贺修激烈地道:“美?不错,她是美,非常美,出乎人们想像中的美,但,这副美丽的外表,却是她蛇般狠毒心肠的掩饰,是她无比丑恶灵魂的糖衣,她有如鹤顶之冠,色彩鲜艳,却可蚀骨糜心,有如罂粟之花,娇丽婀娜,却可蚀人志节,腐人神智,她在美丽的姿容包含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女巫,是一副蛊神的害人工具,是一条剧毒无比的赤练蛇!”
觉得喉咙里有些泛干泛苦,燕铁衣控制住自己不安的情绪,他没有回头望,却若有所失,若有所悟地感到心往下沉。
贺修脸色又转为严肃,他一字一字地道:“现在,你对这个女巫已经有了些印象么?”
燕铁衣涩涩地道:“她是谁?”
贺修的唇角微微抽搐,声音迸自齿缝:“‘血蒙妩媚’冷凝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