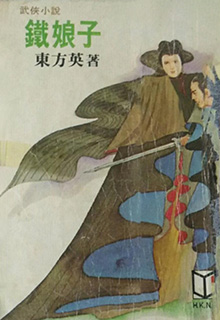约莫是半个时辰之后,朱乃魁转了回来,这一次,只有他独自个进了石室,而且,有些偷偷摸模、贼头贼脑的味道。
任非一见他,立即低促的问:“怎么样,解药到手了吧?”
朱乃魁先回手把门带上,始吁一口气,抚着前胸道:“老不死的,你挑着我去偷解药,算是找对了人,七姨放置解药的地方,除了师叔之外,就只我晓得,另有个好处,便是我出入他们的住处不受怀疑,但话是这么讲,真个动起手来。却仍不免捏着一把冷汗,直到如今,心腔子还跳得不太正常,娘的,这到底不是一桩光明正大的事体……”
任非也暗里移去了心口上的一块石头,开始轻轻松松的笑了:“你没有被贾如谋和姓阴的婆娘发觉吧?”
朱乃魁小声道:“当然是不能被他们发觉,要是露了形迹,场面就尴尬了,我行事的时候特别谨慎,真个连口大气都不敢喘,幸亏师叔和七姨也累了一夜,又受了伤,敷药之后中里间睡得正酣,神不知鬼不觉,我就把东西拿到了手……”
任非连连颔首,语带嘉许:“朱乃魁呀,其实只要再练上几次,你就可以改行去做窃贼了,那辰光,你也不用称为‘飞熊’,索性改叫‘赛时迁’还更妥当。”
沉下脸来,朱乃魁不快的道:“什么意思?我就他娘如此出力卖命,到头来还要吃你一顿讥讽?老不死的,你可得搞清楚,现在你仍然是我的掳囚,一个弄翻了面,我随时随地剥你一层皮下来!”
任非忙道:“开开玩笑,开开玩笑嘛,又何必当真?”
朱乃魁狠狠的道:“开玩笑?娘的皮,你有这个心情,我却没有这个兴致,眼下是开玩笑的时候么?”
打了个哈哈,任非放低了姿态:“好好。算我混帐,算我失言就是,如今言归正传,朱乃魁,解药拿出来吧2我们早早交割清楚,省得另生枝节。”
朱乃魁伸手入怀,小心翼翼的取出一个黄纸包来,打开纸包,里面是六颗绿豆大小,色泽朱红的药丸,他拿给任非看了看,又仔细包好,一边做着解释:“唠:这就是专治‘鸠藤’剧毒的解药了,共是六粒,第一次服四粒,第二次吞两颗,吃药的间隔要相距一个时辰,药效发作的当口,会全身涌污汗,亦可能引起呕吐,不过不要紧,这乃是毒性排出体外的必然现象,解毒以后,身子免不了有些虚脱,只要歇息个一天半日,就没事了任非慎重的问:“一定有效么?是不是服下这六颗药丸,所中的毒性就会砌底排除干净?”
朱乃魁板着面孔道:“这还用说?如果没有效或不能排尽毒性,又叫什么解药?老不死的,我朱乃魁可是正人君子,说一算一,你不要疑神疑鬼的行不行?”
任非陪笑道:“不是疑神疑鬼,更不是不相信你,凡事小心点总没有错……”朱乃魁抿着嘴唇沉思片刻,侵吞吞的道:“老不死的,你先别忙着要解药,咱们之间,还有些细节得讲明白……”任非生恐对方变卦,赶紧道:“你说,你说,交易是彼此有利的事,我当然会全力与你配合。”
朱乃魁道:“姓雍的服下解药,体力很快就会恢复,等他体力恢复之后,显而易见的便将破门出困,我可要问仔细,他一且出困,都准备干些什么事?”
任非犹豫了一下,转头问雍狷:“老弟台,朱乃魁的话你听到了?我想,这个问题我不便越咀代□,得请你亲自回答才行。”
雍狷淡淡的道:“好,出困之后,我仍要设法索回我的儿子。”
朱乃魁道:“但是,不可再次伤害我们的人,也不能和我师叔及七姨发生冲突。”
雍狷坦白的道:“只要他们不阻拦我、不碍我的事,我就会尽量避免伤害他们。”
指厂指任非,朱乃魁道:“想来你也要带他─齐走喽?”
雍狷额首道:“不错,任老大留在这里,只是死路一条,郎五迟早不会放过他,而你,在他失去利用价值之后,恐怕亦是瞧着他大不窝心。”
朱乃魁眼珠子─翻,悼然道:“别他娘把话说得这么难听,我可是个饮水思源,有情有义的人!”
雍狷道:“咱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朱乃魁,还是相见不如怀念的好。”
朱乃魁冷冷的道:“我不和你扯这些闲淡了,最后一句话,这件事决不能泄漏出去,你们的逃走,也与我毫无干系,此外,姓雍的,在你服下解药并证实药效灵验之余,总可以告诉我郎五哥的下落了吧?”
雍狷干脆的道:“可以。”
于是,朱乃魁拔出靴筒中的短刀,先替任非松了绑,将包交到任非手里,边叮吁着:“马上就给姓雍的服药,我到外面先去安排─下,在这期间,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们,可是你们也出不去,我将在适当的时间里进来取册页以及聆闻郎五哥的消息,希望大家坦诚合作,不要玩花招,事成以前,我已有万全的准备,谁想搞鬼,就注定倒霉!”
任非笑道:“你宽念,不会有问题,一切都照你的吩咐去做就是。”
朱乃魁大步离开,并将室门关上,有清晰的下锁声响起,看来,这位朱二爷嘴里希望双方”坦诚合作“,实则却─点也不放心。
任非略略搓揉手脚的关节部位,等活过血脉,他一跃而起,找着那只破瓷碗,在墙角的木桶里舀了半碗清水,又打开纸包,找了四颗药丸在掌心,合着清水叫雍狷吞下,然后,他开始为雍狷解绑,由于绳子捆得紧,又是密密麻麻交叉相缠,他用十根手指行事,就远不如刚才朱乃魁使刀子那么方便了。
雍狷服下解药,靠着壁脚闭上双眼,默默等待药性散开,任非─面双手不停,一面显得有些紧张的问:“怎么样?老兄台,有什么感觉没有?”
雍狷均匀的呼吸着,微微笑道:“才吃下药,药效大概不会这么快……”
解开了雍狷双臂双腕上的束缚,任非已是一头的汗,他接着动手去解雍狷足踩间的绳索,口中忍不住嘀咕:“朱乃魁那龟孙子口口声声提醒我们不要玩花样,倒不知他自己有没有使歪点子?如果这解药有毛病,他就休想看那册页一眼……娘的,还有这身捆绑,怎的就紧密到和蛛网一样?难解难分,累死人了……”
雍狷七情不动的道:“用不着急,任老大,慢慢来,横竖也捆了这一阵子,早点解绑,晚点解绑,都无所谓……”
拿衣袖拭了拭额头的汗水,任非吁着气道:“有反应了么?”
雍狷静静的道:“你先别急着问我有没有反应,任老大,我却一直担心着一桩心事。”
任非道:“什么心事?”
雍狷低沈的道:“不管朱乃魁拿来的解药是真是假,任老大,我们姑且当它是真的解药,他就算履行了这笔交易的诺言,但是你呢?任老大,你到底有没有第二本册页?”
任非嘿嘿笑了:“我当然有,老弟台,否则怎么敢和他谈买卖?”
雍狷不由纳闷:“可是,我明明亲眼看见你把那本‘落雁三击’的原册交给你的伴当刁不穷了呀,却又如何再变一本出来?”
任非形色诡秘的道:“老弟台,我不是说过么?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刁不穷那狗娘养的,仗着自己有几分本领,便待欺压于我,强取豪夺,咄咄相逼,哼哼,我打不赢他,却耍得了他;不错,‘落雁三击’的秘本原册我是交给了他,但在交给之前,我早已私下抄蓦了另一本收藏起来,换句话说,他有一本,我也有一本,而且,说不定我那一本,比他那本原册更要精密翔实……”
雍狷若有所悟的问:“莫不成你在原册里动了什么手脚?”
任非干笑道:“这个,你就不必多问了,总而言之,想占我的便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年头儿,光靠硬吃楞抢是不行的,主要还得会动脑筋……”
摇摇头,雍狷道:“你真是只老狐狸,任老大。”
任非褪下雍狷足踩问的绳索,无所谓的耸耸肩膀:“人要活下去,就该想法子保护自己,老弟台,世道便是如此,弱内强食,适者生存,若不多花点心思,就连剩菜残羹也没有你的份!”
雍狷正想说什么,忽然呼吸粗浊起来,面孔泛赤,汗水涔涔,他坐直身子,双手捂住胸口,频频干呕,模样似乎十分痛苦。
任非急忙为他轻拍背脊,边焦切的问:“怎么样,是药力行开了么?”
从雍狷额头上,毛孔里涌冒出来的汗水色呈污紫,颇有粘性,且隐隐发出一股腥臭气息,汗水分泌的速度极快,不片刻已浸透了他的衣衫,跟着就呕吐起来,吐出来的秽物,亦是黑糊灰杂─团,味道相当熏人。
任非又拿起破碗去舀清水,边送水给雍狷嗽口,他边喜形于色的道:“好象是真有效验了,老弟台,你还好吧?”
雍狷含水嗽了几口,这阵折腾下来,只觉内俯十分熨贴,呼吸也舒畅甚多,混身里外轻快不少,就是四肢虚软,骨节松散,有点提不起劲来。
放回破碗,任非又道:“你且歇息一会,老弟台,运运气看,能不能流走经脉,贯通穴眼?朱乃魁那王八羔子,这次还算是有诚意,不会耍弄我们……”
后脑靠在墙上,雍狷有气无力的道:“任老大,有桩事可别忘了,等一会交出册页的时候,犹得附带一个条件,叫朱乃魁把我的弓箭砍刀交还给我:“任非笑道:“一定,家伙便是我们习武之人的第二生命,当然不可随意丢弃,你放心,我必然会叫朱乃魁把你的兵刃带过来。”
雍狷闭目调息了一阵,始经声道:“我已经好得多了,任老大,这里还要再向你说声谢。”
任非呵呵一笑,正待开口,室门外已响起启锁声音,转眼间,朱乃魁那胖大的身影已经出现于石室之中一真叫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这小子简直把时辰拿捏得准透了,竟然一步都不差:仍然先把室门关好,朱乃魁端详着雍狷的气色,似乎完全不觉得屋里有股熏人的臭味;他搓着两只手,一副志得意满的德性:“喂哼,我这解药的效力可不是假的吧?所谓真金不怕火炼,灵不灵一试便知,任老鬼,我救了雍狷一命,该做的已经做了,现在,轮到你实践诺言啦,‘落雁三击’的册页在哪里?”
任非笑道:“你倒是立马追踪,猴急得紧,莫非还伯我不给你?”
朱75魁硬绷绷的道:“我们依约行事,其它一切少扯,我尽到我的本份,你就该尽到你的本份,老不死的,册页拿来,你再要罗嗦,可别怪我翻脸!”
任非连连摆手,一叠声道:“莫恼莫恼,朱乃魁,我惹不起你,册页拿去就是说着话,他伸出右脚,把那只又脏又破的干层底布鞋脱下,用手指模索鞋帮边沿,然后撕开一条缝,拿两指拈出一本薄薄皱皱的羊皮册页来,册页已呈淡褐色,且泛着阵阵异味,但朱乃魁却毫不犹豫,一手接过,就着石室内微弱的灯光仔细翻阅,册页距离他的鼻尖很近,由任非站立的角度望去,就好象姓朱的正捧着册页在不停嗅闻似的。
突然间,朱乃魁脸色变了,兽嗥般从喉底哮吼:“老不死的,册页里怎么只载了两招的图说及口诀?第三招呢?你分明撕下一页隐藏起来,打算只拿这本残缺不全的东西搪塞于我,我操你个亲娘,你给我玩这种卑劣把戏,以为我就治不了你?”
任非不慌不忙的道:“你急什么?册页里明明缺了第三张,我要想骗你,岂会如此大大方方的叫你检视?这第三张也在我这里,还没有拿给你呢……”
朱乃魁怒道:“这个老王八蛋,你在搞什么鬼?我可是于干脆脆,决不拖泥带水,你这么半隐半露,莫非是存心留一手吊我的胃口?”
任非的表情诚恳,语气平和:“我没有这个意思,朱乃魁,谈交易,做买卖,原就该遵诺守信,无诈无欺,你履行了你的条件,我当然也不会违背我的承诺,册页的第三张,我一定给你,只不过,呢,还有桩小小的要求,得请你周全……─”朱乃魁势成骑虎,恨得牙痒痒的:“老不死,你若待节外生枝,借故耍赖,我断断不会轻饶了你,你说,还有什么要求?”
任非道:“很简单,朱乃魁,在你仅为举手之劳,雍狷的兵器,包括他的双环砍刀,长弓大箭,尚烦你一并赐交……”
稍一考虑,朱乃魁爽快的道:“好,你们等着,我这就去拿,但是,可不能再出别的花样,只要另加一端,咱们的交易就算拉倒:还有郎五哥的下落,姓雍的也不能打马虎眼:“任非点头道:“一句话,就这么决定!”
朱乃魁一阵风似的卷了出去,关门下锁,动作连贯,而访佛仅是眨眼的功夫,他人已转了回来,好家伙,两手所提,可不正是的雍狷的双环砍刀,长弓大箭?姓朱的果然挺罩得住!
任非二话不说,伸手入鞋,又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羊皮页张来,异味隐隐中,他赶紧递交给朱乃魁,朱乃魁迅速接过,就着灯光重新检视。
雍狷慢慢背起他的箭囊,将刀鞘掖进腰板带里,在抄扎之间,依旧觉得四肢乏力,提劲不易,尤其伤处抽痛有如火灸─一虽然已经过任非的包扎,但不曾上药,只是止了血而已,创口却仍是一样的创口,未有半分愈合。
任非讨好的道:“怎么样,没有错吧?”
“昭”了─声,朱乃魁道:“应该没有错,老不死,难道你认为会有错么?”
任非干笑道:“不要开玩笑,这可是武林异人‘大痴子’的真迹手本朱乃魁似笑非笑的道:“好,我们之间的交易已经圆满完成,往后去,就全靠你们自己了,室门会照样关上,但守卫我可撤走,如何出困,二他就多琢磨吧。”
任非拱手道:“多谢成全。”
朱乃魁不再多言,却未忘趋前向雍狷问明了郎五的留置处,然后转身离去,关门上锁,步履声极快便已消匿。
靠墙坐着不动,雍狷沉沉开口:“任者大,你有没有感觉到不对劲?”
任非一楞,道:“不对劲,什么地方不对劲?”
雍狷思付着道:“一时我也说不上来,只不过朱乃魁的神色好橡透着几分诡异,直觉里,这家伙似乎在进行某项阴谋一……”
任慎重的道:“老实说,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姓朱的是块恶胚,歪点子说起就起,我们不得不防,我看,还是先出去为上策,老弟台,你的身子挺得住么?”
雍狷道:“勉强还行……”
任非上前,扶着雍狷缓缓站起,却不免忧形于色:“你看起来相当虚软,要不要再歇息一会?”
摇摇头,雍狷沙着嗓门道:“不用,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任老大,我们且闯上一闯试试:“任非低声道:“屋子是石砌的,门是铁铸的,朱乃魁那王八蛋在门外加了锁,老弟台。我们却如何出困?”
雍狷道:“等我过去看看。”
挣开任非搀扶,他独自蹭蹬到铁门之前,伸手一试,铁门果已下锁,推撑过去,纹丝不动。
任非也来到一边,跟着推推门沿,不禁叹了口气:“这朱乃魁麻子不叫麻子,简直就是坑人,他把门下了锁,照样等于瓮中捉鳖,我们半步也走不出去,任凭他赔上几颗解药,对我们来说还不是白格?”
雍狷镇定的道:“稍安毋躁,任老大,让我们慢慢想法子,姓朱的拿出解药,实则帮忙不少,首先,我的性命得救,其次,束缚尽去。兵器在握,亦有利我们出困,这不叫百搭,但看我们的造化与手段了!”
任非苦着脸道:“当时就应该再加上一条,不准他关门下锁!”
雍狷道:“他不会肯的,这样做,岂不是摆明了他在徇私放水?朱乃魁固然贪心,可是更懂得如何保护他自己……”
干涩的咽了口唾沫,任非道:“如今姓朱的把守卫也撤走了,我们现下的处境,真合了那两句话─一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雍狷没有吭声,只管用手在铁门四周轻轻摸索,当他摸到门例螺栓的部位,将手缩回来时候,指尖上沾满了如屑的铁锈。
望着手指褐黑斑斑的锈痕,他的精神立时一振,双瞳中亦透出了光亮:“大概有法子了,任老大,这铁门的螺栓锈蚀的很厉害,弄断它或许不难!”
任非不大起劲的道:“问题是拿什么把螺栓弄断?单凭我们两个的四只肉掌?”
雍狷慢慢抽出掖在腰板带间的双环大砍刀,淡淡的道:“我这口刀,乃是百炼精钢所铸造,几乎接近断金切玉,无坚不摧的地步,用这口刀来斩砍螺栓,你看台宜不合宜?”
拍了拍自己脑瓜,任非失笑道:“合宜、合宜,太合宜了,他娘,人的岁数一大,有时就免不了胡涂,我居然不记得你腰上还掖了这么一把利器啦……”
雍狷不再多话,他抽出大砍刀,觑准螺栓突出门框的位置,双手握刀;猛力斩去,但见寒芒暴闪,“克啷”一声,上头的一只已经应声断落,刀光再映,下端的另一只螺栓亦折为两半,任非适时抢前,两手扯紧螺帽外缘,使劲往反方向拉开;哈,“吱”“吱”几声轧响,铁门竟被扯开了尺许宽的一道空隙,刚好可容一个人侧身挤过。
略退一步,雍狷微笑道:“任老大,你先请。”
任非也顾不得客气,身子一偏,人已到了门外,雍狷跟着出来,才发觉铁门之外原是一条甬道,囚人的石室,便是在原来的大库房内特为加盖隔出来的;甭道尽头,又是一门,却只是一扇木门了。
招呼一声,任非领先而行,来到木门旁边,他试着用手去推,那扇木门居然没有加锁下栓,任非一推之下,便无声无息的应势启开。
走出这道木门,就算离开库房了,外面,正是大白天,寂静的大白天,空气中,有清新的松香味隐隐传来,旷野辽阔,轻风舒徐,快意的自由,仿佛已在向他们喊了!任非洒开大步走出门外;迎春蓝天白云,先长长伸了个懒腰,又活动了一下四肢,忍不住眉开眼笑的冲着身后随至的雍狷道:“操他个二舅子,我被关进那鬼地方,少说也有十来天了,这十来天里,真正是不见天日、吃尽苦头,嘿嘿,不想我亦有脱困的日子!”
雍狷淡淡的道:“人都是这样,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而人就是人原不该受拘禁的。”
任非挺挺胸膛,道:“走,老弟台,我们赶紧离开此地,待久了,别又着了那些王八蛋的道!”
─边挪动脚步,雍狷边问:“去哪里?”
任非低声道:“先找个地方歇腿,你身上的伤也要请个郎中仔细诊治诊治,我知道有个小镇甸,离此不远,就走路去,半个时辰足够了……”
雍狷稍稍迟疑的道:“但是,我要领回我的孩子……”
拍拍他肩膀,任非道:“我明白你的想法,也体会得到你的心情,老弟台,儿子一定要找回来,不过,你现在的身子状况却该先行料理妥当,万一伤口炎肿溃烂,麻烦就大了,等你调养键愈之后,不是─样可以来找儿子么?”
想想也是,雍狷颔首道:“也好,任老大,我们且去看看,我的坐骑还在不在原处?”
任非欢然道:“是了,我差点忘记你尚有一匹又骠又骏的高头大马,有马骑,到底比劳动两条人腿受用!”
于是,两人相偕寻到半里外隐蔽“乘黄”的所在,好马就是好马,灵驹便是灵驹,“乘黄”果然仍旧安详自若的待在原处,见到雍狷,连连发出几声低嘶,还直拿马头朝主人胸前磨擦呢。
任非笑道:“好马,伯值不少银子吧?”
解开拴在软枝上的缰绳,雍狷面无表情的道:“没有卖过,所以不知道价钱。”
任非打着哈哈道:“我他娘是习惯成自然了,看到什么好东西,就直觉的想到价钱上,老弟台,你可莫见怪呀!”
雍涓吃力的登上马,边道:“你也上来吧,任老大。”
任非爬上马背,紧靠在雍狷身后坐稳,他一手抓住鞍沿,一面道:“那片小镇甸,就在这附近,大约只有十来里路,出了这片黑松林,顺着来路去,前面有条叉道,往左拐,一直走就到了……”
雍狷策马前行,任非又好心好意的叮吁:“慢点走,老弟台,你身有伤,可经不得颠簸。”
马儿的步伐不快,用小碎步慢跑,马上的人却不知道,如此一来,竞给了埋伏在黑松林的一于杀手莫大便宜……
那干杀手约莫有十余名,为首者,正是那眼露凶光,满脸狰狞之色的朱乃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