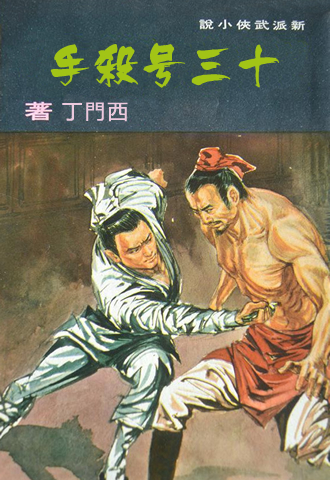金蜈神君厉啸的功力如何,曾希自然是再清楚也没有的了。
她一见双掌击中,心知普天之下,能够当得起他双掌全力一击的人,当真还寥寥可数,只怕连天一堡主凃龙,都不在其内,那么,自己这一方面,当然已可以大获全胜了。
是以,她一昂首,“桀桀”一声,怪笑了起来。
可是,她笑声才发,却听得厉啸突然发出一下异样之极的闷哼声来,曾希猛地一惊,已见厉啸的双掌,还未曾收回,身子便已腾地向后,退出了一大步。
在他退出了一大步的刹那间,他的脸色,已迅速地由白而红,由红而白,连续三次。
这时在场的,全是武林高手,人人都可以看出,那是厉啸已然受了极其深重的内伤,才会这样的。
而黑风仙后曾希,心中的吃惊,更是难以形容,她也不多去问厉啸究竟伤成怎样,手腕倏地翻起,六枚毒蒺藜,已然射出。
那六枚毒蒺藜的去势极快,“嗤嗤”连声,向前射出,“啪啪啪啪”六下响,一齐射在嫦娥的身上,可是嫦娥伸手一拂,却将之拂落,一面又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来,道:“唐豪在哪里?你抓住的是唐豪么?”
她问了两句,厉啸已然是口中鲜血,汩汩地涌了出来。
这时候,曾希再看到嫦娥向前逼来的势子也不快,她一向后避去,嫦娥也如旋风也似,向前卷了过来,道:“你可不准抓住我的唐豪。”
在嫦娥向前逼来之际,曾希只觉得一股大力,迎面压到,几乎连气也喘不过来,而且,这时她的丈夫,也已身受重伤,她可以说一点斗志也没有了。
虽然她追踪二十年,为了报杀子之仇,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唐豪,实在是不肯放手的。
但是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她却实在非放手不可了。她心中又惊又怒,一面真气暗提,一面厉声道:“你的唐豪在这里。”
她一个“里”字才出口,手臂一挥,已将唐豪挥得直向嫦娥跌了过去。
唐豪本已受了重伤,生死由人,而曾希在将他挥出之际,扣住他脉门的五指,又疾一运力,更令他伤上加伤,一面向嫦娥跌去,一面口中鲜血,又自狂喷。
而曾希一拋出了唐豪,使已带着厉啸,身形向上,疾拔了起来,一翻而越过围墙,口中则叫道:“凃堡主,阁下相助之情,实不敢忘。”
要知道她这时,只求全身而退,却是不敢再得罪天一堡中人的。
神刀双虎等人向凃龙望了一眼,凃龙一扬手,示意放他们两人离去,不必追赶。
众人仍然不动,一起向嫦娥看去,只见她扶住了一碰就跌的唐豪,泪水迸流,又在痛哭着,甘德霖低声道:“大哥,这妇人……”
凃龙扬手,道:“我们别出声,静悄悄越出围墙去再说。”
神刀双虎道:“堡主,这也不是办法。”
凃龙苦笑道:“你们刚才没有看到么?她的武功,如此之高,谁是她的敌手?她只怕要哭上些时,唐豪多半也活不成,我们先在花园围墙之外,多派人守着,她有什么动静时,再作打算。”
众人都点头称是,一个个相继跃过了围墙,最后,才是凃龙带着凃雪红,跃了出来。
直到出了围墙,凃雪红惊定思惊,才“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凃龙忙道:“红儿,现在已没有事了,还哭什么?”
凃雪红一面哭,一面道:“爹!你连一个疯妇人也敌不过,我以后在江湖行走,若是说自己是天一堡主之女,连我自己也觉得面目无光。”
凃龙神色尴尬,道:“别胡说,这疯妇人……我是不愿和她真正动手。”
凃雪红“哼”地一声,但是她却不再说下去,一拧身,道:“爹!那么林浩生和玉琴这两个人呢?我可还得带人去追他们。”
凃龙长叹一声,道:“红儿,你听我的话,别再去理会他们了,他们既然已离开了天一堡,那就让他们去吧!今晚若不是你定要去追他们,只怕也不会惹出那么多的事情来。”
凃龙一面讲,凃雪红的脸色就一路变。
凃雪红本来容颜俏丽,看来十分动人,可是这时候,她面色铁青,目射凶光,却给人十分可怖之感。
一等她父亲说完,她就尖声叫了起来,顿着足,道:“不能!不能!我一定要立时去追他们,一定要将他们追了回来。”
凃龙在武林之中,是顶天立地,一等一的高手,可是在这个他从小就娇纵惯了的女儿面前,他却也摆不出高手的威严来。
他略呆了一呆,眼眉紧蹙,道:“堡中乱成一片,又要派人守着那院子,还是——”
不等凃龙讲完话,凃雪红便一跺足,道:“好,没有人跟我去,我自己去。”
她一面说,一面已向外走了开去,凃龙急叫道:“红儿,你再胡闹!若不是你胡闹,怎会将血掌唐豪这样的人,引进了堡中来?”
凃雪红大窘,道:“你在做梦哩!林浩生和玉琴两人,就躲在血掌唐豪挖成的地道之中,唐豪是他们两人引进来的。”
凃龙面色一沉,道:“雪红,你越来越没规矩了,这是对我在说话么?”
凃雪红噘起了小嘴,道:“那怪得我么?谁叫你不分青红皂白,就硬派人的不是。”
凃龙对这个女儿,实在也有无法可施之感,他只得又长叹一声,道:“红儿,浩生好歹是你的表哥——”
可是,他的话还未曾讲完,凃雪红却又尖叫了起来,道:“不是!我可没有这样的一门亲戚,他算是什么,嘿!我和他可是什么关系也拉扯不上。”
对于凃雪红的任性,凃龙心中也不禁发怒,他面色一沉,道:“好,那我问你,若是找回了他们两人,你准备怎样?”
凃雪红咬牙切齿,道:“我……我要将他们……将他们一齐……”
凃雪红的话还未曾讲完,可是凃龙已然急道:“别说了。”
他一声喝断了女儿的话,可是他的心头,却仍然不免犹有余悸,凃雪红的母亲死得早,为了照料这个女儿,他多少年来,未曾离开过天一堡,女儿的任性,和有什么人违了她的意思之后残酷的报复,凃龙怎有不知之理?而这次,林浩生和玉琴一起逃走,凃龙更知道女儿的心中恨到了极点,他实在不愿意听女儿口中讲出如何折磨他们两人的方法来。
而凃雪红却残忍地笑了起来,道:“爹!你放心,只要抓到了他们,我一定有办法出气的。”
凃龙慢慢地向女儿走过去,道:“红儿,你不是从小就十分喜欢浩生么?或者我们找到了他,待我去劝劝他,那么也许——”
凃雪红用力地咬着下唇,她的面色,又变成了惨白,而她的双眼之中,却是泪花乱转,只不过她竭力忍着,才使泪水不致于落下来。
半晌,她才道:“多丢人,爹,别再丢人了。”
凃龙一呆,道:“这是什么话,那有什么丢人?”
凃雪红并不回答,却陡地转过身去,凃龙伸手向她的肩头搭去,想将她的身子扳回来。
但是,他却太知道自己女儿的脾气了,是以他手还未曾碰到凃雪红,便缩了回来,只是道:“又怎么了?”
凃雪红缓缓地吸了一口气,道:“我,我已经对他说过了。”
凃龙一怔,心中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女儿,已对林浩生表示过爱意了。
他呆了一呆,道:“浩生这浑小子怎么说?”
凃雪红的声音,变得十分冷酷,倒像是她在讲的是人家的事情,与她无关一样。
她道:“他怎么说?他说,他绝不想在天一堡中,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他总是要出去另闯天地的,他绝不要人家以为他只有靠了天一堡,才能活下去。”
凃龙紧皱双眉,他听得女儿转述林浩生的话,心中自然不能没有怒意,但是他也终究是武林大豪,听到了这样的话,心中也有几分豪意顿生之感,脱口道:“好小子,居然有些志气。”
凃雪红尖声道:“是的,他有志气,哼!他既不想靠天一堡,他既不要我,我……我就叫他立即就滚,别再赖在天一堡中。”
凃龙吃了一惊,道:“你赶他走?”
凃雪红刷地转过身来,道:“怎么?人家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不要靠天一堡了,咱们反得低声下气地来求他么?莫非天一堡还要靠他?”
凃龙顿足道:“话不是这样说,你一直很喜欢他,这样做不是……唉?不是太……”
凃雪红冷傲地一笑,道:“这样做太好了,本来,我还不知道是这样狼心狗肺的畜牲,还是当他是男儿志在四方,现在,他将玉琴拐跑了,他将我的丫头拐跑了,爹!你说我能放过他么?你说,你说,我可能放过他么?”
凃雪红讲到后来,声音尖利之极,一面泪珠迸流,显见她的心中,实在是气苦之极,难过之极。
凃龙看了这等情形,也不禁心如刀割,大声道:“对,这小子太可恶了。”
凃雪红渐渐止住了哭声,道:“爹,那么,你就让我带人去将他们两人抓回来,我知道他们还在地道中,就算他们已出了地道,林浩生受了伤,也定然走不得很远的。”
凃龙一惊道:“林浩生已受了伤?”
凃雪红道:“是的,他自以为走得很秘密,事实上,他一走,我就知道了,我追了出去,自然和他动手。”
凃龙迟疑地望着凃雪红,道:“可是……可是你什么时候,武功高过了他了?”
凃雪红道:“他——”
她讲了一个字,突然顿了一顿,道:“他本来是可以胜得我的,但是他只顾护住玉琴这贱人,所以才落了下风,被我打伤了。若不是当时雪大,风大,又有血掌唐豪帮他,他定然走不脱的。”
凃龙心中,将信将疑,道:“原来如此,那么,由甘二叔陪你去可好?”
凃雪红大喜,道:“那再好也不过了,二叔,二叔。”
甘德霖这时,刚向外走出,转过了墙角,一听得凃雪红叫唤,连忙转过身来,道:“雪红,什么事?”
凃雪红奔过去,道:“二叔,爹和我央你去陪我找两个人,你可肯么?”
她十分乖巧,心知甘德霖是武林高人,绝不是自己所能颐指气使的,是以她不说“爹命你陪我去找两个人”,却说是央请甘德霖帮忙。
甘德霖笑道:“那自然可以。”
凃雪红一跃而起,发出了一声长啸,道:“走,快备雪橇。”
甘德霖又道:“去找哪两个人,可还是浩生么?”
凃雪红咬着唇,点头道:“是的。”
甘德霖叹了一声,道:“雪红,我在天一堡中的日子虽然不久,但是浩生却不是坏人,雪红,就算找到了他们,你也别太为已甚了。”
凃雪红的心中大怒,但是她却一点也不显露出来,道:“二叔,你还未曾帮我找到那两人,倒反帮着他们,讲起话来了。”
甘德霖笑了一下,转过头来,道:“大哥,这院子内的妇人——”
凃龙叹了一声,道:“我会小心防范的,二弟,你可得小心照看着雪红啊!”
甘德霖笑了起来,道:“大哥只管放心,雪红就跟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这时,獒犬的吠声,已传了过来,又有人奔了过来,道:“雪橇已准备好了。”
甘德霖和凃雪红两人,一齐向外走去,出了堡大门,十六条獒犬,拉着一副雪橇,已在门外相候,两人登上了雪橇,凃雪红拿起了长鞭,“叭”地一声,挥了下去,十六条獒犬,一起急吠了起来,向前飞奔而出,雪橇的去势极快,迎面而来的寒风,劲疾无匹,简直就如同千百柄利刃一样,连甘德霖这样的高手,也觉得难以再讲得出话来了。
其时,天色已然渐渐放亮了。
大雪之后的天明,是十分奇妙的,光亮不像是从天上射下,而像是从地上冒起来的一样,刹那之间,整个大地,便像会发光一样地亮了起来,等到第一丝阳光,自天际射下之际,大地像是一大盆硕大无朋的炭火一样,燃起一阵熊熊的大火。
但是那种火光,却只是一种极其微弱的温煦,再接着,太阳浮了起来,光芒跟着上升,直到灿烂得连眼也睁不开来。
天色大明了。
在天色渐渐明亮,雪橇向前飞掠而出,溅得积雪激漩而起之际,在雪地上,却还有两个人,在缓缓地向前移动着。
他们移动得如此之缓慢,以致乍看来,他们几乎是静止不动的一样。
实际上,他们却是艰难地在向前走动着的,那是一男一女两人,男的身上,只披着一件羊皮袄,那件羊皮袄像是被什么利刃划破过的,而且,上面还全是血迹。
那女的披着头发,由于那男的身子,几乎全倒在她的身上,她是吃力地扶着那男的一起行走之故,是以她的头低着,以致一头乌云也似的长发,将她的脸也盖住了,看不清她的脸面。
他们两人在雪地中慢慢地挣扎着,终于,她的脚一软,两人一齐滚跌在积雪上。那女的连忙又站了起来,伸手去拉男的。
那男的年纪还十分轻,大约二十三四岁左右,他十分瘦削,苍白,从他紧抿着的嘴上,可以看出他正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然而,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的硬汉,不论怎样痛苦,他都不会叫出声来的。
那女的连拉了他两下,都未能将他拉得起来,这时,她已掠开了长发,她的脸色,也同样苍白,而且此际她正在哭着。
但是,这一切却都无损这个少女的美丽。
那真是一个绝顶美丽的少女,如果她不是哭,而是微笑地站在雪地上的话,那么遇到她的人,一定会以为她是仙女,而不是尘世中的美女。
她的美丽,是那样的柔和、纤巧,使得人家对她,都容易自然而然地起一种怜惜之感。
她,就是天一堡堡主唯一的爱女,凃雪红的丫头玉琴,而不消说,那男的就是堡主的外甥林浩生了。
他们两人在地道中,当血掌唐豪忽然不再要胁他们,而自顾自离开之后,他们简直像是在做梦一样,他们仍在地道中呆了许久,这才想起,现在是自己逃出去的机会。
他们又在地道中爬行着,林浩生身受重伤,几乎是玉琴托着他爬行了。
而当他们爬到了地道的入口处时,又发现那所茅屋早已倾坍了,玉琴又用尽力量,才和林浩生两人,一齐钻了出来。
玉琴的武功,乃是林浩生抽空教的,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根基。
但是,她在筋疲力尽之后,却还要拖着林浩生在雪地上逃命。
他们绝不能就在雪地上停着不动,就算凃雪红不再带人追来,他们也会冻死、饿死在一望无际,积着厚雪的平原之上的。
玉琴知道,他们要活下去,就得一直向前走,走,一直走到有人能庇护他们,能救他们为止。
然而,这时候,玉琴虽然仍紧紧地握着林浩生的手,可是,她却一点力道也使不出来的,她一面哭着,一面又跌倒在雪地上。
林浩生在雪中挣扎着,他整个人都几乎陷进了雪中,他的身上,有许多被软鞭抽得皮开肉绽的伤痕,本来是热辣辣地发痛的,这时被雪一浸,精神反倒一振,他挣扎着弯起身子来,手发着抖,拨开了玉琴额上披下的长发,轻轻地抹着她的眼泪。
他的声音,坚毅而低沉,他道:“别哭,玉琴,你什么都听我话的,是么?别哭。”
玉琴仍然在抽噎着,道:“浩生哥,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林浩生勉力使自己的声音,听来不致断断续续,他道:“你别哭,玉琴,你别哭,只要你肯听我的话,就一定……有办法的。”
玉琴渐渐止住了哭声,道:“浩生哥,你想,你的话,我怎会不听?”
林浩生紧紧地握住了玉琴的手,道:“那么,这一句话,你是一定要听的。”
玉琴觉出林浩生的声音,已显得十分异样,在她而言,听林浩生的话,那乃是绝无疑问的事情,是以她连连点头,道:“你要我做什么,只管说好了。”
林浩生喘着气,道:“你若肯听我的话,那就……好了。玉琴……你……一个人快走吧!你……别理会我,一个人快走吧!”
玉琴本来,虽然已止住了哭声,但是还仍然在不住地抽噎着的。可是此际,她一听得林浩生这样讲,整个人都不禁呆住了。
过了好半晌,才听得玉琴颤声道:“你……你说什么?浩生哥,你说什么?”
林浩生叹了一声,松开了玉琴的手,道:“你刚才讲过,说是要听我话的,你快走,一个人往南走,到关里去,再也别回来,那么,你还可以走得脱,如果你一定要拖着我,那么……只是害了你自己。”
玉琴这时候,却不再哭了,她非但不再哭,而且,动作也镇定了不少,只见她抹了抹眼泪,将长发束到了头后,道:“浩生哥,你是说,我们两人,定然逃不出去的了,是不是?”
林浩生急道:“我没有这样讲过,我是说,如果你先走,我会设法跟上来的。”
玉琴凄然笑了起来,道:“你在骗我,你说过绝不骗我的,何以你骗我?”
林浩生挣扎着,像是想站了起来,但是,他的身子只是略挣了一挣,反倒又全跌在雪地之中了。
玉琴望了他片刻,一声不出,在他的身边,躺了下来。
林浩生发出了十分干涩的声音,道:“玉琴,你这是做什么?”
玉琴缓缓地道:“我们如果可以逃得出,那就一起逃出去,如果不能,那我们就一起死。”
林浩生叹着气,道:“这是……何苦。”
玉琴仍是缓缓地道:“你不知道,浩生哥,我自从懂事起,就从来没有人对我好过,每一个人都是粗声粗气地对我讲话,最粗重肮脏的事,轮到我来做,任何人都可以出手打我、骂我,你大概想不到,在我十岁的那年,我就曾想到过死吧?”
林浩生并没有回答,他脸上的肌肉,却在可怕地抽搐着。
“那一天晚上,我在井边立了很久,想着,如果我跳了下去,那会怎样?我当然会死,但是死了之后,又怎样呢?我也见过死人,死人不会被人骂,也不会被人打,只是躺着,我在想,做死人有什么不好呢?”
林浩生断断续续地道:“别……说了,玉琴,你……别说了。”
玉琴摇了摇头,道:“我要说,因为你想赶我走,我说了,你就不会赶我走了,你就会明白,我绝不是怕死的人。”
林浩生的喉间,发出奇怪的“咯咯”声来,他张大了口,可是他还未曾讲话,鲜血却已顺着他的口角,汩汩流了下来。
玉琴连忙坐起身,用自己的袖角,轻轻地去拭擦林浩生口中淌出的鲜血,她的脸色苍白,但是她的脸上神情,却是出奇地平和。
她低声道:“浩生哥,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尚且想死,现在我可以和你死在一起,我尚有何求?”
林浩生勉力挣扎着,终于又讲出了一句话来,道:“可是……可是你年纪还如此之轻。”
玉琴凄然笑道:“你难道是老头子么?浩生哥,自从你来了之后,我过的日子再苦,可是我夜间一想到你,我就觉得心中甜丝丝地,你对我实在太好了。”
她的脸上竟出现了一丝红晕,她将头枕在林浩生的胸前,在天一堡时,当他们趁人不觉时相偎相依之际,她也时时这样子的。
但那时候,她将头枕在林浩生的胸膛上,将耳朵贴住了林浩生的胸膛,就可以听到林浩生心跳的声音,然而现在,她一样将耳朵贴在林浩生的胸口,她却几乎听不到有心跳的声音。
她的眼泪,又一串串地落了下来,林浩生吃力地将手扬起来,放在她的脸颊上。
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了獒犬的吠叫声。
在獒犬声才一传入他们耳中之际,他们两人的身子却曾经震动了一下。
但是他们就只不过是那样轻轻地震动了一下,以后,他们便伏着不动。
獒犬的吠叫声,迅速地自远而近,传了过来。
渐渐地,玉琴已可以看到一个小黑点,紧接着,小黑点迅速扩大,除了獒犬的吠叫声之外,还可以听到长鞭的“啪啪”声。
再接着,雪橇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玉琴也看出,雪橇上两个人,一个是小姐凃雪红。
等到她看清楚了雪橇上的一个人是凃雪红时,她便闭上了眼睛,不再向前看去。
雪橇将积雪划得飞溅而起,飞溅而起的雪花,又盖得玉琴和林浩生两人,一头一脸,可是他们两人,还是一动也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