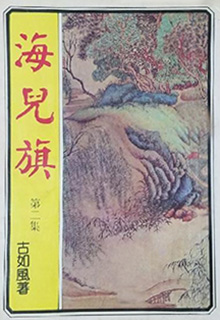那两人仍是呆呆地站着,过了半晌,一个才道:“四师弟我们怎么办?”
那一个道:“二师哥,我看……我看……只要过得一个时辰后,我们便可以再追上去了。”
一个苦笑道:“就算我们再追上他,他仍然挟持着那位凃姑娘,那我们岂不是一样不能下手,这……怎生回山去复命?”
那一个叹了一声,忽然面有喜色,道:“那倒不打紧,他……从来也不对任何女子有长性,他过了几日,定然会离开凃姑娘的。”
一个更是苦笑不已,道:“就算他离开了凃姑娘,难道不会又找第二个少女么?这事情,这事情……”
两人愁眉不展,心中实是为难之极,就在这时,他们突然听得有一个十分尖锐的女子声音,自远而近,传了过来。
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听得一个女子在尖叫,由于隔得太远,还听不到她在叫些什么。
但是,呼叫声迅速地自远而近,他们立时听出,那女子在不断地叫道:“二师哥,四师哥。”
他们两人大吃了一惊,失声道:“是小师妹。”
他们在叫了一声之后,却又异口同声地道:“不会的,小师妹怎会来到这里?师父师娘怎肯放她出来?”
可是,就在这一句话间,叫声却已近了不少,转眼之间,只见一条血也似红的人影,倏地穿进了林子来,在两人的面前停下,乃是一个披着大红披风的女子。
那女子至多也不过十七八岁年纪,披风领上的一圈银缎毛,衬着她一张瘦削的瓜子脸,再加上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极之秀丽。
然而,在她的眼睛中,却又有着极度的幽怨。
那两个年轻人一看到了她,手足无措,像是不知怎样才好。
只是不住地道:“玲师妹,你怎么来了,师父可知道么?”
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那两个年轻人的师妹,也是武林怪杰,席大先生的唯一爱女,单名一个玲字,这时,她摇了摇头,道:“爹不知道。”
那两人急得直顿足,道:“那么,师娘呢?她老人家总该知道的了?”
席玲缓缓地摇着头,她双眼之中,泪花乱转,但是她却又显然不欲给她两位师兄看到她的流泪,是以她抬高了头,道:“妈也不知道。”
两人更是急得双手乱摇,道:“师妹,这怎么可以,你一个人在江湖上,唉!峨嵋到这里,万里迢迢,你一个人,这怎么可以?”
席玲凄然笑着,道:“两位师哥,我还怕什么?你们说,我还怕什么?”
她在讲到最后一句“我还怕什么”之际,声音发颤,闻者心酸,那两人眼睛已不由自主润湿起来,齐声叫道:“玲师妹。”
看他们的神情,分明是想讲两句劝一劝席玲的,但是他们又实在不知讲什么才好,是以只是叫了一声,便没有了下文。
三人全不出声,过了半晌,还是席玲先开口,席玲显是已将心中的悲痛,尽量抑制了下去,她道:“我将我的衣服,留在后崖峭壁边上,装着我是堕崖而死,偷偷走下山来的。”
那两人道:“师妹,你这样做,师父和师娘两人,不是要伤心欲绝了么?”
席玲又凄然道:“我当然也想到这一点了,但是我想他们已经够伤心的了,就算知道我死了,大约也不过如此了吧?尤其是爹,他一世英名,武林中人提起了他,谁不敬畏三分——”
席玲讲到这里,实在没有法子再讲下去。
而那两人的心头,也像是堵了块数百斤重的大石一样,说不出来的闷郁,说不出来的难过。
席大先生的武功何等之高,身份何等之尊,声名何等之显赫,可称是近百年以来,武林中的第一奇人,但是,他却瞎了眼,收了这样一个徒弟,累了自己唯一的爱女,这件事,对席大先生的打击之大,实在是可想而知,作为席大先生的徒弟,当然更可以深切地感觉得到,这叫他们怎能不难过?
两人齐声长叹,席玲苦笑了几下,道:“我一路追下来,总算也得了一点线索,知道他一些事,我知道他在天一堡中。”
那两人一呆,点了点头。
席玲又道:“我又知道,血猿神君也在找他。”
那两人又点了点头。
席玲再道:“可是,我刚从天一堡来,天一堡中,血猿神君和一个疯妇人,正在打得天昏地暗,是易老怪告诉我,他向北来了,二师哥、四师哥,你们两人,可有见到他么?”
那两人听得席玲这样问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
席玲在问他们,可有见到雷三,事实上,他们不但见到了雷三,而且,雷三可以说是他们两人放走的。
如今席玲这样问他们,却叫他们如何回答才好?
他们两人,面面相觑,讲不出话来,席玲心中生疑,道:“两位师哥,你们可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么?”
两人连忙摇手道:“没有,没有。”
席玲叹了一声,道:“我早知你们不会的,我遭遇如此之惨,若是你们还会有什么事瞒着我的话,那怎么说得过去?”
席玲这样一说,那两人更是手足无措,一个支支吾吾道:“雷三他……他……刚才我们倒是遇到他了。”
席玲的身子,突然一震,道:“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拦住他?”
另一个苦笑道:“我们自然拦住了他,而且是准备将他擒回山的,可是他……他却抓住了一位凃姑娘,说是我们如果向他下手的话,那么他定然先打死了这位凃姑娘,是以我们……我们……”
席玲道:“是以你们便放走了他,是不?”
那两人惭愧地点了点头。
这时,他们的心中,全感到愧对席玲,但是,席玲却知道,如果他们再遇到一次那样的事,他们一定仍然会那样做的。
她苦笑着,道:“你们人太好了,他……实在太坏了,凃姑娘……”
一人道:“她是天一堡主的女儿。”
席玲沉声道:“你们不去追他,我去,就算我不能将他怎样,至少也救了凃姑娘。”
席玲这句话,将两人陡地惊醒。
两人刚才,只怕雷三下手打死了凃雪红,却是未曾想到,女孩儿家,落在雷三的手中,所受的淫辱,实是比死更甚。
是以他们两人直跳起来,道:“师妹说得是,我们快去追他。”
三人向着刚才雷三的去向,疾追下去。
可是,等到他们离开,约有半盏茶时分,只听得雷三“哈哈”一笑,就在附近的一株大树之上,抱着凃雪红,落了下来。
他落地之后,再是一笑,道:“凃姑娘,你看我行事计谋如何?你能认得我这样的人,也不枉你做人一世。”
原来他刚才,根本没有离去,只是悄悄地躲在附近的树上。
凃雪红刚才被他封住了穴道,出不得声,这时穴道已被他拍开,她立时用尽了气力,尖叫起来。
可是雷三却只是笑道:“小乖乖,你叫哑了喉咙,也不会有人听到的了。”
凃雪红停止了叫喊,道:“你,刚才那是你的师妹么?她如此美丽,你就和她结为夫妇,为什么不好?”
雷三贼忒嘻嘻,道:“比起你来,可差得远了。”
凃雪红心中不住地叫苦,她实是想不到,一夜之间,事情会起了那么大的变化,她用力地挣着,但是她被雷三制住了脉门,能使得出的力道,也少得可怜,而雷三却强扭着她的手臂,待向她的朱唇强亲过来。
凃雪红又尖叫起来,她这次,只叫了两声,眼看她的檀口,要被雷三封住了,突然之间,听得有人道:“好风流啊!”
这四个字,是在凃雪红的惊呼声中,传了出来的,声音听来十分平静,十分恬淡,但是,凃雪红的尖叫声,却一点也未能将之盖过去。
雷三一听,陡地一震,连忙回头看去。
只见在身后不远处,一个累雪甚厚的大树桩之上,站着一个人。
那人大约三十左右年纪,书生打扮,脸又瘦又长,在左颊边,有很长一个伤痕,使得他的脸,看来更是长了许多。
凃雪红一见有人,立时又叫了起来,道:“这位英雄,快快救一救我。”
那书生打扮的人,仍然站在那个树桩之上,他身上穿着一身雪也似白的长衣,又是站在累雪的树桩之上,是以乍一看来,就像是一株树上,长着一颗人头一样,看来十分怪异。
凃雪红一叫,雷三便厉声道:“你再叫,我便点了你的麻瘁穴。”
凃雪红自然知道若是被雷三点中了麻痒穴的话,那全身又麻又痒,比死还难过,而且她绝不怀疑雷三真的不会那样做,是以立时住口不言。
那白衣书生直到这时,才又再开口,道:“看阁下一表斯文,何以行径竟然如此不堪?”
雷三一见到那白衣书生,心中便迅速地在转着念,将武林各门各派的高手,全想了一想,可是他却也弄不明白那人的来历。
他在席大先生的门下多年,席大先生乃是武林之中第一怪杰,他门下弟子不但武功高,而一个个见识极广,雷三如今既然认不出那白衣书生的来历,心中暗忖,那多半是关外不知名的武林中人,是以他根本未曾将之放在心上,一声冷笑,道:“干你甚事?”
那白衣书生瘦长的脸上,现出十分惊讶的神色来,道:“咦?阁下不是学武之士么?”
雷三笑道:“废话,你看不出来么?”
白衣书生道:“那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正是学武之士的本分,阁下何以问我干甚事?”
雷三冷笑道:“原来你也是学武之士,那你倒露些武功我看看。”
那白衣书生身形一耸,慢慢地从树桩之上,跳了下来。他的动作十分慢,但是正因为他的动作慢,是以令得雷三陡地一惊。
那树桩只不过四五尺高,可是他向下跃来之际,却像是飘了下来一样。
雷三虽然穷凶极恶,但是见识终究是广的,一见这等情形,便立时知道自己刚才是料错了,这白衣书生决计不是等闲之辈。
是以他立时拉着凃雪红,后退了一步,全神以待。
可是,却不料那白衣书生自树桩上飘落下来之势,快疾之极,紧接着,他的动作,却快到出奇。
以雷三的武功而论,甚至未曾看到他的双足,是不是曾经点地,突然之间,一股劲风,挟着一条人影,已然迎面扑过来。
雷三大出意外,幸而他早已有了准备,左掌一翻,呼地一掌,向前拍出。
但是,他一掌拍出之后,只听得他掌风呼啸汹涌向前之声,那条人影,早已不见,紧接着,他右腕之上,却突然一麻。
原来,白衣书生向前扑来的势子,虽然劲疾之极,但是倏忽之间,他却已转到了雷三的右边,伸指向雷三的脉门便弹。
那一指,其实也并未弹中雷三的脉门。
但是,他一指弹出,指风嗤然,却已令得雷三的脉门一麻,五指不由自主一松。
而白衣书生的变招,当真快捷之极,雷三手才一松,白衣书生已一伸手,握住了凃雪红的手臂,顺手向外一挥,将凃雪红稳稳地送出了丈许间外。
雷三心中大怒,趁着白衣书生挥臂送出凃雪红之际,骈指如戟,点向对方的“华盖穴”。
那“华盖穴”在人身胸前,属于太阴肝经,乃是五脏之华盖,人身一等一的要穴。
雷三此际,一出手就攻对方的“华盖穴”,那是分明想置对方于死地了,身手之辣,竟是罕见。
白衣书生身形陡然地向后一缩,双肩一扬,道:“你是席大先生弟子?”
雷三在峨嵋胡作非为,等于是已被迫出门墙一样,但是在武林之中,“席大先生”四字,具有无上威力,雷三也深明这一点,是以有人一问他是不是席大先生弟子之际,他却是绝不否认的。
此际,他一声冷笑,道:“你既知我的来历,还不快夹着尾巴逃走?”
那白衣书生在问出了刚才的那句话后,一直凝视着雷三,他缓缓地道:“你真是席大先生的弟子?看你刚才这一招,掌法确是席大先生所传,但是席大先生门下,怎会有你这等无耻无法之徒。”
雷三并不在乎人家骂他,但令得他心头大怒的是,凃雪红在被那白衣书生挥开之后,已然没命也似,在向前奔了出去,眼看若是再被那白衣书生阻拦下去,就要追不上凃雪红了。
是以他厉声道:“让开!”
他刚才一击不中,此际急于求胜,“让开”两字才出口,一抖手,“铮”地一声响,只见在他的衣袖之中,射出了一柄短剑来。而当那短剑射出之际,他五指一紧,恰好抓住了剑柄,紧接着,就势向前送,短剑已然挑向对方的咽喉。
那白衣书生却又叹了一声,道:“你武功算是不错了。”他一面说着,一面又向后一退,雷三那一剑,疾逾闪电,可是仍被他从容避了开去。
雷三一剑又不中,再去看凃雪红时,凃雪红已然逃得只剩下一个小黑点了。
那白衣书生避开了一剑之后,伸手指着雷三,道:“你这人行动可疑,我看你多半是盗了席大先生的一招半式,在武林中招摇生非,坏席大先生名头的,我要将你带往峨嵋,听候席大先生发落。”
雷三一听得对方如此讲法,实是又惊又恐,而且,他连攻两下,却未能击中对方,也知对方的武功甚高,他这时索性不再进攻,只得冷冷地道:“好啊!看你有什么本领来带我走。”
那白衣书生在一退再退之后,离雷三已相当远,这时,身形飘飘,又向前欺来。雷三早已蓄定了势子准备以逸待劳。
只见白衣书生向前欺来之势,十分快疾,雷三心中暗暗欢喜,暗忖你来势却是越快越好,他身形微矮,在白衣书生来到了离他只有六七寸时,一扬剑,狠狠一剑,向前刺出。
却不料他一剑才出,眼前一花,对方身形,突然不见,紧接着,背后已有一股劲风,压了过来。
雷三的心中,陡地吃了一惊,别说他这时,半年前受的伤,伤势还未曾痊愈,就是他根本不曾带伤的话,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要预防,也不是易事。
百忙之中,他实是来不及转身应敌了,只得反手一剑,疾刺而出。
那一剑回手反刺,在百忙中使来,剑势也是十分凌厉的了,但是却已然慢了一步,他一剑再出,手腕便自一麻,脉门已被人扣住。
紧接着“呛啷”一声响,他那柄短剑,落到地上,只听得那白衣书生道:“哼!原来是喂了毒的,你哪里有正派中的半分风范。”
雷三的那柄短剑之上,的确是沾过毒的,而且所沾的乃是极厉害的毒药,见血封喉,但是在剑上而言,却只有极细心地观察,才可以看到剑身之上,有一丝极细的红线而已。
如今,短剑才一落地,对方便已指出剑上有毒,可知他目光锐利,非同小可,雷三更是惊上加惊。
他脉门被扣,已没有反抗的能力,但是他为人极其机灵,却是一点也不急,只是“哈哈”一笑,道:“阁下身手不错啊?不知是哪一派高手?”
白衣书生道:“家师和席大先生至交,其实,我刚才这一下身法,你也应该可以知道我是什么来历了。”
雷三的心中,陡地一楞,也更加吃惊,他立时想起,师父曾说过,他多年不见的好友之中,有一人最爱着白衣,可是其人性子却一点也不恬淡,相反性烈如火,嫉恶如仇,这人生得奇丑无比,天生是一个驼子,武林中人称之为烈火神驼。
神驼生得虽然不成人样,然而他却有一个美丽无比的妻子,他妻子武功平常,当神驼和她同行之际,每每遭来嘲笑。
而烈火神驼一听得嘲笑,必然无名火起,那嘲笑他的人,便算是遭了殃,后来还是几个正派的高手,联袂去求神驼夫人,要她劝一劝神驼,别再在江湖上行走了,神驼才归隐不出的。
烈火神驼有三大绝技,其中之一,号称“迷踪神步”,刚才那白衣书生一冲上来,自己一剑刺出,倏息之间,那白衣书生便到了自己的背后,步法如此之奇妙,那自然是“迷踪神步”功夫了。
雷三虽然力持镇定,可是一想及此,他却也不禁面上为之色变。
因为若是对方是烈火神驼门下,或是神驼的儿子的话,那么以神驼传说中的嫉恶如仇,出手绝不容情来看,自己可说绝难幸免了。
他心念电转,刹那间,已想了许多事,随即笑道:“我明白了,兄弟是烈火神驼门下。”
白衣书生叱道:“谁与你称兄道弟。”
雷三“嘻嘻”笑道:“那可怪不得我,若是阁下和烈火神驼有关,那么我们便非称兄道弟不可,谁叫烈火神驼和家师席大先生,是莫逆之交呢?”
那白衣书生正是烈火神驼的爱徒,这时听得雷三这样讲法,倒也颇难以反驳,他“哼”地一声,道:“你如此行为,没地玷污了令师的名头。”
雷三大笑了起来,道:“看来烈火神驼,正是名不虚传,我看兄台至多也不过沾了他一两分脾气吧?已是如此性如烈火,行事不分青红皂白了。”
那白衣书生虽然是烈火神驼之徒,但是实际上,他性子却没有一分似烈火神驼,不但不似,而且还截然相反,若是他像烈火神驼时,那早已一掌击下,将雷三打死了,如何还有这许多废话?
也正因为白衣书生的性子不像烈火神驼,是以他听得雷三这样说法,便讶然道:“你这样说,却是什么意思,我什么地方不对了?”
雷三笑着道:“你可知道这刚才给你救走了的女子,是什么人?”
这一问,令得那白衣书生突然一呆。
他当时只看到雷三抓住了凃雪红,要对凃雪红施轻薄,而凃雪红则在尖叫,至于凃雪红是什么人,他却是并不知道的。
这时雷三这样问他,他当然也答不上来,是以只得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但是你这样对付这位姑娘,却是大大不该。”
雷三听了,更是“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道:“什么姑娘,她是我老婆。”
那白衣书生大吃一惊,道:“你说什么?”
雷三一字一顿,道:“她是我妻子,是我老婆。”
白衣书生大有手足无措之状,连讲话也不顺溜起来,道:“她……她若是尊夫人,那么……何以尖叫?”
雷三笑道:“兄台定然尚未成婚,是也不是?”
白衣书生赧然点头,道:“未曾娶妻。”
雷三道:“这就是了,兄台尚未成亲,又怎知人家夫妻之间这么多事?她要我替她做一件事,我未曾答应她,她心中十分气恼,不肯和我亲热,若是你这冒失鬼不撞了来,早就没有事了。”
白衣书生摇头道:“不对,不对,我看到你们时,曾听那位……她说,要你娶你师妹的。”
雷三道:“是啊!拙荆的醋劲,一直是十分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