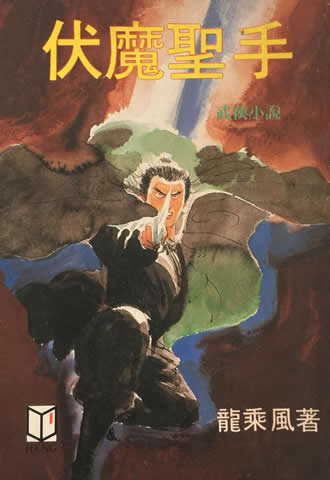三人一起抬头看时,只见前面一道老大的河,拦住了去路,河水因为下了半夜大雨,涨得极满,水色也极是浊混,水流更是湍急。
可是在河中心,却有一艘乌篷小船,船首站着一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艄公,手中持着一根长得出奇的船篙,正撑着船,向对岸而去。
在这样的大雨急流之中,普通船家,自然不会冒着覆船之险,撑船出来的,沈觉非来到河边,鼓动真气,大声道:“兀那艄公,请撑过船来!”
那艄公只是略抬了抬头,但谷守昆等三人,却听得“哈哈”一笑,从河中心,传了过来,正是那个艄公所发。
那一下笑声,清越无比,传到了三人的耳中,宛如发出笑声之人,就在眼则一样!
谷守昆等三人,一齐呆了一呆,只见那船在急流之中,虽然去势并不太快,但是没有多久,也已然在对岸靠了岸。
船一靠岸,尚依稀可见那艄公一跃上岸,接着从船舱中,也钻出一个人来。
虽然隔着一条大河,但是三人也一起可以看到,那人胁下,支着双拐,不是别人,正是阴风蛇叟司徒本本!只见那艄公,一等司徒本本上了岸,便将他挟在胁下,司徒本本似还挣扎了一下,那艄公却一伸手,将他两柄钢拐,夺了过来。
紧接着,便见那艄公向前,疾驰而出,等到他身形,几乎已然看不见时,还可以隐约听到有“哈哈”的笑声,自对岸传了过来!
谷守昆等三人,呆了半晌,俱不知道那趁机挟走了司徒本本的是什么人。
他们三人正在发怔间,又觉出有人,向河边驰来。三人回头看时,只见来人,正是太行双雄和绿发婆婆,看来他们三人,打了半夜,未分胜负。
绿发婆婆一到,便自尖声道:“追到了司徒本本没有?”
谷守昆冷笑一声,道:“司徒本本不知被哪一个武林中人,假扮一个艄公,渡到对岸去了!”太行双雄和绿发婆婆三人,一齐呆了一呆,太行双雄,各自一声'陆晡,便沿河驰了出去。,此际,雨势已然渐渐小了,绿发婆婆向董小梅狠狠地瞪了一眼,陡然之间,身形一提,拔起了两丈高下,在半空之中,一个转折,身形斜斜向河中心,掠了过去,在离岸三丈处,一点水花也未曾溅起,便已然没入了水中!沈觉非吃了一惊,道:“谷老前辈,这位婆婆的水性,如此之好么?”
谷守昆道:“自然,她住在苗疆第一大溪,弱水溪环绕的那一个孤岛上,若不是水流湍急,她根本不消潜水,便可渡过!”
讲到此处,谷守昆又叹了一口气,道:“如今,不论那柄折扇,是落在何人之手,只怕都没有夺回来的希望了。”
董小梅呆了半晌,无话可答,谷守昆望了她一眼,忽然道:“小梅,那柄小扇子,乃是精钢打就,扇骨的形状,也十分奇特,我得手近十年,几乎日夕想参悟上面的隐语,却一无所得。但那几句话,我却已然记得滚瓜烂熟了!”
董小梅一听,不由得喜道:“如此说来,就算有人得了折扇,岂非也无用处?”
谷守昆摇头道:“也不尽然,或则其人,天资颖悟,立即可以参透其中之意,而且,我深信这柄小扇,还另有用处。”
沈觉非道:“谷老前辈,你何妨将那小扇上的语句,说来一听?”
谷守昆抬首望天,只见乌云四散,青天复现,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我得此扇十年,没有一天安稳过,如今反倒觉得一身轻松,实是颇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我也无意再去争夺回来。小梅、沈公子,你们记着,那扇的一面,画着一幅山水,乃是三座笔也似直的高峰,云雾缭绕,积雪皑皑。在三个山峰之下,又有着一道清溪,溪旁怪石嶙峋,我自负走遍天下,但是却不知那是什么所在。另一面,乃是几句似诗非诗的话,道:‘三峰聚一顶,武汇天下寻,五花幵一峰,石尖留痕深,留待有缘人。’还有一行小字,道:‘天下武汇副册,号称《九原清笈》,有缘人得之,万万不可作恶,需防天谴。,”
沈觉非和董小梅两人听了,不由得莫名其妙,道:“那算是什么话?”谷守昆苦笑道:“我若是知道,早已得了《九原清发》在手了!”
沈觉非和董小梅两人,将那几句话,又默念了几遍,记在心中。谷守昆道:“我要告辞了。”董小梅还想说什么时,谷守昆早已走了开去。
沈觉非和董小梅两人,在河边又呆了半晌,董小梅忽然伸手向对岸一指,道:“沈公子,你看!”沈觉非抬头看去,只见绿发婆婆,已然身在对岸,向前面飞驰而出!
董小梅道:“沈公子,我们已然知道了扇上的话,大可不必再去追逐。”沈觉非道:“不错,小梅,我想到点苍去看看我的外公。”
…董小梅不假思索,道:“我和你一起去,顺便看看可有什么地方,有一道溪水,绕着三个山峰的!”沈觉非沉吟了半晌,才道:“也好,但是我们一路之上,却不要再多生是非!”
董小梅笑道:“当然不会。”太阳出来,他们各自拧干了衣服,向南而去,当晚,在一个小镇上宿了一宵,第二天又继续赶路。
他们两人,一直向南而去,一路上行来,已有六七天,倒也没有什么事发生。
只是他们看出,整个武林中人,都为巫山朝日峰上,将要举行邪派人物排名比武大会一事,而感到十分兴奋。流言四起,有的说,有几个隐藏了四五十年的高手,也要出手,有的又说正派中人,也要干预,离奇古怪,种种流言,不一而足。
他们也曾遇上了几个武当的第二代弟子,看他们的情形,像是急急赶路回武当去,武当、蛾嵋两派,和佛道两门高人,是否会插手,倒也是十分难说!
半个月后,他们两人,离点苍山,已然只有七八十里路程了。
当晚,他们宿在一个小镇上,只觉得一夜之间,车马之声不绝,不知多少人,连夜赶路,经过了那个小镇。
两人不欲生事,只是在窗内向外看去,黑夜之中,看到一大群人,男女老少都有,赶着车,向北而去,那些押车的男子,都像是武林高手,但因为天色黑暗,是以看不清他们的脸容。
其中有两个人,沈觉非觉得十分眼熟,但因为车行迅速,再加上天色昏暗,一闪即过,沈觉非也看不清那是什么人,他也未曾想及其他,和董小梅两人,看了半晌,还只贫是什么大镖局保了红货,由此路过,不作理会,径自睡去。
第二天一早,他们两人,又继续向前赶路。点苍山乃是沈觉非的外公家,但是沈觉非却只有在十二岁头上,随父母来过一次,路途依稀记得,却又不是十分熟悉,摸索着向前走去,当天傍晚时分,便已然进入了雄峙天南的点苍山了!
沈觉非记得,要到青葱峰去,必需翻过一重悬崖,两座高岭,还有通过一条极长的峡谷,方始能够望得到青葱峰。
而青葱峰半峰以上,全是寸草不生,陡上陡下的峭壁。当然,对于轻功已有造诣之人,可以仗着轻功直接上去,但轻功不到火候的人,却要由峰顶上放下吊索来,方能上得峰去。
两人一鼓作气,越过了一座悬崖,天色已然渐渐地黑了下来。
沈觉非虽然心急赶路,但是他路途不熟,一到天黑,却也不敢乱闯。因为点苍山幅员广阔,若是迷失了路途,只怕一两个月,闯不出来,更是误]大事!两人来到了悬崖之下,只见一个老大的水潭,有几股泉水,注入潭中“叮咚”有声,地方极是幽静,在潭旁,有着四五块方方整整,足有丈许高的大石。
两人便跃上了大石,董小梅笑道:“就在这里睡上一晚,倒也不错。”沈觉非道:“是啊,在这里结庐而居,也是十分幽静。”
董小梅忽然仰起头来,望定了沈觉非,面上的神色,十分怪异,沈觉却向之一看,心中不由得抨然而动,暗忖自己刚才那句话,在对自己如此痴的董小梅听来,可能引起误会!因此,他连忙又道:“我只是说,像这样好存地方,竟没有人隐居,实是十分奇怪!”
当董小梅听得沈觉非刚才那两句话之际,她芳心的确是忐忑不已,以)沈觉非肯和她在一起,在这儿结庐而居,等到沈觉非又解释了几句,她才矢道自己会错了意。
当下,她也不说什么,只是幽幽地叹一口气,眼中已然饱蕴泪水,但I她又不愿被沈觉非看到自己流泪,连忙又转过头去。
沈觉非只是觉得心中歉然,但是却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董小梅的好。两人正在默然相对之际,忽然听得高处,传来“哈哈”一下笑声!那一下笑声,不但突如其来,而且是由半空中传了下来的,董小梅和办觉非两人,不禁尽皆一怔,立即抬头向上看去。
那一晚,天色很黑,星月微光照映之下,两人向上一看,并没有看至什么。
董小梅心中不禁害怕起来,连忙向沈觉非靠近了些,低声道:“沈公子刚才是有人在发笑么?怎么看不到有人啊?”
沈觉非心中,也是诧异之极,道:“别出声,再仔细看看!”
两人刚讲了一句话,便听得又是在半空之中,一个人道:“你还不认菊么,我这一子下去,你那一角土的棋子,全都完了!”
另一个人道:“只怕未必,你看看那一角土,你能逃得过去么?”
先讲话的那人“啊”的一声,道:“原来你有此一着,倒是难防!”
沈觉非和董小梅听出那讲话的两人,像是正在对笑,可是最莫名其妙的就是两人的声音,不知何以会从半空中传下。
两人循声仔细望去,好一会儿,董小梅才伸手向上一指,低声呼道:“办公子,你看!”沈觉非此时也已然看到那两个对弈者的所在!
就在那水潭之旁不远处,有一棵极高大的松树,几乎已在松树顶上一身粗细才如手臂的横枝之上,面对面地坐着两个人,在两个人中,还放着一引棋盘……^
那横枝只有手臂来粗细,微风过处,上下摇动,可是那两个人,坐在上面,却是稳当到了极点,看他们的情形,正全神贯注在棋盘上,根本不关心是否会跌下来!
天色甚黑,那两个人的容貌,看不十分清楚。沈觉非只当既然在点苍山中,可能那两人内便有自己的外公和舅公在。
可是他看了一会儿,那两人却又全都未曾见过,回头看董小梅时,只见她面上现出了骇然之色,道:“那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我认识的。”
沈觉非忙道:“是么?是哪一个?”
董小梅道:“在外面那个,身穿灰衣的,便是我和你说起过,一举手间,便吓跑了司徒本本的那个灰衣人。”沈觉非和董小梅两人,在一路南来之际,相互之间,各将分手后的遭遇,详细和对方说过,是以董小梅一说,沈觉非便自明白。
沈觉非又向那灰衣人望了几眼,道:“还有一个呢,是什么人?”
此际,他们两人向黑暗中望得久了,已然可以看清,那坐在灰衣人对面的人,乃是一个身材十分矮小,看来简直像是孩童一样的蒙面人。可是其人的手足,却又细又长,看来又像是一只猴子一样。
那蒙面人的一身衣服,也怪得出奇,紧贴着身子,像是水靠一样。
董小梅道:“那人我不认识,但是他既和那灰衣人在一起,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沈觉非悄声道:“小梅,我们还是快些走吧,这些武林高人,不喜欢有人打扰他们的。”
董小梅道:“怕什么,我们在此,他们当然早已发现,并不赶我们走,可见他们并不讨厌!”沈觉非一想,也觉得有理。
只见那灰衣人举手拈着一枚棋子,沉吟半晌,忽然一伸手,道:“不下了!”
他一面说,一面伸手向棋盘上便拍了下去,只听得“啪”的一声响,棋盘上百余枚棋子,全部跳了起来,那蒙面人怪叫一声,道:“你想耍赖么?”双手一按,只听得一阵密集无比的“叮叮”声过处,那百余枚棋子,又一起落了下来!
沈觉非和董小梅两人,一见那两人各自露了一手这样的绝顶武功,心中实是骇然欣羡已极。
那两下动作,看似简单,但如不是内力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怎能做得到?
那灰衣人在棋盘上一拍之际,所有的棋子,俱都跳起了尺许高下,绝无参差不齐,可知他内力之纯,实是罕见!
而那蒙面人在双手一按之下,仍将那些棋子,按了下去,落在原位,可知他掌力凝滞,已然如同磁石一样,而且出手之快,也是匪夷所思!
两人心中,正在惊骇之际,只听得那蒙面人道:“快布子!”灰衣人笑道:“猴子精,你当真要我出尽奇丑,方肯放过我么?”
蒙面人“哈哈”大笑,笑声之中,隐隐有金石渊渊之声,道:“你肯认输了也好,人急悬梁,狗急跳墙,我也不为已甚。”
灰衣人笑骂道:“轻骨头猢狲,赢了一盘棋,便狂成这样,忘了输棋之际,怎样搔耳挠腮了么?”
蒙面人笑道:“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自然由得我神气!”
灰衣人一面笑,一面伸手一拂,“叮叮”之声不绝,将棋子全都没收人袖中,道:“猴子精,你提起当年勇来,我倒想起一件事!”
那蒙面人对于“猴子精”这一称呼,像是甘之如饴,绝无反感,道:“什么事?”
灰衣人道:“阴风蛇叟司徒本本,静极思动,又拟在巫山朝日峰,搅风搅雨,你还去不去?”
沈觉非本来,不想偷听人家的谈话,想要及早离去,可是他一听得灰衣人如此说法,却不禁又引起了好奇心来。
因为,上一次巫山朝日峰,邪派中人,为了排名比武一事,虽然事隔多年,但在武林之中,却是流传极广,人人皆知。
在上一次比试中,参加的人,自然都是顶儿尖儿的高手,全都是威震武林的人物。但是却也有两个极其神秘的人。
那两个极其神秘的人物,全都是蒙面参加的。尤其神秘的那人,便是在独占鳌头之后,便飘然隐去的那一人,至今武林之中,不知他是何人。
而另一个蒙面人,则位居百花洲百花老怪之下,黑骷髅连无异之上,排名第六,事后也是不知他是何人。但因为他是排名第六,因此便不及那位第一名蒙面人那样,受人注意。
沈觉非心中暗忖,那灰衣人的口气之中,蒙面人像是也曾参加上一次大会。只是不知他是第一名那个,还是第六名的那个!因此,沈觉非便想听了下去,弄个究竟。
只听得那蒙面人叹了一口气,道:“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三十余年来,武林之中,不知又出了多少出类拔萃的高手,司徒本本既敢再来生事,当然也是有恃无恐,我不想去了!”
灰衣人一笑,道:“猴子精,你什么时候,参起禅来了?”
蒙面人道:“我只是不想生事而已,谁参他妈的禅?”
灰衣人也叹了一口气,道:“我只是想将皓首神龙也引到会上去,当着普天下武林中人,再和他一见高下,即使仍然不敌,也死了此心了!”
沈觉非和董小梅两人,听到此处,心中又不禁吃了一惊。
因为那灰衣人,虽然气度雍容,非同凡响,但是和皓首神龙谢音威武无匹的神态一比,却还差许多。而且,皓首神龙谢音,不但威震华夏,其声名远至西域、天竺,也是震摄人心,已然被公认为武林泰斗,乃是高不可及的人物!但是,那灰衣人却公然想和皓首神龙,当着天下武林人物一见高下!只听得那蒙面人道:“你这人,可以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你在他手下,败过多少次了?”
灰衣人的语音,顿时显得激动无比,反手在横枝之上一拍,“啪”的一声,老大一蓬松针,纷纷而坠,道:“前后共有七次了!”
蒙面人笑道:“可知你这人,当真朽木不可雕,顽蛮如孟获,被孔明七擒七纵,尚且心服,你却仍要和他一见高下?”
灰衣人朗声道:“我若是不能胜他,死不瞑目!”
蒙面人摇手道:“好!好!你可还记得十年来前,你练了三招自以为天下罕见的‘擒龙手法’,结果却在两招之内,便为谢老头儿破去一事么?如今你又练成了什么武功,想找谢老儿动手,不妨充使出来让我也见识见识如何?”那灰衣人“哈哈”一笑,道:“还是我那一套风花雪月剑法!”
蒙面人一听,突然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几乎跌了下来,道:“你那四招风、花、雪、月剑法,我认你是第一流的武学,我与你为敌,也不易对付,但是你忘了,你以此四招剑法,和谢音对敌之际,是怎样落败的了么?”董小梅和沈觉非听到此处,更是不忍离去,董小梅轻轻一碰沈觉非,道:“沈公子,天下之大,当真无奇不有,剑法也可以以风花雪月为名,当真是闻所未闻!”沈觉非对那套剑法的古怪名称,心中也是感到好笑,但是他知道,那灰衣人既然在谢音手下,败了七次,而还要再去找他,一定也是武功已臻绝顶的人物,心内却并未有轻视之感。
只听得灰衣人道:“我当然记得,在第三招‘雪花六出’头上,被谢音双手,将我双剑抓住,断成了两截!”
蒙面人道:“这就是了,你难道还想在普天下武林人物面前,再一次出丑么?”
灰衣人道:“这就是我此次前来找你的原因了,猴子精,若是你肯助我一臂之力,我定然可以一雪前耻,打败谢音。”
蒙面人笑道:“好么,我早就知道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帮你忙不要紧,话可得说在前面,两个打一个我可不干!”
灰衣人道:“你将我当作何等样人了?你看,这是什么?”
那灰衣人一面说,一面便自怀中,摸出了拳头大小的一块物事来。
那块物事才一出手,便泛起了一团紫殷殷的光华,映得那灰衣人须眉皆紫!
那蒙面人一见,猛地一怔,劈手便抢了过来,道:“好家伙,这是紫金英哇!你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灰衣人道:“我以后再和你细说,这块紫金英,足够镶在两柄剑的剑锋上之用,我知道普天之下,只有你一人,有此本领,你可能帮我忙么?”
那蒙面人只顾翻来覆去地看那块紫金英,露出的双眼之中,异光四射,好一会儿,才道:“原来你是有求而来,所以才让我羸了一盘棋,是也不是?”灰衣人哈哈大笑,并不说话,显然已经默认。
蒙面人抬起头来,道:“若是将这块紫金英,镶在剑锋之上,当然威力大增,但是只怕仍然难免为谢音神力震断。”
灰衣人道:“无论如何,你替我铸成了剑,我可以去试一试!”
蒙面人沉吟半晌,道:“承你看得起我,我一生铸剑,不下千柄,这紫金英还是第一次看到,若能给我半年功夫,我就能以这一块紫金英,为你铸成一双旷古未有的宝剑!”
灰衣人大喜过望,叫道:“真么?当真么?那紫金英够了么?”
蒙面人抬头向天,眼中光芒更盛,像是已然看到那一对旷古未有的奇剑,经他半年心血铸炼,已经出炉一样,语音也极是激动,道:“这一对宝剑,薄如蝉翼,轻若无物,柔软之处,可以绕指,钢锐之际,可以断玉,只怕欧冶子复活,干将再生,见了我所铸的这两柄宝剑,也要自叹不如!”
灰衣人忙道:“那你就快动手吧!”
蒙面人道:“好!”
他一个“好”字才出口,身子便猛地向下一沉,将那根横枝,压得沉下了三尺,猛地又弹了起来,就借着那一弹之势,他双臂一振,向半空之上,直窜起两丈高下,身子在半空之中,盘旋不已,不一会儿,便已然落了下来,隐在黑暗之中!
那灰衣人也是身形拔起,向下落去,片刻间,两人尽皆不见。
沈觉非看他们两人离去时的情形,竟像是根本未曾发觉自己和董小梅两人一样,心中不禁一怔,就在此际,只听得董小梅道:“沈公子,我知道那个蒙面人是谁了!”
沈觉非丨忙道:“你怎么知道?”
董小梅道:“我曾听得谷公公说起普天下英雄人物,他曾经告诉我,在点苍山附近,另住着一个高人,叫侯子青一”董小梅那“侯子青”三字,在沈觉非听来,就像是“猴子精”一样,忍不住笑了出来,道:“小梅,你又淘气了!”
董小梅忙道:“不是,他是姓侯,公侯的侯!”沈觉非这才明白,道:“这个人,却是未曾听到过啊!”董小梅道:“他的夫人,却是大大有名,你应该知道的,就是大理南诏国雪罗公主,武林人称南天一凤的段翠!”
沈觉非一听得董小梅讲出“南天一凤段翠”的名字来,心头不禁猛地―怔。
段翠之为南诏国公主,尚在其幼时,南诏国亡后,段翠为高人收去,学得一身本领,行走江湖,她又美艳,武功又高,不知曾引得当时多少英雄人物竞相折腰,连谢音也在所不免。声名之噪,无以复加,人人都知道她的名头,沈觉非也曾听人讲起过不知多少次。但是其人,不几年,便突然销声匿迹,不知去踪,却是未曾想到,她会在这里,而且还嫁了那样一个七分似猴,三分似人的人!
沈觉非心中虽吃惊,但是却也不无疑惑,道:“谷公公可会弄错?”
董小梅道:“不会的,谷公公说,南天一凤段翠的下落,知者绝少,他也是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之中,才知道段翠已然嫁给了侯子青的。那侯子青固然本身武功也已臻极高的境界,但是他却绝不在武林中走动,其人生平最好铸剑!”
沈觉非道:“那也不对啊,他会铸剑,更应该声名大噪才是,何以侯子青三个字,我竟是从来也未曾听人说起过?”
董小梅道:“我问你,你可曾听得武林之中,有‘剑窟’的传说么?”
沈觉非道:“有啊,众人相传,说是在某一地方,有利剑千柄,只要找到,便可任意取之,但这只不过是传说吧了!”
董小梅笑口吟吟,像是因为她自己所知多过沈觉非,因而感到异常得意,道:“绝不是传说,而是事实!”
沈觉非笑道:“若是事实,你一柄我一柄,也早已被人取完了?”
董小梅道:“你倒说得容易,南天一凤和侯子青两人,是死人吗?那剑窟,就在他们两人所住附近的一个山洞之中,侯子青铸剑之能,天下无双,历年来所铸之剑,不下千柄,但是他却没有一柄满意,将所有的剑,全都封在山洞之中,常叹佳材难得,他自己铸剑一生,也没有一柄好剑使用!其实,那些剑已全是罕见的利器,但还是不人他眼而已!”
沈觉非听了,不由得大感兴味,道:“所以那灰衣人便来找他了?”
董小梅道:“当然,你看侯子青刚才高兴的样子,这一下,他大概对自己所铸之剑,可以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