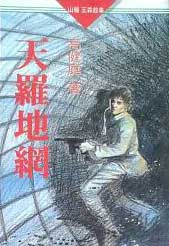(一)
屋子里没有燃灯。
谢晓峰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黑暗里,坐在他们吃饭时总要特地为公主留下的位子上。
——她一生下来就应该是个公主,你若看见她,也一定会喜欢她的,我们都以她为荣。
炊火早已熄灭,连灰都已冷透。
狭小的厨房里,已永远不会再有昔日的温暖,那种可以让人一直暖入心底的肉汤香气,也永远不会再嗅得到了。
但是他的确在这里得到过他从来未曾得到过的满足和安慰。
——我叫阿吉,没有用的阿吉。
——今天我们的公主回家吃饭,我们大家都有肉吃,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块,好大好大的一块。
肉捧上来时,每个人眼睛里都发出了光,比剑光还亮。
剑光闪动,剑气纵横,鲜血飞溅,仇人倒下。
——我就是谢家的三少爷,我就是谢晓峰。
——天下无双的谢晓峰。
究竟是谁比较快乐?
是阿吉?还是谢晓峰?
门悄悄的被推开,一个纤弱而苗条的人影,悄悄的走了进来。
这是她的家,这里的每样东西她都很熟悉,就算看不见,也能感觉得到。
现在她又回来了。
带她回来的,是个胖胖的陌生人,却有一身比燕子还轻灵的功夫,伏在他身上,就像是在腾云驾雾。
她不认得这个人。
她跟他来,只因为他说有人在这里等她,只因为等她的这个人就是谢晓峰。
阿吉慢慢的站起来,轻轻道:“坐。”
这是他们为她留的位子,她回来就应该还给她。
他还记得他第一次看见她坐在这张椅子上,她乌黑柔软的头发长长披下来,态度温柔而高贵,就像是一位真的公主。
那时他就希望自己以前从未看过她,就希望她是一位真的公主。
——你总不能让谢家的后代娶一个妓女做妻子。
——妓女,婊子。
他又想起他第一次看见她时,想起了他的手按在她小腹上时感觉到的那种热力,想起了她倒在地上,腰肢扭动时的那种表情。
——我才十五,只不过看起来比别人要大些。
小弟还是个孩子。
——没有人愿意做那种事的,可是每个人都要生活,都要吃饭。
——她是她母亲和哥哥心目中的惟一希望,她要让他们有肉吃。
但是小弟才十五岁,小弟是谢家的骨肉。
娃娃已坐下来,像一位真的公主般坐下来,明亮的眼睛在黑暗中发着光。
谢晓峰迟疑着,终于道:“我见过你大哥。”
娃娃道:“我知道。”
谢晓峰道:“他受的伤已没事了,现在也绝不会有人再去找他。”
娃娃道:“我知道。”
谢晓峰道:“我怕你不方便,所以才请那位谢掌柜去接你。”
娃娃道:“我知道。”
她忽然笑了笑:“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我来。”
谢晓峰道:“你知道?”
娃娃道:“你要我来,只因为你不要我嫁给小弟。”
她还在笑。
她的笑容在黑暗中看来,真是说不出的悲伤,说不出的凄凉。
她慢慢的接着道:“因为你觉得我配不上他,你对我好,照顾我,只不过是同情我,可怜我,但是你心里还是看不起我的。”
谢晓峰道:“我……”
娃娃打断了他的话,道:“你用不着解释,我心里也很明白,你真正喜欢的,还是那位慕容夫人,因为她天生就是做夫人的命,因为她用不着出卖自己去养她的家,用不着做婊子。”
她的泪已流下,忽然放声大哭:“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婊子也是人,也希望能有个好的归宿,也希望有人能真正的爱她。”
谢晓峰的心在刺痛,她说的每句话,都像是尖针般刺入了他的心。
他忍不住走过去,轻抚她的秀发,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已痛苦般扑倒在他怀里。
对她说来,能够被他抱在怀里,就已经是她最大的安慰。
他也知道,他怎么忍心将她推开?
忽然间,“砰”的一声响,门被用力撞开,一个脸色惨白的少年,忽然出现在门外,眼睛里充满了悲伤和痛苦,充满了恨。
(二)
谁知道仇恨有多大的力量,可以让人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来?
谁知道真正的悲伤是什么滋味?
也许小弟已知道。
也许谢凤凰也已知道。
华少坤的尸体,是一个时辰前在六角亭里被人发现的。
他的咽喉已被割断,衣服上,手上,苍白的须发上都是血。
他身旁还有把血刀。
没有人能形容出谢凤凰看到她丈夫尸身时的悲伤,痛苦和愤怒。
在那一瞬间,她就像是忽然变成了只疯狂的野兽。
她大哭,大叫,抓自己的头发,抓自己的脸,恨不得把自己整个人都撕裂,撕成一片片,再用火烧,再用刀切,烧成粉末,切成浓血。
七八只有力的手按住了她,直到一个时辰后,她才总算渐渐平静。
可是她还在不停的流泪。
二十年患难相共的夫妻,二十年休戚相关,深入骨髓的感情。
——现在他已是个老人,你们为什么还要他死?死得这么惨?
她的悲伤忽然变作仇恨,忽然冷冷道:“你们放开我,让我坐起来。”
天虽然已快亮了,桌上还燃着灯,灯光照在慕容秋荻脸上,她的脸色也是惨白的。
谢凤凰已在她对面坐下,泪已干了,眼睛里只剩下仇恨。
真正的悲伤可以令人疯狂,真正的仇恨却能令人冷静。
她冷冷的看着跳跃的灯火,忽然道:“我错了,你也错了!”
慕容秋荻道:“你为什么错了?”
谢凤凰道:“因为我们都已看出,今晨那一战,败的并不是谢晓峰,而是华少坤,可是我们都没有说出来。”
慕容秋荻不能否认。
谢晓峰的那柄剑,若是真正被震飞的,又怎么会恰巧落在谢凤凰手边?
他借别人的一震之力,还能将那柄剑送到谢凤凰手边,这种力量和技巧用得多么巧妙?
谢凤凰道:“谢晓峰本来不但可以击败他,还可以杀了他,可是谢晓峰没有这么做,所以现在杀他的人,也绝不会是谢晓峰。”
慕容秋荻也不能否认。
谢凤凰盯着她,道:“所以我想问你,除了谢晓峰外,这里还有什么人能一剑割断他的咽喉?”
慕容秋荻沉思着,过了很久很久才回答:“只有一个人。”
谢凤凰道:“谁?”
慕容秋荻道:“就是他,他自己。”
谢凤凰用力握住自己的手,指甲刺入掌心:“难道你说他……他是自杀的?”
慕容秋荻道:“嗯。”
谢凤凰忽又用力摇头,大声道:“不会,绝不会,为了我他绝不会这么做。”
慕容秋荻叹了口气,道:“他这么做,也许就是为了你。”
她接着又道:“因为他看得出你也知道真正败的是他,你不忍说出来,他自己也没有勇气说出来,这种羞侮和痛苦,一直在折磨着他,像他那么刚烈的人,怎么能忍受?”
谢凤凰垂下头,黯然道:“可是……”
慕容秋荻道:“可是如果没有谢晓峰,他就不会死。”
她自己是女人,当然很了解女人。
女人们在自己的悲伤愤怒无处发泄时,往往就会迁怒到别人头上。
谢凤凰果然又立刻抬起头,道:“谢晓峰也知道他的脾气,也许早就算准了他会走上这条路,所以才故意那样做。”
慕容秋荻轻轻的叹了口气,道:“那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谢凤凰又盯着跳跃的火焰看了很久,忽然道:“我听说只有你知道谢晓峰剑法中的破绽。”
慕容秋荻苦笑道:“我的确知道,可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
谢凤凰道:“为什么没有用?”
慕容秋荻道:“因为我的力量不够,出手也不够快,虽然明明知道他的破绽在哪里,等我一招发出时,已来不及了。”
她叹息着,又道:“这就像我虽然明明看见有只麻雀在树上,等我去捉时,麻雀已飞走。”
谢凤凰道:“可是你至少已知道捉麻雀的法子。”
慕容秋荻道:“嗯。”
谢凤凰道:“你有没有告诉过别人?”
慕容秋荻道:“只告诉过一个人,因为只有他那柄剑,或许能对付谢晓峰。”
谢凤凰道:“这个人是谁?”
慕容秋荻道:“燕十三。”
(三)
小弟已转身冲了出去,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转身冲了出去。
他已亲眼看见他们拥抱在一起,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就算亲眼看见的事,也未必就是真的。
他还不了解这句话,也不想听人解释,只想一个人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因为他自觉受了欺骗,受了伤害,纵然他对娃娃并没有感情,但是她也不该背叛她,谢晓峰更不该。
谢晓峰了解这种感觉。他也曾受过欺骗,受过伤害,也曾是个倔强而冲动的热血少年。
他立刻追了出去。
他知道谢掌柜一定会照顾娃娃的,他自己一定要照顾小弟。
只有他能从这少年倔强冷酷的外表下,看出他内心深处那一份脆弱的情感。
他一定要保护他,不让他再受到任何伤害。
小弟明知他跟在身后,却没有回头。
他不想再见这个人,可是他也知道,谢晓峰若是决心想跟住一个人,无论谁都休想甩脱。
谢晓峰没有开口。
因为他也知道,这少年若是决心不想听人解释,无论他说什么都没有用。
天已经亮了,日色渐高。
他们从陋巷走入闹市,从闹市走入荒郊,又从荒郊走上大道。
道上的过客大都行色匆匆。
现在秋收已过,正是人们结算这一年盈亏利息的时候。
有些人正急着要将他们的收获带回去和家人分享。
有些人带回去的,却只有满心疲劳和一身债务。
谢晓峰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
——这一年我是否已努力耕耘过?有什么收获?
——这一年是我亏负了别人,还是别人亏负了我?
他无法回答。
有些人的账,本就是谁都没法子算得清的。
正午。
他们又走入了另一个城市,走上了热闹的长街。
不同的城市,同样的人,同样在为着名利和生活奔波。同样要被恩怨情仇所苦。
谢晓峰在心里叹了口气,抬起头,才发现小弟已停下来,冷冷的看着他。
他走过去,还没有开口,小弟忽然问:“你一直跟着我,是不是因为你已决心准备要好好照顾我?”
谢晓峰承认。
他忽然发现小弟了解他,就正如他了解小弟一样。
小弟道:“我已走得很累了,而且饿得要命。”
谢晓峰道:“那么我们吃饭去。”
小弟道:“好极了。”
他停下来的地方,就在“状元楼”的金字招牌下,一转身就可以看见里面那和气生财的胖掌柜,正在对着他们躬身微笑。
“八热炒四荤四素,先来八个小碟子下酒,再来六品大菜,虾子乌参,燕窝鱼翅,全鸡全鸭,一样都不能少。”
这就是小弟点的菜。
胖掌柜微笑鞠躬:“不是小人夸口,这地方除了小号外,别家还真没法子在仓促间办得出这么样一桌菜来。”
小弟道:“只要菜做得好,上得快,赏钱绝不会少。”
胖掌柜道:“却不知还有几位客人?几时才能到?”
小弟道:“没有别的客人了。”
胖掌柜道:“只有你们两位,能用得了这么样一桌菜?”
小弟道:“只要我高兴,吃不了我就算倒在阴沟里去,也跟你没关系。”
胖掌柜不敢再开口,鞠躬而退。别的桌上却有人在冷笑:“这小子也不知是暴发户?还是饿疯了?”
小弟好像根本没听见,喃喃道:“这些菜都是我喜欢吃的,只可惜平时很难吃得到。”
谢晓峰道:“只要你高兴,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没有人能吃得下这么样一桌菜,小弟每样只吃了一口,就放下筷子:“我饱了。”
谢晓峰道:“你吃得不多。”
小弟道:“若是吃一口就已尝出滋味,又何必吃得太多?”
他长长吐出口气,拍了拍桌子,道:“看账来。”
像他这样的客人并不多,胖掌柜早就在旁边等着,陪笑道:“这是八两银子一桌的菜,外加酒水,一共是十两四钱。”
小弟道:“不贵。”
胖掌柜道:“小号做生意一向规矩。连半分钱都不会多算客官的。”
小弟看了看谢晓峰,道:“加上小账赏钱。我们就给他十二两怎么样?”
谢晓峰道:“不多。”
小弟道:“你要照顾我,我吃饭当然该你付钱。”
谢晓峰道:“不错。”
小弟道:“你为什么还不付?”
谢晓峰道:“因为我连一两银子都没有。”
小弟笑了,大笑,忽然站起来,向刚才有人冷笑的桌子走过去。
这一桌的客人有四位,除了一个酒喝得最少,话也说得最少,看起来好像有点笨头笨脑的布衣少年外,其余的三个人,都是气概轩昂,意气风发的英俊男儿,年纪也都在二十左右。
桌上摆着三柄剑,形式都很古雅,纵未出鞘,也看得出都是利器。
刚才在冷笑的一个人,衣着最华丽,神情最骄傲,看见小弟走过来,他又在冷笑。
小弟却在看着他手边摆着的那柄剑,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好剑。”
这人冷笑道:“你也懂剑?”
小弟道:“据说昔年有位徐鲁子徐大师,铸剑之术天下无双,据说他曾应武当第七代掌门之邀,以西方精铁之英,用武当解剑池的水,铸成了七柄利剑,由掌门人传给门下剑术最高的七大弟子,人在剑在,死后才交回掌门收执。”
他微笑问道:“却不知这柄剑是否其中之一?”
冷笑的少年还在冷笑,身旁却已有个紫衣人道:“好眼力。”
小弟道:“贵姓?”
紫衣人道:“我姓袁,他姓曹。”
小弟道:“莫非就是武当七大弟子中,最年轻英俊的曹寒玉?”
紫衣人又说了句:“好眼力。”
小弟道:“那么阁下想必就是金陵紫衣袁家的大公子了?”
紫衣人道:“我是老二,我叫袁次云,他才是我的大哥袁飞云。”
袁飞云就坐在他身旁,唇上已有了微髭。”
小弟道:“这位呢?”
他问的是那看来最老实的布衣少年:“彩凤不与寒鸦同飞,这位想必也是名门世家的少爷公子?”
布衣少年只说了三个字:“我不是。”
小弟道:“很好。”
这两个字下面显然还有下文,布衣少年就等着他说下去。
老实人通常都不多说,也不多问。
小弟果然已接着说道:“这里总算有个人是跟他无冤无仇的了。”
袁次云道:“他是谁?”
小弟道:“就是那个本来该付账,身上却连一两银子都没有的人。”
袁次云道:“我们都跟他有冤仇?”
小弟道:“好像有一点。”
袁次云道:“有什么冤?什么仇?”
小弟道:“贤昆仲是不是有位叔父,江湖人称千红剑客?”
袁次云道:“是。”
小弟道:“这位曹公子是不是有位兄长,单名一个‘冰’字?”
袁次云道:“是。”
小弟道:“他们两位是不是死在神剑山庄的?”
袁次云脸色已变了,道:“难道你说的那个人就是……”
小弟道:“他就是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
“呛啷”一声,曹寒玉的剑已出鞘,袁家兄弟的手也已握住剑柄。
“你就是谢晓峰?”
“我就是。”
剑光闪动,三柄剑已将谢晓峰围住。
谢晓峰的脸色没有变,胖掌柜的脸色却已被吓得发青。
小弟忽然走了过去,拉了拉他衣袖,悄悄问:“你知不知道吃白食最好的法子是什么?”
胖掌柜摇头。
小弟道:“就是先找几个人混战一场,自己再悄悄溜走。”
小弟已经溜了。
他说溜就溜,溜得真快,等到胖掌柜回过头,他早已人影不见。
胖掌柜只有苦笑。
他并不是不知道这法子,以前就有人在这里用过,以后一定还会有人用。
因为用这法子来吃白食,实在很有效。
(四)
正午,长街。
小弟沿着屋檐下的阴影往前走。
能够摆脱掉谢晓峰,本是件很令人得意高兴的事,可是他却连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
他只想一个人奔入原野,放声呐喊,又想远远的奔上高山之巅去痛哭一场。
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谢晓峰是不是能对付那三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小杂种?
——他们谁胜谁负,跟我有什么狗屁关系?
就算他们全都死了,也有他们的老子和娘来为他们悲伤痛哭,我死了有谁会为我掉一滴眼泪?
小弟忽然笑了,大笑。
街上的人全都扭过头,吃惊的看着他,都把他看成个疯子。
可是他一点都不在乎,别人随便把他看成什么东西,他都不在乎。
一辆大车从前面的街角转过来。
用两匹马拉着的大车,崭新的黑漆车厢,擦得比镜子还亮,窗口还斜插着一面小红旗。
身上系着条红腰带的车把式,手挥长鞭,扬眉吐气,神气得要命。
小弟忽然冲过去,挡在马头前,健马惊嘶,人立而起。
赶车的大吼大骂,一鞭子抽了下来。
“你想死?”
小弟还不想死,也不想挨鞭子,左手带住了鞭梢,右手拉住了缰绳,赶车的就一头栽在地上,车马却已停下。
车窗里一个人探出头来,光洁的发髻,营养充足的脸,却配着双凶横的眼睛。
小弟走过去,深深吸了口气,道:“好漂亮的头发,好香。”
这人狠狠的瞪着他,厉声道:“你想干什么?”
小弟道:“我想死。”
这人冷笑,道:“那倒容易得很。”
小弟微笑,道:“我就知道我找对了地方,也找对了人。”
他看着这人扶在车窗上的一双手,粗短的手指,手背上青筋凸起。
只有经过长期艰苦奋斗,而且练过外家掌力的人,才会有这么样一双手,做别的事也许都不适宜,要扼断一个人的脖子却绝非难事。
小弟就伸长了脖子,拉开车门,微笑道:“请。”
这人反而变得有些犹豫了,无缘无故就来找死的人毕竟不太多。
车厢里还有个猫一样蜷伏着的女人,正眯着双新月般的眼睛在打量着小弟,忽然吃吃的笑道:“他既然这么想死,你为什么不索性成全了他?胡大爷几时变得连人都不敢杀了?”
她的声音就像她的人一样娇弱而柔媚,话中却带着猫爪般的刺。
胡大爷眼睛里立刻又露出凶光,冷冷道:“你几时见过我胡非杀过这样的无名小辈?”
猫一样的少女又吃吃的笑道:“你怎么知道他是个无名小辈?他年纪虽轻,可是年轻人里名气大过你的也有不少,说不定他就是武当派的曹寒玉,也说不定他就是江南紫衣袁家的大少爷,你心里一定已在顾忌着他们,所以才不敢出手。”
胡非的一张脸立刻涨得血红,这少女软言温柔,可是每句话都说中了他的心病。
他知道曹寒玉和袁家兄弟都到了这里,这少年若是没有点来历,怎敢在他面前无礼?”
小弟忽然道:“这位胡大爷莫非就是红旗镖局的铁掌胡非?”
胡非立刻又挺起了胸膛,大声道:“想不到你居然还有点见识。”
江湖豪杰听见别人知道自己的名头,心里总难免有些得意,如果自己的名头能将对方骇走,那当然更是再好也没有。
小弟却叹了口气,道:“我也想不到。”
胡非道:“想不到什么?”
小弟道:“想不到红旗镖局居然有这么大的威风,这么大的气派,连镖局里一个小小的镖师,都能摆得出这么大的排场来。”
这样的鲜衣怒马,香车美人,本就不是一个普通镖师能养得起的。
红旗镖局的声誉虽隆,总镖头“飞骑快剑”铁中奇的追风七十二式和二十八枝穿云箭虽然是名震江湖的绝技,可是镖局里的一个镖头,月俸最多也只不过有几十两银子。
胡非的脸涨得更红,怒道:“我的排场大小,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弟道:“一点关系都没有。”
胡非道:“你姓什么?叫什么?是什么来历?”
小弟道:“我既没有姓,也没有来历,我……我……”
这本是他心里的隐痛,他说的话虽不伤人,却刺伤了他自己。
像曹寒玉那样的名门子弟,提起自己的身世时,当然不会有他这样悲苦的表情。
胡非心里立刻松了口气,厉声道:“我虽不杀无名小辈,今日却不妨破例一次。”
他的人已箭一般窜出车厢,铁掌交错,猛切小弟的咽喉。
小弟道:“你虽然肯破例了,我却又改变了主意,又不想死了。”
这几句话说完,他已避开了胡非的二十招,身子忽然一转,“嗤”的一声,中指弹出,指尖已点中了胡非的腰。
胡非只觉得半边身子发麻,腰下又酸又软,一条腿已跪了下去。
那猫一样的女人又笑了:“胡大镖头为什么忽然变得如此多礼?”
胡非咬着牙,恨恨道:“你……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
那猫一样的女人道:“我吃里扒外?我吃了你什么?凭你一个小小的镖师,就能养得起我?”
她看着小弟,又道:“小弟弟,你刚才只有一样事看错了。”
小弟道:“哦?”
猫一样的女人道:“一直都是我在养他,不是他在养我。”
胡非怒吼,想扑过去,又跌倒。
猫一样的女人道:“最近你吃得太多,应该少坐车,多走路。”
她又用那双新月般的眼睛瞟着小弟:“可是我一个人坐在车里又害怕,你说该怎么办呢?”
小弟道:“你想不想找个人陪你?”
猫一样的女人道:“我当然想,想得要命,可是,我在这里人地生疏,又能找得到谁呢?”
小弟道:“我。”
胡非一条腿跪在地上,看着小弟上了车,看着车马绝尘而去,却没有看见后面已有人无声无息的走过来,已到了他身后。
(五)
车厢里充满了醉人的香气。
小弟跷起了脚,坐在柔软的位子上,看着对面那猫一样蜷伏在角落里的女人。
这女人要甩掉一个男人,简直比甩掉一把鼻涕还容易。
这女人也在看着他,忽然道:“后面究竟有什么人在追你,能让你怕得这么厉害?”
小弟故意不懂:“谁说后面有人在追我?”
猫一样的女人笑道:“你虽然不是好人,可是也不会无缘无故要抢人马车的,你故意要找胡非的麻烦,就因为你看上了车上的红旗,躲在红旗镖局的车子里,总比躲在别的地方太平些。”
她的眼睛也像猫一样利,一眼就看出了别人在打什么主意。
小弟笑了:“你怎么知道我是看中了车上的红旗,不是看中了你?”
猫一样的女人也笑了:“好可爱的孩子,好甜的嘴。”
她眨着眼,眼波流动如春水:“你既然看中了我,为什么不过来抱抱我?”
小弟道:“我怕。”
猫一样的女人道:“怕什么?”
小弟道:“怕你以后也像甩鼻涕一样甩了我。”
猫一样的女人嫣然道:“我只甩那种本来就像鼻涕的男人,你像不像鼻鼻涕?”
小弟道:“不像。”
他忽然间就已坐了过去,一下子就已抱住了她,而且抱得很紧。
他的身世孤苦离奇,心里充满了悲愤不平,做出来的事,本就不是可以用常理揣测的。
他的手也很不老实。
猫一样的女人忽然沉下了脸,冷冷道:“你好大的胆子。”
小弟道:“我的胆子一向不小。”
猫一样的女人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小弟道:“你是个女人,很漂亮的女人。”
猫一样的女人道:“漂亮的女人,都有男人的,你知道我是谁的女人?”
小弟道:“不管你以前是谁的,现在总是我的。”
猫一样的女人道:“可是……可是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小弟道:“我没有名字,我……我是个没爹没娘的小杂种。”
一提起这件事,他心里就有一股悲伤怨恨之气直冲上来,只觉得世上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对得起他,他又何必要对得起别人?
猫一样的女人看着他脸上的表情,脸已红了,好像又害羞,又害怕,颤声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是不是想强奸我?”
小弟道:“是。”
他的头已伸过去,去找她的嘴。
突听车窗“格”的一响,仿佛有风吹过,等他抬起头,对面的位子上已坐着一个人,苍白的脸上带着种说不出的悲伤。
小弟长长叹了口气,道:“你又来了。”
谢晓峰道:“我又来了。”
(六)
车厢很阔大,本来至少可以坐六个人的,可是现在三个人就似已觉得很挤。
小弟道:“我知道你从小就是个风流公子,你的女人多得连数都数不清。”
谢晓峰没有否认。
小弟忽然跳起来,大声道:“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我也有个女人,难道你要我做一辈子和尚?”
谢晓峰脸上的表情很奇怪,过了很久,才缓缓道:“你不必做和尚,可是这个女人不行!”
小弟道:“为什么?”
猫一样的女人忽然叹了口气,道:“因为我是他的。”
谢晓峰的脸色惨白。
猫一样的女人已坐过去,轻摸着他的脸,柔声道:“几年不见,你又瘦了,是不是因为女人太多?还是因为想我想瘦的?”
谢晓峰没有动,没有开口。
小弟握紧双拳,看着他们,也不动,也不开口。
猫一样的女人道:“你为什么不告诉这位小弟弟,我是什么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弟忽然笑了,大笑。
猫一样的女人道:“你笑什么?”
小弟道:“我笑你,我早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又何必别人来告诉我?”
猫一样的女人道:“你真的知道我是什么人?”
小弟道:“你是个婊子。”
他狂笑着撞开车门,跳了出去。
他狂笑,狂奔。
谢晓峰是不是还会跟着他?路上的人是不是又要把他当作疯子?
他都不管了。
他又奔回刚才那城市,“状元楼”的金字招牌仍旧闪闪发光。
他冲进去,冲上楼。
楼上没有血,没有死人,也没有战后的痕迹,只有那胖掌柜还站在楼头,吃惊的看着他。
曹寒玉和袁家兄弟刚才是根本没有出手,还是已被打跑了?
小弟也不问,只咧开嘴对那胖掌柜一笑,道:“吃白食的又来了,把刚才那样的酒席,再给我照样开一桌来,错一样我就拆了这状元楼。”
酒席又摆上。
八热炒四荤四素,先来八个小碟子下酒,还有六品大菜,虾子乌参,燕窝鱼翅,全鸡全鸭,一样都没有少。
可是小弟这次连一口都没有吃。
他在喝酒,二十斤一坛的竹叶青,他一口气就几乎喝下了半坛子。
他已几乎醉了。
谢晓峰呢?
谢晓峰为什么没有来?是不是在陪那婊子?
有了那么样一个女人陪着,他为什么还要来?
小弟又笑了,大笑。
楼外忽然响起一阵“隆隆”的车声,一行镖车正从街上走过。
有镖车,就有镖旗。
镖旗是走镖的护符,也是镖局的荣誉,这行镖车插的是红旗。
比鲜血还红的红旗。
(七)
第一辆镖车上的红旗迎风招展,正面绣着一个斗大的“铁”字。
反面绣着一把银光闪闪的利剑和二十八枝穿云箭。
这就是红旗镖局总镖头的令旗。
有这面旗在,就表示这趟镖是威镇江湖的“铁骑快剑”亲自出马押送的。
有这面旗在,大江南北的绿林豪杰,纵然不望风远避,也绝没有人敢伸手动这趟镖的。
有这面旗在,才有遍布大江南北一十八地的红旗镖局。
所以这已不仅是一个人的荣誉,也是十八家镖局中大小两千余的身家生命所系。
无论谁侮辱了这面镖旗,红旗镖局中上上下下两千余人都不惜跟他拼命。
小弟又笑了,大笑,就好像忽然想到了一件极有趣的事。
大笑声中,他已跃下高楼,冲入镖车的行列,一拳将前面护旗的镖师打下马去,身子凌空一翻,摘下了车上的镖旗,双手一拗,竟将这面威震大江南北的银剑红旗一下子拗成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