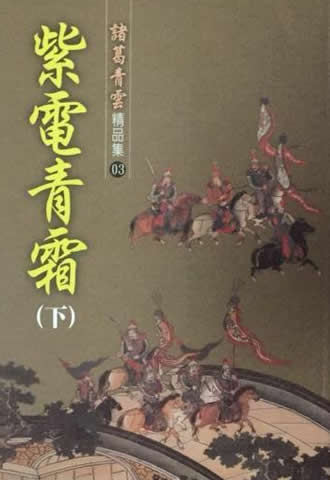易兴汉心头一震,只好硬着头皮走了出来,望着那人抱拳一礼道:“晚辈田兴汉拜见前辈!”
他称那人为前辈,显然已把对方视为武林人物,否则,就该称呼老伯或大叔才对。
岂知那人并未多看易兴汉一眼,却望向宇文婉儿道:“这是怎么回事,是你收留他的?”
宇文婉儿立即向那人盈盈跪倒,颤声答道:“他深山迷路,投宿无门,实在可怜,我只好把他安置在柴房里暂住一夜,明天天一亮就走。”
那人不动声色地道:“你是越来越能干了,留人也自己做得了主,还要我这叔叔做什么?”
宇文婉儿打了个哆嗦道:“叔叔那畤正在房里睡着,我怎敢打扰你老人家。”
那人道:“咱们这‘白云草庐’,除你常伯伯常来常往外,什么时候留过生人来,连叔叔我都从不留人,如今你竟做了主,婉儿,叔叔平日都向你讲过什么?”
宇文婉儿哪里还敢答话,跪在那里,体似筛糠,连头也不敢抬。
那人重重咳了一声,又道:“就算你可怜他,把他留了,为什么还要在柴房陪他,你已经十四五岁了,深夜之间,孤男寡女同在柴房里,成什么体统?”
宇文婉儿见叔叔已起了误会,不得不硬着头皮道:“叔叔,我是见他一天没吃饭,弄了些剩菜剩饭送给他吃的。”
那人哼了一声道:“算这小子走运,又有管吃的,又有管住的,我那半壶酒呢?”
宇文婉儿呐呐答道:“也被他喝了。”
那人点点头道:“真好,连喝的也有,等那一天叔叔出外迷了路,也希望能找到这么个地方,也希望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心人。”
他这些话,虽然是对宇文婉儿说的,但易兴汉听着,却不觉大为气愤,忍不住朗声道:“前辈如果舍不得这顿酒菜,明天晚辈多奉赠些银两就是。”
那人霎时双颊一阵抽搐,喝道:“好一个不知死活的混帐东西,竟敢在我面前出言无状,我就让你永远住在这里算了,不但不要你的银子,你赔上一块葬身之地!”
说着,缓缓举起手中长笛,一步步向易兴汉逼去,他的动作虽然缓慢,但那气势,却十足的震慑人心,连易兴汉在这刹那,也几乎有些透不过气来。
虽然如此,易兴汉却脚下并未稍动,也看不出有任何迎敌准备。
宇文婉儿芳心大骇,急急站起身来,一面向易兴汉尖叫道:“你还不快躲!”一面拦在那人面前道:“叔叔手下留情,他只是个小孩子,纵然冒犯了你老人家,也犯不着生这样的气!”
那人冷笑道:“刚见面你就对他这么好了,这要等到明天,是不是叔叔反而不如他了?”
边说边抬手拨开宇文婉儿,长笛骤然举起,斜斜地向易兴汉肩头压下。
易兴汉心头立感一震,只觉对方来势虽然甚为缓慢,但却先有一股奇大的潜力涌出,笛势未到,已迫得他几乎无法站立。
当下,易兴汉情不自禁急急滑步旋身,飘闪三尺,总算没被击中。
谁知他尚未站稳,那长笛如影随形般又攻袭上来。
易兴汉被迫之下,只得迅快地拔出长剑,反臂架了上去。
剑笛一接,一声“呛啷”大震,火星迸飞之下,易兴汉顿时虎口欲裂,整条右臂都近乎酸麻。
到这时他才知道对方的长笛竟是百炼精钢打造。
所幸那人见好就收,并未再行进逼,收起长笛,冷冷笑了几声道:“不错,小小年纪,竟有这等功力!”
易兴汉抱剑一礼道:“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那人带着不屑的意味道:“少说废话,报上姓名来!”
易兴汉道:“晚辈田兴汉。”
那人听得似是十分留意,两眼眨动了一阵,许久,才鼻孔里哼了一声道:“口气倒不小,连我当年联合多人之力都兴不了汉,你凭什么兴汉?”
易兴汉心头怦然一震,抱拳又是一礼道:“兴汉不过是晚辈的名字,名字是父母所取,前辈怎么想到别处去了?”
那人耸了耸肩道:“你现在可以走了,以后不可以再闯到这地方来!”
易兴汉顿了顿道:“难道晚辈只在柴房里度过一夜,前辈也不见允?”
那人道:“白云崖从不留住外人,你想破了我的规矩不成?”
易兴汉自知恳求无用,进入柴房,背起行囊,躬身一礼道:“多谢前辈一饭之恩,大恩大德,易兴汉永不敢忘!”
那人道:“哪里这多的礼数,快走!”
易兴汉再向宇文婉儿抱拳道:“在下多谢姑娘!”
宇文婉儿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却并未出声说什么。
这时已近二更,由于肚子已不再饿,又加方才的一阵折腾,他已毫无寒意。
转瞬便离开那三间茅舍甚远,深山苍苍茫茫,连白天都会迷路,何况夜间,此刻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个避风之处,度过一夜,等天亮后再寻找白云洞。
好在不久之后,终于发现两块巨石之间,中间有一条缝隙,刚好可容一人睡卧,而且上面也有巨石遮着。
他找来一些干草把地上铺好,枕着行囊躺了下来,起初似乎还颇为舒适,但不久之后,便渐渐感到寒气袭人。
身上一冷,自然无法入眠,辗转反侧间,很自然地脑海中便涌现出方才“白云草庐”那一幕。
他对宇文婉儿有着一种莫名的感激,对她的叔叔却又莫测高深。
但他对他并无恨意,以他方才接下他那一招长笛攻势,可知此人是位武功已经登峰造极的绝顶高手,而他隐居深山十余年不曾在江湖走动,其中又必有一段耐人寻味的隐秘,可惜自己虽然有心查明原委,却无从查起,试想他连外人踏进白云崖一步都不肯,又怎会把这段隐秘告诉外人。
心念像风车般打着转,大约三更之后,终于朦胧睡去。
他自幼在苗原夫妇的爱护之下,一直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几曾受过颠沛流离之苦。尤其最近两天,昨晚睡在草堆里,今晚则连睡草堆也变成了奢望,每次被冻醒,都不禁要伤心落泪,而想起自幼爱他甚于己出的苗原一家落难,以及“铁瓦寺”的群豪惨死在清帝鹰犬爪牙手下,更是悲愤莫名。
这一晚,在他来说算是有生以来最长的一夜。
好不容易天已微明,他背起行囊,又开始在深山中奔走的行程。
可以想见,在问路无人之下,茫茫一座周围二百里的大山,想找一处山洞,等于大海捞针,根本无从找起。
好在他想起那怪人和宇文婉儿住的地方叫白云崖,也许白云洞不会离得太远。因之,他尽量保持方向,不离开白云崖太远。
当真皇天不负苦心人,大约在午后不久,白云洞居然被他找到了。
这里就在白云崖山后大约五六里,在接近山巅之处,居然出现了一道小小的狭谷。
那狭谷两边笔直如削,谷壁直达峰巅,谷口处窄得仅能容一人通过。进入谷口后,约五、六丈便出现了弯路,因之,站在谷外,看来像一眼便看到谷底,哪里会知道里面深处别有洞天。尤其,能攀登到这里的,普通人已是绝无仅有,这也就是明空神尼所以要选择这地方作为潜心静修之处的原因。
转过谷内弯路,里面豁然开朗,谷道渐渐宽阔开来,两边谷壁,虽然多半是岩石形成,却生满了异草奇花。
再前进数十丈,谷道已至尽头。
就在谷道尽头的左边崖壁上,现出一扇石门。
推开石门,先是长约三丈的地道,地道尽处,是一间极大的圆形石室,里面石几石案,正面墙壁上雕着一尊笑面迎人的佛像。
巨大石室的四周,石壁上另有好几扇石门,想必里面都是些供人居住的小型石室。
本来,易兴汉原不知这里就是白云洞,只是偶而在外面发现一处谷口盲目闯了进来而已,直到他进入那巨大石室燃亮火折点起神案前的长明灯,才发现石壁上雕着“白云洞”三个大字。
他本来在发现“白云洞”三个大字后,内心充满一阵惊喜,但立刻又本能的感到气氛有些不对,因为既是白云洞里有人,为什么自己直闯进来竟无人出声喝问。
他猜想到那些石门内的石室里也许有人,但又不便推开查看,只得轻咳了一声,叫道:“小凤!小凤!快快出来,是我来了!”
他对苗凤飞一直是称呼小凤的,在他预料,苗凤飞此刻纵然在里面睡着了,也必会马上惊醒奔出来相见。
岂知一连叫了几声,竟无半点动静。
于是他顾不得冒失,快步过去,推开一间石门。
石门内果然是间石室,里面有床榻也有用具,但却并无一人。
再依次把所有石门推开,竟全是空洞洞的。
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因为他想到这里除了苗凤飞和她的师姐慧因之外,必定另有其他比丘尼,怎会全数不在呢?何况这外面的巨大石室,也算一座佛堂,佛堂怎可无人守护?
不过他已觉出这里可能已很久无人,否则,石室内的长明灯为何已经熄灭?
那么,白云洞里的人又到哪里去了呢?当然,他最关心的,还是苗凤飞的下落,她是苗家的唯一后代根苗了,万一发生不测,苗家从此岂不断了香火?
他焦虑不安地在石室内踱步等待,只盼着曾有奇迹出现,同时,也为自己今后的何去何从苦思。
他本来已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若白云洞已经无人,天下虽大,在他来说,竟无容身之处了。
在洞内直等了将近半个时辰,见仍无丝毫动静,心知已经不可能有人回来,只好离开白云洞,先下了山再说。
谁知出了谷口,竟又使他情不自禁一惊,不过这次却是惊中带喜。
但见离谷口不远,站着一名清丽脱俗,秀媚可人的紫衣少女,赫然是宇文婉儿。
易兴汉跃前几步,急急问道:“婉儿姑娘,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宇文婉儿眨了眨星眸道:“当然是找你,想不到这样巧,在谷外就遇到你了。”
易兴汉道:“姑娘怎知道我在这里?”
宇文婉儿道:“你昨晚不是已经告诉过我要到白云洞么?”
易兴汉哦了一声道:“这样说昨晚姑娘就该告诉我白云洞的地点,好在我碰得巧,不然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这里。”
宇文婉儿带些不好意思的神色道:“并非我不告诉你,而是我只听说附近有处白云洞,却从来不曾到这里来过。”
“你现在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呢?”
“叔叔告诉我的。”
“那么姑娘为什么来找我?”
“也是叔叔要我来找的。”
易兴汉怔了一怔道:“莫非令叔昨晚把我放走又后悔了?想把我捉回去杀死在白云崖?”
宇文婉儿蹙了蹙黛眉道:“你怎么喜欢说这种话?他如果要杀你,昨晚就把你杀了,而且凭你昨晚接下他老人家一招的身手,我也不见得一个人就能把你捉回去。”
易兴汉茫然问道:“这样说他又要我回去做什么呢?”
宇文婉儿道:“当然是有事啦,不然他何苦打发我老远跑来找你。”
易兴汉摇头道:“抱歉,在下不想去了,你叔叔脾气太怪,我真有点怕他,昨晚我已受够了他的气,怎可再回去自找苦头吃。”
宇文婉儿撇了撇嘴道:“其实也不是我叔叔一个人要叫你,是他听了常伯伯的话,才派我来找你的!”
易兴汉道:“就是姑娘昨晚说过常到府上的那位常伯伯?”
宇文婉儿点头道:“不错,昨晚你吃的那半条鱼,就是他老人家带来的,今天他又来了,又带了好几条大鲤鱼呢。”
她不等易兴汉开口,再道:“常伯伯今晚不打算走了,要我把鱼烹了,晚饭时和叔叔好好喝一顿,常伯伯说如果你是他找对的人,今晚就更要大喝特喝了。”
易兴汉越感不解,顿了一顿道:“我更不想去了,他们一定是要杀了我,尽情庆贺一番。”
宇文婉儿又眨起星眸道:“莫非你有仇家?”
易兴汉道:“实不相瞒,在下身负血海深仇,到处都是仇家,而且这些仇家时时刻刻都在追捕我。”
宇文婉儿默了一默,摇头道:“你即便有仇家,也不可能是我叔叔和常伯伯,叔叔在白云崖隐居十几年,常伯伯也自我记事起就在江边打鱼,他们从不和任何人来往,又怎会是你的仇家呢?”
易兴汉道:“可是他们要找我回去,又怎能说是事出无因?”
宇文婉儿微一沉吟道:“也许和你身上那口剑有关系吧。”
易兴汉心头一震道:“他们怎能看到在下这口剑呢?”
宇文婉儿道:“是你昨晚在柴房吃饭时,我偷偷注意到你剑鞘上刻有‘广寒剑’三字,今天常伯伯到来,叔叔对他提起你昨晚闯进‘白云草庐’的事,常伯伯起初并未大惊小怪,直到我说出你身佩‘广寒剑’时,他才吃了一惊,叔叔的表情也立刻显得大不寻常,经过他们两人商议,才要我马上来找你回去,因为我也曾告诉他们,你要到白云洞,这地方的详细位置,是叔叔刚才告诉我的。”
易兴汉暗道:“莫非宇文姑娘的叔叔和常伯伯也是乾隆手下的鹰犬爪牙?……”
不过这意念很快便被另一个想法推翻,因为他觉得既是乾隆的鹰犬爪牙,怎可能在这种地方隐居起来,而且一住就是十几年呢。
但他们若非清廷派出的人,又为什么要找自己回去?而且此刻自己所认识的武林人物,几乎已被乾隆的手下杀尽,哪里还有再认识自己的人?
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不想跟随宇文婉儿到白云崖,但想到对方既然已知白云洞所在,必定也知道慧因和苗凤飞的下落,说不定白云洞的人,已经落在他们手中。
想到这里,他似乎又觉得必须冒险前往一探究竟才对了。
宇文婉儿见易兴汉久久沉思不语,不觉催促着道:“有什么可考虑的,我看他们对你亚无丝毫恶意,只管放心。”
易兴汉略一沉吟道:“在下但求姑娘实话实说,府上此刻除了令叔和那位常伯伯外,还有些什么人?”
宇文婉儿似是大感茫然,楞了楞,反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易兴汉道:“不瞒姑娘,白云洞此刻已空无一人,是否都已到了府上?”
宇文婉儿越感愕然,摇摇头道:“白云洞的人怎么会到舍下去呢?我昨晚才对你说过,舍下除了当伯伯常来常往外,从没有别的人去过,就连白云洞在这里,我也是刚才听叔叔告知的。”
易兴汉虽弄不清对方的话是真是假,却已在顷刻间下了决定,即便白云草庐是龙潭虎穴,他也要闯上一闯。
想到这里,挺了挺胸道:“好吧,我随姑娘再到府上走一趟就是。”
宇文婉儿芳心一喜,笑道:“总算让我办妥了一件事,来的时候,我还一直担心会使常伯伯和叔叔失望呢。”
她说着,转身在前面带路。
易兴汉紧紧随在她的身后,见她像只美丽的大蝴蝶般,步履间有如飞絮飘花,不难看出对方的轻身工夫,似是不在自己之下。
他轻咳了一声道:“姑娘好俊的一身轻功,可都是跟着令叔学的?”
宇文婉儿笑道:“白云草庐就是我跟叔叔相依为命,当然是叔叔教我的了。”
“令叔的武功称得上是高不可测了。”
“你怎么知道?”
“昨晚我接了他一招,难道心里还没有数。”
“你能接下叔叔一招,叔叔照样也对你另眼相看。”
易兴汉再问道:“姑娘那位常伯伯是否也会武功?”
宇文婉儿道:“当然也会,他还教过我不少招术呢,有时酒后来了兴致,也和我叔叔对练,只是看不出来他们谁的身手高。”
易兴汉笑道:“他们是好朋友,当然不会玩真的,你怎能看出他们谁高谁低。”
宇文婉儿道:“你又怎样来的一身好工夫呢?”
易兴汉道:“当然是有人教的。”
“是谁教的?”
“不是你叔叔。”
宇文婉儿“噗哧”一声笑道:“废话,我叔叔从前根本没见过你,怎会教你武功?”
易兴汉道:“那就对了,我就是告诉你教我武功的是谁,你照样也没见过他。”
宇文婉儿对易兴汉这种似是而非又有些强词夺理的话,不愿反驳,只是漫声道:“咱们快些走,我回去还要做晚饭,说不定今晚我叔叔会好好招待你一番。”
说话间已到达白云草庐前,远远就望见一个人站在竹篱之外。
宇文婉儿低声道:“这人就是我常伯伯。”
易兴汉在这刹那,不觉微微一惊,只觉这人好像有些面熟。
宇文婉儿快走几步,奔上前叫道:“常伯伯,您要见的人已经来了!”
那人捋着颔下的山羊胡子,也似吃了一惊道:“原来就是他!”
易兴汉跟上前去,望着那老人抱拳一证道:“在下拜见前辈,请恕晚辈一时间记不起来,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前?”
常姓老人笑了笑道:“好记性,前天晚上才见过,现在就忘了。”
易兴汉心中一动,这才想起此人就是前晚在江边芦苇中茅屋内烤鱼饮酒把自己渡过江的那位老渔夫,只因当时是在夜间,两人又不曾多讲话?故而此刻才觉得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常姓老人虽在说话,视线却早已盯注在易兴汉所佩的那口剑上,他不须细察剑鞘上所刻的字,心里便已有了数,急急转头望向茅舍,高声叫道:“老七,一点不错,他身上佩的正是‘广寒剑’!”
接着双颊抽搐了几下道:“小伙子,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竟敢把这口剑带在身上,若被大内高手认出,还有命么?”
易兴汉哦了一声道:“老前辈是什么人?”
常姓老人道:“老夫只是个捕鱼渡船的山野之人,前晚还是我把你渡过江的,难道不到两天就忘了?”
易兴汉道:“可是老前辈怎会认识这把剑?”
常姓老人道:“‘广寒剑’在武林中算得上是神兵利器之一,老夫当年也曾在江湖走动过,曾经见过这口剑。”
易兴汉顿了顿道:“老前辈可知道当年使用这剑的是什么人?”
常姓老人霎时神色黯然,叹了口气道:“当然不可能是你了。”
易兴汉暗道:“废话,我不过才十四岁,当然不会是我。”
常姓老人却望着茅舍自言自语道:“老七怎么还不出来?”
心里想着,不由再叫道:“老七,你是怎么啦,还不肯出来?”
只听茅舍内传出那阴阳脸的声音道:“三哥把他带进来不就结了。”
常姓老人望向易兴汉道:“小伙子,随老夫到那面去吧!”
易兴汉却站着不动道:“晚辈不想进去。”
常姓老人楞了下道:“为什么呢?”
易兴汉道:“那人脾气古怪,性情恶劣,晚辈昨晚和他见过一次就不想再见了。”
常姓老人笑道:“他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子,连对我有时候都不客气,何况你只是一个小孩子。”
易兴汉道:“你们是多年朋友,老交情,当然不必在乎,晚辈来到这里是客人,何苦自己找气受!”
常姓老人伸手抓住易兴汉道:“只管随我进去,有我在,他不敢把你怎样。”
易兴汉只感常姓老人五指间有股似有似无的巨大力量,使得他不想走也要跟着走。
穿过竹离,进入茅舍,只见那阴阳脸的人正坐在几案边饮茶。
易兴汉到道时才看清此人原来并非天生的阴阳脸,那边昨夜所见的黑色的面颊,似是被毁容所致,由于筋肉纵横模糊,疤痕累累,所以月下看来,和另一边对比,才似是一张阴阳脸,若单看那好的一边,此人当年必定是眉清目秀,甚至俊逸潇洒。
常姓老人松开手,吩咐道:“年轻人请坐!”
宇文婉儿本来紧紧地跟在后面,忙着为易兴汉倒过一杯茶后,怔怔地站在一旁。
常姓老人瞥了她一眼道:“婉儿,没你的事了,快到厨下准备酒菜去!”
宇文婉儿本想在旁看看即将发生什么事,听了常姓老人的话,虽不情愿,也只好转身往厨房而去。
常姓老人再望向易兴汉道:“年轻人,可否把你身上的剑解下来让我瞧瞧!”
易兴汉此刻已觉出对方似是并无恶意,略一犹豫,随即将剑解下,双手递与常姓老人。
谁知常姓老人并未多看,却递给阴阳脸道:“老七,你自己看去!”
阴阳脸探臂接过,当目光触及剑鞘上那“广寒剑”三个字,双颊立时抽搐了几下,接着“呛啷”一声,将剑身抽出,半晌,才一字一句的问道:“这把剑是从哪里得来的?”
易兴汉不便说出苗原名字,顿了一顿道:“自然有人相赠,但晚辈不便奉告此人是谁!”
阴阳脸再问道:“说实话,你叫什么名字?”
易兴汉道:“前辈当真贵人多忘事,晚辈昨晚已经说过,在下姓田名兴汉。”
阴阳脸不动声色道:“你可知道这把剑原是我的?”
易兴汉笑道:“岂有此理,那赠剑之人,自晚辈记事起,就佩用此剑,怎会是前辈的呢?”
忽听常姓老人道:“有个叫苗原的人,你可认识?”
易兴汉心头一震,但表面却不得不强自镇定,摇摇头道:“晚辈从没听过这人。”
常姓老人两眼眨动了一阵,侧脸说道:“老七,很可能这口剑由二哥手中失落,又落到别人手中。”
易兴汉心头又是一震,因为在“隐园”事件中,他已得知苗原是江湖九义中的老二,莫非常姓老人和二伯父苗原认识?果真如此,此刻反而该是他向对方查问了。
他呼吸紧促地问道:“老前辈,莫非您认识江湖九义?”
常姓老人哦了一声道:“你小小年纪,怎么也知道江湖九义?”
易兴汉道:“江湖九义都是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大名鼎鼎,晚辈虽没机会见到他们,但对他们却心仪已久。”
常姓老人不动声色道:“你想不想见到他们?”
易兴汉神色黯然道:“可惜他们全已被清廷的鹰犬爪牙残杀殆尽了!”
常姓老人摇头道:“不然,他们仍然还有活在世上的。”
易兴汉怔怔地道:“这是不可能的。”
常姓老人摸着山羊胡子道:“这人就在你面前,老夫便是九义中的一个。”
易兴汉呆了一呆道:“老前辈是九义中的哪一位?”
常姓老人道:“老夫就是九义中的老三,人称‘摘星手’的常乐天。”
易兴汉啊了一声,急急离座而起,扑身向常乐天拜倒,激动无比的叫道:“侄儿拜见三伯父!”
常乐天不由也呆了一呆道:“你……你究竟是谁?”
“侄儿不叫田兴汉,易兴汉才是小侄的真实姓名!”
“你可是‘飞霜剑’苗原夫妇一手抚养长大成人的?”
“不错,二伯父和二伯母一直把小侄视同己出,直到‘隐园’之役后,侄儿才知道他们并非自己的生身父母!”
常乐天急急手指那阴阳脸的人叫道:“还不快快拜见你父亲!”
易兴汉只感一阵热血沸腾,他做梦也想不到,这阴阳脸的人,就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江湖九义中的老七“金笛书生”易朋,其实昨夜他听到笛声又接了对方一招长笛,又听常乐天叫他老七,早就该想到事不寻常了,偏偏他自昨晚至今,竟然疏忽过去。
当下,易兴汉热泪盈眶地扑倒易朋怀中,父子亲情,久久不能自己。
在这刹那,易朋也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冷漠,紧紧拥抱着爱子,泪水像断线珍珠般洒落了易兴汉一身。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推开易兴汉道:“告诉为父,这十几年来,你们在‘隐园’是怎样度过的,‘隐园’一役,他们都是怎样死的?”
易兴汉立即含泪把“隐园”事件以及“铁瓦寺”之役从头到尾详细说了一遍,他因过于激动,竟至声泪俱下。
易朋和常乐天也听得老泪纵横,唏嘘不已。
接着,易兴汉又问起父亲和三伯父常乐天当年“天桥”一役是怎样得能逃生的。
原来当年“天桥”一役,常乐天和易朋虽已身受重伤,却仍逃出一劫,“金笛书生”易朋那一边面颊,正是中了番僧的“密宗大手印”,所幸那番僧也是在力尽之下,故而发掌已失去原有功力,否则,易朋岂能幸得不死。
两人身负重伤逃出京城,躲到一处好心的民家,疗养月余,痊愈后自知大事已不可为,随即双双南下来到九华山,建下了这座白云草庐。
半年之后,两人为了能设法获得一些江湖上武林同道的消息,遂决定一人住在山上,一人住在山下。住在山下的,既可与人接近,又可赚钱谋生,因易朋半边面容被毁,容易招人注意,便由常乐天改扮成渔人模样,在江边捕鱼渡船,可惜十几年来,只知苗原已逃出皇城,隐居“隐园”,但却始终打听不出“隐园”在什么地方。至于易朋之妻“云裳观音”江如苹被乾隆掳进宫去,也是后来才听人说的。
易兴汉听罢上述经过之后,迫不及待地问道:“那位宇文姑娘又是谁呢?”
易朋道:“她就是你四伯父人称‘霸王锤’宇文鑫的独生女儿,当年才不过两岁,为父和你常伯父由京城南下时,也设法把她带了出来,她今年十五岁,算来你该叫她姐姐。”
他深深一叹,再道:“你一个人来到九华山到白云洞去找谁呢?”
易兴汉叹道:“孩儿方才已经说过,在‘铁瓦寺’时已被明空神尼收归门下,二伯父的女儿凤飞妹妹也被她老人家收为弟子,先一步和她的另一弟子慧因来到白云洞,特命孩儿前来和她们相会。”
易朋若有所思地道:“你刚才见到了她们没有?”
易兴汉道:“孩儿正在奇怪,白云洞里竟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易朋面色凝重,默了半晌道:“我对白云洞那边的事,完全不清楚,今天你我父子相会,就用不着再去白云洞了,从现在起,就在这里住下,过几天不妨再过去看看。”
易兴汉忽然又泪流满面,拭着泪水道:“孩儿想到京城救出母亲,把她老人家接回来全家团圆!”
易朋神情激动地道:“为父和你常伯父何尝不是早有此心,但大内高手如云,你去了岂不死路一条?我们父子好不容易团聚了,我岂能让你枉送一命?”
易兴汉只得又把在安庆府有幸得遇纪晓岚的经过说了一遍道:“目前乾隆仍在江南,大内空虚,若不趁现在去营救母亲,以后只怕永远没有机会了!”
他说着探手入怀,取出纪晓岚亲笔所绘的大内图形,双手递与父亲。
易朋神色凝肃的看了一遍,又转交给常乐天。
常乐天看得更仔细,一边说道:“汉儿,明天你利用时间,把这图形重绘一张,带在身上,就不会出事了。”
易兴汉茫然问道:“为什么要重绘一张呢?”
常乐天道:“这张图形,万一营救你娘时失落在皇宫内院,必然会送给乾隆,乾隆如何会认不出纪大人的笔迹,若因而连累了纪大人,教我们于心何安?”
易兴汉不觉悚然警惕,忙道:“侄儿明天重绘一张就是。”
只听易朋道:“三哥的意思,是希望汉儿有这趟行动了?”
常乐天道:“他说得对,若不趁现在去,以后只怕就永远没有机会,你和弟妹当年是人人称羡的一对恩爱夫妻,难道就不想和她见面?”
易朋长叹一声道:“兄弟担心的是他此去凶多吉少!”
常乐天道:“我的意思,也并非让他明天就走,咱们先好好聚几天,不妨趁这几天商议商议,总要想出个万全之计才成。”
易朋沉吟了半晌,终于颔首道:“就依三哥,今晚咱们要痛痛快快喝个不醉不休,汉儿,到厨房去看看你婉儿姐姐饭菜准备得怎么样了?”
易朋当年“天桥”一役后,只是在传闻中得知爱妻江如苹已被乾隆的爪牙掳进宫去,也知道江如苹有了一个月的身孕,但却不知这孩子生出后是否尚在,当然更不知孩子取的什么名字,因之,当昨晚得知留宿在柴房的年轻人叫田兴汉,并未引起他的半点留意。
易兴汉应了一声,随即往厨房奔去。
厨房在茅舍东侧,用山石砌成,虽然也在竹篱内,却和茅舍隔了两三丈远,这是因为万一不慎失火不致波及茅舍之故。
宇文婉儿正在忙着做菜,额头上满是汗水。
易兴汉鼓足了勇气,才叫了一声“婉儿姐姐”。
宇文婉儿绽唇一笑道:“汉弟,你可是来帮忙的?”
易兴汉楞了楞道:“莫非婉姐知道了?”
宇文婉儿笑道:“我刚才已经在门外悄悄偷听过了,你们父子相认,令我高兴得几乎流下了眼泪,你来了正好,负责烧火吧!”
其实易兴汉在这方面,也只有烧火的分儿。
有了易兴汉的帮忙,各种菜肴很快便烹调好,然后两人再忙着端菜,摆了满满的一桌。
餐桌上仍然以又肥又大的鲤鱼最鲜美可口,另有几样野味。
这一餐,常乐天、易朋、易兴汉果然是饮得不醉不休,若不是宇文婉儿还是清醒的,只怕连碗盘也没人收拾了。
次日,易兴汉又到白云洞去了一趟,仍然不见半个人影。在以后的几天里,也是每次去都扑了个空。
大约半个月之后,常乐天和易朋商量的结果,决定让易兴汉到京城走上一趟。
本来,他们两人至少想有一人与易兴汉一起行动,但易朋面容被毁,出门容易惹人生疑。常乐天虽想去,易朋却又不愿他再去涉险,因为他们已知易兴汉一直被乾隆误认是失踪的小王子,即便不幸在宫院内落于那群鹰犬爪牙之手,也不至于有杀身之祸,但若常乐天去了万一被擒,反而会大大对易兴汉不利。
不过,他们对易兴汉一人前去放心不下,最后决定让宇文婉儿也一起去,以便多个照应。
宇文婉儿自幼随常乐天和易朋习艺,身手不在易兴汉之下。
在这些天里,常乐天和易朋也把自己修习半生压箱底的绝活儿,一古脑儿都传授了易兴汉。
常乐天顾虑周密,又把自己的一柄剑鞘,换下了易兴汉身上的“广寒剑”鞘,原属易朋之物,因易朋当年一向以金笛为兵刃,故而把这剑赠给了二哥苗原,而苗原死后此剑又为易兴汉所得,等于物归原主。
易兴汉由“隐园”随带而来的行囊,全是些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或珍奇之物,临行时把行囊之物交给了常乐天和易朋,只带了足够往返京城的银两,便和宇文婉儿一同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