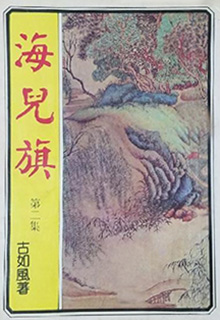回到“大盈若冲”五层楼,水老妖抓起一尾海中大鱼,据案大嚼。
大鱼是生吃的,一张红桃大木案上,摆满数十款颜色,味道不同的酱汁,也有熟油、炸得酥脆的花生,切得幼幼细细的青、红辣椒,至于名瓷银器,更是琳郎满目,美不胜收。
这一尾大鱼,是海蛇甫自大海石礁间钓获,鱼鳞早已刮净,肉质闪亮鲜明。但更夺人眼目的,却是水老妖右掌之中的一把黄金匕首,柄端镶着龙眼般大小的绿宝石,花纹形状古朴典雅,锋刃更是寒气森森,锐利异常,厚厚的鲜鱼肉在这匕首之下,固是形同嫩滑豆腐,便是又粗又厚的鱼骨、鱼头,只消匕首轻轻划过,无不轻易切破,切口之处整整齐齐,摆放在银盆瓷碟之上,美仑美奂十分好看。
马小雄才跨入大厅门槛,水老妖已把匕首上一块切割得大小恰到好处的鱼肉,弹指飞射入他口中。
马小雄笑而尝之,走到大厅中央,又是一支形状奇古的酒具平平地凌空飞来,马小雄也来不及瞧清楚这是怎样的盛酒嚣皿,已把酒具拉入掌中,仰首把酒液喝个点滴不留。
酒已饮尽,马小雄把酒器拈起一看,只见这是青铜铸造,呈圆筒形,口部向外移,腹则为圆鼓状,而底部亦稍稍外移。再看酒器体上,有兽形纹饰,马小雄瞧了一眼,微笑道:
“这是饕餮,据说是古时一种很贪吃的恶兽。谚语有云:‘饕餮之徒’,贪财者为饕,贪食者则为餮。”
水老妖大是高兴,招手示意叫他在旁边坐下,道: “干儿子,你手里捧着的,是殷商年代的服方尊,在那时候,用来盛酒的器皿,计开有尊、觚、彝、觥、钵、壶等,但在所有酒器中,以尊最是高尚。因此,到了后来,就被引伸为尊贵,以至是尊敬之意。”
马小雄道:“义父用尊盛美酒给干儿子饮用,意思便是我这个干儿子十分尊贵,你老人家也对我很尊敬的意思。”
水老妖道:“你将来是否十分尊贵,值得别人尊敬,全看你日后怎样做人。”
又用匕首切了几块鲜鱼肉,醮了几种酱汁混和混和,送入马小雄嘴里。
马小雄道:“这种混酱鲜鱼,比什么都还更好吃。”
水老妖摇摇头,道:“天下间最美味的不是美酒、鱼肉,而是仇人身上的鲜血和肉块。”
马小雄心中大不以为然,但却也不与义父争拗。水老妖大口大口地喝酒,接道: “当今天下,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先有契丹铁骑,四处扩充势力,在我国大好河山之上千里燎原,辽贼未破,女真蛮夷相继兴起,完颜部之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抗辽节节大胜,立国号‘大金’,定都黑龙江会宁,成为大宋北方心腹大患。
“完颜阿骨打并非一介莽夫,在此人整顿之下,军民编制严谨有度。规定三百户由一‘谋克’带领,而十个‘谋克’又归一‘猛安’管治,这便是当今著名之‘猛安谋克制’。
“金帝在蛮夷之中,肚子里很有点墨水。他既读汉人书卷,在心仪大汉文化之余,更下令创制女真文字,使政令能够有效地推行。
“数年前,金国建立之初,何骨打御驾亲征,大破黄龙府。辽帝领军七十万之众,前来讨伐,竟惨遭大败,死亡兵将尸体遍布百余里。自此,辽军声势似是一颓不起。次年,金兵再破东京辽阳府,并宣布‘除辽法,免税赋。’以收买人心。
“女真族金人气势大盛,源于领袖英明,虽在契丹人逼压之下仍能武功大盛,扭转乾坤。
反观大宋江山,自创国迄今,朝纲一年比一年更败坏。单是冗兵数目,便已大得惊人。
“自太祖以来,国家奉行养兵之策,兵员军费不断膨胀扩大。在太祖开宝年,养兵三十七万八千,禁军就占了十九万。至英宗治平年代,兵员已暴增至一百二十万,内禁军达六十余万人,才不过百年光景,兵额竟增加三至四倍,可怜天下所入财用,单是养兵所需,已占了岁入的六分之五。
“除了冗兵之外,冗官亦多。既有冗兵冗官耗尽百姓民脂民膏,国力又怎能昌盛?除此之外,边防薄弱,民变四起,昏庸官吏都足以使国势有如江河日下,变成强敌金戈铁马下的……这块东西!
说到这里,水老妖用匕首刺入已吃剩一半的鲜鱼,喟然长叹。
马小雄钦佩地瞧着水老妖,良久才道:“我第一次瞧见你老人家的时候,怎么说也猜想不到,你竟然会是一个大有学问,更大有见识的人物。”
水老妖道:“在朝廷鹰犬眼中,你义父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江洋大盗,但在我眼中,这些贪官污吏,比世上最可恶的强盗还更可恶该杀。只要有机会,凡是贪赃枉法得来的民脂民膏。
我就算拼着一身剐也要劫回来再说。你义父老啦,纵使有金山银海,也用不着,但我用不着并不等于没有人用得着,除了可以还富于贫民之外,也可以储存起来,静候适当时机好好花用。”
马小雄道:“要到怎样的形势,才可以好好地花用?”
水老妖道: “你年纪尚幼,跟你说也说不明白,来日方长,就算义父死了,也会留下一些锦囊妙计之类的东西,教你将来怎样为天下百姓做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
马小雄听了,默默地记在心中,历久不忘。
水老妖今天兴致甚好,喝酒十余斤,虽无大肉,却有大鱼佐酒,又跟义子慷慨谈论天下大事,胸怀更是豪迈如同大雕一飞千里,他道:“义父有一套刀法,不敢妄言天下第一,却也有威震武林同道之力,趁我未死,耍给你开开眼界。”
“要是木小邪的大刀在此,更能把这套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这把匕首,也是举世难求宝物,以此利刃耍出这套刀法,最少也有七八分苗头。”
酒意上涌,一双老眼却比平时更明亮,足尖轻轻一挑,逾丈长短宽及两尺的红桃木大案,连同案上大大小小器皿酱汁鲜鱼刺骨,齐齐飞上半空。
水老妖一声大喝:“还我山河十八刀!”
这七个字,原来便是他这一套刀法的名称。
这一喝之威,声震大厅。马小雄耳中嗡嗡大响,险些把持不定栽倒下去。
只听得嗤嗤连声,匕首在红桃大木案底下左右翻飞。这张大案重逾数百斤,能够给一个年逾八旬老人轻易地踢上半空,已属难能可贵之“踢”,在水老妖“还我山河十八刀”
之下,更是奇景接踵而至。
只见那张巨案,自始至终,都在水老妖头顶之上不断滚动。这大厅梁粗柱大,便是四五条大汉叠罗汉般堆叠上去,也未能触及屋顶,巨案却一而再再而三险险撞向横梁,其蔚为奇观之处,绝非一般江湖杂耍之流可以比拟。
每次眼看巨案从高而下,这冲击之力,又何只万斤?便是巨案之下有一头万斤巨象,恐怕也会被立时压成“象酱”,但水老妖仅以匕首轻轻一挑,巨案又再有如飞絮一般,腾空飞舞,而且不住旋转滚动像个巨大陀螺,煞是好看。
水老妖连挥十八招,每招都大有名堂,既有“江山如画”、“乘锐攻之”、“降奴斩将”,也有“拔人之城”、“鸟起兽骇”、“围地则谋”……水老妖每出一招,都把名堂厉声叫出,而最后几下招式,显是蜕变于孙子兵法。
十八刀连环使出,招招举重若轻,每一个转折,跃动,纵身,无不神威凛凛,直至最后一招“全国为上”,更是雄浑无比,仅以匕首尖端之力,以卸子诀把巨案自高空引纳回到原来地面之上,摆放得四平八稳,仿佛是根本没有把巨案移动过分毫的模样。水老妖一气呵成的刀法,直把马小雄瞧得呆住,久久连眼睛也没眨动一下。
良久,马小雄方问:“义父什么时候教我这套刀法?”
水老妖向兵器架上一束一束的头发指了一指,道:“要练刀法,先练头发,只要把这些头发捏在手中,久而久之,你就会明白本派武功入门之道。”
马小雄沉吟半晌,道:“义父,咱们这一派,江湖中人怎样称呼?”
水老妖道:“这里是东蛇岛, 自然便是东蛇派,但我从没把自己当作什么一派的掌门。”
马小雄奇道:“这是什么道理?”
水老妖道:“东蛇岛虽然地方不算细小,但东蛇派却只得我一个人,要是自己封自己为掌门,便有如一个麾下空无一兵一卒的大元帅,如此元帅掌门,大则大矣,但却不是大大的威风,而是大大的一个笑话。”
马小雄眉头一皱,道:“海蛇大叔不是东蛇派中人吗?”
水老妖摇了摇头,道: “他只是无家可归,所以数十年来一直跟随着我,我既不是他的师父,也不是他的义父,看来似乎像是我的管家、从仆,但我一直把他当作朋友。”
马小雄又问:“东蛇岛的那个‘蛇’字,是什么意思?”
水老妖道:“‘蛇’者,鲨蛇也,是一种在湖泊、河流中常见的大鱼,但在海中,其实也有更巨大的鲨蛇,我年轻时见过一尾,比这一张红桃木巨案还更粗大数倍。”
马小雄点了点头,算是明白了过来。
水老妖神功盖世,那是不容怀疑的,但他毕竟年事已高,在半醉后演出“还我山河十八刀”,虚耗内力极钜,跟马小雄谈了几句,便自回到房中憩息。
马小雄在兵器架上抓起一束头发,又搓又捏,忽然心血来潮。在头发中左挑右拨,恶婆婆走了过来,奇怪地问:“你干什么啦?”
马小雄道:“要是此人生前是个叫化,说不定头发内藏有虱子。”
这一天,马小雄在大厅之中,接二连三换了五束头发,时而把玩,时而当作兵刃般挥舞,耍出一套无师自通的武功,到了晚上,疲不能兴,躺在红桃木巨案上呼呼大睡。
这一觉睡得甚是香甜,也没有任何人打扰他。倒是到了晨曦将至时分,阵阵凉风把他吹醒。
揉揉眼睛,只见大厅内黑沉沉地,只燃亮了一盏油灯。
打了一个呵欠,伸一伸懒腰,把裤子左抽右摸,朦朦胧胧中便要前往茅厕。
到了茅厕,正要小解,忽听远处传来一阵怪声。马小雄侧耳倾听,那声音已然消失,当下不再理会,脱下裤子撒了一泡份量十足的尿。
小解之后,正待回去再睡一觉,那怪异的声音又再响起。
马小雄用指把耳窝撩拨,再听一会,终于知道那是一个女子正在啜泣,不禁心中咕嘀:
“东蛇岛上除了干妈恶婆婆跟阿玫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女子……干妈嗓门苍老,这声音决不会出自她老人家之口……”
如此推算,这啜泣的女子,自是阿玫无疑。
马小雄心想:“阿玫这个不姑娘,身世比我还更可怜一些,她孤苦伶仃在这岛上,自是酸楚悲苦,兼而有之。”
此时,哭泣的声音,似是渐渐远离而去,但却仍是隐隐可闻。马小雄忖道: “她这个女儿家,心思甚是怪诞,便是上前劝慰,她也不会领情,还是少管闲事为妙。”
但走不上几步,又自寻思:“听她的哭声,甚是悲苦,这里四面环海,要是她自萌短见投身大海,那可不妙……”
愈想愈是感到不妥,急急拔足狂奔,循那哭泣之声追出去。
岂料天色漆黑,他脚步一急之下,撞在一块石头上,登时摔倒,随后往额上一摸,但觉一片黏濡濡的,竟给摔个头破血流。
要是他就此一撞之下晕迷过去, 自然再也不会继续追前,但他神智尚算清醒,虽则额头疼得厉害,仍然咬紧牙关,直追出去,只是脚步再也不敢太快,以免再摔一跤,撞个天崩地裂。
到了海边,终于瞧见一条窈窕身影,孤零零地伫立在石岩上。马小雄上前,在距离数丈之外叫道:“阿玫姊姊,小雄马来啦。”
那窈窕的身影动也不动,马小雄也没听见啜泣之声。他吸一口气,再走上前,蓦然发现,这个女子绝不会是阿玫。
阿玫比马小雄大上一岁,个子当然不会高大到什么地方去。眼前这女子的背影,虽然也是窈窕纤瘦,但只要稍为接近,便可分辨得出,她比阿玫还是个子高了一点点,身材更成熟甚多。
马小雄大为惊讶,失声道:“你……你是谁?”虽在黑暗之中,还是可以瞧得出,她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
白衣女子面色向大海,背对着马小雄,缓缓地说道:“小兄弟,我的事情,你是管不着的,你回去吧。”声音清脆,但语声中悲苦之情,令人闻之心酸。
马小雄道:“真是很对不住……初时,我以为你是我的一个朋友,她叫阿玫,年纪比我大一点点,身世十分可怜,我……我在睡梦中听见你的声音,以为是她在哭泣,就赶了过来……打扰了姊姊的……雅兴……真是很对不住!”
他再三道歉,但心中却又在想:“她在这孤岛之上孤苦伶仃地哭泣,又怎能算是什么雅兴了,当真是胡说八道。”
白衣女子陡地冷笑起来:“这么说,你年纪虽轻,却有一副菩萨心肠啦?”
马小雄忙道:“姊姊见笑了。”
白衣女子嗓子一沉,语气转变得十分严厉:“笑?有什么好笑了?是了,你一定是在讥笑我,是也不是?”
说到最后一句,声音竟是充满怨毒。
马小雄心中一凛,同时却又感到愤怒,心想:“我一片好心而来,又没得罪于你,怎么竟把我当作仇人看待?”气恼之下,说了一声:“告辞了!”转身便走,再也不回头瞧她一眼。
但他走出了七八步,却又停止了脚步,心想:“这位姊姊,分明心中大有冤屈伤心之事,小雄马并非心胸狭隘之辈,又何必跟她斤斤计较?她心情不好,无理骂人也是女子之常情,要是我就此一走厂之,她连随往碧波大海里一跳,岂非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吗?”
愈想愈是汗颜,又再转身回去。
但他转身之后,左顾右盼,竟是再也看不见白衣女子的踪影。
马小雄心中急了起来,暗叫糟糕。
“莫不是白衣姊姊悲从中来,已扑向海水里吗?”正待高声呼叫,却听见背后有人幽幽的叹了口气,道:“要是独自赴往龙宫,也未免是太寂寞了,难得你肯陪我一块儿上路,咱们这便投身大海去吧!”
马小雄再回头一望,差点没当场昏倒过去。
此时,已渐渐到了晨曦时分,东方远海平面之上,微露鱼肚白色,虽然光线还是十分微弱,但已然可以依稀视物。
在马小雄眼前呈现的,是一张女子的脸,但这张脸,又怎能算是一个人的脸孔?只见她没有眉毛,额头上生了一个比鸡蛋还要大的疮,左眼眯成一线,右眼却又大又恐怖,既青光闪闪也血丝满布,说到鼻子,向下凹陷还不算,甚至根本看不见鼻梁,倒像是在脸的正中央位置,开了一道两寸长的深坑,还有嘴唇,上唇奇薄下唇奇厚,完全不对称也还罢了,下唇更是溃烂不堪,宛似随时随地都会掉落下来一样。
马小雄活了十三岁,至今为止,他从没见过如此恐怖的一张脸。
在长江大船上,恶婆婆走火入魔,后来更身中奇毒,当时,她的脸也可算是十分难看丑陋,但若跟眼前这张脸相比,简直便是小巫见大巫。
以十三龄童而言,马小雄已可算是胆色卓越的人物,但在黑夜之中,蓦然瞧见一张这样的脸孔,也不禁为之魂飞魄散,身子发抖。
这一张脸,正是那名白衣女子的容貌,她伸出了手,不由分说便搂住马小雄的腰,一步一步向海里走去。
马小雄颤声道:“你……你真的要投海自尽吗?”
白衣女子冷冷道:“既已做人做得了无生趣,又何必活在世上丢人现眼?”
马小雄心想:“你这副尊容比我干妈厉害百倍,便是到了海底龙宫,也会把虾兵蟹将龟丞相吓得屁滚尿流,还有东西南北四大海龙王,也说不定会给这张脸孔吓得由龙变蛇,再由蛇变作了一条烂蟮!”
胡思乱想之间,已给白衣女子搂着步入海水之中。
此时,天气渐渐清凉,但海水却还是十分暖和,马小雄心神不定,初时给海水浸住双足,竟是浑然不觉。
但渐渐地,海水已浸至他腰间,他方始如梦初醒,心想大事不妙,要是给这女子一直搂住步入龙宫,那可不怎么好玩。
一股求生欲念陡地冒升,马小雄全力挣扎。那白衣女子看来只是随随便便搂住他的腰,但他无论怎样挣扎,始终挣脱不开。
马小雄只好放声大叫,但他拚尽一身力气,却连半点声音也叫不出来,只听得白衣女子缓缓地道:“到了海底龙宫,我自会把你的哑穴解开,好让海龙王能够和你促膝长谈。”
马小雄心中又惊又怒:“海龙王跟小雄马毫无交情,又有什么好谈?”
马小雄受制于容颜恐怖丑陋的白衣女子,完全一筹莫展,只见海水不住在眼前上涨,由腰腹浸至胸口、颈际、以至是下颚。不禁暗暗长叹:“我命休矣,只恨死得糊里糊涂,不知所为何事。”
未几,海水已把他整个人淹没,白衣女子比他身材略高,但也只是高出少许而已。她再向前踏步,两人已双双齐顶淹没。
海水本身,具有很大的浮力。马小雄精通水性,要是他自己一个人浸在海水里,决计不会就此轻易淹死,但白衣女子求死心切,而且功力远在马小雄之上,她搂住马小雄逐步踏入深海,但身子却并不在海水中半浮半沉,竟是强行凝运真气,一直都双足紧贴海底下的岩石,如此一来,两人都陷入凶险无比的险局。
初时,马小雄尚自勉强屏息呼吸,盼望能支撑得一时便得一时。只要白衣女子给海水淹得头昏脑胀神智昏迷,便可伺机挣脱。
相反地,要是白衣女子给海水一浸之下,头脑忽然清楚起来,也可能会改变初衷,不再求死,那时候,也同样有机会可以脱出险境。
但无论白衣女子给海水一浸之下,究竟是更糊涂还是更清醒,最少他自己必须还有一口气在,事情才有转寰余地,否则,一经淹毙,那便万事皆休。马小雄在这凶险万分之际,心中居然又想及另一椿事:“昨天才跟义父饱尝大海里的鱼肉,想不到相隔不足一天,自己却得葬身海底,变作海底大鱼的食物,大概这便是因果循环之道吧!”
海水一直浸住马小雄的脑袋,白衣女子神智如何,他不得而知,只知道眼前一片漆黑,海水早已从七窍中乱窜乱钻,他叫不出声音,也听不见声音,整个人陷入一片死寂境界。
终于,他不再挣扎,因为他已再也没有半点力气,甚至不晓得自己身在何方。
便在此时,一道大力自海面澎湃地冒起,但马小雄全然没有任何感觉。他已在海水中淹得不省人事。
当白衣女子搂着马小雄走向海底之际,一条灰影自岩石那边走了过来。
这人正是跟随着水老妖多年的海蛇。
他目睹白衣女子,意志坚决地搂着马小雄步入海中求死,不禁百感交杂,更是内心说不出的矛盾。
一方面,他巴不得白衣女子就此死掉,好让烦恼事情一了百了,可是,要是白衣女子真的就此跟自己阴阳永隔,却又是毕生中最大的遗憾。
海蛇的脑海中,乱成一片,他心中在想:“椒萍妹气在头上,让清凉海水把她浸得清醒一些,也是好的。”
可是,他的椒萍妹没顶了好一阵,还没有冒上水面,海蛇忽然着急了,他首先在脑袋上重重轰了自己一拳,同时怒骂:“海世空,你不是个人!”
到了海边,海面虽然平静,但他再也瞧不见椒萍妹的踪影,到了这一刻,他忽然又想起了马小雄,心中更是慌乱;自责也更深: “小马若有什么闪失,他可是岛主的义子呀!他妈的海世空,你真是千古罪人!”
形势危急,凡是遇溺者,每耽搁多一刻便更增一分危险,海蛇急急扑入海中,宛似“拨草寻蛇”般疯狂地找寻二人。
但在一片漆黑海水里,急切问要找回两个已人踪的人,又是谈何容易?海蛇急惶之下,运起掌功,把眼前的海水卷成水柱,远远望去,便如同龙卷风把海水卷起的情况一般无异。
但龙卷风是自然界巨大力量,海蛇武功再高,毕竟只是尺人血肉之躯,决不可能持续不断地如此施为,但他救人心切,只要有最后一口气,也会全力豁出,非要把二人救出生天不可。
此时,太阳自东方海平面上缓缓升起,景色异常美丽,再加上一道一道的水柱自海面不断升起,看来更是奇幻壮观,世间罕见。
渐渐地,水柱的高度,一道比一道矮了下去。海蛇泪如雨下,但海水已把他整个人浸得湿透,什么是眼泪,什么是海水,就连他自己也无从分辨。
“椒萍妹,是我不好,是我辜负了你的情义,海世空真不是人!”他已渐渐筋疲力竭,但倏然之间,在太阳光线映照之下,他看见海面上飘浮着一束乌黑的秀发,距离自己才一丈左右光景。
海蛇陡地目光大亮,掌劲再发,卷起最后一道水柱,海水在雄浑掌力下被逼开,他终于瞧见了椒萍妹的白衣身影。
海蛇总算把二人从海底里救了出来,太阳渐渐升起,岛上景色又再恢复了生气,但躺在沙滩上的二人,却面色苍白,奄奄一息。
海蛇久居东蛇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海上各种见识,便如同一般渔夫船家无异。
他知道,在这危急情况下,必须采用以嘴对嘴输气急救之法,而且刻不容缓,愈快愈好。
但在同时间之内,沙滩上摆放着两个人,一个是他非救不可的椒萍妹,另一个是东蛇岛主水老妖的义子马小雄,海蛇应该先去救那一个?
他揉了揉眼睛,抹去热泪,然后扑向马小雄身上,先救水老妖的义子。
马小雄终于在晕迷中转醒,“哇”的一声呕吐出大量海水,海蛇不再理他,立时抢前,扑在白衣女子脸上,如法施为。
但海蛇还没碰到白衣女子的嘴唇,已给她一个耳光掴在脸上。
她也苏醒了,一脸都是恨意。马小雄斜着眼一看,只见这白衣女子年约二十七八左右,脸色虽然苍白得很,但却眉清目秀,长得十分美丽。忍不住问道:“你是谁?难道也和我一般,给那个厉鬼般的恶女抓到海底里吗?”
白衣女子冷冷一笑,道: “我叫霍椒萍,我很爱哭,更喜欢害人。没有人能把我抓到海底里,只会是我把别人送到龙宫里去,跟海龙王促膝长谈。”
听见“促膝长谈”这四个字,再仔细辨认这白衣女子的声音,马小雄这才如梦初醒,随即叫道:“你本来不是那么难看的,为什么要装做冤魂厉鬼的模样来吓人?”
霍淑萍道: “那副人皮面具粗劣无比,也只有你这样的无知少年,才会给吓一大跳!”
马小雄道:“那面具呢?且拿过来让我开开眼界。”
霍椒萍冷冷道:“你要讨取那副面具,到龙宫找海龙王吧!”
说到这里,勉力站起,在旭日映照之下,她的身段窈窕好看,一张美丽的脸庞,更是说不出的凄艳楚人。
海蛇站在她侧边,道:椒萍妹,都是我不好,你杀了我吧!”从腰间摸出一把短刀,交在霍椒萍的手上。
霍椒萍道:“你把我救起,就是要我一刀杀了你?”
海蛇道:“是我对不起你,你就算把我全身上下割开几百块,我也不敢怪你。”
霍椒萍清澈的瞳孔掠过忧戚的神采,怔呆良久,才道:“在你心中,我始终不能算是一个好女子。”
海蛇听了,拼命地摇头,道: “不!在我一生之中,除了岛主之外,你便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霍椒萍嘿嘿一笑,道:“刚才你为救人以嘴输气救人,但先救的并不是我。”
海蛇道: “小马是岛主的义子,比我的贱命珍贵万倍,我不能让他有什么不测。”
马小雄听了,大是讶异,也大为感激。想不到海蛇叔叔对自己竟是瞧得比性命还更重要。
但霍椒萍听了,却大是恚怒,倏地一刀插入海蛇胸口。
这一刀,插得不算太深,但也绝不太浅,虽然并非插入心脏部位,却也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海蛇吃了一刀,竟似是给情人吻了一下脸,面露甜甜的笑意。这个精壮的汉子,虽然容貌并不如何俊美,但却另有一股男子英伟之气,这一下匪夷所思的笑意,倒也令人目眩。
霍椒萍的脸更是煞白三分,叫道:“我刺你一刀,为什么不肯闪避?”
海蛇笑道:“我不是说过,你就算把我全身上下割开几百块,我也不敢怪你吗?现在你只是轻轻地一刀捅过来,要是我闪开了,岂非自掌嘴巴,给天下英雄人物耻笑?”
霍椒萍跺了跺脚,骂道:“你是个混蛋,天下英雄人物,才不会像你这般胡涂荒谬,乱七八糟!”
一面说,一面从怀中取出药瓶,把金创药用力倾泻在刀锋伤口附近,但那一把明晃晃的短刀,却怎么说也不敢拔出来。
海蛇在一块岩石上坐下,全然不理会身上的伤痛,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霍椒萍,道:
“在这世上,除了岛主之外,再也没有人像你对我这般好。”
马小雄在远处依稀听这些说话,心中大奇,忖道:“一刀捅将过来,还说是好极了,这对男女,准是给海水浸得齐齐疯掉。”
随后一想,自己也给海水浸得七荤八素,险些已堕入龙宫跟海龙王谈天说地,不禁悚然一惊:“莫不是我也疯掉了吗?”
只听见霍椒萍忧心忡忡地说道:“这把刀要是不拔出来,恐怕……恐怕……很不好看。”
海蛇又是一笑,道:“椒萍妹说的是。”
反手一下子就把刀刃拔出,伤口立时鲜血狂涌,霍椒萍张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蓦地把脸庞埋在海蛇胸口间,以两片樱唇把伤口封住。
过了片刻,海蛇伤口流出来的血渐渐减少,霍椒萍又把另一瓶金创药敷上去,海蛇握住她的手,道:“椒萍妹,自始自终,都是我负了你的情义,你还是把我一刀杀掉算了。”
霍椒萍依偎在他怀中,雪白衣衫上血渍斑斑,她摇了摇头,细声说道: “我不杀你,你既负情负义,我便要你一直活下去,永远都给我好好地折磨。”
这两三句说话,马小雄站在远处,已没法子听得清楚。
此际,旭日初升,天色完全明亮,霍椒萍紧紧抱住海蛇的身子,痴缠之极。
马小雄忖道:“好一对痴男怨女,我老是站在这里,定必惹人憎厌,还是不如归去练功可也。”
正要离开,海边忽然从水底里冒出一个魁梧大汉。
这大汉极其雄壮,鼻如狮子,嘴似血盆,一身黄袍湿淋淋地紧贴着粗壮的身躯,形貌说不出的凶狠诡异。
倏然之间,在这东蛇岛上,竟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人物,马小雄不禁大为惊诧。在此同时,他也在思索:“霍姑娘又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荒岛上的?”
黄袍大汉神出鬼没地从水底冒出,海蛇只是冷冷的瞧着他,脸上神情依旧,似乎只当是有一条大鱼跃出水面,根本不足以为异。但霍椒萍乍然目睹这大汉出现,却立时花容失色,连身子也在颤抖,显然心中十分害怕。
黄袍大汉自水底走到岸上,一开口便大声骂道:“贱人,还不放手?”
霍椒萍更是惶恐,竟是害怕得哭了起来,但她还是紧紧的抱住海蛇,迭声道:“我不放!
我不放!”
黄袍大汉脸色一沉,道:“妹子,你要男人,做哥哥的—定可以如你所愿,你要怎样的男人都可以找给你,唯独这姓海的贱种,你绝不可以跟他在一起!”
马小雄心下恍然,忖道:“原来是做哥哥的反对妹子跟海蛇叔叔来往,倒不晓得姓霍的跟姓海的有什么恩怨?”
海蛇给黄袍大汉骂了两句,也不禁脸色骤变,道:“霍大侠,咱们的恩怨,终须有个了断,但你不能口出秽言,污辱海某!”
姓霍的黄袍大汉哼的一声,没有反驳,只是对霍椒萍道:“妹子,跟我走!”
霍椒萍摇摇头,道: “海郎刚才给我刺了一刀,伤势沉重,我不能在这时候舍他而去。”
黄袍大汉又是冷哼一下,道:“你要杀他,只消再刺向左边一寸五分,他立时便心脏爆裂,立死无救!”
霍椒萍道:“我是他未过门的妻子,要是他死在我刀下,我便是天下间最恶毒最不祥的贱人。”
黄袍大汉怒喝一声:“混帐!”大步上前,伸手便要捉拿自己的妹子。
伤口兀自不断渗出血水的海蛇倏地出手,一掌向黄袍大汉当胸挥过去。
黄袍大汉却身如鬼魅,轻飘飘地绕过避开,这人身形高大粗壮,但轻功身法之佳妙,却是令人难以想象。
他嘿嘿一笑:“你给我妹子插了一刀,有伤在身,要是我在此刻取你性命,算不上是英雄好汉。”
马小雄暗暗喝采:“不肯乘人之危,总算是光明磊落的人物。”
霍椒萍却在这时,用短刀抵在自己咽喉之上,叫道:“哥哥,你若再相逼要我离开海郎,我宁愿立刻死在他怀里!”语气决绝,一张美丽的脸庞却是泪痕串串,令人为之恻然。
黄袍大汉粗壮的手掌,本已即将抓在霍椒萍右肩之上,最后却再也抓不下去。
他双目圆睁,粗眉倒竖,似乎又要厉声喝骂。但过了片刻,却只是轻叹一口气,轻轻说道:“你不后悔吗?这个人……是咱们霍家非杀不可的心腹大患啊!”
霍椒萍道: “别说是以后怎样怎样,便在眼前这一刻,你也可以把他一掌毙了,但我不管,什么都不管,无论生生死死,我都要和海郎在一块!”
黄袍大汉脸上的每一根肌肉,完全僵硬。
良久,他转过了身,向东蛇岛的南端走去。一艘木船,已在岛南之端航行过来。
他一边走,一边说道:“我会回来的!一定会再回来!海世空,你好好的养伤吧,不要辜负了椒萍。但无论怎样,我一定会杀了你……”语声渐渐嘶哑,也渐渐显得无奈,甚至是苍凉。
------------------------------
drzhao 扫校, 独家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