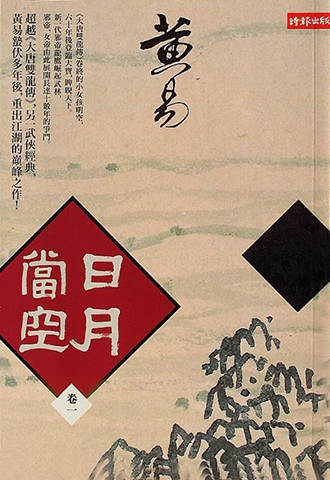林木萧萧。
山风阵阵。
郑雷与那白衣少女两人两骑,策马缓行。
那白衣少女一路上流目盼兮,只是一言不发,有时低吟着前人的诗句,有时似乎在吟着不知名的曲儿。
因此,郑雷也不知该如何搭讪着开口。
因为,此刻郑雷的心中,也在思潮起伏,想着自己的如麻心事。
父亲自从孔庙中由地道一走,生死存亡未卜,为了种种的关系,自己无法抽身探寻其中的奥秘。
甚至,父亲为何要假扮仗剑的护卫?
芳凤,为何要冒充“花衣死神”?
这是一个令人难解的谜!也是郑雷急欲知道底蕴的事。
走了一阵,眼见山势越来越险峻,道路也越来越崎岖。
然而,走在前面的白衣少女,兀自悠然自得,在马上游目四眺,像是在欣赏黄昏夕阳的景色,半点也没有焦急的神情。
郑雷再也耐不住了,抖动缰绳催马赶上几步,朗声道:“姑娘,究竟还有多远?“
谁知白衣少女淡淡地道:“连我也不知道有多远。”
“啊!姑娘?”
郑雷不由大疑,双目连眨几眨又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衣少女从容不迫,缓缓地道:“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奉命引着你向这条路上走,根本不知道要到哪里,怎会知道还有多远呢?”
“你说什么?”
郑雷的双脚一夹,那坐下的马儿扬蹄抢上几步,与白衣少女的白马,已成了并辔同路的形势,他不由沉声叫道:“难道你不是领我去见……”
白衣少女微笑道:“我们这是第一步,喏,第二步的带路人,在前面等着你呢!”
她纤手一指着山路前边不远的峰头。
果然,不高的峰头,十分显眼的地方,夕阳斜映之下,有两个高大的人影,挺立在一块大石之上,双手高举摇动不已。
白衣少女又道:“明白了吗?我只是奉命带你到此为止,前面的路,由那两人负责引导,我们是缘尽于此了!”
说着,她忽然一弓腰,人竟站在马鞍之上,又由袖管内抽出一面三角黑旗,高举右手,连摇了几下。
不远山峰上的两个高大人影之一,也举起一面同样的三角黑旗,不住地在空中划着圈子。
白衣少女这才收起小旗,跃下马背,含笑道:“前面已不宜乘马,少侠,我可要失陪了!”
郑雷如梦如幻,狐疑不定。
但是,为了急欲要见老父,又明知这白衣少女不会告诉什么,他只好应了声道:“也好!”
应话声中,人已飘身下马,探手揭开锦匣,取出那张宣笺,冷然道:“姑娘,区区总有一天会知道你的来龙去脉。”
白衣少女无动于衷,俏皮地道:“到了那一天再说吧,珍重了!”
她接过了空匣,人又已跃上白马,捏唇呼哨一声,招呼黑马,两骑一人已由来路绝尘而去,转眼不见。
郑雷觉得这白衣少女太神秘,回头,看那山峰上的两个高大人影,正在向自己连连招手。
此时不容他多想,一展轻功,凌空虚渡,向那两个大汉立身的山峰掠去。
没有等他落地,那两个大汉也一声长啸,双双划空而起。
原来这两人的身法居然是高手的式子,功力之深不在郑雷之下。
郑雷不由心中一凛,高声喝道:“二位,慢走,在下我……”
两个大汉如同不闻,一味疾驰狂奔,飞涧越岭,向山势深处射去。
于是,两个大汉在前,郑雷在后,双方相隔十丈光景,如同风驰电闪,流星赶月似的一追一逐。
先前,郑雷存心赶上前去,不怕那二人不露庐山真面目。
然而,足有盏茶时分。
郑雷知道自己要失望了。
因为,那两个汉子的功力修为,不在自己之下,任由你快,他俩更快,既不许郑雷追上,也不使郑雷落后,始终保持十丈的距离。
眼看天色入暮,夜色已浓。
幸而,一钩新月,斜挂树梢。
月色下的雁荡山无限无尽,深幽一片。
忽然,东方的山洼内,冒起一道血红的火花,曳起三五丈长的火焰,陡然射入半空,令人心神一惊。
而前面的两个汉子,双双回头向郑雷一招手,同时沉声道:“到了!”
喝声中,两人一齐落下,正是红色火焰射起之处。
郑雷眼见这等情势,不由心头大骇,暗忖道:“这些事分明是有了十分神秘的安排,莫非‘死神教’今晚对我不利?”
想着,不由又摸摸怀中的那幅宣笺。
宣笺上的字迹,分明是父亲的亲笔。
哪里容他多想,两个汉子已又高声道:“到了,来吧!”
这声音好熟,像是那儿听到过,只是急切间想不起来。
郑雷急忙抢前几步。
但见那两个高大的怪人,都是一袭“一罩钟”的宽大披风,蒙头盖脸,只露出两个精光碌碌的眼睛,根本瞧不出面目。
他不由朗声道:“二位何人?引区区来此所为何事?”
两个蒙面大汉鼻孔中同时冷冷一哼,并不答言。
然而,这一哼之中,可以听出夹着七分的杀气,三分的恼怒。
郑雷更加警惕,暗中蓄功戒备,又道:“二位为何不说话?”
两人之一伸手一指谷内,狠狠地道:“请!”
郑雷眼见这等情形,怎肯再进一步,因此脚下一立桩势,冷冷道:“这是什么地方?引区区来此为何?”
两个蒙面汉子尚未答言,谷内忽然发出一声清晰的呼声:“教主有请郑少侠!”
是女子的声音,低沉中含着一股冷嗖嗖的意味,使人听在耳内,不由一阵毛骨悚然,鬼气森森。
这时,两个蒙面人闻声双双撤身,倏然退到谷口,分为左右肃立,低头垂手,似乎十分恭谨。
郑雷本想发作,但耳闻“教主有请”,心中反而一震,暗忖:“莫非是‘死神教’的教主?那就是‘花衣死神’无疑了,找正主儿要紧,这一回也许可以见到她的人了!”
想着,反而一改适才犹豫之心,挺胸向谷内走去。
谷内,茫茫水气,仿佛是笼罩一层薄纱。
郑雷走进谷口不远,斜刺里忽然有人一跃而出,惊呼道:“少侠,你……”
突然跃出一人,郑雷猛吃一惊,振掌护身,凝目倾视,不由既惊又喜地道:“芳凤,是你!”
原来是茫茫峡中“金面魔君”的侍女戚芳凤。
郑雷有千言万语,要问芳凤,只是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情不自禁地抢上前去,大声叫道:“芳凤,我爹呢?”
戚芳凤的一双眸子里,充满了情感的光芒,凝视着郑雷,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清泪,在眼眶内转了几转,终于顺着粉腮滴下来。
“当!”
一声尖锐的钟声,四谷回应。
芳凤耳闻钟声,忽然面色一寒,眼中的泪不流,光彩顿失,若痴若呆地与先前判若两人。
郑雷不由大奇,忙道:“芳凤,你哭了,难道我爹……他……”
不料,戚芳凤的双眉一掀,猝然叫道:“郑少侠吗?教主有请!”
她既不再向郑雷凝视,也不回答他的话,冷森森硬梆梆地说完,扭身又向谷内走去,好像陌生人一般。
郑雷怎能不大吃一惊,急忙追上去,口中连声道:“芳凤,芳凤,我问你,我爹他……他……”
戚芳凤依旧死板板的,铁青着脸色道:“到了,稍候!”
她说着,恭身肃立,向着茫茫白雾的谷内叫道:“上禀教主,金银二护法引郑少侠来到!”
谷内,空洞洞的,传来一声冷冰冰的声音:“戚芳凤退下!”
“遵命!”
戚芳凤应了一声,忽然原地矮身弹腿,一射上升三丈,直向谷底射去,连郑雷想拦都来不及,坠入茫茫白雾之中,芳踪顿渺。
郑雷不由心头一震,啊了一声,叫道:“芳凤,你到哪里去?”
喊着,起势就待追去。
“郑少侠!”
一声低沉的喝止,由谷底发出。
语声低沉,然而,震得人耳鼓嗡嗡不停,郑雷的内功修为,已是少数高手之列,也不由被这深厚的内功所慑,心头不由一震。
接着,低沉的喝声又道:“你是要见你父亲?还是要见戚芳凤?”
郑雷脸上一阵发烧,但却朗声道;
“阁下是谁?为何鬼鬼祟祟的,难道怕见人吗?”
谷内先是冷冷一笑,道:“嘿,嘿,我是谁?你不知道?”
郑雷不觉心头一震,高吼道:“死神教主,花衣死神,是不是?”
谷内淡淡地一哼,应道:“嗯,算是你猜对了吧!”
郑雷不觉怒火高燃,气愤至极,吼道:“如有种就露面与区区见识见识。”
“我们不是早已见过了!”
“都是冒牌的。”
“也不见得!”
“啊,现在你为何藏藏躲躲!”
“本教主从来不作无谓的争论。”
“这不是争论,你出来,郑某见了你一面死也甘心。”
“真的吗?”
“真的!”
一片沉寂,只有谷内的白雾,比先前更浓,袅袅缥缥的,既不上升,也不褪去,把一座深谷,涌得像是在云堆里,更增加了神秘感,也更觉得恐怖异常。
郑雷不见回声,又高声叫道:“怎么?不敢了吗?”
谷内的沉低冰冷语声依旧:“好吧,眼前有两条路,任由你郑雷选择一条,可是,你只能择一条。”
郑雷不加思索地道:“哪两条路?”
“要见本教主,就不能见你父亲,要见你父亲,就不能见本教主,你愿意择哪一条?本教主破例由你作主,只是两者不能兼全。”
这是一个难题。
因为,郑雷急欲一睹“花衣死神”的庐山真面目,看看她到底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以解武林中方兴未艾的风波。
然而,一见老父,也是他当务之急。
故此,郑雷一时不由难以决定。
谷内冰冷的语声已催促道:“怎么?你犹豫不决?”
郑雷无从选择,朗声道:“难道两者不能全让区区一偿宿愿吗?”
“办不到,本教主已声明过,这是我破例由人作主的第一回。”
“好,我见我父亲!”
郑雷左思右想,总是父子情深,自从他离开了“蛇园”,与老父就未晤面,孔庙中疑梦疑真的一见,不但没有详谈,而且更增加了自己心中的疑团,一见老父,乃是他梦寐所求而不可得之事,此时焉肯失去这千载一时之机。
再说,在他心目之中,只要见到了父亲,可能就明白了“死神教”的内幕。
因此,他择了“见父”的这条路。
就在他打着如意算盘之际,谷底,又传来一声低语:“郑雷稍候,总护法已出谷了!”
白雾茫茫之中,忽然有两盏绿晶晶的灯火,由远而近,渐渐踱出。
两个绿衣少女执着两盏纱灯,缓步前行。
后面一人,正是“花衣神”郑昭烈。
郑雷远远地已看见老父的面色红润,额角发亮,只是,目光呆滞,没有往昔的威严逼人气慨。
他疾步紧跨,迎上前去,欢快地叫道:“爹爹!爹……”
谁知,“花衣神”郑昭烈神情似乎十分冷漠,皱着一双眉头,半晌无言。
这等冷漠的神态,使郑雷大惑不解。
在他记忆之中,父亲是最喜爱自己的,而且父亲是最重情感的一个人。
为了母亲有病,父亲十年来,抛却江湖上的盛名,追寻疗治怪病的奇蛇,十年如一日,餐风露宿,从无怨言。
而平日对自己更是是爱护备至,为何今晚……
想着,郑雷不由仰脸含泪道:“爹爹,你……据说你已做了‘死神教’的总护法?是吗?”
“花衣神”的目光一凛道:“怎么?不应该?”
郑雷见老父好像隐有怒容,更加大惑道:“孩儿怎敢说爹爹不应该,只是……只是‘死神教’的企图不明,教义不正,武林正道的人……”
“住口!”
不料“花衣神”勃然大怒,厉声吼道:“你乳臭来干,懂得什么?滚,告诉你,我做老子的事,还用不到你来管!”
“爹,爹爹!”
郑雷做梦也料不到父亲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回想自己为了恢复彩衣门在武林中的声誉,不知受了多少苦难,遭了多少次的打击,由于“花衣死神”与父亲“花衣神”的绰号相近,自己不知经过多少磨难,几经挫折。
想着,不由两行清泪如注的流出,流在“花衣神”的手上。
“花衣神”郑昭烈突地神色一凛,似乎打了一个寒噤。
他低头一看郑雷,也禁不住滴下两行清泪,双臂一抱郑雷,凄楚地叫道:“雷儿,你……你爹累了你了!”
刹那之间,洋溢着父子的情份。
郑雷不由心中一动,觉着这才是自己的父亲,这才表现了父亲的性格,不由喜道:“爹!这些日子你怎么呆在……”
就在他的话未尽意,忽然谷底暴起第二声尖锐刺耳的钟声。
钟声甫起,“花衣神”的双臂突松,挺胸直立,硬生生的眼望天色,木然喝道:“雷儿,今晚只谈家庭私事,不准提起江湖的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