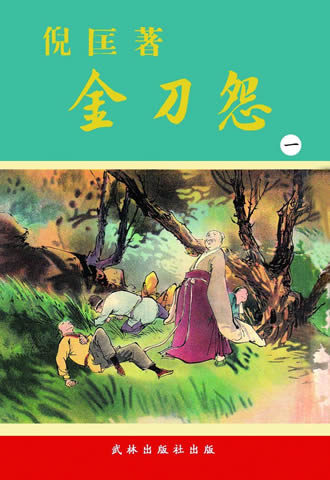因此,令狐英想急于知这道位王棋,究竟是不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兄台说棋艺生平未逢敌手,但小弟知道还有一个人也以‘棋’字为号,不知王兄可跟他较量过?”
“谁?”
“四艺的第二位!”
王棋本来正举杯欲饮,闻听讶然色变,双目中突现异光,道:“四艺之名,老弟在什么地方知道的?”
令狐英心中暗惊,心说:“这一下问对了,我应该从‘棋’字上早想起才对。”
当下暗作戒备,但表情上仍没事一般,故意笑了一笑道:“王兄别问我怎么知道?是我在问王兄可会过这人?”
王棋忽然哈哈笑道:“老弟与那个穷书生是什么关系?”
“也是适才在这儿遇上,若不是王兄找来,我还不知他姓王呢?”
“老弟真不知他是谁?”
“正想请教王兄呢!”
那王棋正想说话,口才一张,窗外已传来一声冷笑,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又在这儿遇上了!”
王棋脸色陡变,右手倏扬,一阵嗤嗤响声,每个窗格上立即现出指头般在小孔,身形一矮,人已顿失所在。
动手之快,连坐在他对面的令狐英,也未看他是如何打出一把棋子和如何离去的。
令狐英晃身追出,只听前院屋脊上传来王棋的笑声道:“终于等到你了!”
适才那冷笑声渐渐远去的说道:“可惜你来迟一步,若是你们二艺联手,也许你这趟没白跑!走吧!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
令狐英这次听清了,那冷笑之人正是那个穷书生,不由大吃一惊,心说:“二艺?难道那华服少年就是书艺?也都是女人?怎么我一个也没看出来。”
心中在想,人也跟着霍地拔起,等他落在对面房脊上时,夕阳光下,那里还有人影,就在他略迟一步瞬间,两人已走得无影无踪。
令狐英呆呆的站在房脊上,夕阳,拖长着他的影子,他忘了这是白天,也忘了是在侯府隔壁,口中喃喃自语道;“遇四艺中人而不败,这穷书是谁呢?”
令狐英站在房上心中好生纳闷,他不知这是巧合?还是人家故意安排,假若这侯府中是施翠琴,而半天不到棋书二艺也在这店中现身,若然不是巧合,那么那位金剑令主,是想用全部力量对付自己了。
但继而一想,又觉不对?因为不但那华服少年的书艺并不认识自己,连那适才离去自称王棋的棋艺,更不像为自己而来,若然那是冲着自己前来,他就不会好整以暇的跟自己下棋饮酒而无所动作,这是怎么回事?使他纳闷不已。
至于那个穷书生,他是更感不解?从不相识,居然对自己十分友善,武功似还在四艺之上,不然他怎敢与书艺约斗而去?一个人无事回来,显而易见,他是胜了,但他到底是谁呢,他是真与这些人有过节?还是为助自己而来?
就在这时,忽听下面右上房门一声轻晌,他才蓦然警觉,赶紧伏身下去,他不是怕,而是大白天站在房上有些不便,另外则是那右上房住的是受伤的华欣,是那书艺的随从,他想暗中看看,是不是那华服少年的书艺回来了?
他刚伏身下去,只见那右掌被穷书生一指点穿的华欣,正由房内探出头来张望,一脸惊惶之色。
不用说,是他一直在房中疗伤,适才听见了穷书生的声音,当时不敢出来,等到人家走了,才偷偷探头张望,一方面也是想看看他的主人是否回来。
换在别的武林中人,这时他正满脑子疑问?正好趁机下去,捉着书艺这个从人,逼他说出他想知道的一切。
但令狐英一点也不想这么做,这是他一生光明磊落的胸怀使然,一则华欣是一个受伤的下人,他不屑这么做,再则他令狐英从来不威逼人,他觉得这么做,有欠一个侠义中人的光明行为。所以,他趁华欣缩头回去之后,飘身落地,依然回到那间左上房中。
哪知他才一脚跨入房中,登时一怔。
你道为何,原来那穷书生正悠闲的坐在桌边,独自在饮酒,一见令狐英跨入,向他微微含笑。
令狐英一怔之后,双手一拱,正想出声。
穷书生却右手食指在唇边一竖,示意他噤声,而且向房门一指,还叫他关上房门。
令狐英转身将房门掩上,回身坐下。
耳边响起穷书生用蚁语传音之法的声音道:“你一定想知道我是谁?但我不许你问。”
令狐英虽觉有点奇怪?但人家第一句话,就封住自己的嘴,只得微微点头。
穷书生见他点头应诺,才又传声道:“相信我对你没有恶意,幸好你恢复了本来姓名,不然啊!那书棋二艺今天绝不会放过你。”
令狐英恍然大悟,敢情这书棋二艺果然是冲着自己来的,但他们找的独孤青,自己因已改用本来姓名,无意中免去了一次麻烦。
穷书生一笑又道:“我引开他们,目的是使他们不再注意你,现在他们还在四下找我呢?”
令狐英这才也用传音说道:“你不怕两人找回来?”
穷书生微微一笑又道:“短时间内不会,因为他们不会想到我敢跑回来!”
“适才你并未打赢书艺?”
“打赢他们?”穷书生莞尔一笑道:“我根本打不过他们!”
令狐英微觉吃惊,道:“那你如何脱身的?”
穷书生神秘一笑道:“我就是比他们跑得快!”
“这样说来,阁下是冒险相助了!”
穷书生又是一笑,道:“别客气,假若少侠不嫌我是个穷酸,我倒想以知已论交呢?”
“可是……”
“你怀疑?”
令狐英道:“在下一生信己信人,但武林中波云诡谲,前车之不远。”
“嗯!够坦白!”穷书生又笑道:“你是指那个吕不澜与你论交之事!”
“咦!兄台怎么知道?”
“有心人焉有不知之理。”
“兄台别见怪!”
“假若少侠不见疑,这兄台二字似乎应该免了!”
“可是阁下也称我少侠!”
“那我们以兄弟相称如何?我年龄比你小,来,咱们来个杯酒订交。”
令狐英心中虽仍疑怀难释,但他一生坦诚惯了,又见穷书生一脸诚恳神色,当下也饮了杯酒,点头道:“老弟仍不肯以姓名来历相告?”
“就是这一点不许你问!”穷书生神秘一笑,又道:“当然,以后你是会知道的。”
令狐英见他笑得很神秘,忽然心中一动,疑他是侯府中人,爽然一笑,故意用话试探道:“是不是我今夜就会知道。”
“今夜?”
“唔!”
穷书生眼滴溜溜一转,伸手向后窗一指道:“老兄说的是这儿?”
令狐英一听,更认为自己猜对了,心说:“不管你们有备无备,反正今夜我总得查个水落石出,到底上午看见的那姑娘,是不是真的施翠琴,和那琴音诱我去此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当下,毅然道:“不错,老弟是侯府中人,那最好请便,咱们应该说,晚上见了。”
哪知那穷书生忽然咧嘴一笑,好一口洁白的牙齿,一笑之后才摇摇头道:“老兄真是多心,你看我这一身穷酸相,会是侯门中人么?”
令狐英笑道:“真人谁肯露相?”
“唔!这句话倒是不错,好吧!既是令狐兄见疑,咱们后会有期。”
说完,身形倏晃,便到了门边,回头一笑,人已飘身而出。
等到令狐英起身追出,那里还有穷书生的影子。
这穷书生倏忽而来,又飘忽而去,真是神龙不见首尾,不但行踪如此,连行事也令人莫测高深,谈了这一半天话,对他的出身来历,和此来的真正目的,一点也未探出来,不由又把他怔在门口,目注着那渐渐被夜幕笼罩着的天空出神。
就在这时,只见那个么司燃着一盏油灯走来,一见令狐英站在房门口,笑道:“公了爷,天黑啦!我给你送灯来了。”
令狐英见他只送来一盏油灯,故意问道:“隔壁的客人还没回来?”
么司做了一个不屑的表情,道:“真倒霉,为了争房间还打架伤人,结果,那人一去不回,那个受伤的也走了,小费也没赏一个。”
这么司倒是说得坦白,令狐英一笑置之,也不愿再说下去。
等到么司走后,令狐英掩上房门,轻轻推开后窗,只见侯府后园静悄悄的,一点声息也没有,只有那右前方一座高耸红楼,绿纱窗中,隐隐有灯光射出。
他不由想起白天么司的那一番话来,微微一笑,闪身飘出。
令狐英刚刚落上墙头,蓦觉一股锐耳啸风迎面射来,心中一惊,右掌倏扬,轻轻向旁一引,施展出吸字诀,将那股锐利指风引了开去,身形左晃,人却翻落园内。
就在他飘落瞬间,耳中却听到一声嘿嘿道:“好小子,你能逃得过老夫这追魂一指,算是老夫小看了你,老夫生平不出第二次手,这是你的造化。”
等到令狐英停身回头,循着话声处看去,那儿根本又没人,只有两株小树,在夜风中摇晃。
令狐英心中思索,暗忖:“追魂一指,可能就是这人的名号,他生平不出第二次手,更证明自负清高,不是一个庸手。证明店中么司所言,并非虚语,可是他却没听人提起过这位人物。”
心中在思索,其实双目却在四下察看,未见再有动静,才一晃身,飘落在一座假山之后。
令狐英来此的目的,先还只是想查明一下那琴声诱已前来的目的为何?迄见了那位姑娘像施翠琴,便坚定了他夜探侯府的决心,偏生在店中,又听过侯爷夫人是一位琴中圣手,连琴仙也自叹不如,又说自己看见的那位姑娘,是过继而来,但连府中人也不知她来自何处?一连串的疑问?他更觉这侯府不只是一个侯门而已,有理由相信它与武林中关!而且其中还蕴藏着很大的秘密。
等到适才被追魂一指拦截,更证明他的想法没错,若然这侯府与武林无关,何以会有名号追魂一指这种厉害人物在此为他守护后园,官府中人虽说常有护院的设置,但绝对不至于落到像追魂一指这等人物来充护院。
他心中在盘算,双目却注视着那绿窗人影,但两耳则留心着四外,一点也不敢大意。
但奇怪得很,照说自己行藏己被那追魂一指发现,这府中应该再有人现身拦截自己才对,何以静得像没事一般?这种异乎常情的现象,更使令狐英感到十分蹊跷?也觉得静得有些神秘?
虽说情形有些异常?但令狐英既然已经进来了,总不能折身回去,真所谓艺高胆大,一晃身形,便扑落那八角亭中。
但他第一目的,便是那座红楼,又非过去不可,心中正在思忖,忽听红楼上绿窗,“呀”地一声开了,迎窗站着一个绿衣人,虽然她背灯而立,看不清面貌,但从那婷婷玉立的倩影上,可以看得出是一个少女。
忽听那绿衣少白女莺声呖呖的说道:“秋月姐,时间快到啦,你准备香炉,我去拂试琴台!”
跟着窗纱上人影一动,楼房内又传出一个少女娇滴滴的声音道:“是呀!春花姐,怎么冬梅妹和夏荷姐还不回来呢?去通知园中人离开,怎么费这大的时间?”
令狐英一听,便知红楼上有人要弹琴,只不知弹琴的人是谁?而那窗前的姑娘,仅是个婢女而已。
正在思忖,忽然心中一动,暗说:“不对?‘通知园中人离开’,这是怎么回事?弹琴为什么要让人离开?难道这就是追魂一指之后,不再发现有人的原因?”
继而又想:“假若自己这一想法对了,那么等一下楼上弹出的琴曲,一定不是什么对月遣怀的逸兴之曲,而是像庐山隐仙崖上的离魂曲,甚至还是残形操。”
心中恁地一想,立时浑身直冒冷汗,白天,令狐英在三义墓前领教过,自己的九全真气根本无法与人家琴声相抗,那么少时琴声一起,自己不是被毁灭,便是只有束手就缚的份儿。
就在这时,身后似有一片落叶飘落!
令狐英一惊,蓦回头,只见自己身后数尺处,一株亭柱之侧,隐立着一个人,正伸头对着自己咧嘴而笑。
令狐英一眼便看出,正是下午在客店中那个穷书生,心想:“果然没有料错,你真是侯府中人。”
既然料定穷书生是侯府中人,又被人家欺近身后,令狐英便想索性立起,但当他才想长身而起时,耳边已响起那穷书生的传音道:“假若你不想死得快一点,最好别站起来!”
令狐英一听他仍用传音说话,而且不要自己站起,不由又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判断错了,当下也用传音道:“阁下难道不是这侯府的人?”
穷书生咧咧嘴,嘴唇微动,又道:“咦!怎么又改了称呼,这阁下二字,多生分!”
“这么说咱们用兄弟相称?”
“老兄忘了咱们曾经杯酒订交!”
“不错,老弟,你既不是这府中人,来此做什么?”
穷书生又一咧嘴,阴影中,那一口牙齿,便显得其白如玉,传音道:“老兄不是约我晚上见么?我还指问着是不是这儿?可对!”
令狐英一怔,心说:“那不过是我一句试探之言,哪是真约你了,你倒认真了!”
穷书生的声音笑道:“再说,咱们既然杯酒订交,便应该义同生死,你来送死,我岂能苟生?”
令狐英道:“老弟,别说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兄不是明知故问!”
“可是指楼上有人弹琴!”
“是啊!听了残形操,咱们全都会无疾而终。”
“是那位侯爷夫人?还是施翠琴?”
“不是!”
“难道是琴仙?”
“当然不是!”
“谁?”
“琴仙的宝贝女儿!”
“施翠琴不是琴仙的女儿?”
“谁说的?”
“我们都这样判断!”
“但判断不一定是事实!”
“老弟你怎么知道的?”
“要证明么?”
“我只是想知道得详细一点而已。”
“好!那么你看!”
令狐英回头看时,只见楼上房门已开,正缓步走出四个绿衣女人,第一人抱拂尘,第二人捧金炉,第三人抱着一柄红光闪闪的短剑,第四名则双手捧着一张古琴,鱼贯走向楼前,但这四婢的出现,并不能证明施翠琴不是琴仙的女儿。
令狐英当下回头又用传音间道:“老弟,你叫我看什么?”
“喏!你再看,那不是出来了么?”
令狐英再又回头,则是一个一身白衣的姑娘,那姑娘螓首低垂,莲步跚跚,缓缓随着两婢向前走来。
令狐英目注那姑娘,用传音问道:“不错!她正像施翠琴!”
一声轻笑,那穷书生的声音道:“相貌相似,你就那么肯定?”
“但施翠琴为四艺之首!”
“你是说她会琴?”
“唔!”
“假若施翠琴是琴仙的女儿,一曲残形操,足可震服武林,何必再屈居人下?再说,那夜在林中,也不必布置那些爆炸,仍然被你们占去上风了。”
“这……”
“可以证明了么?”
“也许她有顾忌,不敢以琴仙的绝学胡作非为!”
“那么再看下去!”
一会儿工夫,只见那姑娘轻抬螓首,慢理云鬓,然后,舒皓腕,抚古琴,叮叮咚咚,轻试着琴音。
静极,也美极,有如仙子降世,令人对她肃然起敬,那里还像杀人不眨眼的魔女。
心中正在思索,忽然耳中听到一阵淙淙流水声,隐隐传来。
令狐英一怔,心说:“这荷池的水,难道是流动的么?”
忽又觉那流水声中,有鱼跃声,有松风声,有鸟语声,最后又隐隐传来渔歌。
令狐英好生奇怪,这花园中有荷池,听到流水声,鱼跃声,松风鸟语俱不足为奇,但何以会有渔歌?这儿距江边甚远,虽是夜静,但当他回头看到那隐在亭柱边的穷书生时,他正冲着令狐英咧嘴一笑,传音道:“咦!你没听见?”
“什么呀?”
“渔歌声!”
穷书生微微一笑,向楼上一指道:“不是渔歌,是琴!”
令狐英这才蓦然明白过来,脸上不由一红,回头时,果然见那姑娘皓腕微动,玉指轻移,那些声音,正是由琴弦上跳出。
令狐英心说:“这姑娘果然琴艺不凡,琴声中,竟传出高山流水,孤松白云的仙境,而且使人如置身其中,若非琴中圣手,绝难到这种境界。”
这时,忽听楼台上,那姑娘随着琴音唱道:“余之生兮不辰,余之遇兮多烦忧,怀故乡兮天涯,之子何所兮……”
刚唱至此,“铮”地一声轻响,琴弦忽然断了!
令狐英知道琴弦忽断,必有变故,正抬头张望,忽觉穷书生一闪而至,紧靠着令狐英隐在石桌之后,低声道:“快低头,有人来了!”
就在这时,楼台上忽传来一声轻喝道:“什么人?”
两声娇笑之后,楼下已有人应声说道:“施姐姐,你真好雅兴,怎会到这儿来抚琴?”
令狐英偷眼且看,楼下月光中,并肩站着两人,心中一怔,忖道:“怎会是他们!”
穷书生低笑道:“看清楚了没有?”
“棋书二艺!”
“不错!”
“啊!对了,她们应该是女人才对。”
“谁说不是,难道你没听见适才的笑声和说话声音?”
楼上忽又传出一声轻叱道:“你们是什么人?”
令狐英一看,正是那抱剑女婢站在楼栏边上,面向楼下两人说话,那抚琴的姑娘,仍端坐不动,大约这两人扰了她的清兴,在嘟着嘴儿生气。
只见并肩立在右面的华服少年脆声笑道:“是我啊!换了装难道就不认识了?”
“呸!谁认得你们,可知这是什么地方?”
“咦!”华服少年退了一步,看了旁边的王棋一眼,又道:“我是方秀书,她是王玉琪,我们听到你施姐姐的琴声,所以寻来,怎么会不认识我们?”
令狐英一怔,心说:“怪啊!原来她当真不是施翠琴?难道……难道施翠琴真不是琴仙女儿?”
楼上女婢冷笑一声,仍叱道:“谁管你书呀棋呀的,深夜闯我们后园,又扰了我们小姐琴兴,罪不容死,你们是自行了断,还是等我下来动手?”
穷书生这时在令狐英耳边轻说道:“听见么?若然人家知道还有我们两人躲在这儿,还不是一样!”
那王玉琪忽然脆声说道:“这么说,楼上弹琴的,不是施姐姐了?”
楼上又是一声“呸”,那女婢冷笑道:“去你的,我家小姐是侯府千金,谁说姓施了?”
方秀书一声冷哼道:“原来我们弄错了,听到琴声,误以为是施姐姐在此操琴,偏偏这位楼上的姑娘,又长得与施家姐姐一般无二,才现身相见,虽是一时误会,也没什么大了不起,你这丫头息能如此目中无人,哈哈!侯府?在我们眼中算得什么?凭这块牌子还骇不倒我们!”
令狐英低声问道:“这楼上的姑娘,听说是十年前过继来的,而且是琴剑双仙在候府住过之后的事,王兄可知道?”
穷书生点头道:“传闻如此!”
令狐英又道:“那么这姑娘会不会才是双仙的女儿?”
“我也有这种想法,但那不是因为双仙来过侯府之故,而是这姑娘也会琴仙绝学。”
“会弹离魂曲?”
“也会残形操!”
“真的!”
“那就是我适才说,你来送死的原因!”
令狐英道:“王兄何以知道?”
穷书生咧咧嘴,低声道:“这个你别闻,看吧!她们再僵下去,只怕我们也要陪同尝试一下那‘残形’琴音的滋味。”
令狐英大惊道:“那我们快走!”
“走?!”穷书生笑着低声道:“走得了么?”
就在此时,楼上女婢又娇叱道:“你们是什么人?”
方秀书冷笑道:“你还不配问我们是什么人?你这丫头若是再敢出口伤人,小心我割下你的舌头来!”
只见那王玉琪忽然在方秀书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才仰首向楼上说道:“你也别问我们是什么人?反正我们来此并无恶意,既然弹琴的那位姑娘不是施姐姐,算是我们弄错了!”
掉头又向方秀书道:“书妹,咱们走吧!”
话声甫落,两人同时掠起!
就两人离地丈许同时,那端坐楼上的侯爷小姐,玉指轻轻一动,君弦“铮”的一声轻响,只见那掠起的棋书二艺,忽然身子一个滚翻,依然落回地上。
令狐英是过来人,知这两人是被琴音震散真力,才落回原地的。
楼上那女婢冷笑道:“现在你们知道了么?侯府后园,是来时容易去时难,仗着一点武功就想剑这儿来撒野,呸!真是自不量力。”
那方秀书和王玉琪二人,落地之后似是大出意外,两人忽看了一眼,那王玉琪忽然双手向上一拱道:“原来这位侯府千金,果然来自连云峰隐仙崖,我们真是失敬了!”
这时,那位侯爷千金,才经缓缓站起,双手轻抚琴台,娇声说道:“两位方才说我像-位姓施的姑娘,可是真的?”
王玉琪道:“不错!”
“她也会琴艺?”
“是的,弹琴与姑娘一样的美妙!”
“但两位怎知我是来于连云峰隐仙崖?”
“武林中对双仙来过侯府之事,早有传闻,姑娘又是双仙来过之后,又才进入侯府,而且又身习绝世琴艺,早已引人猜疑,现在经姑娘一拨琴弦,便能震散我们真力一点看来,姑娘一定是双仙之女无疑了,只是姑娘何以不在隐仙崖享那神仙般的静恬生活,却到这纷乱的尘世来,令人有些不解?”
那姑娘抬起手来,理了一下鬓发,轻叹一口气道:“那是我爹娘说我一个女儿家,不应该过那种高山上的枯燥寂寞离世生活,才将我托付给这儿的义父母,啊!你们那位姓施的朋友住在什么地方,我倒想聆听一下她的琴音呢。”
“这个……”
王玉琪看了方秀书一眼,好像交换了一下眼色,才道:“假若姑娘不究今夜我们误闯后园之罪,我们自然去通知施姐姐,要她亲来领教姑娘的琴艺就是,至于她的往处,歉难随便告人,请姑娘原谅!”
“啊!”那姑娘略作沉思之后,点头道:“好吧!你们可以走了,但两位今夜确知我的来历,请不要传扬出去,我不是怕什么,而是我不愿与武林中人往来,这就是我这后园,不许人随便进入的原因。”
说完,那姑娘挥手示意,随即缓缓坐下。
那站在月光下的王玉琪向上拱手道:“如此,我们告退了!”
声落,两人再次掠起,在月光下闪得两闪,便已由对面飞走。
穷书生轻轻吁了口气道:“谢天谢地,总算她们没有谈僵。”
令狐英听了她们那一番话,不但证明自己先前的猜想没错,而且更证明施翠琴不是双仙的女儿,只是有一点仍使他疑团难解?何以双仙这女儿,会与施翠琴长得一般无二?这其中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楼上忽然传来声音道:“小姐,还要弹琴么?”
那姑娘的声音道:“不啦!琴兴被扰,还是回房去吧!”
但就在此时,只听楼台上所有的人,一齐回头向后看去,好像有人正在此时上楼。
果然,一会儿工夫楼头转角处灯光一闪,现出一盏宫灯,那持灯的女婢高声道:“禀小姐,老夫人来啦!”
跟着楼角处传出一群女婢,拥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夫人,她手拄一枝龙头拐仗,问道:“琴儿,适才可是有人偷听琴音?”
那姑娘连忙站起,离开琴台迎了过去,一面笑道:“是啊!娘,你说可笑不可笑,来的是两个女扮男装的人,她们误认为儿是一位姓施的姑娘呢?”
“啊!有这等事,人呢?”
那姑娘道:“孩儿让她们走了,因为她们只是弄错了,并投什么恶意。”
老夫人这时已到琴台之前,那姑娘亲手扶她坐下,一个女婢忙又搬出一把椅子,给那姑娘坐下,只听那老夫人又问道:“她们是谁?”
适才那抱剑的女婢却道:“回老夫人,她们自称是方秀书和王玉琪!”
那老夫人点点头,好像毫不在意的,忽然向园内四下张望一阵,又问道:“可还发现另外有人?”
穷书生一惊道:“糟了,咱们可能被府中人发觉了?”
令狐英微微一笑道:“岂止发现而已,我根本是人家请来的。”
“请来?”穷书生一惊,用疑惑的目光看了令狐英一眼道:“兄台是说,这府中请你来的?”
“那与请来差不多!”
于是低声将自梅林边听到琴声,自己便跟踪来此之事说了一遍。
穷书生听到追魂一指之名,脸色大变道:“兄台是说,他在守护这园子?”
令狐英心中大感不解,这穷书生对书棋二艺尚且玩弄于指掌之中,何以对一个追魂一指如此惧怕?当下点头道:“一点不错!”
“适才兄台进这后园时,他真曾出过手,而且兄台以引字诀将他的指风轻易引开?”
“有什么不对?情形确实如此!”
“那就怪了。”
“怪?”
“唔!兄台可知道他是生平不出第二招的!”
“适才他自己说过?”
“一个没有特殊造诣的人,敢如此自信么?”
“但我确实仅用引字诀,便避开了他那一指!”
“这就是我说怪的原因,不然追魂一指不是一个狂妄自大之人,就是一个浪得虚名之辈。”
令狐英听穷书生恁地一说,心中也不免奇怪起来,忽听楼上那老夫人哈哈大笑道:“孩子,你弹一曲离魂曲试试,保管这园中另有佳宾!”
穷书生咧嘴一笑道:“原来如此,现在不用怪了!”
令狐英道:“老弟是说那追魂一指是故意放我进入?”
“大约如此!”
“但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问人家用琴音引你来为什么呢?”
“啊!是的,追魂一指是奉了那老夫人之命。”
“那不就得了,可是人家要以离魂曲迎宾呢?”
“那是逼我们现身!”
“知道就好,兄台能抗拒人家的琴音么?”
“听说离魂曲能使入迷失心神?”
“比釜中游鱼更坏来做些。”
“那么老弟何苦也来做罐前鱼肉呢?”
穷书生苦笑着看了令狐英一眼,轻轻一叹道:“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看,人家又开始焚香抚琴呢。”
令狐英抬头看去,果然楼台上一个女婢,正又新燃起一炉清香,那位老夫人已移痤琴台之侧,那位自称是双仙之女妹的姑娘,正襟危坐,月光轻轻的照在她的脸上,有如一尊玉雕仙女,令人又不由起一种肃然之感。
穷书生伸手递给令狐英一物,低声道:“快衔着这个,然后气结三花,神归真璞,诚意澄心,不使外感相浸!”
令狐英一看,穷书生给他的,乃是一枚其色乌黑的指环,入手甚沉,似是钢铁铸成,当下疑惑的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穷书生道:“九毒钢环!”
令狐英一怔道:“环上有毒?”
穷书生肃容道:“不错!不但有毒,而且是剧毒,天下无药可解。”
令狐英见他肃容相答,说得非常认真,不像是玩笑话,不由大惊道:“那么老弟你……?”
话未说完,楼上君弦“铮”地一声轻响!
令狐英陡觉那一声轻响,似是一只铁棒,蓦撞在心上,身子不由向上一跳。
穷书生适时伸出手来,按在令狐英肩上,低声道:“快放人口中,别怕,要是我想加害兄台,也就不必告诉那钢环有剧毒了,要知毒能害人,亦能教人,药中有的是含毒之物,但医生对症下药,却能起死回生。”
钢环入口,令狐英暗觉一股冷气,直下丹田,身上机冷冷一战,立时有如五毒攻心,逼得他不敢旁鹜,全神凝气护心。
此时恍如仙乐渺渺,自空而降,那声音入耳,立即有使人飘飘欲仙乘风而起的感觉。
但那一般冷气,这时似已将他的四肢僵硬了,使他欲起不能。
一会儿工夫,仙音渐渐远去,立时万虑居寂,天籁无声,又恍如置身在一个玻璃世界中,眼前是一片山环水抱,风景绝佳之地,纷纷白雪,满天飞舞,将四周装饰成粉装玉琢,风过处,隐隐一阵沁心花香,好似不远处正有梅花盛开,心中不由兴起踏雪寻梅之兴。
但兴念才起,忽然觉得体中有无数条冰蛇游走,身子又机冷冷一战,才蓦然醒觉过来,原来自己依然盘坐在亭子石桌之后,而且就在此时,那护心真气,几乎被那钢环所发冷气攻入。
不由大吃一惊,敢紧澄心静虑,默运九全真气,将那股冷气逼退。
忽然,他听到身侧发出轻微响动之声,掉头一看,原来那贴身而坐的穷书生,此时满脸笑容,正自由地上缓缓站起,但双目发直,神情十分异样,显而易见,是被那琴声所诱,人已入幻境。
令狐英大吃一惊,赶紧伸手将他拉住,不使他站起。
那穷书生好像巳浑身无力,令狐英这一拉,他虽未站起,但微起的身子,却向令狐英怀中倒来。
令狐英只得伸臂将他搂着,穷书生的一张脸,正倚在令狐英胸膛之上。
又是一阵奇怪的香味袭来,但却不是花香。
就在他闻着那阵奇怪香味瞬间,琴声“叮咚”,又传人耳中,心神立又一荡。
此时,他那还敢去分析那奇怪的香味是什么?左臂紧紧接着穷书生,右手则握着穷书生的左手,全力运行九全真气,由穷书生左手传人,分护他的心神。
这时,那琴声忽然音高节促,耳中先是所见风声啸耳,松涛怒吼,跟着隐隐夹着万马奔腾声,怒马嘶鸣声,喊杀声,锣声,鼓声,那声音由远而近,恍如千军万马正向自己奔来。
令狐英不觉又由这些惊人的声音所幻,好像自己正遇上一场惨绝人寰搏杀,应该赶快走避。
但却苦谥双腿冰冻麻木,欲避不能。
忽然,身子一阵动荡,霍然一惊而醒,睁眼一看,原来是那穷书生在怀中挣扎,似是想脱离令狐英的左臂,狂奔而去。
令狐英心知也是被那琴音所幻,只得用力将他抱着,不让挣脱。
这时,楼上突然传出一声惊“咦”道:“怪啊!怎不见有人现身?”
令狐英抬眼看去,只见那位老夫人和那弹琴的姑娘,并肩倚栏而立,正自四下张望,几个婢女也紧倚在两人身侧,那惊“咦”之声,似是发自一个婢女。
令狐英这才知道一曲已终,忙将九毒钢环吐出,真气四逼,立将那股冷毒之气,遇出体外,自己竟丝毫无害。
这时,楼上响起那老夫人声音道:“唔!真是怪事?”
那位弹琴的姑娘娇声道:“娘!怪什么啊?又有谁会在这园中呢?”
那老夫人道:“孩子,是一个英俊不凡的年轻人,娘故意将他引来,想考验一下他的所学。”
那姑娘又脆声道:“年轻人?娘想考验他做什么?”
“哈哈!”那老夫人哈哈大笑道:“武功还算得过去,但难能可贵的他竟有这种超人的定力,竟然能与离魂琴音相抗?好!好!算是找到了,娘多年的心事,大约可以了。”
那姑娘似是才忽然领悟老夫人的用意,娇羞的一扭纤腰,匆匆向房内跑去。
群婢女拥簇着那位老夫人,也缓缓跟去,隐隐传来一阵笑声。
倚在他怀中的穷书生,忽然一挣坐起,向他神秘一笑道:“兄台听见么,小弟应该替你贺喜了。”
令狐英道:“喜从何来?”
穷书生向楼上一呶嘴,道:“你没听见?人家老夫人已选中你作侯府娇客了呢!”
令狐英一怔道:“谁说的!”
穷书生脸色一肃,掠过一抹凄然神色,道:“你在装糊涂!”
令狐英迅速回味了一下适才楼上老夫人那几句话,心中栗然一惊,道:“老弟,我们快走!”
说完,当先向那粉墙下掠去。
等到穷书生扑到,令狐英已安然越过粉墙,进入那间客房之中。
两人刚翻过粉墙,那红楼绿窗内有两人轻轻对话,道:“这一幕安排得如何?”
“可算是天衣无缝,多亏你老人家帮忙!”
“现在不用担心有人上连云峰了!”
“是的!”
“也许这一来,还会完成你的私愿呢?”
“唉!只怕还远得很?”
“为什么?”
“他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 。
“但谋事在人,我不相信一个年轻娃娃,会逃得过这脂粉陷阱,必要时,我们再来一幕戏。”
但隔着一道粉墙的客房中,此时,桌上一灯如豆,隔桌对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令狐英!
另一个,却是那个谜样的人物——穷书生。
“啊!老弟与那叫王玉琪的棋艺,有什么过节?”
“在他的西北第一庄中,我伸手管了一件事!”
“西北第一庄?”
“唔!跟西南第一庄一样,是金剑令主在西北建立的基地。”
“这么说,一定还有东南和东北了?”
“是的,那是书画二艺在主持!”
令狐英冷然一笑道:“金剑令主野心真大,设想也够周密!”
穷书生微微一笑道:“网罗的人物更不少,可是,就有人自不量力,想与金剑令主作对呢!”
令狐英长叹一声道:“不,在下是有些自不量力,但在下本意,不是想与金剑令主争什么?只是想为天下武林,略尽棉薄!”
“还想振兴武德,使武林中化戾气为和祥,一身任武林中安危,因此公而忘私,把自己许多事都忘了。”
“咦?老弟这话是指……”
“怎么,说错了?”
“不!”令狐英又是一声长叹,道:“老弟责备得对!令狐英却是有许多私事,可惜,一到成都,就卷入这场是非之中。”
“我倒想听听兄台有些什么私事呢!”
令狐英犹豫着,他本想说出自己这次离家寻母访仇之事,但这穷书生到底来历不明,因此,又不想说了。
那知穷书生一笑道:“我是想知道,兄台除了查访杀父仇人,和找寻令堂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
令狐英一怔道:“老弟,你到底是谁?怎会知道许多?”
“我知道的事多着啦!”穷书生神秘一笑,又道:“还有许多姑娘们,为兄台而倾心,是不是?”
令狐英点点头道:“不错,可惜令狐英在心愿未了之前,还不想涉及儿女私情。”
“唔!兄台真是一个义薄云天的侠义之士,我问你,假若兄台那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到了八九十岁仍不能如愿时,是不是让倾心你的姑娘,也一直等到那时?而且,据小弟所知,倾心你的姑娘有好几位,在她们中兄台有没有选择和决定?”
令狐英心中好生纳闷?觉得这穷书生不但问得奇怪,而且还问得咄咄逼人,忍不住双目神光炯炯,直射在穷书生脸上。
穷书生忽然低下头去,好像在故意避开他那一对锋利的星眸。
令狐英虽是一个心怀坦荡之人,这时又不由疑心大起,他倒不是疑心穷书生是敌人,而是怀疑他是受自己认识姑娘中那一位托付而来。
当下笑了一笑,坦然道:“老弟,你是受那一位之托?”
穷书生低着头道:“谁说我受人所托!”
“但老弟不觉问得奇怪么?而且适才老弟所感慨的不情不义之人,原来是指在下而言。”
穷书生忽然抬起头来,冷笑道:“不错,那是指你!”
“但在下并没有不情不义!”
“让一个姑娘为你憔悴,为你伤心那就是不情,害人家一生,最后含恨死去,那就是不义。”
令狐英道:“老弟说的是桃花令主?还是黄幼梅姑娘!”
那知那一句才出口,那穷书生目光一呆,身子摇摇欲倒!
令狐英大吃一惊道:“老弟,你……怎么了?”
穷书生凄然一笑,嘴唇紧抿几下之后,忽又毅然道:“没甚么!只是有点头痛,大约是适才抗拒那离魂琴音时,耗费不少真力,我想歇息。”
这句话令狐英倒是不疑,因此他自己也觉得有昏昏欲睡的感觉,当下笑道:“好吧!咱们抵足而眠,有话明天再谈!”
那知那穷书生忽双手乱摇道:“不成?小弟不习惯与人共榻,兄台请安息,我就在这儿行功调息就行了,再说,那棋书二艺说不定还会找来呢?”
令狐英听他提到棋书二艺,倒是认为大有可能,当下又道:“不错,老弟虑得是,那么老弟去床上休息,我坐在这儿守护如何?”
穷书生点头笑道:“那就有劳兄台了。”
说完,便去到床上倚枕而卧。
令狐英面对着一盏残灯,心中直在思索这穷书生的来路,但始终得不到一个结论,惟一可以相信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穷书生之忽然前来,对自己并不存什么恶意。
夜!静悄悄的。
忽然,街头传来一阵术梆声音,令狐英一听,已是四更了,心说:“要不是遇上这人,自己应该赶去黄衫神翁庄上看看,佟叔是不是已将幼梅救出?”
当然也想到其他,但想得很乱,乱得使他心烦,但渐渐的他也感到困乏了,两只眼睛开始朦胧起来,他索性闭起双目养神。
就在他双目闭起不久,人在朦胧之际,夜空中,响起若有若无的洞箫声,幽怨,凄凉,尤其在静静的深夜中,那声音更是令人回肠荡气,不忍卒听,是谁?在深夜中诉出了断肠之声?
令狐英虽然也隐隐听到,但他实在太困乏了,因为是箫声,他并来睁开双目。
但床上的穷书生却突然睁开双目,看了令狐英一眼,轻轻的下了床,动作十分小心的溜出房门,在夜空中一闪而逝。
等到令狐英霍然惊觉,奔出客房时,穷书生已不知去向,他奇怪的站在阶前。
站了一回,只好转回房中,依然倚桌而坐。
晨鸡报晓,曙色窥窗。
令狐英蓦一睁眼,那穷书生依然好端端的坐在床上,何时回来,他竟一点也不知道。
令狐英心中暗惊,当真他的轻功造诣,已到了神出鬼没之境,竟然在自己不知不觉间回到房中,若是敌人,那后果不堪设想?
当下轻咳一声道:“老弟,天亮啦!”
穷书生双目朦胧的打了一个呵欠,道:“啊哎!真好睡,连天大亮了都不知道。”
一面说话,一面整衣下床。
令狐英含着笑道:“是么?可是老弟为什么还半夜跑出去呢?”
穷书生一惊:“真的?”
令狐英笑了一笑道:“是真是假,老弟应该知道,可惜老弟轻功超人,我没有来得及跟去看看。”
穷书生如释重负的咧嘴一笑道:“若是真的,那就是小弟的旧病复发了。”
“旧病?”
“唔,小弟从小就有夜游之症,自己也不知何故,常常深夜跑出去溜一趟。”
有人患夜游症之事,令狐英倒是知道,当下仍疑惑的问道:“那么老弟何不求医诊治?”
穷书生笑道:“从小如此,也就习以为常,反正也没什么害处,再说,天下名医,好像还没有治夜游症的验方,所以小弟也就由它去了。”
令狐英虽不全信,但也不能一口咬定人家不是,当下笑了一笑,道:“老弟,我还有事想走啦!”
他本是想与穷书生告别,哪知穷书生点头道:“好!咱们走!”
令狐英微怔道:“老弟要跟我一道?”
“为什么不?咱们曾经杯酒订交,更应该祸福与共,再说,我也没事,在一起也许对兄台有帮助呢!”
令狐英犹豫着说道:“可是,小兄是一个满身是非之人,老弟何苦……”
话来说完,穷书生哈哈一笑道:“我何尝不如此,跟兄台一道,要是二艺同时寻来,小弟便不致怕她们了,这叫做助人助己,有何不可!”
令狐英见婉拒不能,也只好听之,当下两人到了店堂,要了两份早餐吃罢,付了银两,离店向西门走去。
两人刚走出城门,忽见前路道旁,站着三个灰衣老者,像貌奇古,双目神光炯炯,一看便知是武林高手。
令狐英微微一怔!
那三个老者中,已有一个秃头老者横跨一步,将去路阻住,嘿嘿笑道:“独孤青,你可认识老夫?”
令狐英虽觉这声音好像听过,又直呼自己过去的姓名,心中不由暗暗纳罕,但一时之间,却又想不起来,当下抱拳道:“恕晚辈眼拙,不认识你老人家,晚辈已恢复本姓名,请叫我令狐英!”
旁边另一老者哈哈笑道:“娃娃,老夫可认识你,不管你叫什么,可有胆量跟老夫等走一趟?”
令狐英道:“去什么地方?可否先请教三位老人家大名?”
另一老者也哈哈笑道:“你娃娃还不配问老夫姓名!”
令狐英虽是心中不悦,他明知三人来意不善,仍客气的说道:“但晚辈身有要事,没空陪三位老人家。”
拦在道上的老者嘿嘿道:“难道还要老夫动手,你小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一直冷眼旁观的穷书生,忽然哈哈一笑道:“三位这不是以老卖老么?请客也得客气点儿呀!”
那拦路老者双目寒光暴射,瞪着穷书生道:“你小子是什么人?”
穷书生向令狐英一指道:“他的盟弟!”
老者怒喝道:“我问你小子,是何人门下?”
穷书生耸耸肩,做出一个不屑的表情,咧咧嘴道:“跟你们说的一样,不配问我。”
这一句话,顶撞得那拦路老者大怒,突然右手疾伸,向穷书生抓来,五指才伸,便听到一阵啸耳风声。
穷书生尖嚷一声:“啊哟!以老欺小,不要脸!”
嚷声中身形一矮,反而由那拦路老者腋下一溜而过。
令狐英虽不知穷书生武功如何?但却知道他身习上乘轻功,因此,并不替他担心,反而负手旁观,想借此看看他和三个老者的武学。
那秃头老者一爪抓空,反而被穷书生溜了,骇然大怒,身形猛转,身法奇诡之极,一晃又到了穷书生面前,嘿嘿道:“小子,好俊的轻功!”
穷书生仍咧嘴而笑,道:“老小子,你也不错呀!”
秃头老者怪目圆睁,寒光逼射的嘿嘿道:“适才你小于叫什么?”
穷书生道:“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出手,又是这一把年纪,难道我骂你以老欺小,不要脸,会错了么?”
秃头老者不怒反笑,仰天一阵嘿嘿道:“好!现在我要教训你小子对老夫无理,而且先告诉你老夫要出手,小心点!”
穷书生忽然双手乱摇道:“不成?你得先说明,为什么找我盟兄的麻烦?”
秃头老者突大怒道:“放屁,老夫教训你小子是一回事,找那小子又是一回事?假若你小子怕了,跪下给老夫磕个头陪罪,老夫便放了你小子滚!”
“啊哟!好臭,真是臭而不可闻矣,老小子,我可不是怕你,你给我磕头,我还不放你呢!”
令狐英站在原地未动,另外那两个老者也静静的站着,但四道炯炯有神的目光,却一直监视着令狐英,好像生怕他趁机溜走。
那边穷书生话未说完,秃头老者已气得哇哇大叫,怒吼一声,翻腕就是一掌劈出。
穷书生仍是那幅玩世不恭神态,咧嘴一笑道:“老小子,你真……”
那知“打呀”两字尚未出口,陡觉那掌风有如奔涛迅电,手才一扬,如狂涛一般的劲力,挟着隐隐雷声,已当胸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