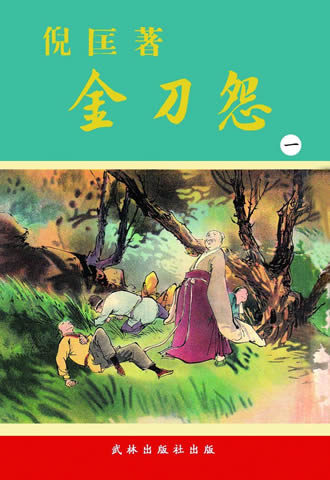声势的确吓人,若是一般庸手,不被小贺、杜老大打死,也会压扁。
很不幸,活该他俩倒霉,遇上的对手是大名鼎鼎的廖添丁与双枪坤仔。
根本不会还手,仅仅一矮身,运手“四两拨千斤”高级技巧,巧妙无比的轻轻一拨,两个大块头便应势穿窗而出,飞到监房外面去。
还好外面有栅栏挡着,又有一点武功底子,危急间,施出了游泳的技术,猛抬间,向上冲,胸部撞上栅栏,反弹回来,一屁股栽在地上。
不然,一定会脑袋开花,成为阎王爷的座上客。
或者,飞出楼外,落在地上,摔成血浆、肉饼。
晓是如此,仍然撞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昏昏沉沉的,想爬也爬不起来了。
廖添丁冲出去,仿若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抓住杜老大的领子,将他提了起来,冷厉的声音:“杜老大,还能不能再战?”
杜老大大摇其头道:“不行啦,不行啦!”
廖添丁道:“不行就歇一会儿再干,咱家绝不会趁人之危,占你的便宜。”
手一松,杜老大差点倒下,靠住墙壁才稳下来。
有样学样,阿坤也将小贺一把提了起来,面笼寒霜,吐字如刀地道:“姓贺的,你怎么样?”
副室长小贺的情形更糟,精神萎靡,有气无力的道:“我也不行啦,好像喝醉了酒。”
阿坤神气十足的道:“不行就歇歇脚,喘口气,等一下咱们再一决高下,今天一定会要你吃饱喝足,心服口服。”
松手放开,小贺险些倒栽葱,踉跄了几步,抓住铁栅栏,才将重心稳住。
室长杜老大寻思少顷,长叹一声,道:“罢了,罢了,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不必再比划了。”
廖添丁一怔,道:“姓杜的,你的意思是说,承认技不如人,输了?”
杜老大道:“是的,认输。”
“承认咱家的拳头比你大?”
“事实确是如此。”
“心服口服?”
“心服口服!”
“绝不反悔?”
“绝不反悔!”
“你最好再考虑一下。”
“不必再考虑了
“那么”,廖添丁双眉一挑,神采飞扬的道:“你这个室长是否表示已经垮台?”
“现在的室长是你蔡老大。”
“你是老几?”
“老么。”
“一条小毛虫?”
“可以这样说。”
“区长呢?”
“自然也非蔡老大莫属。”
“咱家睡床上,你睡床下。”
“当然。”
“叫你往东,不会往西?”
“一定。”
“我吃肉,你喝汤?”
“蔡老大喝酒,我喝水。”
常听人言,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廖添丁的风水却转得特别快,前后不到半不时,便由老么,小毛虫,一变而为老大,一条龙,自己也觉得好笑,蛮好玩的。
阿坤不让廖添丁专美于前,找上小贺,耍起威风来:“姓贺的,现在该你表示一下意见了。”
小贺垂头丧气的道:“小的跟杜兄一样啦,甘愿做老么,做小毛虫。”
“啧啧,太可惜了,一下子从天下掉在地下,你会不适应的,最好再考虑考虑。”
“贺某吃几碗饭,自己心里有数,没有再考虑的必要,也不想再献丑。”
“不会后悔吗?”
“绝对不会。”
“心甘情愿吗?”
“心甘情愿!”
“从今以后,我们的衣服由你俩来洗?”
“理所当然。”
“我们的工作由你俩来做?”
“可以。”
“有什么好吃好喝的,绝不藏私,会毫无保留的献出来?”
“这是内规,谁也不敢违反。”
“俺副室长,睡你的位置。”
“应该的。”
“你是老么中的老么,睡马桶边上。”
“是!”
“对蔡老大绝对服从?”
“不敢不从。”
“对我张老二也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
“阿坤耍足了威风,过足了瘾,接着廖添丁又开言道:“杜老么,报上你的名字来。”
“我叫杜照邦。”
“可有外号?”
“人家叫我大头杜。”
“嗯,你的头是不小,可惜内部不发达。”
“以后还请蔡老大多多教诲。”
“今年多大?”
“二十三。”
“家住哪里?”
“三重埔。”
“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就在下孤家寡人一个。”
同一时间,阿坤也在查小贺的户口:“你叫什么名字?”
小贺道:“贺永川。”
“有外号吗?”
“和尚川仔。”
“好怪的外号,如何得来的?”
“以前喜欢剃光头,油光发亮,所以……”
“和尚戒色,你他妈的却吃嫩草,真正岂有此理!”
“以后再也不敢了。”
“倘若再犯,小心把你那条‘棍儿’剪掉。”
贺永川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颤,本能地捂住自己的“棍儿”,没敢应声答话。
早已惊动了其他监房的囚犯,包括另外九个监房的室长老大,一齐围拢过来看热闹。
廖添丁挺一挺胸脯,昂一昂头,摆出一个威风凛凛的架式来,道:“大头杜,咱家是这一区的区长,把其他的九位室长老大介绍一下吧,免得办起事来不方便。”
此刻的杜照邦,骄横之气早就不见了,乖得像一只小猫咪,当即如言照办,将九位室长老大一一介绍给廖添丁与阿坤。
个个都是横眉竖目的家伙。
每一位老大的拳头都不小。
但在廖添丁的面前,却俱皆甘心臣服,未敢有丝毫不敬之意。
阿坤神气八啦的道:“没意思,新官上任,随随便便的介绍一下就算,太马虎了吗,别偷工减料。”
大头杜愕然一楞,道:“老大的意思是……”
廖添丁道:起码应该喊几句好听的口号。”
阿坤补充道:“再送几样好吃的东西来,以资庆贺。”
“恭喜蔡老大。”
“贺喜蔡区长。”
“恭喜张老大。”
“贺喜张副区长!”
九位室长老大,都是在外面混的人,很上路,不单为廖添丁新官上任贺,还临时给阿坤封了一个副区长的官儿,拍足马屁。”
同时,返回监房后,大头杜与和尚川仔立刻乖乖的将自己的位置让出来,请廖添丁、阿坤名符其实的当上了室长、副室长。
其他九位室长也很够意思,及时送来了不少贺礼,吃的、喝的、用的都有,琳琅满目,不一而足。
另外,廖添丁还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将原来睡在床上的几个拳头胳膊粗的家伙赶到地下去,将睡在地上的几位糟老头,请到床上来睡。
时间已到。
监房下锁。
在管理员的统一命令下,所有的囚犯,倶皆盘膝坐好,开始闭目思过。
每一个管理员都很凶,好似凶神恶煞,有那动作迟缓,或是交头接耳,以及其他不遵守规定者,一律被拖出监房,饱以老拳,甚至挨鞭子。
直到九时过后,才熄灯就寝,结束了新奇刺激的入监第一天。
由于用拳头打出一片江山,监狱的生活并不箅难过,工作有大头杜、和尚川仔代劳,日常的生活起居,更有全区的囚犯孝敬、照顾。
吃香的。
喝辣的。
颐指气使。
耀武扬威。
除了失去自由,不能随便离开监狱这个小圈圈外,简直跟有钱人家的大老爷相去不远。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室长、区长、楼主、盟主的人,也有他们的难处,日本鬼子刁蛮成性,贪财好货,最少必须每周孝敬一次,方可平安无事。
此外,室长要孝敬区长。
区长要孝敬楼主。
楼主要孝敬盟主。
做盟主最好,只要监狱各方面的关系搞好,按时送礼钱,典狱长、管理员等,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差不多皆任令这位囚犯中的龙头老大,作威作福,予取予求,俨然以监狱中的小皇帝自居。
的确很像小皇帝。
尤其在“放风”的时候,更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来。
放风,是囚徒自由活动的时间所有的犯人全部出了监房,来到中间的大操场,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
也许有人会交朋结党,也许有人会惹是生非,但总有不少人围在司令台前欢呼、致敬、献礼、献钱。
因为,在这个时刻,盟主,囚犯中的龙头老大,一定会高高在上的坐在司令台上。
虽然只是一张破椅子,在大家的心目中却与金交椅无异。
它代表权威。
也代表拳头!
这盟主的拳头很大,张开像一片芭蕉叶,握紧了比小孩的脑袋还要大,黑脸堂,络腮胡,站起来仿若一座铁塔,坐下来好似一只猩猩,魁梧昂藏,虎虎生威。
年龄不大,仅二十四五。
名叫张富,乃新竹北门外,番仔庄人。
从小学得一身好本事,刀、枪、棍、棒、拳、脚、掌、腿,样样精通。
本来在新竹县衙里当捕快,后来,满清政府跟日本人在朝鲜打仗,吃了败仗。
那位割地赔款的专家,李中堂李鸿章大人,与小日本签下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方。
日本鬼子来了。
张富却失业啦。
他的父兄也在日军攻打新竹时被杀。
于是,为了国仇,为了家恨,纠结了地方上的一批地痞流氓开始与番仔作对,打家劫舍,扶弱济贫,下手的对象十之八九都是土豪、劣绅、恶霸、汉奸与狗腿子。
张富的胃口很大,钱必上千,银必上百。
功夫也十分了得,飞檐走壁,来去如飞。
因此,赢得了大盗张富的封号。
也赢得了新竹穷苦百姓尊重。
然而夜路走多了,免不了会遇上鬼,终于在一次行动中,中了日警的埋伏,生擒活捉,判了二年徒刑。
因为新竹监狱人满为患,所以才特地将他们这一批人,移来台北监禁。
当时的龙头老大,是一位杀人犯,凶焊得很,就好像动物园里的猴王一样,谁也不敢向他的权威挑战。
谁料,大盗张富入监三天,便夺下了室长、区长、楼主。第四天立即向盟主提出挑战。
二人就在司令台上展开一场龙争虎斗。
结果,张富技高一筹,不到三十个回合,便将那个杀人犯打得灰头土脸的滚下司令台,顺理成章的坐上了金交椅,当上了猴王,干起龙头老大来。
这些事,阿坤、廖添丁已经听说了。
大盗张富的威风他二人也亲眼看到了。
阿坤道:“阿丁,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斗一斗这一头黑猩猩?”
廖添丁道:“算啦,咱们是来避难的,不宜过份招摇,免得惹麻烦。”
“你不想当猴王、盟主、龙头老大?”
“阿坤,别妄自菲薄,咱们的眼光应该更远,目标应该更大。”
没料到,廖添丁不想招惹大盗张富。大盗张富却主动的找上他。
第三天放风的时候,命人将廖添丁叫上了司令台。
大盗张富的一双眸子,比刀片还要锋利,在廖添丁的身上冷冷一刮,阴恻恻的声音道:“你叫蔡万全?”
廖添丁颔首道:“不错。”
“听说你第一天入监,便将大头杜打垮了?”
“有这回事。”
“赢得了室长,也夺得区长?”
“这是因为凑巧杜照邦身兼二职。”
“为何没再更上一层楼?”
“什么意思?”
“向楼主挑战呀”?
“没兴趣。”
“是没兴趣,还是没胆量,或者没信心?”
“就算没胆量,没信心好啦。”
大盗张富报以一声轻视的冷笑,皱着眉头说:“本盟主虽然身在狱中,外面的事情可是了如指掌,若论道上的人物,廖添丁当推第一号英雄。”
阿坤听得好舒服,在台下应道:“这是句公道话。”
张富继道:“再下来自然是飞鹰帮的老大黄猛,四海帮的老大吴涂壁,以及马正雄、唐林木、张木村、丁二喜、陈玉梅等,至于以朱星羽为首的那一帮牛鬼神蛇,就更等而下之了。”
阿坤不悦道:“还有一位大英雄,阁下为何没说,是孤陋寡闻?还是故意遗漏?”
张富朝台下望一眼,道:“朋友指的是那一位?”
阿坤往自己脸上贴金道:“双枪坤仔呀?”
张富忙补正道:“是啊,是啊,这一位双枪坤仔也很了不起,跟廖添丁是老搭档,二人来台北不久,已闯出了金字招牌,日军日警畏若虎狼。”
阿坤满意的笑笑,道:“嗯,这还像句人话。”
廖添丁疑云满面的道:“不知盟主老大此话是何用意?”
转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儿,大盗张富才说出实话来:“张某人甚是纳闷,蔡万全、张有金名不见经传,江湖上根本没有你们这一号人物,怎会在举手投足之间,便令大头杜、和尚川仔败下阵来,甘心当老么,当小毛虫,为你们端洗脚水?”
廖添丁听得一呆,道:“也许是在下的运气特别好,有超水准的演出。”
“张某倒怀疑是另有隐情。”
“什么隐情?”
“你根本就不姓蔡。”
“是姓蔡,如假包换。”
“爱说笑,细数道上好汉,没有一个是姓蔡的。”
“在下初出道,尚未斩露头角。”
“初出茅庐的小子,没有这份胆识,分明是久经阵仗的成名人物。”
“成名人物,会是谁?”
大盗张富的脚前,堆满了囚犯奉献的各种礼品,喝了一大口酒,吃了一大口肉,还点燃一根烟卷,叨在嘴上,慢条斯理的道:“江湖上盛传——廖添丁、土确壁、双枪坤仔、飞鱼张木村地(古道幽蘭按:未審作何改,且存)在逃,并未在龙山寺附近的警匪枪战中丧命!”
廖添丁截口道:“盟主千万别瞎疑猜,想我蔡万全,自信‘菜’得很,不过是一个微不足的扒手而已,岂敢与廖添丁他们相提并论。”
阿坤也大声疾呼道:“廖添丁他们那一伙人,胆大妄为,是亡命之徒,也是抗日份子,被皇军皇警逮住是会砍头的,这个玩笑开不得。”
二人矢口否认,顿使张富坠入五里雾中,沉吟一下,道:“蔡朋友,不管你是谁,本盟主欢迎你向我越级挑战。”
廖添丁愕然反问了一句:“越级挑战?”
张富解释道:“在正常情形下,向龙头老大挑战,必须具有楼主的身份,换句话说,一定要先取得楼主的资格,才可以与本盟主一决雌雄,张某对你特别的优待,愿破一次例。”
廖添丁淡淡一笑,道:“盟主高估了在下的实力,谢了。”
“怎么?你好像不愿意?”
“是在下不配。”
“何妨一试?”
“我不想自找麻烦。”
“怕暴露了你自己的身份?”
“误会了,是自己知道吃几碗饭,不想自取其辱。”
“假如本盟主坚持要跟你一决高下呢?”
“在下自认非盟主敌手,甘拜下风。”
“你想不战而败?”
“战亦无功。”
“张某非要跟你拼搏一场不可。”
“激将无用,在下不会还手的。”
“哼,这可由不得你!”
谁说激将无用,张富芭蕉叶大的铁掌一拍,廖添丁顺势借力,跳下司令台去。
张富却毫不放松,捉住他的衣领,揪住他的屁股,又将廖添丁丢回到台上去。
接又如疯狂似狂,拳打脚踢。
廖添丁依然故我,打不还手,退到台下去。
可是,大盗张富却打得兴起,欲罢不能。
将廖添丁从台上打到台下,又从台下打到台上去。
不管你还不还手,他照打不误。
不管你愿不愿意,他猛追猛揍。
“臭小子,不还手是没种,是饭桶,是懦夫!”
“臭小子,男子汉,大丈夫,要做英雄,不要做狗熊。”
“臭小子,老子今天非要打到你还手不可,即使将你砸成肉泥,捣成血浆,闹出人命来,被判处死刑亦在所不惜。”
猛打不算,又开始猛骂,这言词,这气势,把廖添丁打得灰头土脸,骂得狗血淋头,简直一文不值。
是泥人还有三分火气。
是木头也会着火燃烧。
廖添丁终于被激怒了。
阿坤更火更怒,大声鼓噪道:“老大,跟他拼啦,老虎不发威,他会以为你是病猫,甚至死猫。”
“弄一个龙头老大来干一干也不赖。吃香的,喝辣的,风风光光的玩一个月。”
廖添丁想不干也不行,大盗张富又疯狂的攻上来,拳打脚踢,无休无止,破口大骂,没完没了。
激得廖添丁暴跳如雷的道:“你娘,想死就死,不想干龙头老大就滚下台去吧!”
说干就干,真的施出了浑身解数,跟张富大打出手。
打得惨烈。
打得精采。
天摇地动。
惊心动魄。
张富果非弱手,比大头杜高明得多。
但與廖添丁相较,仍略逊半筹,百合之外,一掌劈空,被廖添丁一个“过肩摔”摔到台下去。
不简单,猛一个大迥旋,便将身形稳住,脚落实地,没有大马趴,亦未做滚地葫芦。
阿坤一怔神,道:“大块头,看不透你还真有两刷子,不服气可以上去再干,保证可以打得你屁滚尿流,叫你趴下起不来!”
张富倒很识货,也很知趣,哈哈一笑,道:“按照规矩,老盟主一被打下司令台,就表示挑战成功。”
阿坤好不兴奋,眉飞色舞的道:“也就是说,我们蔡兄现在已经是大家的龙头老大。”
老富立道:“不错。”
“要不要举行交接仪式?”
“不必,坐上金交椅,就表示就职。”
“总该祝贺一下吧?”
“那当然。”
廖添丁本无此意,只不过由于张富欺人太甚,想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而已,结果竟弄成一个黄袍加身的局面,禁不起阿坤的一再耸恿,只好勉为其难的登上那只陈旧的破椅子。
台下马上响起一片欢呼。
“贺新盟主登基!”
“祝龙头老大视事!”
“新盟主万岁!”
“龙头老大万岁!”
监狱里的陋规真多,千奇百怪,简直近乎胡闹。
一点也不胡闹,监狱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龙头老大有绝对的权威,地位崇高,神圣不可侵犯。
在这里,没有公理正义。
在这里,拳头就是真理。
龙头老大仿若动物园里的猴王,高高在上,谁也不敢轻视。
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生活更优裕。
日子更舒坦。
有吃不完的山珍海味。
有喝不完的佳酿美酒。
出则前拥后护。
入则呼仆唤奴。
除了没有办法弄一个女人进来“趴”以外,在这里几乎应有尽有。
最难能可贵的是,不打不成交,昔日与飞鱼、土确壁的往事,又在此重演。
大盗张富、杜照邦、贺永川不但不恨他,相处日久,反而变成了患难之交的好朋友。
廖添丁、阿坤乐得清闲,将与监方打交道,管理囚犯的事全权交给张富、杜照邦他们来办,彼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一眨眼的工夫便到了礼拜天。
这是个大日子。
是亲人会面的大日子。
也是身为室长、区长、楼主、龙頭老大的大丰收的好日子。
因为,不论囚犯们收到任何礼物,都会毫不保留的往上面孝敬的。
却不料,有一位囚犯传来消息,阿坤与廖添丁居然也有人指名会见。
廖添丁闻言一愣,道:“什么人要会见咱家?”
囚犯毕恭毕敬的道:“一个老头。”
“多老?”
“约莫六七十。”
“可知此人姓名?”
“叫李阿土。”
“李阿土,他……”
“他说是龙头老大的老邻居。”
清水秀水村,根本没有一个叫李阿土的老邻居,弄得廖添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将传话的囚犯打发走后,阿坤马上迫不及待的说:“老大,会是谁呀?”
“除他之外,大概不会有第二人。”
“那一位?莫非……”
“去一看便知!”
’
那时候还很落伍,会面的地方没有电话,也没有玻璃,双方只是隔着一道铁栅而已。
不过,倒也好处多多,彼此可以面对面,拉拉手,倍感亲切。
那囚犯之言不差,指名要见阿坤、廖添丁的果然是一个老头。
一个白发苍苍,满面皱纹,佝偻着背,穿着一身粗布衣裳,年逾古稀,已是风烛残年的糟老头。
廖添丁不认识。
阿坤也莫宰羊。
廖添丁好会演戏,趋前道:“阿伯,您好。”
白发老者白眉一轩,连说:“好,好。”
“你老人家要见我蔡万全?”
“还有那一位阿金。”
“我们是老邻居?”
“多年的老邻居。”
“老先生姓李?”
“本姓吴,过继给姓李的,所以改姓李。”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是该想起来了,监狱之外,知道蔡万全、张有金这两个名字的人为数不多。老邻居自然也是老朋友的意思,阿坤与廖添丁只有一个姓吴的朋友。
阿坤忙上去紧紧的拉住老头的手,将声音压至最低,道:“吴老大,你的易容术好高明。”
土确壁吴涂壁噤声道:“完全是廖兄弟指导有方。”
廖添丁道:“吴兄,外面的情况如何?”
“很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那八个字?”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鬼子还在继续追捕?”
“追得很严,捕得很紧。”
“那么,四海帮的弟兄……”
“全部逃往外地,停止一切活动。”
“最重要的是,大嘴狮、徐福田、飞鱼他们是否已安然脱险?”
土确壁振振有词的道:“托天之幸,大嘴狮他们,那天夜里连挖了好几道土墙,总算逃离虎口。”
“为了替你们解厄,还特意干了几件案子,这才使番仔不再怀疑两位,不然廖兄弟的锦囊妙计,很可能会弄巧成拙,变成自投罗网。”
阿坤摸一下自己的脑袋,道:“好里加在,果不幸而言中,此刻可能已经入土了。”
廖添丁道:“藏在龙山寺的东西取回来了吧?”
土确壁道:“没有,近来动都不敢动。”
“可曾回去过醉仙楼?”
“那儿的风声也紧得很,没敢去。”
“这几天吴兄是怎样过活的?”
“到处躲躲藏藏,苦得很,也穷得很。”
“吴兄交游广阔,很兜得转,怎么会?”
“怎么不会,所有的朋友都不敢去找。”
“起码还有三十二块八毛五。”
“别提了,这三十二块八毛五,支付我与飞鱼的生活,固然绰绰有余,谁想到半路上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
阿坤道:“那个程咬金?”
土确壁道:“就是那个扶桑浪人花十郎嘛,一下子就被他榨去三十块。”
“这小子的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花十郎钓上一个鬼子兵,整天抽花烟,喝花酒,开销很大,说是正在加紧进行中,并且表示,放长线,钓大鱼,这事急不得,事关军事机密,急则会坏事。”
“只怕是个无底洞,骗吃骗喝罢了。”
“姓花的穷途末路,潦倒他乡,骗吃骗喝乃意料中事,但还不至于胆敢将正事完全撇开。”
“但愿如此。”
廖添丁道:“钱被花十郎榨去,两位何以为生?”
土确壁苦笑一下,道:“演戏演上了瘾,弄假成真,为了生活,跟飞鱼真的干起小贩来了。”
廖添丁一闻此言,反而精神大振,意气风发的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当小贩也没有什么不好,不知吴兄卖啥?”
“老本行,卖糖葫芦。”
“飞鱼呢?”
“茶叶蛋。”
“生意如何”?
“马马虎虎,可以糊口啦,另外还有能力给两位买些吃食之物送来打牙祭。”
阿坤见他两手空空,道:“开什么玩笑,该不会是‘话’饼充饥吧?”
土确壁道:“东西在隔壁,管理员正在检查,他们说会完后,便可以领回去。”
廖添丁道:“吴兄何必破费,其实小弟的床上床下,多的是佳肴美酒,吃也吃不完,喝也喝不了,日子过得舒坦又逍遥。”
土确壁困惑不解的道:“爱说笑,监狱犹如地狱,哪来的佳肴美酒?又如何能舒坦逍遥?”
阿坤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个大概,神采飞扬的道:“你没有坐过监牢狱,自然莫宰羊,其实里面也是一个花花小世界,只要当上龙头老大,就可以享荣华,受富贵,呼风唤雨。土确壁道:“阿坤,你刚才说,前任的龙头老大是大盗张富?”
“是呀。”
“张富是一条血性汉子,劫富济贫,锄强扶弱,在新竹那方面颇负盛名。”
“吴兄认识他?”
“久闻其名,未见其人,不过……”
“不过怎样?”
“此人可以结交。”
“鸡婆,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怎样?”
“我们早已结为生死之交的朋友。”
“如此甚善,张富一旦出狱,必可为抗日大业出大力。”
自此而后,每逢周日,飞鱼、土确壁必来探望阿坤、廖添丁。
都是空手来的,因为他们知道,二人的东西堆积如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纯粹是来传递讯息。
可惜并未带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鬼子的查缉依然很紧。
军械库的进展十分缓慢。
黑川熊的地址迄未查明。
亦未与廖金莲搭上线。
也不曾追讨回飞鹰帮的欠债来。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因为廖添丁的入狱而停滞下来。
所幸,一月易过,明天就要刑满出狱。
大盗张富、大头杜、和尚川仔,以及另外四位楼主,还真够意思,利用头一天放风的时间,特别为阿坤、廖添丁办了一个惜别晚会。
酒满樽。
肉满盘。
大家皆开怀畅饮,颇英雄相惜,依依难舍之慨。
连喝三五斤烈酒后,杜照邦忽道:“蔡老大,张老大,两位出狱之后,不知做何打算?”
阿坤想了想,故作傻笑道:“嘻嘻,假如找不到工作,可能还会继续当扒手,做小偷呀!”
廖添丁以试探的语气道:“也许会做一些专门跟日本鬼子捣蛋的事。”
和尚川仔贺永川道:“如何捣蛋?”
阿坤道:“骗钱,偷东西,破坏设施,放火烧房子等等,都可以。”
廖添丁说的更清楚:“甚至干脆去投效义军,或者做一些支援协助的工作也可以。”
大盗张富听到这里,乍然跺一下脚,道:“蔡老大的这一句话最中听,番仔犯我国土,占我家邦,你我身为男子汉,岂可袖手旁观,纵使无法投效义军,跟鬼子拼死拼活,最低限度也该帮一些支援协助的工作。”
一位楼主慷慨激昂的道:“对,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你我心中,多数皆非善类,作恶多端。”
“但自出狱之日起,便当革面洗心,弃恶从善,以一种赎罪的心情,投身义军,为我台湾同胞流血流汗!”
入狱之后,廖添丁本来就有招兵买马之心,闻言甚觉欣慰,朗声道:“好极了,诸位既然这样说,蔡某人愿作马前卒,先去探探路。”
阿坤接着说道:“路一旦开好,各位出狱之后,便可大家一起来。”
“对,咱们大家一起来抗日。”
“咱们大家一起来杀鬼子。”
“非我族类,驱逐出境。”
“非我族类,格杀毋论。”
“还我河山!”
“复我国土!”
就在这样激昂、奋发,充满斗志与希望的情形下,结束了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惜别会。
廖添丁和阿坤出狱了。
脱下囚衣,又换穿上他们原来的破旧衣裳。
有两个人前来迎接。
一个是土确壁吴涂壁。
另一个是飞鱼张木村。
两个人都打扮成小贩的模样儿。
土确壁依旧是个老头儿,在卖糖葫芦。
飞鱼扮成一个愣小子,在卖茶叶蛋。
四人相见甚欢,寒暄数语后,廖添丁马上转入正题,道:“外面的情况可有转变?”
土确壁道:“转变是有,但幅度不大。”
阿坤道:“你是说番仔仍在继续追捕咱们的工作?”
飞鱼朝四下望一眼,道:“不错,只是稍稍放松一些,不似过去那样雷厉风行。”
廖添丁道:“花十郎有无再来要钱?”
土确壁道:“这小子好像失踪了,久未晤面。”
“可曾将枪支取回?”
“目前尚不宜轻举妄动。”
“是否跟大嘴狮保持联系?”
“徐福田的船一直停靠在渡口,三天两头都会见一次面。”
“义军那边的情形怎样?”
“日军同样步步进逼,大家都避入观音山去了。”
“回去过醉仙楼吗?迎春花别来无恙?”
飞鱼张木村翻了一个白眼,道:“哇噻!想不到廖老大对迎春花如此专情,很想念,是不是?”
廖添丁毫不隐瞒,大大方方的道:“她是我第一个碰过的女人,我是她第一个碰过的男人,想啊,当然想,想得要死。”
土确壁抢一个鬼脸,问阿坤:“你想不想赛水仙?”
阿坤也很坦白,据实说:“想啊,王八蛋才不想,想得要命!”
土确壁叹息一声,道:“可惜风声太紧,到现在为止,仍未敢冒险重返醉仙楼,迎春花、赛水仙情况不明,连我的小白鸾至今也同样生死下落不明”。
廖添丁道:“回不了醉仙楼,又不敢去找亲朋好友,囊空如洗,沦落街头,为了掩藏身份,也是为了顾三顿,只好继续沿街叫卖,妈的,日本鬼子害得大家好惨啊。”
阿坤嘻皮笑脸的道:“人生如戏,尝试一下各行各业的辛酸苦辣也不赖,干脆咱们大家都改行做小贩好啦,有人买就卖,没有人买就自己吃,挺好玩的嘛。”
廖添丁啐骂道:“好你的头,咱们若是永远做小贩,弄不到大钱,中南部的义军不饿死才怪。”
土确壁亦道:“单单花十郎的这一个洞就填不满,浪人一旦拿不到钱花,必会掉头而去,非但军械库大搬家的计划会泡汤,说不定还有会被他出卖的危险。”
阿坤闻言可傻眼了,道:“惨啦,惨啦,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可如何是好?”
廖添丁略一寻思,道:“咱们讨债去。”
飞鱼道:“找谁讨债?”
廖添丁道:“找洪茂川。”
阿坤道:“姓洪的只欠咱们二百五十块,为什么不去找飞鹰帮,飞鹰帮欠三万块啊!”
土确壁迟疑一下,道:“飞鹰帮人多势众,高手如云,眼前四海帮重创之后,余众又皆星散,此刻绝非与飞鹰帮摊牌的最佳时机。”
阿坤道:“难道就此罢手不成?”
土确壁道:“当然不,只要风声一过,必当重振旗鼓,将这笔帐讨回来。”
阿坤回头望一下台北监狱的高墙,道:“张富、杜照邦、贺永川等人很快就会刑满出狱了。”
“这是一支生力军,只要这一批亡命之徒加入咱们的行列,必可声威大振。”
廖添丁神采飞扬的道:“没错,只要张富他们加入行列,咱们又可以轰轰烈烈的干起来。”
“再见吧,台北监狱!”
“再见吧,龙头老大。”
“再见吧,弟兄们!”
“再见吧,英雄们!”
无论如何,能够离开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总是一件好事,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倍感兴奋。
阿坤、廖添丁齐声低唤,挥挥手与飞鱼、土确壁结伴离去。
六馆街(南京西路)。
彰化恶霸洪茂川的小公馆。
“卖糖葫芦,香脆可口的糖葫芦!”
“卖茶叶蛋,营养好吃的茶叶蛋!”
应声从两头来了四名卖小吃的小贩。
廖添丁的行动十分老练,一掌贴在门上,轻轻一推,凑巧没关,一推就开。
马上作了一番部署,命飞鱼在门外把风,请吴涂壁到后去放哨,以防肥羊走脱。
然后才领着阿坤,跨步而入。
旧地重游,驾轻就熟,兀自登堂入室,进入洪家的客厅。厅内无人。
有吃剩的残羹剩菜。
以及半瓶日本清酒。
“有人在家吗?”
“洪老大在家吗?”
无人现身?
亦无人应声。
却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经验告诉他们,这是男女之间兴云作雨时发出来的交响乐——喘声、嗲声、水声、床铺吱吱声,乃至不堪入耳的秽言秽语。
怪声突然停了,从卧房之内传出一个银铃也似的,娇喘的声音来:“谁呀?”
廖添丁故意打马虎眼,含混其词的应了一声:“是我。”
“到底是什么人?”
“你老公的朋友。”
“哪一位朋友?”
“从大和行辜家来的。”
“来干嘛?”
“找洪老大。”
“有事吗?”
“是有一件事想当面请教。”
“我家那个死鬼他不在。”
“请大嫂出来谈谈也一样。”
沉默了好一会工夫,那女子声音才说:“好吧,请先在外面坐坐,奴家就来。”
廖添丁道:“最好快点,别泡蘑菇。”
阿坤道:“等太久当心我们会冲进去。”
“来啦,来啦!”
这一着还真灵,余音未落,二人便觉眼前一亮,在卧室的门口,出现一名女子。
年纪不大,约莫二十二三。
很美,柳叶眉,杏儿眼,櫻桃小口一点红,瓜子型的脸蛋儿上挂着两个大酒窝,美则美矣,只可惜眉宇之间笼着一股子淫荡之气,一看就晓得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身上披着一件睡衣,两只手抓得紧紧的,怎奈睡衣稍嫌短了一些,顾得了上面,顾不了下面。
有时候会露出来双峰。
有时候会露出来大腿。
显然,里面八成在唱“空城计”。
长发散乱,钗簪不整,额头有汗珠,仍在娇喘不止,一张脸红喷喷的,可以在她的眼内看到欲火,也可以从她的身上找到证明,这一仗定然十分“惨烈”。
洪茂川的细姨长发女子羞答答的道:“两位有何贵事?”
廖添丁道:“咱家想先知道,洪茂川到哪里去了?”
长发女子:“回彰化。”
阿坤怒气冲天的:“狗娘养的,他好大胆,上次曾言讲当面,不准他离开台北,竟敢开小差,是什么时候溜的?”
长发女子道:“三天前。”
廖添丁道:“这话可当真?”
“句句实言。”
“恐怕不见得吧?”
“公子何出此言?”
“我问你,你在跟谁干‘那码子事’?”
“没有,没有呀!”
“放屁,事实摆在眼前,小爷一点也不外行。”
长发女子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是你老公洪茂川?”
“不是。”
“那是你在偷人养汉子,倒贴小白脸?”
“不是,也不是。”
“究竟是那一个风流鬼?”
长发女子坚不吐实,惹恼了阿坤,道:“老大,别跟她噜七八嗉,臭婊子不说,咱们自己去查,是否洪茂川,一看便知分晓。”
当即大踏步的冲上去,长发女子死守着门口不让,怎能挡得住双枪坤仔,拉拉扯扯,推推挤挤,两三下便将她撞回到房里去。
睡衣掉了,果然全身赤裸。
的确是个大美人,有一副魔鬼似的身材。
阿坤、廖添丁却连正眼也没瞧她一眼,一头闯进卧室去。
室内无人。
床上有被。
被里鼓得高高的,还在动。
廖添丁的动作好快,手一伸,刷!的一声,便将大红缎被掀开来。
被下有人。
是个公的。
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的大男人。
这人的反应也不慢,还没有看清楚他的面貌长相,就在廖添丁将被子掀开的那一间,立如怒矢般破窗箭射而逃。
没有逃走,合该他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土确壁就守在窗外,一记劈空掌,再加两招打虎拳,揍得他头昏眼花的倒退回来。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廖添丁又及时出手,点住他他的“麻穴”,像个木头人似的,杵在长发女子的身旁,靠在墙上不动了。
不是小白脸。
不是洪茂川。
是一个日本鬼子。
一个熟透了的番仔,黑龙会的八段高手,樱花俱乐部的负责人——石太郎。
奸夫淫妇,人人痛恨,阿坤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顿毒打,赏了石太郎二十个“水煎包”,外加二十个“五百”。
一时兴起,欲罢不能,打完奸夫,再打淫妇,如数照赏,不折不扣。
石太郎还好,长发女子可禁受不起,一张俏丽妖娆的脸蛋儿,已经扭曲的变了样儿,差点晕倒在地。
裸男对裸女。
大眼对小眼。
可惜已看不到半点旖旎风光。
也不可能听到半句枕边细语。
只有恐惧、惊骇、颤抖……
廖添丁咬牙切齿的道:“石太郎,你和洪茂川是何关系?”
石太郎从牙缝里挤出来两个字:“朋友。”
“是很要好的朋友吧?”
“普普通通的朋友。”
“放屁,如果是普通朋友,洪茂川不可能把我姐姐送给你。”
“你原来是……”
“不错,你爸正是廖添丁,今天算你衰,要倒大霉。”
“是的,石某与洪茂川是很要好的朋友,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你听说过吗?”
“哪一句?”
“朋友妻,不可欺!”
“这……”
廖添丁故意耍威风道:“阿坤,对付这种猪哥臭男人有何妙法?”
阿坤道:“照老规矩来。”
“什么老规矩?”
“一个字。”
“阉。”
“好,就照着你的意思去办!”
“是,老大!”
眼前小桌上正巧有一把剪刀,阿坤拿起剪刀来,咔嚓!一声,可怜的石太郎,好事未成,连“棍儿”也丢了,被阿坤齐根剪下,从此只好向风月说再见,向云雨道永别,与女人绝了缘。
痛得他呼天抢地,鬼叫不止,卒告晕厥过去。
奈何麻穴”被制,空有一身的本事,却施展不出来,只有挨揍挨剪的份儿。
廖添丁又说话了,目标是长发女子,道:“你是洪茂川的小老婆,对不对?”
长发女子早已吓出一身冷汗来,全身抖个不停,闻言微颔螓首,表示认可,没开腔。
“第几号?”
“第三号。”
“吃得饱不饱?”
“什么吃得饱不饱?”
“嘿,老土,连这个都听呒,就是夫妻在床第之间,他能否使你满足?”
“马马虎虎啦!”
“也就是说,你并没有闹饥荒?”
“可以这样说。”
土确壁早已越窗而入,怒容满面的道:“你娘,贱啊,骚啊,丈夫才走三天,你就穿不住裤子,守不住床,大白天就偸男人。”
阿坤随声附和道:“你娘,烂啊,臭啊,三天没给男人碰,就耐不住寂寞,守不不住空闺,给你老公戴绿帽子。”
骂得三姨太狗血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廖添丁道:“说实话,是你投怀送抱?还是他强行登陆?”
三姨太犹豫一下,道:“差不多都有啦。”
“都有啦的意思是否表示,他有强行登陆的事实,你也有投怀送抱的行动,一样的下流,一样的贱,干柴烈火,一拍即合?”
“大概就是这样吧。”
“你们来往多久啦?”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洪茂川不在,他就来填空?”
“有时茂川在,太郎也会来偷吃。”
“不怕撞车出车祸?”
“怎么会,觑准死鬼去应酬时,石太郎才会来。”
“骚娘们,臭婊子,你的胃口不小。”
“好玩嘛,何必大惊小怪。”
“好玩可以找一个少年仔,为什么要跟番仔姘?”
“换换口味嘛,同时也找不到适合的少年仔,倘若早一天与公子相遇……”
“骚啊,贱啊,烂啊,臭啊,下流加无耻,少跟咱家吊膀子,本少爷从来不碰三手货的!”
脸一沉,廖添丁又道:“吴兄,这种淫荡的女人如何处置比较好?”
土确壁不假思索的道:“作废!”
“作废?怎样作废?她又没有‘棍儿’?”
“可以剪掉她的奶头。”
“还有吗?”
“在额头上划一个‘×’,表示作废,相信不会再有男人去碰她。”
“这个主意不错,只有二百五才会去碰一个没有奶头,已经作废的烂女人。”
阿坤晃一下手中的剪刀,朗声道:“好极了,让我双枪坤仔马上操刀行刑。”
却被廖添丁伸手阻住了,道:“且慢,等债主回来再行动。”
石太郎依然昏迷不醒,三姨太也早已吓得花容大变,颤声道:“什么?茂川欠你们的钱?”
廖添丁道:“不假。”
“欠多少?”
“不多,只有两百五十块,再加利息。”
“还要加利息?”
“非亲非故,自然要加。”
“请说个数字。”
“一共五百。”
“我的妈呀,这么多,加一倍?”
“这是高利贷!”
三姨太想一想,惶恐不已的道:“不管是什么钱,也不管合不合理,小女子愿意尽量给你们凑,但请高抬贵手,千万别毁我的容,剪我的奶。”
土确壁冷哼一声,道:“别讨价还价,看你孝敬的多寡再作定夺。”
三姨太确有花钱消灾的意思,可是,翻箱倒柜,连石太郎的衣服都找遍了,仅仅才凑出三百块来。
阿坤嗤之以鼻:“妈的个巴子,只有区区三百块,连还债都不够,还想买容颜,买奶头?门儿也没有。”
土确壁冷冷的道:“身为女人,总该有点首饰吧?”
三姨太道:“有是有,不多。”
阿坤道:“想要剪下超生,最好是多一点,快一点,别磨蹭,惹火了老子,当心把你那个洞也剪烂。”
三姨太哪敢怠慢,立即付诸行动,手上戴的,项间挂的,箱子里藏的,为了保全漂亮的脸蛋儿,以及挺拔的双峰,一古脑儿全部拿了出来。
廖添丁冷然一哂,道:“破铜烂铁的,这也值不了几个钱”。
三姨太道:“这些东西,若是买新的,最少也值一千块。”
阿坤道:“可惜旧的,不值半价。”
三姨太急辩道:“金子角子,都是论钱算两的,新旧都差不多。”
土确壁道:“就算是八百块你也过不了关,最好是再把洪茂川搜刮来的金银钱钞拿些出来,或可网开一面。”
三姨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哭丧着脸,苦苦哀求道:“洪茂川给我的东西,都在这里,没有了,真的。”
廖添丁略一寻思,将金银钱钞收起来,道:“咱家言而有信,看在钞票的份上,姑且免去毁容之罪,不在脸上的打‘×’作废,但万恶淫为首,你不守妇道,还是要略施薄惩,将你的两个奶头剪掉。”
他这儿掉字甫出口,阿坤的剪刀已经剪下去,咔嚓!咔嚓!两声,两个花生大的奶头,带着一片肉,应声掉落在地。
三姨太的惨叫声,正好将石太郎吵醒过来,廖添丁双眉一挑,道:“石太郎,听清楚,你的‘麻穴’,一个小时之后便解,传一句话给犬养幸助,叫他马上把我姐姐放出来,否则,当廖添丁杀上黑龙会总坛时,将会赶尽杀绝,鸡犬不留!”
根本不给石太郎说话的机会,话一出口,便与阿坤、土确壁向室外行去。
一边走,一边还在猛说风凉话。
“祝两位爱河永浴。”
“祝两位百年好合。”
“再见。”
“拜拜!”
“莎哟娜拉!”
钱数实在太少,虽可解四人眼前的燃眉之急,但若是助中南部的义军,可谓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
也不敢去变卖首饰,怕的是被日警的密探踩上。
四人密商的结果,决定再干一票大的。
不是去找飞鹰帮讨债。
而是想向兄弟会的一位富商“募捐”。
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件大事,又不冒被抓的奇险,由廖添丁匹马单枪一个人,摸黑潜入龙山寺,将藏在一个秘密所在的枪支衣物取回来。
古道幽蘭OCR於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四日戌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