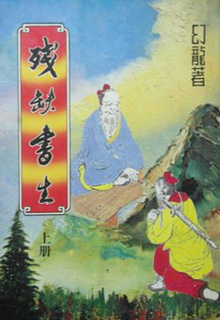一座富丽华贵的大厅,正中的八仙桌上,接着银盏金匙象牙筷,只有两副,看来稍待用饭的人也是两位。果然一男一女,在四名劲衣中年人陪同下,踱进大厅,适时那女子柔美轻抬,手一挥,向四名中年人道:“你们退下,唤‘轻云’这丫头出来斟酒。”四名中年人齐声恭庞,移时,一名翠衣女婢,步履娇娜而轻巧地进了大厅。此时,那一男一女已然入座,翠衣女婢正赶上斟酒。
男的,正是先前在广场,夸言有席好酒可吃的雪衫书生。
女的看来二十出头,美到使人有一见难忘的魅力,瞥目偶见,也会终生不忘。她一身宝石蓝衣,鬓间云丝,斜插一朵杏黄玫瑰,襟上也有一朵,不过这却是用整体黄色宝石雕刻而成。她是谁?“老印记”的主人,印天蓝。
轻云,这名翠衣女婢,斟满酒,退到了印天蓝的身后,星眸闪射出奇异的光采,注视着雪衫书生。印天蓝柔荑轻握银盏,嫣然一笑对雪衫书生道:“公子请尽这一盏酒。”雪衫书生冷着一张脸,端起银盏,仰颈而干。印天蓝媚目斜眺,娇笑出声道:“我该陪饮。”于是她也一饮而尽,接着转对轻云道:“斟酒,吩咐上菜!”轻云恭庞一声,轻轻拍了几下手掌,厅门开处,四名美女,各捧盘菜鱼贯而上,一次又一次次,菜樱满了一桌。轻云再提金壶,更斟美酒,然后依旧站于印天蓝身后右侧,那双星眸,竟一瞬不瞬地盯在雪衫书生的银盏上,印天蓝长睫一眨,道:“公子请再尽一杯,然后该谈一谈正经事了。”雪衫书生冷冷的嗯了一声,左手端起银盏!突然?他看到轻云星眸中,闪射着希冀而激动的光芒,他暗自一凛,继之恍然,神目末转,心念已动,道:“姑娘,区区十分焦急,要先知道……”说道这里,他极为自然地放下了手中银盏。但那双神目,却在暗中注意着轻云。
果然,轻云见他放下了银盏,神色恨然若有所失。他暗自颔首,心中已有了数目,印天蓝这时接话道:“公子,我先前就说过了,这席酒饭用过以后,我们开始来谈正经事,公子当代英雄,应该是提得起也放得下的!”雪衫书生笑了笑,似乎无奈地摇摇头,伸手取那象牙筷子,那知手脚微抖,将一双牙筷碰落地上。印天蓝吩咐轻云重换一双,就在她微顾轻云的刹那,雪衫书生已施展出“心佛静挪”神功,调换了酒盏。轻云取来牙筷,雪衫书生首先致谢,接着捧盏敬向印天蓝道:“姑娘,就先干了这杯,开始用饭可好?”这在印天蓝说来,自然是好,立即含笑举盏,各自干杯,那轻云在雪衫书生酒罢后,不待吩咐,已将金壶银盏收起端走,这举动,更使雪衫书生心头雪亮。酒过用饭,饭后换茶,茶间,宾主谈起正事。首先是雪衫书生开口,道:“姑娘,你有什么条件?”印天蓝一声娇笑:“难道公子还没想明白?”雪衫书生剑眉一挑,道:“区区不惯猜测女孩子的心中事!”印天蓝朱唇一损,道:“就算是这样好了,那我告诉你,不论郝甫抑或是胡梦熊,他们全要听我的……”雪衫书生冷冷地说道:“这我已经知道了,否则的话,我也不会在发现古刹留字之后,如约坦然而来了。”印天蓝嗯了一声道:“公子你爽快,那我也爽快些说,我一共有三个条件,公子必须接应,才能够换取令弟的平安!”雪衫书生心头一凛,道:“你指那个素衫文弱的少年,是我兄弟?”印天蓝长睫一颤,瞥了雪衫书生一眼,道:“大概错不了!”雪衫书生哈哈一笑,道:“姑娘,这何以见得?”印天蓝嘴角掠过一丝微笑道:“公子府上是山东蓬莱,他也是,公子身畔有枚寸步不离的‘半月’古钱,他也有,他远自故乡,万里奔波,目的就是来找公子,还有件极巧的事,公子姓郭,他也姓郭……”雪衫书生突然哼了一声,接口道:“冯京马凉,我错到天上地下,区区的姓氏,无人知晓,区区的故里,更非蓬莱,至于那‘半月’古钱,我能有,不敢保证别人就不能有,另外还有件极不巧的事,区区三房一子,无兄,无弟,也无姐妹!”印天蓝嫣然一笑道:“这样说来,是我弄错了?”
雪衫书生冷冷一笑道:“反正错的不是区区!”印天蓝噗地一笑道:“那我岂不是弄巧成拙?”雪衫书生冷笑一声道:“不错,你太自作聪明了!”印天蓝神色一怔,道:“既然那素衫的少年,并非公子兄弟,公子却不惜犯险遵约来这‘天道镇’作甚?”雪衫书生也正色道:“来找罪魁祸首!”印天蓝咯咯一笑道:“那公子可算找对了地方!”她话锋一顿,媚眼儿在雪衫书生身上一瞟,又道:“现在公子找到了我,可能请教一声,要怎样发落我呢?”
雪衫生冷冷地站了起来,道:“姑娘,你该交代清楚那些可怜异乡客的下落!”印大蓝黛眉微蹙道:“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雪衫书生哼了一声道:“姑娘不懂?”印天蓝摇摇头,以诧然而又有疑的眼光看着对方,雪衫书生目注印天蓝,一瞬不瞬,神色威凌。印天蓝不由移开了眼神,道:“公子究竟何指?”雪衫书生哼了一声,道:“事情发生在十几年前,直到现在仍未停止……”话没说完,印天蓝已接口道:“到底是什么事嘛?”雪衫书生目射寒光,道:“姑娘的矿场,林班,参场,牧场中,这多年来,可有已到时限恢复了自由的工人?”印天蓝顿首道:“当然有喽,他们做满了约定卖身的年限,又想再来赚些钱,所以就留在场内……”雪衫书生冷笑一声道:“都留下了?”印天蓝道:“谁说的,有不少人在期满后,领取了五年或十年的存蓄工资,发财还家了。”雪衫书生怒哼出声道:“姑娘,据区区所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离开过辽东……”印天蓝黛眉一挑道:“他们愿意落户辽东的话,谁又管得着?”雪衫书生字字沉声道:“姑娘矫作得真像,实话告诉姑娘,这些可怜的异乡人,在卖身期满,携带着五年或十年作中当马为奴换得的银子,一心想回家园,夫妻团聚,父子相会,哪知在离开场以后,就断无消息,离奇失踪了!”印天蓝闻言一惊,道:“公子是说,他们并非落户辽东,而且从此失踪!”雪衫书生咽了一声道:“不错,第一次事情是在十几年前,当时没人注意,可是近两三年来,失踪的人日多,于是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话没说完,印天蓝已接口道:“公子就是有心人?”雪衫书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神色凝重地说道:“也许姑娘不了解山东乡人的性格和品德,他们多半是一生没有作过亏心事的好人,责任心重,说一不二!”印天蓝哦了一声道:“是这样又如何呢?”雪衫书生哼了一声道:“是这样,就引发了种种悲惨的结局,近十年来,说归说是升乎年景,但山东河南两地,不是连早,就是水淹,官家虽有济助,可惜杯水车薪,所以在谣传‘关东遍地是黄金’之下,创闯‘关东’,就成了当地百姓的救难菩萨。”印天蓝微一蹙眉,道:“事实上并非如此,真要说起来的话,近十几年来辽东能够有现在这般繁荣,还该归功这些佣工才对。”雪衫书生似乎有些诧然地扫了她一眼,道:“姑娘这是由衷之言?”印天蓝正色道:“当然,先父在日,也这样说过。”雪衫书生剑眉一挑道:“既然这样,区区就要直问姑娘一句话了,姑娘何忍对这些可怜人,施弄诡漏杀手!”印天蓝霍地起座,沉叱道:“公子,你这句话指着什么说的?”雪衫书生冷冷地说道:“指着这千百名下落不明,或许是早已惨遭不幸,埋骨于冰雪白山黑水间的佣工而言!”印天蓝恼了,手指雪衫书生道:“老印记是道地的生意商号!”雪衫书生怒哼了一声道:“南北两霸天,是如假包换的绿林巨盗!”印天蓝星眸怒射煞光道:“也许。不过他们绝对不敢做这种事!”雪衫书生道:“也许。但是有人他敢!”印天蓝沉声追问:“谁?是谁?你说个清楚?”雪衫书生道:“胡梦熊和郝甫听谁的话行事,那个人就是我所指的!”印天蓝哼了一声道:“你明明知道,那个人是我。”雪衫书生道:“不错,所以今天我找到这里!”印天蓝嗤之以鼻,道:“大言不惭,别忘记,若是我不故意在古刹留字约你前来,你现在不会坐在这里的!”雪衫书生一笑道:“我不会坐在这里是真,但若说你不留字,我就找不到这里来,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印天蓝才要接话,雪衫书生在目光横扫了她一眼之后,突又说道:“我对令尊生前的事,很清楚!”印天蓝笑一声道:“先父一生事迹,在辽东一地中非秘密,你知道,和其他的人知道,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分别!”她俩从十分客气的“公子”,“姑娘”,“区区”等自称称人的阶段,一变而为直接了当说“你”
和“我”!因之气氛也由虚假的客套,转为针锋相对的紧张。
雪衫书生此时微微一笑,道:“令尊艺出‘天山’一门?”印天蓝哼了一声接口道:“哪个不知?”雪衫书生依然微笑着说道:“他是‘天山冰叟’的大弟子,一身技艺功力和剑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印天蓝玲冷地说道:“不劳谬绩!”雪衫书生神色突然一怔,道:“但他却未能接替‘天山’一派掌门之位,何也?”印天蓝心头猛地一凛,强捺着激动道:“老人家志不在此。”雪衫书生哼了一声道:“尽管他志不在‘天山’掌门之位,然则对恩师惨死的事,也无动于哀不思报仇吗?”印天蓝闻言,如道雷般楞傻在一旁,瞪着眼说不出话来!雪衫书生看到印天蓝的这个表情,已有些不忍,故意头一低,不再看她,可是话却没停,又道:“令尊的作为,我不敢批评,但是若想由交结绿林朋友,进而侦得恩师死因和谁是凶手的话,那就谬之千里了!”
印天蓝此时咬了咬下唇,嘲讽地说道:“你知道的可真不少?”岂料雪衫书生竟顿首微笑着说道:“这句话我可以坦然承认,对令尊生前的事情,我若说一句狂言大语,恐怕知道的还比令尊本身要多了一些!”印天蓝冷笑起来,道:“这倒透着新鲜。”雪衫书生仍旧面带笑容道。
“你不信吧?”印天蓝反问一句:“你说我能信吗?”雪衫书生道:“我要是你的话,就会信。”印天蓝轻蔑地说道:“那真可惜,可惜你不是我。”雪衫书生不加分辩,道:“我是三年前,到辽东来的,原因是堂叔及二舅,在说好的归期内没有回去……”印天蓝从这句话内,发现了破绽,接口道:“令尊令叔也是卖身的佣奴?”“佣奴”这两个字,是印天蓝有心挖苦雪衫书生。哪知雪衫书生,却不以堂叔身为“佣奴”为耻,道:“不错,寒家贫困,堂叔及二舅,在十四年前,离乡随大队族老和一群闯关东的人,一道前来,到达此地后,曾有银两书信托族中父老带回,临行时及来信中,俱皆言明十年后必定返乡,讵料自此就断无消息……”印天蓝很快地接口道:“所以你就从山东来了?”雪衫书生默然一笑道:“不,我就由家乡来了!”印天蓝仍不算完,道:“不是山东?”“不是!”
“不是蓬莱?”“不是!”
“你不姓郭”“不姓郭。”
“那你姓什么?哪里人?”雪衫书生笑出声来,道:“现在不说。”印天蓝哼了一声道:“大丈夫磊落光明,假如你连自己的姓氏家乡都不敢向人说明,其余的话谁还敢相信呢?”雪衫书生面色突然一沉,道:“信不信由你。”印天蓝头一摇道:“看来我们是都找错了目标。”她话声一顿,瞟了雪衫书生一眼,接着又道:“你请吧,临行我有句话嘱咐你,今后请不要和郝、胡二人手下为难,你该知道,他们是秉承我的命令办事……”雪衫书生沉声接口道:“譬如郝甫手下四煞,血洗‘白石小树’又像胡梦熊两个盟弟,横霸‘连江’码头,惨杀‘公记船行’等这种勾当,都是你下的命令?”印天蓝沉斥道:“胡说!”雪衫书生冷哼了一声道:“你回答我?”印天蓝道:“你该知道他们因为什么才受我令派行事,你更该明白,他们替我办什么事!”雪衫书生冷笑一声道:“不错,这些事情我明白,你以重金,请他们将大批货物运送过‘女真族’地,可是你却并不知道,他们仍然干着杀人越货的残忍勾当!”印天蓝一楞,道:“你有证据?拿将出来!”雪衫书生道:“当然有!”雪衫书生才待答话,厅门适时被人推开,进来了一位三旬左右,乍看上去相当英俊的中年人!印天蓝瞥目看清来者,黛眉一皱道:“有事?”中年人笑着说道:“蓝妹,没有事就不准我来?”此人话声一顿,目光一扫雪衫书生,问印天蓝道:“此人是谁?”印天蓝不高兴地说道:“我的客人!”雪衫书生这时竟也问道:“印场主,这人是谁?”印天蓝不能不答话,道:“他是……”中年人接上口道:“我姓范,字凤阳,阁下是……”雪衫书生哦了一声道:“原来是范凤阳矿场的场主,失敬失敬。”范凤阳一笑道:“好说,阁下贵姓?”雪衫书生道:“落拓书生,羞提姓氏。”范凤阳双目光华一闪,脸上掠过一丝残酷狰狞的冷笑,这种冷笑,使人印象深刻,进而不觉地发生警惕之心。在这一丝残酷狰狞的冷笑后,随即传出令人更觉寒冷的话声:“朋友,你连个名胜都没有吗?”雪衫书生冷冷扫了范凤阳一眼,转对印天蓝道:“难不是‘老印记’和‘范风阳矿场’已经合并了!”但印天蓝不理睬雪衫书生,却对范凤阳道:“这里是我的待客堂,请你自重!”范凤阳作出关怀的神态,道:“蓝妹你听我说,我已知道了这个人的来意,所以才……”
印天蓝声调一扬,道:“他是我请来的客人,如今正在谈着一件只能由他或我才能解决的事,与你无关,你也不必懂得?”范凤阳颔首道:“这我懂,但是……”印天蓝脸色一沉,手指厅门道:“你懂就好,那就请暂时离开这里。”范凤阳双眉一挑,道:“不,我必须陪你!”印天蓝火了,道:“你别不识趣!”雪衫书生此时一笑,道:“两位不必为了我来争论,再说范场主来得正巧,在我来说,是十分欢迎。”范凤阳目光斜一过印天蓝身上,哼了一声道:“恐怕未必欢迎我吧?”雪衫书生仍含笑意道:“不瞒范场主说,我拜访完了印姑娘,就准备去见场主的,如今场主不请而至,我自是十分欢迎。”范凤阳哦了一声向印天蓝道:“蓝妹听到没有,这样一来,我可以暂时借你这间会客厅堂,和这朋友一谈了吧?”印天蓝没有答话,只皱皱眉。范凤阳放作未见,向雪衫书生道:“朋友,你准备找我姓范的干什么?”雪衫书生道:“问几句话!”范凤阳冷哼两声道:“你很自信,莫非认为姓范的应该有话必答,会告诉你?”
雪衫书生道:“恰好是不,我希望你拒绝答复!”范凤阳一楞,道:“你这人很怪,说吧,想问什么?”雪衫书生道:“外传你是已故老印记主人,‘飞鹏’印盖世的弟子。确否?”范凤阳冷冷地说道:“不错,怎么样?”雪衫书生淡淡一笑道:“印场主故世已有七年,传闻你是带艺投师……”范凤阳接口道:“很对,九年前,为了双方矿山问题,相约会谈,十分佩服老人的德格和武技,遂以弟子……”雪衫书生不待范凤阳说下去,又问道:“又据说,印场主死前年余,你曾聘媒议婚……”范凤阳哈哈一笑道:“大概传说不太清楚,再不就是你没听明白,我与现在的印场主,成婚已有六年!”雪衫书生报之极淡的一笑道:“这点我清楚,不清楚的是,印老场主死前半月,曾有悔婚之意……”
范凤阳抑色随变,吡道:“你敢挑唆离间胡说八道!”印天蓝也由接口道:“你是听谁说的?”雪衫书生对印天蓝微微一笑,不作答复,范凤阳沉不住气,接着又说道:“你要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否则……”雪衫书生头一抬,目光如电注视着范凤阳道:“否则怎么样?”范凤阳嘿嘿两声,那股残酷凉薄而狰狞的冷笑,又自他嘴角眉尖掠过,这也等于回答了雪衫书生!范凤阳的嘴脸,使旁立的印天蓝芳心暗凛,她十分纳罕,相认已久夫妻多年的人,在这一刹那,怎会变了?不错,变了!变得竟加陌生般从未见过的人,那神情,那嘴脸,那令人寒透骨中的笑意,怎会出现在这里?
不对,这人自然并不陌生,更不对的是,这种令人窒息的冷笑,也不陌生,她见过,但却想不起在何处!印天蓝的神情,使范凤阳暗生警意,迅即换了另一种嘴脸,是虚诚的,坦宜的,有些老实堪怜的神色,这种神色,印天蓝看在眼中,温慰在心怀,这才是她认定的范凤阳,自己终身的依靠。但那先前的暗影,却煞是作怪,竟绕行脑海心田,无法抹掉,她摇摇头,像要甩脱掉那丝寒凛的阴影。此时,范凤阳话声又起:“朋友,你知道我们不会对你怎样,不过你这种不当的话语,实在使人无法缄默!”雪衫书生暗中冷哼着,表面却坦然地说道:“传闻也许失真,我原向场主致歉。”范凤阳摇摇头,苦笑一声道:“算了算了,过去了不再谈它就好。”话声一顿,更见诚恳地又道:“朋友问了不少事和话,我还没有请教一声,这是为什么?”雪衫书生摇摇头道:“场主慷慨,不再追究过去了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却必须挖好死人的棺木,找寻过去!”范凤阳心田一凛,这话他懂,但他不能承认懂,固之作煞费心思的神情,楞怔地看着雪衫书生。雪衫书生也正双目凝神直盯着他,印天蓝竟也星眸神射,扫向他的身上,范凤阳只有装糊涂,问道:“朋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雪衫书生目光一扫印天蓝道:“请问印姑娘吧!”印天蓝不待范凤阳开口,黛眉一锁说道:“凤阳,近几年来,你那农矿山方面,不会没有满期离开的工人吧!”范凤阳坦然答道:“有,当然有,可以说每隔十天半月,都有满期离开的工人,有时十个八个,有时多到五六十人。”他话锋一停,以诧疑的眼光看了看印天蓝和雪衫书生,又道:“怎么样,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印天蓝低沉地说道:“人家指责说,那些业已满期身怀巨款的佣工,并没有回家……”范凤阳一笑,接口道:“这也难怪,当年一片朴直的辽东城镇,如今是多繁华,他们久困矿山,乍见那种气象,自会流恋忘返。”印天蓝摇摇头道:“人家却说,大批满期的佣工,不但没有回家,并且也没在辽东各镇居留,而是失踪了!”范凤阳啊的一声叫了出来,道:“这怎么会?”雪衫书生冷笑一声道:“这是事实,怎么不会!”范凤阳皱着眉头,摇着脑袋道:“这简直不可思议!”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他似是突然又想到了什么事情,立刻以诚恳的态度,怀疑的语句问雪衫书生道:“朋友,你既然敢这样武断此事,那一定是有证据的?”雪衫书生目光直盯住范凤阳,一瞬不瞬,对范凤阳的这句“巧妙”问话,不由暗中冷笑,他用“武断”这两个字来形容此事的可疑,最后更直接了当地问雪衫书生要证据,此人之难缠难惹刁滑都可想见了!不过雪衫书生早有成竹,立即回答道:“我早说过,有证据!”范凤阳暗自惊心,但事迫如箭搭弓弦,不得不发,硬着头皮,作出欣然之态道:“那太好了,请朋友指示个明白!”雪衫书生扫了印天蓝一眼,道:“这事印娘姑也知道。”范凤阳“哦”了一声,对印天蓝道:“蓝妹,是吗?”印天蓝黛眉微蹙道:“人家家里的尊长,曾为佣工,和家人相约回里的时期,至期并未返乡,所以……”范凤阳不待印天蓝把话说完,已接口向雪衫书生道:“这就是朋友你所说的证据?”雪衫书生“嗯”了一声道:“莫非这不是证据?”范凤阳豪放地哈哈笑了起来,然后点着头道:“不怕朋友你听了生气,说实话,这无法当作证据,辽东如此大,天下这样宽,一两个人若是突发了游兴,走走名山,逛逛河川,事属平常……”雪衫书生冷哼了一声道:“也许,但总难一去四年杳无音信吧!”范凤阳道:“当然是不该这样久的,只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事,出门在外,保不定遭上什么怪事突变……”雪衫书生低沉地接口道:“范场主说的不错,是经验谈,家叔和舅公,和那千百佣工,就是遇上了突变的怪事,才下落不明!”
范凤阳不能自打嘴巴,于是颔首道:“这也许有此可能。”雪衫书生冷哼了一声道:“他们究竟会遇上什么变故呢?范场主?”范凤阳摇摇头道:“这就很难推测了!”雪衫书生声调一扬,道:“不难,若想通了其中的一件事,就能非常容易地发现他们失踪的原因,和究竟碰上了什么变故?”范凤阳心中又是一凛,不由问道:“哦,那就要烦朋友指教了。”雪衫书生冷冷地说道:“我打听过,以五年期满的佣工,是月入五两银子,年得六十两正,五年期满,连应得利息,共三百六十两纹银,除押约的当日,场方先付一年计六十两纹银作工奴之安家日用外,余银满期日一次付清,这规矩可对?”印天蓝和范凤阳,不约而同地点着头道:“不错,是这样规矩。”雪衫书生目光如同一柄利刃,扫过范凤阳和印天蓝,道:“我又打听过,去年一年,五年级工期满的佣工,计有五百七十名,计算起他们的总收入,是纹银十七万一千两正!”
说到这里,雪衫书生故意停下话来,以奇特的眼光,扫视着印天蓝和范凤阳,范凤阳紧皱着眉头,印天蓝是眨动着睫毛,似有所悟。雪衫书生冷笑了一声,接着说道:“这十七万一千两白银,就是这群可怜佣工,遭遇变故的因素,被人谋害惨杀!”范凤阳没接话,印天蓝却惊叫出声道:“这……这……可是……”雪衫书生似乎明白印天蓝要说些什么,“嗯”了一声道:“我和姑娘有共同的想法,凶手是南北二霸那两伙人……”范凤阳开了口,道:“要是这样,那太好办了,蓝妹火速派人去找来郝甫和胡梦熊,三头六面,问他们个青红皂白水落石出!”雪衫书生哈哈地笑了,笑声如同春雷,震得人心寒胆战!笑声乍停,他话声已起,道:“好主意,只是可惜!”范凤阳故作不解,道:“可惜什么?”雪衫书生道:“一无苦主,二无见证,三无尸体,四无凶器,只凭我所说的这点事实,他们就会承认吗?”范凤阳心中暗自得意而笑,表面上却愁苦着一张脸道:“要是这么讲,那可就没有办法了!”雪衫书生冷冷一笑:“不,办法是有的!”“哦?”范凤阳有些惊心不安了!印天蓝追问不迭道:“你说,还有什么办法,什么办法?”雪衫书生道:“首先请印场主明确地作个决定!”印天蓝双睫一眨道:“可是自即日起,和郝、胡等人,断绝东伙关系?”范凤阳眉头一皱道:“朋友且慢,印、范两场,所以和郝、胡等交结的原因,是为了……”雪衫书生接口道:“我知道,那算不得理由!”印天蓝适时有了决定,道:“好,我答应你?”雪衫书生淡然一笑道:“我先向姑娘致谢,另外我还有个声明,今后哪家矿场,再和郝、胡勾结,我就拿他当作主谋凶手对待!”印天蓝闻言,只是微蹙蛾眉,范凤阳却哼了一声道:“朋友,你这是威胁?”雪衫书生正色道:“我不管范场主你怎么想。”范凤阳道:“朋友你不能不讲理?试想印、范两家,和他们往来多年,一期变脸,就视同陌路,这总说不过去吧?”雪衫书生冷冷地说道:“这没是什么说不过去的,除非有什么不足与外人道的秘密,生怕就此决绝,引起无穷后患,否则不该再有顾虑!”范凤阳仍要答话,印天蓝已开口道:“我说过答应你这件事了,那就是决定,不过今天已来不及办,明朝我会通知他们!”范凤阳急声对印天蓝道:“蓝妹,这件事要仔细考虑才对,别忘了,咱们还有近五万两白银的货物,如今仍在郝、胡的手中存着!”印天蓝沉着粉脸道:“是又怎么样?”范凤阳道:“难道不怕他们一朝翻脸,挟货而遁!”印天蓝哼了一声:“他们敢!”范凤阳唉了一声道:“蓝妹,假如你这位朋友,指罚他们的那件事是实在的话,试想他们连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全敢作,其他更敢……”印天蓝星眸陡射寒光,道:“那就叫他们作作看!”范凤阳看了雪衫书生一眼,道:“蓝妹,何不换个办法,沥渐和他们断绝呢?”印天蓝笑一声道:“凤阳,你该知道我的脾气,我虽然是个女流,作事却干脆利落,我的意念已决,你最好不必再多说什么!”范凤阳作出个无奈的表情,道:“好,不过我必须警告你一声,今后对他们要加意防范了,须知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印天蓝轻蔑哼了一声,没有接话。
雪衫书生微微一笑,对印天蓝道:“姑娘,范场主和你是一家人,他这些请也是好意,小心点总胜过大意。”印天蓝冷冷地说道:“不劳挂心!”雪衫书生依然微笑着说道:“好,既然姑娘胸有成竹,区区自然不便多事,只是如今郝、胡问题业经解决,姑娘所扣押的无辜,是否应该释放了呢?”印天蓝尚未答话,范凤阳已开口道:“蓝妹,什么无辜……”印天蓝没有理他,转对雪衫书生道:“可以,不过在释放此人以前,有几句话要向你说明,这人在万里奔波,不计风雨下,早已染病,古刹被擒前,又遭到封穴之苦,所以现在他很难挪动!”雪衫书生心急于内,淡然的神色权现于外,道:“伤势如何?”印天蓝瞟了他一眼,道:“是病,不是伤!”雪衫书生一笑,印天蓝接着又道:“现在已无大碍,但他体质索弱,恐怕要有十天八天的静养,才能复原。”雪衫书生点点头道:“人在哪里?”印天蓝道:“在我‘锦州’城内的别庄中。”雪衫书生道:“何时能将这人交给区区?”印天蓝嫣然一笑道:“此人既非你的家人,又非朋友……”雪衫书生接口道:“不错,但此人以弱质书生,能不远万里奔波而来,必怀情事,区区义不容辞,要问个明白,或能帮他个忙。”印天蓝又一笑道:“算你会讲话。”声调一顿,印天蓝沉思刹那,接着说道:“这样吧,此间事情,根本不必我来过问,现在我就带去锦州,把人交给你如何?等我换了衣服。”说着,印天蓝转身就走,范凤阳适时相拦道:“蓝妹,留步!”印天蓝停步道:“有事?”范凤阳道:“我想是蓝妹忘了,今夜约好‘杜丹’商量佣工工资的事情,蓝妹若去了锦州……”印天蓝摸口说道:“你作主好了,是一样的。”话声中,印天蓝柳腰微摆,姗娜而去。
范凤阳对着印天蓝的背影,冷哼出声,那残酷凉狰狞的冷笑,又极为自然地现露在眼角嘴边,雪衫书生看在眼中,记于心上。也许是范凤阳突生警兆,迅即恢复了平静,看看雪衫书生,脸上很想做个无可奈何的苦笑,但天性的刚愎和残忍,压制不住有心的矫作,终于又冷哼了一声,骂出一句“贱婆娘!”
“贱婆娘”三个字出口,换来雪衫书生的木楞之色,雪衫书生似乎梦想不到,范凤阳会当着个初见面的人,来漫骂自己的妻子。妙事还有,范凤阳大概要加以解释自己的粗鲁,竟对雪衫书生道:“朋友也许奇怪,我怎会用这种话骂她,其实说穿了分文不值,她就是贱,越在人前,她越不拿我当回事看,没了人,却又说她什么听什么,叫她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夫妇间那……”雪衫书生听不入耳了,插口换了话题,道:“区区听人家说,范场主在没有经营农场以前,曾任过河北步政司使的干吏,可对?”范凤阳一笑道:“不错,是派驻津沽海防!”雪衫书生哦了一声道:“那是好差使呀!”说道“好差使”,范凤阳却够警惕,道:“也没有什么。”雪衫书生一笑道:“范场主可别生气,区区又听了传说,场主及到职的头半年,只有一套便衣,并且还是和另外一位同仁所共有,每当假日,你们交换替穿着出客……”范凤阳神色变了,道:“笑话,这是谁说的!”雪衫书生别有用心地说道:“当然这是笑话,以今日场主的身价来说,自不会再和别人共有一套衫裤,不过英雄何怕出身低。路是人走的,钱是人赚的,只要这些钱,不带别人一丝血和汗,心坦荡,安睡香,已很够了!”范凤阳才待接话,印天蓝已更衣而出,她换了一身黄,鬓间襟前,花饰改作蓝色,美!俊!俏!绝!印天蓝已吩咐人备了车,和雪衫书生微一客套,出厅登车驰去。
“马家老店”,在锦州赫赫有名,店东马千里。是个回回因此他这店里附设的酒楼,不准客人带进,任何菜肉,他那单间或厅院客房,更不准在内饮食。虽说客人要受拘束,但依然宾客常满,只为他这店,干净价廉。
他那东跨院,从今天起有人包租下来,这位客人大概是来头不小,照料东跨院茶水的,竟然是店东马千里本人!马千里啥出身,没人知道,不过传说他有一身“刀枪不入”的外门功夫,这大概和他至今仍是孤家寡人有关系。平日,他只是靠在柜台后面的摇摇椅上,左手团揉着一双钢蛋。哗啦啦地直响,钢蛋早已擦成雪亮,又传说每只足足够一斤重。
今天从东跨院的客人一到,他就没闲着了,现在稍停下来,关照店伙,他也暂住东院了,不见客。不召唤人,谁也不准进去。客人是一大早来的,现在中午头了,悄静无声。
其实,马千里这时正左手紧握着那对钢蛋,端坐在堂屋太师椅上。他双目注视着堂屋门,神态肃穆而严紧,偶而会瞥目向左暗间棉帘一看,但很快地就又注视着前方,这动作令人奇怪。这时,左暗间传出了话声,声音娇柔,竟是女子。那娇柔的声音说:“瞧你,你这是何苦,唉,何苦?”另一个声音,低弱无力,却十分激动,道:“晚眉,我终于见到了你,你……”娇声接口道:“别说话,你病这么重,现在刚刚能开口,有话等这几天再说吧。”低弱的声音,接了话说道:“不,我要说,我好想你,我忍不住了,我也不明白怎么能走到此地,不过我自信,会见着你,现在果然……”娇声吁叹了一下,又接口道:“瞧,你又不听话了吧,我不许你再说话,你再说半个字,我就走,走得更远。到你再也找不到的地方,你信不信?”低弱的声音笑了,笑虽勉强,但却极甜,道:“你还是这样不讲理。”
“启哥,从现在起,我真的不许你开口了!”
“唉!好容易见到你,我有千言万语……”
“我就知道你不听话,别生气,我要逼你睡上一会儿了。”
“我不想困,只想看着你,看着你,你……你……你要……”
左暗间内,静了下来,棉帘一挑,走出来了那雪衫书生!马千里霍地起身,恭敬地问道:“公孙公子他……”雪衫书生微吁一声道:“他不听话,我只好点他睡穴,让他休息。”马千里点了点头,目光向雪衫书生脸上一转,道:“姑娘你……”雪衫书生双目一瞪,“算了,他突然追来这里,我这身份已难掩饰,”马千里倏忽住口,接着诚惶的说道:“小的一时忘记……”雪衫书生突然双眉一蹙,道:“你忙去吧,走更以后过来,顺便做两样可口的菜,一碗浓浓的人参乌骨鸡汤,吃着谈。我忘了,在房里吃东西是不准的,那……”马千里红了脖子,接口道:“姑娘你要也这么说,我可急了,若没有姑娘,那还有我马千里的命在,这店,这……”雪衫书生又是一笑,道:“好了,我逗你的,就这么说定啦。”马千里又应声是,退出了跨院。马逵,马千里的义子,楞怔地看着马千里亲自收拾食盒。从中午后,马千里就没闲着,天刚黑,鸡汤正波,马千里亲下厨房,爆炒羊肚丝,葱白火烤中,做好了这香煞一店旅客的菜,再打开了“佛手香花露”好酒,那冬菇素鱼,麻油薰海带,更是无上妙品,然后马千里挽着食盒,小心迈步奔向东跨院。马逵看傻了,开了口道:“义父,您老这是招待谁?”马千里扬声道:“少问!”马逵头一摇道:“您老忘了,客房里不能开饭?”马千里眼一瞪,道:“妈巴子的,从前不能,现在能,别的客房不能,东跨院内能,妈巴子的你懂?”马逵老实,说话更老实,道:“不懂。”马千里叱斥道:“不懂更好,那就滚远点别碍事。”说着,他已走出了厨房,转向通往后面东跨院的巷道。
马千里进了东跨院,立刻回身急扣上了那个“月圆门”,雪衫书生已推开堂屋木门走出,含笑道:“辛苦你了。”马千里提起食盒,大步进屋,手忙脚快,刹将那酒菜摆好,手一垂恭恭敬敬地说道:“公孙大侠快请……”话没说完,左暗间棉帘挑处,素衫少年已走了出来。素衫少年公孙启,脸上的病态已失,看着马千里,剑眉一挑道:“马老大,你真要看得起我公孙启,不要就直呼姓名,再不,亲热点叫我声老弟,若再称一声太侠,恕我不敢高攀了。”
马千里慌了手脚,一个劲地回头看那雪衫书生,雪衫书生不由娇笑着说道:“看我有什么用。我也正预备这样对你说呢,干脆,你叫我郭三弟,称呼他老二,你当大哥!”马千里双手直摇道:“这……这小的死也不敢!”公孙启寒着一张脸道:“那么好办,在下告辞就是,马掌柜可莫要轻生!”他说要走,还真就走,这可急坏了马千里,慌不迭道:“好好好,怎么说怎么好,千万别走。”公孙启笑了,雪衫书生也笑了,他们两个人挤挤眼,马千里恍然大悟上了当,但他无话好说,只有连连摇头。
入座,三人边谈边饮,东路院外,突然传来马逵高昂话声:“喂喂喂!我说过小店没有这么个人,你可怎么还往里闯呀?”马千里停了筷子,一双浓眉紧紧的皱起。这时,话声又起,是个女人的腔调道:“马逵,你不认得我?”马逵声调仍然很高道:“认识你也没有用呀,没这个人就是没这个人……”话没有说完,又有个密亮的嗓音接上话:“你小子可把眼珠子睁大点,我们印场主是何等身价,别说是你小子,就是你干老子马千里,也不敢对我们场主这样说话!”马千里虎的站起,大步往外就走,院外印天蓝已向手下怒斥道:“你们给我滚到店外去,快!”话声一落即起,这次又转对了马逵,道:“马逵,我打听得很清楚,这人住在你家跨院,这样办好不,你替我进去问一声,就说我印天蓝来拜,人家愿见我就进去,人家说个不字,我扭头就走如何?”堂屋中的雪衫书生,这时扫了公孙启一眼道:“启哥你说……”公孙启一笑,接口道:“你该请人家进来的。”雪衫书生开口一笑,对正好已走到门口的马千里道:“那就麻烦马大哥代为肃客吧。”公孙启头一摇,道:“不,人家是冲着你来的,你该去接。”雪衫书生瞟了公孙启一眼,又一笑道:“你的想法我明白,接就接,反正都是女儿身,到最后也不过是闹场笑话,我才不怕呢!”说着,她果然闪身起座,快步而出。马千里值此机会,紧行几步到了公孙启身边,低声道:“公孙大……不,老弟,你当真再也不施展那身盖世无双的奇技了!”公孙启笑一声道:“不错。”马千里浓眉一皱道:“可是辽东不比中原,姑娘一个人再能干,本领再大,怕也是独力难支,老弟你怎能忍心看她的笑话?”公孙启星眸一辉道:“马大哥,莫非辽东道上,还真有功力技艺过她的人?我相信晓梅应付得了!”马千里犹豫了刹那道:“这难说,就拿印天蓝讲吧,功力够深,据说她生平还没碰上过对手,还有那范凤阳,十有八九是身怀奇技!老弟有所不知,我奉姑娘谕示,暗中侦访失踪佣工事已很久,发觉幕后人物非只歹毒刁滑,更具罕见的智力和身手,那人……”
话正说到这里,印天蓝在雪衫书生陪同下,已步入堂屋,马千里立即住口,并且作恭敬的样子走向一旁。印天蓝扫了马千里一眼,冷冷地一笑道:“原来马掌柜也在。”马千里也笑着,对印天蓝拱手道:“老没见印场主照顾小号了,您老好?”印天蓝目光一扫桌上的残酒菜肴,哼了一声:“马掌柜,如今客房中能摆酒宴了?”马千里头一摇道:“不能。”印天蓝黛眉一挑,手指桌上酒菜道:“那这是……”马千里冷冷地接口道:“这不同,客人有病。”印天蓝又哼了一声,转对公孙启道:“还认得我吗?”公孙启扶桌站起,笑道:“荒郊古刹,在下不幸落入一些恶徒手中,蒙女英雄相救,昨夜方自女英雄府上分手,怎会不识呢?”印天蓝一笑,回顾雪衫书生一眼后,又转对公孙启道:“你身体复原得真快!”公孙启从容而答:“托女英雄福。”印天蓝突然身躯斜退,目光在公孙启和雪衫书生脸上,紧迫地看看,雪衫书生微微一笑道:“印场主,你看我们像兄弟吗?”印天蓝被雪衫书生讲透心事,笑了,道:“大概是错了。”雪衫书生肃敬印天蓝入座后,自己坐于公孙启对面,才答道:“大概本来是错了,区区早有声明,并无兄弟,这位公子复姓公孙,远来辽东的目的,却和区区相同……”话没说完,印天蓝已接口道:“那好极了,我突来拜望公子。是为了释疑,明午我就回山,想请公子到我那矿场作客几天,顺便可以调查一下有关失踪佣工的事,既然公孙公子也为寻访亲人而来,我希望也能答应……”雪衫书生接口道:“这是印场主个人的意思?”印天蓝一笑道:“你好聪明,今天凤阳来了,他认为这件事我们应该有所澄清,否则谣传太多,将使佣工裹步,所以……”公孙启剑眉一挑道:“印场主现在来了,范场主呢?”印天蓝坦然地说道:“他回山了,说该叫人准备一下接待事宜,再说山上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必须早早地预备才行。”说到这里,印天蓝对雪衫书生嫣然一笑,又道:“大侠客你该明白,月魄追魂是何等人物,不是轻宜能路到作客啊?”雪衫书生神色一正道:“场主有这大把握,月魄追魂一请必到?!”印天蓝尚未开口,公孙启哈哈一笑道:“晓弟真笨,就因为如此,范场主才请印场主亲自驾临,那自是有十成把握的事!”印天蓝也许外貌聪智,内心忠厚,没能听得出来公孙启话中有话,也许她被另外一件事情,引开了思路,所以她接话道:“公子你称呼谁‘小弟’?”她将“晓”字,误听认作了“小”。
雪衫书生郭晓梅,并非须眉,是位道道地地的娇娇姑娘,但因从小被家人、亲友视若男儿,又穿惯右襟扣的男儿衣衫,外人是难以分别的。当着印天蓝,公孙启不能以“晓梅”相称,改作“晓弟”。印天蓝误听,公孙启正好将错就错,道:“难道印场主还不知道,她是舍弟公孙眉?”印天蓝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道:“他……你……姓公孙?”公孙启禀了一声道:“这没有错,不信马掌柜就是证人!”马千里老江湖,立刻道:“公孙公子是甘凉世家,老朽昔日在甘原落魄,若非公孙公子昆仲相扶,焉有今日,所以……”他手向桌上的残酒剩莱一指,又道:“所以才能破例。”印天蓝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郭晓梅却白了公孙启一眼,公孙启故作未见,对印天蓝道:“本来如此。”印天蓝却眉微皱,似是自语般说:“公孙梅,梅?梅?该是个女人名字嘛?”她又将“眉”字,误作了“梅”,公孙启若无其事地点头道:“不错,舍弟生来多病,老人家从俗,生怕舍弟太娇,永远长不大,改个女儿名字,据说好养些。”晓梅鼓起了小腮帮,狠狠地瞪着公孙启,马千里看在眼中,笑不敢笑,硬蹩在脸上,状极滑稽。印天蓝瞥目看见,心中掠过了一丝疑云。公孙启竟哈哈一笑道:“别气,晓弟,如今你已经长大了,并且强过我这个作哥哥的,只瞧你在辽东闯出来的威名,足证不虚,对于幼年间事,偶而一提,何伤大雅,这值不得生气的。”晓梅闻言更气了,可是印天蓝心头的那丝疑云,却被公孙启这几句话,驱散天际,无影无踪,并且她手掩擅口,笑了出来。马千里如今再也忍不住了,也哈哈地大声笑着。晓梅手指着公孙启,才待开口,公孙启已抢先道:“闲话到此为止,晓弟,人家是来奉请你的,去不去总该给人家个话吧?”晓梅心里有气,头一摇道:“不去!”印天蓝一楞,公孙启却道:“以我看,你是该去的。”晓梅好容易有了使公孙启为难的机会,怎肯放过,道:“要去你去!”公孙启一笑道:“我怎么能去,第一,人家是专诚请你,在情在理,作哥哥的代表不了弟弟,第二,我手无缚鸡之力,万一应了那‘宴无好宴,会无好会’的古话,我岂不是死路一条,就为我偶提幼年事,你就这样狠心,不是太无‘弟恭’了吗?”
印天蓝慌不迭正色说道:“公孙公子这是什么话,我印天蓝虽系女子,但敢生平待人磊落光明,此番上山,设有二心,天必……”话未说完,公孙启“唉”了一声道:“印场主你真笨,我这是对舍弟用的激将法,你这么一声明,完了,全功尽弃!”印天蓝脸红了,转向晓梅道:“你当真拒绝我诚意的邀请?”晓梅目光一扫公孙启,有了主意,道:“场主也请……家兄?”印天蓝不明所以:“当然该一道奉请。”晓梅头一摇道:“他去我就不去!”公孙启立刻摆手道:“不,不,不,印场主,在下一向是惟舍弟之令从事,他说不叫我去,我就只好不去,事情就如此说定了。”晓梅习惯上对公孙启一向不让,因之接话道:“怕你不听!”印天蓝又一笑,道:“难道我讲个情都不行?”公孙启接话道:“说实在的,在下身体尚未复原,山上气候酷寒,怕我这单薄的身体抗不住,舍弟是好心,印场主该明白的。”话说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已不用再讲,遂作决定,印天蓝立刻告辞,为了礼貌,晓梅和马千里送行,公孙启以身体不支为借口留下。
潇湘子扫描 风云潜龙OCR 豆豆书库独家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