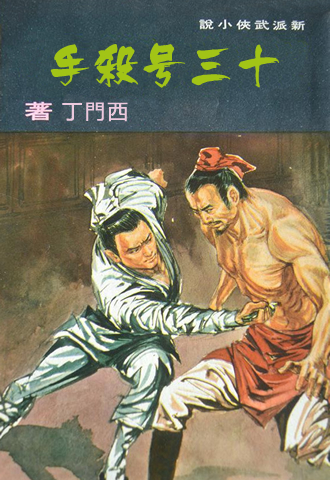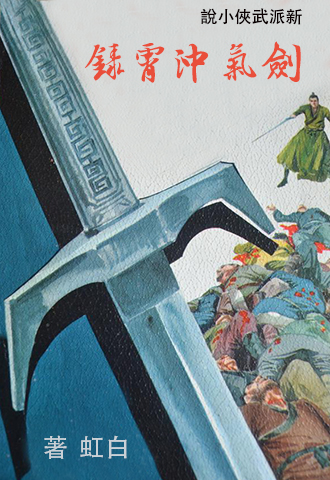贺耕原也真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眼见刀光闪来,并不慌张,脚下一错,使个身法,让过刀锋,嘴里说道:“小乖乖,我早就看出了你会有这一手了,还有什么用呢?”
说着剑已递出,凑上绣鸾刀,一绞之下,便把一把绣鸾刀绞飞了出去。
原来贺耕原一到庙前,便已听出红娘子娇喘之声,知道她必然藏身在庙门背后,尽等自己进去,暗下毒手,这一看出之后,不由得微微一笑,仗着艺高人胆大,也不迟疑,胸有成竹地便去推门,红娘子当然就砍他不着了。
红娘子一刀不中,反被把刀绞脱出去,心中更慌,正想向庙里逃走,可是贺耕原已经挤身进了庙,横着剑,正挡在红娘子的面前。
笑着说道:“小乖乖,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辄儿呢?乖乖儿的替我把刀放下,我有话要和你说,绝不伤你的性命就是。”
红娘子虽听贺耕原这样说了,因为不知道贺耕原的目的何在,所以并未相信,仍然一举手中的那一把绣鸾刀,又对贺耕原拼力扑来。
贺耕原笑道:“这有什么用呢?你是不相信我的话是不是?我若想要杀你,便是十个你,也早就杀了,还用得着来骗你吗?”
说时一招“披云摘月”,早已又把红娘子的绣鸾刀,摘到手中,向地上一抛,连自己的剑也舍了,欺身而上,两手一伸,便把红娘子拦腰抱住。
红娘子一惊之下,本能地尖着嗓子急叫了一声,又伸手向贺耕原的脸上乱抓起来。
贺耕原既然擒住了红娘子,又哪里还在乎她的这一套,因此一面笑道:“这里四无人烟,你便喊死了也不会有人来的,还是乖乖儿的不要动,免得自己多讨苦吃。”一面又使了个擒拿手法,把红娘子两只手,一齐制住,抱着红娘子,便向佛殿上走。
红娘子至此,也就瞧出一半来了,因此放大了胆问道:“你打算要对我怎么样?”
贺耕原笑道:“还有别的怎么样吗?以你这样的美貌,陷身贼中,尽和熊胡子做一起,固然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里,而我这样的一个人,也不见得就会辱没了你,说什么也要比熊胡子强,你道是与不是呢?现在这里四下无人,我们……”
说到这儿,便又凑上了红娘子的红腮之上,亲了一下,贼忒忒的一双眼睛,尽瞧着红娘子直笑,脚下也并没停住。
红娘子在贼营之中,对于这些事,本来就是跟喝茶喝水一样的,是家常便饭,并不认为奇怪,何况又真的见识过贺耕原的武功,确实要比熊胡子高明得多,并且虽然贺耕原也是个络腮胡子,但比起熊胡子来,却已经漂亮得多了,更何况又年轻的多呢?
所以心下早就愿意,因此说道:“那为什么还要制住我,给我苦头吃呢?”
贺耕原知道她是肯了,并且也不怕她逃走,因此便释手放她下地,二人厮搂着走上佛殿,依着贺耕原,便想唱一个玉堂春里的关王庙,还是红娘子不肯,便又找到了一间禅房,里面有床有椅,虽无袤枕,倒也可以将就。
一阵事了之后,双方都觉得非常之满意,便又亲热了好一会儿,这才相偕起身,又商量了一阵子,便决定了由红娘子先回贼营,去打埋伏,然后贺耕原带人前去劫寨,杀了熊胡子,一则可除掉红娘子的后患,再则红娘子也就成了龙村中的有功之人,谁也不能阻止他们二人的好事了。
二人计较既定,这才相将出庙,寻回了武器马匹,恋恋不舍地各人上马,分道各自回营的回营,回村的回村。
这说按下红娘子不谈,单说贺耕原一人打马回转龙村,心中真是越想越觉得高兴,心想:“真的把熊胡子杀了,我这场功劳,也就不小了,到了那时,龙村便等于是我保了下来,还不是我想怎么样,便能够怎么样吗?又何况我还可以暗暗的示意龙伯高,表明白兰花是我让给他的,他当然也就要对我另眼相看,认为知己了。”
贺耕原就这么一路之上,自我陶醉的想着,信马而行,所以直到日没之后,方才到了村头,抬头一看之下,不由大惊。
原来有一个女人的人头,正悬在庄前高竿之上,血迹犹新,再仔细一看,不是红娘子的,还有谁的?因此心头大乱,连忙进庄,看到龙伯高,便跳脚说道:“这是谁做的事,这不是误了大事了吗?”
龙伯高本来尚未知道一切,便问何事?
贺耕原道:“是谁把红娘子杀了的,我已经和她约好今夜我们前去劫营,由她做内应,准保可以取到熊胡子的头颅,这一把她杀了,不是就误了大事了吗?”
龙伯高道:“竟有这样的事,那仲平他们的确是杀错了她了,不过事已如此,贺兄也就不用再着急了,因为熊胡子看到了红娘子的头颅之后,立刻拔营遁去,现在贼围已解,目的已达,贺兄只准备畅饮庆功酒吧!”
原来龙仲平、禹颖达和诸天寿出村之后,便追了上去,不久之后,也就来到那片树林之前,一眼便看到了贺耕原和红娘子的马,三人不由得相顾一视,依着龙仲平,便想立刻去找他们。
但诸天寿却把龙仲平和禹颖达拉到一边,说道:“我们就是要去,也不能就这样前往,必须暗地里前去,才是道理。”
龙仲平和禹颖达当然同意,三人也就把马藏好,穿进树林,四处寻找,结果贺耕原和红娘子没有找到,却找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人正慌慌张张地向前急奔。
龙仲平一看,便认出是村子里的一个人,也姓龙,名叫小毛,便上前喊住,问他何事这样惊慌?
龙小毛一看是龙仲平,连忙说道:“二叔,你过来,我告诉你们一个新鲜消息。”
说着便把龙仲平向一边拉,禹颖达和诸天寿也就跟了上去。
龙仲平问他有没有看到贺耕原?
龙小毛说道:“你听下去就会知道了。”
接着便说道:“今天该我出来打柴,我知道这里轻易不会有人前来,因此就独个儿来了,哪知正在砍柴之际,忽然听到了有马蹄之声,远远传来,当时我正爬在树顶上,所以一看便看到了正是贼妇红娘子,把我吓得从树上跌了下来,连忙奔进庙里去躲避,因为庙里别的都没有了,无处躲藏,只剩下东厢屋里还有一米囤子在那儿,我躲了进去,根本就不会被人想得到。
哪知我才进去后不久,便看到那贼妇也进了庙门,手举钢刀,在门后等着,我那时还不知道她等的是谁,但已为追她的人担心,只是我又不敢出去。
哪知就在这时,庙门一开,贺教习又闪了进来,那贼妇也就当头一刀,对贺教习劈了下去,我一看之下,竟几乎吓得叫出声来,可是贺教习不知怎么一来,便把那妖妇的刀给磕飞了,后来……后来……”
龙小毛说到这儿,竟吞吞吐吐再也说不下去。
龙仲平是性急的人,连忙问道:“后来怎么样?”
龙小毛道:“我不敢说,说出来怕以后使贺教习听去,会要我的命。”
龙仲平道:“你告诉我们,我们不说出去也就是了。”
龙小毛这才接说道:“后来贺教习便把那贼妇擒住了,要贼妇嫁给他,那贼妇也就答应了。”
龙仲平道:“竟有此事?现在他们人呢?”
龙小毛道:“还在那庙里快活呢?我看到他们走进了和尚的房间,又等了一会儿,直到听到他们两个都在喘气,知道他们这时一定不会有空来注意到我,这才壮着胆子,爬出囤外,蹑着脚向庙外开溜,到了门口,回头偷看了一下,他们不就正在和尚的床上吗?
我怕被他们看到会送命,又想着这事不小,所以打算赶快赶回村去,向村主龙大叔报告去呢?”
龙仲平等三人听了,都不由得面面相觑起来,依禹颖达,便恨不得立刻赶去庙中,杀了他们才称心,还是诸天寿拦住,说道:“且慢,我们应该先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说,如果他真的要通了贼,当然可以杀了他,如果他只是玩弄个贼妇,我们便不妨把这事报于伯高兄,由他去处理好了。”
说着便又问龙小毛道:“你还听到他们说了什么没有?”
龙小毛摇摇头道:“再没听到他们说什么了。”
禹颖达问道:“他有没有说过要通贼的话呢?”
龙小毛道:“我不懂,我也没有听到。”
龙仲平等三人同议了一阵子,依然毫无结果,可是这时贺耕原已经和红娘子手挽着手,亲亲热热的出了庙门,向林中走来。
龙仲平等三人看到,便连忙带着小毛,将身藏起,直等贺耕原和红娘子分道而行,这才出来。
禹颖达已急不能待的说道:“这事万分蹊跷,如果说他们没有阴谋,为什么红娘子不跟他一起回村呢?我看不如先下手为是。”
龙仲平听了也作急起来,认为有理。
还是诸天寿比较谨慎,说道:“不可,现在他恶行未彰,且无证据,我们哪能随便杀人,倒不如先把红娘子擒住,问个明白为是。”
龙仲平就同意了,三个人便向红娘子赶去。见面之后,没上几招,红娘子便被诸天寿打下马鞍,摔倒在地。
诸天寿正要打前捆缚,哪知禹颖达别有用心,早就起手一刀,把红娘子一颗伶伶俐俐的头,割了下来。
诸天寿想拦都没来得及,便埋怨禹颖达鲁莽。
禹颖达笑道:“这种淫妇,留下她做什?便是贺耕原不想投贼,万一把淫妇弄进村中,终是祸胎,倒不如砍了干净,我们还是赶快回去,报与大哥得知吧!”
龙仲平和诸天寿也就无可奈何,只好带着人头,上马抄近路赶回龙村,把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龙伯高。
龙伯高也觉得禹颖达做事,太嫌任性了一点,但事已过去,悔已无及,便叫人把红娘子的首级,号令城上,贼众一看,连忙报于熊胡子,熊胡子吓得哪里还敢再留,当即率领贼兵,纷纷遁去。
所以等到贺耕原回到庄上,向龙伯高一说,龙伯高觉得没有什么,也就轻描淡写的把事情扯了过去。
贺耕原虽说心中气愤,但已无可奈何,不过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极微妙,所以俗语说得好:“有三个和我好的,当然也有三个和他好的。”
贺耕原虽说居心不正,但面前总还有几个人,因此没有几天,这事的详细情形,便传进了他的耳中,从此不但把龙仲平、禹颖达和诸天寿恨得要死,便连龙伯高也都一起恨上了,有心想离开龙村他去,但一则无路可走。
同时,也还舍不得就把白兰花给轻易丢下,总想白兰花对他能有一份真情,在龙伯高手里,把银子骗足以后,和他一同私奔,因此这才又耐心耐意的住了下来,其实白兰花母女是个怎等样人,别说龙伯高在地位上,在家财上,都要比贺耕原强,即就是在人品上来说,龙伯高是个翩翩佳公子,贺耕原又哪一点能比得上他。
因此在“妓儿爱俏,鸨儿爱钱”的这两大原则之下,白大娘固然巴不得白兰花能够嫁给龙伯高,而白兰花也就早已对贺耕原的那一脸的络腮胡子,感到厌恶万分了,只不过是怕他的狠,才暂时还不敢得罪于他罢了。
这也是合该要出事,刚好龙游县又有信前来,请龙伯高派人去替他看看所组织的团练如何?龙伯高当然不能推却,正在考虑谁去,而贺耕原已闻讯赶来,上前请命说道:“此事让小弟前去一趟吧!近来小弟无事可做,感到非常烦闷,便乘此出去走一趟,藉此散散心也是好的。”
龙村对于贺耕原,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让他单独出去,这当然也就是不太相信于他所致,只是现在贺耕原既然当面向龙伯高要求,龙伯高实在不便拒绝于他,但脑筋一转,便已得计。
笑着说道:“这就再好也没有了,我本来已决定请广生兄前去辛苦一趟,广生兄客气,说是恐怕一人能力有限,怕办不好,现在既然耕原兄不辞劳苦,便请你们两位同去一趟,不是要好得多了吗?同时广生兄回来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米要带回来,有耕原兄相帮照应着,也就要安全得多了。”
龙伯高要孔广生和贺耕原同去的用意,孔广生当然知道,是在拒绝不得之下,要他前去监视贺耕原,孔广生本来不大愿意,但再一听到龙伯高提起米的事来,也就不便再拒绝了。
原来龙村这几个月以来,由于不断与贼相拒,开支既大,而农事又废,原来种下去的,也被贼糟蹋无余,所以不独口粮发生了恐慌,便是在经济上,也有点捉襟见肘,接济不上起来,直把个龙伯高急得走投无路。
这事被孔广生听到了之后,便想起了自己怀中的蛇珠来,虽然说已经为着合药,用去了几粒,但还有十几粒存在身边,算起来也还值十几万银子,这时拿出来,不是正好派上用场吗?因此立刻去和龙伯高说了。
龙伯高也是个非常爽快的人,又知道孔广生做事实在,并非虚语,因此大喜,立刻把这份人情接受了下来,只说了一句:“等贼氛过去之后,再容设法归还吧!”
然后立刻命人带着珠子,到城里去找到了一个大主顾,把珠子脱了手,收购了三万担粮米,另外还带回了几万银子应用,这粮米搬运起来,当然并不简单,既怕饥民,又怕盗贼,所以早就计定,非孔广生亲自前去接运不可。
这事交代明白,不必多赘。
单说孔广生和贺耕原到了龙游之后,便帮着那位县太爷把团练整顿了一番,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总算一直平安无事,十天以后,就又接到了龙伯高的来信,催他们紧快回去,信上并没有说明是为着何事,孔广生只猜想是村中可能是口粮不继,因此连忙向龙游县告辞,把粮米装运上路,和贺耕原两人押回龙村。
龙伯高闻讯,早已春风满面的老远的接出庄来,笑向两人道了辛苦,接着又说道:“两位兄台回来得正好,今晚便请赏光,小饮三杯,一来为两位兄台洗尘,二来替小弟增光如何?”
孔广生不知何事?便问所以。
龙伯高笑道:“这事说来惭愧,小弟素有寡人之疾,平生不耐孤衾独宿,所以自从两个小妾相继亡故之后,便觉得郁郁寡欢,刚好村子里有一家人家,知道了这事,自愿把女儿送给小弟为妾,小弟情实难却,也就只好老着脸来个受之有愧,却之不恭了,今晚便是吉期,两位兄台不是回来得正是时候吗?”
孔广生听了,倒无所谓,只向龙伯高贺了一声,也就算过,自去洒浴更衣,休息不提。
而贺耕原听了,立刻心上一惊,便知道不妙,虽然当时也一般的向龙伯高道贺,答应晚上一定准时前去,但心里早就乱成一团糟了,在向龙伯高告别之后,也等不及洒浴更衣,便放开脚步,向白兰花的家中走去,到得门前一看,果然门上已经是铁将军把门,白兰花母女都不知道何处了。
虽说如此,贺耕原仍未死心,还存着一线希望,希望白兰花已经银钱到手,离开了龙村,那么自己还可以前去寻访,重新聚首。
哪知向左邻右舍一打听之下,白兰花不是为龙伯高娶了去,还是什么?因此一方面好似冷水浇头,一方面又不由得怒火中烧,外冷内热,人也就变成矛盾非常,又是心灰意冷,但又恨不得立刻便把龙伯高和白兰花杀死刀下,这才觉得畅心。
因此在白兰花的门前,站了好一会,又转了几个圈儿,然后这才一咬牙,一跺脚,掉头匆匆便走,可是走没几步,就又慢了下来,信足而行,来至一家酒店门前,抬头看了一阵子。
店家的人本来认识于他,忙迎了出来,赔笑说道:“贺教习,你回来啦!这趟可辛苦你啦,想喝几杯吗?请进来坐吧!”
贺耕原只点了点头,并未进去,反说了一句:“给我送一坛好酒,配几样可口的小菜,送到我的下处去。”说完之后,丢下了一块银子,掉头就走了回去,这且不谈。
再说龙伯高的家,已经布置得喜气洋洋,人来客往,道贺的络绎不绝。龙伯高更是里里外外忙个不停。
龙仲平和禹颖达两个,是见了酒就是命的人,这一天早已拉住诸天寿,痛喝了一天。
就只有龙经礼有点愁眉苦脸,好象陷藏着一腔心事似的,一直等到孔广生来时,这才把孔广生拉到一边去说道:“贤侄!我把你当做自家子侄,才和你商量,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才好?”
孔广生道:“叔父有事,但请明示,小侄无不尽力。”
龙经礼道:“难道贤侄还不知道目前恐怕就要出事了吗?”
孔广生道:“小侄出去多日,难道这些日子当中,又发生了什么事端来了吗?刚才看到伯高,他怎的未见说起呢?”
龙经礼摇头叹气说道:“此事由来久矣,而伯高当局者迷,他也正在神魂颠倒,又怎么会知道什么呢?再说即使就是他明明知道了,恐怕也未必便肯就此歇手呐。”
龙经礼这么一说,孔广生大概也就有了一点数了,便问道:“叔父所说,莫非是指着伯高今日纳宠之事而言吗?”
龙经礼道:“你也听到了什么话了吗?”
孔广生道:“侄儿这不过是猜测之辞,并未听到有什么言语,便是新妇何人,侄儿还不知道是谁呐!”
龙经礼这才把龙伯高纳白兰花为妾的事情说了出来,并且又说出,白兰花曾和贺耕原相好之事,因此说道:“你瞧,伯高这不是做了一件糊涂极顶的事了吗?”
孔广生听了,也不由得皱起眉来说道:“叔父既然知道此事有许多麻烦,为什么不早告诉伯高得知,我相信伯高兄虽说是寡人有疾,但也未必肯强夺朋友之所好,而做出这种糊涂事来的。”
龙经礼道:“我若早知道了,又哪有不说之理,别说是有这许多顾忌在内,便是伯高要想纳妾,我虽然未便加以禁止,但他要取这样一个粉头回家,我也非加以干涉不可了,只是这事却来得突然,一直到今天早上,那粉头进了门,我才得知,等我觉得不妥,去找伯高时,他又接你们去了,及自他回来之后,来客已经满堂。
我当然要替他顾点面子,不能当着人给他难堪,所以到现在还没捞住机会和他开口呢?老贤侄,你看这事如何是好?”
孔广生道:“那么伯高兄知道不知道白兰花和贺兄之间的事呢?”
龙经礼道:“这却不得而知。”
接着又叹了一口气说道:“恐怕事已如此,他就是知道了,也未必肯听劝呐。”
孔广生又想了一想,这才说道:“既然如此,叔父空自作急,也无用处,我们大家多担一份心,防着点儿,也就是了,不过刚才伯高去接我们的时候,也曾说起这事,贺兄好象若无其事的还向伯高兄道了喜似的,这些风月场中的规矩,小侄虽然不懂,但凭理而论,贺兄也许不至于会因为一个粉头,去恼掉一个朋友吧!”
龙经礼道:“真的贺耕原答应了来喝喜酒吗?”
孔广生点头应是。
龙经礼才放下了一点心,又和孔广生谈了一些将来整顿之事,仍认为长把贺耕原留在村中,终是祸根,且在不经意之中,又说了一句:“他是一个外人,知人知面不知心,谁又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些什么鬼主意。”
龙经礼这话,虽然是冲着贺耕原而言,但孔广生也是在龙村做客,虽然听了不至于便多龙经礼的心,但到底再接不下话去,不便表示自己的意思了。
好在这时华筵已张,龙伯高派人找了来,请他们去入席,孔广生也就乘此收场,来到大厅之上,只见人头钻涌,笑语喧哗,都已坐下,只剩下当中一席,尚缺着好几个座位。
这席上已经坐着的,便是龙村二三两父老,和诸天寿、龙仲平和禹颖达几个,禹颖达的儿子小达,死赖在诸天寿怀里不肯走,一定要和诸叔叔坐在一起。
堂上红烛高烧,琉璃灯也一律点齐,照得堂上堂下,如同白昼,在旁侍候斟酒上菜的人,更是往来穿梭一般,好不热闹。
龙伯高一看到龙经礼和孔广生,连忙招呼说道:“大叔和孔兄快来,现在就等着你们了。”
白兰花打扮得满头珠翠,低头带笑,手捧酒壶,紧随在龙伯高的身边,见龙经礼和孔广生来到,立刻上前斟了酒,又低低的说了一声:“大太爷请入席。”
龙伯高便推孔广生上座,孔广生哪会肯,又拉了半天,还是由龙经礼坐了首席,白兰花又斟了一巡酒,这才告辞,退进后堂,堂上的人,也就开怀畅饮了起来。
孔广生是个细心人,四面一看,未见贺耕原来到,便开口说道:“怎的贺兄还没来呢?”
龙伯高听了,也才发觉,忙道:“我已命人去请过好几次了,怎的还不见来?”说着便查问是谁去请的。
早有人上前回道:“贺教习在他的下处,一个人把房门关上,在里面喝酒,我们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龙经礼和孔广生听了,便不由得相到对看了一眼。
龙伯高不知就里,还催人立刻去请,说道:“这是什么话?我这儿有喜酒不来喝,要一个人关在房时喝闷酒,这怎么可以呢?你们赶快与我前去,拉也得替我把贺教习给拉了来。”
龙伯高话声才了,庭前人影一闪,已从屋檐上飞下来了一个人,狂笑说:“你打算请我喝喜酒吗?不用去请了,我已经自己来了。”
大家一看,不是贺耕原还有何人,这时他已喝得满面通红,醺醺大醉,手里还提着一个空酒坛子,摇摇晃晃地便向厅上走来。
龙伯高见了,笑着说道:“贺兄,你怎以到这时候才来呢?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现在别的也不必说了,来迟罚酒三杯,你快来先把这三杯罚酒喝了下去再说吧!”
贺耕原仍是哈哈大笑,叫道:“你伯高兄是个够朋友的了?好吧!该罚多少,我喝多少好了,不过我的酒已完了,你先替我把这个坛子装满了,我来喝就是。”
说着一伸手,便把手中的空酒坛子,对着龙伯高的头颅,直抛过来,来势之猛,疾如闪电。
龙伯高没想到他会有这一着,竟几乎被酒坛子砸个正着。
幸亏贺耕原一照面,孔广生看他神情不对,早就对他留了心,所以一见他用酒坛子对龙伯高砸来,连忙伸手一拍,把个酒坛子拍落地上,打了个粉粉碎碎。
贺耕原来此,本来就是倚酒三分醉,打算来大闹一场,好出出心中闷气,正感到无题可借,一看到孔广生拍碎了他的酒坛子,因此立刻冲到孔广生的面前。
指着孔广生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也狗仗人势,胆敢打碎了我的酒坛子,你赔我的来,否则我便要你的命。”
孔广生也不动气,只笑着说道:“贺兄请坐,这里有的是好酒佳肴,你请坐吧,爱吃什么,便有什么,小弟奉陪就是。”
贺耕原哪肯坐,眼睛一瞪说道:“你不肯赔吗?好,你问我想吃什么是不是?告诉你吧!我想拿你的脑袋来下酒,你就给了我吧!”说着用手把另一桌上的一个人一推,推倒在地,随手拾起了那张椅子,便对着孔广生直劈下来。
大家看了,都不由得惊的哄叫起来。
孔广生又哪里能够让他砸到,一伸手便把那张椅子接住,贺耕原夺了几夺,并没能夺得回去。
禹颖达早已忍耐不住,在旁边跳了起来,指着贺耕原大骂道:“姓贺的,你别倚酒三分醉的前来生事,是识相的,乘早替我回去安安稳稳的挺尸去,再闹下去,便说不得要给你丢人了。”
贺耕原立刻又放下椅子,舍了孔广生,扑奔禹颖达,说道:“你想挺尸吗?大爷便成全了你吧!”话未说完,遥遥一掌,便对禹颖达打去。
还是孔广生运起“先天大乘神功”,把贺耕原的“排云掌力”挡住,禹颖达方才没有吃亏。
贺耕原便又疯狗似的,转向孔广生,孔广生也不还手,一味躲让。
诸天寿也就忍不住了,把禹小达交到禹颖达的手上,一闪身便到了贺耕原的面前,把他截住,不准他再对孔广生胡闹。
贺耕原狂笑说道:“你们都一起上来好了,大爷如果惧了你们,再不姓贺。”说着一招“指路问樵”,便对诸天寿喉头点到。
诸天寿见贺耕原出手狠毒,也就动了真火,喝了一声:“姓贺的,对付你,还用得多人吗?”
说着也就还手出招,略一闪身,便已让过,跟着出手如电,叠伸两指,便对贺耕原胸前点去。
贺耕原的武功,本来就不如诸天寿,何况他这时酒也真的喝多了一点,更何况诸天寿的这一招,乃是八卦掌中的绝招。
贺耕原又哪里招架得开,同时四面都挤满了人,连闪让的余地都没有,眼看着便非被诸天寿点着不可了。
孔广生在旁看了大惊,连忙喝道:“天寿弟,不准伤他。”
诸天寿听了孔广生的这一声喝,方才在间不容发之间撤招收回,否则的话,贺耕原便是不死,也非带伤不可了。
贺耕原虽然从死里逃生,但并没有就此罢手,手脚并用,连推带踢,便一连推倒了十几个人,打翻了好几张桌子,那些人看到贺耕原凶狠,早已吓得纷纷向外逃走,哪里还敢再留。
顷刻之间,一个极热闹欢乐的场面,立刻变成卷堂大散,走了一光,就只剩下了龙伯高兄弟,龙经礼和孔广生、诸天寿、禹颖达等五六个人,由诸天寿缠住贺耕原,不使他过分放肆。
龙伯高已经气得满脸铁青,直道:“这简直岂有此理,这从哪儿说起。”
龙经礼正要开口,孔广生连忙拿眼色把他止住说道:“贺兄不过是喝醉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我们便让他再闹一会儿,等他酒涌上来,人睡着了,也就没有事了。”
孔广生说这话的意思,是他已猜出了龙经礼所要对龙伯高说的是什么?而觉得这时来说这些话,并非其时,同时也看准了贺耕原的用意,不过是借酒出气,所以也就递话给他,要他自己下台。
果然贺耕原又闹了一阵,把厅上所挂的灯,所结的彩,一起打落在地之后,人也就一个歪斜,倒了下去,一阵呕吐,狼藉满地,跟着便呼声如雷,躺在地上,就像死狗样的睡着了。
龙伯高道:“我真没见过酒德有这么坏的人,你们有谁知道,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刚才我去接他的时候,他不是还好好的吗?”
龙经礼又想开口,依然被孔广生用目止住,说道:“我们先派人把贺兄送回去休息,然后再说吧!”说着便招呼龙家的佣人进来,吩咐把贺耕原送回下处。
那些佣人仍怕贺耕原发疯,不敢动手。
孔广生道:“不要紧的,你们只管送他回去就是,有什么再回来告诉我好了。”
龙伯高道:“要不要你去照应他一下?”
孔广生当然知道龙伯高的意思,便道:“用不着的,你放心好了。”
那些佣人这才大着胆,取过一张躺椅,把贺耕原抬在躺椅之上,送了回去,没有多时,便回来报说:“已经送回去了,并且替他脱了衣服,上床睡了,并未闹事。”
龙伯高这才放下心来,这一顿酒,当然也就没有心情再吃了,便把大家邀进书房,落座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龙经礼叹了口气,说道:“伯高,你的年纪也不小了,这事还要来问我们吗?我真不知道你是真的不知,还是明知故问呢?”
接着便把白兰花和贺耕原之间的事说了出来。
龙伯高听了,急得直跳起来,说道:“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了,又怎能夺人所好呢?”
龙经礼道:“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龙伯高想了一想,愤然说道:“我绝不能对不起朋友,你们请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来。”说着大家也就静静的等着,好半天这才看到龙伯高皱着眉头,走了出来。
龙经礼问道:“你已经决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