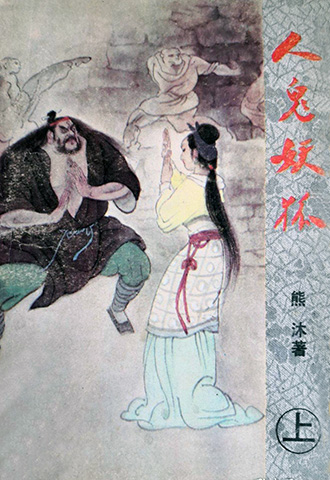她低下了头,再也不抬一下,慢慢地吃起来。
葛长生面对着这个奇怪的女孩子,已然无心饮食,一双俊目不由自主地盯视着她,而她的一举一动,都似乎有着莫大的魔力,吸引着每一个人。
任何人看她,她都不会生气,也不会不自然,可是葛长生看她,她却显得非常的不自然,这一点,他们彼此都发觉了!
她匆匆地吃完一块籽粑,又喝完了那碗奶茶,抬目之下,发觉葛长生的一双俊目,仍然盯视着她,嘴角也挂着一丝不自觉的笑容。
青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头对小二道:“伙计!我的马喂好了没有?”
在新疆,骑马的客人,向来用不着嘱咐,店家便会自动喂的,小二连忙含笑答道:“喂好了,你瞧!已经牵过来了!”
青姑点了点头,站起了身子,在怀中掏了半天,摸出了几块碎银丢在桌案上,又顺手拿了一把籽粑,拖拖拉拉地出了店。
葛长生的目光一直追着她,心中思忖道:“她真不像个女孩子,怎么还带一个籽粑走?”
葛长生转念之际,青姑已然跃上了马背,她突然转过了脸,双目如炬,对葛长生叱道:“看什么看?贼头贼脑的东西!”
葛长生一怔,才觉出是对自己讲话,他正要答话,突见青姑右手一扬,一团白光闪电般打到,口中喝道:“快吃饭吧!小贼!”
葛长生一惊,连忙闪身让开,原来青姑所丢的,正是她带走的那块籽粑,葛长生虽然让开,可是青姑却是故意把它投向碗中。
只听得“砰!”的一声响,肉汤四溅,溅了葛长生满身。
葛长生不禁大怒,推桌而起,就在当时,青姑已然带着一连串银铃般的笑声,纵马如飞而去。
店内之人,只当葛长生意态轻浮,青姑临去示警,当下一齐笑了起来,数十只眼睛,一齐盯着葛长生。
葛长生又羞又怒,被弄成个大红脸,匆匆把衣服上的油污拭了拭,转脸对小二道:“笑什么?还不快去备马?”
小二强忍住笑,用手指着店外道:“小爷!你的马早就备好了!”
葛长生满腔愤怒,出得店来,上马就要紧追,小二却追出店来,大声叫道:“小爷你饭钱还没给呢!”
葛长生不禁脸上一红,摸出一块银子丢了过来,足跟用力在马腹一点,那匹骏马立时放蹄奔去。
葛长生坐在马上,极目四望,已然不见青姑踪迹,可是远处黄尘翻滚,尚未落尽,足见她尚未去远。
葛长生深怕追她不上,双足用力一夹马腹,右掌用力地在马屁股上击了一掌,那匹疾奔着的快马,速度更加快得惊人了!
一路黄沙,飞尘丈,蔽人耳目,葛长生以袖遮目,眇目以视,大片黄尘中,已难端详。
好在由洛甫往策勒只有这么一条路,除非她折向沙漠,否则不愁追她不上。
大约跑了有一盏茶的时间,葛长生来到一个分岔口,这两条小路,分别通往策勒,大约有十余里的岔路,而后再合为一条路。
在这两条路口,均有马蹄印,葛长生一时竟不知如何选择,他勒住马缰,心中忖道:“我坐下是一匹千里良驹,一路急奔下来,怎么追她不上,莫非她的马比我的还要快么?”
葛长生思忖之际,只见靠右边这条道路,远处黄沙飞扬,他不再思索,双手抖缰,马行如龙,冲刺而去。
葛长生这一骑快马,速度可是惊人已极,由“洛甫”往“策勒”,沿途甚是僻静,葛长生知道这条路,更是人烟稀少,只见有一两户人家,在日光下晒皮毛和药材。
他急奔了一阵,远远果然看见了一骑背影,心中不禁一喜,忖道:“哼!总算追上了你,倒要看看你凭什么这么轻狂!”
不大的工夫,两下相距只有百十丈,前面的人回头望了一下,似乎发觉有人追赶,立时把马催得箭似的,狂奔如飞。
葛长生哪里肯舍,催马猛追,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她坐下的马,丝毫不比自己逊色,那骑术更是惊人,高低起伏,稳得像是贴在马背上面一样。
葛长生心中不禁暗暗佩服,忖道:“这青姑果然是个不得了的人物,单以这身骑术来说,如果我不是在新疆住了这么久,还真不如她呢!”
这两匹快马,分骑着一男一女,疾奔如狂,像是黑夜中两颗流星,又好似天幕上的两道闪电,快得让人不可捉摸。
这一阵急奔,足有一个时辰,时近傍晚,天色突然昏暗下来,大片的乌云也集聚起来。
葛长生始终没有把她追上,心中又急又怒,忖道:“看样子就要下大雨了,在下雨之前,我一定要追上她!”
葛长生一念未毕,天空突然响起一声震天的霹雳,葛长生不禁吓了一大跳,抬头望了望天,忖道:“糟了!这场雨不小呢!”
在新疆,天气的变化是很无常的,往往正午烈日炎炎,到了傍晚便是暴雨寒风,尤其是在沙漠,早晚温差之大,有时竟在数十度左右。
就这么一霎那,天上已落下了大颗的雨点,一颗颗地打在脸上,湿凉无比。
雨点越来越急,一霎那便成了倾盆大雨,葛长生不禁皱着眉头,暗叫倒霉,忖道:“这一下衣服全湿透了,还没有换的呢!”
他冒雨狂奔,不久赶到了一排石屋之前,他匆匆地下了马,用力地敲着门。
门内传出了一个苍老的新疆口音道:“莫待!可是你回来了?”
葛长生立时以新疆话,大声地答道:“我是过路的,请你开门让我避避雨!”
葛长生说完之后,隔了一会儿,石门开处,露出一个老年的新疆人,他一面开门,一面埋怨道:“唉……你们年青人就是不在乎,早就看出要下雨,也不准备一下……进来吧!”
在新疆住过的人,都可以判断天气的阴晴,可是葛长生这几日,不知是什么事情分了心,以至于没有注意到。
葛长生含笑致歉,连马一起进入了石房,身上的雨水,立时流了满地,葛长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真是抱歉,因为急着赶路,打扰了!”
那年老的新疆人,摇了摇头,说道:“没什么……还好家里女人都出去了,你快把衣服脱了,我去给你拿干衣服!”
葛长生道了谢,匆匆把衣服脱了,这时那新疆人,已然递过了干布和一套新疆人常穿的裙衣。
葛长生再三称谢,匆匆换了,那新疆老人,把马拉到后院系下,这才把葛长生让到了另一间小房,二人闲谈起来。
这老人名叫里罕,已经五十七岁了,可是他一生从没离开过新疆,为人倒是非常热心。
他搅拌着奶茶,放在一个小火炉上热着,葛长生坐在温暖的小屋,体会着他们那种朴实的生活,回想自己闯荡江湖,四海为家,心中不禁起了不少感触。
这时前室突然又传过了一阵急促地敲门声,里罕扬了一下短眉,说道:“大概是孩子们回来了,你自己热茶,我去开门!”
他说着起身而去,把石门关上,葛长生自己热好了茶,慢慢地喝着,耳听房外疾雨之声,心中忖道:“看样子这场雨最少要下一整夜,今天晚上只有在这里过夜了!”
他一个人坐在房中,喝了两碗奶子茶,刚才的雨寒已然一驱而尽,耳旁听得门外,似有女子谈话之声,由于石门很厚,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
过了很久的时间,里罕才推门而入,见了葛长生皱了一下眉头,笑道:“又是个避雨的!唔……”
他说着吁了一口气,葛长生笑着接着说道:“你的房子盖得太好了!”
里罕搓了一下干枯的双手,摆了摆头,说道:“你坐一坐,我该去准备晚饭了!”
他说着出房而去,不大的功夫,又推门进来,笑道:“好了!来吃饭吧!”
葛长生笑着称谢,随着里罕出得房来,木桌之上,已然摆上了酒食,葛长生见桌旁,坐着一个俊美的姑娘,二人双目相视,不禁各自发出了一声惊呼。
原来那坐在桌案之旁,等候用食的,正是沙丽白,这可真是大出葛长生意料之外。
在这一霎那,葛长生才觉悟过来,原来他在分岔路口的时候,居然追错了人,错把沙丽白当成青姑了!
沙丽白微笑着站起了身子,很大方的说道:“又碰见你了!”
“啊!原来你们认识,真是太有趣了!”
他们各自落坐,用籽粑夹着牛羊肉,慢慢地吃了起来,席间除了里罕外,他们都很少说话,沙丽白的神情倒很自然,只是葛长生却觉得处处别扭。
他也不时地偷看她几眼,被雨水淋透的头发,长长的披在两肩,乌黑发亮,看着她雪白的皮肤和明亮的大眼睛,真个是美丽已极。
葛长生心中不禁忖道:“这么美丽的姑娘,不要说是新疆,就是中原也难找到,可是她为什么要摆擂招亲呢?”
想到了摆擂招亲,想到柳谷子交给自己的玉虎,不禁又望了她一眼,只是有里罕在旁,不好张口。
沉默一会儿,沙丽白猝然问道:“你现在可是回中原去?”
葛长生摆了摆头,简单的说个“不!”字,沙丽白轻轻一笑,似乎是明知故问地说道:“你不回中原,那么你到哪里去呢?”
葛长生望了里罕一眼,沉吟着道:“我要去找你!”
“找我?找我作什么!”
她轻轻地笑了起来,露出了扁贝般的玉齿,她的语调非常柔和,可是在葛长生听来,却使他很生气。
葛长生闪动了一下俊目,有些不悦地说道:“我要还你一样东西!”
沙丽白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自己半潮的黑发,笑道:“你说的可是那朵红连?那是我送给你的!”
葛长生依然寒着脸,摇头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不能接受你的东西,还有那只玉虎,那是我朋友之物,你必须还给我!”
沙丽白闻言面上似有失望之色,她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微微转动,用很低的声音说道:“这件事我们等一下再谈好了!”
说着她捧起了奶茶,慢慢地喝着,里罕好奇地看着他们,室内非常寂静。
里罕先用完了饭,回到自己房中,只剩下沙丽白和葛长生二人。
他们互相对望了几眼,沙丽白轻声地说道:“照你刚才这么说,你是不承认那次打擂了!”
葛长生觉得自己有些理屈,嚅嚅道:“这……我上擂台,本是无心,说起来实在是个误会,到后来与姑娘动手,也是被你相逼……”
葛长生越说越脸红,因为这件事很明显,对方明明是招亲擂台,自己上台便是有意,而且当着数千人,把对方折取,而不允婚事。
一切的一切,对方都站在一个“理”字上,他自己所说的,只不过是强词夺理罢了!
沙丽白闻言之后,半晌不语,葛长生简直在她脸上找不出一丝表情来,心中纳闷,猜不出她的心意。
沙丽白发了一阵子怔,微微地抬起了双目,葛长生在她脸上,发现一片迷惘,心中很是歉然。
她缓缓地站起了身子,轻声道:“明天早晨再谈吧!我要休息了!”
葛长生对她深感歉意,一时觉得有很多话要向她解释,可是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直到沙丽白的身影消失之后,葛长生才缓缓地站起,叹了一口气,自语道:“唉,这是为什么呢?”
他推开了房门,倒在床上,风雨愈发加紧了。
翌晨,天光才亮,葛长生已经梳洗完毕,大雨已停,天边已有彩霞。
雨过天晴,葛长生心中有一种轻快的感觉,在门外散着步,沙丽白和里罕都还没有起床。
葛长生望着被雨水冲洗过的道路,他真不愿意离开新疆。
在新疆住了七年,他似乎已经把他全部的感情,都付出在这里了。
葛长生正在痴想之际,突听里罕在室内叫了起来。
他连忙赶进房中,里罕手中拿着一封信,和一大锭银子,对葛长生道:“你看这个姑娘怪不怪?不知不觉地走了,留下了这封信和银子,我又不识汉字呀!”
葛长生心中一惊,伸手把书信接过,只见上面写着:“沙漠客亲阅”
葛长生匆匆拆开,对里罕道:“信是给我的……”
他说着出了房,在旭日之下,仔细地看着,上面写着很工整的字迹:“沙漠客,由于你击败了我,是在千人之前,所以我才以终身相托,既然你不愿意,请你等我三年,三年之后,我要力雪此辱,到时不论胜负,定将玉虎还你!”
葛长生看罢,说不出是何滋味,把书信匆匆塞在怀中,回身对里罕道:“老先生,谢谢你留我过夜,我要走了!”
老人还来不及说话,葛长生已然摸出了一块碎银,递于老人道:“这点意思,你不要客气,我要赶路了!”
老人还在推辞,可是葛长生却是不顾,径自走向侧院,牵出了马,把东西略为整理,跃身上马,向老人略一拱手,风驰而去。
老人还来不及讲一句话,葛长生已然跑得没了踪迹,他低头望着手中的两块银子,摆着头道:“这个年青人可真奇怪,钱也是乱花……”
葛长生策马狂奔,他又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追沙丽白,追上她以后又说些什么?
他的确心情很乱,自古至今,“情”之一字,最是扰人,无论你付出感情,或者接受了感情,都足以乱了你的方寸。
葛长生想到了沙丽白的用心,她是想三年以后,再摆擂,把今日之辱,当众洗脱,至于她与自己的婚事,也自然地消失了!
由于昨夜的酣睡,葛长生精神抖擞,但是他的心情却是沉重的,这个女孩子,实在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烦恼。
他紧贴在马背上,暗自寻思:
他活了二十二个年头了,经过了一连串的紧张和孤独,他似乎已经很习惯了,从来没有想到别的,从没有想到自己的孤寂。
由于沙丽白的闯入,使他想到了婚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名词,在你没有想到它以前,你会觉得它很遥远,并且是不属于你的,可是当你想到它之后,他似乎又围绕在你的四周,非常的接近你。
可是,他第一次感兴趣的女人,确是青姑,她的举动虽然奇怪,确深深地扣住了葛长生的心!
他一路上,胸中一直萦绕着这个女人的影子,驱之不去。
正午时分,葛长生已赶到策勒,沿途没有发现一丝异状,他也曾问过了一些路人,他们都说没有见过骑马的人。
这不禁又使他发生怀疑,忖道:“莫非她们真地折入了沙漠?……若说沙丽白折入了沙漠,倒有此可能,至于青姑,她是绝不会入沙漠的!”
所以他相信,他不停地追,这两个人,必定有一个会被他追上。
一上午的疾奔,他的肚子又饿了,寻了一家较大的店,下得马来。
策勒位于新疆正北,也是沿着大戈壁沙漠的一个重镇,也是南疆一带的一个重镇。
葛长生所投宿的是一家名叫“三春饭店”,这家店是北方人所开,面食为主,在南疆一带颇负盛名。
葛长生尚未进门,店主已笑着迎了出来,含笑道:“小爷!你可是姓沙?”
葛长生一怔,用手扶着马颈,问道:“不错,你怎么认识我?”
店主满面带笑,施了一礼道:“我们早知道你要来,等了半天了,你快快请!”
他说着把马拉了过去,葛长生好不诧异,追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店主一面招呼小二喂马,一面道:“早上有位姑娘,在这留下话了,叫我们等着伺候您,我们等了一早上了!”
葛长生闻言心中一动,便知道必是沙丽白,随着店主向内走,边问道:“那位姑娘什么时候到达的?”
店主闻言立时答道:“啊!天一亮就来了,看样子是冒雨赶夜路来的,在小店休息了一下,换了衣服就走了!”
葛长生点了点头,又问道:“那姑娘临走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没有?”
“没有了,只叫小店好好伺候,银两已经先留下了!”
葛长生闻言心中更是一惊,略一思忖,点头道:“我知道了,你去吧!”
店主走后,葛长生一人沉思,他不知道沙丽白为何要这样做,忖道:“她早晨就到这里,那么一定是昨天半夜冒雨而行,还是为什么呢……她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好?”
葛长生想不透这些问题,可是这些全变成一种很大的压力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少时,店家送来食物,竟是非常丰盛地一桌酒席,使得葛长生更是惊奇,他估计着这一桌饭最少也要一两银子,有很多都是新疆很名贵的。
他食不知味地吃着,就仿佛沙丽白坐在他的身旁,殷切地劝他饮食一般,愈使他心中不安。
他不知道沙丽白这些举动是什么意思,到底是爱?这是一种奇怪的泄忿?
他不禁伸手入囊,摸出了那块玉牌,那朵雕刻得非常精细的红莲,落入他的眼帘,使他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梦一样的女人,梦一样的相逢,一切都飘渺得不可捉摸,一切都这么突然。
他大口地喝了几杯酒,性情愈加不能稳定,想想沙丽白,又想想青姑,有时又想想那从未见面的柳黛黛,酒不觉越喝越多。
在目前他所邂逅的两个女人中,他已爱上了青姑,这似乎不可解释,这就是感情神秘的地方。
北方菜似乎特别合他口味,因此他大口地喝着酒,不觉有点醉醺醺,觉得很舒适。
他把那块玉牌,放在了身旁,举怀一饮而尽,有些神经质的低声自语道:“姑娘,我敬你一杯……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那支玉虎你必须给我……”
他说了一阵,没有人来回答他,这时如有人看见,一定以为他陷入了深深的相思。
他也感觉到,自己这种自语,是很无聊的,于是笑了一笑,闭上了嘴,可是他的双目,一直紧盯着那块玉牌,因为在红莲的中心,似乎有一个姑娘的影子!
葛长生正在看得入神,突听身后不远,有人一声轻笑,接着说道:“最难消受美人恩,沙老兄,这话不错吧?”
葛长生一惊,急忙把玉牌收入怀中,回头看时,竟是与他在擂台上交手,不分胜负的叶潜秋!
他的打扮可怪透了,身上穿着一件玄紫色的长袍,外罩一件古铜色的坎肩,头上戴着一顶全红色的小圆帽,不回不汉,不伦不类。
葛长生还未讲话,他已笑着走了过来,像老朋友见面一般,握住葛长生的手,一阵猛摇,说道:“谁说新疆大,我们又见面了!哈哈……”
他笑声那么响亮,毫无做作之情,葛长生见他对自己如此友善,不得不点了点头,含笑道:“你来得很巧,我们一块吃饭吧!”
叶潜秋毫不客气,一屁股在葛长生身旁坐下,拍了拍葛长生的肩头,大笑道:“好得很!好得恨!这么大一桌菜,你好像消受不了,我既然赶上了,就沾沾光吧!”
葛长生听他言中似有别意,但又不好问,只有微微一笑,叶潜秋夹了一筷子菜,送入口中,接着说道:“唔……不错,还是北方菜好吃……”
“喂!老沙!我听说你要回中原去?此事当真?”
葛长生心中一动,忖道:“他怎么知道的?”
葛长生点了点头,并未回答他,叶潜秋似有深意地望着他,问道:“你在新疆住了不少年,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你可知道?”
葛长生点了点头,说道:“你说出来看看……”
葛长生刚说到这时里,一骑快马闪电般由店门冲过,他们二人不禁同时站起了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