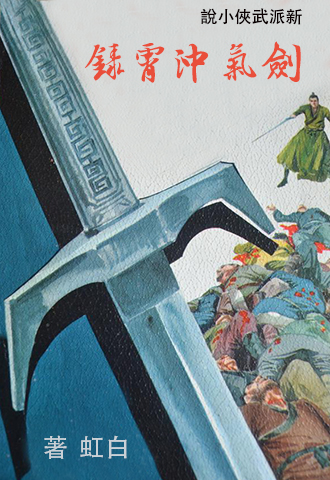拂晓时分,整个的西藏,被一片薄雾掩饰着,使得这塞外的高原,愈加显得神秘。
拉萨河上有一层浓浓的水气,显得昏暗和模糊,但也有几分妩媚,像是一个迟暮的美人,虽然年华老去,失去了青春的气息,仍然有着那雾一样,使你感觉到轻忽飘渺,而又迷人的魅力。
大地显得极度的幽静,秋虫拖高了嗓子,一递一声地合唱着。
有一阵轻微的衣履声,以极快的速度,由江边划过,快得简直令你感觉不出来!
当你仔细看时,你才会惊讶,原来江边上有两条灰淡的人影,轻风似的向前疾奔着,四只肥大的衣袖,在秋风中发出了忽噜噜的声响,一直传出了老远。
原来他们正是枯竹老人冷古,和心灯萧正庸!
他们挥泪别了病侠和克布,一点也没有耽误,立时沿着拉萨河向“牟卓雍”湖赶去。
诚如冷古所说,拉萨离牟卓雍湖并不远,总共还不到二百里地,以冷古和心灯的身法,用不到一天就可到达了。
可是冷古却是征心似箭,因为这一天他等待了二十年,在往常,每当他活动在这条路上时,他总是咬紧了牙齿,狠狠的说道:“魔崽子,让你逍遥吧!……我现在虽然不能去,可是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徒弟,一同走向这条路的……”
如今他的话果然实现了,他带着苦授十余年的弟子,踏上了复仇之路,他的心是多么的紧张和兴奋啊!
他们已经奔驰了将近一盏茶的时间,可是他们彼此却没有说一句话,心灯的心充满了一种不可形容的滋味,这种情绪不是几个名词就可以代表的,但是正确说来,这是属于悲哀的一种。
脱离了佛门,离开了沉病的病侠,而去报复一个阴毒、凶狠和杀父夺母的仇人,去会见身负大罪的亲生母亲,和一个自己爱恋着的,仇人的女儿!
这种事情,单单是其中任何一件,就够心灯悲哀的了,如今这一切完全蕴集于他一身,怎不令他悲伤欲绝呢?
又是一段长久的沉默,冷古斜眼看了看心灯,见他有些呆迟和茫然,好像自己不说话,他便永远不会开口似的。
冷古摇了摇头,轻声说道:“徒儿,你可觉得冷么?”
每当冷古叫他“徒儿”或“孩子”而不称“心灯”的时候,也就是他最亲切慈祥的时候。
心灯闻言略微转了一下眼珠,笑着摇了摇头,用很低的声音回答道:“我不冷……”
停了一下,心灯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迅速地转过了头,连向冷古看了几眼,很急切地问道:“师父,你呢?……你是不是有点冷?”
冷古笑笑,放大了声音道:“傻孩子,师父怎么会冷?你没看见我还在出汗么?”
心灯闻言往冷古看时,果见他额角颔下都有微小的汗珠,当下不由一惊,蓦地停下了身子。
冷古已然冲出了好几丈,见状又跑了回来,奇怪地问道:“怎么了?走得好好的,你怎么停下来了?”
心灯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冷古的面部,他充满了关切地说道:“师父,你一向是寒暑不侵,以你的功夫,跑这么一点路么会出汗呢?……我看你一定有病吧?”
冷古一惊,连忙大笑了几声,打断了心灯的话,笑着说道:“你看,你大概被骆老儿的病吓坏了,见我出点汗也当是病,我是在练功夫,不信你呆会看,我绝对不会再出汗的!”
心灯何等聪明,闻言自是不信,焦急地说道:“师父,你倒瞒我,前天我就觉得不对,你一向不怕冷,怎么在病师父那里烤起火来,今天又……”
心灯的话未说完,冷古面色大变,他那双白眉一挑,沉声作色道:“胡说!你才多大,你懂得什么?没事咒起你师父有病来了……以后再不准说这些话,走!”
冷古说完了这句话,拂袖之下已然出去了十余丈,好像要用这种超绝的身法,证明他还是与往常一样健康似的。
心灯痛苦地叹了一口气,连忙追上,他深知师父的脾气,一生刚愎自用,永远掩饰自己的弱点,像今天这种情形,心灯很明显的判定他是病了,并且病得还不轻!
可是心灯再也不敢问这件事,于是他们又沉默着在寒地里疾奔着。
大约又是一盏茶的时间过去,冷古才再次说了话:“心灯,你可喜欢你师父这种脾气么?”
冷古这句话问得很突然,心灯转过了头,见冷古双目望着远方,似在思索什么,根本不像在与自己讲话。
心灯沉吟了一下,迟缓地答道:“我……我喜欢!”
心灯这句话使得冷古轻声的笑了起来,说道:“好哇!你才离开佛门几个月,就学会打诳语了……不要骗我,我知道你不会喜欢这种脾气的!因为……我闯荡江湖七十余年,从来没有一个人喜欢我的脾气,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交到一个朋友。”
心灯不知如何接嘴,干脆不言语,静听这个老人的感叹。
“……我与你也相处了十余年了,我相信你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好感的。我这脾气,天生的让人嫌恶,可是……我有着一颗善心,与你们出家人一样的一颗善心。
“我这种怪脾气,冷漠的性格,使我在江湖上失去了每一个朋友,也得罪了所有的武林高手——尤其是黑道中人!可是也由于我这种性格,使得天下震惊,群魔退身,而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奇人!
“以往的数十年,我一直孤独着,就是有人想与我亲近,也被我拒之千里,像你就是这样……然而我却从没有后悔过……
“也许是人太老了,就有些怕孤独了,奇怪!……我从不后悔,现在竟有点后悔了……”
这个白发老人,在寒凉的秋风里,痛心地吁喟着,他的语气很坚定,连一点令人劝解的空隙都不留。
心灯不知冷古为何如此感叹起来,但他却油然而兴同情之心,相处了这么多年,心灯似乎现在已开始慢慢地了解他。
冷古仍然在感叹着:“所以现在我变了,我想你一定也会感觉出来,我想我是对这个世界太冷漠了,所以要在这最后的几寸光阴里,给它留下一点温馨……”
心灯偷眼向冷古望时,果见他脸上一丝汗水也无,心中非常难过,忖道:“师父是多么刚强的一个老人啊!”
冷古说完了那句话就开始沉默了,似乎把他胸中的话,简略的吐出之后,感觉到有点舒适。
他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由于天寒,立时化为一片雾丝飘散开来。
心灯这时才有机会说话,他移转了话题,含笑问道:“师父,我们到了牟卓雍湖,住在什么地方呢?”
冷古这才由幻想回到了现实,“啊”了一声道:“啊!这些你就不要操心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贡噶’,明天上午便可到达,本来今天就可以到的,可是我不愿意这么赶。”
他们说着,又出去了百十丈。
两三个时辰以后,雾气已经退尽,江面上渔帆点点,已经开始忙碌,沿岸行人也慢慢的增加了。
冷古及心灯不得不放慢了脚步,冷古皱了皱眉头,说道:“早知道这条路有这么多人,我们宁可多走点路,由‘沙漠叶’绕过去了!”
心灯也不知道:“沙漠叶”是什么地方,他突然想起了一事,不由停下了脚步,对冷古道:“师父,现在这么多人,我们不能加速行走,倒不如坐船到“贡噶”去如何?”
冷古闻言略一思索,随即点头道:“也好!坐船也可省点力气呢!”
冷古说着,迳向江边走去。心灯连忙跟上,恰巧江边有一空船,心灯立时用西藏语招呼道:“舟子,船可以租给我们一用么?”
那划船的舟子,是个十八九的藏人,闻言摇了摇头,含笑道:“对不起,客人,我这船已经有人定了,你们另外再找吧!”
冷古及心灯,见附近船只多为渔船,预料必不载客,一时竟再找不出第二只船来。
冷古想了一下对心灯道:“心灯,你问问他这船到哪里,可能带我们一程么?”
心灯闻言,立时用藏语对舟子道:“你的船到哪里?什么时候开?可以带我们一段路么?”
舟子闻言立时答道:“船马上就开,我们是到“贡噶”去的,能不能带人,那就要问客人了。”
他说着用手指了一下船舱,心灯把他的话翻给冷古听,冷古搓着一双手道:“啊!他们也是到‘贡噶’去的,说不定船上就是熟人。心灯,不必问了,我们上船吧!”
冷古说到这里,不容心灯答言,立时由跳板上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心灯也只好连忙跟上。
那摇船的舟子有些着急了,扯着嗓子怪叫道:“不行!不行!我说过有客人了。”
冷古一掌把他推开,冷冷说道:“你鬼叫些什么?”
冷古说到这里,扭过了头对着舱门叫道:“舱里面是哪位老朋友,请出来吧!”
冷古话才说完,便听得舱内传出了一个极苍老的声音道:“你们要搭便船就进来吧,难道还要我给你们开门不成?”
那老人说毕,又用藏语对舟子说了几句,表示应允。舟子立时伸手把舱门推开,并向冷古及心灯鞠了一躬,含笑说道:“二位客人请进吧,就要开船了!”
冷古及心灯一齐往舱内望去,只见船舱倒很宽敞,在靠左边的床上,有一个白发老人,拥着一床厚厚的棉被,靠在船窗上,萎缩成一团。
冷古及心灯不由全是一惊,因为这个老人的长相太奇怪了!
他面色漆黑,双目如炬,射出了一阵阵的精光,两片血红的嘴唇,衬着满头的白发,其状甚是恐怖。
冷古及心灯不禁怔了一下,那白发老人似乎有些不耐,皱着眉道:“看什么?左不过是一个人!……你们还不进来,莫非要往舱里灌冷风么?”
冷古淡淡一笑,拉着心灯的手入内,迳往另一张床上坐定,这时舟子立时把舱门关好,起锚行船了。
心灯见舱内窗户关得紧紧的,便想支开看看江景,谁知他才一动手,那怪老人立时喝叱道:“不许开!难道你要把我老人家冻死么?你要看风景到外面去看好了!”
心灯闻言心中虽然有些气愤,可是他是研佛之人,当下并未在意,只好把手收回。
心灯再看冷古,见他闭目养神,对于一切,直如未闻。
心灯再看那白发老人,见他一双眼睛,正注视着冷古,目光显得甚是柔和,心中不由颇为奇怪,忖道:“怪了!他好像对师父特别注意……”
心灯才想到这里,突见老人那一双精光四射的怪眼,向自己射了过来,当下连忙把目光避开。
那怪老人向心灯看了一阵,突然问道:“喂!你就是布达拉宫的心灯小和尚么?”
心灯闻言不禁大吃一惊,因为离开了布达拉宫以后,他已换了藏人打扮,头上并戴着很低的风帽,却料不到这个素不相识的怪老人,一眼便看出了自己的根底。
心灯惊奇之下,略一停顿,立时答道:“是的!……你老人家怎么会知道呢?”
那老人怪声地笑了一下,用厚棉被揉了揉光秃秃的下巴,说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我老人家虽然数十年未出江湖,可是没有一件事我不知道的。”
怪老人说到这里,得意地笑了两声,他的笑声很哑涩,令人听来很不舒适。
心灯听他笑完之后,不禁问道:“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呢?”
怪老人用眼睛望了望船顶,停顿了一下说道:“我姓萧,你就叫我萧老好了!”
心灯闻言不禁脱口道:“萧老!我也姓萧呢!”
萧老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你俗家名字叫萧正庸,我们还有点关系呢!不过很远,很远……”
心灯听了越发惊异,在萧老说他姓萧时,冷古已然睁开了眼睛,颇为注意地观察着萧老。
萧老与冷古对了一阵子目光,他嘴角微微泛起了一丝笑容,可是他的皮肤过于干涩,肌肉也非常僵硬,所以笑容在他脸上并不明显。
他用枯如鸟爪的手指,抓了一下头皮,冲冷古扬了一下头,傲然说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心灯见他对师父说话如此神态,心中不禁替他捏一把冷汗。因为冷古在江湖上是最难惹的人物,任何人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的。
相反的,冷古却没有愤怒的表示,他脸上冷得连一丝表情也没有,淡淡地说道:“你知道心灯竟不知道我,这倒是件怪事!……我姓冷,单名古字!”
萧老闻言点了点头,说道:“啊……冷古!这名字我在数十年前听说过,近来却没有,只当你死了,却不料你还活着,虽然比不上我硬朗能活,可是活得也够久的了!”
心灯听他说话越来越难听,冷古却是一丝也不恼怒,心中大是奇怪,忍不住说道:“萧老,我师父都快八十了,你难道有九十岁么?”
萧老微微一笑,说道:“岂止九十?反正比你师父大就是了。”
心灯闻言大是惊异,不禁用充满了疑惑目光,向冷古望了一眼,却不料冷古点着头道:“不错!他是比我大些。”
心灯简直不敢相信,可是冷古一向卖老,连他都如此说,是绝对不会错的,当下惊异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冷古若有深意地笑了一下,对萧老道:“萧老,如果我猜得不错,你与‘萧然亭’的人总有点关系吧!”
萧老闻言奇怪地眨动了一下眼睛,随即恢复常态,笑着说道:“不错,被你猜对了!可是我并非‘萧然亭’中弟子,所谓关系也只有一点,远得很!”
冷古面上现出一种从来未有的神色,他的声音也有些颤抖,低声问道:“……请问……老将军可好?……”
萧老闻言怪笑一声道:“你这话是怎么问的?老将军失踪数十年,恐怕早已去世,他牌位都供了五十年了!”
冷古点了点头,感触颇深地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唉……这真是我最大的憾事!”
心灯一点也不懂他们谈的是什么事情,可是他素知冷古脾气,又不敢问,只好闷在心里。
萧老把两只膀子收进被窝里,打了一个哈欠,说道:“不要说话了!我老人家就爱睡早觉……啊——”
说着又打了一个哈欠,把身子往下一缩,立时闭目安眠,不再说话。
冷古稍为一怔,也闭上了眼睛调息起来,也许他的心里正在想着什么事情,可是表面上一丝也看不出来。
船舱内立时一片寂静,心灯只听得一阵哗啦哗啦的水声,小船的行速似乎很快,飘飘荡荡的,甚是舒适。
心灯觉着甚是无聊,正想出舱去看江景,突见萧老又睁开了眼睛,对着自己挤了一挤。
心灯见状轻声问道:“萧老,什么事?”
萧老把身子往上挪了挪,说道:“你过来,我有话和你说!”
心灯闻言走过,坐在了萧老的身侧,这一离近,愈发觉得他面目可怖。
可是他的声音却非常柔软和悦,似乎与他的外形不太相衬。
萧老仔细地看了看心灯,说道:“你把鞋脱了,上来睡觉!”
心灯闻言大奇,连忙说道:“萧老,我不困……”
心灯话未说完,萧老已作色道:“谁说不困?不困也要上来睡!你没看见大家都在睡觉吗?你一个人干什么?”
心灯实在有些不惯,闻言嚅嚅说道:“萧老,我真的不睡,我……我出去看风景,不吵你们……”
萧老却把怪目一翻道:“我是一番好意,怕你受了凉,你怎么一点也不明白?快上床来!”
心灯简直被这怪老人弄得啼笑皆非,正在为难,突听冷古说道:“徒儿,上床睡吧!这一觉你会得益不浅的!”
心灯闻言大是奇怪,再看冷古还是双目垂帘,一动也未动,这时萧老已然笑着说道:“哈……还是你师父聪明,快上来吧!”
心灯万般无奈,只好把鞋脱掉,萧老已然一把把他拉进了被窝。
心灯只觉被内温暖舒适,那老人穿的却是一身少年人穿的劲装,耳旁又听老人笑道:“你学了这么多派的功夫,也不怕消化不了?有我这个大夫给你治治病,你难道还不乐意么?”
心灯听出萧老言中似有深意,正要询问,突觉一阵昏迷,已然被老人点了“睡穴”,昏沉沉地睡去。
心灯迷迷糊糊之中,只觉老人双手一指,分别扣着自己胸腹十大要穴,一阵阵的奇寒猛热,透体而入,简直是难过已极,那滋味就有点像随着病侠学艺时,在地洞内历七劫一样。
大约一盏茶的时间过去,心灯痛苦全失,只觉浑身舒适,不觉沉沉睡去。
等到心灯再次睁开眼睛,已是两个时辰过去了。
他耳旁听得一阵叮咚之声,睁眼一看,原来冷古及萧老正在下围棋,棋子棋盘全为纯钢铸制,是以发出了轻脆悦耳之声。
心灯爬起了身子,不禁说道:“啊!我这一觉可睡了不少时候啊!”
萧老及冷古直如未闻,各自全神贯注地望着棋盘。
心灯穿好了鞋,走往二老身旁,连说了几句话,二老却是一言也不答理。
心灯亦擅此道,当下不再讲话,拉过了一把椅子坐在一旁观战。
心灯一看之下,不由大感奇怪,原来他们所用的棋盘,比普通的恰好大上一倍,偌大一个棋盘,上面只不过布了二三十个棋子。
这二三十个棋子零零散散,既不抢角,又不保地,七零八散的摆着。
心灯实在看不懂,这时萧老又在中盘按下一子。
这一子才放下,突听冷古一阵大笑。
这阵大笑对冷古来说实在是太罕有了,他笑个不停,泪水像珍珠般的,随着笑声落了下来。
冷古一边笑,一边用手指着萧老,喘息连连地说道:“果然是你!……你总是在第十六子试敌……哈哈……你还没有死……还没有死!……哈哈……”
萧老也对着冷古嘶哑的大笑起来,他边笑边道:“小竹子!……你那份儿精灵还在……”
这一幕奇事,简直把心灯吓傻了,看看冷古,又看看萧老,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们二人这一阵大笑,似乎没有完,直笑了良久,连划船的舟子都奇怪地进来看过一次。
最后当他们笑声停止时,冷古胸前已被泪水打湿了一大片了!
他用衣袖抹了一下眼泪,说道:“你又来找我,可是你已原谅了我么?”
萧老点了点头,用手把棋子拂乱,说道:“我早就原谅你了。我所以耗着不死,为的就是找你聚一聚……现在既然被你识破,这捞什子也不戴了!”
他说着伸手往脸上一抓,但听一声轻响,他那张丑恶的面孔,竟是一张精制的人皮面具,被他抓了下来。
这时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有着一张焦黄而又充满了病容的脸,眼睛很大,刚才已经说过充满了神光,口鼻都很方正,颔下无须,上唇却留着一撮银白的胡子,一排细白的牙齿。
他有着很浓的书卷气,令人看得出他的性格很沉默,但是也很刚毅,他嘴角浅浅地笑容,使你感觉到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可是他那微锁的眉头,又使你感觉得他很忧郁,一定是个孤独惯了的人。
心灯惊讶万分,怔怔地望着这个奇怪的老人。
冷古从不曾流露过他的心情,可是此刻他整个的表现出来了,眼睛里充满了挚爱和追忆,更流露出一种孩子似的依恋。
萧老轻叹了一口气,对冷古道:“你没有想到我还活着吧?……岁月如梦,连你都老成这个样子了!”
冷古紧紧的拉着萧老的手,贴在自己的面颊上,他忍不住又哭了起来,说道:“梦!梦!……”
萧老拍拍他的肩膀,像一个慈父似的说道:“孩子!你还是当年的脾气啊!”
他似乎也非常伤感。
心灯听萧老居然叫冷古“孩子”,不禁惊得出了声,拉着冷古的袖子问道:“师父!他是谁?”
冷古也住了泪,痛苦地笑笑,对心灯道:“徒儿!你做梦也想不到……我做梦也想不到……他就是我的师父萧鲁西,我记得曾经告诉过你。”
心灯闻言之下,立时惊得呆若木鸡,“啊”了一声,像看怪物似的盯着萧鲁西。
萧鲁西对心灯点了点头,说道:“心灯!你师父的话不错,他是我生平惟一,也是最得意的一个徒弟,就如同你和他的情形一样。”
心灯这才深信,不自主地跪了下来,叫了一声:“师爷。”
萧鲁西把心灯拉起,笑道:“至于我的事,你师父一定很少告诉你,以后再慢慢谈吧!……我已经一百一十五了,五十岁时脱离江湖,那时你师父才二十多,因为犯了我的忌,所以我终生不愿见他,可是人太老了,心也就软了!”
(关于冷古与其师萧鲁西失和详情,将在本书前集中叙述,此处暂略。)
于是,这一个不平凡的相遇,使小小的船舱内,充满了一片喟叹和欢笑,实在是太不平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