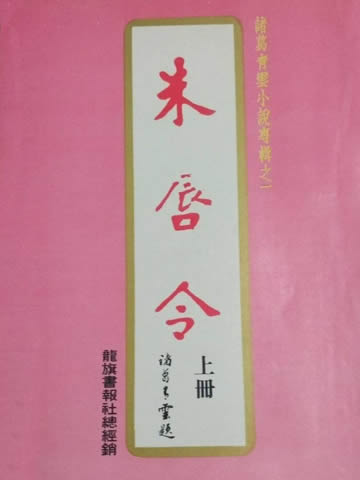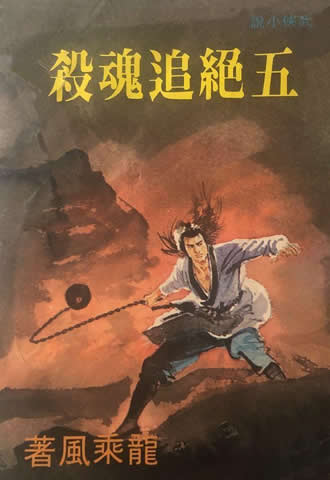上回谈到,西藏布达拉宫主持叠布诺大师,把心灯找到禅房,谈了一阵,他是非常希望打断心灯还俗的念头,其实这个小和尚又何尝愿意离开布达拉宫呢?
叠布诺大师轻叹了一口气,轻声说道:“唉!你明天把头发剃了吧!”
这句话使心灯吃了一惊,不禁怔了一下,迟迟地问道:“大师!……为什么?”
叠布诺大师摇了摇头,面上浮出了一丝慈祥的笑容,说道:“准备还俗呀!这是规矩,你下去就把头剃了吧!”
心灯闻言这才恍然,迟迟的应了一声,合十而退,这时他悲哀的情绪,愈加变得浓厚,虽然他是自幼出家,寄身佛门四大皆空的人,可是他总是想得比别人多,在这个世界上,想得多的人,总是比别人的痛苦多得多!
心灯下了楼,时间已经很晚了,可是他却没有丝毫睡意,茫然若失的在布达拉宫徘徊着,心头蕴集着一阵阵不知所以的烦闷,这一年的时间,使得他变了许多,也变得成熟了,因为只有成熟的人,才会烦闷的。
夜,永远是沉寂的,尤其是西藏的夜,总是那么寒凉和充满了梦想。心灯迟缓地走到了侧殿,轻轻的推开了门,他准备为云姑的那块牌位念一段经,同时也好使他混乱的心安静一下。
当心灯的眼帘,接触到那只黄绫包裹着的牌位时,心中又泛上了几丝疑惑,忖道:“怪得很,云姑一家人不是团圆在一起吗?这牌位莫非是她的什么亲人?……可是她为什么要瞒着她丈夫呢?”
心灯想到这里,再把这两次与云姑相处的情形,细细的思索一下,疑惑之心越来越大,他始终觉得,云姑这样的人,嫁给一个西藏人,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并且云姑所表露的,是何其的忧郁和哀伤呀?
心灯不知为何,他竟是如此的关怀云姑,他默默地想道:“我可不可把这牌位打开看看?……”
心灯才想到这里,他立时停了下来,忖道:“阿弥陀佛!我怎么能做这种事?……云姑交给我的时候,还再三说过不能打开来着……”
心灯这么想着,立时打消了原来的念头,燃上香烛,喃嘀地念起经来。
在以往,每当心灯念经的时候,也就是他心情最宁静的时候,可是今天却不同了。
在他一卷经尚未念完时,他的心情已经开始浮燥起来,那只被香烟缭绕供着的牌位,好似有莫大的魔力,吸引着心灯,使他再次的睁开了眼睛。
那只令箭形的小牌位,再次接触着心灯的目光,赋予他一种莫大的幻想,他想道:“这个死去的人,一定是她的亲人,说不定是她的孩子……她不是这么喜欢年青人么?”
心灯这么思索着,越发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忖道:“是的!一定是她的儿子!”
想到这里,心灯再也沉不住气,他似乎听见,那块令牌在低声嘤啜呼唤!
“心灯……打开我……打开我……我闷了十几年了……”
心灯战栗了一下,他慢慢地站起了身子,移动到灵位之前,一双眼睛紧紧的盯在那块小牌上,心中不停地想道:“我到底能不能打开看呢?……不管它!这总不算是什么大罪过吧!”
心灯这么想着,双手立时握住了那块牌位,他全身有一种莫名的,轻微的颤抖,好似他手中握着的,是一个弱小的生命,而这弱小无力的生命,在以往或许是一个咤叱风云的人物!
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促使心灯打开了这个小牌位,当他才把黄绫退去了一部分,他的目光接触到头三个字时,不禁使他浑身战栗起来!
原来那是朱刻的三个小字“先夫萧……”
这三字,就像闪电一般整个地袭进了心灯的心田,他有些昏眩,他仿佛记得,当他第一次到病侠所居的石屋中去时,病侠曾经告诉了他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曾经使他一直不安。
现在,这件已经死去了十余年的故事,显然由于心灯的好奇,而又复活过来了!
在他打开了整个的黄绫之后,上面写着的字,清清楚楚地呈现了,那是:“先夫萧乾元之灵位”
只有这么几个字。心灯捧着这块牌位,失神地跌坐在地上,他想道:“难道就是病师父告诉我的故事?……是的,一定是的!云姑就是那个谋害亲夫的人!……那么墨林娜的父亲,就是西藏魔头卓特巴了?……”
这个念头,像是一把火似的,烧得心灯浑身大汗,一颗心怦怦地跳动着,他默默地叫道:“天啊!……这是什么因果?墨林娜的父亲就是卓特巴!……云姑竟是那个罪恶的女人!……”
石室中燃着一盏昏灯,夜寒得很。
心灯捧着那块令牌,坐在病侠的床侧,正在展视着,病侠及克布都充满惊异地盯着他。
他们都在怀疑着,这么晚了,心灯捧着的这块小牌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又显得这么惊恐和不安?
在心灯打开了包裹着的黄绫时,病侠的目光,非常迅速地接触到牌位上的几个字,他那双久病失神的眼睛,突然比平常张大了一倍,发射出一种奇怪的光芒,令人看得出,他的心在极度的激动和惊诧之中。
心灯急忙握着病侠的膀子,不住的问道:“病师父,快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这个人?……告诉我呀!”
心灯焦急的催问着,可是病侠的一双眼睛,仍然呆迟的盯视着木牌上面的字,他的眸子里,流露出一种沉痛之色,仿佛坠入了回忆的深渊里。
心灯见病侠如此模样,便知道自己推测的八成不会错,不禁凉了半截,再次问道:“病师父,你说呀!到底认不认识他呀?”
病侠这才惊觉过来,抬起了眼睛,注视了心灯一下,然后无力的眨了一下眼睛,那表示他是认识这个人的。
心灯越发确定自己所料不差,那握着病侠的手,不禁微微地颤抖起来,嚅嚅说道:“病师父……他可是你以前告诉我的故事?……他的妻子和卓特巴把他杀了?”
病侠犹豫了一下,终于用眼睛表示心灯的猜测是正确的。
于是,这个小和尚,由于过大的悲惧,显然的瘫痪下来,他无力地垂着两手,闭目叫道:“天呀!原来墨林娜就是卓特巴的女儿!……云姑……云姑竟会杀害了她的丈夫,我所接触到的,所爱的,怎么都是这些罪恶的人呢?”
病侠默默的听着这个小和尚的自语,他尚不能断定,心灯是否知道,这牌位上的名字,就是他亲生的父亲,可是他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心灯是在无尽的悲哀中。
克布对这突来的事情大为惊奇,他双手扶着心灯的膀子,不停地问道:“师兄,这是怎么一回事?这……”
片刻之后,心灯渐渐的冷静下来,他像是一个才遭受过重击的人,显得疲惫与无神,两只手紧紧的交错在胸前,像是在咒诅世间一切罪恶似的。
病侠在心灯冷静之后,用眼睛询问他:“你怎么会得到这块令牌的?难道你到‘牟卓雍湖’去过了?”
心灯极度失望地,把他与墨林娜,以及卓特巴相处的情形,详细的告诉了病侠。
病侠这才恍然,忖道:“阿弥陀佛!幸亏他还不知道云姑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否则事情就麻烦了!”
心灯在述说完他与墨林娜等的详情后,用着怀疑并沉痛的口吻问道:“病师父,难道像云姑这么文静慈祥的人,竟会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来?”
病侠虽然不忍令心灯失望,可是这是事实,他不能不作一个肯定的表示。
心灯确定了这件事实之后,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悲伤,也不知道为谁悲伤,或许是为云姑,或许是为墨林娜,又或许为他自己。
他不禁紧握了双手,喃喃地叫道:“阿弥陀佛!……原来是一个罪恶的家庭!……每一个人都是的!难道墨林娜也是一个恶人么?”
一个真诚的佛教徒,对于任何一点微小的罪恶,都感到恐惧和不安,何况是这种滔天的大罪呢!
病侠见心灯如此模样,知道这件事大大的伤了心灯的心。因为他所挚爱的墨林娜,是卓特巴的女儿,而他所敬爱如神的云姑,就是那个谋杀亲夫的,罪恶的女人!
这一切,像是几把极锋利的刀刃,深深的刺到心灯的心里,当他悲痛归于平静之后,他不禁默默地想道:“这些痛苦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啊!这都是因为我要还俗了,一个出家人,本来是不会遭遇到这些痛苦的!……多么可怕的大千世界啊!”
病侠见心灯双手捧着灵位,近乎于呆迟地痴想着,他不禁有些焦急,接连不断地向心灯眨着眼,可是心灯却丝毫没有觉察出来。
病侠不禁向一旁不知所以的克布看了一眼,克布见状连忙扶了心灯一把,问道:“师兄,你到底怎么了?师父在看你呢!”
心灯这才觉醒过来,抬目向病侠望去。
病侠那张苍老而慈祥的面孔,洋溢着一种极大的关怀,他那只深陷无神的眼睛,流露出一种莫大的同情,好像是在说:“孩子,用不着这么难过,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的!”
心灯有些迷惑的问道:“病师父……在一个不是出家的人看来,一个犯了罪的人,是不是会得到人们的原谅呢?”
病侠作了一个很难答复的表示,心灯定了一下神,提起了他最大的勇气,再次问道:“病师父,我是说……像云姑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原谅呢?”
病侠很想给心灯一些安慰,可是他却不愿意作违心之论,于是他用充满了歉意的目光,向心灯看了一眼,然后连续地眨了两下。
这个答复果然使心灯失望极了,他痛苦的叹息了一声,紧紧的握着手中的灵位,怀着一丝希望地,再次问道:“病师父,难道……难道外面的世界,比我们佛家还要苛求?……我佛说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她忏悔了,她的罪是可以减轻的……”
病侠颇为感动地看了心灯一眼,然后用他的眼睛说出了一篇大道理:
……唉!(他每次用眼睛向下看,就表示他在叹气)人的善恶存乎一心,全在一念之间,为恶的人,有的是无心之失,那么他的心还是纯洁的,可以得到原谅。
“可是像云姑这种事,她是不会得到任何人的谅宥。因为她不是无心之失,虽然她当时是临时起意,可是谋害了自己亲夫,这是大逆不道的事,对于人类的结合,也是一种绝大的讽刺!
“一个人的心,就像是一块洁白的布巾,如果染上了污点,是无法洗涤的,你们佛家所谓的多种善因,倡因果之说,并不是说善恶可相抵,而是鼓励那些恶人,忘记他们的罪恶,而为这个世界多做些善事而已!
“当然,我们站在人道的立场,对于改过自新的人,应该另眼看待,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原谅了他……啊,这话很难说得明白,我只知道天底下的事,没有什么不应该的,错就错了,‘原谅’这两个字,根本不适用于任何人。”
或许是病侠想到了他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说得这么零乱,虽然都有很明显的表示出应该“报复”的意味,但多少也有点“天谴”的意思。
心灯有些迷糊,他仿佛已经意识到,云姑所犯的罪,是无法赦免的了!
病侠看着这个痛苦的小和尚,他心里有些难过,他渴望着去安慰心灯,可是上天却剥夺了他说话的力量,只能用那充满了挚爱的目光,不停地向心灯爱抚着。
在三更半夜的时候,心灯快快地回到了“布达拉宫”。当他再次把灵位供好时,有一个突来的念头,在他的心中涌起:“不论病师父说的话对不对,我每天为云姑念几卷经,对她或许有些好处呢!”
心灯想到这里,他拼命的静下了心,右手敲打着木鱼,喃喃地念起佛来。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心灯只是反复不停地唱着这一句,虔诚得像是一个失去了感觉的人。
第二天的上午,心灯又把头发剃光了,那是因为他在还俗的时候,有一个蓄发的仪式。
心灯在水面中,照见了自己的样子,又是“牛山濯灌”了!
这个影子,是那么的亲切,心灯仿佛找回了失去的自己,这时他更确定了他的心愿:“我一定要回来!我一定要回来……”
……
夜晚,当心灯出寺去赴万蛟的约会时,他仿佛意识到,又有新的劫难到来了!
他双手合十,垂着眼皮,喃喃地念着:“……青山无语,青山无语叹……人……意……青山无语叹人……意……
草露风灯!
草露风灯闪电光,草露风灯闪电光……
人归何处!
人归何处青山在?人归何处青山在……
总是南柯!
总是南柯梦一场,总是南柯梦一场!……”
心灯念的,是一首和尚尼姑们常念的“叹之赞”,这仿佛是他为了却魔的颂祷。
来到了那日的山谷,落叶满地,没有一个人。心灯痴痴地坐在草地上,山风吹时,又听见他在念:“娑婆极苦无人晓,
轮回何日了?
浮萍水上飘!
束缚笼中鸟……
叹亡灵……何不早回头?
归去好……”
韵调很单调,但是充满了虔诚和觉悟,由这个大慈大悲的小和尚口中唱出,更显得真切动人。
万蛟早已到来了,他就坐在距离心灯七八丈左右的一枝树桠上,他被心灯的叨念,深深地吸引了,轻轻地重复着:“娑婆极苦,何时了?……何不早回头,归去好!”
万蛟粗哑的声音,在静夜里传出了很远,惊动了心灯,他惊诧地扬了一下头,轻声道:“万师伯你来了,好高的身法啊!”
万蛟哈哈一笑,身子轻轻的一晃,已然来到了心灯身前,他细细地看了心灯一阵,含笑道:“怎么了?小和尚,你怎么在这念起经来了?”
心灯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各人一条生死路,只争来早与来迟……”
万蛟闻言大声的笑了起来,说道:“好个小和尚,看得这么清,却是丢不下啊!呵呵!”
万蛟说着,大声的笑个不停。心灯抬目望了望他,含笑自若地说道:“万师伯,你说得一点不错,看得明白不容易,放得下更不容易啊!”
万蛟思索了一下,似懂不懂地摇了一下头,笑道:“好了,别谈这些了。”
万蛟说着,坐在了心灯的对面,朗声说道:“心灯,你可知我为什么要你来么?”
心灯不解地摇了摇头,说道:“我不知道,反正不会再教我武艺吧!”
万蛟用他阴涩的嗓子,干笑了两声,说道:“放心!我可没功夫再传你武艺了!……心灯,你可记得,在我传你武艺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将来要你到牟卓雍湖去,为我取回信物。”
心灯闻言吃了一惊,也不等万蛟把话说完,便抢着说道:“万师伯,你说过你不强迫我的。”
万蛟摇手止住了心灯的话,很冷静地说道:“心灯,你先不用着急,听我慢慢的说。”
“不错,我答应过冷古,将来绝不强迫你为我办事。可是我当时也说过,只要你志愿,你师父是不能过问的!”
心灯听到这里正要说话,万蛟又摇手止住了他,继续说道:“你听我说……当然,你是不会志愿去的,这并不是说你不够热心,或不肯帮助别人,而是你遭遇的事情太多了!
“现在我找你来,就是告诉你一个事实,一件我为你做的事,如果你认为这件事对你很有意义的话,那么或许你会自动的为我办事。”
心灯听到这里,似乎已经有了预感,判定万蛟要告诉自己的事,必然与自己有着莫大的关系,当下便有些沉不住气了。
他不禁睁大了眼睛,问道:“什么事?”
万蛟的脸,严肃得像是一尊佛像,静静的问道:“心灯,你可知道你的身世,你的家,你的父母么?”
这正是心灯月来最感烦心的事,在他听了万蛟的话之后,紧张得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立时说道:“我……我只知道我姓萧,名字叫正庸,在我一岁的时候,便被人送进了庙……我的父母,我的家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因为他们对于我并不重要。”
万蛟摇了摇头,说道:“错了!怎么会对你不重要呢?一个人不能忘记他的出处的!
“你们佛经上不是也说:‘喜是离娘胎,铁树百花开’吗?……现在让我把你的身世详细的告诉你!
“你的父母,在十九年前,都是名振一时的少年侠客,不知为了何事——也许是为了蚕桑口诀——一同来到了西藏。”
心灯虽然心中无父母,这时也不禁贯注了全神,仔细地听着。
万蛟稍停了一下,似乎在整理他的话题,然后接着说道:“你的父亲善于用剑,江湖上有个绰号叫‘惊风剑’,你母轻功特好,人称‘凌云燕’……”
心灯静静的听着,似乎已经感觉到有一种不幸的预感:“西藏,十九年前,一对年青的夫妇……”
心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大声的叫道:“师伯,快告诉我,我父母叫什么?”
万蛟仍然慢吞吞地说道:“你母名秦云倩,你父叫萧乾元!”
心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只觉得天地整个在动荡,令人昏眩得很。
他用着一种可怕的声音叫道:“不!不是的!……云姑……我的母亲?……”
虽然是在叫,可是他的声音,只有他自己听到。万蛟显然有些惊奇,他握着心灯的膀子问道:“怎么了?心灯,难道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心灯一言不发,只是不住地点着头。这倒使万蛟变得惊奇起来,他想不到心灯竟会知道他自身的往事,当下连声的催问道:“你全都知道了?你怎么会知道呢?”
心灯这时心乱如麻,他根本听不清万蛟问的是些什么,只是不停的自语道:“是的!是的!就是病师父告诉我的……”
万蛟闻言在旁叹息了一声道:“唉!既然骆江元已经告诉过你,我也就不再说了,你知道得很详细吗?”
心灯整个的心血都在沸腾,他想不到,他一生连一个蚂蚁均未伤害,吃斋念佛,可是他的母亲,却是一个天大的罪人!
这一霎那,卓特巴、云姑、墨林娜的影子,都在他的面前飘舞着!
一张恐怖丑恶的面孔,代表着无穷的罪恶!
一张忧郁恐慌的面孔,代表着莫大的痛苦和忏悔。
一张娇美天真的面孔,代表着无知和骄傲。
心灯觉得昏眩,他几乎整个的麻木过去!
良久,良久,心灯才清醒过来,万蛟不知在他耳边说了多少话,可是他一句也没有听见。
万蛟由心灯的眼睛里,看出他已经清醒,这才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心灯,我知道这些话会使你很难过,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你马上就二十岁了,并且就要还俗,是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世的。”
心灯茫然地点着头,低声说道:“谢谢你,万师伯。我今天才知道,卓特巴不但是你们的仇人,也是我天大的仇人!”
万蛟点了点头,又说道:“心灯,你父亲的死你是知道的,可是你可知道他骨骸在哪里吗?”
万蛟这句话,使心灯浑身一颤,他极度惊惧地抬起了眼睛,嚅嚅问道:“我……我不知道,你……你快……快告诉我!”
万蛟停顿了一下,搓了搓那两只老手,说道:“这就是我特地找你来的原因,也是我持以利用你的主力。”
万蛟的话说得非常坦白,他的意思很明显,心灯如果要寻他亡父的遗骸,那么必需要答应万蛟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需要到牟卓雍湖,去为他取回令符。
心灯这时心痛如剜,哪里还顾得考虑,当下忙乱地点着头连声说道:“万师伯,快告诉我,我一定为你的事尽力……”
万蛟脸上很快地掠过一个得意的笑容,他拉住了心灯的手沉低了声音,说道:“心灯,我相信你的话,只要你为我盗出了令符,我万蛟的名字,在江湖上又复活了!
“一般人谈到我,都说我是邪派第一高手,事实上是冤枉了我,那是因为我有一个不争气的弟弟,他名叫万潜,时常做些悖理横逆的事,把我的名声都败坏了。
“只要我得到令符,我再出江湖,哈哈……”
这个奇怪的老头子,深深的为自己感叹起来。心灯又悲又急,正要催问,万蛟突然问道:“心灯,骆老头儿可告诉过你,关于你父亲骨骸的事么?”
心灯摇了摇头,无力地答道:“没有,他不愿与我谈这件事!”
万蛟骄傲地点了点头,说道:“除了我和卓特巴,西藏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你母亲在内。”
心灯不敢再听下去,他焦急地说道:“万……师伯,快带我去!”
万蛟一笑,拉住心灯的手,说道:“好!月亮上来了,我们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