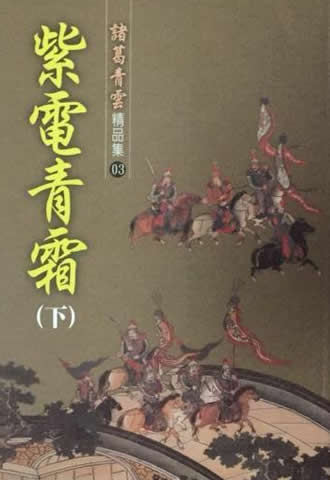这句话使心灯吃了一惊,他以为以卢妪这么怪诞的脾气,是不会这么做的,却料不到卢妪始终没有放过自己。
“拒绝”这个念头,像闪电一般袭上了心头,他苦笑了一下,故意用着很轻松的口吻说道:“卢师伯取笑了,外面素知你老人家绝技是不传第二人的……”
心灯话未说完,卢妪已是一声怪叫,吓得心灯连忙停了下来。
卢妪把她那只独眼睁得大大的,狠狠的盯着心灯,直把心灯看得低下头,这才冷冷的说道:“小和尚,你不用给我耍花枪,谁说过我功夫不传人?难道要我把这绝技带到棺材里去?”
心灯被卢妪骂得异常生气,但又不能回嘴,直气得低头不语。
卢妪停歇了一下,接着说道:“现在听我说,十天以后,我开始传你一套出奇的功夫,这种功夫对你是非常有用的,不过……”
心灯越听越怕,听到卢妪说到这里时,心灯再也忍不住,扬起了头昂声说道:“师伯,下面我都知道了,你不必再说了,还不是要答应你一个条件,将来到牟卓雍湖去替你……”
心灯的语气非常愤怒,当他才说到这里时,卢妪又是一声怪笑道:“放屁!我可不像那一群没出息的东西,我的‘绿骨针’有人拿,就是你要替我拿我还不要呢。”
卢妪这句话,倒是大出心灯意料之外,不禁使他呆痴下来。卢妪向心灯脸上望了一下,冷笑道:“好了,滚吧!十天以后来!”
心灯被她左骂右骂,直弄得怒气满胸,当下也不答话,气愤愤的返身而去,临走的时候还踢断了一颗小树,惹得卢妪又大声的怪笑起来。
心灯满腹懊恼的回到了布达拉宫,想起还忘了替云姑念经,当下也不回禅房,迳往侧殿而去。
当心灯才把殿门推开时,便由门缝中飘飘落下了一片纸条,当下连忙抓在手中。
心灯就着灯光,垂目望去,只见上面写着:“心灯见字:
卢妪传你功夫,应特别用心学习,盖她所传为‘水功’,此将对你入牟卓雍湖大有好处,切记!
为师现正忙于调查一事,不久可有眉目,你还俗在即,吾等所传武功,应加意复习,中秋还俗之时,余将做一考验,勉之!勉之!
师字”
心灯看完了这张条子,说不出是忧是喜,他想不到卢妪所传他的是“水功”,并且他就要还俗了,还俗之后他立刻就要入牟卓雍湖,去为这一群老怪物们效命。
这一切眼看就要在目前发生,可是它们的发展又渺茫得不可捉摸,谁又知道,心灯还俗以后,入牟卓雍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会成功吗?或是失败?成功了以后怎么样?失败了又如何呢?
这些不可预知的问题,一时都汇集在心灯的脑海里,使他的情绪非常激动。
良久,心灯平静下来,他把纸条仔细地收好,然后燃上了三枝香,盘膝而坐,屏心静气的念起经来。
良夜迢迢,布达拉宫的僧人全熟睡了,只有心灯敲着木鱼,低声的叨念着。
僧人的梵唱,本有一种清涤出尘的意境,听来虽然单调,可是却能把你带入一种神奇的境界,在那个境界里,你的心灵永不会空虚,水远会感到满足!……
翌晨,心灯做过了早课,向病侠所居的石室而去。
当心灯进入房中时,病侠仍然这么躺着,床头放着一只空碗,克布则不知往何处去了。
病侠睁开了眼睛,习惯地向心灯眨了眨,表示欢迎之意,心灯连忙赶过坐下,含笑说道:“病师父,克布到哪里去了?”
病侠作了一个否定的表示。
心灯把房间整理了一下,又把卢妪要强迫自己学“水功”之事,告诉了病侠。
病侠闻言,眼睛转了一阵,似乎在衡商这件事情的轻重,可是他最后还是表示同意。
心灯得到了病侠的同意,心理上更舒服了一些,笑着说道:“病师父,你教我的‘九河天风掌’,我已经练得很熟了呢?”
病侠非常高兴地看了心灯一眼,他把目光停留在门外,似乎在表示什么。
心灯见状思索了一下说道:“病师父,你可是要我叫克布吗?”
病侠把眼睛连眨了两下,心灯又猜测道:“那么你是有什么话要给我说吗?”
病侠用眼睛回答道:“是的!”
心灯却不知病侠为何把目光停留在门口,又猜测道:“你是不是要我出去?”
病侠又狠狠的眨了两下眼睛,表示他很焦急,并且目光还流露出一种责怪的意思。
心灯又猜了半天,若有所悟地说道:“啊!你是不是要我把你拾到外面去。”
心灯话未说完,便看病侠一双眼睛,充满了愤怒地盯着自己,吓得他连忙停了下来,病侠的意思似在说:“你呀!你真是笨得出奇,这么久了,连我的意思还猜不出来!”
心灯见状又气又笑,忖道:“这老怪物脾气可真急燥,病成这个样子还骂人。”
心灯又猜了两次均未猜中,病侠变得更为气愤,一次次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心灯,弄得心灯急得几乎出了汗。
直弄了半天,心灯才恍然道:“啊!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要我把门关上?”
病侠这才表示心灯猜对了,但他的目光继续在责骂着心灯,是在说:“没出息的!猜这么点事还猜了这么半天。”
心灯看得出病侠的心意,点着头说道:“唉呀!这玩意那有这么好猜嘛?”
他说着走过将门关上,转身对病侠说道:“好了,病师父,我把门关好了!”
病侠看了看门,这才把目光转向他睡的石床下,心灯见状问道:“病师父,你可是要我到床底下替你拿东西?”
病侠表示这次猜对了,心灯连忙低着头看去,只见床下只有那只变形药水的小盒子,当时拿了出来,放在了床边。
病侠又示意心灯把它打开。
心灯按照病侠的意思做好,把红白两个小瓶子拿了出来,问病侠道:“病师父现在要干什么呢?”
病侠用眼睛示意,要心灯试涂在手上,为的是怕它年久失效了。
心灯当下把那只红色的小瓶子打开,鼻端已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甚是刺鼻。
心灯又将自己僧袍的衣襟撕下了一小块,稍微的沾了一点轻轻的涂在了左手背上,当时只觉药到之处,皮肤冰凉,不禁吓了一跳,说道:“啊!好凉的药啊!”
病侠双目紧紧的盯视着心灯的双手,显得非常注意。
过了一阵,心灯见自己那只左手,仍与先前无甚分别,不禁奇道:“咦!病师父,怎么一点变化也没有?恐怕是坏了吧?”
病侠却充满了信心,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心灯的左手,不大的工夫,心灯只觉自己的左手有些微痒,低头看时不禁吓了一大跳。
原来他那只左手,已然成了全红色,并且光润异常,搓擦下去,就好像天生的这种颜色似的。
心灯简直被这件奇事弄昏了,他就像个孩子似的,用右手紧紧的握住左手,笑着叫道:“真奇怪!怎么会是红颜色……怪呀!”
病侠的眸子里,射露出一种欣慰和骄傲的目光,谁也不知道,他又由这两瓶药水回忆到了一些什么。
心灯简直是惊奇得不得了,他一会用手用力的搓,一会儿又用水去洗,可是任他怎么样,那红颜色就好像是生出来的一样,一点儿也未减退。
最后病侠被心灯吵得不耐烦了,这才令心灯把它洗去,心灯倒有些不舍,直到病侠一再地用眼睛瞪他,这才把那只白色的小瓶打开来。
立时,心灯鼻端又闻到了一股香味,有些像松子的味道,不禁颇为奇怪,自语道:“怪了,这些药水怎么都这么香呢?”
心灯说毕,又用那块布头,醮了一些药水,轻轻的涂在了手背上,双目紧紧的盯视着。
须臾,心灯见那红色果然淡了下去,到后来变得一丝不剩,完全恢复了原先的模样。
心灯万料不到这小小的两瓶药水,竟会有这么大的功效,真有点匪夷所思。
心灯把两只小瓶收好,放在了小木盒中,问病侠道:“病师父,现在药试过了,还有什么事没有?”
病侠费了很大的力,心灯也是累得一身汗,最后才完全明白了病侠的意思,原来病侠所要说的是:“你现把这药水带回去,因为这个药还有些奇异的特性,你不久就要还俗,应该先做一个准备。”
“十天以后,你带在身旁,等卢妪教你游水时,你偷偷擦在脸上,这药的药性很怪,在开始的时候,入寒水并不显,需要连续十余日方不失效。”
“拉萨河虽非寒泉,但有寒性,正好借此机会作一准备,将来你入牟卓雍湖,便可有备无患了!”
心灯在完全明瞭了病侠的意思后,病侠还要他重复说了一遍,证明他确实了解之后才满意。
这时克布也回来了,手中提了一大包食物,放下之后,对心灯笑道:“师兄,师父昨天告诉我,要你今天开始教我‘九河天风掌’呢!”
心灯见克布如此兴奋,心中也很高兴,笑道:“克布,你习武不久,可是进步神速,真比我强多了,我以前跟病师父练武的时候,不知道挨了多少骂哩!”
心灯说着,并含笑望了病侠一眼,病侠的一双眼睛闪烁了一下,好像表示很歉疚的样子,惹得两个孩子全笑了起来。
于是,心灯便在石室中,将病侠的生平之秘“九河天风掌”一招一式细心的传授克布。
病侠那双神奇的眼睛,一直注视着这两个孩子,他心中充满了欣慰,忖道:“天啊!保祐这两个孩子,他们太可爱了!……卓特巴,你的血账就要清偿了!……”
病侠的想法一点也没错,卓特巴即将遭遇到一个生平最大的敌人——心灯。
夜晚很快的来到,心灯在寺里用过了晚斋,与掩海等小喇嘛在房中聊天,可是他心中一直惦记着万蛟昨夜临行之言,忖道:“他今晚要我去是为什么呢?难道他又要传我别的功夫?……不会的,他不会自找无趣,他应该知道我是再不会学艺了。”
掩海见心灯心不在焉,笑着说道:“心灯真是要还俗了,看他谈话都没有心,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心灯闻言才要分辩,那与他邻床的越密小喇嘛已笑着说道:“我知道,心灯一定是想还俗以后娶个老婆!”
他这句话说得所有的小喇嘛一些笑了起来,心灯更是面红耳赤,大声分辩道:“胡说!我才不要老婆,我将来还会回来!”
心灯这句话说得众喇嘛更加发笑,越密指着心灯道:“算了!你还会回来?你恐怕是带着儿子回来烧香吧!”
这句话又惹得哄堂大笑,心灯知道与这些小和尚说什么也是没用,再说他虽然对布达拉宫怀念异常,可是将来是否能回来呢?连他自己也没有把握。
于是,心灯站起来,推门而出,耳中尚听得他们叫着什么“老婆,老婆”的,不禁觉到非常悲哀,因为他感觉到宗教生活即将夹失了!
可是,外界的一切,是否能填补他因失去宗教而感到的空虚呢?
心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不禁深叹修为不易,和自己的道力不坚,如果他一开始就拒绝了外界的干扰,那么现在他不是好好的在研佛吗?
今晚的月亮倒是挺明亮的,为大地涂上了一层银辉,愈发显寒凉和寂静。
心灯见大色尚早,便在院中散步,他正在全神揣度万蛟为何要他去时,突见贴身伺候主持大师的古忽小喇嘛,如飞地向自己跑来。
心灯见状连忙迎上一步,笑道:“小师兄,好久不见你了!”
古忽连忙答了礼,笑道:“心灯,主持大师找了你好几次,今天才找到你,赶快去一趟吧,不知道什么事呢!”
心灯闻言颇为意外,“啊”了一声道:“啊!主持大师找我?……好的,我马上就去!”
古忽闻言点了点头,说道:“快一点,可别再乱跑了,主持大师好像非常注意你呢!常常向经堂大师问起你!”
心灯闻言又是一怔,问道:“是真的吗?”
古忽已然转身跑去,闻言回头道:“可不是’你快点来吧!”
心灯点了点头,古忽已然飞快地跑远了。
心灯心中诧异万分,因为叠布诺大师主寺以来,只不过召见了他两三次,问问自己学佛的事情,连还俗之事均未提起,这一次为什么三番两次的找自己呢?
心灯想着已然走回了禅房,找出一套净洁僧衣换上,小喇嘛们少不得又是一番纷扰,心灯只是含笑不答。
心灯出房之后,匆匆向主持大师的禅房赶去。
自叠布诺大师接掌布达拉宫之后,他仍然住在第四层以前藏塔所居的房间里,因为藏塔生前与叠布诺深交,叠布诺为了纪念藏塔,所以连房中的摆设丝毫也没有变更。
当心灯快到叠布诺禅房之时,便见古忽迎面走来,当下笑道:“大师可在里面么?”
古忽笑道:“在里面等你哩,快去吧!有什么事出来告诉我。”
心灯点头而去,当他走到禅房门口时,他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悲哀的情绪,因为他想到了藏塔,想到了以前自己习佛的经过,那是一段多么平和恬静的日子啊!
当心灯轻轻地把禅门推开了一点时,叠布诺温和慈祥的声音已然传了出来:“心灯,你快进来,我有好些事和你谈呢!”
心灯答应一声,进入了禅房。叠布诺披着袈裟,正在翻阅着一份手抄本。
心灯连忙跪地膜拜,说道:“弟子心灯向大师叩安!”
叠布诺大师欠身答礼,微笑道:“你起来坐好,我们慢慢的谈!”
心灯应声而起,心中有些不安,虽然他并没有做任何错事,可是仍然有些微的慌张。
叠布诺大师等心灯坐好之后,仔细的把心灯看了好几眼,这才摇着白头,微笑道:“心灯,你的头发太长了,不像个出家人!”
心灯闻言又羞又惭,他又无法说是为了准备还俗,怔怔的说不出一句话来。
叠布诺见状淡淡一笑,转了话题道:“心灯,你可知道我看的是什么吗?”
叠布诺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心灯不胜惊奇,他茫然地摇了摇头,低声说道:“弟子不知道,还望大师见示!”
叠布诺微微一笑,可是他的笑容里,却充塞着一种悲哀和怀念的情绪,用着缓慢而又低沉的语调道:“这是藏塔大师在主寺最后一个月中,所记下的日记,他说了很多!……也有很多地方提到你!”
心灯闻言大吃一惊,说道:“啊!……提到我?”
“是的!他不但提到你,还提到你的身世……他一直是很关爱你的!”
心灯不知藏塔的日记上为何写到自己,写的又是些什么事情,当时紧张万分,嚅嚅答道:“是……是的!藏塔大师生前非常关爱弟子,弟子也最敬爱他……”
叠布诺看出心灯在不安之中,他微微地笑了一下,说道:“心灯,你不必害怕,你并没有做错什么事!……藏塔大师对你非常倚重,我虽然不太接触你,可是你的课业我都查询过,确实很有心得,悟性也是极高,如果你继续修为下去,将来是个得道的高僧……”
叠布诺的每一句话,都打到了心灯的痛处,他只是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叠布诺停歇了一下,接着说道:“……这不但是藏塔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以为藏塔是圆寂了吗?……他是被人杀害死的!”
虽然心灯不但知道这个事实,并且还亲眼看着他死去,可是叠布诺这句话,仍然使心灯大为震惊,他抬起了头,眼睁得大大的望着叠布诺大师。
叠布诺慢慢地站了起来,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来回的踱着步,接着说道:“唉——在他的日记上,他说他当初为了贪习武功以至种下恶因,后悔莫及,只怕恶果随时而至。”
“果然,不久之后,他暴尸经堂!……唉!像他这么一位有道高僧,由于一念之差,而在功德垂成之际遇了天谴,虽然习武对别人并不是罪恶,可是对于他来说,却是一种莫大的过失,所以他功败垂成并不是偶然的,这也就我们佛家的因果问题。”
心灯不知叠布诺为何向他说这些话,可是他心中也深深的为藏塔难受,并且想道:“我原是佛门中人,现在我也习了武功我将来会不会像藏塔一样呢?”
心灯想到这里,不觉有些不寒而栗,虽然是在深秋,也惊出了一身汗。
叠布诺转过了身子,目光炯炯的望着心灯,用着非常恳切的声音说道:“心灯!你的佛学极佳,道心也诚,可是你却要还俗,为什么呢?你不知道宗教对你太重要了吗?”
“现在你也不觉得,可是当你离开这里以后,你必然会怀念这里。”
灯这才恍然,叠布诺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刺痛了他,他惊异地张大了眼睛,注视着叠布诺。
叠布诺接着说道:“你考虑考虑,我希望你能打消这个念头!”
心灯这时思维复杂,他知道不还俗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他低声的说道:“大师!我……我不能!”
叠布诺对心灯的答复很失望,他怔了一下,轻叹一声道:“唉!……你明天把头发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