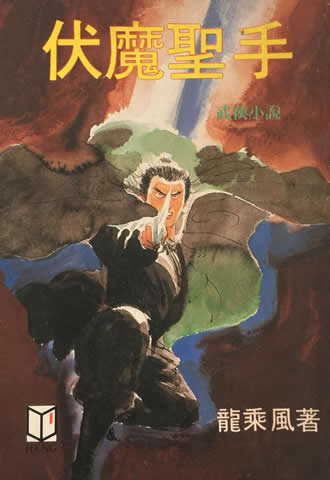蒙着面孔的头巾后面,那人现露着一双淡褐色的眼睛,眼中的神韵在冷漠中更透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寡绝意味;他盯着靳百器,语声平板地开口道:“靳二当家!”
靳百器点点头:“不敢当。”
对方目光流动,道:“其余的人呢?”
靳百器道:“走了。”
哼了一声,那人似乎颇为不悦:“走了?往哪里走了?”
靳百器毫无笑意地笑了笑:“你以为我会告诉你?”
这一次,他居然没有发怒,反倒有所顿悟的样子:“不错,你不会告诉我,但我可能有法子找到他们。”
靳百器道:“那是你的事。”
那人忽道:“我姓岑,叫岑玉龙,‘大龙会’的‘总管司事’;知道我的人,都称呼我为‘血蛇’。”
靳百器道:“席卷‘鹰堡’那天晚上,你似乎不曾到场?”
岑玉龙颔首道:“那晚上我奉命镇守堂口,却是失去一次立功的大好机会!”
靳百器淡淡地道:“不用急,眼前的机会你正巧淌上。”
岑玉龙猛古丁冒出另一句话:“孩子呢?”
靳百器不禁有些错愕:“孩子?什么孩子?”
岑玉龙放缓了声调:“我是指耿杰,也就是你们当家的耿一坤的独子,我方破堡之夜,姓耿的不是把他那宝贝儿子托付于你了么?”
靳百器道:“正是,所以你们‘大龙会’的二龙头史道全才能活到现在,若非为了孩子安全,姓史的早不知埋到哪个窝里去了!”
岑玉龙竟笑了起来:“难怪史老二恨你入骨,提起你来就咬牙切齿,想是那天晚上吃了你不少苦头!”
这岑玉龙称呼他们的二龙头竟用这样的口气,表面上似乎狂妄逾矩,实则正显示出他在“大龙会”中的身价与分量,虽然靳百器早就晓得岑玉龙这“总管司事”的权力甚重,却也未曾料到几有驾凌“大龙会”第二号人物之上的威风!
岑玉龙又接着道:“如此说来,孩子是安全的了?”
靳百器不免疑惑地道:“孩子的情况如何,与你何干?”
岑玉龙言词闪烁地道:“大人拼命,幼儿无辜,我只是表达一个长辈的对晚辈的关切而已,人都有某一方面的仁恕心怀,不是么?”
冷冷一笑,靳百器道:“像尊驾这种长辈,还是少有为妙,尊驾的善意,只怕孩子消受不起!”
岑玉龙眼中光芒映动,古怪地道:“这却不一定,靳二当家。”
靳百器大声道:“什么意思?”
岑玉龙蓦地腔调转为僵硬,变化之快,有如风谲云诡:“意思是说,替史老二他们报仇雪恨的辰光已经到了,靳二当家,你想拖延时间,好让你们那一干釜底游魂从容逃逸,我却由不得你这么称心如愿!”
大砍刀斜举胸前,靳百器平静地道:“你原是为这个来的,岑玉龙。”
岑玉龙慢慢转动身子,当他转到一半,插在后腰板带上的一柄龟壳鞘套长剑业已握在手中,剑锋拔出,映起一溜冷电似的莹莹青光,然后,长剑倏分为二,交叉闪耀,老天,居然是双刃合一的利器!
站在靳百器身侧的“矮罗汉”胡甲凑近一步,压低嗓门道:“二当家,由我先上——”
靳百器摇头:“不,你掠阵。”
胡甲知道靳百器的用意,是恐他敌不过岑玉龙,事实上也的确有些顾虑,搏命当前,不是客气的事,没有把握,只能白白牺牲,便毫无意义可言了,他不再多说,默然退出圈外。
岑玉龙斜瞅着胡甲,声音里似笑非笑地道:“朋友,你要对我有兴趣,且等过了这一场,迟早总会轮上你的。”
胡甲面孔僵沉,双目平视,半句话也不回答;靳百器左臂一抬,道:“请吧,大司事——”
两道剑刃就好像双龙出水,仅仅一晃之下已到了靳百器的眼前,他的大砍刀皮鞘下沉,刀锋暴起,但见冷焰炫映于鞘口,一对长剑已经荡出,先有火星飞溅,才响起连串的金铁撞击之声!
岑玉龙身形回旋,双剑芒彩骤现,宛如万千光雨倾落,口中同时叱呼:“好拔刀术!”
靳百器刀随人走,匹练般的银带绕体流灿,光接合着光,刃连系着刃,镝锋破空,声同裂帛,岑玉龙九次运剑罩盖,全然无功!
就在双方急速的腾掠交触里,岑玉龙猛的一声断喝:“并肩子上——”
应合着他的叱喝,围侍四周的“大龙会”诸人中,立时跃起三条人影,飞扑而来!
不待靳百器分神动手,一旁掠阵的胡甲立刻纵身迎战,短刀钢矛伸缩如电,竟然照面之下就被他截住了两员!
第三个夹击者冲过胡甲的拦截,盾斧并举,悍不畏死的攻向靳百器,靳百器猝旋三步,让过岑玉龙的连环剑式,大偏身,砍刀忽而从他的右手贴肘溜滚,肘尖适时上抬,刀锋便不可思议的突出于肩顶,那夹击者攻扑落空之下,做梦也想不到对方的家伙会自这样的角度冒现,慌忙躲避,却已慢了半分,血光涌处,胸前业已裂开一道尺许长的血槽!
靳百器左手反穿,握住刀柄,刀刃由下而上,划出弧光,以快得无可言喻的速度再次飞虹,斩肉声才起,那甫受创伤的夹击者已被拦腰劈为两段!
同一时间,岑玉龙双剑闪掣,倏然在靳百器背上带起两抹鲜血,但靳百器宛若不觉,他的大砍刀就地猛撑,人巳一个斤斗倒翻过去,倒翻的过程仅是一条短窄的曲线,就在这条短窄的曲线中,刀出如电光石火,像是骤然间炸碎了千万只冰柱!
岑玉龙身形狂掠,着地时连连踉跄,要不是急忙以双剑撑持,差一点就仆跌于废墟之中!
另一边,胡甲正拼着以短刀硬架敌人挥来的尖矛斧,刀身吃力不住,斧刃压落,在他手臂上割裂三寸人肉,几乎就在肉绽的一刹,他的钢矛也送进了对方的小腹!
并肩子力拼胡甲的两位,如今只剩下一员,这一员亦颇有种,趁着胡甲的钢矛未及自他同伴的小腹中拔出,猛一皮盾砸上胡甲的背脊,斧起如锤,狠狠劈向胡甲后颈。
于是,胡甲往前一个晃荡,借着晁荡之势,原地横滚,这一横一滚之间,手上的宽刃短刀猝往回抛,刀势的强劲,不但完全没入对方的胸膛,更把这位“大龙会”的朋友撞出五步,仰头翻倒!
又有五名“大龙会”的人马扑进场中,在他们尚不曾有所行动之前,浑身浴血、衣裂肌绽的岑玉龙已急急挥手,提气叱呼:“住手,通通住手……”
五个人齐齐收势站定,却全拿眼睛望着岑玉龙,姓岑的不理他们,先试着以双剑维持重心,颤巍巍的走出两步,才冲着靳百器道:“难怪史老二在你手下吃了大亏,靳二当家,对‘大龙会’来说,你是一个祸害!”
靳百器舐舐嘴唇,道:“祸害将会更深——岑玉龙,只要我一天不死,你们‘大龙会’便永无宁日!”
淡褐色的眼睛泛现着赤红,岑玉龙艰辛地道:“我们不会允许你继续对‘大龙会’肆虐,靳二当家,我们要使用一切可行的法子除去你……”
靳百器冷硬地道:“彼此的心愿完全相同,岑玉龙,如果你们认为我仅至此而已,就未免轻估你们血洗‘鹰堡’之后所种下的仇恨了!”
深深注视着靳百器片刻,岑玉龙扭头便走,由于身子转动太急,险些又摔在地下,两名“大龙会”的兄弟赶忙抢步过来将他扶住,才歪歪斜斜行向山下,他这一走,“大龙会”其余的人马立时收拾残余,一阵风似的随卷而去。
靳百器目送着这一批凶神离开,默立无语,胡甲步履蹒跚的移了过来,神色怔忡又迷惘,这须臾前后的死斗狠拼,来得快、去得急,对他而言,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将大砍刀连鞘插回腰侧,靳百器用力在脸上抹了一把,微显倦意地道:“好歹又过了—关……”
胡甲愣愣地道:“真是雷声大,雨点小,二当家,我没想到他们这么容易就被打发了!”
靳百器道:“容易么?胡甲,其实一点也不容易,这里面有个关节,我一指明,你就心中有数了,姓岑的精刁得很呢。”
胡甲茫然问:“什么关节?”
靳百器缓缓地道:“岑玉龙起先打的如意算盘十分明显,他认为我们只是一群残兵败将,不但斗志衰竭,可能连抵抗的余勇都已消失,加以他对个人的本领相当自负,行动之初,在实力的掌握上就不很仔细,换句话说,他高估了自己,轻估了我们,等到朝面对阵之后,才知道实际上不是那么码事!”
胡甲咧嘴笑了:“姓岑的约摸以为只待他们一到,立时便可以风卷残云之势将我们一扫而光,杀得落花流水,所向披靡,如何料及竟是撞上大板,碰了个丢盔曳甲,鼻塌嘴歪?”
靳百器道:“我们仅有两人,就我们两个,已生杀他们一双有半,岑玉龙自己亦受创不轻,在这种情形下,他如何还敢轻举妄动、继续深入?岑玉龙尤其担心的是不知我们背后尚有多少伏兵,刚刚开头已然损卒折将,征兆一坏,难免动摇士气,硬撑下去,而敌情未卜,局面将会更糟,姓岑的懂得这个道理,方才下令退兵,胡甲,现在你明白他们撤离的关节何在了吧?”
连连点头,胡甲道:“原来是这么一层因由,难怪岑玉龙走得比兔子还快,我先时犹在奇怪,就凭他,如何会生生咽得下这口鸟气?”
靳百器道:“忍一时之气,总比怀千古之恨要合算,否则,岑玉龙也不会是岑玉龙了!”
胡甲寻思着道:“二当家,你有没有去想,他们是用什么法子探悉出我们集结之处的?”
靳百器道:“我想过,而且想了很久。”
胡甲忙问:“有着落啦?”
目光上眺,天空白云悠悠,靳百器的声音也和天上的云絮一样飘忽:“还不能确定,但是,早晚会有着落的……”
“哦”了一声,胡甲心想:这话不等于白说?他口中却道:“二当家,我们还是早点归队吧,你背脊上的创伤,也该治一治了!”
靳百器似乎忘记了他背上还带着伤,经过胡甲这一提,他才感觉到那股子灼痛,稍微移动了一下腰肩,确定过伤口的位置与深浅之后,他迈步向山侧,姿态形色从容不迫,竟看不出是个受伤的人。
四边是高耸的峰岭,夹着中间一条半涸的河床,就在河床边,三十多个“鹰堡”的余生者开始安营扎寨,几堆营火熊熊燃起,境况虽然凄凉,却也有几分温暖的意味在人心中散漾。
靳百器将手上的羊皮水囊凑近嘴里,深深吮吸,皮囊中装的不是水,是酒,醇厚的老黄酒。
孟君冠与胡甲和他对面坐着,两个人的脸孔上都流露着一种空茫落寞的神色,夕阳余晕透过岭隙照了进来,映染着这两张人脸,那等失依无靠的孤寂韵息就更深沉了。
又吸了一口酒,靳百器放下皮囊,扫了对面两人一眼:“你们不来上一口?”
孟君冠叹了口气:“唉,酒入愁肠愁更愁……”
胡甲也呐呐地道:“我现在才知道,喝酒也要有心情,心情不好,酒喝起来就像苦水,呛鼻辣心,味道实在不怎么样……”
靳百器笑了笑:“光是自怨自艾,长吁短叹就能解决问题、宣泄一肚子窝囊?酒没有招惹你们,漫天的愁苦和酒无关!”
胡甲嘿嘿笑道:“二当家真有办法,我就硬是看不开。”
靳百器转脸问孟君冠道:“你刚才说,我和胡甲是在你们抵达‘旧旱沟’一个时辰后赶到的?”
孟君冠颔首道:“至多一个时辰……”
靳百器道:“而在这一个时辰前后,并没有任何我们的人到来应卯?”
孟君冠苦笑道:“鬼影子也不见—个……”
靳百器沉吟着道:“为了安全上的顾虑,我们撤离‘旧旱沟’,把队伍拉过来应该没错,怕只怕后续到来的兄弟看不到人而心生犹豫,不敢露面,这样就费事了……”
孟君冠忙道:“二当家已派遣徐铁军和两名精干兄弟守在‘旧旱沟’附近接应,照说不会发生漏失的情形才对!”
靳百器道:“这得看他们招子亮到什么程度;后来的人心神必定紧张,行动自然隐密,如果在徐铁军他们发现之前先已察觉沟中无人,恐怕就将逐个远扬而去了……”
沉默了片歇,孟君冠道:“设若如此,也是各人的命,二当家,我们不能拿着三十多人的生死冒险。”
抬头望望天色,靳百器低呼一声:“朝下等吧,我看不用多久,徐铁军那边就该有消息了。”
孟君冠没有答腔,目光虚虚的投向西边绵亘的岭峰,西边的岭峰正浴着火红的晚霞,仿佛把那一片幽翠苍青都燃烧起来,他刚刚没来由的又叹出一口气,视线却突然被一样物事吸引住——
斜晖之下,有一个小黑点在移动,在向这边移动,黑点移动的速度非常之快,仅仅俄顷之间,形状已由黑点转为人体,清晰可辨的人体,这样的飞纵之势,委实惊人!
孟君冠怔愕之余,急忙开口惊告:“二当家——”
靳百器的声音平静而镇定:“我看到了。”
孟君冠顾不得再说话,因为他同时又发现了另三个黑点,三个出现的位置相苦、移动方向相若的黑点,光景像是,前面的在跑,后头的在追!
胡甲双目凸瞪,有些慌张地道:“二当家,我们如今的情况特殊,可不能被外头的人撞见——”
靳百器站起身来,表情木然:“恐怕是避不开了,胡甲。”
胡甲搓着手道:“那,二当家,那我们该怎么办?”
不等靳百器回答,孟君冠已意外的低呼起来:“我的天,跑在前头的这一个,居然还是个女人!”
靳百器补充道:“不只是个女人,这女人年纪已经很大了,或者说,是个老太婆比较恰当!”
孟君冠两眼发直,喃喃地道:“果然是个老婆子,你们瞧瞧,人家这一把年纪,却有那么俊的身法,奔走起来和飞有什么两样?脚下就像他娘踩着风火轮……”
靳百器低声道:“再注意看,老孟,这老婆子似乎还带了伤,左肩上一片殷红——”
;
孟君冠聚目细瞧,一边点着头道:“可不是,受了伤脚下却仍这么个快法,更叫不简单了!”
他们几个人都站在河床边,并没有上前拦阻那老太婆的意思,事实上,只要对方不生麻烦,他们已经阿弥陀佛了,但正急速奔掠中的那位老婆子,倒好像早已觑准目标,冲着他们站立的方向腾身而至。
这老婆子大约有六十以上的年纪,头发花白,扎在脑后的烧饼髻散开大半;原本富态丰腴的一张满月脸,如今青里透紫,左肩上血糊一片,玄色衣裳染得斑斑猩赤,宛如洒上花边,她一阵风似的卷了过来,气喘吁吁中,没头没脑的大叫:“无功不受禄,受禄必有功,你们哪个人帮我一把,老身必有后报——”
靳百器与孟君冠、胡甲互望一眼,又掉转目光上下打量着对方:“老大娘,不知你捅的是什么纰漏,又要我们如何帮你?”
老婆子回头张望,急切地道:“火烧屁股,现在来不及细说了,你们可看清后头那三个天打雷劈的恶煞?他们追来是待取我老命的,你们只要能帮着我打退他们或是打死他们,我定然重重回报!”
孟君冠接口道:“但是,事情真相我们全不清楚,孰是孰非更难确定,却要我们如何帮法?”
猛一跺脚,老婆子怒道:“你看我这把年纪,又是个妇道人家,还能干出什么歹事?性命交关,生死当前,你们要帮就帮,不帮拉倒,可别净扯闲淡,耽搁老身逃命的辰光!”
靳百器眼瞅着远处的三人迅速接近,又瞧了瞧老婆子的模样,微微摇头道:“老大娘,任你轻功再好,以目前的形势来说,要想逃脱人家的追逐,怕是难了!”
老婆子忙不迭地点头道:“我知道,所以我才跑来向各位告帮呀,三位老弟,我们虽是萍水相逢,也算有缘,素昧生平的际遇,有时亦会形成一辈子的契合,你们三位行行好,这更乃积德积福的事哪!”
胡甲有些动容,转问靳百器:“怎么说,二当家?”
靳百器一笑道:“以我们如今的境况而言,正需要多多积德积福,广结善缘,而且这位老大娘也说过了,以她一把年纪,又是个妇道人家,还能干出什么歹事?所以,麻烦我们接下啦!”
老婆子双手合十,眉开眼笑:“好小子,我一看你的相貌,就知道你深具侠性,天生义胆,是一号有担当、有作为的人物,你帮我一把,包管错不了!”
一旁,孟君冠却忧形于色,欲言又止:“二当家,你这么做,呃,恐怕不大——”
摆摆手,靳百器道:“老孟,我自有主张!”
说话间,追来的三个人瞬息已到了近前,那三个人对于目下的情势,显然相当迷惑不解,他们在丈许距离外停下脚步,十分戒惕的注视着这边,犹豫片刻后,才开始缓缓接近。
靳百器端详着这三位不速之客,不禁心里暗暗打鼓——三个人的岁数约摸都在四十上下,走在前头的一个,生得肥头大耳,满面红光,身着织锦夹袍,手执一具精铁算盘,猛然一见,倒似个财主员外;中间的这位却猴头猴脑,火眼金睛,一举一动,搔捞蹦跳,活脱的孙悟空现世;最后面的那个长相魁梧,高有八尺,两柄又粗又重的方头锏握在手里,竟如一尊门神!
老婆子紧贴着靳百器站立,一面细声细气为靳百器指点那三号人物:“老弟,前头走的那个胖子你看到啦?他就是道上最最恶名昭彰的‘黑大户’,‘无相算盘’牟长山,姓牟的后面,是西陲三大杀手之一‘鬼猴’尹双月,那大块头名叫林妙,其实一点也不妙,他是牟长山手下的头一号爪牙,人称‘飞象’的就是他……”
靳百器点着头,边低声道:“然则老大娘你又是何人?”
老婆子嘻嘻笑道:“实不相瞒,人家都叫我‘狼婆子’,我娘家姓崔,闺名是六娘……”
靳百器有些意外的深深看了崔六娘一眼,微带诧异地道:“江湖传言,说崔六娘已在五年之前遭到仇家暗算身亡,莫非此说不确?”
崔六娘气咻咻地道:“都是一干没安好心、绝子绝孙的泼皮货在那里乱嚼舌根,故意咒我!五年前我遭到仇家暗算是没有错,却是大难不死、后福无穷,又几曾身亡过来?真正一窝子碎嘴——”
这时,靳百器已来不及再听崔六娘发牢骚,因为走到跟前来妁三个人已经在那里说话了,开口的是“无相算盘”牟长山:“兄弟牟长山,先在这里向老兄拜过码头,拿清言语,且劳兄弟与姓崔的老虔婆把帐算过,再赔闯山之罪!”
靳百器拱手道:“牟大户言重了,不知尊驾与崔大娘有什么过节,竟闹到这等水火不容的地步?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江湖同道,草莽系缘,要能揭过,还是以化解为上……”
牟长山脸色一沉,重重地道:“老兄,我牟某人可是按照规矩来的,至于我与姓崔的老虔婆有什么纠葛,别人无须多问,问了也不管鸟用,老兄和我不亲不故、无怨无仇,奉劝你还是勿趟浑水,一边风凉为妙!”
崔六娘怪叫一声,火辣地嚷着:“你们听听,你们可是都听到了,这他娘的牟长山说的话还像是些人话吗?人家一番好意,出来打圆场、做仲裁,他居然狗咬吕洞宾,扯下面皮骂起山门来了,发横卖狠到这步田地,真正是可忍孰不可忍!”
牟长山板着面孔,恶狠狠地道:“崔老帮子,你不用在那里挑拨怂恿、火上加油,牟爷既然追了来,就非摘你的脑袋回去不可,谁也拦不住,谁也不敢拦,你拿着这批孤魂野鬼,当是找到护身符啦?”
靳百器不愠不怒,轻描淡写地道:“牟大户,我们尚未表明态度,只是为了息事宁人,劝说两句,此亦非什么大逆不道之事,况接受与否,但凭尊驾,尊驾却嘴上伤人,出言无状,未免过于嚣张了吧?”
牟长山冷冷一哼,抬眼望天,将手上的精铁算盘摇得“哗啦啦”直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