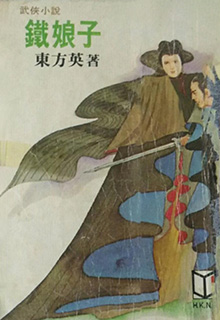天色漆黑,日月无光。
坐落旺水县城北大街中段的“苇记顺水局”、城东“升和巷”的“苇记骡马行”,同时起了大火,火势起得突兀,烧得炽烈,一发便不可收拾。从四边窜燃的火苗中,还穿梭着多条蒙面人物。这些蒙面人物可不是来救火的,而是专来宰杀救火的人及逃出火窟的余生者。“苇记”这一方人,如遭斩瓜切菜般,被屠戮得尸骸遍布、血流成渠了。
差不多的辰光,一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宜兴县城与濮来县城的“苇记”字号。两地四处的水陆买卖场所,宛如约定了似的大火齐烧,杀手骤至,只落得一片灰烬,遗尸纵横。
前后大概不到两个时辰吧,挂着“苇记”标志的六个门堂,已全部荡然不存,化做焦土残垣,端木一苇苦心经营了十二年的生意亦就此烟消云散。
当晨曦熹微,摸来端木一苇、荆力疾等养息处的人井非他要召唤的得力手下曲从杰或石辉,而是原先就被差去传讯的饲科行伙计杜小三。
急促的敲门声惊得端木一苇打竹榻上一跃而起,却因身体的平衡力不匀差点猝跌在地。荆力疾赶紧喝止了他,自行下床开门,到底荆力疾的伤势还不怎么影响行动。
启门的一刹,杜小三踉跄扑进,干瘦的一张脸孔上面如土色,因为喘息迫急而至嘴角溢漫白沫。
坐在榻沿的端木一苇但觉脑子里一片空茫,两耳“嗡”“嗡”作响,须臾之间,似乎任什么感触、任什么思维全没有了。
荆力疾拉了把椅子,强按着杜小三坐下,顺手斟了杯冷茶递过,一面尽量把语调放得平缓、低沉:“不急,老弟,不急,天大的事慢慢说,反正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急也不管用……”
捧起茶杯,杜小三仰颈“咕噜”喝了个净,来不及抹去唇边茶渍,已上气不接下气地叫嚷起来:“不好了,端木爷,大事不好了哇!你老那三县六家门堂,全被一把火烧了个片瓦不存,你手下伙计们也遭到外来袭杀抢掠,如今还不知死伤了多少人?这辈子我尚不曾见过这辱惨事……”
端木一苇呆呆僵在那里,目光直愣愣地瞪着气急败坏的杜小三,好像听到了杜小三说的话,又似乎并不确认杜小三话中表达的信息,人显得有些迷乱。
荆力疾倒沉得住气,相当镇定地道:“你的消息确实无讹?”
杜小三不停点头:“回荆爷的话,我奉到端木爷的交待之后,先请来叶大夫,接着立马加鞭就赶到旺水县城,旺水隔着这里近嘛,谁知才抵北大街,通天大火已把‘苇记顺水局’烧了个透红,大火中,还有些蒙着脸的凶煞四边冲扑,对着打火窟逃生出来的人们恶砍狠劈,我吓得赶紧调头奔往城东‘升和巷’,想去骡马行再找曲从杰曲爷或石辉石爷传信报警,却做梦也没想到,骡马行的光景也同北大街一个样,火苗子亦染夜空,刀口子净剖人肉。烟呛和着血腥味,我差点胆都惊破了……”
荆力疾重重一叹:“如此说来,你是亲眼目睹了。”
杜小三自己斟了半杯冷茶,一口喝下。
“旺水县城的情景我亲眼看见,一点不错,等我跌跌撞撞跑回饲料店,我们老板站在门口,脸都绿了,他哆嗦着告诉我,方才有人专程前来报信,邻近的濮来、宜兴县城,凡属‘苇记’字号的买卖亦全被烧杀一空。老板叫我尽快知会端木爷,早做应变。老板还说,铺子经营牲口饲科,多年来大半由‘苇记’照顾,这么一搞,眼看生意都难维持下去啦……”
荆力疾不知怎的,也觉得喉干口燥,他索性举起茶壶,对嘴灌了几口,但冷茶毕竟浇不熄心中那股怨火,“碰”声放下茶壶,他眸底漾出一抹血彩;
“晁二头陀那些天打雷劈的杀胚,真个心狠手辣、无情无义,把事全做绝了,这明着要逼我们走投无路、不得超生……”
忽然间,端木一苇似已回到现实,彻底清醒过来,这一清醒,情绪反而十分平静,仿佛看透了、顿悟了:“烧的烧了,杀的杀了,只不过,所烧所杀,决不会白搭!”
杜小三惶恐地道:“端木爷,事到如今,你老可得有个打算。”
端木一苇咧嘴惨笑:“力疾,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一昂头,荆力疾道:“照眼下情势看来,我们唯有避之一途。”
端木一苇颓然道:“先留青山在?”
荆力疾道:“要不,刨根究底,岂不全完了?我荆力疾、你端木一苇,还算个称字道号的人物?”
一拍榻沿,端木一苇道:“好,我们走!”
荆力疾道:“不但要走,尚得快走,端木,这干邪碎不但手段狠毒,而且剽悍积极,行事毫不拖延,如果我没有猜错,很快他们就会循线找上门来!”
下意识望了望门扉,端木一苇挣扎下床:“事不宜迟,我们避之则吉——”
杜小三连忙指指桌上瓶罐所盛的药物:“端木爷,这些一齐打包吧?”
端木一苇道:“快!”
迅速收拾妥当,荆力疾先行启门探视,然后,他低声道:“还好尚无状况,端木,走人再说。”
杜小三立在门边,脸上明显流露着依依惆怅之色:“端木爷,这一去,可是去哪儿?”
拍拍杜小三肩膀,端木一苇笑得苦涩:“小三,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我必定回来!”
于是,夜色凄暗中,两条身影很快已消失在茫茫远处,走得可够寒怆。
山坳子里,这爿小茅屋背靠着苍苍郁郁的坡脊,面对迤逦起伏的旷野,右侧一湾流泉蜿蜒而去,溪上有道小小的拱石桥,地方可称隐蔽,景致嘛,说清雅不如说荒寒。
荆力疾和端木一苇,落脚在此处避难,已有大半个月了。
这天大早,荆力疾出了茅屋,开始每日例行的遛腿功课。他经石桥往荒原中走,打算照以前一样,绕上个十里八里再弯回来。
一边深深呼吸,他一边在晨雾轻漾的野地间有规律地举抬受过骨伤的左臂。调养了这一阵,他自己亦感觉到甚有起色;伤痛的部位,已越见轻缓平和,那位“叶大国手”,果然是有两下子。
就在他行经一棵合抱大树侧旁不远,几声低弱的呻吟,已似有似无飘进他的耳膜。
所谓“似有似无”,只是形容声息的细微,有无之间,荆力疾自则分辨得一清二楚。他略略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凑到大树之前探探究竟。
这一探究竟,不由令他又是后悔,又是懊恼。因为树根盘错的另一边,明明白白有个女人蜷缩在那里,这个女人非但呻吟不绝,而且混身连连颤抖,江湖人素重侠义,他岂可将这两字践踏脚底?
那女人身材纤细,个头娇小,躯体缩成一团,便益发显得柔弱零丁,楚楚可怜了。
搓着手,荆力疾近前儿步,开口道:“呃,这位嫂子,你是怎么啦?”
女人非常费力地仰头侧面,慢慢迎视荆力疾——嗯,却是长相不差的一个小女人,清水脸儿,五官均匀而娟秀,若非目下形态憔悴,神情滞重,平日里,该是个漂亮惹眼的娘们。
干咳一声,荆力疾又道:“这位嫂子,我在跟你说话,可是哪里感到不妥么?”
那女人惨白着面庞,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声若蚊蚋:“我……我全身虚软,手脚无力,又发烧,又恶心……走到这儿,就再也走不动……”
当然是走不动了,若走得动,还会窝倒在这个四面窜风、一片荒寒的旷地里?荆力疾道:“天气冷,地方又处山野旷郊,你待在这里,怕挺不住,还是去我那茅舍暂且歇一阵吧?”
女人并不推拒,亦未多生疑虑,只感激地道:“敢情好,就偏劳这位大哥了。”
眼看对方连走路都有困难,荆力疾好人索性做到底,送佛送上天,伸出右胳膊,一把扶起这位妇道,几乎是完全承担了对方的体重,半搀半抱地转回来路。
一边走,他一边思忖——这女人软塌塌的还真不大有份量,可怜仅剩几根瘦骨头了。
茅屋里生了一盆炭火,熊熊火光旺一团融融暖气,使这片狭隘的居停满室如春,荆力疾扶着少妇推门进屋,女人原本紧绷的身子很显然的放松下来,这种松弛,不用说乃是一项舒泰的反应。
另一项反应出自正躺在以草垛为床的端木一苇身上,他骤见荆力疾连拥带抱弄了个女人回来,不禁大吃一惊,慌忙坐起,瞠目不知所云。
荆力疾扶着少扫来到自己那张平铺的草垛之旁,小心翼翼地先让人家躺下,这才回头冲着一脸怔愕的端木一苇笑笑:“天寒地冻,这位嫂子偏生病倒荒野,人心是肉做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咽了口唾沫,端木一苇道:“你认得她?”
荆力疾道:“不认得,是我出门遛腿时碰上的。”
端木一苇有些苦笑不得:“救人一命,不论造几级浮屠,却也得想想自家的处境,力疾,我们目前好比泥菩萨过江,哪有余力管这些闲事?”
荆力疾“嘘”了一声:“小小落了点难罢了,有什么大不了?前人骑马我骑驴,后面还有走路的,咱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位嫂子,情况岂不更要惨上二分?端木,种善因,得善果哪。”
端木一苇翻了翻眼珠子:“上次关头一过,你好像开朗了许多,看法也似豁达了?”
荆力疾干笑道:“只是不再去钻牛角尖。”
转头望了我草垛上躺着的女人,端木一苇道:“这一位的芳名是?”
荆力疾摊摊手:“还不知道——”
那女人吃力地微微撑起上半身,落落大方,却也幽幽凄凄地道:“二位大哥,我叫迟莲,迟早的迟,莲花的莲……”
荆力疾忙道:“莫动弹,躺着说话就好。”
端木一苇在嘴里念了两遍,接着道:“迟,呃,迟姑娘,这大清早,你怎么会抱病倒卧于荒郊野地,你可知道,这是桩要命的事啊。”
这位迟莲姑娘的貌态神韵固似人妇,但处世情操仍纯真无邪,如未嫁的少女,她闻言之下,眼眶立红,泪水忍不住顺腮而淌,好一付委屈痛苦的模样。
端木一苇赶紧道:“对不住,姑娘想有难言之隐,是我冒昧了——”
看来,迟莲不是一个老于世道,并善于掩饰情感的人,她边以袖口拭泪,边直率地道:“不要紧,我只是心里难过,有感自己的命苦运舛,遇人不淑,一时又想起未听老爹的教诲,而自作自受,越增悲楚惶恐,这两位大哥千祈见谅……”
端木一苇道:“我姓端木,双字一苇,救你的这位,姓荆,名力疾。”
荆力疾斟了碗热茶捧过去,不好托喂人家,但以指尖扶着碗底,给迟莲喝了下去,举止之间,有少见的温柔。
迟莲谢了一声,大半碗热茶落肚,人也稍稍增添了几分精神,双颊晕染起两朵酡红,好看是好看了点,毕竟仍不脱病态。
放下茶碗,荆力疾顺口问道:“迟姑娘,你原本打算往哪里去?如何又闯进了这个鬼地方?”
迟莲叹了口气,亦不矫遮什么:“我,我是想回我老爹的家,也就是我原来的家,我生出来不到三岁没了娘,从小便是与我老爹相依为命,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那可是一段非常快乐、非常令人怀念的时光,直到四年以前,我遇上了涂铮这个冤孽——”
荆力疾砸砸嘴:“既称‘冤孽’,想是恶缘——”
端木一苇瞪了荆力疾一眼:“听你的还是听谁的?”
荆力疾道:“陪衬陪衬嘛。”
迟莲续道:“涂铮在离我家不远的小镇上一爿酱园里当账房,我是去打酱料时认识了他,他对我很好,一直很好,我看他为人殷勤,做事又巴结,久而久之就有了感情。但是我爹不赞成,说他虚浮不实,巧言令色,不是个可托终身的对象。我当时被涂铮的追求冲晕了头,偷偷跟涂铮离家出走,做了他没有名份的妻子……”
荆力疾道:“这叫‘私奔’,结局好坏难说,全得看造化了。”
迟莲浅然一笑:“荆大哥,你已看到我是个什么样的造化了——自我跟了涂铮出走,不到几十月工夫,他便原形毕露。……四年多来,他不顾家,不理我的生活,全靠我在外接些针线活计来糊口。靠后,他昧着良心又搭上别的女人,则更变本加厉,张口骂,动手打已成习惯。我委实忍受不下去了,只好逃了出来,我要回到我早先的家,回到我爹身边,但求老天还能赐给我悔过的机会……”
端木一苇道:“你个单身女子,路上难保不出差池,怎就不雇一乘轿子或套辆车?”
迟莲垂下脸来:“我,我没有钱,雇不起车轿,约莫路上遭到风寒,人一迷糊,方向也摸不清了,这才阴错阳差,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会走来了此地,遇上荆大哥…”
端木一苇低喟道:“可真应合那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
荆力疾接口道:“你有病在身,总得找个郎中来瞧瞧,拖久了,小病变大病,可不是做耍子的。”
迟莲呐呐道:“就怕太麻烦二位大哥……”
荆力疾自告奋勇:“不麻烦、不麻烦,出山坳子十几里地,那小镇甸上即有郎中悬壹,我这就去请了来,顺便也给你带点穿的用的。”
迟莲脸庞涨红,带点儿受宠若惊:“不,不用,荆大哥,我还能凑合——”
没再犹豫,荆力疾已一阵风似的卷出门外,劲头十足。
端木一苇笑道:“让他去吧,这家伙向来不爱管闲事,这一遭,倒热心得少见。”
迟莲语气有些激动:“端木大哥,我是绝处逢生,算遇上贵人了,二位的大恩大德,真不知该如何图报?这人世间,到底还有温情啊……”
果有温情么?端木一苇不由心生感慨,家破人亡之余,自己企盼的温情又在何处?
“龙尾岗”下有座小村落,名为“双塘村”,其中一户人家,就是迟莲故居。从山坳子来到这里,纵然雇了篷车也足足走了三天,端木一苇伤未大好,行动仍旧不甚便利,所以,是由荆力疾护送迟莲回家的。
荆力疾对这位萍水相逢的小妇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向,他只是觉得彼此有缘,怜悯与同情反是其次。他珍惜的是迟莲那份纯真直率,喜欢那种毫不做作的亲切感受,确实来说,有几分小妹妹的味道。
他从来没有妹妹,甚至,连同胞兄弟也没有。
荆力疾扶着迟莲在篱门旁下车,并上前呼问,叫不几声,一个银发白髯,蚕眉凤目的老人走了出来。老人中等身材,着一袭黑布夹衫,打扮土俗,却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逼人英气。
用不着猜测此为何人,只听迟莲悲惭瑟缩的叫那一声“爹”,便知是父女团聚了。
老人蓦地一愣,等瞧清楚来人是谁,便趋前几步,迎住扑入怀里的迟莲,轻轻抚拍着女儿的肩膀。尽管双眼中泪光闪动,却了无愤恨责难,流露的只是宽慰与谅解:“好,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这时的迟莲,已哭得宛如个泪人儿。
老人不曾多同,更没有半句斥骂,仿佛这一切的一切,早在他洞烛之中。
老人亲自送上茶来,在荆力疾对面坐下,他手捋白髯,清朗地一笑:“这丫头好任性,竟熬了四年,我原本思忖,她一年半载便该受够了。”
荆力疾端容道:“老伯睿智,断事如神——”
摆摆手,老人目注荆力疾,道:“我叫迟弧鹤,老弟是?”
荆力疾报上姓名,同时心里暗自索寻老人的名字,因为他竟觉得相当耳熟。
迟孤鹤淡淡地道:“荆老弟,你是不是听过我的名姓?”
荆力疾敲敲自家的脑门:“觉得很熟,老伯尊讳,我一定在哪里入耳过,因为,这并不是个很通俗平常的名姓!”
迟孤鹤道:“莲儿进屋之前,曾告诉我她在逆旅穷途之际,病苦缠身之时,全承荆老弟搭救施援!”
荆力疾忙道:“不足挂齿,老伯,任是谁碰上这种情形,都会做同样的事。”
微微摇头,迟孤鹤道:“只怕未必。”
他笑了笑,又道:“看老弟言谈举止,大约是江湖中人吧?”
荆力疾坦然道:“说来惭愧,多年草莽翻腾,至今仍混不出个名堂来。”
迟孤鹤平静地道:“老弟客气了,实不相瞒,多年以前,我们还算道上同源,这所谓‘多年’,屈指算来,已是二十余载的往事了。”
荆力疾立道:“就是嘛,初见老伯,我已觉得老伯气宇不凡,威仪自在,似非扶犁荷锄之辈!”
迟孤鹤神志安祥,状如古井不波:“都是陈年旧事了,不提也罢;其实种种田、收收粮,日子虽平淡,却也过得不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人这一生,不和四季农序差不多?”
荆力疾有所感触地道:“人要看得开,抛得去,才能享这般的清福,若有负累背着,想悠游洒脱也难……”
迟孤鹤一笑:“‘负累’也者,大多脱不开恩怨屈辱,情仇纠葛,老弟却是为的哪一桩?”
端起杯子啜了一口茶,荆力疾赫然道:“可以说,算屈辱吧。”
迟孤鹤道:“如蒙不外,是否可说来与闻?”
于是,荆力疾坦坦白白把他和端木一苇怎么跟晁松谷结怨成仇,又怎么牵扯出“彤云山庄”的这段经过始末详述了一遍,末尾叹着气道:“‘彤云山庄’那老家奴屠默山出面之前,自认笑傲江湖,不可一世。但只这姓屠的单枪匹马,挥杖上阵,已将我们打得丢盔曳甲,灰头土脸。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是不错,可一个‘彤云山庄’的家奴就能嚣张成这样,他再怎么称人上人、天外天,却如何令我们心服?!”
迟弧鹤沉默半晌,缓缓地道:“荆老弟,不怪你怨叹难平,缘因你太不了解‘彤云山庄’的内情,亦太不了解那屠默山来历了。”
荆力疾睁大双眼:“莫非老伯对他们知之甚深?”
迟孤鹤往椅背上一靠,神情仍是贯常平静:“也说不上‘知之甚深’,闻你所言,大概要比你多清楚他们一点,荆老弟,‘彤云山庄’扬威武林,名倾江湖,自有他们的渊源历史,家族背景,你可晓得,‘彤云山庄’的字号打响多少年了?”
荆力疾茫然摇头:“我只记得,似乎我出道之初,已听过‘彤云山庄’的名声……那已是许久以前的事。”
迟孤鹤道:“约莫三十年前,山庄甫创不久,业已声誉鹄起,威名大噪。这固然有赖于庄主鞠仁宽的艺业超凡,交游广阔,会做人,懂交际,却也蒙受了他老子鞠悟非的若干荫庇。鞠悟非本身便是‘玄剑门’的宗主,剑术精湛,自成造化,平时四方结缘,疏财仗义,替他后代子孙奠下了称雄于世的深厚基础,轮到他儿子鞠仁宽,在‘浩峨山’筑立‘彤云山庄’,上承其父遗荫,下接八面捧抬,自更水到渠成,风云际会,声势之隆,即非同小可了。”
荆力疾怔怔地道:“老天,我还不知道鞠氏家族中另有一个‘玄剑门’的门派……”
迟孤鹤接着道:“至于那屠默山,号称‘天魔杖’,早年拜师于‘震山神’古习尧门下,手上一杆四环杖使得出神入化,刚猛无比。他可以从身上任何部位运力震杖,亦能在走势之间随心调换方向,荆老弟,你知道屠默山和‘彤云山庄’是个什么关系?”
荆力疾苦笑道:“尚请老伯见示。”
迟孤鹤道:“屠默山的老娘,便是‘彤云山庄’庄主鞠仁宽的乳母,屠默山不仅自小习武受教,皆由鞠家一手安排,连他这辈子的出路发展,鞠家亦都替他铺妥了。”
吞着口水,荆力疾道:“就凭他那付德性,岂能干上‘彤云山庄’的大管事?”
迟孤鹤哂道:“你看屠默山卖相欠佳功,功夫却是一等一的,你败在他手下,不算屈辱。”
心里虽然不大是滋味,荆力疾表面也只好唯唯喏喏:“呃,姓屠的是不好对付。”
迟孤鹤的两眼,似能穿透人的肺腑:“老弟,我这样说,乃就事论事,直言无讳,如有逾越之处,还请包涵则个。”
荆力疾连忙拱手道:“老伯言重了。”
迟孤鹤续道:“姓屠的虽是大管事,然而头上还有副总管事,总管事,那两个的能耐,就更够瞧了!老弟,你与你的伴当,这次纰漏不独是捅翻了马蜂窝,简直可谓打开了地府门!”
荆力疾又咽着唾沫道:“老伯,只不知老伯对‘彤云山庄’的各项内幕,如何知晓得这等详尽?”
迟孤鹤抚须髯,道:“二十余年前,我与‘彤云山庄’各属,亦颇有过往。”
能和“彤云山庄”“颇有过往”的人物,当然不会是泛泛之辈,寻常之流,荆力疾试探着问:“老伯那时是?”
迟孤鹤的形色在平淡中仍掩不住那一股隐隐而显的孤傲自雄之态:“那时候,人称老夫我为‘化龙镇岳’。”
霍然起立,荆力疾重重抱拳,极顺口的溜出两句歌诀:“孤鹤儿龙来,云爪镇五岳——不提老伯尊号,我一时竟连想不起迟孤鹤即为‘化龙镇岳’,老伯盛名不衰,当年睥睨武林,迄今留誊江湖,如雷贯耳,真个如雷贯耳了!”
迟孤鹤目光烟蒙雾远,低叹一声:“老了,老了,俱往矣……”
荆力疾凝视着眼前这位曾经名闻遐迩的皓首老人,却想不出,会是什么原因,在他极一时之盛的当日,竟突兀销声匿迹,退隐林下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