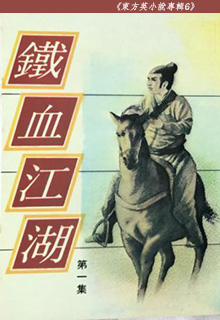东方霸主心知这掌定可将席大先生击中的,是以在他推出那一掌之际,他心情之轻松,实在是难以形容。
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那一掌才推出,突然之间,他的背后,便有一股劲风袭到。
那股劲风,倏然而至,来势快到了极点,而且事前一点迹象也没有,等到东方霸主觉出有股劲风自后袭到,心知不妙,想要反击之际,却已然迟了。
只听得“叭”地一声响。
那“叭”地一声,并不是他的一掌击中了席大先生,而是他的背上,被人家一掌击中。
东方霸主的功力果然非同凡响,那一掌的力道着实不轻,自然令得他不能再袭击席大先生,但是他在受了如此沉重的一击之后,身子陡地向侧避开了一步。
就在他一步避开之际,一条人影,在他身边,刷地掠过,跃向席大先生,东方霸主看得十分分明,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那自称姓白的怪人。
东方霸主眼看可以得手,却两番被那怪人坏了事,心中实是恨极,身形尚未站稳,一脚便已飞踹而出,直踢向那怪人的腰际。
东方霸主不认识那怪人就是东方白,是以那一脚的去势,十分之猛,“砰”地一声,踢中了东方白。
以东方白此际的功力而论,他勉强可以挨上东方霸主的那一脚,但是在挨了那一脚之后,再想将席大先生救走,却是有所不能了。
然而这时的情形,却多少有点不同,因为东方白正以极快的势子向前窜去,当东方霸主那一脚踢中他的时候,他身形仍然在迅速的向前扑出,是以在自然而然之间,将东方霸主的力道,卸去了大半。
所以他非但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反使向前的去势,加快了许多。
他在席大先生的身边掠过,一伸手,便挟住了木立不动的席大先生,电光石火之间,身形已掠出了三五丈开外,足尖跟着一点,再度飞掠而起。
东方白此际的模样,可怖之极,根本不像是一个人,他向前疾冲而出,在他面前的许多人,各自发出一声喊,便纷纷退了开来,东方白如入无人之境,转眼之间,便已冲过了演武场的人群。
直到此际,东方霸主又发出一声巨喝,身形展动,像要追了上去。东方霸主若是立即倾全力追上去,东方白是不是可以带着席大先生安然离开日月庄,那可大成疑问。
然而,东方霸主还未曾起步,血猿神君的双眼通红,便已经向他扑了过来。
东方霸主好几次机会,都被人半途破坏,心中实是恨极,虽然真正坏事的是东方白,但此际血猿神君向他扑来,他却将一口恶气,全都出在血猿神君的身上,他突然转过身,一声大喝,挺胸相迎。
血猿神君来势何等快速,但东方霸主迎上去的势子更快,电光石火之间,“蓬”地一声响,两人的身子已重重地撞在一起。
血猿神君和东方霸主的身子相撞,所发出的那“蓬”地一响,实在惊人之极。在演武场旁的千余武林中人,看到一个怪人突然将席大先生带走,已是心中惊讶得难以形容,突然之间,又看到东方霸主和血猿神君两人的身子,忽然重重地撞在一起,不禁大是骇然。
需知高手过招,各种怪异的招式出得再多,看的人至多叹为观止,也不会有那样的骇然之感的。
但是此际,东方霸主和血猿神君两人,却根本不是动手,而是他们的身子疾扑在一起。
那样的打法,实在是任何人都没有看到过。
事实上,那样打法,对东方霸主这样一等一的高手来说,也是大失体面之事。但是东方霸主心中,实在已将血猿神君恨之切骨,是以才那样的。
紧接着那“蓬”地一声响,只听得血猿神君发出一下撕心裂肺的怪叫声,身子突然呼地向外飞了出去,而东方霸主却立时落了下来。
东方霸主和血猿神君身子相撞,东方霸主占了上风,那已是在人意料之中的,只是看到血猿神君如何败法而已,只见血猿神君的身子一面向外飞出,惨叫之声不绝,连叫了三下,他才落于就地。
他刚落地之际,人还是站着的,可是转眼间,他整个人却软了下来,竟是软成一圈。
一个人的身子,竟可以软成那样的一圈,那也是在场众人,见所未见的事,一时之间,人人倒抽了一口冷气,见识较多的人,已然知道,血猿神君刚才和东方霸主一撞之间,已被东方霸主运内力将他的全身骨骼,尽皆震得寸断了。
若不是全身骨骼都成了寸断,一个人如何会软成那样,倒在地上。
血猿神君虽然全身骨骼已被震得寸断,但是一时之间,却还未死去,只见他身子软成了一圈,但两只眼睛,却还在骨碌碌地转着,实在是恐怖之极。
在演武场之旁,虽然有上千人之多,但是人人看到那种可怖的情形,却是一声不出,屏气静息,以致静得鸦雀无声。
足足过了半盏茶时,才看到血猿神君的眼珠,停止转动,已死于非命了。
血猿神君本是邪派中人,此际在演武场四周的各派人中,不乏和他友谊甚深的,可是看到他是死在东方霸主之手,而且死得如此惨绝,谁还敢出声?
血猿神君虽死,东方霸主的恨意未消,仍然是脸色铁青。
所有人之中,倒是东方雷最先开口,东方雷也是刚定过神来,他朗声道:“爹!大敌已去,可以安枕无忧了。”
东方雷的话,人人可闻,他一出声,席玲立时向他奔了过来,接着有百余人围了上来,有的道:“东方先生神功盖世,真了不起。”
有的道:“席大先生这一走,虽然侥幸逃出一条命去,但是他在日月庄中栽了那样的筋斗,只怕再也不好意思在江湖上行走了。”
这世界上,要找别的难,但若是武功高了,要找人来奉承,那实在太容易了。
转眼之间,围在东方霸主、金兰花、东方雷和席玲四人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七嘴八舌,奉承的话儿,也是越来越肉麻。
东方霸主虽然气走了席大先生,撞死了血猿神君,但是他和席大先生动手之际所用的手段,却是十分卑劣,贻笑方家,实在是十分丢脸的事,他自己的心中,自然是有数的。
是以众人的奉承话说得太过火了,他听着也不是味儿,然而人家是在恭维他,他却也不能怎样,是以只得抱拳道:“多谢各位,请在小儿喜筵之上,多喝两杯。”
他一面说,一面便向外走去。
他向外一走,围住他的人,自然而然便让开了路,金兰花仍拉住了东方雷的手,跟在他的后面,席玲也跟着,日月庄两位庄主道:“东方先生,你们夫妇得以团圆,理应庆祝一番。”
两位庄主是存心讨好的,却不料金兰花却翻了翻眼,道:“你们都让开,我和他还有旧账要算。”
两位庄主碰了一个钉子,也不敢说什么,只是陪着笑脸,讪讪地走了开去。
两位庄主尚且如此,其余的人,自然更是自己识趣,一齐散了开去。
这时,他们已来到了一个小院落中,东方霸主见左右无人,勉强笑道:“兰花,过去的事,还提它作甚?不如就此算了。”
金兰花面色一沉,道:“什么算了。”
东方霸主指着东方雷,道:“兰花,当年你和我,会忽然大起龃龉,当然是因为他而起的,如今你看到他已长大成人,佳儿佳妇,心中还不高兴么?以前的事,还有什么好提的?”
东方霸主那样说法,自然是在暗示金兰花,过去发生争执,都是你的不是,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金兰花“哼”了一声,道:“可是你对付我的手段,也太毒辣些了,竟趁我不觉,将我自千万谷的百丈悬崖上推了去,若不是我命不该绝,现在早已成了一堆白骨了,我怎肯干休?”
东方霸主笑道:“你还好说呢!你自己要用天女教规来惩处我,我有什么办法?”
金兰花的脸拉得更长,东方霸主心知金兰花虽然恼怒,但见她没有立时出手,那已是有商量的余地了,是以他忙又道:“雷儿,你求求你母亲,说都是你爹的不是,当时为了保存你的一条小命,才生出那么多事来的。”
东方雷为人,何等乖巧,一听父亲如此说法,立时双膝一屈,在金兰花的面前跪了下来,道:“娘!你别和爹多计较了,若是你定要和爹计较,那么,当年的争执,既然是由我而起,不如先让我死去,也好让父母因为我死而息争。”
金兰花虽然恨东方霸主当年的薄情寡义,但她知道自己也有不是。何况现在儿子也那么大了,如果一定照着天女教的教规行事,哪里会有人跪在自己的面前叫自己娘?一想到这里,金兰花的心中,便软了下来,道:“雷儿快起来,便宜他了。”
东方霸主一听,首先“哈哈”一笑,向金兰花作了一揖,道:“多谢娘子开恩。”。
金兰花呸地一声,道:“谁和你油嘴滑舌?”
东方霸主此际,心中的高兴,实是难以言喻,他虽然未曾将席大先生当场击败,但是席大先生真气走入岔道,已是凶多吉少。
而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和金兰花之间的一段夙仇,竟然因为东方雷的原故,在三言两语之下,便已一笔勾销。
东方霸主自然知道金兰花的武功极高,有了她做帮手,那么就算席大先生一点也未曾受伤,那也全然不足为惧了。
是以他不由自主,呵呵大笑,道:“雷儿,你先领你母亲前去休息,我还有点事要办。”
东方雷笑道:“爹!你和妈久别重逢,怎地又立时分开?有什么事,吩咐孩儿去做就是了。”
东方霸主笑骂道:“扯蛋,没规没矩,来寻你父母的开心,我去去就来,你先伺候着你母亲,和她讲一些你在江湖上被人欺侮的事。”
东方霸主一面说,一面向东方雷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他跟出来,东方雷会意,诈作送东方霸主出去,父子两人走开了三五丈,东方霸主便低声道:“雷儿,你母亲一来,有一个人绝留不得了。”
东方雷一呆,还不知道父亲那样说法,是什么意思,但东方霸主已接着道:“你母亲的妒意极重,那瞎眼女人的事,你千万不可提起。”
东方雷立时了然,明白东方霸主指的是什么了,他呆了一呆,道:“爹!大哥要是回来——”
东方霸主低声道:“你大哥回来,你母亲是不会发怒的,记得对你大哥说,他母亲为了去找他,已然不知所踪了,明白么?”
东方雷心中暗忖,自己在离开峨嵋之后,做的坏事虽然多,但也没有一件及得上父亲现在要去做的。
自然,东方雷心中是那样想,但是他口中却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道:“我省得了。”
东方霸主身形掠起,穿过了一个院落,走进了一扇月洞门,来到了一个雅致的厅堂之中。
他才一进去,便看到月芬和玉琴两人,一起站了起来,月芬立时道:“我听得庄中忽而喊声连天,忽而鸦雀无声,究竟有什么事?”
东方霸主若无其事,道:“没有什么,倒是有一件事,可以令得你大大高兴。”
月芬喜道:“可是白儿回来了么?”
东方霸主道:“正是,你跟我来,玉琴,你在这里等着,不要乱走。”
玉琴本是极柔顺的少女,东方霸主怎么吩咐,她便怎么做,立时应道:“是,师父。”
东方霸主握住了月芬的手,向外走了出去,月芬喜容满面,道:“白儿肯回来了,他好么?”
东方霸主随口应道:“好得很,只是他脾气仍然十分倔强,你要多劝劝他。”
月芬忙道:“我会劝他的,他肯听我话的。”
两人边说边走,这时正来到院子中的一口井前,东方霸主连考虑都没考虑,手起掌落,一掌便向月芬的头顶拍下。
那一掌击出,月芬的头顶,几乎连任何声音都未曾发出,月芬的身子,便已软了下来,东方霸主顺手一推,便将月芬的身子,推进了井中。
东方霸主的动作何等之快,一刹间,东方霸主将月芬推下了井中,跨出几步,顺手抱起一块假山石,投入井中。
他心知金兰花若是知道他和月芬在一起,必然大大不满,说不定才和好,又会反目,是以非将月芬杀死不可。而他在对月芬下手之际,心中一点内疚也没有,也根本没有一点忧戚之心。
他向四面一看,并不见有人,心忖这件事,除了东方雷之外,别无人知,东方雷自然不会讲出来的。
而所有人中,也只有玉琴和席玲两人,才会问起月芬的下落,席玲是个没有主意的人,容易应付,自己只须向玉琴警告一番,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是以,他又转回院子去,迎面见到玉琴,便沉声道:“玉琴,你月芬师娘有事远行,这件事十分秘密,有人问起你,你只说不知道就可以了。”
玉琴人十分精细、柔顺,听得东方霸主这样吩咐,心中虽然起疑,还是立即道:“是。”
东方霸主又道:“雷儿的母亲来了,那自然是你的师娘,你见了她,要执礼十分恭谨才是,她武功很高,若是能得她欢心,那你就受用不尽了。”
玉琴又应道:“是,我知道了。”
自从到了日月庄之后,玉琴的心中,说不出地烦闷,她眼看东方雷和席玲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她心中日夜思念的林浩生,却不知人在何方。
日月庄中喜事的气氛越是浓,她的心中便越是难过,此际东方雷的母亲又到了日月庄,虽然东方霸主说如果得到她的欢心,受用不尽,但是她自然先喜欢席玲,几时又轮得到自己?自己孤苦伶仃,只有一个人,真可以说得无依无靠。
她心中深叹了一声,跟在东方霸主的身后,向外走了出去。
东方霸主解决了月芬,不让金兰花知道,心中怡然自得。可是,他走了十来步,陡地想起,别人或者不会追问月芬的下落,但是有一个人,如果见了自己,必然会问起月芬来的,那人便是东方白。
东方霸主一想到这一点,不禁皱了皱眉,如果东方白来了,那的确是十分麻烦的事。
但是东方霸主却立时将这件事放下,不再去想它,因为那不是现在的事,而且以东方白的脾气而论,是不是会来见他,也大有问题。
等他又来到金兰花身前时,只见金兰花正笑容满面,可是一见东方霸主和一个年轻女子一起进来,立时面色一沉,道:“这是什么人?”
东方霸主忙道:“这是我新收的女弟子,她叫玉琴,资质还过得去。玉琴,快拜见师娘。”
玉琴忙踏前一步,但是玉琴还未曾拜下去,金兰花却已沉声道:“慢,你不必行礼。”
她抬起头来,望定了东方霸主,道:“你倒风流得很啊!多少人不好收,却收这样一个女弟子。”
东方霸主见金兰花的话,如此不留余地,他也不禁为之大窘,玉琴更是手足无措。
金兰花更是一声冷笑,道:“你有两个儿子,自然会有两个媳妇,已有四个人要你传授武功,却还要收什么弟子,你说。”
东方霸主心中大怒,但此际他却不敢得罪金兰花,反倒陪笑道:“娘子说得是。”
金兰花沉声道:“我既然说得是,那你就将她逐出日月庄去,千万别再提什么弟子、师父。”
东方霸主人虽然极邪,但是武林之中,不管正邪,对于师徒名份,倒是十分尊重的,玉琴并无过犯,又是他自己要收玉琴为徒的,若是忽然之间,要将玉琴逐走,倒也说不过去。
是以他沉吟道:“这个……”
金兰花面容更怒,道:“这个什么?”
东方霸主乃是何等自负的人,金兰花那样叱责他,他心中实已怒到了极点,几乎忍不住要发作了。但是他究竟是十分深沉,觉得在如今那样的情形下,犯不上为了玉琴的事而得罪金兰花。
是以他立时一笑,道:“娘子何必发怒?”
他一面说,一面转过身来,道:“玉琴,你立时离开日月庄,从此再也不准叫我师父,也不准对任何人提起你曾拜我为师,可知道了?”
玉琴刚才还在感叹身世,但是她却还有一点可供安慰之处,就是她总算拜在东方霸主门下,而且她师父是一个武功极高的人。
虽然她拜师以来,什么功夫也未曾学到,但是这些日子来,东方霸主十分繁忙,玉琴也是看到的,她总希望自己会有和林浩生再见的一天,希望到那时,自己的武功已十分高超了。
可是此际,她听得东方霸主竟然那样吩咐自己,她不禁整个人都呆住了。
一时之间,她张大了口,不知说什么才好。
东方霸主既然已决定不和金兰花决裂,在他来说,还有什么道理不道理可讲?他面色一沉,道:“刚才我的话,你可听到了?”
玉琴只觉得心中一阵委曲,几乎立时哭了出来。但是她在天一堡的时候,也是被凃雪红欺负惯了的,早已受惯了委曲,也不敢哭,只应了一声,道:“听到了。”
东方霸主叱道:“那还不快走?”
玉琴忙道:“是,我……走。”
她转过身去,已是泪水盈睫了,她急步几步,出了门,以袖抹着泪。
她实在不知道自己走到什么地方去才好,但是她却只得快快离开了日月庄。
她急急地向外走去,日月庄的人认识她是东方霸主的弟子,也不知她已然被东方霸主逐走,是以都对她十分客气。
玉琴的心中虽然难过,但是她人缘很好,有人向她招呼,她自然一一点头。及至出了庄外,她拔足飞奔,一面已忍不住大哭起来。
开始时,一面哭,一面还在向前奔着,但奔出了里许,她越想越是伤心,泪眼模糊,根本就看不清眼前的物事,身子向前一仆,便伏在草地上,痛哭了起来。
玉琴从来也没有那样哭过,那并不是她不想哭,而是她不敢哭。
以前,当她是凃雪红的丫环之际,她不敢哭,后来,当她成了东方霸主的弟子之后,她也不敢哭,她只是战战兢兢,小小心心地做人,唯恐被人责骂。
然而到了此际,却是再也不必小心伺候别人的脸色了,世上似乎只有她一个人,她不必讨别人欢喜,也不必怕别人呵责,是以她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如决了堤的江河一样,滚滚而出。
她一面哭,一面想着林浩生,林浩生下落不明,不知到何处去了,她也不知道此生此世,是不是还能和林浩生再见面。
当她想到这一点,更是不能自己,哭得更加伤心。不知自己哭了多久,她的泪似乎已流尽了,只是不断地干嘘着。
就在这时候,她才发觉,四周竟是如此寂静,除了自己的抽噎声之外,几乎什么声音都没有,她的双眼,哭得又红又肿,她睁开眼来看时,才发现已然是薄暮时分了。
而她自己,是在一个山坳之中了一群群飞鸟,从山外飞了进来,停在林木上,天已黑了。
玉琴看到飞鸟投林,心中又不禁一阵凄楚,因为天黑了,飞鸟尚且有巢,自己的归宿在何处呢?
玉琴虽然会些武功,但那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是在天一堡的时候,林浩生教她的。
林浩生自己的武功也不高,而且还要避着凃雪红,两人也不能时常见面,玉琴能学到些什么?
但是玉琴此际的凄楚伤感,却还不在于她武功太低,而是因为她性子柔顺,总想有一个依靠,和别的学武之士,心里只喜欢四海飘泊,到处为家,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她更觉得难过。
她勉力站了起来,只觉得双腿发软,几乎站也站不稳,要扶住了一株树,才能立直了身子。
然而她刚一站了起来,又觉得自己就算站直了身子,那又和仆倒在地上,有什么分别呢?她心中一阵剧痛,身子一软,又待向草地倒去。
就在此际,忽听得有人叫道:“玉琴姑娘,玉琴姑娘。”
那一声叫唤,乍传入她的耳中之际,玉琴以为一定是自己哭得太久,不但泪眼模糊,连耳朵也有了毛病,才会听到有人在叫自己,是以她并不理会。
可是,那叫唤却一下一下地继续着,而且,玉琴还听出,叫声就在不远处传了出来的。
玉琴吸了一口气,用哭哑了的声音问道:“是谁?可是有人在叫我么?”
才问了一句,便听到了回答,那声音又道:“是的,我在叫你,玉琴姑娘,你过来帮帮忙,我们来救一个人。”
玉琴的心地十分好,这时候,她自己虽热是烦恼伤心之极,但是一听到救人,她仍是一点犹豫也没有,忙道:“好,你在什么地方?”
一面说,一面循声走了过去。
她才走出了一步,便听得那人道:“玉琴姑娘,我的样子十分古怪,十分可怕……但是我绝不是鬼怪,你见了我,不必害怕。”
玉琴听得对方那样说法,也不禁为之一呆,但是却也听出对方并没有恶意,是以她略停了一停,便又继续向前走去,一直到了一大丛灌木之前,她又听到了那人的声音,道:“你拨开树丛,就可以看到我了。”
玉琴又踏前一步,伸手去拨开身前的枝叶,向前看去。
这时,上弦月已然升起,月色甚是清明,玉琴向前一看,先看到一个双目紧闭的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