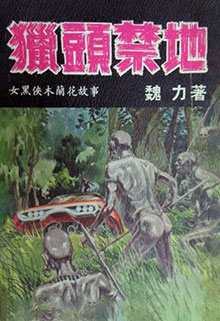苏天民笑着道:“愿闻其详。”
萧魔嘿嘿道:“就是向你爷爷发封信,备道缧绁之苦,望能念及苏家三代单传,祖孙相依为命之亲情,速令九帝,共朝天王!”
苏天民本想调侃老魔一下,说道:“我在这里并未吃苦啊!”
心中一动,主意顿改,仰脸道:“写这样一封信,老总以为在下,是否应该慎重思考一番?”
萧魔应声道:“如此甚好,本座决议将祭典延至后日午时举行!”
语毕,人音顿杳。苏天民倒下身去,继续闭目养神。
他知道萧魔这只是一种恫吓,不过,这也难说得很,安知老魔到时不会来个恼羞成怒?
可是,话虽如此,他刻下身囚密牢中,除了等待,又能怎样?
是的,等待,多等上一个时刻,在时间上,便无异与希望更接近一刻,这是他目前惟一能做的他得信赖剑帝!
而剑帝所安排之来使,也许过了后天午时才能赶到,若果如此,那也只好叹做造化弄人了!
天色,再度露出曙光,又是新的一天,总计他在牢中这也是第五天了。
早餐过去,接着又是中餐送来,日子还像往常一样,假使这样继续没有变化,那么,连明天的一顿中餐在内,他在这世上,将还有三顿牢饭可吃。
苏天民午餐后一觉醒来,园门方面,忽然响起一阵轻微而耳熟的沙沙之声,隐约地由远而近。
唔,很好,晚餐又来了,还剩下两顿………
突然,脚步声于近假山边处遽尔停歇下来,接着,只听一名庄丁,以颇为惊讶的语气问道:“巴师父,您”
跟着巴金贵的苦笑声道:“我怎样?”
那名庄丁期期道:“巴师父您……你……不是已经升了……怎么……现在……又……
又……回复到……原……原先的准武士身份?”
巴全贵叹了口气道:“一言难尽!”
那名庄丁似给引起了很大兴趣,忙问道:“怎么回事?”
巴全贵恨声道:“怪只怪我巴全贵有眼无珠,竟然跟上一名奸细!”
那庄丁诧异道:“那……跟你巴师父有甚关系?”
巴全贵反问道:“怎么没有!”。
那庄丁咦了一咦道:“是……是他……选中你的,不是么?”
巴全贵接口道:“为何未选中别人?”
那庄丁顿了一下,方才问道:“最后总管竟因此降了你一级?”
巴全贵叹了口气道:“那倒不是!”
苏天民正在想,不意姓巴的这厮却遭我连累了,现在听得这一说,不由得为之一愣,心想,怪了,不然他又是怎么回事!
只听巴全贵又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是我自己请求的!”
那庄丁似乎呆了一下道:“巴师父……这……什么意思?”
巴全贵慨然道:“我辈当奴才的,最要紧莫过于忠诚二字;巴某人不学无术,别的不懂什么,只知道为表示寸心起见,除了这样做,再无更好的剖白方式,幸蒙庄主和总管俯伶愚捆,总算成全了巴某人一片苦心。”
那庄丁凛然起敬道:“巴师父真了不起!”
巴全责咳了咳道:“本分而已。”
苏天民差点没给呕了出来,切齿暗骂道:“卑鄙顽劣,莫此为甚,这厮如再落到小爷手上,不一颗颗敲碎他满口狗牙才怪!”
苏天民正愤怒间,忽听那庄丁失声道:“哎唷,不好!”
巴全贵忙问道:“怎样了?”
那庄丁低促地道:“小弟昨夜酒醉,早上起来,灌的冷茶太多,这会儿……他奶奶的………尿好急!”
巴全贵咦了一声道:“这算什么?手上东西放下来,跑到那边去,随便找个地方,哪里不好办事儿?”
那庄丁低语道:“你……你不知道,后庄的那批丫头,多喜欢抄近路,打这园中过,万一碰上之后,回去搬弄一声,说是我裘某人……这……嘿,可万万使不得”
巴全贵似乎在挥着手道:“去,去,快去,我在这儿替你临时看顾一下就是了。”
那庄丁感激涕零,连声道:“谢谢,谢谢!”
一阵促步声起,连奔带飞而去。
苏天民负手踱步,绕壁而行,心头为上面两个俗物搅得烦躁之至,他知道这一顿晚餐,他是无福消受的了。
就在这时候,牢顶圆洞中,嗤嗤嚓嚓一阵轻响,跟着穿花蝴蝶般瓢下一张纸片!
苏天民心念微动,连忙上前一把接住,就着洞中漏下的微弱光线匆匆一看。刹那之间整个人都呆了!
是的,庄中确有己方卧底之人但他绝未想到此人就是“巴全贵”!
苏天民惭愧而激动地弹身向上轻呼道:“巴侠!”
上面,巴全贵突然扬声道:“晦,老裘,你跑快点好不好?小弟身上,也搁着一件紧要事呢!”
那位老裘遥答道:“谢谢巴尼,小弟来了,巴兄请便可也。”
苏天民从语气上猜测,这个姓裘的,如果不也是一名准武士,就必然是威字庄丁中的老大老二之流,否则他是不够资格眼巴全贵称兄道弟的。
接着,没有多大工夫,一叠食盒自圆洞中放了下来,苏天民按巴全贵传示吩咐,静静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
停了停,悬索冉冉上升,只听姓裘的忽然咦了一声道:“怎么难道睡着了不成?”
苏天民轻轻哼卿了两声,表示他并未睡着。
姓裘的喃喃道:“人明明醒着,食盒却原封未动,这是在捣什么鬼?”
接着,凑近洞口向下喊道:“朋友,过了这一顿,直到明天早上,才有第二额可吃的,你仁兄不将空盘换上,是不是这顿不想吃了?”
苏天民一声不响,这次连哼也不哼一下。
那厮口里嚷着,一面又将食盒重新放落,苏天民当然不去理睬。
那厮第二次吊上去一看,食盒仍旧依然故我,还下可慌了,口中不知叽咕了几句什么,“夺”的一声,放回食盒便向前庄奔去。
不到盏茶光景,一片杂沓脚步声匆促入园而来。
接着,萧魔的声音于上面传来道:“老弟是否哪里不舒服?
苏天民呻吟了一声,仿佛想说什么却乏气力一般。
萧魔扬声道:“老弟,怎么啦?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说话?”
苏天民以舌抵齿,含混呻吟道:“老总,有人……想……毒……”
萧魔一啊,忙喝道:“紫老去厨房检查,来,洪师父,我们一起下去瞧瞧!”
苏天民不敢怠慢,迅将那张浸过某种药水的纸片揉成一团,匆匆吞入腹内;说也奇怪,纸团一进喉咙周身果然顿时烘热起来。
轧轧一阵问响,最后一道铁门开启,萧魔和那名姓洪二级武士相继奔入。
洪姓武士打亮了一根火招子,萧魔伸手接下,大步走过来,高举着火把子俯身促声道:
“中毒?舌尖吐出来我看看!”
苏天民呻吟着摇摇头,这次并非做作,他感觉身有如火烤,的确热的难受。
不过,他没有自信舌尖是否也已生出异状,萧魔采取此一步骤,足证其为个中行家,拒绝照办,可强调情况之严重,他绝不能功亏一篑,于紧要关头露出破绽!
萧魔手一伸,左手食、拇两指于喉骨间轻轻一捏,苏天民喉头立即泛起一阵要吐的感觉,暗骂一声老贼,舌尖不由自主地向外吐了出来。
萧魔目光所及,骇的失声道:“啊,舌苔全黑了?洪师父,先拿一颗清血护心丸来,火速派人去请潘家集潘老大夫来一趟!”
洪武士匆匆递出一颗绿色药丸,匆匆转身出牢而去。
苏天民被强迫服下一颗清血护心丸,通身果然舒泰不少。
他人舒适了,心头反而着慌起来:万一潘老大夫请来之后,他的病状已经消失,那可怎生是好!
还好,他感到凉爽的,只是心胸一隅之地,手足四肢,仍然热烘如故。
最使他感到快慰的,便是这时的萧老魔,活似一名问汤奉药的孝子,这里摸摸那里探探,口里一面不住问着:“好一点没有?还难过不难过?”“是不是想吐?”“头部不发晕吧!”
苏天民高兴便点一下头,或者摇一下头,假使感到不耐烦,便来个相应不理。
现在,他知道,萧魔已将他当成一件无价之宝,以为这件无价之宝可换得九帝之俯首听命。
他在心底说道:“是的,老魔,如你应用得当,九帝方面的确会有投鼠忌器之感,不过,抱歉的是,小爷今夜就要离开矣!”
这样,直折腾到将近起更,上面洞口方才有人低报道:“潘老大夫到!”
萧魔精神猛地一振,忙应道:“叫洪师父快带进来!”
不多一会,南道中脚步声起,洪师父掺着一位须眉俱白,背拱如弓,年约八旬上下的老人走入牢室中。
苏天民一颗心不期而然地紧张起来。传书上末段说:“一位潘老大夫,将会助你脱困!”
密书系由巴全贵送达,语气则出自剑帝,他不得不信。现在,这位潘老大夫来了
这位潘老大夫,将如何助他脱困呢?
这一点,苏天民无法想象。好在这位潘老大夫已经到来,用不着多久,谜团便可以打开!
跟在洪姓二级武士,和潘老大夫身后的,是天威院三名劲装准武士。两人提着灯笼,另一个手里端着一张编藤便椅。
萧魔迎上一步,含歉拱手道:“这么晚了,还要麻烦老先生,真是对不起得很!”
潘老大夫表情异常严肃。轻咳着点点头,没说什么。瞧宾主间的应对神情,这位开封名医,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魔庄看病!
跟着,洪武士将潘老大夫扶去椅中坐定。
那名腾出双手的准武士,连忙过来将苏天民轻轻一把抄起,平平托置膝头,半蹲着凑去椅前。
潘老大夫颤巍巍地伸出鸡爪般的右手五指,先行查看了一遍舌苔、眼神、和呼吸;然后开始瞑目把脉。
经过约莫盏茶光景,诊察手续完毕,最后比比手势,令那名准武士掀开衣角,又以手背于周身各处试了一遍热度。
萧魔从旁迫不及待地问道:“是不是中了什么毒?”
潘老大夫捋髯摇头,缓缓答道:“只不过是一时烦躁过度,寒湿外侵,导致郁火攻心而已!”
萧魔一哦,面露喜色道:“这么说,不碍事了?”
潘老大夫点头道:“是的,一帖清凉散,也就尽够?不过,这帖药在调制和灌服方面,尚有几点须得注意,这个留到外面去再说吧!”
萧魔转过脸去道:“洪师父,您”
潘老大夫一摆道:“在服药之前,先让他睡一会儿,不要留人在这里打扰他。”
萧魔奉命唯谨,连忙应是。接着,一行相继退出。机括推动,钢门层层封闭。
石牢内复又冷清清的只剩下苏天民一个。
苏天民待最后一道钢门合上,犹自地面一骨碌挺身坐起,双目发直,眼眶中止不住浮起一片激动的泪光。
那双温暖的手掌,以及那种以手背按穴的独特手法,差不多打七八岁开始,他便对它们熟得不能再熟了。
啊,爷爷,您终于来了!
他抬起衣袖,拭净眼角,勉强收敛心神,调息用功。他知道,爷爷为他赶走洪姓武士,便是暗示他不可错过这珍贵的一刻!
现在,万事俱备只等那名送药者莅驾。
“潘老大夫”离去了,天威院那名叫麦大原的贴身近卫,一手拿着水壶,一手拿着药罐,快步走向庄后石牢。
萧魔则留在天威院一间书房中负手躞蹀,静候那名卫士回报牢中犯人服药后的情形。
这时约当二更左右,初冬之后,弦月斜挂,万里无云,银灰色的月华,静静地笼罩着整座洞仙山庄。
一切都显得那样肃穆而柔和……
那名天威武士麦大原,果真能办事。
只见他入牢不久,便即匆匆走了出来;只不过出牢之后,并未返转天威院,而是一逞奔去庄者警塔。
这位武士一近警塔,塔顶便自传下一声沉喝道:“来者何人,止步通名!”
“麦大原!”
“啊是什么事?”
“密令待发!”
“什么密令?”
“火速征召紫、魏、吴三老,集齐后,嘱往虎啸院,洪、尤两位二级师父叛变有据,庄主吩咐着即当场格杀!”
警塔上一声轻啊,警钟随即敲响起来。
当当当!
当当当!
当当当!
钟声一长两短,正是调集一级武士的紧急信号!
钟声一响,麦大原立即腾身而起,流星一般再度扑向庄后逍遥宫庄主寝处。
天威院书房中,萧魔听得钟声,不禁猛然一呆道:“咦!这……这怎么回事?”
院后众姬妾,纷纷仓惶涌出。
天威院那名卫士队长,五级武士祁杂宜,这时亦自对面厢房中一个箭步窜出。由于出屋匆促,连外衣都没来得及披一件,光着一副脚板,慌慌张张的便向书房这边奔了过来!
萧魔挥手怒喝道:“快去看看是谁下的号令!”
一名侍妾插口道:“不会是庄主吧?”
萧魔扭头怒声答道:“即使令出庄主,也应先行知照一声,不然还要我这个总管干什么?
五级武士队长祁维宜应命飞步而去。
可是,太迟了。这位卫士队长赶抵警塔时,钟声已停,紫。魏吴三名一级武士刚自塔下聚而复散!如等这位卫士队长问清原委,再采制止措施,洪、尤两名二级武士也许早已变成一堆肉酱了!
就在五级武士祁维宜到达警塔时,那位冒牌的麦大原,也已赶抵庄后逍遥宫外。
逍遥宫前两名值夜武士,正为刚才那阵钟声在那里疑惑不已,现见天威院正总管身边一名卫士来到,不禁齐声高问道:“喂,老麦,前面刚才”
麦大原气急败坏地叫道:“前天来的那位扫花叟,不是好东西,他勾结……紫老……
现……现在虎啸院已遭血洗……老贼功高,又有紫老为助,看情形,魏、吴两老亦似不妥,萧总管分身乏术,独木难支,请……请庄主赶快过去,亲手收拾,那……那个扫花老贼,刻不容缓,火急万分!”
两武士大惊失色,抹额便向宫内奔去!
苏天民微微一笑,一个闪身,纵登宫侧松顶,待宫中那位小魔王领着七八名武士奔去庄前,方又提气飘身而下,绕去宫后,打起火种,直至火舌熊熊窜起,方由庄后那条只有少数的高级魔徒清楚的秘径奔向庄外。
苏天民一口气奔出七八里,估计已达安全地带,乃驻足稍事喘息,同时转身向来路望过去。
只见这时魔庄中,烈焰迸腾,如在跟前,依稀仍可听得一阵阵呼叱杀伐之声。
苏天民止不住又是微微一笑。
他知道,值此好梦初回之深夜,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这笔糊涂帐,将不啻一团愈理愈乱的烂麻,等这笔糊涂帐算清了,魔庄的人力和物力,大概报销个三分之一,是不成问题的了!
苏天民正自暗暗得意之际,来路上突有一条人影如飞而至,人在三数丈外,已然传来一声沉喝道:“阁下干得好事!”
苏天民见来人一身道装,不禁深为迷惑,魔庄芸芸武士中,几时有过这么一位道士?
一念未竟,来人已至跟前。
苏天民真气一提,正想来个先下手为强时,来人星冠一除,突然放声哈哈大笑!
苏天民暗道一声惭愧,连忙拱手笑道:“赵大侠好,晚辈一时不察,几乎……咳……几乎……骇坏了,赵大侠怎会忽然跑来此地?”
慧眼仙樵赵中峰大笑化苦笑,最后摇摇头道:“不提也罢,提起来真能愧煞人,老汉奉命接应,不想老弟脚程如此惊人,如非你老弟自动止步,今夜老汉这两条腿,八成是报废定了。”
苏天民赧然一笑道:“赵大侠真会取笑。“
说着,忽然一怔道:“赵大侠适才怎么说?接应?接应晚辈?这是不是出自剑帝高老儿的安排?”
慧眼仙樵点点头道:“此地非说话之所,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于是,老少两人双双折身向西,穿过一片荒林、沿着黄河南岸,取道奔向汜水方面。
天亮之后,两人在一座古庙中歇下来。
慧眼仙樵说道:“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大前天,令祖忽然传回密讯说他已与三十多年前的老友,豫东神医潘郁方取得默契,将冒伊人身份混入魔庄,就在同一天,你老弟落难的消息,也由魔庄辗转递达,于是,剑帝遂一面通知今祖,一面差老汉前来开封,与魔庄那位卧底者觅取联络,事后便在魔庄附近相机接应……”
苏天民插口道:“魔庄中那位巴全贵,究竟是何来路?”
慧眼仙樵微微一笑道:“提起此君,来头可大了。”
苏天民一呆道:“怎么说?”
慧眼仙樵道:“此君本姓高,表字隐雷,实即剑帝高老儿之亲胞弟!”
苏天民失声道:“有这等事?”
慧眼仙樵笑道:“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苏天民道:“小魔王徐永都原为高府书童,他对这位小主人难道一点印象也没有?再说,这位高隐雷如为剑帝之胞弟,照道理,身手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怎么他在魔庄,连个七级武士也混不上呢?”
慧眼仙樵笑笑道:“事隔多年,再加上刻意掩饰,你以为小魔王会是神仙不成?同时,一名准武士不大不小,正好办事,职位太高了,又有什么用?”
苏天民怔了怔道:“那么,您是说,他……这位高府二少……他这种庸庸俗俗的外相,全是做作出来的了?”
慧眼仙樵道:“那还用说。据老汉估计,这位老弟如凭真才实学,混个四级武士当当应该没有问题!”
苏天民摇头苦笑道:“好小子,居然连我苏天民也给瞒了个结结实实!前些日子,他起手一招,便将一名最强的七级武士击败,我都还以为是我私下指点之功,不意小子竟是真人不露相,原来本身就具有这份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