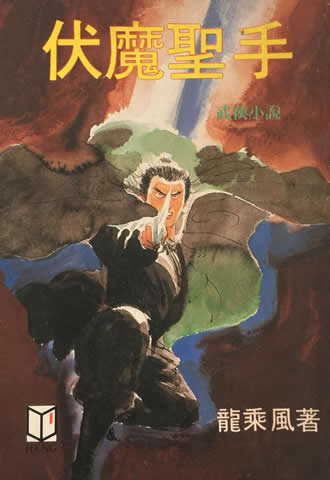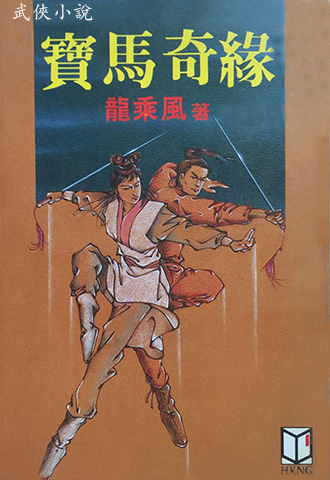萧凌朦胧中醒来,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侧目一望窗外,东方才微微显出一点鱼肚白色,映得窗纸也泛起一片鱼青。
四周静得很,她觉得自己出了一身大汗,人仿佛好了许多,就连日前自己眼皮上那种沉重的负担,也像是消失了。
她觉得有些口渴,这时当然不会有人侍候她,她只得试着挣扎,看是否能爬起来,这些天她的这种企图也不知试了多少次了,但总觉得全身一丝气力也没有,总是爬不起来。
哪知她此刻身子像是轻了不少,稍一挣扎,居然爬起来了,她说不出有多么高兴,也顾不得冷,从被中钻了出来,看到床头有件袍子,她就拿来穿了,套上鞋,她竟然走下了床。
借着微光,她看到茶水放在靠门的小几上,于是就扶着墙,慢慢走过去,在万籁无声中,她突然听到有人在说:“……玉剑萧凌……古公子……残金毒掌……”有些话她虽然听不清楚,但这几个名字,却令她入耳惊心。
这几天来无时不在她心中纠结的一个问题,又倏然袭向她的心:“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难道……难道这地方又和古浊飘有着什么关系吗?”她暗忖着。
于是,那甚至在她晕迷的时候,仍在她芳心中萦绕的古浊飘的影子,那可爱、又可恨,令她沉醉、又令她痛苦的影子,就随着日光投向她心上,也正像日光那样的不可抗拒。
她需要将自己心中纠结的问题打开来,突然间,她像是又增加了几分力气,走到了门口,悄然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她的屋子外是间小厅,小厅的那边就是程垓所睡的房子。
萧凌一脚跨进小厅,却恰好有—人从另一扇门中走了进来,她一抬头,晨光虽微熹,但就只一眼,她已认出这人是谁来。
这人就是古浊飘,就是那被她恨过千百次,她爱过千百次的人,即使此处没有一丝光线,她只要看到他一丝影子,就能认出他,即使影子都没有,她也能感觉出他。
刹那间,她心中情潮翻涌,不能自禁,久病小愈的身体,此刻又像是突然虚脱了,再也支持不住,眼前一黑,跌在地上。
古浊飘一跨进小厅,当然也看到萧凌,在这同一刹那里,他心中是不是也在翻涌着和玉剑萧凌共有的同样情感呢?他嘴角的讥诮和面上的冷笑,在见到萧凌后就消失了,变成另一种表情,却是任何人也解释不出的,像是自责,像是怜惜,像是不安,像是无情,却又像是有情,但无论如何,这坚冷如石的古浊飘,总是动了情。
萧凌倒在地上,宽大的袍子散在地上,秀长的头发,半落在她那已被病魔折磨得苍白瘦削的脸上,鞋子也落去一只,露出她那洁白如玉小巧玲珑的脚,使她看起来有种难言的美。
古浊飘迟疑一下,这秀发、这玉面、这小巧玲珑的脚,这宽大袍子里小巧玲珑的胴体,都是他所熟悉的。
他微微叹息了一声,脸上露出的怜悯之色,在此刻里,掩住了他其他的各种情感。
于是他走过去,温柔地为她拂开乱发,温柔地抱起她那娇小的身躯,缓缓走进房去,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到床上。
他不知道该留在这里,抑或是离去,但他却知道,无论他留在这里抑或是离去,对他都是种痛苦。
他不知自己是否了解自己,但这世界若还有一人了解他,那么这人除了他自己之外,再无别人,因为若有人自己也不能十分清楚了解自己的时候,那么这世人还有谁能了解他呢?对于玉剑萧凌所给他的这分纯真无邪,却深入腑肺的情感,他也不知究竟该怎么好,那么,为什么他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事呢?于是他不禁自怜地叹息一声。
就在他这声悠长的叹息,消失在清晨冷而潮湿的空气里后,萧凌的眼睛蓦的张了开来,瘦了的她,眼睛更大了。
两人目光相触,古浊飘微笑了一下,俯下身去,轻声问道:“你好些了吗?”
这温柔的问候,像是一柄利剑,直刺入萧凌的心里。她想起在雪地上和古浊飘的初遇,暖室中的浅酌,卧房里的温情,这一连串温馨而美丽的回忆,已牢牢地编织在她的心里。
但她也不能忘记自己被摒于门外时的凄凉、失望、深入骨髓的痛苦,甚至这险些使她形销骨立的病,都不也是为着他吗?于是这一分爱和这一分恨,这两种绝对不同,可却有时又奇妙地发生着关连的情感,便在她心里激烈的争战着,是爱呢?是恨呢?纠缠难解,连她自己也无法分解得开。
她想回过头来不去理他,但古浊飘的眼睛里,却生像是有着一种强大无比的力量,在吸引着她,使她的头再也转不过去。
古浊飘微喟一声,道:“你怎么不理我?”
伸手想去抚摸她的柔发,但却又中途停住,带着几许叹息之意地微笑了一下:“你病好了,我高兴得很。”
这两句话,像一只无形的温情之手,轻轻抚摸着她那已被情感折磨得千疮百孔的心。
嘤咛一声,她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那一分刻骨铭心的深情,投向古浊飘的怀里,让古浊飘那双手抱着自己,抱着自己整个身躯,也抱着自己整个的心,她已经整个投向他了。
良久,他们沉醉于似水柔情里,浑然忘了世间其他的一切。
带着娇喘,萧凌问道:“那天你为什么不等我,害得我——我知道,你有许多许多事骗我,我本来在那破房子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古浊飘的目光,缓缓从萧凌脸上移开,远远投向墙角,沉声道:“凌妹,我有我的苦衷,终有一天你会谅解我的,现在我向你解释也无用,唉——”
他叹息一声,收回目光,又道:“以前的事,让它过去不好吗?现在我已在你身旁,你也用不着去想以前的事了。”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他脸上有一种焕然的光彩,使得萧凌不可抗拒地接受了他的话。有些人与生俱来就带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使别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他,古浊飘就属于其中之一。
就在古浊飘和萧凌互相沉醉着,而忘却了外面的人世的时候——门外突然有人轻轻咳嗽一声,虽然只是一声轻轻的咳嗽,却已足够使他们由沉醉中惊醒,从拥抱中分开。
天灵星大跨步进来,哈哈笑道:“老夫无礼,老夫无礼——”笑声突然一顿道:“但萧大侠的伤势严重得很,老夫对医道却一窍不通,古公子是否先请个大夫来,先看看萧大侠的伤势,迟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古浊飘站了起来,不知道是因为尴尬,还是为了别的原因,脸上又闪过一丝奇异的神色,拂了拂衣服,沉声说道:“我这就去。”转身走了出去。
萧凌听了孙清羽的话,心头猛然一跳,急切地问道:“萧大侠是谁?”
她已隐隐觉察到了有不幸的意味存在。
天灵星却已转过头去,踱到窗前,将窗子支开一线,向外望去,见那古浊飘已沿着侧轩前的小径向内走去。
“你告诉我,萧大侠是谁好吗?”萧凌又焦急地问道。
上半个身子已支出床外,想是因为气力不支,全身微微颤抖着。
天灵星孙清羽嘴角突然泛起一个奇异的微笑,走到床前,道:“萧姑娘,你要知道萧大侠是谁,随老夫去看看就知道了。”
萧凌冰雪聪明,刚发现他笑容的古怪,哪知孙清羽突然右手疾伸,向她头顶之中的“昆仑顶”上之“百会穴”点来。
萧凌久病之下,体弱不支,但她自幼训练而得的武功,却再也不会忘去,一见天灵星手指点来,惊诧之下,喝道:“你这是干什么!”
她本想往后闪避,但却扑的向前倒下。孙清羽手势一转,倏然划下,在她项上大椎下数的第六骨节内的“灵台穴”轻点了一下,左手托住她的肩头,道:“萧姑娘,莫怪老夫放肆,日后你就会知道老夫的苦心了。”
这“灵台穴”直通心脑,为人身大穴之一,萧凌只觉全身麻痹,脑中也是混沌一片,孙清羽的话她约莫听到,但身子突凌空而起,想是已被这天灵星托了起来,向外走去。
一出门外,孙清羽轻轻咳嗽一声,对面的门中,立刻掠出数人来,除了林佩奇、程垓、孙琪外,竟多了一个“入云神龙”聂方标——原来正在孙清羽等听说萧凌病重,觉得此刻不便去打扰,而再去探看飞英神剑病势的时间,房间的后窗突然有人在外轻轻弹了一下,房中各人都是老江湖,林佩奇翻然一掌,熄灭油灯,嗖的,掠到窗前,向外低喝道:“什么人?”
“是我,聂方标。”
林佩奇松了口气,方支开窗子,窗外已翩然掠进一个人来。孙琪打开火折子,点亮了灯,见到进来的这人,身躯瘦长,却穿着家丁奴才一类的青衣呢帽,但脸上清癯坚毅,目光炯然,却是武林中新进高手“入云神龙”聂方标。
聂方标这一出现,众人才想到在残金毒掌突然出现的那天,这聂方标本是和龙舌剑林佩奇同居于一室之内的,但自那天后,即未再见,大家因为心中忧患重重,也没有想到他。
但此刻各人心中都奇怪:“这聂方标这几日去了何处?为什么作这种打扮?此时此刻,却又怎的突然出现了?”
入云神龙聂方标目光一扫,看到各人脸上的疑色,将手一摆,沉声道:“小侄这两天来颇有所获,此时却不便解释,但是小侄可先简略地告诉各位,那古公子就是残金毒掌的化身,而且方才孙老前辈在房中之言,他已在窗外听得一清二楚——”
他稍一喘气,屋中各人都面色大变,却听聂方标又道:“幸好他此刻被那玉剑萧凌缠住,依小侄之见,此人深藏不露,阴鸷已极,武功却又极高,此刻既然知道了我们已猜出他的底细,可能会对我等不利,我等还是早早离开这是非地,再作打算。”
他一口气说完,目光却一直盯住房门,像是生怕那位“古公子”会突然走进来似的。
孙清羽止住了大家都想问话的企图,瞑目沉思了半晌,突然道:“你们在此稍候,老夫再出去一下,等会儿老夫咳嗽一声,你们就赶紧出来。琪儿抱着萧大侠,其余的人都将兵刃备好,以防生变。”
天灵星以机智名闻江湖,这调度是有用意的,他果然骗走了古浊飘,又将萧凌捧出,几人极快地掠出侧轩,入云神龙却一马当先,轻声道:“各位跟着小侄出去。”
沿着轩后三转两转,竟然走到一个连程垓都不知道的小门,乘着破晓之际,园中无人,走出了相府,四顾一下,连这条小小的弄堂也渺无人踪。
沿着墙角急走,走在最前面的人云神龙回头问道:“孙老前辈的意思,往哪里去最好?”
孙清羽目光一转,见到正路上已有行人,便道:“我们先雇辆车——”
突然转身向林佩奇问道:“铁指金丸韦守儒的舍处你可知道?”
龙舌剑略一点首,当先带路,出了弄堂向左转去。这时相府后院的那小门中,探出一个头来,眨着两只灵活的大眼睛,正是古浊飘的贴身书僮——棋儿。
铁指金丸韦守儒乃北京城平安镖局的镖主,这平安镖局名声虽无“镇远”响亮,但在河朔道上,也是颇为吃得开的镖局。
但自从残金毒掌重现,镇远镖局封门,铁指金丸便也收了业,但此刻平安镖局的两扇黑漆大门却是开着的,门口也停着两辆马车,原来天灵星孙清羽等已经到了。
安顿下来之后,疑团最重的是韦守儒,这几天来发生的变化,他自然一概不知,尤其令他奇怪的,当然也是这位潇湘堡主怎的会到北京城,又怎的会受了这么重的伤。
别的人的心中也有疑问,就是这入云神龙这几天来的行踪。
于是聂方标便说出一番惊人的话来:“那天晚上我肠胃有了些毛病,上茅房时,耽误了很久,那时回到房中,林大叔竟不在了,我心里奇怪,哪知跑到孙老前辈的房中一看,孙老前辈和程大叔、黄大叔也全不在了。”
“我就知道这一定生出了变故,再听到院子里的声音,越发知道情形不妙,但这个时候外面像是人很多,我又不知道详情,就只有留在房子里先等一下,看看情形再作打算。”
龙舌剑林佩奇暗中点头,忖道:“这聂方标年纪轻轻竟比我还沉得住气,姑不论他的武功怎样,就凭这分沉稳,已无怪他能成名立万了。”
却听聂方标又道:“但是我一看两间房子都没有人,我怕你们出了事,一想之下,觉得也不能留在这两间房里,因为万一有人来查的时候,又不便,于是我就想从那间侧轩后面绕出去。哪知我刚走到后面,突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声响,在这种时候,我可不能不注意,就往旁边一闪,哪知那里也有个门,我心里奇怪,突然从后面的气窗中看到有条金色的人影掠进来。”
他略为喘了口气,又道:“我大惊之下,慌不择路地退到那间房里,看到那间房很小,房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大柜子,我迟疑一下,想先避在这大柜子里,哪知这时候外面又有响动,我来不及再转念头,只能先躲到床底下去,却不知这么一来,反而救了我。我伏在床底下,连大气都不敢出,看到有个人进来,我看不到他的上面,只看见两条穿着金色裤子的腿,我几乎吓得闭过气去,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进来的这人就是残金毒掌。”
他透了口气,听着的人也跟着透了口气,却听他又接着道:“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极点,一方面奇怪这残金毒掌怎会跑到这里来,一方面却在担心,假如这残金毒掌发现我在床下面,那岂不是糟了?是以我越发地不敢喘出气来。
“房子里窸窸响动着,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忽然,这残金毒掌竟把身上穿着的金裤子脱了,露出里面的灰色裤子来,又换了双薄底粉履,这时我真恨不得伸出头去,看看这位武林大魔头残金毒掌的真面目。”
大家凝神静听着,铁指金丸韦守儒尤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入云神龙聂方标又道:“哪知这时候外面突然又进得一人来,看他的脚,却是小孩子的样子,我听这小孩说:‘公子,车子都准备好了,就停在外面。’
“那时候我就希望这残金毒掌说话,因为这时候我已经从这小孩子叫的“公子”两字上,猜出这残金毒掌到底是谁来,只是还不能够十分确定罢了。”
铁指金丸实在忍不住道:“是谁?”
聂方标微微一笑,并不回答他的话,兀自说道:“过了一会儿,他果然说话了,他说:‘棋儿,你也跟着我去吧,假如那里还有人,那最好,不然我们就随便去拖个人来。’那小孩却说:‘公子,你何必一定要把大姑娘留在这里呢?’他却叹了口气,再没有说话。
“等一会儿,这两人都走了出去,可是我已经从两句话的口音里,听出这残金毒掌竟然就是那位古公子古浊飘。”
铁指金丸韦守儒惊“呀”了一声方过,又有一声极轻微的“嗯”声,聂方标眼角一动,发现这“嗯”声是从卧着的玉剑萧凌那边发出来的,忙一掠而前。
原来他们是在韦守儒的后房中谈着话,萧旭、萧凌父女就分躺在这间房里的两张床上,此刻聂方标略一检视萧凌,回头道:“孙老前辈,这位萧姑娘的穴道,还没有解开吗?”
天灵星孙清羽微笑一下,道:“我倒忘了。”走过去轻轻两掌解开了萧凌的穴道,哪知萧凌仍然动也不动,竟又晕过去了。
原来她穴道虽然被点,可是别人说的话,她仍听得见。
她听到聂方标说那残金毒掌竟是古浊飘的化身,脑中轰然一响,便又晕过去了。
入云神龙证实了古浊飘确实就是残金毒掌的化身时,非但事先丝毫不知道真相的韦守儒惊异,别人也是吃惊的。
林佩奇摇了摇头,像是想不通这位古公子为什么要这样诡谲,八步赶蝉程垓却问道:“那么聂老弟之后又怎么呢?”
聂方标看了躺在床上晕迷着的萧凌一眼,回头道:“我等到他们两人一走,就赶快出来,这时候天色已经亮了,你们还没有回来,我当然不知道你们到哪里去了,再三考虑之下,就从后面越墙而出,但是心里仍放心不下,又怕你们都遭了残金毒掌的毒手,但是我自问也不是那残金毒掌古浊飘的敌手。”他竟将“残金毒掌”这名字,加到古浊飘头上了。
稍微一顿,他又道:“这时候我就想,多联集几个人的力量,来对付这古浊飘,于是我急忙出城,但究竟要找谁,这时我心里并没有谱,除了家师不说,别的人不是武功不够,就是离得太远。我想来想去,只有雾灵山上玄通观的玄通道人,他虽然久已不出江湖,但却是这河朔地面上武功最高的一人,而且家师与他也有渊源,我若去找他,告诉他这些事情,也许他会出手也未可知。”
天灵星孙清羽却“哼”了一声,手捋长须,冷冷说道:“那个牛鼻子的武功也和我老头子差不多,把他找了来,也未必有用。”语调颇为不悦。
聂方标暗中一笑,知道自己方才那句“河朔地面上武功最高的人”已将这位也在河朔地面上的天灵星惹得不高兴了,暗忖:“这孙老前辈年龄这么大了,好胜之心还如此盛。”
心中虽如此想,口中却赔着笑道:“但那时小侄也没有别的法子,哪知到了雾灵山一看,那位玄通道长却偏偏不在,于是小侄只得又赶回北京城来,冒着奇险,又潜回相府,想搜集一些证据,使得这古浊飘以后无法抵赖。”
“哪知我刚剥了他们一个家丁的衣服穿在身上,沿至侧轩,就看到那古浊飘竟悄悄站在窗口听着你们说话,于是我就绕到后面,一边看他的动静,一边也听听你们在说什么。”
孙清羽哈哈大笑一声,接口道:“我们房子里的这些‘老江湖’,以后可再也别充字号了,有两个人站在外面,我们竟像死人一样!”他又大笑一声:“聂老弟,看来你这‘入云神龙’,倒真的名副其实呢!”
聂方标微笑一下,却不禁露出得意之色,接着往下说道:“后来那古浊飘竟走了进去,我伏在后面向里看,看到他——他跑到萧姑娘的房里去了,我就赶紧去通知你们。”
龙舌剑林佩奇长叹了一声,也暗暗惭愧,自己这“老江湖”竟都比不上一个出道江湖未曾多久的小伙子。
八步赶蝉程垓心中却突然一动,沉吟着向聂方标问道:“聂老弟,闻得江湖传言,你是武当派掌门人黄羽真人的关门弟子,可是确言?”
聂方标点了点头,程垓却又道:“那么你可知道贵派的灵机道长近年来,可曾收过弟子?”
聂方标微一沉吟,道:“灵机祖师叔,早已封关避世,小侄也只见过他老人家数面,还是他老人家特别开恩,他老人家已届百岁高龄,近三十年来,根本未曾下过山,若说近年来收弟子,恐怕不可能吧?”
程垓心中暗骂一声,起先他险些被那棋儿骗了,认为古浊飘真是少林玄空、武当灵机、钟先生、七手神剑这些高人的门徒。哪知聂方标沉思半晌,突然又说道:“不过他老人家近年来却授过一个人几天武功,那是因为——”他话还未说完,程垓心中又是一凛,急切地问道:“那是为什么?他老人家授了什么人的武功?”
聂方标觉得有些奇怪,这八步赶蝉此刻怎的问起这些不相干的事来了?但人家既然已经问出了,自己也不能不说,遂道:“这原因小侄并不清楚,只是听家师说过,少林嵩山的神僧玄空上人发现了一个资质绝佳的人,就到灵机祖师叔他老人家这里来,请他老人家造就这人,说是因为这人不是空门中人,是以才送到他老人家这里来,但不知为了什么,他老人家传了这人几天武功之后,又将他送走了。”
程垓又抢着问道:“送至何处?”
入云神龙摇了摇头,道:“这事已经隔了许多年,那位据说是资质绝高的人,我根本没有见过,我也不知道祖师叔他老人家为什么不收留他,也不将他留在武当山。至于后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知道,但是祖师叔他老人家确实是传过他几天武功的,而且据家师说,这人的资质,确实很高。”
程垓长叹一声,道:“这就对了——”于是他就将那废屋中棋儿所说的话,说了出来,又道:“如此看来,这古浊飘可能就是聂老弟所说之人,足以——”
聂方标却连连摇头,接口道:“不对,不对,小侄虽未见过那人,却知道那人是个孤儿,甚至连父姓都不知道,怎会是这位相国公子古浊飘呢?”
此言一出,程垓又堕入五里雾中,只觉得这件事就像是在大雾里,刚依稀看了一点影子,但扑上去时,又扑了个空。
大家虽已知道古浊飘确实装过残金毒掌,但他这残金毒掌伤人时,却并没有留下金色掌印,那么真的残金毒掌是否另有其人?而古浊飘为何要装出残金毒掌的样子?他和真的残金毒掌到底有何关系?这些问题仍然令人不解,天灵星孙清羽虽然以“机智”名满江湖,但此刻,也只有皱着两道灰白长眉,说不出话来。
静了半晌,孙清羽长叹一声,道:“这些日子来,有些事令老夫的确是参详不透,而且这残金毒掌,一真一假,真假难辨,以后到底要做出什么事来,我相信芸芸天下,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其中的真相吧?”
萧凌被孙清羽拍开穴道后,晕晕迷迷的,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甚至连自己是不是自己都有些模糊了。
混混沌沌中,仿佛有一个极小、极淡的影子,向自己冉冉飞来,但那影子瞬即扩大,瞬即清晰,带着一脸似笑非笑的神情,向自己默默注视着,却又是那恨也不是,爱也不是的古浊飘。
“他是会武功的。”她对自己喃喃说着:“原来那雪地上的跌倒是骗我的,在房中他是故意点中我的穴道来欺负我,唉——我那时为什么不一指点在他的‘锁喉穴’上!”
晶莹的泪珠,悄然滑在她的面颊上,使得她的脸有一丝痒痒的感觉,但是她连伸手去搔一搔的力气都没有了。
突然,她觉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对自己说着话,于是她努力睁开眼睛来,看到那天灵星孙清羽正对着自己说道:“萧姑娘,现在你该知道老夫的意思了吧?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令尊大人此刻就卧在你旁边的床上。”
萧凌的瞳仁突然扩散了,一瞬间,她似乎不能完全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
然后她被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支持着,从床上跳了起来,目光无助地四下转动了一下,身躯向另一张床上扑去。
飞英神剑痛苦地呻吟一下,他被残金毒掌一掌击中后背,幸好他本是前掠之势,是以并未致命,但若不是有他这种数十年性命交修的深湛内功在支撑着,此刻怕不早就不成了。
孙清羽劝着萧凌,韦守儒拿了些内服的伤药,但这种普通的伤药,怎治得了被内家掌力击伤的伤势?萧凌忍着泪说道:“家父的伤势那么重,需要静养,我……我也不想留在这里了。”
她转向孙清羽道:“你老人家能不能帮我个忙,替我雇辆车子?我想,我们今天就回江南,反正,我们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
名重武林的潇湘堡,上下两代竟落到这种田地,令得天下武林闻之,都不禁为之扼腕。
孙清羽长叹一声,道:“姑娘的病势未愈,令尊的伤势更重,还是先在这里将息两日吧。”
“还是回去的好。”萧凌摇着头说,声音虽然微弱,但语气却是坚决的,好像是她在北京多留一刻,便多增一分痛苦。
“我永远不要再见他,若是我有这分能力,我要将他一剑刺死,然后——然后我再陪着一齐死去。”她悲哀地暗忖着,因为她不能忘去他,是恨也好,是爱也好,这爱与恨,都是刻骨铭心的。
突然,一人匆匆自外行来,众人闪目望去,却是韦守儒以前镖局中的镖伙,此时家中的仆人手中拿着一物,向韦守儒道:“门外有个人将这个交给小的,小的问他是哪里来的,他说是古公子派来的,就匆忙地走了。”
孙清羽一皱眉,取过一看,却正是潇湘堡成名武林的兵刃——玉剑,于是他双手捧向萧凌,这老人对萧凌的尊敬,倒不是为着别的,而是对这美貌的少女觉得怜悯而同情。
入云神龙聂方标的目光,一直望着萧凌,此刻突然道:“萧姑娘要回江南,小可愿效犬马之劳,陪萧姑娘和萧大侠回去。”
孙清羽微微点头,道:“这样也好,有了聂老弟的照料,老夫才放心让这一伤一病两个人上路,唉——此后恐怕还有麻烦潇湘堡主的地方,唉——芸芸武林中,怎的就没有一人是那残金毒掌的敌手!”
他一连长叹了两声,心情像是沉重已极,龙舌剑突然接口道:“但愿那位古公子不是和残金毒掌一路,凭他的那身功夫,恐怕还能和残金毒掌一斗。”
聂方标却冷哼了一声,目光瞟向萧凌,冷冷道:“就算他不是那残金毒掌,就算他也不是残金毒掌的弟子,而是为着别的原因伪装残金毒掌的,可是他手段之狠辣,心肠之恶毒,恐怕不在残金毒掌之下呢。”
林佩奇望了他一眼,又复默然。
萧凌此刻仍怔怔地捧着那柄孙清羽递给她的玉剑,心中柔肠百结,对别人讲的话,根本不闻不问。韦守儒却皱着眉道:“那古公子怎么知道你们来到我这里的,他会不会——”
孙清羽微喟一声,接口道:“这位古公子真可称得上是神通广大,老夫一生号称‘天灵星’,但比之他来,仿佛还差着一筹,唉,但愿苍天有眼,不要再为武林造个煞星,他若也像那孤独飘一样——”
说到这里,他语声突然凝结住了,喃喃自语着:“孤独飘,古浊飘。”猛地一拍大腿,忽然又站起来,低头绕了两个圈子,然后突然长叹一声,像是支持不住似的倒在椅子上。
“孤独飘,古浊飘。”林佩奇跟着念道,双眉也皱到一处,道:“难道这古公子真和残金毒掌有着渊源吗?他若是假的残金毒掌,那么真的残金毒掌又在哪里呢?”
下午,入云神龙聂方标兴匆匆地雇了辆车,送着大病方愈和重伤的萧旭父女走了。他似乎对这趟差使极其高兴,因为自从第一眼看到玉剑萧凌的时候,他就对这美丽的少女起了一种难以自制的情感,“一见钟情”往往是最为强烈,也最为不可解释的情感,因为那是真正发自内心,而绝无做作的。
只是,这多情的少年侠士的用情,却迟了一步。
孙清羽眼望着他们的车马消失在北国的沙尘里,这马车外表上看去和任何别的马车都一样,但是车中坐的,却是名满天下的人物——无论是飞英神剑或是终南郁达夫,这两个名字的任何其一,便足以名倾天下。
萧门中人,来了,又走了,这本是他们唯一希望——用以对抗残金毒掌的,然而这希望却破灭得如此突兀、如此狼狈,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事,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
到目前为止,他们再无一条可行的办法用以对抗残金毒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残金毒掌在哪里,他们完全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等待着残金毒掌的再次出现——而且即使他再次出现了,他们也辨不出真伪,只有从另一个被残金毒掌击毙的尸身上有无金色掌印,他们才能推断出一些,然而这岂不是太过悲哀了吗?
×
×
×
古浊飘静静坐在侧轩中那间房里的床上,床似乎仍有萧凌留下的温馨,他目光投向窗户,窗户是支开着,窗外月色将瞑,那种昏暗的黑线,却正和古浊飘的目光混为一色。
他在沉思着,削薄的嘴唇紧闭,于是他脸上便平添了几分冷削之意。然而,他所沉思着的是什么呢?
突然,他站了起来,嘴角泛起笑意,只是这种笑意是落寞的,因为天下虽大,并没有一个人了解他,然而,他自己能了解自己吗?
他自己,真的就是他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