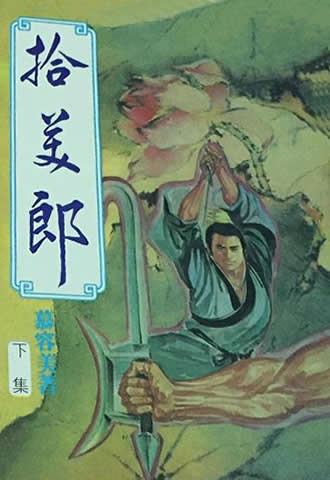天色傍晚,独孤樵到得一座小镇。即将入镇时,他随手抓了些炭灰抹在脸上,顿叩变得
象个士里土气的乡下人,心里这才踏实了些。
因为他真正的面孔太容易为自己甚至别人惹来麻烦。
他在镇子最东面寻了家颇为冷清的小客栈,这类小客栈的底楼一般都是小酒店,不象大
客栈那样除了酒店还有赌场。没有赌场就容易避开那些负刀佩剑的人——这类人最爱惹事生
非,并且个个都对他独孤樵过意不去,究竟因何如此,独孤樵实在弄它不清。只暗叹命运乖
蹇而已。
整个酒店内此时只有一个人在低头独饮,那是一个形状威猛的虬髯大汉。
掌柜的则在柜台内打盹儿。
独孤樵携带的银子虽不算少,但他明白怀里的这些银子并非他一人所有,而是七个人的。
虽然湖乐村柴家惨遭灭门,他也不能乱花自己兄弟三人披星戴月所攒起来的这些血汗钱。
因而他对掌柜的道:“酒肉是不要的,只胡乱吃些饭食,再给间下房住一宿,须得多少
银子?”
掌柜的抬起头来,只随便看了独孤樵一眼,旋即又合上眼皮,爱理不理地道:“你说什
么?”
独孤樵只得又将方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这回掌柜的竟连一个字儿也没说,只伸出一根指头。
独孤樵见状道:“一钱银子,那倒不算很贵。”正欲伸手入怀,却听掌柜的“哼”了一
声道:“一两。”
独孤樵的手立即便僵住了。
他这一路东来,除餐风露宿外,所住客栈最贵的也只收过他的四钱银子。
忽听那独自闷饮的虬髯大汉道:“一人独闷,甚是没趣,那位小兄弟若有雅性,何不过
来与在下畅饮一杯?”
言罢更不抬头,微一挥手,一锭足有十两的纹银恰若有线悬着一般,慢腾腾地飘向柜台。
掌柜的怎知这是极为上乖的内功手法,见银锭“飘”向自己,先是一愣,随即一张老脸
顿时乐得似风干的橘皮,立起身来伸手一抄,冲那虬髯大汉道:“多谢!多……”
第二个“谢”字尚未开口,早“啊哟”一声叫将出来。那到手的银锭,也“呼”的一声
落到柜台上。
独孤樵和掌柜的便是大惑不解:柜台上那锭银子并无丝毫异状,何以掌柜的会惊叫出声;
而掌柜的更不明白,那虬髯大汉的银子怎的如此烫法。
掌柜的看看烫得通红的手心,又看看那虬髯太汉,怔怔的难以出声。那虬髯大汉则若无
其事地连干了三大碗酒,自顾道:“俗话说狗眼看人低,此言当真不假,唉!”
掌柜的方才转过神来,连忙陪笑道:“是是是……是小的没长眼。”转向独孤樵,又道:
“乡下小子,今日算你福星高照,遇上了胡大爷,酒肉自不必说,上等客房也有得你住的
了。”
他虽一直陪着笑脸,却是殊无喜意,更不敢伸手去摸柜台上的那锭银子。
没料独孤樵转身便走。
掌柜的连“喂”了数声,独孤樵才在门槛边站住,转头道:“我可不是孙二狗!”
掌柜的惑然道:“孙二狗?什么孙二狗?”
未等独孤樵答话,那虬髯大汉忽然笑道:“并非所有穷人皆是嗟来之食之辈,现在掌柜
的可明白贵店因何生意冷清了么?哈哈!”
他的笑声直震得独孤樵和掌柜二人双耳发疼。
半晌,掌拒的才结结巴巴地造;“胡……胡大爷你……你说什么?”
虬髯大汉道:“那位小兄弟既无意与在下共饮,何不依我之见,二钱银子成交。既无酒
肉,食宿一宿,贵店大约也只当得起这个价吧?”
掌柜的连忙道:“正是,正是!胡大爷所说的话,无一不是金玉良言。”
那大汉只“嗯”了一声,不再多言。
独孤樵也觉得二钱银子很公道,便随小二上楼,开了间虽不雅致却颇宽敞的客房,落脚
未久,掌柜的亲率数名小二捧了酒肉上来。
独孤樵连忙道:“方才在下宜已言明,酒肉是不要的。”
掌柜的忙道:“是小号奉请这桌酒席给少爷食用的,怠慢之处,还请少爷多多担待。”
亲为独孤樵斟了杯涵,续道:“不知少爷尊姓大名,与楼下那位胡大爷是如何称呼?”
独孤樵道:“在下姓乔……这个名石头,少爷二字嘛,是说不上的,至于楼下那位仁兄,
在下也是初次会面。”
掌柜的大奇,问道:“少……阁下真的是初次与胡大爷会面么?”
独孤樵也自奇道:“是啊?莫非掌柜的觉得有何不妥之处么?”
掌柜的吱唔道:“不不不,只是……胡大爷在敝小号呆了三天,似是在等人。他等的既
不是阁下,怎的会花……这个……嗯……五两银子请……嘿嘿。”
其实那锭银子足有十两。
方才独孤孤樵上楼之后,掌柜的又小心翼翼地去摸它。
发现已无古怪,且货真价实,禁不住又看了那虬髯大汉一眼,那大汉却头也不抬地道:
“十足纯银,童叟无欺,就算是本人请方才那位小兄弟喝杯薄酒,哈哈。”
掌柜的闻言大喜过望,纵是他再蠢十倍,至此时也知“胡大爷”是身怀绝技之辈了。他
既未为难此客栈,已是十分难得。更以十两银子请人吃喝一顿,那么那“乡下少年”只怕来
头更大,纵是王孙公子装疯卖傻出门找寻乐子也未可知。当下便忙不迭的应了。亲自率人奉
上酒肉。此时听独孤樵如此说话,言辞间绝无作伪之色,心头个禁大犯疑窦,故而将十两银
子来了个虚报一半。
独孤樵却又怎知这许多关节,连日茫然奔波,只觉疲惫不堪,听掌柜的语言吞吐,倒也
不以为意,举箸便吃,接杯则饮,不多时早将酒菜一扫而光,扔过二钱银子,倒头便睡。
掌柜的见状更是满蹊跷,却不敢再问独孤樵。更不敢找那虬髯大汉自寻晦气,只率一干
小二下楼自犯嘀咕去了。
夜半酒醒,却听得隔着几间屋子有人压低声音笑道:“老叫化当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竟连自己的徒儿也看管不住。”
独孤樵先是一愣,随即不禁哑然:说话的正是晚间在楼下独饮的那虬髯大汉,先还怪道
在如此地方还会听到相熟之声。
又闻一豪迈的声音低低道:“都是天山二怪那两个老邪物,甫一见面便一口一个师祖,
叫得我老叫化骨头轻飘飘的,便随他们去喝了几杯,却中了那小滑头之计,自己溜了不说,
还把瞿姑娘也给……带跑了。当真对师太不住。”
一老妇忙道:“阿弥陀佛,姚大侠说哪里来着。让翟腊娜随陆小侠去江湖中磨炼,也未
尝不是好事,且此事贫尼也是知道的,又怎能怪……”
话音末落,自称老叫化的急道:“这么说师太是知他二人此番去向的了?”
几乎在同时,另一男一女两个声音同时传来。
男声道:“师太怎生不将他们带至此间?”
女声则道:“此事事关重大,虽瞿姑娘不知原委,鬼灵子却是知晓的,他为何……咦?!
对了,非是侯某对师太不敬,敢问师太怎知我等将在此地相会?”
鸿孤樵自是不知,这一行人,正是千杯不醉胡醉、布袋和尚姚鹏、江湖浪子童超、毒手
观音侯玉音、峨嵋掌门绝因师太和司马青青了,只是有师傅和爱侣在侧,青青此时尚未开口
说话。
毒手观音既直言相询,一声旨号宣过之后,便听绝因师太道:“有劳姚大侠、童少侠和
侯施主动问。贫尼今夜至此,并非适逢其会,实是受了鬼灵子指点。”
布袋和尚啊了一声,急道:“师太怎不早言。咱们这便去追那两……追鬼灵子那小滑头,
不知能否追上?”
绝因师太道:“阿弥陀佛!定然是追他们不上的了。”
稍顿又道:“贫尼是在四日前遇上他们的,随后贫尼便星夜兼程赶至此间。”
布袋权尚连连跺足,道:“这小叫化子真是活见鬼了,他刚知此事事关中原武林侠道气
数,却偏又……”
一语未了,却听绝因师大道:“这可奇了,鬼灵子也说他所要办的事关系到武林侠道名
誉,故尔未及与师父道别,并重托贫尼到此间来传一句话……”
众人俱是大奇,同声道:“一句话?!”
绝困师太道:“阿弥陀佛,鬼灵子说,独孤樵独孤施主已现身江湖了。却不幸又落入了
复圣盟手中,他正与敝小徒设法相救。”
数人同声惊道:“独孤樵?”
胡醉和童超则失声道:“独孤拜弟?”
绝因师太连宣佛号。
一阵沉默。
独孤樵先前还只觉这一行男女的声音恍然有些耳熟,却偏又记不起何时曾听到过,只想
如此偷听别人言谈大是不该,正欲蒙头再睡,“鬼灵子陆小歪”六字忽然传来,心头不禁大
约惑然:陆小歪为救他独孤樵性命,四年余前曾与金童赌命,不是早自戕身亡了么?莫非他
们口中的鬼灵子陆小歪与曾救他性命的陆小歪同名同号不成?
既如此想,独孤樵便不由得不去听了。此时听得众人惊呼他的名字,其中二人甚至口称
他为“拜弟”,其中之一更是晚间所见那虬髯大汉,独孤樵顿即如附十里雾中:什么叫“复
圣盟”?他几时又落入其手中了?
正惶惑间,忽闻楼道上传来三个人的脚步声。
而布袋和尚的声音也同时传来:“老叫化不许他坑蒙拐骗,玩那下三滥的勾当,他早就
想逃了,什么独孤公子重现江湖云云只怕全是那小叫化胡编出来的。哈哈!”
最后两声大笑有若重锤,直击得独孤樵气息翻涌,端的有说不出的难受。而楼道上立即
传来“砰砰”两声,却是姚鹏以内家真力贯注于笑声之中,将楼道上的人给震翻了两个!
另一人则强提一口真气道:“可是胡大侠和姚大侠在此么?晚辈崆峒派属下弟子曹国沙
求见。”
布袋和尚“咦”了一声,道:“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哈哈!”
末了这一笑恰若柔风轻佛,独孤樵只觉胸腹间翻腾不停的气息顿即平缓。楼道上被震倒
的那二人也已立起身,同声道:“姚大侠好深厚的功力!”
曹国沙则道:“深夜来访,实在冒昧。晚辈方才在楼下听掌柜的言及胡大侠容貌,擅与
二位师弟上楼,事急从权,还望签谅。”
言罢三人越过独孤樵居所,径直走到胡醉等人门前,但闻“哎呀”一声,显是有人为他
们开了。随即便闻崆峒派三人“咦?哦?!”之声,布袋和尚一一替他们引见众人,未了道:
“方才老叫化不明究里,行事孟浪,还请勿须介怀。”
崆峒派三人愣得一愣,方齐声道:“不敢当!”
曹国沙续道:“今夜得见这许多高人侠士,我师兄弟三人也不知是哪世修来的福份,姚
大侠如此说话,真折然晚辈了。”
众人少不得又客套了一番,未了胡醉问道:“曹兄方才所言‘事急从权’四字,敢问言
下所指?”
曹国沙道:“有劳胡大侠动问。四年之前,在下……”
当下将其时他如何误伤自称为乔石头的独孤樵;崆峒派内讧而得丐帮执法长老卢振豪解
难;崆峒派掌门五丁开山焦石子因何将镇派之宝《七伤拳谱》藏于独孤樵身上而事后独孤樵
偏又下落不明……等等细节悉数道出,直听得人人称奇不已,只这边厢独孤樵一人不以为意,
暗道这个姓曹的倒并未撒谎,并且他不叫我做乔石头而叫独孤樵,又承认当日他是误伤于我,
还算得上是好人一个。
随即又忖道:这曹国沙虽为人不错却是糊涂,想当日我醒来时你们一个人也不在身边,
且又不在你们崆峒山了,何况纵是还在,没人我还不会自行走开么,其时又不知你伤我是事
出有因,莫非我还想让你再打一拳不成!
正胡思乱想之际,便听曹国沙又道:“半月之前,忽有一蒙面人到敝派传言,说敝派的
《七伤拳谱》已落入了复圣盟,敝掌门师尊问其讯息由来,那人却长笑而去,并未以真面目
相示。然此事有关敝派气运,总是宁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掌门师尊便率了十余名弟子到江
湖上暗中查证此事,不料十日之前,《七伤拳谱》又蹊跷地出现于敝派议事厅内,并附有一
简短书柬,说独孤少侠确实已现身江湖,只是年来他并不知怀中的《七伤拳谱》便是敝派镇
派之宝,要晚辈尽快寻回掌门师尊,免中奸人之计。”
布袋和尚道:“贵派的‘七伤拳’在江湖中实可算一等一的拳法,那人既已取到,为何
又要归还?此事倒是有些古怪,不知——”
曹国沙已明其意,忙道:“多谢姚大侠赞誉,然实是惭愧,敝派之中,唯掌门师尊一人
曾得修习,此时拳谱虽在晚辈身上,却实难以辨真伪。”
武林之中,各门各派的武功心法皆是决不能泄漏于外的,饶是胡醉姚鹏等人侠名盖世,
也断不便让曹国沙掏出《七伤拳谱》帮着参详真伪。
过得少顷,却闻胡醉道:“那封书柬是何模样,曹兄可还记着么?”
曹国沙道:“在下也恐口说无凭,顾尊他老人家难以置信。
故将敝派拳谱和那书柬随身携带,便是这封书柬,请胡大侠过目。”
只过片刻,忽闻胡醉“啊”了一声。
众人惊道:“怎么啦?!”
胡醉道:“又是那位头戴斗笠的前辈异人!”
须臾,请如此类的声音不断传出:“是他!”
“不错!”
“是那位前辈的笔迹。”
只有绝因师太不停地口宜佛号。
曹国沙奇道:“请恕晚辈愚鲁,留此书柬之人,莫非——!”
胡醉道:“曹兄放心,此书柬既是那位前辈所留,便决计错不了了,还望曹兄对贵派重
宝多多留意。”
曹国沙道:“那位前辈有如此大恩于本派,却未能一睹他老人家仙容,当真是平生憾
事……唉!”
言下之意却是:胡大侠可肯告知那位前辈仙居何处么?
胡醉一笑道:“那位前辈宛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此间诸人,竟未有能一睹其侠骨风范者,
好生令人抱憾!”
江湖浪子也道:“咱们虽也曾得那位前辈留书指点,却连他老人家尊姓也是不知,当可
算是无能之极了。”
听江湖浪子也如此说话,曹国沙连忙道:“既是如此,在下等须得依那位前辈之意行事
尽快找回家师才是。告辞了。”
与崆峒派三人别过之后,布袋和尚道:“如此看来,鬼灵子那小滑头此番倒并未撒谎。”
江湖浪子笑道:“怎的姚大侠总对自己徒儿信他不过,依我看来,鬼灵子……哎哟不
好!”
布袋和尚奇道:“什么不好?你……胡闹!”
也是一语未了,忽已明白江湖浪子心思:“凭鬼灵子和瞿腊娜二小要从复圣盟中救人,
只怕早是身涉险地了!”本想打趣一句“你江湖浪子怎的也变得说话不痛不快了。”临了却
改成“胡闹”二字,那是在说鬼灵子。话虽如此,却毫无责备之意。鬼灵子所行,正是义不
容辞之举。
众人一般心思,当下胡醉道:“事这宜迟,烦请绝因师太带路,咱们这便接应鬼灵子和
瞿姑娘去!”
之后再无声息传来。
这边厢独孤樵心道:你们都上了鬼灵子的当了,他不想到这儿来,才谎说去什么复圣盟
救我,可我好端端躺在这儿,又何来落人别人手中之说了。哈哈,看在那虬髯大汉下午曾帮
我说过话来的份上,我独孤樵须得去与他们说明此节才好。
思忖既定,便移步至先前胡醉等人言谈之所,却无一人踪影,愣得一愣,回至自己居所,
忽地心间一动,暗道糟糕,这伙人越窗走了,明日没人帮着说话,那掌柜的定然饶我不过,
大约总有三、四两银子保不住了!自怨自艾,干脆倒头便睡。
正睡得懵懵懂懂,忽闯耳际传来一个细柔的声音:“老朽已代你将《七伤拳谱》还给崆
峒派了,这对你有益无害。明日你离开此间时,掌柜的会对你奉若神明,你可不得惶然无措。
若与曹国沙等人相遇,你须得装作不认识,速速离开,出店后依旧往东南方向走,或会别有
际遇,那却得看你的造化了。老朽便是先前那些人所说头戴斗笠之人,你吃过老朽钓的鱼,
记得么?唉!老朽违背先人遗训,自练神功,又管闲事过多,有干天和,再不能教你武功了。
它日你若有缘得遇一位与老朽年纪相若的老姬,她的脾气很古怪,兴许会无缘无故一掌便取
了你性命,到时你就说你亲眼见过公孙鹳,他是公孙鹳的后人,并已将天冥掌练到掌风无毒
并到中原来找过其祖母了。你必须牢牢记住公孙鹤、公孙鹳和天冥掌三个名字,否则……唉!
老朽也不知对你说这些话是对是错,独孤樵,你好自为之吧。”
言语到此,便即嘎然无声,独孤樵就此沉沉睡去。
醒来已是次日日上三竿,甫一开门,便见一干小二肃立门口,端水的端水,捧面巾的捧
面巾,更有一抱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华丽衣物。
独孤樵大奇,问道:“你们干什么?”
众小二满面堆欢,齐声道:“大爷您老醒啦?!”
独孤樵懵然不解,那怀抱衣物的一挥手,小二们群涌而上,将地拥回屋内。
独孤樵骇然道:“喂!你们这……这是要干什么?”
众小二齐声:“小的们服待乔大爷洗漱更衣!”
独孤樵失声道:“乔大爷?你们一定是认错人了,我叫……
我叫……”随即想昨天晚间自己曾说自己姓乔名石头,且此时若报真名,不知又会惹什
么麻烦,一时竟是惶然无措。
掌柜的已得报,飞奔上楼,高声道:“乔大爷醒了么?”
随面色一肃,沉声道:“怎么还不服待乔大爷洗漱更衣!”
众小二齐声道:“是。”
言语间中由分说,七手八脚地为独孤樵擦去脸上的污泥,更为他换了一袭白衫,且戴了
一顶文土巾。
独孤樵一刻不停地道着:“怎么回事?这……这是不对的。”
无奈这些小二俱是手脚利索之辈,不多时已将他打扮得焕然一新,也不知是受了谁指使,
他们将独孤樵的银两和锦盒依旧放入他怀内,更特意制了一青绸袋子,将独孤樵本已包扎妥
当的松纹木剑套入袋内,仍是负于其背,倒象是背了张古琴。
独孤樵顿时变的似是一介书生,委实不知该当如何区处,只翻来覆去的讲一句话:“你
们这佯做是非常不对的。”
掌柜的则笑吟吟地道:“乔公子好俊秀人物,难怪!难怪!”
难怪什么,独孤樵恰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少顷,一名小二捧上一副托盘,上面猛然齐刷刷地放着五锭十两一锭的纯银,恭恭敬敬
地托到独孤樵面前。
独孤樵一惊更甚,失声道:“这是……什么意思?”
掌柜的连忙道:“小的昨日有眼无殊,不知是乔公子驾到,实是罪该万死,还望乔公子
大人不记小人过,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公子爷笑纳。”
独孤樵心头之惊异,端的难以言表,观掌极言辞间并非作伪,当即道:“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请恕在下不能无端受这许多银两。”
话音甫落,忽闻“卟嗵”连声,自掌柜以下,众小二已齐刷刷跪在独孤樵面前。
独孤樵大惊,也连忙跪下还礼,口中道:“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掌柜的磕头如蒜,边磕头边道:“乔公子若不受礼,小的们便没命了,还望公子爷慈
悲。”语音中竟有哽咽之色。
独孤樵心头大惑,问道:“请恕本……本公子愚鲁,不知掌柜的言下之意?”
掌柜的骇然道:“小……小的不敢说。”仍是磕头不止。
独孤樵闻言心头一动,顿即想起昨夜朦朦胧胧间听到的那一番话,当下略作沉吟,轻叹
一声,道:“各位快快请起,本……公子收了你们银两便是。”
掌柜及众小二闻言大喜,齐声道:“多谢公子爷!”
待独孤樵接过银两,才一齐立起身来,俱是满面喜色。
独孤樵又轻叹下一声,才道:“若无要事,本公子这便要走了。”
掌柜的连忙道:“公子爷既有要事,小的们恭送公子爷。”
当下掌柜的率先引路,众小二前呼后拥地送独孤樵下楼。
楼下曹国沙和两名师弟正在炊酒。见店掌柜及店小二拥着一介青年书生下来,其中一位
名叫耿明冬的“哼”了一声,高声道:“我还道店里的人都死光了呢!还不快给大爷打斤酒
来!”
掌柜的唯唯陪陪连声称是,却依旧率众小二将独孤樵恭送出店。耿明冬当场便要发作,
却被曹国沙止住。
直过了一袋烟时光,掌柜才与众小二急奔回店,忙不迭的与曹国沙等人陪礼告罪。
耿明冬又冷哼了一声,怒道:“什么东西……”
曹国沙连忙道:“耿师弟休要多言。”
耿明冬愣得一愣,兀自咕哝道:“哼!什么阿狗阿猫也冒充起公子爷,这年头真是越来
越不成话了!”
掌柜的连忙道:“是是是!小的耽误了三位大爷要事,这便请三位大爷赏脸,小的奉送
大爷们一桌酒席如何?”
耿明冬怒道:“哼!你以为咱们是吃白食的么?!”
掌柜的连忙道:“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曹国沙也忙接口道:“我这位师弟性子急燥,掌柜的勿须介怀,这便请去打了两斤酒
来。”
掌柜的连忙应是,奔人柜台捧了一壶上好竹叶青来,亲自把盏斟酒。
曹国沙道:“不知方才掌柜的恭送出门的是何方公子,竟尔——?”
耿明冬道:“什么屁的来头,老子最看不惯那些贵介公子,自己没狗屁本事,全仗着财
势欺人,呼!”
掌柜的忙道:“是是是。小的也不知那乔公子是何来头,只是今后寅卯时分,小的正睡
得香甜,不知怎的便撞上了鬼,那鬼也端的了得,只用两根手指,便捏住小的脖颈子,将小
的拎起来,小的吓得六魂出窍七魂升天,只道此番我命休也。没料那鬼扔了五锭纯银在小的
床上,让小的待乔公子醒后,便将那银子给他送去,还要小店所有人手服侍乔公子洗漱更衣,
小的自是没口子的答应了。”
曹国沙等人俱是心头暗惊:要捏住脖子将这掌柜的拎起来那倒不难做到,但若只用两根
指头便将掌柜的脖子夹位拎起,他们却是自忖不能。
便听曹国沙道:“寻常护院家丁,断无此等身手,不知那姓乔的公子是何方神圣,此事
倒委实有些古怪。”
掌柜的道:“可不是么。实不瞒客官说,那乔公子初到敝店来时,打扮得与一叫化相似,
也怪小的有眼无珠,竟欲将之逐出门外,若非那满面浓须的胡大爷解围,乔公子一怒之下,
小的这项上之顶是否能保得住,那可就难说得很了。”
曹国沙奇道:“胡大爷?可是——”当下将胡醉的容貌形容了一番,未了问道:“——
此人么?”
掌柜的连连点头,道:“原来客官也认识胡大爷。”
随即也将独孤樵入店前后之事道了出来。
耿明冬怒道:“哼!那姓乔的好大架子,竟不愿和名扬四海的胡大侠共饮,却不知他叫
何名,它日遇上,我姓耿的倒要向他讨教几招!”
掌柜的道:“是啊!胡大爷最是豪爽不过,那姓乔的却不知好歹,后来小的替他送酒菜
上楼,问起他的姓氏,他顺口说他叫乔石头,哼,我看这名字八成是……”
“假的”二字尚未出口,曹国沙等三人早失声道:“什么?!”
掌柜的大骇道:“小的所言句句属实,还望……”
曹国沙连忙道:“他说他叫乔石头?”
掌柜的惶然不知所揩,只吓得连连点头。
曹国沙只道得一个“追”字,掌柜的陡觉眼底一空,眼前哪还有三人踪影,愣怔半晌方
自言自语道:“莫非又遇着了鬼不成。”
却说独孤樵与掌柜及一干小二别过之后,茫然不知其所往,只觉此事之奇,端的匪夷所
思,心道往日总得寻个因由,将这五十两纹银还给人家才好。
正思忖间,忽闻有人惊“咦”了一声,独孤樵尚未转过头去,便觉右胁一麻,人早委顿
于地。恍忽之间,只觉自己腾空而起,正自御风飘荡。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刻,独孤樵悠悠醒来,发现自己正置身于莽莽林海之中,三丈开外,
一个身着淡黄衣衫的背影正对着他,那人盘膝而坐,也不知在忙什么。
独孤樵道:“喂!你是谁?是你将我带到此间的么?”
那人闻声转过头来,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独孤樵一观之下,顿即目瞪口呆,更难道出第二个字儿来。
万人乐!
此人非它,正是飞天神龙万人乐。
见独孤樵满面惶恐之色,飞天神龙突然沉下脸来,厉声道:“我那树屋可是你这小子烧
的?!”
独孤樵大惑,问道:“什么树屋?”
飞天神龙目光中陡现杀机,盯着独孤樵,一字一句地道:“裴文韶已被人杀了,那叫做
死无对证,我问你,那木屋是你烧的还是裴文韶烧的?若有半句谎言,哼!”一掌将身旁的
一块巨石拍下一角,续道:“这石头就是你的榜样!”
一提裴文韶之名,独孤樵反倒宽下心来,当下道:“是裴文韶烧的。”
飞天神龙冷冷道:“凭区区—个裴文韶那点儿微末技行,断无能出我那树屋之理,哼!
我为何要相信你的话?”
独孤樵机伶伶打个寒噤,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日我便觉得裴文韶做的不对,
难怪时隔数年,阁下仍是这般生气,却也怪你不得。”
飞天神龙怒道:“不怪我?!哈哈哈!纵要怪我,你却又将怎生怪法?”
独孤樵奇道:“我说过不怪便是不怪,又何何来怎生怪法了?”
飞天神龙怒极反笑,连声道:“好好好!”
独孤樵喜道:“既然阁下也说好,那就……那就太好了。
至于阁下若还不相信我的话,那也叫做无可奈何。”
飞天神龙以其邪怪之名“享誉”江湖数十年,此时竟被独孤樵弄了个啼笑皆非,一时倒
不知如何说话才好。
却听独孤樵又道:“裴文韶死了?是阁下杀了他么?唉!那也叫做恶有恶报,当中他和
胡涂杀那叫化时,我就认为那是非常不对……”
飞天神龙暴怒道:“管你妈的对不对,大爷行事,向来是爱怎样便怎样,只须遵守江湖
规矩就行。”
独孤樵道:“我说的是裴文韶和胡涂不对,又没说你。”
飞天神龙怒极反笑,笑罢道:“四年前我还只道你是个笨蛋,没想到现今你却变成了个
浑人,天下一等一的浑人!难怪陆小歪没法教会你武功,却这般作奸使诈!”
独孤樵奇道:“阁下不说,在下倒还不知自己是天下一等一的浑人。至于阁下说陆小歪
教在下武功不会云云,那却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鬼灵子从未教过在下武功……”
一言未了,飞天神龙早一弹而起,一把扣住独孤樵手腕,厉声道:“那你身上的内力,
却是何人所授,说!”
独孤樵只觉飞天神龙的五指有若铁圈相似,几欲将他手腕夹碎,泪花早在眼眶内翻滚,
却强忍没叫出声来,颤声道:“你……你说什么?什么叫内……内力?在下一无所知,阁下
可能详告么?”
飞天神龙“哼”了一声,手指微微放松了一些,道:“你跟我装什么蒜!方才大爷点你
昏睡穴之时,早发觉你身负内功,虽只是一丁点儿,却已打下了习练上乘内功的根基,说倒
底是谁传授你的?”
独孤樵奇道:“没有呀。”
飞天神龙变色道:“你想找死么?”
独孤樵连忙道:“不想。”
见飞天神龙凶霸霸地瞪着自已,又道:“这些年来在下在湖东村与二位拜兄捕鱼,确实
无人教在下习练过什么内功。”
飞天神龙也自奇道:“湖东村?那是什么地方,竟会有身负如此博大纯正的内功之人?”
独孤樵当下便将湖东村的位置及自己如何与柴氏兄弟结拜经过讲了—遍,待讲到拜兄全
家如何惨遭暴死时,再也忍耐不住,泪水早汹涌而出。
飞天神龙见独孤樵言色间更无丝毫作伪之色,心头也不禁大是犯疑,沉吟良久,方道:
“你将四年前随陆小歪和瞿姑娘走后所发生的事全讲出来,不准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听到了
么?!”
独孤樵道:“这倒使得。”
当下将自己四年来自己的诸般际遇细细讲了一遍,只遵嘱避过日前自己在“梦”中听到
的话语不提。在讲到两位拜兄时,少不得又是泪湿衣襟。
飞天神龙听经又沉吟良久,方自言自语道:“古怪!邪门!当真古怪!当真邪门!”
独孤樵道:“阁下有何难以索解之事,何妨道了出来,也让在下一道,与你参详参详?”
飞天神龙玲哼道:“与你这浑人参详个屁!”瞪了独孤樵一眼,见对方默不作声,便又
冷哼道:“你为何不问我觉得何事古怪?”
独孤樵道:“反正我问了阁下也不愿说,在下只好免开尊口了。”
飞天神龙道:“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说?”
未等独孤樵开口,又自顾道:“那—剑刺死太阳叟东方圣的独孤樵我虽未能亲眼得见,
但金童非杀你而不甘心,陆小歪又不惜以一己之命换你性命,崆峒派焦老儿更冒险将其镇派
之宝藏于你怀中,如此看来,你倒确实……有些像是独孤樵……”
独孤樵忙道:“我本来就……”突然想起说自己是独孤樵,又难免被这飞天神龙“教”
武功,当即改口道:“不是独孤樵,并且……并且日前晚间听那许多人说鬼灵子陆小歪不知
在哪儿发现独……独孤樵已落入复圣盟手中。在下就更不可能是独孤樵了,阁下以为然否?”
飞天神龙道:“那是自然,你没半丁点儿本事,又怎能杀太阳叟东方圣了!”
独孤樵喜道:“既是如此,咱们何不各走各的,阁下自去贵干,在下也……咦?怎的在
下半边身子麻木不仁,莫非是中了风么。”
飞天神龙大笑道:“大约正是中风了。”
独孤樵黯然长叹一声,稍顿又道:“在下有一不情之请,不知阁下可肯应允么?”
飞天神龙奇道:“你说。”
独孤樵道:“敢劳阁下替在下寻了根木棍来。”
飞天神龙一奇更甚,问道:“干什么?”
独孤樵道:“在下想以木棍权当手杖,去寻个郎中给治治,否则落个半身不遂,那可不
是闹着玩的。”
飞天神龙闻言一愣,随即笑得浑身打颤,连在地下翻了几个跟斗,兀自棒着小腹大笑不
已。
独孤樵奇道:“阁下——”
飞天神龙边笑边道:“好,好。”却不去寻木棍。
独孤樵惑然不解地看着他,过了良久,飞天神龙好不容易才止住笑声,撕了一块不知什
么兽肉给独孤樵,道:“你吃,吃饱了才有力气赶路。”
独孤樵喜道:“这也说得是。”
授过烤肉便吃。
一时二人俱未开口出声。
待独孤樵堪堪将那块烤肉吃完,天神龙忽然嘿嘿冷笑数声,阴恻恻地道:“现在你叫什
么?”
独孤樵惑然道:“我叫……我叫……”他不知自己该叫什么,顿得一顿,忽然心头一亮,
自己此番一路东来,实是因悲愤所至,要为湖东村的两位拜兄报仇,当下道:“我叫柴方
圆。”那却是将柴方柴圆两兄弟的名字合在一起了。
飞天神龙冷冷道:“怎的我带你到此间时,有三个崆峒派的小辈在后面叫你叫乔石头?”
独孤樵道:“可是曹国沙他们呢?他们在哪儿?”
飞天神龙道:“凭他们那点儿道行,只怕连大爷的屁也闻不到!怎么?莫非你认识曹国
沙他们?”
独孤樵道:“方才在下已言明目分曹国沙曾打过!我阁下怎的这般快便忘记了。”
飞天神龙“哼”了一声,道:“你一会儿冒充独孤樵,一会儿自称乔石头,眼下又说自
己叫柴方圆,到底你的真名叫什么?说!”
独孤樵道:“在下自然不能叫做独孤樵。至于乔石头之名嘛,却是昔日裴文韶胡乱摊派
给我的,那也不能作数。实在没法,就算叫柴方圆吧。”
飞天神龙怒道:“是便是,不是便不是!何来就算叫柴方圆!这算什么意思?”
独孤樵道:“好!既是如此,我便叫柴方圆。”
飞天神龙道:“这名字可没人胡乱摊派给你,而是你自报的家门,是也不是?”
“是”
“你的真名便叫柴方圆?”
“就算……是!”
“好啊!姓柴的,你胆子不小,竟敢消遣起本大爷来了!”
“我……没有!”
“嘿哩!没有?!你是欺本大爷无知,竟连你身怀内力也查不出来么?哼哼!想必你是
不要命了!”
“这个……这个嘛,在下决不敢说阁下无知,更不存半点相欺之心,阁下说在下身怀内
力,大约也是……不,那是不会错的,然在下实在是……实在是对不起之至,何以如此,在
下实是一无所知。至于阁下最后一句话,那却问的有……有些儿欠通,试想蚁髅且偷生,在
下又怎会不想活命?”
“哼!”
“在下所言句句属实,阁下如若不信,在下也是无可奈何。
依我之见,咱们这便分手如何?”
“姓柴的!你是第一个敢这般对我飞天神龙说话的人,纵若你身怀何等惊人技艺,莫非
我飞天神龙便不能一掌取了你性命么?”
“阁下所言差矣,在下并未身怀什么惊人技艺,故而阁下一掌,大约是能取了在下性命
的。”
“大约?哈哈哈!大约!来来来,咱们这便比划比划!”
“不用比划不用比划,何况在下也比划不来。是在下一时失言,阁下一掌,那是……那
是……”
“如何?”
“毫无疑问是能取了在下性命的。”
“咱们尚未试过,你怎的便知道了?来来来,咱们先试过一掌之后再说。”
“不!不!这是试不得的。”
“为何试不得?”
“因为……因为一试在下便没命了,那是一目了然的。”
“这么说你是相信我一掌能取你性命了。”
“当然,当然,在下坚信不疑。”
“但我不取你性命。”
“这……?”
“你想死?”
“不想。”
“哼!你可知我为何不取你性命么?”
“请怨在下愚蠢,确是有些不知。”
“大爷不妨告诉你,是因为鬼灵子陆小歪。”
“哦。”
“你还记得四年前本大爷与陆小歪打赌之事么?”
“这倒记得。”
“那就是了,此时你仍不会丝毫武功,却又身负内力,故陆小歪是彻头彻尾的输了,本
大爷要带了你找他当面对质。”
“原来如此。”
“不管那真的独孤樵是否身怀武功,也不管你到底叫何名字,反正本大爷与陆小歪是赌
他半年内能教会你武功,此时已过了四年……哈哈,大爷的筹码,只怕要加上那么一丁点儿
了。”
“什么筹码?”
“到时你便会知道了,走吧。”
“可在下这身子……咦?!古怪古怪,在下这中风怎的不医自愈了!”
飞天神龙哈哈大笑,心头之畅快端的难以言表。数年来遍寻独孤樵不到!陆小歪偏又不
肯撤了赌约,使他不得不时时避免与陆小歪朝相,实是憋气得紧,此时这独孤樵已在他手中,
更兼不会丝毫武功而身怀内力,依他们昔日的赌约,陆小歪是输得不能再输了。他虽不知独
孤樵那点儿内力从何而来,甚至连独孤樵自己也不知当日在汉水岸边,那头戴斗笠的老者以
钓杆抛其过江时,力透鱼线,以末稍轻拂其膻中穴,输了一丝儿内力给他,其时他只忙着想
求那老者传艺,且那老者的内力又柔和之极,竟末觉出丝毫异样,若飞天神龙不说,他实是
毫无所知。但正因如此,飞天神龙才倍加欢快:这自称“柴方圆”
的独孤樵已成浑人一个,他万人乐岂有不稳操胜券之理!故而当他说到“走吧”二字,
暗运内力个大袖轻抚,解开了独孤樵被封穴道,而独孤樵还在为自己的“中风”不医自愈大
觉古怪时,他岂有不大乐之理。
待独孤樵立起身来在天神龙忽然心头一动,四年前他带着这独孤樵东藏西躲,九天竟与
人打了三十七架,只怕这“柴方圆”当真与独孤樵相貌酷肖,甚至有何血缘关系也未可知,
此番若大摇大摆地带了他去找鬼灵子理认论,只怕有些麻烦会无缘无故地沾惹上身,那倒大
为不妥。当下收住脚步,对独孤樵道:“喂!柴方圆,你等等。”
独孤樵一愣,随即想起飞天神龙所说的“柴方圆”乃是叫他,便惑然道:“等?等谁?”
飞天神龙心念电闪,他对易容改妆之术并非行家里手且此地更是刻不沾村后不落店,易
容之一应物事是断断没有的,只有如此这般了……
便闻“嗤”的一声,飞天神龙早撕下半幅衣袂,不由分说,已将独孤樵面容严严实实罩
住,只以手拽剪了两个小孔让他露出双目。
独孤樵大惑不解,问道:“阁下这是干……干什么?”
飞天神龙以为自己这一招干得很漂亮,哈哈大笑道:“如此一来,便绝没人再能认出你
了。”
独孤樵道:“纵若被人认出,却又怎样呢?”
飞天神龙面色一凛,道:“自此刻起,无论遇上何人,你都只可说自己叫柴方圆,‘独
孤樵’三字是万万不可出口的,记住了么?”
独孤樵道:“记是记住了,但在下还是不明白……”
话音未落,早闻飞天神龙一声暴喝:“够了!”
见独孤樵一派惶然之色,飞天神龙又冷冷道:“你怕死么?”
独孤樵愣得一愣,道:“死嘛,自然是怕的,却不知阁下言下之意,莫非……?”
飞天神龙截口道:“你一说自己叫独孤樵,或者让人看到了真实面目,少不了便会有人
要取你性命,懂了么?”
独孤框心头也自凛然,他虽不知是何缘故,但四年前羊头村何志福父女俩和数月前湖东
村全村百十号人的惨遭暴亡,皆因他是独孤樵而起。此时听飞天神龙如此说话,禁不住泪水
潸然而出,半晌才缓缓点了点头。
飞天神龙见状大喜道:“事不宜迟,咱们这便找陆小歪去也。”
话音甫落,忽听二十丈开外传来一怪叫声:“究竟是何方小辈活得不耐烦了,竟敢将我
天山二怪的师父之名抬着大呼小叫!”
飞天神龙眉头大皱,尚未及叮嘱独孤樵不可泄漏身份。天山二怪早双双立于对面五丈开
外,一齐向天神龙怒目而视。
便听牧羊女梅依玲道:“方才大呼小叫的,便是万人乐你这小子么?”
飞天神龙万人乐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之人,但此时他却不愿多生枝节,当下赔笑道:
“经年不见,二位前辈是越来越……这个……朗爽了。”
牧羊童阳真子忙道:“什么叫‘今年不见’!咱们是有三年多未见过面了,哼!你这小
子的话狗屁不通之至,我和依玲以天山二怪为名;而朗爽便是丰朗爽直的意思,是讥讽咱们
名不副实么?”
飞天神龙忙道:“晚辈不敢。”
阳真子道:“你固然是晚辈,但鬼灵子是我歪邪派开山掌门,更是我二怪的师父,推算
下来,他便是你前辈的前辈了。
偏你这小子不识天高地厚,竟将前辈之前辈的名讳大呼小叫,莫非是这三、四年来,你
已然武功大进,竟不将我歪邪派放在眼里了么?来来来,咱们便比划比划再说!”
言罢便欲动手。
飞天神龙心头大叫倒霉,口中却连忙道:“四年前晚辈便是二位前辈手下败将,此时观
二位前辈更是龙精虎猛,若论动手,晚辈是断断不敢的。”
梅依玲“哼”了一声,道:“然方才直呼我二怪师父尊姓大名的,莫非是那蒙面的小子
么?!”
飞天神龙道:“这——”
阳真子也“哼”了一声,道:“你是欺我二怪老耳昏馈了,竟然听不出你的声音来了么?
很好,很好!四年前你败于我和依玲之手,心中大约是一直耿耿不服的,今日你们是两人,
我们也是两人,便来重新打过再说!”
其实四年前二怪与飞天神龙那一战,虽说二怪功力深厚而占尽上风,然轻功却比之飞天
神龙有所不及,更何况在莽莽森林中,飞天神龙更是如鱼得水,虽凶险万端,却还是被他挟
着独孤樵上树逃脱了,并未有丝毫损伤。四年来天山二怪倒是一直为此事耿耿于怀,心道凭
他二人功力,竟让区区一个飞天神龙将人带了逃循,那委实是大丢颜面之事,故尔闭口不谈,
只一心欲与飞天神龙找回场子。偏这四年飞天神龙为避开鬼灵子,恰似自武林中消失了一般,
今日巧遇,纵是飞天神龙并未高呼什么陆小歪之名,天山二怪也是要逼着与他重新打过的了。
二怪行事虽邪,却并非莽撞之辈,待阳真子话音刚落。二人心意相通,早一前一后将飞
天神龙和独孤樵围住。
飞天神龙见状大怒,邪气贲张,哈哈大笑数声,道:“天山二怪,若凭功力蛮打,姓万
的自不是你二人对手,但此时此地,他们自信能困住我飞天神龙么?!哈哈。”
阳真子也大笑两声道:“好说,好说。”
梅依玲则只淡淡地道:“别让他上树。”
飞天神龙闻言一凛,凭二怪身手,要逼住他在地上死缠烂打倒真并非难事,若不飞身上
树,后果端的大为堪虞。当一只冷笑不语,暗自计较脱身之法。
忽闻阳真子暴喝一声:“何方狂徒!竟敢在我天山二怪面前蒙面不见,当真是见不得人
么?照打!”
他说“何方狂徒”四字时,已是功布全身蓄势待发。说到“蒙面不见”时,人已若鹰隼
相似,飞身疾射独孤礁,待最后“照打”二字出口,左掌已触及独孤樵神庭穴,右掌则早抚
中独孤樵胸前鹰窗穴!
陡见阳真子飞身跃起,飞天神龙心头之惊骇端的难以言表,只道得“不可”二字,人已
电射而上。
然天山二怪心意相通,阳真子甫一出声,梅依玲便明其意。待飞天神龙身形微动,她也
飞身跃起,空中截住飞天神龙。电光石火之间,二人已交换了一腿三掌!
也是在电光石火之间,阳真子已觉出独孤樵并不会丝毫武功,其内力也微弱至极。他一
生行事虽邪,却并非滥杀无辜之辈,当下强自收回真力,只左手化零为爪,将独孤樵的蒙面
巾一把揭去。
“嘭”的一声,独孤樵虽只胸间鹰窗穴吃了阳真子不到半成真力,却已经受不住,仰身
倒地。
变起仓促,飞大神龙纵身而起时所提起的内力尚未及三成,哪堪与早有防备的梅依玲相
比,硬接了一腿三掌之后,人被震得“腾腾腾”倒退出七步之多,方才立稳脚跟,“哇”地
吐出一大口鲜血,面色惨白地坐下盘膝运功调元。
而阳真子倏然间强收真力,恰似以自己数十年功力回击自身,也是一口浓血喷出,委顿
于地。
仅刹那间,场中四人便行三人人事不省,只梅依玲呆若木鸡怔立当场。双目紧紧盯着独
孤樵面容,惊愕得更难呼出一口长气。
良久。
一阵凉风吹过,梅依玲骇然一惊,见阳真子面呈死灰,了无生气,比之独自盘膝运功调
元的飞天神龙万人乐,显是所受内伤更重。他天山二怪数十年伉俪情深,心头狂震之下,梅
依玲哪还能顾及其它,当下疾掠过去,伸手一探鼻息,只觉阳真子气若游丝,少顷便有性命
之厄。惊骇之际,忙将阳真子翻身侧卧,连点了他中冲、合谷、百会、人中、大敦等穴,运
气于劳宫穴,力达指尖,以左右中指将内力源源输入丈夫体内。
天山二怪所习内功本是一种,更是夫妻形同—体,虽阳真子所受内伤极重,不到盏茶时
分,梅依伶便以强劲内力将其已被震离的五腑归位。
饶是如此,梅依玲仍是深知丈夫的性命虽己从鬼门关前被拉了回来,但她苦在此时撤了
内力,阳真子说不得依旧还须找阎王爷会面,更不敢有丝毫松懈,反运出平生修为,将内力
自阳真子百会人中二穴绵绵不绝地输入。
少顷,阳真子、梅依玲和飞天神龙万人乐二人,俱是头缠氲氤白雾,更不知方外之物了。
又过了半个时辰,反是独孤樵穴道自解,率先醒来,陡见天山二怪和飞天神龙之状,不
由大感蹊跷,还道他们准是在弄何玄虚,当下复又闭上双目。不敢有丝毫异动。
如此过得盏茶时分见他三人仍是了无异状,不由心头犯疑,暗道:这三人皆是好斗之辈,
那是断断不能与他们同行的。只是他们武功太高,身形如同鬼魅,跑是跑不掉的,那却如何
是好?
随即又忖道:此时他们一动不动,状似老僧入定,纵若他们是故弄虚玄欺骗于人,我好
歹也得试试,若能逃离那是最好,纵若不能,大不了也不过再被他们捉了回来。
思忖既定,便轻轻翻身立起,蹑手蹑足地悄悄离开,先是进住呼吸,一步一步慢慢移动,
直如此步离三十余丈后,方放腿狂奔。并不见天山二怪和飞天神龙追来,心头还暗道侥幸。
独孤樵自是不知,天山二怪和飞天神龙“故弄悬虚”之时,纵是个不会丝毫武功的寻常
少年,也可轻而易举地将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三邪”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