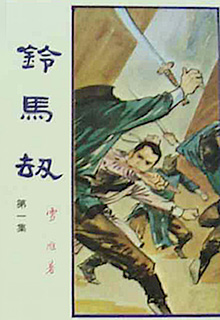四十年前龙虎山武林大会,“魔道霸主”姒不恐在擂台上单掌力毙八大门派二十一大高手,事发当日,固然哄动天下,时至四十年后今天,武林中人仍然犹有余悸。谁也想不到,久已不出江湖隐伏于阴山之幽冥宫主,忽尔再度重现,更把和尚战将带走,与太叔梵离定下三年后的一场决战。
但那并不是姒不恐与太叔梵离亲自动手一搏之争,而是由贫僧和尚大战水老妖之义子马小雄。
老太叔眼睁睁地瞧着姒不恐带了和尚儿子,却是无计可施,只得呆愣愣地坐在吊桥边,喃喃道:“老相好,你说怎办?”
服难师太道:“姒老魔魔功盖世,不知如何,竟是冲着琴茶而来,硬要传授他一身幽冥派武功,其间必然大有文章。”
老太叔道:“谁是琴茶?”
服难师太道:“咱们的儿子,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就叫琴茶。”
老太叔道:“咱们喜欢喝茶,那个茶字是大有意思的,但为什么不叫青茶、绿茶、乌龙茶?”
服难师太灰白眉毛一皱,道:“要是名字叫乌龙茶,连名带姓便是太叔乌龙茶,听起来岂不十分蹩扭?”
“不蹩扭!不蹩扭!”老太叔咧嘴一笑,“要是取名太叔乌龙茶,定必万民爱戴,四方景从。”
服难师太沉声道:“乌龙茶是用滚水冲泡的,你要把咱们的儿子天天给万民冲泡饮用吗?”
老太叔一愣,立时摇头不迭:“这可万万使不得。”
服难师太道:“当年,我把孩儿命名为琴茶,那个茶字的意思,你是明了不过的。”
老太叔道:“那个琴字,又有什么意义?”
服难师太叹了口气道:“在龙虎山武林大会之后,你曾经送了我一具五弦琴,也许你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老太叔听了,默默无语。
马小雄捧着木小邪的大刀,走到老太叔面前站定,道:“三年后,要是我跟你的和尚儿子比拼,你老人家会渴望哪一边获胜?”
老太叔道:“只要你是我调教出来的,我自然渴望你能够把乌龙茶击败。”
服难佛然不悦,道:“是琴茶,不是乌龙茶。”
老太叔道:“好,就是如此。”
服难怒道:“说话含含糊糊不清不楚,什么叫‘就是如此’?”
老太叔道:“从此以后,你叫你的,我叫我的,太叔琴茶也就是太叔乌龙茶。正是此茶即是彼茶,彼茶也即是此茶,但要是谁敢把咱们的儿子冲泡饮用,我决不轻恕。”服难闷哼一声,不再说话。
马小雄却道:“又琴茶又乌龙茶,听来甚是混淆,不如各取其尾字,未知两位前辈认为如何?”
老太叔“咦”一声:“你为什么叫我‘前辈’?我比你只不过大一两岁,你叫我一声小大哥便可。便是我要把一身武功向你倾囊传授,你也不必拜我为师,反正要你这种牛脾气的人拜我为师比起逼一条母猪爬上泰山封禅台上跳舞还更困难……
嗯,何谓之名取其‘尾’字,是不是我的和尚儿子应该唤作‘尾尾’?”服难师太听了,差点当场喷血。
马小雄忙道:“世上虽有‘娓娓动听’这一句话,但要是名为‘尾尾’也好,‘娓娓’也好,那就很不好听了,我的意思,是师太喜欢叫令郎琴茶,你却喜欢把师太的儿子称为乌龙茶,既然如此,不如各取尾后的一个‘茶’字,就叫茶茶好了。”
老太叔一听,轰然叫好。服难初时紧绷着脸,但隔了半晌,苦笑一声,道:“这样也好,就当作是他的乳名吧。”
贫僧和尚到了这把年纪,才有一个叫“茶茶”的“乳名”,未尝不是天下间一椿稀奇之至的怪事。
“换命医舍”虽然灯光明亮,但在这一夜,人人的心头都很是沉重。
在医舍外,柳生衙向服难师太道:“晚辈自从离开华山,至今已有数月,如今必须回返师门覆命,小雄和阿玫二人,就有劳师太代为看顾了。”
服难师太叹一口气,道:“满朝奸党为祸苍生,如今国家正处于灾难频盈多事之秋,很需要像你这种有志气的青年侠客支撑大局。八大门派缉捕海世空之事,自从东蛇岛一役后,我也曾屡屡思量,也许八大门派多年以来对海禅王所抱的偏见,着实是太深重了。贫尼越思越想,越是觉得事有蹊跷,但真相关键何在目前却总是说不上来……这样吧,反正贫尼这个峨嵋掌门已做不下去,且待我重回峨嵋山,把掌门一事交待妥当,然后再以自由之身,四出彻查当年种种怪事及悬案。最少,也该把海禅王夫妇离奇暴毙之事查个水落石出,然后才能对海世空此事下个判语,未知柳大侠认为如何?”
柳生衙深深鞠躬,抱拳答道:“师太此举,今晚辈由衷折服。海世空是我结义金兰异姓兄长,师太仗义愿为其先父翻案,晚辈谨此代为谢恩。”
服难叹道:“事情演变会变成怎样,世上根本无人能够逆料,你要谢我,未免是太早一点了。”言下之意,是指“事情两边开”,也许在彻查之后,仍然认定海禅王父子罪大恶极,那时候柳生衙也不能怪责于她。
柳生衙毋惧夜色沉沉,说走便走,马小雄和阿玫知道后,都是依依不舍。
老太叔把马小雄拉过一旁,道:“男儿志在四方,女流躲在一角,小柳要走,切莫挽留。”
马小雄道:“若然我也要走呢?”
老太叔哂然道:“你要走便走,但木小邪的大刀,你有本领保得住吗?”马小雄想了片刻,叹一口气,摇了摇头。
老太叔接道:“这一天,我已把事情想通想透。最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老夫原来并不是十五岁。”
马小雄吃了一惊,道:“莫非只有五岁不成?”
老太叔道:“要是老夫才五岁,又怎能有一个已做了二三十年峨嵋掌门的老相好?”
马小雄心中嘘了一口气,嘴里却道:“二八娇妻一岁郎,老相好比自己老一点点,也不是什么奇事。”
老太叔展颜一笑,道:“老夫疯疯癫癫,也不知道在江湖上虚耗了多少光阴。但不要紧事情已然成为过去,从今日开始,老夫便是老夫,今岁贵庚,虽然他妈的早已忘掉,但反正一定不会只是活了十五岁。”
马小雄大喜,道:“恭喜前辈。”
老太叔道:“你恭喜我什么?是不是恭喜老夫忽然老了六七十岁?”
马小雄道:“恭喜便是恭喜,用不着指定恭喜些什么,总之,前辈从此以后,他妈的喜事重重,连放屁都比旁人更响更臭。”
老太叔大笑:“说得好,要是放屁不响不臭,放来何用?”
大笑之后,脸色忽然沉下,道:“要你拜我为师,你是决计不肯的了。今日做大哥的苦思了大半天,还是认为你做得很对。
“你这一生,可以拜神拜佛,可以拜天拜地也拜太阳拜月亮拜星星,但有两件事绝不能做。
“第一:绝不能拜相。
“当今天子,昏庸无道,无论是谁拜相,都命中注定要做个大贪官。为官之道,不贪不富贵,一贪便遗臭万年。因此之故,在这大宋年代,拜相比拜婊子的大腿还更他妈的不像话。
“第二:绝不能拜我为师。
在很久很久以前,拜我为师是很不错,甚至是很光荣的事情。但老夫老啦,近年以来,更是他妈的又老又糊涂,更喜欢把自己的徒儿一个一个撕开五大块。
“你若拜我为师,我相信一定不会把你撕开五大块,但我相信我自己,那是我老人家自己的事,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因为就连我自己,都不晓得会在什么时候又再变成一个只有十五岁的疯子。
“武功,我是一定倾囊传授的,要是老相好不挟秘自珍,峨嵋派的武功,也要她向你悉心传授。
“峨嵋派的武功路子,虽然有人认为以阴柔为主,甚至是有点娘娘腔,但峨嵋绝学,千万不能小觑。
“峨嵋派开山祖师厄渡神尼,在无定河超渡亡魂之际,创出一套震古炼今之‘中流剑法’,单就以这一手剑法而言,就有极强大之威力。我的老相好虽然做了二三十年嵋掌门,对这一套‘中流剑法’练得滚瓜烂熟,了如指掌,但我知道,以她在这方面的成就,十成中最多只能比得上厄渡神尼二三成左右。
“但这种秘密,江湖上不只有我和她自己知道。论天资,我这个老相好未必便会比她的太师祖厄渡神尼输亏,但厄渡神尼是处子之身,在其有生之年,从没生过孩子。
“但我这个老相好,纵使资质本来比厄渡神尼更佳,却因我的缘故,曾经生下了茶茶。
“她为我生下了茶茶,我是十分感谢的。但她心里可不会感谢我这个老太叔。要不是因为我,她绝不会生了个孩子,要是她至今依然白璧无瑕,她在武功上的成就,绝不会仅此而已。
“有人以为,峨嵋派的武功,也便是女子的武功。凡是有这等偏见之人,统统都是他妈的笨虫。须知天下武功,鲜有男不能练,又或者是女不能练者。即以少林派之大力金刚掌,世人咸以为只有男子汉始能练就,更无知者,甚至以为只有和尚才能练成这种掌功,殊不知自少林派创立以来,大力金刚掌掌力最雄浑者,既非少林僧侣,也不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而是一个住在少室峰下的卖酒妇人。
“这卖酒妇人,颇具姿色,但丈夫忽然一声不响,跑上少林剃度削发为僧。十年后,心痒难熬,悄悄下山跟老婆幽会,此谓之‘僧俗岔口大折腾’。
“夫妇二人,虽则夫君已成为牛山濯濯之和尚,但和尚六根未净,对老婆之要求,也自是无所不允。
“卖酒妇人什么都不央求,只是央求和尚老公传授她一套少林武功。和尚老公心想:
‘要是私自把少林武学传授给妻子,给寺中其他和尚知道,那可大大不妙。’但却又无法拒绝妻子所求,只得把大力金刚掌传授给老婆,心想:‘这套掌法,你这个妇道人家便是长命八百岁,也是练不成的。’
“夫妇二人,如此这般偷偷摸摸厮混了七八年,有一晚,他妈的事机不密,给少林寺一位长老查悉‘奸情’,未几,寺中十余高僧下山,要把那个六根未净的和尚揪出算帐。
“和尚当场被众僧逮住,无所遁形,只得要求还俗。但寺中有数名长老,对这和尚素有嫌隙,得此把柄,如何肯轻轻放过。
经过一轮大战,和尚老公被数大高僧所伤,危急关头,妇人大喝杀出,竟以大力金刚掌连败众僧。更扬言若论大力金刚掌这一套武功,她这个妇道人家犹胜少林寺中任何高手。
“众长老自然不服,公推由当年掌功至为上乘之步雨大师出战。
“步雨大师不愿跟一名妇道人家比拼,严词拒绝,妇人大怒,用月布带挟着一封挑战书遣人送给步雨,扬言要是不接纳此战,天天杀一和尚泄念。
“步雨大师初时置若罔闻,但其后终于接受挑战,于少林寺外与这妇人对掌。但其时,已是一月之后,少林寺僧侣,果然已有三十人死于妇人掌下。
“比掌那一日,少说也有数百少林僧侣在场围观,人人都一致认为,步雨大步必可轻胜。
岂料二人互拼三掌,三掌之后,妇人大笑离去,此后再也没有人目睹她和那和尚老公之踪影。
“倒是步雨大师,在比拼三掌之后,颓然倒下,受创极深。
虽然最后全仗少林方丈以内力抢救,得以不死,但已全身武功尽废,战果令人惊诧。
“要是那妇人用其他门派武功击败步雨大师,虽则令人震惊,也未必便是什么难以想象的奇事,但最令人惊诧的是妇人以大力金刚掌,击败了步雨大师的大力金刚掌!由此可见,许多武功,都不是只有男人,又或者是只有女人才能练成的。
“峨嵋武功,除了中流剑法,也有‘三小绝学’,这便是众所周知之‘小念净心咒神功’、‘小青灯金佛掌’及‘小疯魔剑法’,这些武功,在峨嵋派中,自然只有其门下女弟子才有机会练成。但要是由我的老相好向你倾囊传授,以你的资质,一定会比峨嵋派的女弟子、女尼姑练得更出色。
“总而言之,要战胜姒不恐,必须首先由你开始,三年之后,无论如何一定要击败乌龙茶,这一点他妈的十分重要,老弟子千万不可丢了我这个老大哥的脸。”太叔梵离侃侃而谈,越说越是口沫横飞,兴高采烈。
马小雄却是听得双目发直,道:“义父的武功,说不定已是向我倾囊传授,干妈的武功,也曾向我不断的灌输,还有海蛇大哥,也在东蛇岛上教我一套‘不败神拳’,到了今天,你固然要把一身武功向我这个老弟倾囊传授,也很想峨嵋掌门师太,把峨嵋派的各种武功统统传授给我……他妈的,练武功可不是吃‘九大菜’,可以吃了一道菜又再吃另一道菜。
“别的不谈,便以义父传授我的刀法,那是非常厉害的‘还我山河十八刀’,这一套刀法,便是练它二三十年,也未必及得义父一半那样炉火纯青。
“义父练功,别有一手,他叫我天天抚摸一些死人头发,但摸不了几摸,连东蛇岛摸得陆沉下去,也不晓得是否我这条命太硬,这大盈若冲五层楼都已沉在海底之中。
“那些死人头发尚未抚摸透彻,‘还我山河十八刀’大概连第一刀还不曾练成,正是刀法不成刀法,倏然之间,老大哥又要我练剑,你的剑法固然他妈的十分好看,什么以气御剑,就像是玩弄仙法一样,但你贵庚了?你练了多少个春春秋秋,才能练成这种境界?要是我忽然练剑,‘还我山河十八刀’又要练到什么时候?这还不算,正是多多益善,只要是上乘的武功,便是再练三几百种,想来都是十分划算的。好极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老大哥的老相好是峨嵋派掌门,什么中流剑法、三小绝学,只要你哄得老相好欢欢喜喜,她老人家自然也会倾囊传授……
“哇!真是越想越美妙啦!个个都是当今武林绝顶高手,人人都把压箱底的绝世武功一古脑儿塞入我的脑袋,只要我一一练成了,准会变成天下无敌之绝世高手,但要练多久呢?
粗略估计,最少得苦练三五百年,哈哈,要是真的可以达成愿望,武功高低尚在其次,‘寿比南山’这一句话,倒是非要应验不可。”
老太叔侃侃而谈,马小雄也同样侃侃而谈,一老一少的说话,双方都同样地“很有点道理”。
老太叔沉吟良久,道:“话虽如此,我这一身武功,是绝不会在你身上稍有半点保留的。
但我的老相好,心眼不大,甚至也许会是个死心眼的婆娘。否则,她也不会叫什么服难师太。
服者,服侍也。难者,难缠也。由于服侍此人甚是困难,因此法名就唤作服难。
“你是我的好贤弟,做大哥的,怎么说了要把你栽培成材。
就算你练功不勤,武功练来练去都他妈的不外如是,我也不会把你‘喀嘞’、‘喀嘞’地撕开五大块。总要你争争气气,用老大哥的武功,把姒不恐调教出来的和尚徒儿击败,那便上上大吉,万事胜意。
“但这只是我的想法,常言有道:‘人心隔肝皮’,老相好虽然对我这个老不死关怀备至,但普天之下妇人之心,无不护短偏袒自己的儿女。
“我渴望你能够挫败和尚儿子茶茶,那是以本门声誉站想。但老相好就算嘴里不说话,心中多半渴望她的劳什子琴茶能胜此仗。唉,平情而论,我怎么说也不能怪责于她……只是,乌龙茶武功根基远在你之上,在这短短三年之内,你要胜过老大哥的和尚儿子,却又是谈何容易?但不要紧,在这三年之内,我绝不会让你虚渡光阴,总要你自己发奋图强便可。”
马小雄道:“就算三年后没有这一战,我也不能躲懒,义父、干妈对我期望甚殷,要是小雄马长大之后仍然庸庸碌碌,一事无成,甚至连木小邪前辈铸造的大刀都保不住,岂非罪业深重之至吗?”
老太叔哈哈一笑:“很好,你有这样的壮志雄心,只消假以时日,定然他妈的必成大器。”
又过了一天,金大夫的伤势已渐有好转。服难师太告辞,金大夫把孔有怨唤了过来,当着服难师太面前说道:“有怨,你跟着我已有好一段日子,不能再跟下去了。”
孔有怨大惊:“不!我不要离开医舍。”
金大夫摇摇头:“我的脾性怎样,你应该很清楚,我讲过的话,绝不更改。今日之内,你要是不肯离开这里,明天早上,为师的尸体便会挂在天阶的大树下。”
孔有怨大哭,跪了下来颤声叫道:“师父,徒儿要是做了什么错事,请师父重重惩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徒儿赶出医舍。”
金大夫冷冷道:“你最令我讨厌的,就是动辄哭哭啼啼,为师又不曾死掉,你老是大声哭叫细声低泣的,真是越听越烦。”
孔有怨急急止住哭声,但先前哭得太厉害,一时间要完全收住,也是大不容易。
服难师太把孔有怨扶了起来,缓缓道:“你师父要你离开这里,必有深意,可不是你犯了什么严重的过失。”
孔有怨眼中泪花乱转,幽幽的说道:“师太,你不骗我?”
服难师太叹了一口气,道:“你师父的心意,贫尼是心里明白的,他要你跟着我这个老尼,到外面的世界瞧瞧。”孔有怨听了,一阵怔呆。
金大夫干咳一下,道:“老实说,当年你哥哥孔有恨把你带到这里来,一声不响放下了你便扬长而去,我心中是很不高兴的。
“不但当年心中不高兴,直至如今还是很不高兴,心里总是把你哥哥骂了一百遍之后,又再臭骂了一千遍,一万遍……
“你这个兄长,彻头彻尾的心胸陕隘,自私自利不顾他人死活的家伙,他为什么把你弃而不顾?你以为他是一片好心,让你有机会跟着为师钻研医术吗?
“不!若论医术,你兄长的道行,绝不比我稍逊半分。但他的为人,凤凰无宝不落,你才三岁五岁,他已瞧得出,你和医道无缘。
“世人常言道:‘将勤补拙’,一般而言,补一成两成以至三四成,还是可以的,其成效之高低,得要视乎做什么事情而定。
“但有些本领,某些人无论怎样勤力,就算有百倍愚公移山的精神,也不一定管用。比方说:天生特别肥胖之人,固然也可以苦练轻功,但其成就必然有限,如曰不信,且看千百年以来,武林中以轻功称著的绝顶高手,又有那一位会是身形特别肥大之男男女女?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武学如是,医术也是同样的道理,有怨,说你很愚笨吗?那是不确切的,但一个人聪明与否,和医道是否有缘,却又是另一回事。要是你自幼学的不是医术,而是刺绣,也许,你早已名扬天下。又或者你学的是另一门技艺,仍然很有机会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但你偏偏跟着我学医,单就是这事情的本身,便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你兄长死了,但他活着的时候令我憎厌,但死却死得轰轰烈烈。豪门金庄的公子爷刘复北,其人狼子野心,绝对不容轻忽。有怨,你要紧紧记住,你哥哥是被刘复北所杀的。
“我讨厌你兄长,那是我的事,他是你唯一的哥哥,他惨死在刘复北手中,要是你一直呆在‘换命医舍’,一辈子也不可能为兄长报仇。再说,你根本与医道无缘,便是再在这里浸淫二三十年,也不会在这方面有什么杰出的成就。
“跟着师太走吧,只要有我的一句话,她老人家无论如何一定会把你视如女儿身看待。
也许,有朝一日,你能够用峨嵋派的武功,把刘复北这无耻奸徒歼杀,为你兄长报仇。”说到这里,连声咳嗽,脸色苍白得可怕。
孔有怨怔怔地瞧着师父,知道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他的主意,只得缓缓地点头,道:
“徒儿谨遵师父训诲。”
金大夫又是一阵呛咳,不再说话,转身走向卧室,头也不回。
服难师太瞧着孔有怨,叹道:“人生总是有太多欷嘘之事,你日后年龄增长,就会比现在更能明白人生悲欢离合之道。”
孔有怨目光闪动:“师太,你会把我收为峨嵋派门下弟子吗?”
服难师太摇了摇头:“不,别说是你,就连我也很快便脱离峨嵋派,但不要紧,只要你跟着我,我不但会照顾你的周全,也会传授你上乘的武功,绝不会让你给别人欺负。”
就这样,孔有怨跟着服难师太离开了金大夫的医寓。
又过了一日,太叔梵离也带着马小雄、阿玫告辞。
三人重经吊桥,老太叔道:“三年后,我的老弟便要和姒老魔的和尚徒儿在这里决战,要是吊桥有知,定必大为惶恐。”
马小雄奇道:“要是吊桥有知,却又何惧之有?”
老太叔道:“要是在平地决战,尚且会斗个天崩地裂,区区一道吊桥,又怎不自觉危危乎者也哉?”
马小雄笑道:“高手过招,不一定便会过河拆桥,老大哥幸勿危言耸听。”老太叔呵呵大笑,大步踏前,率先渡过吊桥。
一连数日,老太叔带着马小雄和阿玫,悠悠闲闲地走动,并不急于赶路。
第六日正午,三人到了碧水丹峰,有“奇秀甲于东南”美誉之武夷山。
在山峰下,老太叔精神大振,道:“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本已忘掉此事,如今旧地重临,又再忆起儿时种种旧事。”
马小雄道:“儿时旧事,曾生何事?”
老太叔道:“天天吮奶汁,吮得不够,便吮手指。”
阿玫听了,脸色涨红,老太叔瞧了她一眼:“难道你在儿时不吮奶汁吗?”
阿玫鼓着腮,道:“我是喝西北风长大的。”
老太叔不知道她说的是气话,喷喷称奇,喃喃道:“喝西北风长大的女孩,倒也长得标致。”本篇小说可在公开免费的网站自由转贴。如果读者是在收费会员网站看到这篇小说,说明该网站寡廉鲜耻,把免费的东西拿来骗钱。共唾之。)
到了武夷山城,正要到酒家吃喝充饥,街道上忽然号角长鸣,又有人敲锣打鼓,老太叔眯着眼问酒家店伙;“是谁迎娶新娘子?喜气洋洋好不热闹。”
店伙摇了摇头,道:“这阵子吹的是‘夺命号角’,敲的是‘勾魂锣’,打的是‘送命鼓’,可不是办什么喜事。”说犹未了,街道转角处已冒出十余名身穿白袍,人人脸上涂上朱砂和墨汁相间的汉子,中间挟持着一名女子,由木车以驴子拉动,直往城中一片广场走去。
老太叔瞧着那个女子,道:“虽然比不上我的老相好,却也不失是个漂亮的人儿,她犯了什么罪?是不是谋杀亲夫?”
店伙摇了摇头,道:“不知道。”
老太叔瞪了他一眼,道:“你的脑袋有什么问题,怎么老是摇来摇去?”
马小雄和阿玫已走入酒家中,听见街中鸣锣喝道,双双钻出来探头探脑。乍然望见被押送至刑场的女子,不禁面色齐变,大大吃了一惊。
原来那名女子,竟然便是昆仑派门下的霍椒萍。
在东蛇岛陆沉后,海世空带着霍椒萍乘船重返中土,却在大海中遇上聚英堂战船,双方在怒涛汹涌大海上展开舍死忘生大决战,其时,马小雄和阿玫置身在小舟之中,与数艘大船越漂越远,海世空和霍椒萍的命运如何,二人一直不得而知。
便是柳生衙、乔在野二人,在战乱中也和海世空、霍椒萍各散东西,自此音讯隔断。
想不到在这武夷山城,竟然看见霍椒萍被押送至刑场,但瞧那些白袍汉子,又不像是官府中人,内里情况怎样,着实耐人寻味。
老太叔见马小雄和阿玫瞧得目不转睛,神情有异,不禁眉心一皱,道:“难道你们认得那个女子吗?”
马小雄立时点点头,道:“她是昆仑派的女弟子,是海蛇的红颜知己。”
老太叔瞪目道:“海蛇?谁是海蛇?”
马小雄急道:“总之,海蛇便是海蛇,他是小柳的结拜兄长!”
老太叔“喔”的一声,道:“既是小柳兄长的红颜知己,自是非救不可。”
老太叔自恃武功厉害,立时便要冲出长街救人。忽听一人的声音在侧响起,沉声叫道:
“前辈且慢,这是敌人布下的陷阱!”
老太叔向左侧一望,只见一名中年汉子,也像是马小雄和阿玫一般,不断地在探头探脑望向长街那边。
老太叔瞪了他一眼,道:“你是何方鸟物?”
汉子道:“先父海禅王,我便是海世空。”
老太叔半信半疑,马小雄和阿玫已凑了过来,齐齐叫道:“海蛇大哥!”海世空与二人重逢,虽在忧患之中,脸上仍然露出喜不自胜之色。
海世空带着三人,自人丛中左穿右插,片刻间,已到了广场西方。
只见在广场中央,搭起了一座高约两尺的木台,台上布满柴枝,浸透火油布料等物事,霍椒萍已被绑在木台中间一条木柱上。
台下十几名白袍汉子,人人手持火炬,只要其中一支火炬抛向台上,霍椒萍立时就得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老太叔道:“绑在台上的,是不是你的……嫩相好!”本想说是“老相好”,但瞧见霍椒萍远比自己的老相好年轻得多,最后语锋一改,变成了“嫩相好”。
海世空一愣,接着说道:“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子,要是她死了,我也不能独活。”
老太叔眉头一皱,道:“自古多情空余恨,看来你的头脑,跟你的老子一样,总是混混沌沌,不太清醒。”海世空默然无语,只是默默察看四周形势。
老太叔闷哼一声,道:“你的嫩相好快要变成一团焦炭,你怎不上前勇救佳人?”
海世空道:“敌人早已布置机关,只要我一动手,最少有十个弩箭机括铁匣同时发射,把椒萍变成毒弩下的刺猬。”
老太叔哈哈一笑:“倘真如此,你的嫩相好便是天下间最美丽的刺猬。”海世空脸色一沉,但没有发作。
未几,城东那边,又是一阵喧闹的锣鼓声传了过来。
老太叔眉头一皱,道:“莫不是又一个嫩相好押送过来?”
但这一次,境况和先前大不相同。
同样是吹吹打打,同样是鼓乐喧天,但来到广场的并不是行刑队伍,却是一顶大红花轿。
花轿前面,一人骑着骏马,笑脸吟吟,是个喜上眉梢,国字嘴脸的新郎倌。
花轿前后左右,不是脸上涂粉三寸厚屁股比竹箩更大的喜娘,便是陪嫁丫环,仪仗队八音齐全,到了广场附近,更是沿途大放鞭炮,远比先前的行刑队伍热闹得多。
老太叔道:“这新郎倌怎么有点像是乔镜花的弟弟?咦?看来也不只是像而已,根本就是他!”自从他疯疯癫癫以来,很多事情很多亲戚朋友都在他脑海中消失得一千二净,但对于乔镜花,他是始终不曾忘怀的。
乔镜花的亲弟弟,便是“在朝在野,在公在私”的乔在野。
乔在野曾受重创,全仗乔镜花、孔有恨二人联手抢救,方始保住一条性命。其后,更因为乔饮反怀身内力贯注在他身上,武功更胜从前。
一看见这新郎倌,海世空、马小雄都是心中有数,知道强援已到。只有阿玫,有点莫名其妙,居然问道:“乔大侠怎会在这里做了新郎倌?新娘子是谁?”
马小雄道:“不是嫦娥便是钟无艳,再不然便是把你抬入轿子里充当新娘子。”阿玫知道他在取笑自己愚笨,鼓起了腮不再说话。
这时,广场上被绑住的霍椒萍,忽然发出一声尖叫:“乔大侠快走!”叫声未已,广场东南方、东北方双双杀出一群紫衣武士及银衣武士,人数少说也逾百之上。
那一群紫衣武士,为首一人,年逾六旬,又肥又矮,右手早已给仇家砍了下来,换上一支用“乌金精钢”打造的钢爪,正是来自兰州之聚英堂高手“爪爆心肺”莫穿肠。
至于另一群银衣武士,统率者更是聚英堂之“铁血军师”
严慕。
乔在野曾在大海一战,会过莫穿肠这个肥矮老者。其时,聚英堂声势浩大,高手如云,乔在野苦战莫穿肠,但也只是激战了十几招,便在混乱中各散东西,与其他强敌继续周旋。
双方剑拔弩张,广场上杀气腾腾,但处境最凶险的还是霍椒萍,在木台下,有十几支火炬,也有十几个毒弩匣,只要有人一声令下,无论是星星之火,抑或是一排毒弩,都是足以在顷刻之间取了她的性命。
严慕却在喝令:“不得妄动。”这道命令,是向木台下的白袍汉子施发的,霎时间,气氛更是凝重而诡异。
这时候,双方的锣鼓声、号角声、丝竹管弦声全都偃息下来,广场上虽然人头涌涌,竟在霎眼间变得鸦雀无声,只有火炬燃烧时所发出“必卜”不绝的奇异怪响。
严慕嘿嘿一笑;轻轻摇动羽扇,道:“乔大侠,欠违了。”
乔在野翻身下马,抱拳笑道:“有道是冤家路窄,难怪在海上遇见军师,在山城中也遇见军师。”
严慕道:“明人面前不说暗话,乔大侠虽然一身新郎倌装束打扮,不见得今日便是乘龙之喜。”
乔在野笑道:“挂羊头卖的不一定便是羊肉,跟着新郎倌背后扛着的大红花轿,里面坐着的也许只是一个畜牲。”这一番话,甚是奇怪,有好事者忍不住嘲笑:“这岂不是说自己讨了一个畜牲婆娘为妻吗?”此人只是城中百姓,平素口舌招尤,这时候恶习难改,一句刻薄话才喷出口,脑袋已给一把锋利大刀砍了下来。
倏然出刀杀人,为乔在野出了一口鸟气的,竟然是那个脸上涂粉三寸的喜娘。
她原本手里只有一把葵扇和大红手帕,谁也瞧不见她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把三四十斤重的大刀。这把大刀,虽然远远比不上木小邪铸造的那一口,但却也绝非凡品,用来砍掉一个人的脑袋,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严慕冷冷一笑,道:“想不到乔大侠饮誉江湖,一直与阴山幽冥宫之邪派魔徒互相勾结,只因一言半语听不进耳中,便无辜滥杀平民百姓,着实令人生叹。”
这时候,马小雄、海世空方始认出,那个怪模怪样的喜娘,赫然竟是“丰都刀使”包奈何乔装所扮。
乔在野还没开口,包奈何已怪声叫道:“我是‘丰都刀使’,一天不杀人就得瘦上三斤贱肉,你要是瞧的不顺眼,我便把轿子里的杂种一刀剁翻,瞧瞧你怎样回去向朱腼覆命。”
严慕脸色一沉,不再说话。
倏地,一人大步走向包奈何那边,冷喝叫道:“姓包的,老莫来会一会你!”正是兰州“爪爆心肺”莫穿肠。
包奈何手握大刀,声音更是阴阳怪气:“我道是谁上前送死,原来是‘狼心狗肺’莫老九,你在‘兰州九恶’之中排名第九,武功也是第九,但你可知道其余八恶,都已成为包某刀下无头之鬼,统统送入丰都城会见阎王去也?”说得似模似样不明就里之人,每每信以为真。
但事实上,莫穿肠并非什么“莫老九”,天下间也没有什么“兰州九恶”,既无“九恶”,又如何会有“八恶”成为“丰都刀使”
刀下无头之鬼?
莫穿肠脾性猛烈,但若要跟包奈何作口舌之争,那是远远比不上对方的。一怒之下,也懒得分辨和对骂,“呼”的一爪,直袭包奈何胸前。
他右手已断,换上了一支乌金精钢爪,招数之凶猛狠辣,令人心头颤栗。
此际,莫穿肠含怒出爪,势道迅如骇电,钢爪直抓进去,但却虚中套寮,实中带虚,究竟是虚是实,端的令人无从揣测,防不胜防。
包奈何桀桀怪笑,振臂挥刀,斜身转腰,竟是慢中有快,巧中带轻,刀虽沉重,人却稳捷轻灵,宛若东风戏柳,又似是蜉蝣乱舞,变化悠忽,丝毫不比对手逊色。
莫穿肠身移步换,左足斜踏中宫,横里一招,电光石火般一爪斜插包奈何右腕的关元穴。
包奈何一声冷笑,身形急变,提腰劲一式“老鹰翻云”,以背对背之势避过莫穿肠的钢爪。
莫穿肠背对包奈何,但仍能以左肘拳猛撞敌人背心。这一撞奇快无比,包奈何招式用老,再难闪避,“蓬”然一声中招。
高手比拼,强弱高下,双方都是心中有数。包奈何虽然甫落下风,但已知道再战下去,必然不及对手,蓦地大刀以大轮回之势旋转式疾扫对方腰间。
莫穿肠成竹在胸,瞧出包奈何这一刀是情急拼命招数,突然身如陀螺急转,比包奈何的大刀旋转得更快两倍。
莫穿肠身手疾迅无匹,钢爪倏然迳扫包奈何下盘。
包奈何刀挟劲风,也向下三路反扫过去。岂料莫穿肠这一爪竟是诱敌之势,包奈何刀势一沉,另一支手已霍地插向他胸口疾插而入。
这是左爪。不是钢爪。
但这一爪,才是最致命的一击!爪爆心肺,又何必非要用钢爪不可?触目惊心的一战,在众目睽睽之下爆发和了结。
包奈何败了,这位“丰都刀使”死于“爪爆心肺”,他的心脏和右半边肺叶,都给莫穿肠的左爪完全抓碎。
莫穿肠直挺挺的站着,左手缓缓地从包奈何的胸口抽出。
包奈何心脉已停,眼睁睁地瞪视着莫穿肠气绝毙命。莫穿肠眨了眨眼,伸手轻轻一推,包奈何仰天倒下,死不瞑目。
莫穿肠胜了一仗,面露得意之色,乔在野冷冷一笑,道:“姓莫的,可知道包奈何的义父是谁?”
莫穿肠用舌头舐着左爪染满的鲜血,道:“总不会是乔大侠吧!”
乔在野却点点头,道:“偏偏他便是我的干儿子。”
莫穿肠冷冷道:“简直胡说八道,论年纪,包奈何比你还要大上好几岁。”
乔在野摇了摇头,道:“你弄错了,包奈何看来年纪不轻,但却着实比我还细小四岁,只是一般目光如豆之辈,决计瞧不出来。”
莫穿肠冷哼一声:“便是你比他大四岁,也没资格把他收为义子……”说到这里,倏然住口,知道中了乔在野的奸计。
果然,乔在野哈哈一笑,道:“说得真妙!尊驾言下之意,是说年纪相差四岁,绝不该成为一对父子,要是真有此事,未免十分混帐,对不?”
莫穿肠怒道:“混帐!”才骂出口,脸色又自一变。
他这一句“混帐!”,骂的是乔在野,但乔在野立时打蛇随棍上,大声道:“对了!就连你也认为父子二人年纪相差四岁十分混帐,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莫穿肠连连摇头,怒道:“姓乔的,老子……毙了你!”悍然出招,攻势有如排山倒海,绝不留情。
乔在野哈哈大笑,虽然眼前漫天爪影,形势凶险绝伦,但他身形飘忽如风,左一兜,右一绕,时而在东,霎忽在西,竟在爪影重重之下乘隙罅左穿右插,更在众目睽睽之下朗声说道:“莫兄虽然对在野动手动脚,看来很不客气,但心底里早已把在野引为良朋知己,连说话都同一鼻孔出气。天下间那有父亲只比儿子大上四岁之理?
“咦?……话可不是这样说,一百八十年前,石敬瑭叛,向塞北辽帝耶律德光求助,答允割让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献给辽国作为报酬,其后果然叛变成功,燕云十六州固然尽入辽贼之手,石敬瑭也被耶律德光封为后晋皇帝。
“千百年以来,炎黄子孙拼命修筑的万里长城,就是因为黄土地上出了石敬瑭这一号人物,而完全失去抵御外敌的功用。从边界直至开封府遥遥千里,变成敌人铁骑恣意奔驰的广天平原,大好江山门户只因一人之念而完全洞开。
“到后来,石敬瑭以四十七岁高龄,尊称只有三十七岁之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可算是蔚为奇观之至。
“若照此推算,朱腼虽然只比朱庭校大了四岁,但毕竟还是做父亲的比做儿子的年纪稍大,也不能算是太过分,就算是混帐,充其量只是有点混帐,怎么说也比不上耶律德光与石敬瑭这一对父子吧!”
乔在野一面从容应付莫穿肠,一面侃侃而谈,左兜右转,始终不离打蛇打在七寸上,既把朱腼和朱庭校这一对“父子”
的关系重重地揶揄一番,也用语言牢牢地套住了莫穿肠,“诬陷”他一条“嘲讽”苏杭奉应局总办朱腼与朱庭校的“罪名”。
朱腼是朝廷“重臣”,朱庭校更是小器暴戾,行事手段冷血无情之徒。乔在野以唇枪舌剑,把这条“罪名”无中生有地套在莫穿肠的头上,明眼人固然心中一片雪亮,但是非每每皆由辗转相传,日后传入朱腼耳中会变成怎样的一回事,又有谁能保证?
石敬瑭是人人恨之入骨的大汉奸。凡是稍有血性之汉人,无不深痛恶绝。
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石敬瑭是沙陀人,并不是汉人。
乔在野言词之间,固然把莫穿肠弄得恼怒慌乱,也把朱腼和朱庭校这一对“父子”尽情嘲骂。
——石敬瑭固然不是汉人,朱庭校原本也不姓朱,而是姓潘。但为了更能迎合“父亲”,索性数典忘宗,不姓潘而改姓朱,变成了“朱庭校”。
莫穿肠曾与乔在野交手,二人武功约在伯仲之间,岂料事隔不久,二人再度展开恶战,莫穿肠倾尽全力,非但未能稍占上风,更着着缚手缚脚,简直是任由鱼肉。
他越战越是胆颤心惊,招数渐见紊乱。乔在野不再客气,突然掣剑在手。他原来的兵刃,已在大海中丢失,但乔镜花又送给了他一把“诺诺剑”。
“诺诺”便是顺从的意思。除了一把“诺诺剑”之外,还有一本“诺诺剑经”。
乔镜花道:“诺诺剑法并不是霸道的剑法,相反地,这是顺从着别人而施展的剑法。别人,也就是你的敌人,敌人的招数怎样,这一手剑法也就会相应地顺着对方的意思而作出变化。
以剑法而言,这并不是上乘的剑法,但用来对付凶狠的敌人,每每能奏奇效。
“诺诺剑法”一经施展,莫穿肠反而感到压迫力大减。当下心中寻思:“这小子的武功,想来已是黔驴技穷。”恶念骤起,钢爪招数倏地倍加狠辣。
殊不知道,这一手“诺诺剑法”,便如同“棉里针”功夫,敌人的招数越是阴毒凶险,这种剑法的威力也就越更强大,莫穿肠不明其理,本身招数一招比一招更凶悍,也就等同把“诺诺剑法”带引至比他更凶悍的招数之上。
莫穿肠身形急速抢扑,钢爪咄咄逼人,但他出招越狠,乔在野的剑也就“顺着其势道”
反击过去,不出十招,诺诺剑已斜斜地从莫穿肠左耳上方刺入,剑锋向右下方颈项透出。
莫穿肠比此际招式用老,钢爪伸尽,险险还有三分便插入乔在野胸膛,但也就只是这两三分距离,他永远伤不了乔在野,反而死在诺诺剑之下。
莫穿肠、包奈何先后战死,双方互有输赢,但形势更见凶险。尤其是木台上的霍椒萍,生死只是系于一线。
莫穿肠倒下之后,“铁血军师”严慕干笑一声,目注乔在野朗声说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闲话少说,咱们做个买卖算了。”
乔在野哈哈一笑,忽然把大红轿门打开,只见轿内坐着的,并不是凤冠霞帔的新娘子,而是浑身一丝不挂,更被牛筋索牢牢绑得像大粽子的朱庭校。
严慕脸色一沉,立刻传令手下战士,把一袭长袍送过去,让朱庭校包裹着身体。乔在野也不阻拦,只是冷冷的道:“朱将军身上的衣服,并不是咱们脱掉的,只因为当咱们逮住朱将军之际,他正在强暴一名良家妇女,总不成要咱们动手为他穿上衣服,然后才再捆绑起来。”围观百姓听了,无不哄然耸动。
严慕沉声叫道:“单凭你片面之辞,岂足相信?”虽然心中把乔在野的话,信了个九成九,但形格势禁,只得当面苦苦抗衡。
------------------------------
drzhao 扫校, 独家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