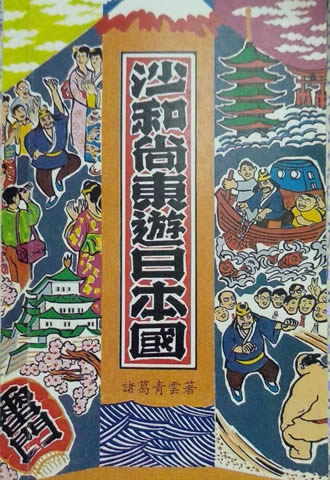梁夫人的邀宴时刻,却是下午时刻。
郑雷这时的功力,只要能调息片刻,足抵一夜睡眠,但郑夫人却爱子情深,于中午睡醒后见爱子仍在堂屋中踱步,非勉强叫他去床上小睡片刻不可。
在不敢违背慈亲的吩咐下,精神焕发的郑雷只有解衣再到二老卧室中,上床休息假寐,只是他脑中想的完全是梁夫人的一切,等待着对方邀宴,哪里还能睡得着?
在翘首等待中,外屋果然响起了丫环的声音。
听到是来邀宴,郑雷连忙一跃而起,迅速穿好衣服,走出卧室,只见这丫环正是昨日侍随梁夫人一对侍女中的一个。
那侍女一见郑雷出来,嫣然一笑,盈盈一福,道:“主母命奴婢问候公子安好,并要奴婢引请郑老爷及夫人、公子赴宴。”
郑昭烈忙道:“夫人也是太客气了,犬子并非外人,何必如此多礼!”
青衣小婢口齿极为灵活,娇声回答道:“主母说,家宴并无佳肴,只是为郑公子聊表洗尘之意,万望二老勿却!”
郑雷满心疑窦,巴不得立刻能见到对方,痛痛快快地试探一番,恐怕老父再虚应故事,拖延时光,忙接口道:“夫人盛意难却,小可与双亲受之有愧了,就劳姐姐引路!”
青衣小婢含笑道:“那么三位请随奴婢来!”
说完转身出房,莲步跚跚,向后进院落走去。
郑雷紧跟着青衣小婢走去,目光却不时环扫,打量着环境,感到屋宇之深广,超过了昨夜潜入时的感觉估计,但这许多屋子,却极少发现家人,气氛显得非常清新。
他这时不由边走边向青衣小婢搭讪着:“贵府这么大庄院,怎么极少见到家人,夜间你们不觉得害怕么?”
青衣小婢回眸一笑道:“主母怕人多嘈杂,故不愿多雇人,不过听说令尊是位大剑客,有剑客同住,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郑雷顿时默然。
转眼已穿过三进,到了第四层院庄,只见一座四丈见方的天井,迎面是座暖厅,那梁夫人正弱不禁风,站于厅口,由三位青衣小婢扶着,似在鹄候,一见郑雷父子,便扬声娇笑道:“佳肴已上,贱妾恭迎二老及公子入席。”
这时郑雷微缓步伐,依礼让父母上前答礼,郑昭烈忙拱手施礼道:“夫人宠召,老朽及拙荆犬子只有领谢了!”
施礼毕,父子三人同时入室,郑雷目光一掠,这座暖厅布置得极为富丽堂皇,壁上挂满了名人书画,一边尚有许多玉器古物,家具是雕花檀木所制,一切装饰果如富豪之家一般,此刻厅中已放了四条长案,长案面面相对,各据一方,案上早放满了热气腾腾的佳肴。
郑昭烈父子背对厅外,各据一案落座,那梁夫人高据正中,立刻殷勤劝酒。
酒过三巡,郑昭烈首先起立道:“老朽有一事相求,未知夫人能赐允否?”
梁夫人颔首道:“什么事?”
郑昭烈道:“老朽想暂时离开夫人!”
话尚未说一半,梁夫人脸色微微一变,沉声道:“郑老忘了昔日之言么?”
郑昭烈叹道:“君子重诺,老朽岂能忘记。只是,唉!最近江湖一段风波却牵涉老朽名声……”
梁夫人微微一笑,打断郑昭烈的语声道:“名声只是身外之物,万事若能忍让一步,未必不是福气,郑老何苦动这份闲气?再说贱妾自遇你老,自思不能一日或离,想贱妾自夫死以后,偌大院落,无人管理,唉!你老忍心抛下贱妾不管么?”
这番话无疑是拒绝不准,只是她婉转说来楚楚可怜,令人不由顿生怜悯之心。
郑昭烈颓然长叹,默默落坐,郑夫人似对梁夫人恩犹未忘,更不愿多言,可是郑雷心头却是一份怒火,他感到梁夫人断然拒绝,似有其他原因,可是却找不出她话中漏洞,他想自己父亲在武林中是具有何等地位,岂能雌伏人下,为人当护院?可是想起父亲早已许下的诺言,空自一腔怒火,即无处发泄。
这刹那,他昨夜对梁夫人的许多疑念,又在脑中回旋起来!
于是,他觉得不能再放过这种机会,也顾不了什么礼节,一手执着酒壶,离座走到梁夫人案旁,沉声道:“小可还有几句话要说,只是在未说之前想亲为夫人斟酒,聊表夫人医治家母之德!”
梁夫人一怔,盈盈起立道:“些许小事,公子何必多谢!”
郑雷鼻中一哼,酒壶一倾,注满桌上酒杯,双手捧起,向梁夫人面前一送道:“请夫人饮此一杯!”
话虽说得恭维,但却有非饮不可的意思。
梁夫人似是盛情难却,罗袖轻举,也伸出一双柔若无骨、莹白如玉的纤手接杯道:“那贱妾就遵命了!”
岂知郑雷此刻却是想试试梁夫人究竟会不会武功,待对方手方接杯刹那,左右双手的食中双指倏然戳出,灵巧地向梁夫人腕脉“七寸”、“寸关”两重穴戳去。
这一突然出手,在他想,若对方是武林人物,必会回避,或有其他反应,要知道这两处血穴,一被重手法封死,照样能逆血攻心,致人死命。
哪知梁夫人视若无睹,非但毫无缩手之意,脸上仍保持着端庄的笑容,使郑雷微微一愕,指锋刚触到对方肌肤刹那,猛然一吸真力,双手执壶而退。
他虽然丝毫不露痕迹,但是心中却暗暗震惊,对梁夫人更觉高深莫测起来,因为以对方的视若无睹只有两种可能,一就是她确实不懂武功,二是她宁受一指也深藏不露。
若属前者,当然一切疑窦,完全冰解,若属后者,郑雷感到梁夫人那份镇定如恒的胆魄,太令人可怕了。
但不论怎么猜想,目前他依然不能确定对方是否会武功。
此刻梁夫人饮罢杯中酒,缓缓落坐道:“公子有什么话要说?”
郑雷拱手道:“小可仍代父请命,小可虽知家父曾有诺言,不离开夫人左右,但此事非同儿戏,家父不得不出面了结。”
梁夫人微微笑道:“郑公子不是也身怀绝技么?为何不替令尊分忧?”
郑雷一惊,忖道:“她的话是暗示早已看清我方才那一手呢?抑是仅表示拒绝?”
心中想着,口中道:“夫人谅必也知道江湖俗事了?”
梁夫人神色怔了一怔微笑道:“贱妾极少出门,怎知江湖俗事是指些什么?”
郑雷冷冷道:“可惜夫人不了解江湖人物的一切,否则小可正想把家父非要离去的理由,奉告夫人……”
“啊!你不妨说来听听,贱妾虽不懂江湖人物终日所为何事,但也可作常理推测,何况公子说得如此严重。”
郑雷早已想说,闻言神色凝重地道:“家父蒙凶嫌之冤,而那人人痛恨的凶手却如雾中幽灵,匿而不出,被害者家属却认为家父不出,更加重了疑心,夫人认为家父该挺身而出么?”
“哦!贱妾是一向信服老庄之学的,耳闻不听,问心无愧,心安所居,又何必多费口舌!”
“哼!别人想的可不是那回事!”
“那么公子应该尽力侦查啊!”
“小可侦查过,而且已有眉目。”
“哦!是谁啊?”
“花衣死神!”
“花衣死神,好动听的名字,‘花衣死神’是谁呀!”
郑雷目注梁夫人,一瞬不瞬,沉重地道:“是个女子。”
“唔!竟是女的?”言中极为惊奇。
“那女子也如夫人这般年纪,只是面蒙纱巾,行动神秘,令人无法见到她的庐山面目。”
“哈哈,公子说是像贱妾一样?”
“不但身材与夫人一样,而且其他方面很多与夫人有相似之处!”
“唔!贱妾益发好奇了!公子说的是哪一方面?”
“譬如说夫人喜于捕蛇、养蛇,那神秘女子也善于养蛇!”
“还有么?”
“尤其‘金须蛇’系天竺异种,听家父说,若不懂特别捕捉之法,反易受噬,而夫人竟能伸手即擒,这一点,仔细想来,又与那蒙面神秘女子能纵奇蛇,不无相同之处!”
“哈哈,以郑公子所说,贱妾竟是那凶手化身了!”
郑雷目闪奇光道:“小可确实如此怀疑!”
陡听得郑夫人厉喝道:“雷儿,你岂可如此冒渎夫人!”
她对梁夫人确是满怀恩德,神色之间,满是恭敬,一听儿子愈说愈不像话,故而喝止。
郑昭烈却是若有所思,听若不闻,似乎也对梁夫人起了疑心,因为他耳闻江湖上出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事,不得不对这位恩人重新估计。
郑雷一听母亲喝止,慌忙道:“孩儿不敢……”
话说一半,却见梁夫人愉快地笑道:“郑夫人不必认真,贱妾未闻江湖事,只当作山海经奇谈,听来却也有趣。”
说完又是一阵愉快的娇笑。
郑雷试探不出丝毫反应,暗暗纳闷,心念一转,道:“夫人养这么多蛇,不知作何用处?”
梁夫人笑道:“补品之中,以蛇为最,令堂大病初愈,宜适时进蛇羹,这全是为令堂啊!”
郑雷望望母亲,默然无言,现在,他觉得没有什么话好问,除非再发现什么疑窦,线索似到此已经中断。
他心中不禁暗暗一叹,费尽心思,想不到今天仍是毫无头绪。
而梁夫人这时依然保持着一份愉快的笑容,她似乎对郑雷意有所指的话当作谈笑,说过就忘,此刻对郑氏夫妇,频频劝酒吃菜起来。
于是郑夫人欣喜地回敬着,气氛似乎已畅快起来。
这一席酒吃得宾主尽欢,直到上灯,才宾主尽欢而散。
不,若真说宾主尽欢,只能指梁夫人及郑夫人,郑昭烈心事重重,完全在虚应场面,至于郑雷,就更不用说了,因心有所疑,脑有所思,简直是味同嚼腊,不知吃在肚中的东西,是什么滋味。
酒席散后,父子二人回到前面二进院落的房中,郑夫人似已不胜酒力,入室先卧,外室中只剩下父子二人,郑雷心事重重,倏然对父亲道:“爸,你以为梁夫人可疑吗?”
郑昭烈没有吭声,仅点点头。
郑雷见状一惊,急急道:“既然你老也认为如此,身在虎口,孩儿认为你老应该考虑一下离去的问题了!”
郑昭烈若有所思地道:“仅为了是怀疑么?”
郑雷灵机一动道:“孩儿认为你老离去,等于是对她一种考验!”
“考验?”
“嗯,孩儿暗自觉得那‘花衣死神’除了面目不觉外,简直像极了梁夫人,而这位梁夫人与那神秘女子也有许多无巧不巧的相同地方,只是唯一令人不敢确定的,就是她是否身怀武功,若是深藏不露,无疑与孩儿的判断又接近了一段距离,因此你们二老离去,若梁夫人是那蒙面女子,她必会追寻二老,露出身份,否则,孩儿觉得你老,就先入江湖,与孩儿查缉到那‘花衣死神’,再来履行诺言不迟!”
郑昭烈听完,微微一笑道:“雷儿,为父的意见与你完全相反。”
“相反?难道爸不想……”
“不,孩子,你听我说,就因我要对梁夫人重新估计,因此决定与你分头并行,个别查探‘花衣死神’是谁,不难水落石出。”
郑昭烈说到这里,深思道:“昨天我听你说过‘通天手’贾谊行临死时曾留下血书?”
“不错,血书是:欲问死神是谁,即按‘骊龙双珠’……”
“对了,为父也曾听说过世上有这么一对宝珠,是罕见奇珍,贾谊行既留下此言,分明表示此珠在他身上,或许已被魔君所得,则从这对‘骊龙双珠’上,必有什么线索可寻,你难道忘了么?”
“嗯!不错。”
“茫茫峡近在咫尺,你应该从这方面着手,至于此地的疑窦,由我负责,结果如何,我们不妨互换消息,再行探讨,这样比你死盯在一点上,要有收效得多。”
郑雷精神一振,道:“爸果然好主意。”
郑昭烈道:“所以我认为耽下去应该比离去更佳,孩子,你认为然否?”
郑雷欣然道:“爸说得不错。”
话方说一半,陡见父亲目注纸窗厉声喝:“谁在窗外窃听?”
右手迅扬,一道掌劲,猛向紧闭的纸窗拍去。
轰然一声,纸屑纷飞,窗户猛开,夜空荡荡,窗外哪里有人?
但在这刹那,郑雷眼角却瞥见前厅屋脊上一个黑影,迅速而逝,他想到自己与父亲商量的计划,竟然被人窃听,心中哪肯甘休,口中忙道:“爸,你照顾母亲,孩儿追敌!”
语声中身形已如箭一般,嗖地穿窗而出,向前厅屋脊扑去。
余音未了,人已一闪而隐,这份轻功看得郑昭烈暗暗感叹,觉得后生可畏!
但是等郑雷扑上前厅屋脊,却见那个神秘的黑影已在前院松林掩映中越出围墙。
这时,他岂肯放松,猛提真元,纵身衔尾而追,这样一追一逃,刹眼出了庄院,那个黑影的速度,竟不在郑雷之下,若不是郑雷此刻功力大非昔比,早已看不见对方人影了。
但是此刻,那人影已在三十丈外,若非目力强的人,在这黑夜中,几乎无法看清,更不用说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了。
郑雷心头急怒交迸,身形如电中,口中不禁大喝道:“朋友,你有种留下来!何必鬼鬼祟祟?”
那一丝闪闪隐隐的黑影却听如不闻,一味向前急掠。
郑雷追着追着,心中倏然更加惊奇了,因为他此刻才觉得对方飞遁的方向,竟是“金面魔君”的巢穴——茫茫峡。
郑雷本就要进茫茫峡,索性提聚全身真力,一味穷追。
追到双峰夹峙的山道上,郑雷目光一眨,竟失去了跟踪目标。
但是因为眼前并无岔路,更无隐藏之处,除了进茫茫峡之外,毫无遁失之误,所以郑雷并不停留,认为对方快了一步,更加疾身形向前飞驰。
果然,不出十丈,前面有了黑影,他心中方自一喜,倏又一怔,因为那黑影此刻不但未逃,反而是迎面急掠而来。
双方速度皆极快,瞬眼接近,郑雷目光一瞬之下,不由一愕!
是谁?嘿!竟是“金面魔君”座下的“落魂阴炼”莫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