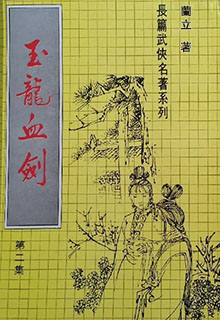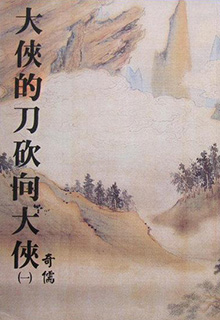那少年双眉仍然不展,望着雷洪,又作了个无声之叹,说道:“不错,你我从未见过面,但小弟却已久仰雷兄为人并受人之托,将薄技相赠。”
薄技相赠?雷洪闻言一怔!那少年已又继续说道:“若雷兄不嫌弃,更恕小弟冒昧,即请现下开始如何?”
那雷洪乃是个豪气干云的少年,他不如人,尚无多大难堪,今竟说要传他武功,这不等于说他武功不如人么?
当下哈哈朗笑,道:“这么说,兄台武功绝高了,倒不知要传小弟何技?”
那少年忽然一叹,道:“雷兄千万不可见怪,小弟不是说过了么,这乃是受人之托,并无丝毫有瞧不起雷兄之处。”
雷洪闻言又是一怔,心道:“莫非这又是寒梅妹妹的意思,我倒不能辜负她了。但她怎知我自离开她后,武功已倍增了呢。”忙道:“兄台乃是一番好意,小弟哪敢不识好歹,小弟这里领招了。”
那少年点了点头,道:“授命于我的那人说过,别样武功,我并不及你,唯有轻身功夫,小弟勉强能胜一等,命小弟相赠的,亦即是这点薄技。”
雷洪登时肃然,适才他自石上飘落,已可见他轻身功夫了得,自己实远不及他。忙躬身一揖,道:“兄台厚意,况又受人之托,小弟敢不拜领。”
那少年说道:“好在此间人迹罕至,就在此处吧。”
雷洪侧立,道:“小弟候教。”少年道:“我赠雷兄这点薄技,其实小弟亦不过才得皮毛,但雷兄智慧过人,闻一必可知十,举一定能反三,非常成就,指日可待。”
雷洪心道:“你好大口气,你能传我甚么旷世武学,敢说便有非常成就?”心中虽是不服,但知这是秦寒梅命他所赠的,他岂能辜负她的好意,道:“兄台过奖了。”
至到此刻,雷洪连他姓甚名谁也未谈起,是他对这少年,心中自然感到酸酸的,那少年已又说道:“其实小弟所赠,不过是简单的几种步伐,但望雷兄勿等闲视之,久之必有妙用。”
雷洪更是不信了,简单的几种步伐,竟会有妙用。那少年分明看出他有不信之意,但却有如未见,忽然面露肃容,道:“我知雷兄武学渊深,现我先说口诀。”
说至此,只见他更是正心诚意。那庄重之态,更见严肃,雷洪不自觉亦是肃然而听。
那少年一字一字,慢慢说道:“变化之道,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是太极而生两仪,太极,道也,两仪者,阴阳也,氤氲交感,变化因而穷,阴阳之动,爻也,阴阳之道,卦也,卦之同奇耦,爻之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
少年说这口诀之时,不但一字一吐,而且每念一句,必重复三遍,雷洪可是听得忘了惊讶,越往下听,越觉奥妙无穷,幸好他悟性过人,那少年三遍而后,他已牢牢记在心中。陡听他又说道:“雷兄记住了口诀,现在我再演练一遍。”
说罢,即在草地上缓缓而行。雷洪一面默诵口诀,一面仔细地瞧,只见他虽是缓缓而行,但每一出步,竟皆三爻六变,九转十二象,那身形简直不能捉摸。
雷洪惊喜也忘了,竟几乎不相信竟有这么神奇的步法,其实雷洪不知,这正是紫府迷宗的上乘轻功,这少年不是别人,乃是桑龙姑的长子南雍。
看官:你道那秦寒梅如何会与南雍相识呢?原来那秦寒梅自在雷波城中起,即一直跟在雷洪身后,要知那秦寒梅乃是自在襁褓,即由镜湖老人抚养长大,论武功,那时实在雷洪之上,是以一直跟在雷洪后面,雷洪丝毫无觉。
那莽苍山中,赤炼人魔杀徒之夜,以及雷洪得遇剑魔,秦寒梅皆是眼见,看官当能记忆,那晚秦九凝突然警觉,飞身跃过溪搜寻,那人即是秦寒梅,幸她机警,相隔又远,一踪迹败露,即刻远远隐去身形,这才没被秦九凝找到,但却因此一来,秦寒梅却因此失了雷洪的踪迹,害她在荒山之中寻了两日两夜。要知那幽谷实是隐密之极,雷洪若非机缘般般巧合,不由溪底,亦万难发觉,而且秦寒梅更想不到雷洪即在近处,倒远出寻找。
这日,秦寒梅已然绝望,出山往北行来,即在那寒潭左近山中,巧与南雍相见,那南雍一见秦寒梅,即惊为天人,要知南雍人物俊秀潇丽,未曾入世,心悦秦寒梅,即不顾男女之别,盯着眼瞧她,而且还即近前与她攀谈,那秦寒梅心中正没好气,即刻与他大打出手,哪知南雍百般忍让,秦寒梅仍奈何他不得,奇怪他并不还手,那奔雷剑何等凌厉,竟是无功,只见他身法怪异,剑出,明明劈在他身上,他却终是轻轻巧巧地避过了。
秦寒梅一者心生奇诧,二来见他人物虽然俊秀潇丽,目光之中,可以瞧出他实是诚笃,而且秦寒梅对他猛攻,他面上一直流露出痛苦之色,渐渐,秦寒梅心肠一软,便收了剑,喝问他是何人。
那南雍当即诚诚恳恳,将出身来历相告,当真不打不成相识,秦寒梅亦是个武林儿女,人也纯真,不料就此成了友好,秦寒梅亦将身世相告。
那南雍对秦寒梅实是一见钟情,一来感叹她的身世,二来见她念念不忘雷洪,感到失望。
他两人订交时,亦即是秦九凝与雷洪赴寒潭之时。故而两人并未见到南雍,他返回寒潭,巧巧与雷洪,秦九凝错过了。
那秦寒梅追失了雷洪自不死心,南雍一走,她一面缓缓北行,一面打听,皆因她知雷洪要赴天姥救母,必打水路,从扬子江舟行东去。果然被她算着,日落时候,忽然发现雷洪自后行来,秦寒梅芳心怦怦,即隐身让他行前,再又尾随于后。心想:“他赴天姥救母,我岂能不暗中相助。一是她不敢对自己说,他对雷洪情牢梦牵,而自我找出暗中跟随他的理由,忖思:“我与雷家虽然是世仇,但与他娘何干,她那可怜的身世,那赤炼人魔的暴酷残忍,当真令人发指。”
秦寒梅尾随着他,见他落店,巧啦,那南雍随他娘桑龙姑,与弟妹等离了寒潭,心说:“我走啦,岂能不与秦寒梅告别,啊哟,她要到天姥,我岂能不与他先约,告她居处,她那时好去寻我。”
当下即托辞追了来,那秦寒梅一见南雍,心中一动,却想道:“那晚在莽苍山中,赤炼人魔原可在奔雷剑下伏死,却因雷洪的轻身功夫还不及赤炼人魔,才被赤炼人魔逃出手去。这南公子的轻功神妙之极,若是能传与雷洪,那赤炼人魔还能逃得出手去么?”
秦寒梅处处替雷洪道想,念念不忘,步步紧跟,实是情真爱执,她一向南雍说出请求,那南雍如何不明白,更是心中如有所失,但他能拒绝她的请求么。
秦寒梅又见雷洪衣杉破烂不堪,见南雍衣华人翩翩,心中不由自主地不服起来,心道:“我洪哥不过幼年失母,身世孤苦,若然他也衣履鲜明,不见得不及你潇丽,心及此,即刻连夜替他身手作了一件衣杉,并买了鞋袜,一早即要南雍送去,然后两人才去东北山中相候。
这便是以上的经过,本来南雍要将这紫府迷宗武学传与秦寒梅,是秦寒梅心中想道:“我虽求你传洪哥哥上乘轻身功夫,但这好处在他,我并未得你的恩惠,我若是接受了你的传授,那可不同。”
原来秦寒梅何尝不明白南雍对她有情,因此,她更要他保持一个距离。
且说南雍将那三爻六变,九转十二象的步伐传罢,雷洪皆紧记在心,此刻哪还有轻视之心,对这少年也油然生敬,却因生敬,也更加失神魄:“他人物已是潇丽,风度更见翩翩,却又身怀神奇武学,我样样不及,寒梅妹妹有了他,心中还会有我么?”
雷洪失魂落魄,一时痴然呆立,南雍道:“雷兄若已记住了,今后只要勤加演练,一月之后,必有成就,小弟有事急于东行,请后此别。”说罢,转身就走。
雷洪呆呆地望着他,竟是不言不语。待得发现自己失了礼,那南雍已去得无影无踪了。忽然一声长叹,心道:“他哪是甚么有事东行,他必是找寒梅妹妹去了,他们,他们两人,正是一对神仙眷属啊!”
他呆呆地立在当地,好久,好久。
他却不知,就在他身后,一株大树之上,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正在望着他,那眼中不但饱含情意,而且哀怨之极。
而在数里之外,那南雍与秦寒梅的约定相见之处,一个少年亦是呆呆而立,他找遍了方圆一里地的山林,找遍了每一个隐密之处,却不见伊人的倩影,半晌,何止半,他才绝望地,幽幽怨怨地,一声长叹,这才往东而去。
话说南雍将武林绝学的紫府迷宗的上乘功传了雷洪,奔去东北山中,却不见秦寒梅。
这南雍是个多情种子,偏是秦寒梅天仙化人,故尔一见钟情,魂牵梦萦,只听他幽幽一声叹道:“一别海角天涯,难道你连话别也不愿说么?”
原来这时南雍已有些明白,由她歌出的心声,从她恳请传雷洪的武林绝学,他心中如何还不明白,伊人芳心已早有所属,若非她思也悠悠,恨也悠悠……
南雍才心念及此,忽然惶恐自责,道:“南雍啊南雍,难道你是希望从她的痛苦中,去获得高兴么?”
要知桑龙姑虽然邪恶,但他这长男,和那幼女,却是一双可人儿,不论相貌高贵,人品心性,皆令人爱敬。
他幽幽一叹,找不着秦寒梅,但他乃是抽空赶来,和秦寒梅一别的,他必须即刻追赶他娘和四个弟妹。只得走了,走了,留下满怀情,满腔怨。
秦寒梅去了何处啊?那雷洪亦在寻找,找遍山林,觅尽了幽谷,现在,他站在高山之巅,遥望那悠悠的苍穹,亦是幽幽一叹。
就在他脚下,那山下林中,一个姑娘在遥遥相望,望着他那临风的洒洒英姿,愁到眉峰碧聚,正是,相见争如不见,那愁在眉梢,相思却到了织腰。
这姑娘正是秦寒梅,她瘦了,因愁人更瘦,为瘦愈添愁,多少恨,多少怨,又多少情爱,造化弄人,敎她怎地不愁瘦。
风在树梢,如泣如诉。溪流在谷底,如咽如噎,那悠悠的白云之下,雷洪绝望地作了一声长叹,这才下山,也不再回彭水,山中无古道,只认定方向,向北奔去,这日晚间,即已到了丰都。不过才三个时辰,他已奔了两百多里,原来他就奔驰之便,演练南雍所授的上乘轻功,果然这武林绝学非同凡响。
第二天一早,雷洪便去江边雇船。那小船不敢下驶长江三峡,大船又昂,雷洪正踌躇间,忽见一支大船上,有个老人向他招手,那老人年在六十开外,须发皆白,但甚是强壮含着旱烟管子,面露慈祥。
雷洪走近,那老人道:“哥儿,我听你要雇船,单身一人,确甚不便,若不嫌我这舟小,不如搭老夫这便船南下。”
雷洪一看,那是一支中型江船,与其他船支并无异处,心道:“船上并未见有他人,可能这老人家独行寂寞,要找个伴儿。”忙拱手道:“老人家若不嫌打扰,在下多谢了。”
那老人微微含笑,道:“哥儿,我一看你,便知少在江湖上行走,孤身行路,原应搭便舟才是。”雷洪道:“是,多谢老人家指教。”
不知怎地,雷洪一见老人,顿生孺慕之念,只觉这老人却是和气可亲,其实是雷洪见到这老人,突然想起了爷爷,只觉这老人亲切的微笑,与爷爷甚是相似,不由心中叹道:“不知爷爷现今去了何处?想到他现今孤单单一人,心里甚是难过,一时不瞬眼望着那老人,发起呆来。
忽听舱中一人说道:“师傅,你在同谁说话啊?”那声音好脆,而且又骄又甜。只见舱门开处,红影一闪,走出个红衣女子来。
那女子年在二十岁以上,白白嫩嫩,有点儿像熟透了的樱桃,眉儿眼儿,恰似秋水春山,像是个少妇。
那老人道;“秋娘,这位哥儿徬徨岸头,我想给他一个方便。”
那女子早打量了雷洪,嫣然笑道:“师傅,正是,与人方便,即是与自己方便,请他上来罢。”
雷洪道:“老人家,这……这,这方便么?”
皆因他见那船虽大,但只有一个大舱,人家舟中有女眷他又是个少年,老人笑道:“可见哥儿诚厚,不碍事的,上来吧。”
雷洪不敢多看女子一眼,当下向那老人谢了,这才上船同时心中一动,这女子称老人是师傅,可见是武林中人,而且若非江湖女子,她也不会这般了无闺阁之气,待雷洪上得船上,更令他奇怪,若大一支船,却不见一个梢公。
老人让他进舱,雷洪微感踌躇,皆因那女子已进舱去了。便道:“老人家,你给我方便,小子已感激不尽,就在船头便了。”
老人拂髯笑道:“我这双老眼不花,哥儿,你也是武林中人,怎么倒如此腼腆,来来来,烈日长途,怎好在船头坐地。”他已当先入舱去了。
雷洪所习皆上乘武功,他自换了秦寒梅所送的华衣儒服他人又文秀,本来不易看出他有一身武功的,心道:“这老人家看来必是位高人,我倒不可太拘礼了。”便随后跟进,才见里面有前后舱,那女子想来已进入后舱去了,前舱并不见人。
他这一进入舱中,才觉出这船的异处来,只见明窗亮几无物不华,不但华,而且高雅,这哪是普通舟楫可能比拟?
老人让雷洪坐下,望望天色,道:“这就快开船了,哥儿,你随便坐,不可拘礼。”雷洪答道:“是,老人家,你请便。”
这时对面而坐,相隔得近,才发现这老人虽是慈祥,但双眉之中,似有隐忧,雷洪心道“莫非船上梢公,去备办食物去了。”果然不到半盏茶工夫,只见岸边奔来两人,都是精壮汉子,却非梢公打扮。两人跳上船来,说道:“禀岛主,我们已打听明……”那人像是突然发现了雷洪在舟,故尔不往下说。雷洪大奇,这两个汉子皆不是本地人口音,两人称这老人为岛主,更是奇怪?
那老人一摆手,道:“那女人与中原武林,并无往来,说下去。”
那个汉子这才说道:“我们已打听出,他们那支船,在此停了足足五天,今日天不亮,即已开行,像是回山去了。
那老人点了点头,道:“我猜想也是这般,好,我们快开船,追!”
一个追字出口,一个汉子已纵身一掠,窜上了船尾,一个在船头抽起跳板,两人不但身手倒落,而且显然武功不弱驾舟驶船,更见纯熟。
只见船头那汉子并不用篙撑上岸,只一推,船即滑离岸边两丈,他却纵身跃回船头,船尾那汉子一转舵,霎眼间,船已入了江流。
雷洪看得目不暇视,实则他心有所思,忖道:“老人的这两个驾舟汉子,武功不弱,可见老人了得,他们这是跟踪甚么人。”
那船行好快,只是一刻工夫,只见丰都城廊已落后很远,舱门一响,那红衣女子已走了出来,雷洪忙站起身来。
一者也知这老人是武林前辈,又是搭人便舟,只见那女子嫣然一笑,老人却道:“哥儿不用多礼,这是小徒秋娘,也随老夫练了几年功夫。和你一比,却差得远了。”
那秋娘听师傅说她与雷洪相比,差得太远,显然不服也不悦。雷洪忙道:“小子便会武功,怎能及得这位姊姊,老人家过奖了。”
原来内功深厚,上乘境界的人,皮肤里像有一层油脂渗出,皮色自是白暂滑润,不然雷洪自幼练武,怎倒外面反而看来文秀呢,也就是这个缘故。
那老人一说,秋娘面带惊容,即不瞬眼的向雷洪面上瞧去。
雷洪被看得十分尴尬,忙谦逊道:“这位姊姊名师高足,小子万万不及的,今后还望老人家和这位姊姊多多指教。”
雷洪年未弱冠,实比这女子年轻,几声姊姊,叫得好甜,叫得她这不服不悦之色,顿化为乌有,说:“师傅,我替你取茶来,你们谈啦,瞧你,连人家姓名也不问。”
那老人哈哈大笑。这才问姓名,又问他的师承。
雷洪暗叫了声惭愧,皆因他虽已入师门,但却未正式拜师,连师门门派亦不知道,洞中的老人,秦九凝的奶奶,亦不知道姓名,听口气,将来要向剑魔拜师,难道也称自己的师傅是剑魔么?心中一转,便道:“小子雷洪,幼随爷爷镜湖老人练过几年功夫,实无高深造就。”
那老人听了一声,但随即面露疑惑之色,念了两声:“镜湖老人,镜湖老人……”
雷洪心中突起不快,心说:“我爷爷名满江湖,他倒像没听说过。”
那红衣女子也奇道:“师傅,镜湖老人是谁?”只听那老人道:“十六年前,倒像听人说起过,那时你还年幼,自然不知了。”
这老人好大口气,雷洪心中好生不快,心道:“我爷爷之名,武林中提起他来,谁不敬仰,十多年前,可说如雷贯耳,你不过孤陋寡闻罢了。”
只见那红衣女子点了点头,道:“当年师傅既会听说过的,想来也是中原有数人物了,自然武功也是好的,难怪他已达到了这等境界。”
说着那女子还瞅着雷洪一笑,好像对雷洪有嘉许之意。
若在先前,雷洪哪还忍受得了,但自见了桑龙姑和她五个儿女后,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人家是好意让自己乘搭便船,更不愿生出是非,当下谦逊了几句,问起,也只说会点普通内外轻功。
那老人显然有满怀隐忧,便在问他话时,亦不时察看两岸,或向前面江中凝神注视,故尔也不会深问。
渐渐,雷洪看出甚多异处,他自幼生长泯江之处,看惯了驶船,现今却见船头船尾的两个大汉,一人持篙,一人掌舵,表面看来,虽与一般无多大异处,但船行倍速。未末申初,已过了白帝城,船入巫峡,江流更是湍急,当真有一日千里之势。
这大半日,除了初上船那一个时辰,这老人与那红衣少女,会问及他出身师承之处,即不再言语,而且两人倒有多半在后舱,饮食亦是另外给他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