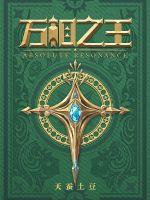单眼老三的赌馆叫昆仑,每日由午后开业,直至深夜才散局。
刚过午,王森和小虎子便“夹”着白栋梁去拍昆仑赌馆的门了,由于白栋梁拍门时用三重两轻的暗号,里面的人,问也不问便把门打开了。
“白少爷,这两位是……”
白栋梁脸色青白,结结巴巴指着王森说道:“他是俺的表哥,今日陪俺来赌几手。”
一个打手问:“兄台是做哪一行生意的?”
“小弟是做山货竹器生意的,跟表弟已有七八年没来往了,昨日来镇上做生意才刚好碰上的。”说着故意摇一摇银袋,发出一片叮叮当当的声音。
那几个打手脸上立即堆上笑容,道:“三位爷们请进。”
赌场就在屋内的大厅上,两边还有几间小房,专给能赌大钱的赌客用的。
一个大汉问道:“爷们要大厅还是小房?”
王森道:“也不知俺今日的手气如何,先在大厅赌几手吧!”
荷官问道:“爷们要赌甚么?”
“牌九。”
“好。”荷官把一副牌九倒在桌上,洗起牌来。王森,小虎子和白栋梁分坐三门,一连推了七手,荷官大败,三人都赢了不少钱。
王森道:“今日咱们的手气不错,到小房内玩吧!不知小房有甚么规矩?”
“这里是大小由人,小房的规定是每注最少一百个大洋。”
“不多。”王森说道:“就到小房去吧!”
四人进了一间小房,立即有两个打扮妖冶的娘儿送上瓜子,卷烟及清茶。
赌了几手,庄家赢了一点,王森道:“不赌牌九了,咱干脆一点,赌骰子。”
荷官大喜,忙叫人收起牌九,问道:“爷们要六颗的,还是玩四颗的?”
“六颗的。”
原来掷骰子赌钱,分四粒及六粒的,掷四粒比较简单,只须掷出三颗同样的点子,余下一粒,所显示出来的点子便是大小,如掷出三粒四,一粒二,这一手便只是二点了,最高的是六点,还有四粒都是六的,是骰子的至天宝,六粒骰子比较复杂,须抛出四粒相同点数的,余下两粒即是一只骨牌,两粒六点是“天”,两粒一点是“地”,一对五点,便是“梅花”。
当下押了赌注,庄家先抛,抛了三手,掷出了一个“梅花”,“梅花”已不算小,是以白栋梁及小虎子都输了,轮到王森抓起骰子,心中暗笑:“你奶奶的,原来灌了水银。”当下喝道:“杀。”一手掷下,即掷出“地”来,庄家只得赔钱,但算起来,因为杀了小虎子及白栋梁,比对之下,尚输了一百块。
王森向小虎子打打眼色,叫他不要加注,自己却把赢来的加上去。
第二手,王森又赢了,小虎子和白栋梁则一胜一败。
第三手,王森的赌注已是四百块,庄家有点紧张,连掷七手,才掷出一个九点来。王森暗暗冷笑:“这小子还不行。”原来骰子灌铅的虽然比较容易控制,但却易为人发觉,灌水银的要使它随心所欲,便非要有十年的苦功不可了。本来对付寻常人,已足大胜,奈何王森自小跑江湖,所识之人,十分复杂,其中有一个跟他师父是同乡的,掷得一手好骰子,人称“宝子大王”,他见王森聪明伶俐,便把平生绝技传授与他,所以除非庄家能掷出六粒六点,否则他都稳操胜券。
“人人均叫我老三。”
说着骰子已送了上来,老三道:“请洪爷先看看这六粒骰子有问题否?”
王森道:“俺信得过你。”
“好。有胆有识,俺老三认你是一号人物。”老三抓起骰子,抛了三手,即是抛出“人”,小虎子掷出七点,白栋梁掷了“牛头”,都输了。
轮到王森,他抓起骰子,试出里面没做甚么手脚,对老三能三手掷出个“人”来,也暗暗佩服。他连掷七手,才掷出“地”来,仅仅赢了庄家。
小虎子及白栋梁身上的钱早已输得干干净净。
老三道:“俺跟你对赌吧!输赢只看这一手。”
“好,爽快。”王森仍把赢来的钱加上去。
老三抛了几手,掷出“天”来,脸色登时松了下来。不料王森竟把六颗骰子分掷成六点,道:“俺又赢了。”
老三道:“你是‘天’,俺也是‘天’,你怎会赢俺?”
“你是‘天’,俺六粒全是六点,是‘至天尊’,当然是俺赢了!”
“咱们这里没这个规矩,这局算和,再来。”老三对几个手下打了个眼色,那些打手立即站到王森的背后。
王森同时也向小虎子打了个眼色,脸上却装出一副忿忿不平的神色,道:“老板怎不早说。”
“俺以为你已知道了规矩。”老三抓起骰子向下一掷。王森出其不意地伸手一抓,一把抓着了老三的手腕,同时长身而起,抡臂一拉,老三猝不及防,身子离地而起,飞了过来,但他也不是省油灯,立即趁势一掌望王森劈去。王森一闪,左手在他肩上一抓,把他的手曲到背后。
这当儿,赌馆内的打手一怔之下,也都抽出武器望王森击去,但王森已把老三的身子挡在自己身前,同时小虎子也把短枪掏了出来,喝道:“全部抛下武器,把手举起,谁敢动一动,俺便叫他躺下。”
白栋梁人虽草包,逃命却快,见状忙站在王森背后,身子如筛米般抖动起来。
老三道:“姓洪的,你是甚么来路,不妨亮出来,大家都是道上的朋友,有话好说,何必动刀动枪的。”
王森冷笑一声,说道:“俺知道你有枪,但俺既然敢来虎口拔牙,自然不会怕你。”
“你有甚么条件便请说吧!”
“其实很简单,俺不要钱,不要人,只要你们合作,答我几个问题。”
老三脸色一变,道:“你们是‘双口’派来的?”
“算你聪明,外面已让咱们包围了。只要你们合作,俺保证从轻发落。”
老三连挣几下,都挣不开王森的手,怒道:“你就算杀了咱,咱的兄弟也不会放过你。”
“那是以后的事。何况俺素来天不怕,地不怕。”王森说道:“这件事与白栋梁无关,你们让开一条路,让他回去,要是有人敢弄手脚的话,俺第一个便先杀了你。”
老三咬一咬牙,道:“好吧!让那脓包出去就是。”
白栋梁如奉纶音,立即冲了出去。局外的人知道房内已发生了事故,都把枪掏出,只望能救出老三,哪里还顾得了白栋梁?
白栋梁离开了赌馆,便给何俊拦住:“里面情况如何?”
白栋梁结结巴巴地转述了一遍,何俊放了他,立即跑入小巷,轻声对一个同僚说了几句话,那侦缉队员随即出镇。
过了一阵,数十个侦缉队员在丁一彪的领导下,赶了过来。众人打开昆仑赌馆的大门,直冲入内,喝道:“通通把手举起来。”
那些打手火力怎能与这队装备精良的侦缉大队相比,见状都把武器抛落地上。
王森哈哈大笑,押着老三自房中走了出来,道:“老三,快招了吧!免得皮肉受苦。”
老三咬牙道:“要打要杀任你,话却在我肚子内。”
王森要想发脾气,忽然小虎子道:“头儿你看。”
王森随着小虎子的手望过去,只见打手之中有一个看来颇为脸熟,一时之间却记不起那人是谁。
小虎子道:“头儿,你看他是不是张药膏?”
王森脱口道:“正是。”
那汉子太阳穴旁贴着一张药膏,一副尖脸猴腮的相貌,此刻身子正不断打颤。
丁一彪吩咐手下用麻绳,逐个把那些打手缚了起来。王森道:“把这个也缚了吧!”
小虎子忙把老三牢牢捆了起来,丁一彪见大事已定,便下令:“到里面搜一搜,看看那批枪械是不是窝在这里。”
王森拿出卷烟,抽吸起来,过了一阵,手下来报,里头只有几柄短枪,还有老三的一个姘头。
丁一彪道:“带老三到里面审问。”
王森道:“先审问那张药膏。”
丁一彪不反对,当下把张药膏带到内堂的一个房子内,丁一彪拍桌道:“张药膏,田横岛外拦劫枪械的事是因你而起的,你小舅子小福子也因此自杀了,你还不把一切招供出来?”
“俺只是贪图几个钱,把消息卖出去而已,可不知道这许多事情。”
王森冷笑一声:“把消息卖给谁?”
“卖给昆仑赌馆的老板老三。”
“不是卖给他的。”王森冷哼道:“你别以为咱们都是三岁的孩子。老三在高陵,你在石臼所镇,相差几百里,小福子上岸后,只两天便发生这件案子了,你哪里赶得及?”
“是,小的把消息卖给老三的一个亲信。”张药膏低着头道:“俺怕事后被你们查出来,所以躲在这里,不敢回家。”
“既然枪是老三抢的,为何不见了那些枪械弹药?”丁一彪道:“老三把枪藏在哪里?”
“我甚么也不知道,你……你问老三吧!”
“张药膏,这件事是由你引起的,论罪可判你死刑,你得想清楚呀!”王森道:“老三若没证据的话,咱们可不能动他。而你因为有小福子的口供,可免不了一个死字,除非你肯合作。”
张药膏哭丧着脸,道:“但小的真的不知道呀,叫俺如何招供?”
丁一彪正想叫小虎子把他押下去,不料王森道:“且慢,张药膏,俺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若不敢开腔,俺便替你说个开头吧!枪是贺光头要的。这赌馆其实也是他的,老三只是个代理人,而枪也是运去了昆仑山。俺可有说错?”
张药膏脸色一变,半晌说不出话来。王森冷冷地道:“这个机会你若还不抓住……哼哼,把他拉出去毙了。”
小虎子在张药膏的后衣领上一提,张药膏立即大叫起来:“俺说俺说,不过俺招出来之后,有甚么好处?”
王森脸色一沉,道:“俺最讨厌讨价还价的人,拉出去吧!”
张药膏脸色灰白,急道:“俺照实招供,一切由长官裁决就是。”
“这才像话,快说。”
“有一日,村内来了几个汉子,要找一个同村叫蔡星的小伙子,俺带他们到蔡家……后来蔡星对我说,有人要找一批枪械,若无洋枪,土枪也要,还叫我帮他们找一批,找到的有赏钱,那时,俺正闹穷,便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过了两三天,俺的小舅子恰好来了,俺自他话中知道他押一批贵重的物品要到烟台,心想也许上天送了一笔钱给俺,便叫他上船后查一查那些木箱装着的是甚么东西,假如是枪弹的话,便叫他两日后在船上多点灯……”
王森截口问道:“你许小福子甚么好处?”
张药膏想了一下才说道:“俺说得到钱之后,便把鸦片戒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哼哼,现在你怎不洗心革面,却跑来这里?”
张药膏说不出话来,丁一彪道:“后来又如何?”
“小福子落船之后,咱便去找蔡星,他那些朋友恰好还未离开,于是他们一面派人去通知附近的弟兄,一边租了一艘船追出后……以后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丁一彪道:“那些枪械真的是贺光头要的?”
“是,现在那些枪械大概也已经运上山了。”
王森忙问:“你去过昆仑山贺光头的窠穴没有?”
“没有。”
王森喝道:“拉下去,带第二个。”
王森跟丁一彪忙了一个下午,终于把昆仑山的情况摸清楚,于是立即商量攻打贺光头的计划。
贺光头这伙土匪盘据昆仑山已有好几年了,手下少说也有二百来个,在山东半岛算是数一数二的土匪,山东省的治安部门早就想把他们连根拔掉,可惜一直没有机会,现在贺光头得了一批枪械弹药,眼看再不制裁,势力必定更加庞大,只是单是强攻,牺牲颇大,而且大部队去时,他们容易得到消息,很可能又转移了。
丁一彪想了一阵,才道:“队长,这次看你的了。”
王森沉吟了一下,又提审了几个昆仑赌场的打手,知道这里的打手除了有数的几个之外,山上的人都不清楚。便决定假冒赌馆的手下,混进山中,相机行事。
这件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何况危险性极大,丁一彪考虑了好一阵才赞成。
小虎子忽然问道:“头儿,你刚才怎会知道夺枪的是昆仑山贺光头的主意?”
丁一彪也抬起头望着王森,王森哈哈一笑,道:“俺是看了这赌馆的招牌而得到启示的。”
丁一彪哈哈一笑:“还是小伙子的脑筋动得快。”
打手之中,其中一个唤鼻涕虫的,为山上的人所熟悉,王森觉得此人较怕死,便把他提上来,晓以一番大义,要他引自己及小虎子上山,假如灭了贺光头那班土匪,便免他的罪,而且还赏他一笔花红。
鼻涕虫起初不发一言,后来才没可奈何地道:“好吧!但假如你们自个露出马脚,让老大杀死,可跟俺没关系。”
王森把脸一沉,道:“你若有心悔过,不泄俺的底,俺又怎会露出马脚?告诉你,你若敢妄动,俺便先一枪干掉你,你自个掂掂轻重。山上的切口黑话如何说,你先教教咱们。”
鼻涕虫说了一遍,王森便记住了,却故意装作忘记,不断问他,鼻涕虫每次所答都是一样,王森估计他不敢使诈,便叫他先去休息,接着三个人便又订下联络,及配合的步骤。
次日一早,王森跟小虎子便“押”着鼻涕虫向昆仑山进发,临行之前,丁一彪又替他们各添一柄快慢机,以防万一。
高陵与昆仑山距离甚近,午后便走入山区了,鼻涕虫不断找寻刻在树上的暗记,沿着记号前进,越走山势越高,树林也更加浓密。
再走了一程,树上忽然跳下几个人来,喝道:“哪里来的?齐都把手举了起来。”
鼻涕虫忙道:“是自家兄弟,别用枪开玩笑,万一走了火,可不是好玩的。”
那几个土匪分别问了些切口,鼻涕虫自然没有问题,而王森及小虎子也对答如流,其中一个土匪问道:“喂,你们在高陵镇好吃好住的,巴巴的进山干甚么?”
王森道:“因为昨夜白家那小子忽然失了踪,老三怕事情露底啦!便叫咱们进山跟老大商量商量。”
一个小头目大概也知道这一件事,忙道:“既然如此,你们快上去吧!这可不是小事情。”
鼻涕虫谢了一声,带着王森及小虎子继续前进。
大约再走了顿饭工夫,便见前面路上拦着几个土匪,问了切口之后,一个土匪道:“三位且等等,俺向郝队长报告一声。”
“请去请去,”鼻涕虫声音有点发颤,话出口之后又改口道:“兄弟。要再见郝队长,可要耽搁不少时间,咱们赶着去见老大。”
“老大现在也无空陪你,你们且等一等吧!不见过郝队长,你也别想上去。”
过了一会儿,那土匪重新回来,带着王森等三人到一个山洞前,他向内通报了一声,只听里面有人喝道:“进来吧!”
那土匪道:“你们自个走去吧!俺要下去了。”
鼻涕虫开门时,王森对他道:“小心一点应付,否则俺不放过你。”
山洞看来颇大,中间用木板隔成内外两进,外面是个厅子,里面大概便是郝队长的寝所。
此刻厅内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头发半秃的汉子,一个是挺着胸膛的壮汉,一身肌肉如铁石,那半秃汉子看来年纪已近五十,脸上圆圆胖胖,一身皮肉雪白,似乎不是土匪。桌上还摆着两樽酒。
那壮汉大概便是郝队长,见鼻涕虫走进来,便道:“他奶奶的,你不留在镇上过年,来山上跟咱们争饭吃么?”
鼻涕虫陪着笑脸,照王森吩咐的话说了一遍,郝队长一怔,道:“真的有这种事,那些‘双口’今次耳目怎地这般灵光?叫老三把赌馆歇了吧!顺便上山跟大伙儿过个肥年。”
“不是的……老三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一定要跟老大说一说。”
郝队长忽然道:“你有没有骗我?”
鼻涕虫吃了一惊,道:“俺怎敢骗你呢?”
那姓郝的看来粗豪,心思却颇仔细,瞪了王森及小虎子一眼,道:“这两个是新来的兄弟么?”
“是的,老三见他俩忠心耿耿,便叫小的顺便带他俩进山拜见老大跟您。”
郝队长眉头一皱,道:“山下既然风紧,他为何还一派便派了三个人来,单你一个来报讯不行么?”
鼻涕虫身子一抖,嗫嚅地道:“这是老三的吩咐,俺不敢多问。”
郝队长忽然道:“鼻涕虫,你奶奶的,上次你还欠咱十五块大洋的赌债。甚么时候才还?”
鼻涕虫哭丧着脸道:“过年吧!请队长再宽限一两个月。”
“不行,做生意的年底算账,咱们赌债,也要过年前清还。”
“但小的身上连个大洋也没有……”
郝队长双眼一瞪道:“俺怎知道你有没有说谎?不行,到俺房内让俺搜一搜。”说罢不由分说便把鼻涕虫拉进里面。
王森及小虎子都大吃一惊,心想万一鼻涕虫对郝队长招了出来,今日便得命丧于此了,刹那间,王森脑海内灵光一闪,便把身上的一枝墨水笔拿了出来,向内走了进去。
郝队长喝道:“俺没叫你,你进来干甚么?”
王森陪笑道:“小弟忘了一件事,这次上山老三叫小弟带了一枝西洋墨水笔,说要送给你的。”说着把金笔递了上去。
郝队长把笔接来,旋开笔帽看了一看,道:“他奶奶的,是帕克21,老三在哪里弄来的?”言词之间露出几丝喜悦。
王森忙向鼻涕虫瞪了一眼,道:“这还是鼻涕虫向老三说的……”
“说甚么?”郝队长抬起头来。
“说队长够义气,一向在老大面前赞老三,叫老三送一些礼物给你……”
郝队长哈哈大笑,转头问道:“可是真的?”
鼻涕虫忙说道:“真的,真的,队长又一向大量,俺欠了你半年的债,你又不追……”
郝队长笑骂道:“你奶奶的,又乘机敲竹杠。好吧!你的赌债再宽限两个月吧!要上山的便去吧!”
鼻涕虫感激地望了王森一眼,便相偕出来,那半秃头发的汉子也道:“队长,俺也要上山了,顺道跟这三位一道走。”
郝队长道:“您老慢慢走。”
四人出了山洞,到了没人之处,那汉子忽然走近王森身边,轻声叫道:“王队长,你来得好快呀!”
王森听了这话,恰似一盆冷水自头顶淋下,他万万料不到自己身份的暴露与鼻涕虫无关,却与这个头发半秃的中年汉子有关。
刹那间,王森心念电转,他借着神色一呆的反应,讶然道:“这位大叔,您叫俺甚么?”
那人诡异一笑,轻声道:“徐某人跟你交个朋友如何?”说着伸出一只手来。
徐某人三个字一入耳,王森几乎要抽出手枪来,幸而对方脸上似无恶意,当下伸手眼对方一握,霎时间,他心头一动,问道:“阁下便是徐百万?”
那人哈哈一笑,不置可否,但王森已肯定他便是徐东卫,原来他徐东卫那天派人去追杀王森,结果那三人没有一个回去,便漏夜出城,来到昆仑山。
王森认出徐东卫的身份,心头疑问重重,不知对方如何要跟自己握手,一时之间,难以委决是否该立即动手把徐东卫杀死以绝后患。
只一犹疑,已至一个开阔地,这广场四周以木板搭建了不少房子,有的还建得甚有气势,广场上有些巡逻的土匪,见到徐东卫立即打招呼:“徐爷您好。”
其中一个土匪见到鼻涕虫也跑了过来:“鼻涕虫,你奶奶的,你跑来山上干甚么?”
鼻涕虫道:“老三派咱们上山有事向老大汇报,老大在山上么?”
“明夜咱们还要庆祝胜利。顺便过个快乐年,老大怎能不在山上?”
鼻涕虫咳了一声:“请带小弟去见见他。”
那土匪道:“老大最近抓了一个小妞上山,现在还在房内,就是徐爷要见他,他也不见,俺看你有话还是明夜才说吧!免得惹他一顿臭骂。”
鼻涕虫向王森看了一眼,王森向他点点头,鼻涕虫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色,道:“好吧!”
那土匪问道:“喂,到底老三派你找老大有甚么急事?”
鼻涕虫道:“老大又不见俺,说给你听又有甚么用?”
那土匪道:“你奶奶的,别像孝子那样,等下俺陪你赌几手。”
鼻涕虫摇手道:“俺已戒赌了。说真的,你们吃过饭没有?”
“你奶奶的,天已黑了,又要站岗,能不吃么?”
徐东卫道:“三位若还未吃饭,不如到我那里吃吧!反正俺还未吃。”
那土匪笑道:“鼻涕虫,你奶奶的真有福气,徐爷这里,鸡鸭猪羊是少不了的了。”
鼻涕虫又望向王森,王森心想:“这姓徐的不知安着甚么心,但无论如何,跟着他总比较安全。”当下便道:“多谢徐爷。”
徐东卫的住所很大,由两间木屋连成,前面是厅,后面有几间房,一个女人,一个姑娘正在桌上摆放碗筷。见父亲带了几个男人进来,都是一怔,那少女放下竹筷,奔进房内。
那中年妇女道:“请坐。”
徐东卫道:“这是内人。”
王森忙道:“徐太太您好。”
徐太太见王森举止斯文,不似土匪,有点奇怪,不过她自小生长富贵之家,极有教养,点头为礼,也不多问。
徐东卫道:“灶堂内还有肉么?再切一盘来,还有,拿我那坛绍兴酒来。”
徐太太又是一怔,心想这坛绍兴酒是丈夫的命根子,以前在城内还没话说,如今在山上,样样欠缺,要想再弄一坛可不容易。为何用这样的酒宴请三个土匪?
徐东卫挥手道:“快去快去。”随又道:“诸位请坐。”
王森道:“咱们一来,累你太太女儿没饭吃,咱们怎好意思。”
“别客气,她们可以再弄。”
吃饭时,王森心头忐忑,小虎子及鼻涕虫,一个身入虎穴难免惊慌;一个做了“奸细”,此刻面对弟兄,心头难安,都是只顾吃饭,不吭一声,倒是徐东卫不断说话逗笑,不过王森却看出他眉宇间带着一抹忧色。
吃饭之后,徐东卫又叫老婆送上一壶清茶,道:“山上一切简陋,招呼不周,请原谅。”
王森道:“不敢,请问徐爷何时到山上的?”
徐东卫道:“比你们早几天,承老大厚赐,送了这栋房子给俺安身。”
王森道:“老大对你一定很不错。”
徐东卫哈哈一笑,道:“现在的确不错,将来如何可就难说了。”
王森心头一动,正想答话,房门忽然被敲响,屋内的人全部一怔,此刻天色早已黑了,还有甚么人来?徐东卫把门拉开,目光一及,神情更是一变,只听外面一个粗豪的声音道:“老徐,你还未睡吧!俺不会打扰你吧!”
徐东卫道:“欢迎贺大哥莅临。”
王森、小虎子及鼻涕虫全是一惊,连忙站了起来,接着外面便进来一个身材高大,满面胡须于思,年纪看来在三十七八岁的壮汉,那汉子见厅上还有几个男人,神情也是一怔,却认得鼻涕虫,骂道:“你这小子怎地跑上山来?”
鼻涕虫连忙道:“小弟本想去见你的,但牛哥又说您……这几天不见人……大哥……”
贺光头摸摸光秃秃的脑袋,干笑一声:“俺现在不是来了,甚么事上山的?”
鼻涕虫看了王森一眼,脸上露出几分惊怕之色,王森也十分紧张,便硬着头皮道:“是这样的,昨夜白家那小子忽然失踪了,老三怕事情会传出去,所以派咱们上山报告大哥……”
贺光头看了鼻涕虫一眼,鼻涕虫道:“真的是这样,大哥是真的。”
王森见他一副哝包相,气得牙痒痒的,却又不能做声,反而贺光头也没在意,他沉吟了一阵,道:“山上的事,可不必挂虑,倒是你们那里……唔,你们明早立即下山,叫老三把赌馆停歇起来,先避避风头再说。”
鼻涕虫连声应是。王森一想明早便下山,自己这一趟岂不是白来?当下便道:“听说明夜山上有庆祝会,咱们想……跟大哥一齐乐一乐……”
贺光头眉头一皱,道:“所谓救兵如救火,怎能再耽误时间。”
鼻涕虫乖巧地道:“老廖跟老何留下来,俺明早便下山去,反正这次去也不是搬家,也不欠人手。大哥,他俩既然兴致大,您便让他们开开眼界吧!”
贺光头瞪了王森一眼,问道:“你叫甚么名字?”
“小弟叫廖先,是老三新收的拜把兄弟。”
贺光头眉头又是一皱,道:“他怎会派你上山?甚么时候进‘门’的?”
“上个月。”
“上个月?”贺光头道:“俺怎没听他说过,也没写个信通知。他奶奶的。”说着眼光露出怀疑之色。
王森吃了一惊,他事先完全没想到这个关节,幸而一急之下,给他想到一个借口:“也许这个月来,大家都忙着呢!”
“嗯,有道理,但是凭甚么跟你拜把?”
王森道:“小弟其实是跟他在赌桌上认识的,俺以前带着个徒弟四处奔跑,靠赌为生,那次跟老三掷骰子,闹了个平手,后来更承他不弃结交。”
贺光头道:“原来如此,我道老三为人十分谨慎,怎会突然转了性子?唔,你说你是四处跑的,去过甚么地方?”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济南、青岛……”
徐东卫忽然插腔道:“廖兄大概也去过烟台吧?”
王森一颗心立即提起,忙道:“三年前去过一次,烟台的赌馆不大,嘻……”
徐东卫道:“难怪,你若是经常到烟台的,俺一定认得你。”
王森心头一松,随又泛起一阵疑云,嘴上却假装一惊:“徐爷是烟台人氏?”
“正是,俺是土生土长的。”
贺光头道:“你们不认识的?”
徐东卫道:“刚才我到郝队长那里坐谈,刚好碰到他们三个,便一道上山,后来知道他们还未吃饭,便请他们到舍下吃顿便饭。反正旧相识是兄弟,新相识的也是兄弟。我一向最佩服满怀义气的人,可惜做不到。”
贺光头大笑一声:“哪里哪里,徐爷本身便是个义气深厚的好汉子,贺某一向十分佩服。”
徐东卫道:“大哥,俺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不知你能否答应?”
贺光头仰天一笑,笑声极响,听在王森耳中却有个干了的感觉:“徐爷,不是俺说你,你我既然是兄弟,再说客气的话,便显得很生份了。”
“是是。”徐东卫道:“小弟刚才跟廖兄倾谈了几句,觉得他见识广,想向你求个情,让他留在山上,小弟有空时,也可跟他聊聊天打发日子。”
贺光头又是一阵大笑:“这又有何难?我就让他做你的守卫吧!”
“多谢大哥栽培。”
贺光头道:“不过他晚上不能住在这里。”
王森等人齐是一怔,徐东卫脸色却微微一变,说道:“这个自然,舍下地方小,也不能安置他。不过,今晚可以破个例吗?”
贺光头道:“好吧!我明天再来看你。”说着站了起来:“鼻涕虫,你还不跟我出去。”
王森又是一惊,忙向鼻涕虫打了个眼色,鼻涕虫显然也不想跟其他人在一起,当下忙道:“小弟在这里坐一夜,明日一早便下山……”
贺光头双眼一睁,道:“你怎地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鼻涕虫道:“大哥千万别误会……俺欠了弟兄们不少赌债,只要走出此门便……俺下次来再陪您吧!”
“没用的家伙,你明天趁早给我滚下山。”贺光头拉开房门,众人立即起身相送。
徐东卫关了门之后,道:“请王兄到小弟寝室一坐如何?”
王森也想摸清他的底,自然不反对。徐东卫带王森进房之后,把老婆也赶了出去,又把房门关了起来,王森冷笑一声:“徐爷怕甚么?”
徐东卫忽然跪在地上道:“请王队长救救徐某一家。”
王森一怔,忙道:“徐爷这样反使王森如坠五里雾中,你替贺光头立了一功,还有甚么性命之忧?”
徐东卫这才把前因后果却说了出来,原来徐东卫跟贺光头根本没有关系,无奈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他不去理贺光头,贺光头却看上了他家的财产,便设下了一个圈套,引他入彀。
徐东卫最错的是请了曾八臂作保镖,因为曾八臂早已跟贺光头勾结,这样他们便逐渐把徐家控制起来。
徐东卫贪好渔色,到花卫柳巷时,不免带曾八臂去壮胆,曾八臂便利用这个机会,想出了一个圈套,吩咐贺光头的人马在半夜埋伏在那个窑姐儿的家中,徐东卫一进去,便被人挟持着,迫着立了一张契约给那窑姐,契约上写着这一幢庄院,五十亩田,一百万块大洋给那窑姐儿。
当时徐东卫性命要紧,自然照做不误,那些人谓只要他听话,便绝不会动他,也不会找他拿钱,但假如不照他们的指示去办,便要取他的狗命。
起初贺光头也只是凭那张契约,向徐东卫勒索一点钱,因为数目不大,徐东卫也没在意,直至上月底,对方忽然说要运一批货到他家暂放几天,徐东卫虽知道贺光头寄放的货物,绝不会是甚么好东西,奈何让人抓住痛脚,只得答应。
这时候,曾八臂跟他的手下便露出本来的面目了,徐东卫后悔莫及,由于事发之时,局子内的人看得紧,曾八臂没法把枪械弹药运出城去,而靠平日有限的手下把枪一枝一枝带到城内的“内应”家内,速度甚慢,危险性又大,所以曾八臂便想出一个“徐家嫁女”的计谋来。
那时候,徐东卫已如肉在砧板上,哪里敢说个不字?
王森夜探徐公馆之后,一来枪枝已安全运出,二来又已暴露,所以曾八臂漏夜持着徐东卫一家到“内应”的家内。过了两天待城内的风声静后,再偷偷来到昆仑山上。
王森听罢道:“贺光头对你似乎不错,你担心甚么?何来性命之虞?”
徐东卫哭丧着脸道:“他们已把我家的田契地契拿了去,又要我把店内的生意清掉,拿钱给他们,假如我的财产被榨光,他们还要我何用?何况这贺光头十分好色,他对我女儿,似乎不怀好意。”
王森道:“要救你也不是不行,你可知道山上放弹药的地方在哪里么?”
“有一山洞,外面守着不少人,我想枪械弹药必是放在里面,明早我便替你去查一查。”
王森道:“那山洞是不是日夜有人守着?”
“是的,通常有四五个土匪。”
王森想了一阵,已有了计较,当下便写了一封信交给鼻涕虫,道:“鼻涕虫,这是你立功的机会,你下山之后,把信交到……”说着把声音放轻,鼻涕虫只连连点头。
这晚王森又与徐东卫轻声谈了好一阵才休息。
次日一早,鼻涕虫便下山了,徐东卫也出去打探消息。午饭时,徐东卫才回来,道:“那山洞果然便是存放枪械弹药的地方,贺光头打算得了这批枪械,过了年便下山洗劫附近的市镇。”
“有几人守着山洞?”王森急问。
“今早有六个人守着,不过今天晚上山上有饮宴,防守一定较松,咱们一定有机会。”
王森道:“很好,咱们等庆祝宴开得差不多了才动手。”
黄昏未至,山上的人已忙碌起来,在广场上安排桌子,拉布条,搬酒抬石的闹个不亦乐乎,而山后更架起几个大锅,屠牛宰羊,准备晚宴的食物。
夜幕低垂,风渐紧,但土匪们却一片毫不在乎的神情,点起牛油火把,把广场照得明幌幌的。
不久,贺光头便走了出来,土匪立即打锣放鞭炮,通知众人出去饮宴。王森昨夜对贺光头要他留在山上过年,虽不想去,却又不能不去。
贺光头见除了巡夜的人之外,都已到齐,便抓起一碗酒道:“诸位兄弟,今晚是大年夜,又值是咱们的庆功宴,大伙儿多喝几碗,哪一个不醉的,便不是自个兄弟。”
众土匪轰应一声,贺光头道:“今夜能够这般高兴,咱们得先敬徐爷一碗,请徐爷出来跟弟兄们见个面,俺打算正月初七跟徐爷结义,做个兄弟。”
众土匪又是一阵大叫,徐东卫拿着酒走了出去,说了几句场面话,最后道:“俺有幸到山上来,又蒙大哥不见弃,心头十分高兴,以后大家有肉同吃,有酒共喝。来,今夜不醉无归。”
众土匪立即争肉吃,争酒喝起来,土匪们几碗酒下肚,都放浪形骸起来,有的放声唱歌,有的大叫大闹,那个姓郝的队长道:“咱们明早下山去抢几个妞儿上来解解闷儿,有兴趣的,明早便拿枪跟我下山。”
土匪们又哄叫起来,王森见已差不多,便与小虎子偷偷溜开,一个土匪醉醺醺地问:“兄弟们,你们去哪里?”
“咱们去解个手。”
“快去快回,晚一点连水也没了。”
王森和小虎子依徐东卫指示的道路,向那个放藏枪械弹药的山洞走去。
山路上不见一人,到了那附近两人把脚步放轻,只听有人道:“他奶奶的,怎地还没人来换班,饿得俺肚子咕咕叫。”
又一人道:“苏大江你去催一催。”
王森只觉那声音十分耳熟,陡地心头一动:“不好。原来曾八臂在这里。”忙拉着小虎子窜入一棵树后。
不料走快了,地上的沙子发出一片“沙沙”的声音,那边的人立即发觉了,喝道:“谁?”
曾八臂道:“拿火把去照一照。”
王森及小虎子都十分紧张,这时候要想走回去又已来不及了,只得静观其变。
火把终于越来越近,幸而此刻远处走来几个脚步虚浮的土匪,大概是来换班的,那个提火把来查看的土匪骂道:“你奶奶的,怎地到现在才来,真不是东西。”
一个土匪道:“别嚎,快去吧!酒快喝光了。”
山洞外的土匪听见这话,都快步跑了出去,曾八臂匆匆交代了几句也去了。王森及小虎子一颗心才松了下来。
一批醉鬼终究要比一批头脑清醒的人好对付。过了一会儿,一个土匪道:“俺去撒泡尿。”另一个也道:“俺也去。”
一个粗豪的声音道:“快去快回。”
王森向小虎子打了一个手势,两人立即悄悄分开。那两个土匪一边解开裤子,一边哼着歌,王森及小虎子同时扑了出去,左臂箍住土匪的脖子,右手刀子一抹,便结果了。
过了一阵,只听那粗豪的汉子骂道:“你奶奶的,你俩死在林子内么?”
一个土匪接道:“九成是醉倒在里面了。”
粗豪声音又道:“他妈的,你们去把他俩拖出来。”
不久,又两个土匪入林,见地上躺着两团黑黝黝的东西,便骂道:“他妈的,真的醉倒了。”
刚弯下腰去拉动,不料王森及小虎子,又自黑暗中扑了出来,一人一个又解决了。接着王森及小虎子便掩了出去。
那声音粗豪的是个壮年汉子,倒是这几个土匪的头目,坐在地上抽着烟,另一个把后背靠在山壁上打瞌睡。
那壮年汉子听到脚步声,头也不抬地问道:“拉出来了没有?他奶奶的饭桶,喝两碗便醉了。”
王森及小虎子一个箭步标前,抽出手枪,一人对付一个,王森枪管抵在那壮汉额上,道:“乖乖的不要叫,否则老子便让你吃‘莲子羹’。”
“你奶奶的,开甚么玩笑的。”壮汉话出了口才觉得声音有点不对,猛一抬头,手往腰上拉,但王森比他更快一步,把他的枪缴了,道:“把山洞打开,乖乖的听话,有你们好处。”
“你们是哪条线上的?”
“‘双口’派来的,山下已被咱们围住了,乖乖听命令,免你们的罪。”
壮汉吃了一惊,只得道:“好吧!到时千万放俺一条生路。”说着拿出一柄大铁匙来,王森命令他把山洞打开,把他们两个推入洞内。
小虎子打亮手电筒一照,见山洞内放着一箱箱的枪械弹药,还有一批小型的炸药包。
王森找了一条麻绳把他们捆了,接着撬开木箱,找出几柄快慢机,装满了子弹,插在腰带上,然后又拿些炸药包出去。
广场上的土匪尚未散去,王森及小虎子先在那些木星内撒上火药,然后钻到人群内去找徐东卫,徐东卫一见他走来,便知大事已准备妥当,连忙悄悄退了出去。
王森急忙转身向外,不料后肩忽然被人一拍:“兄弟快来喝酒。”
王森下意识地一回头,目光一及,登时怔住了,原来此人赫然是曾八臂,曾八臂摸摸脑袋,道:“兄弟贵姓?俺好像在那儿见过你?”
徐东卫也吃了一惊,急忙道:“他是我家的亲戚,上次来找过我……”说着拉着王森走开。
曾八臂忽然叫道:“不对不对……”
王森知道要糟,先发制人,抽起快慢机,一梭子弹发射了出去。
枪声砰砰中,土匪们料不及此,纷纷应声倒地,曾八臂中了一枪,却大声叫道:“有奸细。这人是‘双口’派来的。”
王森左右双枪连发,一个劲催促徐东卫带家人下山。
枪声一响,小虎子便知道事情有变,立即掏出炸药来,准备应变,王森一跑出人堆,小虎子迅速用火点燃了火药引子,随即把其抛出。炸药包落在人丛中,响起惊天动地的一道巨响。火光一闪,血肉横飞,伴着喊爹叫娘,似是一幅人间地狱。
贺光头大声叫道:“快入屋拿枪。”
话音一落,又一道爆炸声响起,这次炸药落在一栋木屋上,火花燃及火药,木屋“熊”的一声,燃烧起来。北风凛冽,火舌飞卷,旁边的木屋立即波及。
混乱之中,王森已至小虎子身边,双枪急射,眨眼之间,那些土匪倒下了一大片,但生命在俄顷之间,那些土匪如丧家之犬般,四处亡命流窜。有几个悍匪拿到兵器的,便纷纷向王森这边冲过来。
小虎子连抛三包炸药包,那些土匪已经分散,杀伤力便大大减少了,他立即改变主意,也举枪还击起来。
王森扫了五梭子弹,五柄快慢机的子弹已用罄,他取出最后那柄匣子炮,用点射应付,同时道:“快退到山洞外那个土墩后。”两人边战边退,到了土墩后,王森又吩咐小虎子把身上的枪留下,再令他入山洞取子弹。
小虎子一去,火力大减,土匪们在贺光头的催迫下,慢慢迫近,王森沉着应付,看看他们逐渐聚集,便又点燃了一包炸药包,脱手向人群中抛去。
这一来土匪们又忙龟缩下去。不久,小虎子抬一箱子弹出来,快手装上子弹,王森趁对方未布成阵势,同时地形不佳,而可作遮挡的木屋,又已成了一片火海,快慢机轮流扫射,仍然死伤了不少土匪。
贺光头看出对手人少,便道:“分一半人兜圈到他们背后,不把他杀死,誓不为人。”
贺光头下令全力进攻,王森及小虎子逐渐抵挡不住,加上其他的土匪自后掩过来,腹背受敌之下,只得缩入山洞内,把木门紧紧关起。
贺光头下令用树干撞门,王森及小虎子各自装了十余杆快慢机的子弹,静观其变。“蓬!蓬!蓬!”那扇坚厚的木门被撞开,小虎子立即把一包炸药包点燃,王森快慢机叫响,把那几个撞门而冲入的土匪解决掉,小虎子自木箱后奔了出去,脱手把炸药抛了出去。
只听“轰”的一声暴响,山洞似乎要塌了下来,震得洞里的人都双耳嗡嗡乱响。洞外的土匪倒下一大片,未伤未死的也被那阵巨浪,掀倒落地。
当他们慢慢自地上爬了上来时,背后忽然响来一阵冷枪,只听一个人大声喊道:“缴械不杀。”
小虎子大喜,叫道:“头儿,丁处长来了。”
只听徐东卫及鼻涕虫也轮流在喊话,那些土匪斗志涣散,有不少人都心生怯意,贺光头道:“谁敢退一步的,俺便先把他毙掉。”
于是枪声再度响起来,王森及小虎子不时跑到山洞外打冷枪,贺光头大怒,道:“都是你这两个狗小子。”回身猛扫两梭子弹,王森及小虎子只得再缩入山洞。
贺光头喝道:“老郝,你带十个人进去,无论如何都得把他俩杀死,另外在洞外布下十条枪,一有人出来,便射他一个脑袋开花。”
话音一落,冷不防王森及小虎子抛出一包炸药包过来,同时趁着硝烟弥漫中冲了出来,四柄快慢机格格格地乱叫。土匪们再也无法约束,四处流窜。
丁一彪率领几个侦缉大队队员,左右围堵,杀得那些土匪大叫投降。
贺光头见大势已去,悄悄爬上一棵大树匿藏起来。
丁一彪见大获全胜,心头大喜,下令打扫战场,找寻贺光头。众人在四处找了一下,都不见贺光头的踪影,王森道:“一定是藏在山洞外的那座树林内。”说着拉着小虎子入林。
贺光头在树上听见,心头暗喜,轻轻把枪管自树叶丛中探出来,正想扣动扳机,树上一头宿鸟忽然“呱”的一声大叫。
贺光头冷不防吃了一惊,手一颤,来不及瞄准便发了火,子弹在王森的身边擦过。王森如同豹子般,一窜几尺,手上的快慢机,叭叭叭地叫响。
一忽,只听“砰”的一声,一具高大的躯体自树上跌了下来,正是贺光头。
丁一彪闻声入林,见了这情况,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同时伸手在王森的肩膊上一拍,道:“今后最危险的任务,我都会首先考虑派你去干。”
王森苦笑一声,问道:“处长,属下有点不明……”
“因为你这小子福星高照。换作别人早已死在贺光头的枪下了。”丁一彪看了他一眼,道:“我不派你去,派谁?”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便把山洞内的枪械弹药搬下山。
半路上,王森道:“处长,你们来得可真及时,假如来迟半步,我就惨了。”
丁一彪道:“咱们在鼻涕虫的带路下,绕开山上的哨岗,一直望上山进发,后来听见爆炸声,便知道你干起来,再见到徐东卫,便派先头队伍抢上山,以配合你们两个。今日是大年初一,下山后咱们开个庆功宴。”
王森笑道:“俺昨夜在山上开过庆功宴,今日却又要在山下开庆功宴,当真口福不浅。”
侦缉队员们听后都大笑起来。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