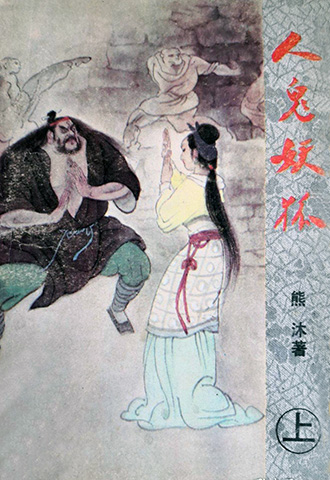官道上,一辆马车慢慢而行。酷暑天下,那两匹马儿亦显得无精打采,只有那车把式看来十分精神。
车把式戴着一顶范阳笠子,遮住大半张脸,看不出年纪,一身粗布青衣,隐约露出结实之骨架及肌肉,皮肤晒得如擦亮之古铜,最奇怪的是车座之旁,放着一坛子酒,难道车把式是以酒代水,以解酷暑?
长长之官道,除此马车之外,未见其他人马,他们都因酷暑天,又当日头正中,在家歌息,只见车把式单手抓起酒坛来,就嘴一阵牛饮,喝得衣襟都为酒渍所湿。人马均不起眼,唯独那酒香,数里之外都能闻着,这莫非是信阳樊家独门秘酿之“十里香”名酿?
樊家所酿之“十里香”酒,虽然名响酒国,唯樊家酿酒除自饮之外,只送予至爱亲朋,从不在市面上沽售,据说武林大豪一共有十三拨人马,先后到樊家盗酒,但竟无一人成功盗出一坛“十里香”。
樊家堡能在一观三教五堡中占一席位,除武功之外,同时以机关设置驰名,如此推测车把式,可不是个简单人物。
“神算”樊智星、“神手”樊天工两兄弟,不胆不喜与同道来往,亦岸傲自高,瞧不起武林同道,“十里香”不管是车把式盗来的,还是樊氏兄弟所赠,都是件值得自傲的事,但车把式却喝得如牛嚼牡丹,亦令人啧啧称奇。
片刻,马车来至一座靠近官途之树林前,车把式略为犹疑了一下,挥鞭驱车入林。他懒洋洋的卸下鞍马,探身进车厢取出干粮,坐在树下以酒送干粮,吃得津津有味,那两匹马则不断啃食树下之野草。
车把式自己吃匏之后,自车厢内取出小半袋杂豆喂马,再倒了半桶水给马喝,正在忙碌时,远处突传来一阵急骤之马蹄声,如雷价响。
马蹄声由远而近,顷刻间便停在树林外面,车把式似是个聋子,连头也不抬,继续喂马儿。
一阵沙沙沙步履声,慢慢走近,车把式依然未曾抬起头来,眨眼间,四周已多了二十多条大汉,全是一色劲装,脸蒙汗巾,将车把式团团围住,马儿不安地踏着蹄子,车把式冷冷地道:“莫把俺的马儿吓坏,快滚出去。”
为首那厮狂笑一阵,倏地厉声道:“燕高行,你太狂了。”
车把式慢慢抬起头来,笠子缘下露出一对黑白分明的眸子来。“朱镇江,在我面前,还轮不到你狂!”敢情那为首之蒙面汉便是云燕十三旗之第一旗的龙旗旗主朱镇江了;依此推测,其他蒙面汉料亦是龙旗成员了,难怪有这份架势。
“燕高行,你早已被逐出十三旗,如今尚有何资格猖狂?呸,一个犯规的登徒子!”
斗笠下那对眸子神光一闪,沉声道:“朱镇江,你说话最好清楚一点。”
朱镇江大笑,“朱某说得还不够清楚么?要否朱某再将当日之情况复述一遍?”
车把式猛地拨开斗笠,露出一张黧黑而端正之脸孔来,双眼神光灿然,两道目光就像一双锋利之匕首般,直迫朱镇江。“燕某光明磊落,有什么事怕你说的?”
朱镇江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有点嗫嚅地道:“你……你如果不是作贼心虚,为何当日甘愿受罚……而远走他方?”
燕高行一字一顿地道:“因为百词莫辩,因为人言可畏!”稍顿又道:“这不过是你跟莫殿元及高琴心三人设下之圈套,目的便是要迫我离开十三旗。”
朱镇江大笑起来:“咱们为何要迫你离开……这对咱们又有何好处?”
“好处可不少,一可取我位而代之;二可为所欲为,擅改十三旗之规矩,以达到你们不可告人之目的!”
朱镇江怒道:“燕高行,想不到你会说反话,哼,轻易把罪名推给朱某,你以为别人都会相信你么?”
燕高行冷哼一声,忽然问道:“朱镇江,你今日带了龙旗弟兄,来此包围燕某,目的何在?”
“要你跟咱们回十三旗,把话说清楚!”
“话早说清楚,已无必要再多说!需要再回十三旗的时候,燕某不请即去,不必劳你之大驾!”
朱镇江冷冷地道;“今日恐怕不是由你主意了……”
他话未说毕,便见燕高行直窜过去,虽不见他作势,但去势其疾如奔马,只见他一拳击在马首上,血光飞溅中,马匹人立而起,几乎把朱镇江掀倒。突见燕高行跃起,凌空刮了朱镇江一巴掌,足尖在马儿脖子上一踢,身子倒飞回原地。
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燕高行身形之快,只能以“鬼魅”两字形容,直至他滚回原地,其他龙旗之弟兄方如梦方醒,发出一片惊叹声。
燕高行厉声道:“朱镇江,这次我是念在多年战友之情份,只给你一巴掌,下次可没这般便宜了!”倏又转首道:“你们也都听清楚,最先向我动手者,燕某出手绝不会客气,届时可莫怪我拳脚不留情。”
朱镇江自地上狼狈地爬起来,左颊五指殷红,神态极之尴尬。燕高行淡淡地道:“还要否‘请’燕某回去?”
朱镇江色厉内荏地道:“燕高行,我知你武功高强,但你再强也只是一对拳头,你有把握打倒咱们二十多人?”
不料燕高行坦然道:“燕某实在没有把握将你们一一打倒,但有两点你必须知道,第一:你们最少得先躺下一半,包括阁下在内;第二:燕高行只会战死沙场,绝不会跟你回十三旗,你自己掂量掂量,不要枉送手下性命!”
这句话软硬兼施,弄得朱镇江也迟疑起来,他多次见过燕高行动手,知他武功在己之上,但像今日这等身法,则连做梦也想不到,莫非燕高行离开十三旗之后,另有奇遇,使武功长足进步。
他心念电转,突然道:“好,算你狠,咱们在十三旗等你大驾,但以一年为期。期满若不见到你,十三旗将顷巢而出,走遍天涯海角,也要将你抓回去!”回首对手下道:“咱们走!”
燕高行哈哈大笑,忽道:“且慢!朱镇江,燕某再说一次,,时机成熟,我会不请自至,也许超过两三年,亦可能只需两三个月,但必是出自燕某自愿,你是绝对请不动我的!”
朱镇江又羞又愧又怒又恨地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他本想说还有什么屁要放,但想起刚才那一幕,心有余悸,话至嘴边,自动改口。
燕高行道:“有,放下两匹马来,这是买马的费用!”两锭银子突然向朱镇江射去。
朱镇江见来势强劲,大吃一惊!不敢伸手去接,连忙闪开,那两锭银子倏地沉下,落在地上,朱镇江又一次出丑,羞愧恨怒交集,连面门话也不敢说下,拔足驰出去,他手下看了燕高行一眼,乖乖放下两匹马,连银子也不拾了。
燕高行哈哈大笑:“多谢龙旅朱镇江赠马之情!”他把马拉过去上辕,十三旗所选之马,均是千中选一之良驹,市面上难以买到,难怪他这般高兴。
眨眼间,龙旅人马已跑得干干净净,燕高行把原来那两匹马拴在车后,轻轻跃上车,挥鞭催马,马车走出树林,又沿官途南下。
安庆是个大地方,水陆交通在此交汇,商客极多,城里之客栈食肆,亦鳞次栉比,而且贵廉兼备。
燕高行懒洋洋地驾着马车,在黄昏后,缓缓进城,他是头一遭来安庆,是以特意驱车在城内走了一匝,顺道挑选一家合适之客栈。
君悦来客栈不在大街上,而在一条整齐之大巷里,马车可以通过,旺中带静,而且价格适宜,房客大多是各地来此经商买卖货物之商人,燕高行那一身打扮,店小二见后有点不屑,但当他的手搭上马车,凭他多年之经验,便知道这辆马车价钱不菲,更可况燕高行出手大方,预付三天房租,打赏他一块碎银。“好好替我照料马匹,俺若满意,尚有赏金!”
“客官放心,小的照顾马匹,一向深得客人赞赏。”
“上好料。”燕高行走了两步,又回首道:“车厢里的酒及包袱替俺搬进房来,其他东西,你干万别乱动!”
店小二讨好地道:“客官,要否小的替你清洁一下马车?”
燕高行双眼突然迸出厉光:“车厢外给我擦干净,车厢里你连动都不能动。东西搬出来后,把车门锁上!”言毕他到居室,一看房内十分干净整洁,一排窗子极是明亮,床铺椅桌柜子,一应均全。
“客官还满意么?”
“先把东西搬进来,再送洗澡水进房°”
“要否替客官准备晚饭?”燕高行不答反问:“小二哥,你住在这里?”
店小二愣了一愣方道:“不,小的家就在本城,家里有老有幼,是以每晚均回家睡觉。”
“好,今晚我请你吃宵夜,晚饭不必替我准备了,俺想到外面走走,对,有关俺的事,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店小二是在亥牌离开,燕高行请他到一间小饭馆里吃宵夜,一口气点了四五个小菜,再加上两壶酒,店小二受宠若惊地道:“客官,你这般客气,叫小的实在不好意思,您有事尽管吩咐就是,用不着客气。”
燕高行举箸道:“没什么事,俺只是觉得跟你投缘,一个人长期在外,难免寂寞,是以找你作个伴!嚼杯。”小二酒量不大好,只喝了一口,他见燕高行一口一杯,不由大为佩服。
“小二哥,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本城何方?”
“俺叫冯成家,俺家就在隔壁巷子里,客官贵姓大名?”
“俺姓高名立,无所事事,到处闲逛,因家父留下一笔财产,家里又没有其他人,不玩白不玩。俺却好结交朋友……嗯,你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吧?向你打听一个人,是个女人,她叫高琴心,她还有一位表兄在河北,她嫁到河北,听说最近回老家了!”
“高琴心?”冯成家抓抓头皮,道:“小的好像未曾听过这个名字,她长得怎么个样子?”
“十分漂亮,今年大概廿六七岁,也曾习过武艺。”
“咦,我好像记得有这么一个女人,但好像不叫高琴心……姓高的倒没有错,嗯,待小的回家问问家里老母亲,她可能知道,不过要找她可也不太难,因为安庆城姓高的都住在高家巷那一带!”
燕高行精神一振,急问:“高家巷靠近何处?”
“在东城区,此处是中西区交界处,也不太远。”冯成家问道:“客官问此有何用意?”
“是俺一位朋友托俺打听的,听说她丈夫已死了三四年,他曾见过她一面,惊为天人……”
冯成家自作聪明地截口道:“小的知道了,客官是想做个媒人?”
燕高行不置可否地哈哈大笑,推搪过去,接着两人又瞎扯了一番,燕高行方叫店家会账。临别时,燕高行又塞了一块碎银给他,“高家的事便拜托小二哥了!再者,咱们之间的事,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希望明天有好消息。”
冯成家哈腰道:“小的一定尽力打听。”两人分手之后,燕高行返店进房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西北善款争夺战之后,他便与十三旅之人员夤夜赶路,要找高琴心算账。谁知赶到十三旗总坛,已经劳碌徒然。更严重的是十三旅多年来之积蓄竟然不翼而飞,时十三旗尚有龙旗、狮旗及鹫旗不在。这三旗是高琴心之同党的嫌疑最大。
燕高行得知高琴心老家在安庆,便决定起程南下,路经樊家堡,竟得“神算”樊智星之青睐,邀其到堡内作客,燕高行只逗留了一天,便又起程,临走时,樊智星送他名牌“十里”佳酿。他对在安庆城找到高琴心之希望不大,但这又是唯一之线索,不能不来,是以睡得十分放心,他已很久未曾睡得这般昏沉。
次日,他还是被一阵拍门声吵醒,张开双眼,已是红日满窗,他打开房门,只见冯成家捧着洗脸水站在门外,让他进去,顺手将门掩上,“你有好消息告诉俺?”
“家母说高琴心可能便是高三娘,她是安庆的美女,错不了!”
“就凭此点?”燕高行边盥洗边问。
“安庆城出过不少美人,但只有一个是姓高的,而且这位高美人,后来离开本城,听说嫁到远方,因此家母认为一定是她。”冯成家加强语气:“家母相信高琴心就是高三娘。”
“有道理,你知道她家在何处么?可否知道她是否已回安庆?”
“她家就是高家巷里的一座红砖小院里,至于她是否已回来,因家母最近身子不好,很少出去串门,是以并不知道。”
“你见过她么?”燕高行见他摇头,又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
“她离开安庆城前,父母已没,只与姥姥过活,家里没有别人,不过听说姨母住在合肥。”
燕高行急再问:“姨母家姓什么?”
“不知道……”冯成家笑道:“客官,其实这些都是问家母的,小的对那姓高的美人,根本不认识!”
燕高行道:“在下是否可与令堂见个面?中午饭后,你可否请个假,带我去见她老人家?”
冯成家沉吟了一下,笑道:“掌柜应该会让小的请假,大概要在未牌末才能走得开。”
“好,我等你,今早给我一碗大卤面,送了面之后,不要再来找我。”
燕高行吃了面之后,便坐在房内冥思,接着运功调息,忽然他觉得纯内真气不如往昔澎湃,再过了一阵,情况依然如此,不由大吃一惊,这种情况从来未曾试过,他再度运功,情况依然,不由怀疑被人在饭中下毒。
燕高行急忙自包袱里取出银针,那吃剩的卤面,尚放在桌上,但银针根本试不出什么来,他当然知道银针不是万能,有许,慢性毒性,如化功散之类者,根本不能测试,如此说来冯成家可有嫌疑了。
午饭时,冯成家又来了。“客官,中午要吃什么?”
燕高行出其不意,一掌击在其肩胛上,店小二痛得泪水也淌了下来,“对不起,俺不是有意的……一时忘记你没练过武……噫!午饭我想出去吃,你不必费心了。”凡是一个练武者,在突遭外力翼击时,体内自然而然会生出反应来,但冯成家却台无反应,看来他的确未曾学过武功了。
燕高行立即伸手替他揉肩膊。“成家,我当你是朋友,希望您说实话。”
冯成家哭丧着脸道:“小的什么时候出卖过您?”
燕高行沉吟了一下,心头一动,道:“对不起,俺会赔偿您。嗯!不出去吃了,午饭您随便替我准备一些,未牌末你再来找俺。”他本想问他是否费叫他在饭内下毒,但看他一脸诚恳,便决定自己暗中调查。
他溜出外面,再自窗口潜进灶房,只见里面有一个炒菜的师傅,一个寿司切菜烧饭的,尚有两个小厮,因时正在午饭时刻,客人多,忙得团团转,无人发现他,他乃飞上横梁。
俄顷,只见冯成家进来道:“周师父,东七号房那位客官要吃午饭,您给他弄几个可口的小菜,一碗饭、一壶酒。”
燕高行睁开双眼,盯着他们,却不见有任何异动,过了近半个时辰,冯成家才进来问:“周师父,东七号房的菜烧好了么?”
周师父回头道::“呶,食盘上搁着呢!”冯成家捧起食盘出去,燕高行穿窗射出,再潜进走廊,躲在柱后偷窥。片刻间,冯成家已至,脸上露出笑容,却未见他动过那些菜。
燕高行等他叫门,才自背后闪出来,道:“门没锁,踢开就行。”
冯成家吓了一跳,回首道:“客官,小的被你吓死了!”他边说边将门踢开,再将菜放在桌上。“怕什么?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来,咱们一齐吃。”
冯成家道:“不是小的的不肯,而是让掌柜知道,小的明天可得卷铺盖了。”
“不吃也得吃一点,咱们是朋友,有福共享。”燕高行把筷子塞在他手中。“每样都得吃一两口,否则不放你走!”
冯成家谢了一声,老实不客气地每样都尝了一点,然后告罪退出去。
燕高行心头不由犹豫起来:“看样子这落厮不是施毒者,那是谁施的毒?如何下毒?”他匆匆吃过饭,又特意喝了点酒,在院子里打了一阵子拳,出了一身汗:心头如陷冰窖。拳式不变,但内功明显又比今早减退,依此速度下去,两三天之后,他便与寻常人无甚分别。后果实在堪忧,会否是高琴心下的毒?
倘是高琴心干的好事,她是如何下毒的?为何自己一点也没觉察?他认为这女人不比寻常,不会只把十三旗之财产卷走,但隐居起来,必是另有图谋。
他摒除杂念,盘膝练起内功,可是内力却越来越弱,他再也不下,一跃而起,将行装扎成一个包袱,待问过冯成家之母亲,便离开此处,以免强敌找上门来,白白送死。
好不容易等到冯成家忙完之后,两人方出店而去。冯家果然就在客栈附近。开门的是他媳妇,长相颇为伶俐,冯成家道:“秀莲,这位便是昨夜俺提过的高客官,快请娘出来,客官快坐下。”
燕高行见那房倒还干净,一座小厅,四间耳房,他坐下不久,便见秀莲扶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走出来,燕高行连忙长身。
那老妇人气度沉稳雍容,似乎见过世面,点头道:“客官请坐,若用得着老身者,尽管开腔。”
“前辈请了,晚辈想打听一下高三娘之情况,希望您依实相告,晚辈感激不尽!”
那老妇不答反问:“老身想先问你,为何要调查她之情况?犬子转述客官之理由,十分牵强,老身不信。”
燕高行料不到这老妇人头脑远在儿子之上,一时之间委决不下,该不该将实情告之,乃岔开话题道:“想不到前辈不但读过,还是个练家子,晚辈来得冒昧,价乃失敬之至。”
老妇微微一哂:“客官不必拐弯探问,老身不妨将实情相告,我的确读过不少书,家学关系,也练过几年武。你一定奇怪,为何犬子反而不练武了,老实告诉你,他不是老身所出,但我视之如同己出,先夫亦是练就之人,却因此惹来杀身之祸,是以我不教他半天就功!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若不问者,该回答老身之问题了!”
燕高行拱拱手道:“前辈,晚辈尚有一个问题,您跟高家有什么关系?”
老妇略为沉吟一下方道:“是表亲关系,但一表三千里,关系实左很疏,只因同住一城,故略有来往,加上三娘父亲早亡,故老身与其母才有来往!”
燕高行再度抱拳。“承蒙厚爱,将内情相告,晚辈亦不敢欺瞒。”当下将自己在云燕十三旗受诬之事,扼要地说了一下。“最近她将十三旗之财产席卷一空,听说她回老家,是以晚辈特来找她。”
老妇又问:“你是来找她要回那些财产?”
“这只是一,因为财产是十三旗所有,岂能由她一人独吞?二是想问清楚她一下,到底她是否跟莫殿元合力诬陷晚辈于万劫不复之境地!”
老妇笑笑。“她会告诉你实情么?除非你动武?那么多钱,她一个人会搬得动回安庆城么?”
燕高行微微一呆,急问:“前辈反对晚辈用武?”
老妇摇摇头。“老身才不管这些,不过就我们知她应该没有回安庆城!她之脾气老身知之甚详,只会衣锦还乡,不会偷偷摸摸回来!你若不信,大可以到高家巷跑一趟,便知真伪。”
燕高行续问:“她父亲早亡,不知她每亲是否尚在安庆城?家里还有什么人?”
“她是在母亲死后才离家到远方的,她走时只向我请辞,未言及去何处。老身只记得她小时候,还有一位比她大几岁之哥哥,后来听他母亲说送给别人了,用意何在却不知道。其实,当时老身也问了,但她母亲不说,老身也不便多问!”
“请问她父母是如何过世的?”
“父亲是被仇家杀死的,母亲是抑郁病逝的。”
“再问高家之仇人是谁?”
“史重生,在武林中之名气并不太响,也许你不知道。”
“知道!”燕高行道:“他是中原三只虎中之长尾虎,擅使长鞭,死在莫殿元剑下。”
“想不到你还知道。”
“据莫殿元说,他跟高三娘是表兄妹,你可认识他?”
老妇想了一下,摇头道:“不曾听高家提过这号人物,但高家也不可能将其家谱全部告诉老身。”
“不过还是有点奇怪……晚辈可否请教前辈之姓名么?”燕高行态度极其诚恳。“请前辈相信,晚辈并无恶意。”
老妇忽然大笑起来,半晌方道:“依老身之见,你还是管好自己之身体吧,其他事都得先搁在一旁。”
燕高行吃了一惊,颤声问:“晚辈身体有什么事?”
“你体内中了一种慢性毒药,此药不会致命,但却也会令你无命。”
“前辈此话怎说?”
“你内功会慢慢消失,直至如一个普通人般,还敢插手江湖事,焉有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