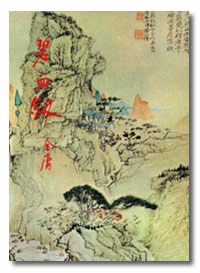天高云淡,骄阳似火,秋老虎更热得使人吃不消。正是日头最毒的晌午,三匹长程健马如一阵风般自南城门冲入郑州城内。郑州古称中州,正处中原的要冲,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此刻日至中天,寻常人等大都在家中,客商亦都歇在客栈饭馆内,街道上行人较疏。那三匹高头大马沿街而驰,一个秃顶的汉子在前,随后是一对青年男女,男的生得相貌堂堂,女的娇俏中带着几分刚健。
马儿很快便转入一条小巷,不一会便停在一座小院前,小院大门紧闭。
那少女飞身下马,正欲上前拍门,大概里面的人听得马蹄敲打青石板的清脆声,“霍”地把门拉开,露出一张年轻的脸庞来。
那青年目光一及,脸上立即露出一丝惊喜之色,叫道:“四妹、头儿,嗯,三哥,你们回来啦?”
少女脸色一沉,嗔道:“没大没小的,四姐也不叫一声!
那青年边把大门拉开,让马匹走进去,边向她扮了个鬼脸,高声叫道:“四——姐!”
少女“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秃顶的沉声问道:“商卫,最近可有什么大案子发生?”
那个年轻人立即收起嬉笑的神色,敛容道:“头儿去后,德州梅大人曾来信讨救兵。萧二哥,不,萧大哥去了一趟,前夜刚回来。其他的却没什么大案子。”
商卫说罢,把马匹系在庭院中的树干上。说话间,大厅石阶上已出现了不少强壮的汉子,齐声亲昵地叫道:“头儿辛苦了,请到厅上歇一会儿!”
当先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脸如金纸,神色十分肃穆,回头道:“快去备水,让头儿跟三弟、四妹洗个澡!彭七,你上街买点酒食回来!”
秃顶老者听了,脸上露出笑容,踏步上厅。
原来此人便是名震朝野的江北总捕头“神眼秃鹰”沈鹰,跟他一齐回来的男的叫“快刀”顾思南,女的叫“云上飞”云飞烟,都是沈鹰的得力助手,亦是御赐六品挎刀龙卫。
那个脸如金纸的汉子名萧穆,有个外号叫“铁面金剑”,是沈鹰手下的第一名悍将,最得沈鹰倚重。
他背后那些人也都是沈鹰的手下,他们不取朝廷的俸禄,只拿沈鹰的酬劳。
沈鹰在江北有二十座“行宫”,分布各处,这当中数中州及洛阳的“行宫”最大,手下亦最多,那是因为这两处地处要冲,交通四通八达之故。
萧穆背后还有一个皮肤黝黑、神色拘谨的青年,此人复姓司马,单名一个城字,投在沈鹰手下还不足一年,也是沈鹰手下四大虎将之一。
当下众人在厅中坐定,沈鹰解开胸襟一颗钮扣,抽出旱烟杆,装了一锅烟,悠然地吸起来。
顾思南却道:“萧二哥既然已升为萧大哥,小弟也该升为顾二哥了吧。”说罢哈哈一笑。
众人也都笑了起来,云飞烟接着道:“小顾既然升为老二,小妹该也升为三姐吧!”
商卫道:“不行不行!你硬要装老,咱就算同意,司马三哥也不同意,他年纪可比你大!”
“但我入门在先!”
众人故意逗她,都说她仍应做其四妹,倒是司马城老实,走前一步拱手道:“小弟拜见三姐,希望以后多多指教!”
云飞烟喜道:“你们看看,还是司马四弟有良心!”众人笑声更盛,连一向沉穆的沈鹰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手下的人都知道这个头儿外冷心热,脸上神色虽然怕人,对待手下却十分爱护。
原来沈鹰以前尚有一个得力助手,名唤公孙良,是个老捕头,对各地官府及大盗都十分熟悉,年纪也最大,众人都称他大哥,后来因公殉职,才补入了一个司马城(详见拙作《刺客惊龙》)。
当下一个手下入来报称,热水已经准备妥当,沈鹰、顾思南及云飞烟立即分别入房梳洗。
洗去一身污垢,三人精神均是大为爽利。此刻彭七亦已采办了酒食回来,众人分两桌坐下吃将起来。
席间,沈鹰吩咐顾思南把到淮南查案的事述了一次,好让众人长一分经验。
饭后,沈鹰斜倚在躺椅上吸抽旱烟,天气炎热,众人都拿着扇子扇拨取凉。
萧穆突然拿了一封信递给沈鹰:“头儿,昨日管神捕派人送来一封信给您!”
他口中的管神捕便是与沈鹰齐名的江南总捕头“笑面神鹰”管一见。
当下沈鹰立即把信展开观阅,只见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几行字:
字谕沈老鹰:小弟手下之端木盛下月初将与小青成婚,届时请老鹰率领鹰子鹰孙前来喝杯喜酒。
只是小青自小即为孤儿,小弟欲要她拜你为义父,着你以义父的身份到杭州主持婚事!万勿推辞,余言面述。弟管一见顿首。
沈鹰一怔,脱口道:“小青是谁,你们可有人知道?”众人尽皆摇头,云飞烟道:“叔叔,管神捕眼角高于头顶,他肯让他心肝宝贝端木盛娶她,料必是个多才多艺的巾帼英雄,最少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叔叔平白飞来一个女儿,这种义父如何做不得?”
沈鹰哈哈一笑:“老夫若收她为义女,只怕你要吃醋了!”
“侄女才不吃醋!叔叔平白多一个女儿,侄女也多了个妹妹,我才高兴哩!”
原来云飞烟的父亲与沈鹰是多年知己,临终之前把女儿交托沈鹰;沈鹰未有妻室,一直视她为女儿,也最为宠爱她。
沈鹰又是哈哈一笑:“你们若都不反对,那么老夫便要去江南捡个便宜了!”回头问道:“今日是七月初几?”
司马城应道:“七月初六,明日便是七巧节。”
沈鹰磕掉烟灰:“你们准备一下吧,咱们初十起程下江南。小萧,你安排一下人手,别让圣上要召见老夫也没个人来传讯!”
×
×
×
七月初十,万里无云。
沈鹰带着萧穆、顾思南、云飞烟、司马城、郎四、葛根生、陶松、彭七及商卫,一行十人出中州南下。
不一日,他们便渡过长江至金陵,早有管一见的手下风火轮在那里迎接,于是歇了一夜,放马直下杭州。
管一见在杭州的“行宫”早已粉饰一新,端木盛喜气洋洋跟在管一见背后立于石阶前。
众人见面,不免向端木盛取笑及道贺一番,把端木盛闹得脸红耳赤。
大厅内多了两堂新置的椅几,管一见见沈鹰肯收小青为义女,心头大畅,特别下厨烹了几壶杭州盛产的龙井茶待客。
沈鹰喝茶之后,又取出旱烟抽吸起来,他徐徐喷了一口烟,问道:“老笑,老夫临过江时便听江北道上的朋友盛传你要在西湖摆下百席宴,未知可是事实?”
管一见笑道:“传闻没错,请帖老夫经已发出,料不日即有贺客临门!”
沈鹰又喷了一口烟,轻叹一声:“大张旗鼓、铺张浪费并非你的作风,今次为何改变?”
管一见老脸微微一热:“老夫吃过别人不少喜酒,今次若不回敬一下,怕别人会有流言!”
沈鹰点头道:“你不是要送一个女儿与老夫么?为何还不请她出来相见!”
端木盛谢了一声,忙走入内堂请她的未婚妻。
沈鹰见他离开,便问管一见:“那位小青是何许人也?”
“她本是赣西楚家的丫环,姓施,”管一见道,“上次端木盛无意中涉及楚家的一件案子中,跟她认识,后来便……咳咳!老鹰,你不会嫌她出身低微吧?”
沈鹰脸现不悦:“老夫自己出身既非名门大派,亦非富豪之家,岂敢嫌人出身低微!”
管一见大喜:“如此甚佳!请帖是以咱们两人的名义发出的。恕老夫事先没通知你!”
沈鹰一怔,心中不甚高兴,但既已成了事实,多说无益,话题一转,问道:“你刚才说到赣西楚家,到底指的是谁?老夫想不出赣西有什么大户姓楚的!”
管一见长叹一声,这才道:“说来你也许不信!‘一刀震南天’熊震南本姓楚,是楚庄王的第六十六代后代。”(有关熊震南的故事详见本系列之《连环杀》。)
说话间,端木盛已带着个妙龄少女自内堂走了出来,那女子相貌虽非国色天香,但清秀中透着几分娴淑温柔,眉宇嘴角间蕴着一丝自然的笑意,另有一种气质。
沈鹰看了心中先自喜了,那女子也不待人介绍,便盈盈在沈鹰面前跪下,口称:“女儿施小青拜见义父!”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
沈鹰哈哈大笑,双手把其扶起,笑道:“有此义女,胜过自己养的,老夫这个义父可真便宜!快请起来,今日见面,老夫也没带什么宝贝作见面礼,这块玉佩已跟你义父二三十年,便送与你吧!日后待你出嫁,老夫再替你好好办一份嫁妆!”
说罢他自腰带上解下一块紫玉双鱼佩,递交施小青。施小青大喜,立即把它佩在腰带上,又谢了一声才俏生生地立起。
沈鹰喜上眉梢,咧嘴问道:“你爱什么东西做嫁妆,快告诉义父!你义父平生从未办过这种事,什么都不懂!要什么最好你自个开口!”
施小青羞红了脸,低下螓首,悄声道:“义父不嫌女儿出身低微,肯收为义女,女儿已感激不尽!这份情义比什么东西都宝贵,其他的女儿都不要了!”
沈鹰故意板起脸孔:“你说不要,是体谅我老人家,生怕义父破费!但外人知道了还以为老夫吝啬!老夫丢了脸,连你也没面子!”
管一见哈哈笑道:“这话大是有理!届时大江南北近千英雄齐集西湖。人家一问,沈老鹰竟然连一份嫁妆也舍不得,连老夫也没面子!”
沈鹰忙道:“女儿你听见没有?外人还未数说老夫,现在已先有人敲响旁鼓了!”一顿:“你若不好意思对我开口,嗯,你告诉烟儿吧!还是叫烟儿替你拿个主意!”
云飞烟轻啐一声:“叔叔这话也不怕笑掉人家的门牙!又不是侄女要嫁,怎能替小青妹子拿主意!”
众人不由哈哈哄笑起来。
施小青粉脸更红,幸而她生性比较大方,连忙上前与云飞烟等人相见,才免得手足无措。
沈鹰问道:“老笑,咱们今夜可不能住在这里!”
“什么原因?”管一见一怔,“老夫可已准备了一切!”
“我女儿还未出嫁,岂能住在这里?待黄道吉日你们去迎亲吧!”
“那你们准备住在哪里?”
“你派个人替老夫包下一座体面的客栈!”
管一见想想也觉有理,便忙把手下四大虎将之一的夏雷派去接洽。
“吉日订在何时?”
端木盛恭敬地道:“八月初二!咱头儿的意思是把小……把新娘接去西湖交拜天地,然后再来此处!”
“老夫没意见,只是你可不能亏待我女儿,否则老夫可不客气!”
端木盛红着脸苦笑道:“晚辈能娶得今媛实乃三生有幸,岂会亏待她!”
“如此最好!”
众人又齐声笑了起来。
管一见见天色渐晚,忙吩咐手下送上酒席,一为沈鹰接风,二为祝贺沈鹰新收一个义女。
席上,杯斛交错,众人谈笑甚欢,呼酒猜枚声四起。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实在甚少有之,因为管一见及沈鹰都是生性爱静。
酒过三巡,只见夏雷匆匆走了入来,管一见抬头问道:“可曾办妥了?”
“属下替沈神捕包下四海升客栈,不过,因为今夜房间很多已住了人,是故明午才能交与咱们!”
沈鹰道:“无妨!今夜只好打扰你们了!”
管一见手下高天翅、端木盛、皇甫雪、夏雷、风火轮、殷公正、路远、冯盛年及黄柏志等跟沈鹰的手下听了都是大喜。
以前他们相见都是在紧张的查案之中,虽然闻名已久,却未能好好互诉倾慕,难得今次相会是在大喜的轻松气氛之中。
这顿饭直吃至二更才散席,饭后,众人谈兴更健,把盏品茶,互诉欣羡之情,以及交流经验,好不热闹,连带施小青也不敢回房休息。
四更的梆子声远远传来后,众人才回房上床。皇甫雪跟顾思南还聊床夜话,直至东方发白……
×
×
×
七月末,长江南北的各路英雄经已纷纷赶到杭州。整座四海升客栈均被包下,沈鹰他们独自住一座小院,其他的地方都腾出来招呼武当派的青虚道长、雪灵道长,少林的百侣、百德两位大师,黄山派的掌门师弟穆一程,峨嵋派的无垢师太,昆仑派的竹剑先生,崆峒派的无音长老,华山派的霍作民,青城派的银冠道人。
这些人不但是一门一派的重要首脑,同时还带了不少门下弟子前来道贺,把偌大的四海升客栈挤得满满的!
甚至稍后到来的七仙教百合仙子、五虎断魂刀掌门彭公志、“孔雀堂“的堂主“五彩孔雀”紫翠雀、霹雳堂堂主秦烈、“断魂刀”袁浩等人亦无法入住。
八月初一大清早,“中州大使”崔一山才自江北及时赶来,跟沈鹰同房而住,再后来的“风云刀”古逸飘亦住将入来,这两人都是沈鹰多年老友,自不便拒绝。
群豪荟萃,每日都大鱼大肉,不醉不散。
沈鹰本来对管一见这次大宴群豪之举颇有不以为然之感,此刻感想全然不同,见到各地英雄不辞千里而来,顿生自豪,心想自己跟管一见的号召力及威望在武林中果然不同凡响!除了九大门派的掌门未能亲来道贺躬迎之外,其余较小的门派主持人,都亲自到贺!
管一见心中之高兴就更加不用说了,他比沈鹰还爱面子。此刻见各派首脑为自己一个手下的婚宴而不远千里急急赶来,心头之舒畅,比吃了廿颗人参果还甚。
自从七月末起,杭州城内每家大小客栈,全部高朋满座,迟来的只能望门兴叹,幸而管一见不愧是管一见,立即向几家大豪商借些屋舍,以作安排!
×
×
×
这天黄昏,沈鹰正与崔一山、古逸飘两人闲话,突听屋顶上传来一声极其轻微的怪响,若非沈鹰内力已臻化境,断难听得出!他立即向崔一山打个眼色,霍地推开窗子叫道:“何方朋友光顾?既然是冲着沈某的面子而来,何不下来一聚!”
猛地听得一声长笑,有人道:“传闻沈神捕武功深不可测,果然名不虚传!老叫化特来讨两杯水酒,不知欢迎否!”
沈鹰心头一动:“阁下是……”
忽见檐前彩光一现,一条人影自上降下。那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相貌堂堂,眉宇间透着几分威严,双眼开阖间,神光迸射,身穿一袭补得五颜六色的灰袍,却甚为干净。只见他抱拳道:“丐帮龙盖天冒昧来访,谅沈神捕不致见怪!”
沈鹰心头一跳,脱口道:“阁下便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帮主‘七彩神龙’龙帮主!沈某闻名已久,惜无缘识荆!龙帮主贵为一帮之主,竟然纡尊降贵前来道贺,沈某真乃受宠若惊,欢迎犹恐不及,岂会见怪!快请龙帮主进来喝杯水酒!”
龙盖天道:“沈神捕之名,龙某也是如雷贯耳,今日一见快慰平生!双鹰神捕具名发柬相邀,龙某岂能不来!再说老叫化有酒喝就算有天大的事也放得下!”说罢哈哈大笑,抬步入房。
崔一山及古逸飘亦忙上前要与他相见,双方寒暄了一阵才分头坐下。沈鹰忙叫人送上酒菜,顾思南等人听见丐帮帮主“七彩神龙”龙盖天莅临,都争相走来拜见。
龙盖天地位虽尊却毫无架子,一一与之点头招呼。不久,店小二便送上一桌盛筵,设在院子中。沈鹰请龙盖天坐在上首,龙盖天推却不得只好坐下,沈鹰坐在下首,其他人在旁相陪。
沈鹰举杯敬酒,三杯过后,问道:“龙帮主可曾去过管老笑那边?”
“刚才去过,敝帮有个弟子跟端木盛捕头甚熟,留在那边,龙某却捺不住性子,出来走走!”龙盖天道,“去年秋,龙某跟管神捕及端木捕头曾有一面之缘!”
话音未了,忽闻脚步杂沓,走来一大群人,原来是青虚道长、百侣百德、霍作民等人听见龙盖天驾临,都前来相见。
沈鹰见人多,便吩咐小二再开一桌在旁,人一多,气氛更加热闹。
席间,龙盖天道:“双鹰神捕的面子的确不同凡响,龙某刚才在城中草草看了一下,这次当真是群英荟萃杭州城!不过,龙某还发现了一件事,须请沈神捕注意的!”
沈鹰微微一怔,问道:“龙帮主发现了一件什么事?沈某洗耳恭听!”
“龙某发觉有不少多年不见的邪教中人以及黑道高手亦夹杂其中!”
沈鹰沉吟一下,道:“如今各地精英尽在此处,料他们也不敢生事!”
“刚才管神捕告诉龙某一件事,城中出现很多没有发柬邀请的人,这些人明日让不让他们去?若不让他们赴宴,情理上难说得过去;但若没柬的也可去,那些邪教中人混杂其中,又怕会在席上生出事端!”
沈鹰吸了一口气,喃喃地道:“这倒是个头痛的问题!”心中有了阴影,兴致当即稍减。
×
×
×
散席之后,沈鹰留下龙盖天,自己却带着司马城去找管一见。
管一见正在厅中踱步,见沈鹰到访,喜道:“老夫正要派人找你过来商量!”
沈鹰叹息道:“可是因为城中发现了不少邪教中人的事?”
“正是!老夫虽不怕他,但假如在宴会上让他们生出事来,咱们两人当着天下英雄可不容易下台!”
沈鹰接道:“问题是请与不请都不好办!”
管一见道:“老夫想加发一批请柬,只派给赶来此地的白道中人!”
“这倒是个办法!反正咱们两人的脾性,武林中人有谁不知咱们跟邪派势不两立?不过,明天还是得小心提防,免得他们老羞成怒!”
“这个老夫自然省得!”
×
×
×
沈鹰返回四海升客栈已是起更时分。
沈鹰刚坐下,椅子尚未暖,只见夏雷进来,轻声在沈鹰耳边道:“启禀神捕,咱头儿得到一个最新消息,城北的邪派中人全部在城门关闭之前出了城!”
沈鹰一怔,脱口道:“他们是路过的,还是生怕自讨没趣才离开?”
“这个咱们还未查出来!”
沈鹰叫他回去,心想那些人离开,总算暂可松了一口气;可是对方行动一致,又隐隐觉得情况不甚妙,心中始终有个阴影。
×
×
×
一夜无话,次日晴空万里,秋风徐吹,好一个黄道吉日!
吉时是申牌时分,午时过后,小院内便开始热闹了。沈鹰亦换上一袭吉服,满脸喜气,昨夜的担心此刻早已烟消云散。
他手下亦都换上新衣,准备迎接端木盛的花轿,云飞烟更是一直陪着施小青。
蓦地,喧闹的锣鼓声远远传来,接着媒人便走了入来。云飞烟替施小青盖上红罩巾,一个新买来的丫环便扶着她出去……
×
×
×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来杭州的,谁不到西湖一游?苏白两堤岸边的杨柳中,夹杂着火红的枫树;黄菊满目,波平如镜,秋日的西湖另有一番景象。
今日偌大的一个西湖,只有一艘颇大的画舫,那画舫布置得美轮美奂,四周挂着大红彩飘。
苏堤搭着一道木板架成的桥子,连着画舫,那木桥架在碧绿色湖水中,上面髹着红漆,益增其艳。
这条木桥长达五十丈,直至湖心,画舫后靠着湖心亭。木桥宽近三丈,两旁各排着一排酒席,正中铺着一幅长而窄的大红布。
迎接新娘的花轿及贺客,沿着苏堤走来,新郎端木盛早已一身吉服站在木桥前准备迎接新娘子。
这刹那,鞭炮声在西湖上空响起,“噼里啪啦”地好不热闹。
新娘步下花轿,媒婆念了一大堆吉词,取出红丝带,叫新郎及新娘各持一端,然后走上木桥。
一干贺客立即随后行走。
画舫高两层,礼堂设在楼上。缀着金色的双喜大红幔,前端坐着沈鹰及管一见,两人脸上都是一片喜气。
新郎新娘步上二楼,众贺客争先恐后上去,只因上面地方少,容纳不了,情况有点凌乱。
管一见及沈鹰的手下连忙劝众人保持秩序。
媒婆高声地叫道:“新郎新娘拜天地!”
端木盛及施小青拜了天地,又跪下叩拜管一见及沈鹰,接着又互相拜了三拜,然后走入礼堂之后的一间房子。
管一见草草说了几句话,宴会便开始了,各人依着自己帖上一早安排的座位入座。
小楼上只有四桌酒席,能够坐在上面都是各门各派的首脑以及一方之雄。
少林寺的百侣、百德,峨嵋的无垢师太另坐一席。
众人入席之后,立即有人先送上酒来,宾客虽多,但这批人亦显然训练有素,一切有条不紊。
沈鹰轻声问道:“筵席是给哪一家包办的?”
管一见轻声答道:“天香楼!”
“果然不错!”
天香楼在苏堤上搭了几个棚子,作为临时的厨房,这当然是因为管一见面子的关系,官府处处与之方便!
突然堤上一个牌官大声喝道:“黄大人驾到!”
群豪均是一怔,忖道:“怎地今日请了咱们,又请了那些讨厌的狗官!”
管一见却神色不变地道:“请诸位稍候,来的是杭州府台黄大人,今次管某在此设宴,黄大人给予不少方便!”说罢与沈鹰及端木盛下楼而去。
群豪之中有人忖道:“管神捕请姓黄的狗官倒不是无理!只是这狗官架子未免太大,待礼成之后才来!”
须知江湖上的英雄好汉,平日干的是杀人放火的勾当,至少也有劫富济贫之举,都是犯王法的事,自来跟官府都没来往,甚至有抗拒之心!
管一见跟沈鹰走上苏堤,抬头一望,都是徵微一怔。只见堤上放着七八顶大轿,当前一顶大轿掀开帘子,走出一人,正是黄纪天黄大人!
背后又走下七八位附近州府的官员。管一见道:“诸位……”
黄纪天笑道:“管大人,下官等冒昧前来,大出两位大人意料吧!”
管一见眉头微微一皱:“的确大出老夫意料!此地的宾客全都是放荡不羁的野汉,诸位大人与他们混在一起,不大方便吧!老夫本来已准备今夜在天香楼另摆下几席请诸位的!如今……”
黄纪天背后的一个长着三绺长髯的老者道:“这点两位大人倒不必担心!”
管一见连忙又问道:“连大人有何高见?”
“下官认为他们不远千里来杭州道贺,也是瞧在两位大人的面子的,而下官等亦是如此!这之间应该没有矛盾!”
沈鹰叹息道:“诸位大人对江湖上的人与事均甚陌生,老夫一时之间亦甚难对你们解释清楚!”
黄纪天脸上现出一丝悻悻之色:“如此说来,两位大人是不想下官等跟他们一起参宴?”
管一见叹息道:“请诸位见谅!老夫们的确有说不出的苦衷!今夜再在天香楼向诸位赔罪!”
黄纪天等人满腔热情而来,如今宛似被一盆冷水自头顶淋下,只得重新上轿,打道回去。
沈鹰及管一见相视苦笑一声,联袂走回画舫。
一路上便有好几个人问道:“那些狗官不来了么?”
“狗官”两字,使沈鹰及管一见甚觉刺耳,却又不好发作,只好以笑作答。
两人快步上楼,忙吩咐天香楼的伙计上菜。彭公志性子耿直,大声道:“那些官儿不来最好!省得大家喝得不痛快!老朽早说两位既然请咱们来,自不会又叫咱们扫兴而去!”
管一见心中暗骂一声,却推下笑脸道:“老夫跟老鹰都是出身江湖,岂敢忘了江湖上的朋友!”
众人齐声喝彩,整座西湖都震动起来了。
管一见气沉丹田发声道:“今日得诸位好友不远千里而来,使老夫十分感动!老夫也不知要说些什么话,只好先敬诸位三杯!希望各位尽兴而归!不醉无归!”
他用内力把话迫出,声音远远传去,群豪不论是在画妨上的还是在甬道上的,齐都举杯一饮而尽。
接着沈鹰也向群豪敬酒,群豪又是一饮而尽。这之后,群豪便三三五五地谈笑起来,不时爆出震耳的笑声。
不久,第一道菜便送上来了,群豪放开怀抱吃喝。
菜上三道,主人陪着新郎逐桌敬酒,气筑更为热烈,沈鹰及管一见都是心头大畅。
敬了画舫上的宾客,又向木桥走去。刚再敬了三席,一个举杯的宾客忽然觉得脑袋一阵晕眩,接着软软地跌倒!
众人刚自一怔,忽闻惊呼声四起,秩序登时大乱起来,原来此刻竟有十分之三的宾客跌倒!
沈鹰及管一见脸色齐是一变,问道:“诸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中年汉子抱头道:“在下……在下一颗头又沉又重……全身没一丝力……”话未说罢,已“砰”的一声跌了下去!
只听一个又尖又细的声音叫道:“酒……酒菜中有……有毒!”
此话一出,场面更乱,只听“砰砰砰”的一阵密集的声音,木桥上的宾客已倒了十之七八!
沈鹰与管一见互望一眼,两人同时提气要奔上苏堤。这一吸气,才蓦地觉得丹田之内,空空荡荡的哪里有一丝内力!
这一惊,实是非同小可,沈鹰及管一见的脸庞登时比冰雪还白,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半晌,管一见才叫道:“桥上有哪位朋友没中毒的么?快把堤上的天香楼伙计叫来!”
可是上千宾客没一个走得动。沈鹰也忙抬头望向画舫,叫道: “有哪位朋友不曾中毒的没有?请把堤上的厨子抓来!”
声音一出,沈鹰才发觉原来自己连说话亦感到困难,说到抓来也是拼力而发,几乎连喉咙亦沙了!
话音刚落,画航内亦传来椅桌碰撞声,以及身体着地声!
管一见叹息道:“老鹰,别叫了,这次咱这个脸丢得实在太大了!”
“全军尽没,传将出去,只怕要笑掉那些黑道中人的大牙!”
管一见心头一动,哑声道:“再过一会,对方如果随便派几个人来,咱们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
沈鹰神心神一震,游目四处一掠,忙道:“快爬上画舫!”言毕当先爬过去,刚爬了两步,又回头道:“诸位假如尚能走动的,亦请爬去画舫。”
可是木桥上的贺客,大都是威望名气较低的,这些人的武功亦是较低,此刻都已陷入昏迷状态中,哪里还有力量爬上画舫?
沈鹰及管一见爬上画舫,刚好少林派的百侣、百德以及峨嵋的无垢师太自楼上下来,他们三个因为武功既高,而且中毒较浅,所以尚能行动。
沈鹰目光一亮,急道:“请诸位把木桥与画舫接触之处弄开!”
百侣道:“沈施主,那么木桥上那些施主又怎办?”
沈鹰轻声道:“下毒之人想对付的必是画舫上的人,而且现在亦顾不得这许多了!请快动手,迟则来不及了。大师,事危之时,该有壮士断腕之志,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
无垢师太在旁听后,冷哼一声,倏地走前几步,运起全身之力,一掌印下,“喀嗤”一声,木桥跟画舫接触之处的木板,登时裂开一道隙缝!
若是平时,无垢师太一掌可把其击断,此刻功力稍减,竟只能击开一道裂痕!
她虽是个出家人,但性子甚烈,当下又再猛提一口真气。不料因为吸气太急,一股真力竟然不受控制涌上心头,只觉喉头一甜,喷出一口鲜血,身子也立时瘫倒。她心知已受了内伤,忙盘膝坐下运功调息,可是丹田内的真气已经点滴不剩!
百侣及百德见状,只好各自伸出一掌,同时向木桥印下。
“喀嗤!”木板应声而断,而百侣及百德同时跌坐地上,嘴角沁出一丝鲜血。
原来他俩也觉得沈鹰之言甚为有理,加上无垢师太当先出手,两人只好把丹田内的真气,全部都提起,拼力击下。
木板虽然应声而断,但亦被反震之力震伤了内腑!
甲板上五人一齐盘膝坐下,久久未收回一丝内力。五人心头齐是一惊,不知对方下的是什么毒。
楼内的宾客亦都一齐盘膝坐下,不敢稍动。
画舫跟木挢分开之后,在秋风中慢慢漂动,终于离开木桥四五丈,益发接近湖心亭!
此刻的形势,对方虽然难以自木桥上跃下画舫杀人,但只要有人把画舫船底凿穿,群豪在四肢无力、内力全失之下,全得葬身湖底。
更要命的是杭州府台一早便出了告示,指明八月初二日暂禁闲人游湖一天,现在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群豪都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时间一点一点消逝,终至西天染上一抹红霞,也把湖面涂上一层黄金。微风吹来,波光粼粼,金光闪动,这情景好不迷人。可是群豪看在眼中,那些红霞宛似一大片的鲜血,闪动的金光却似无数上弦待发的毒箭!
×
×
×
彩霞更红,波光闪动更速,苏白两堤上空宿鸟“呱呱”而叫,宛似盘旋在半空随时会俯冲下来啄食死尸的秃鹫。
幸而对方至今尚未有所行动,就在此刻,沈鹰等五人齐是觉得丹田逐渐缓和,失去的内力渐渐回聚。五人心头之喜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连忙运起功来,加速把内力聚回丹田。
那股内力去得虽快,但亦来得甚速。可是过一会,五人都齐觉丹田热得有点奇怪,脑子中竟然绮念频生,眼前泛起的全是男女间情爱的景象!
管一见心头一懔,忖道:“不好,那毒还有媚药!”连忙震慑心神,运功抵抗欲念。其余四人也都是如此,只要微为一松,欲念即起,一起便难以抑止。幸而这五人两个是和尚,一个是尼姑,沈鹰及管一见亦是少近女色,加上定力较佳,才勉强把持得住。
但楼内的群豪,却没有这般定力,尤其是楼下的宾客,武功、内力稍次,此刻都是脸红耳赤。各人心头虽然焦急,都不敢妄动,拼命运功抵抗,只闹得一个个汗流浃背。过了一会,楼下大厅便响起一道道粗浊的喘息声;再不久,那几个峨嵋派的尼姑也娇喘起来。
这一来,似在暗流汹涌的湖水中投下一块大石,使之波涛滚滚,不能遏止。
此刻,楼下群豪一个个衣衫都为汗水浸湿;那几个峨嵋派的女弟子,平日穿着宽大的袍子犹不觉得如何,如今为汗衣所湿,衣衫尽贴肌肉,露出凹凸玲珑的曲线来,使得端坐在其对面的几个大汉更加难以按捺!
一个虬须大汉轻骂一声:“倒霉,快转过身去,老子忍不住啦。”
他说话分神,丹田内那股热力向下直涌,只见他双眼如同喷火,牙齿咬得格格乱响,额上黄豆般大小的汗珠如泉水般不断涌出!终于忍受不住,大喝一声,双手把衣服抓得粉碎,虎地扑前,把一个峨嵋派的女弟子按倒。
起初那女弟子尚挣扎了两下,待得两人肌肤相触,推出去的手掌,便变成螃蟹的螯子般紧紧地把大汉夹住!
“嘶嘶”声乱响,虬髯大汉三把两下把那峨嵋女弟子的僧袍抓碎,登时露出一具粉雕玉砌的胴体来。
她旁边一个年纪稍大的尼姑喝道:“心慧,你,你……”话音未落,丹田热力向下一涌,一张脸孔登时也如同火烧般,要想再提气压住,已经来不及了,只见她自个拉开衣襟,露出一片雪白的肌肤。
这一举动,立时引得另两个汉子忍受不住,扑了上去,把其按倒。
紧接着,那个叫心慧的峨嵋女弟子已叫出一阵似咒语般的呻吟声,两条虫肉就在舱内滚动起来。
立时再有十来个汉子,齐向那五六个峨嵋派的女弟子扑去。
“嘶嘶”的衣衫破裂声此起彼落,可惜雄多雌少,几个行动较慢的,找不到人,立时挥拳击向那几个浑身精赤抱着峨嵋派女弟子施兽行的大汉!
霎时间,销魂蚀骨的呻吟声,不时夹着惨叫声在船舱内响着!
接着,一些女眷亦被袭,那些单身的女侠尚好一点,有丈夫的妇女被袭之后,其夫必定起而抵抗,可是精神一分散,自己亦乱了性,参与了追奔的行列,有的忍不住按倒自己的妻子胡天胡地起来……
道行比这些稍高一点的,既无能力制止此一惨况,亦不敢看,但那种声音仍不断自耳鼓飘入。这刹那,群豪这在天人交战当中,是人是兽全在一念之间。
船舱内为争女人的打斗声,越来越剧烈,参与兽行的人亦越来越多。
那声音连舱外甲板上的人也都听到。
夕阳终于在西山沉下,大地也逐渐为黑暗吞噬,淡妆浓抹也相宜的西湖已笼在黑暗中,四周没有一盏灯。
画舫上却似人间地狱。
无垢师太耳听门下女弟子的淫声浪语,心田的绮念终为愤怒所驱散,她连忙长身立起步入船舱内,目光一及,当真是又惊又怒又羞,这个一生清修的老尼姑何曾见过此等场面!
这刹那之间,她不由一怔,精神略为一松,绮念又生。她大吃一惊,生怕出丑,大喝一声,急忙重行趺坐地上,运功压住欲火。
无垢师太的出现,使场内的情景有了转变,有几个全身精赤、双目如同火筒而找不到对象的汉子,齐喊一声望她奔来。
这时候欲火如焚,神智尽失,哪还念及无垢师太今年经已将近六十高龄。
无垢师太又急又怒,连忙抽出拂尘一掠,“唰”的一声,抽在一个汉子的脸上,那张似麻子般的脸庞登时开了花!
那汉子只痛哼一声,身子稍顿,便又再冲前过来!
无垢师太喝道:“找死!”用上七成真力,挥动拂尘击在其下肢上,那大汉立即应声跌倒。
那大汉一倒,背后又冲上一人,这次无垢不敢大意,把佛尘倒转过来,以柄戳出,点住那人的麻穴!
就在这时,无垢只觉丹田的热力如火舌高涨的炉子,烘得她欲念频生,也恨不得把衣衫撕碎!
幸而此念一起时,她立即惊觉,慌忙运功压住。
她顾得自身却顾不得面前那些乱了性的汉子,只见一个高瘦的中年汉子怪叫一声,倏地扑在她的身上,一把扯开她的僧袍。
无垢师太大怒,拂尘重重一戳,刺在那人的“灵台穴”上,那汉子身子一歪,登时气绝身亡。
一人倒下,立有一人接上,无垢师太连杀三人之后,自己逐渐亦控制不住那股欲火!
这刹那,后背突然伸来一双手掌,无垢师太霍然一惊,正想反手击出,耳畔忽然听得背后有人高声喧念佛号:“阿弥陀佛!”
无垢明镜登时略为一清,紧接着又有一双手掌抵了上来,两股内力缓缓注入她体内,那翻腾的欲火才逐渐平息。
原来这两人便是百侣与百德。他们两人中毒较浅,所受内伤亦较轻,也因此较快以自身真力把欲火炼化。他俩见无垢危急,所以一齐出手施救。
与此同时,船舱内凌乱的情景倏地止住!那些奔突的汉子以及在舱板上翻腾缠绵的肉虫也都停了下来。
群豪蓦地觉得身上的欲念,逐渐退却,都是暗舒一口气,大厅之内,只闻此起彼落的喘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