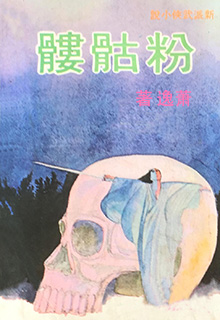(一)
刚砍了别人十条腿的吕大总管,他怎样也想不到报应竟然会来得这么快。
他现在已不再要求什么了,只要求一死。
高大名俯首盯着他,脸上带着一种怜悯的表情。
蚌娘冷冷一笑:“姓高的,你为什么还不给他一个爽快?”
高大名摇头。
他吸了口气,然后慢慢的说:“我现在虽然很容易就可以让他死去,但是我不惯于杀自己的人!”
他的目光忽然转到神龙张脸上:“你是个好人,何不成全了他这番心愿?”
神龙张叹息一声,看了看蚌娘。
蚌娘眉儿一皱,终于道:“你喜欢怎样便怎样。”
神龙张忽然大声道:“好,就给你一个爽快,这一剑之德,俺也不必你来世回报。”
剑锋一闪,直刺入吕祥的咽喉。
吕祥受此一剑,既不挣扎,亦没有闪避。
就在剑锋没入吕祥咽喉的时候,信仓刀竟也在这时候突然飞起。
“嗨!”
好险毒的高大名,竟然趁神龙张一剑了结吕祥残命的时候,突然发难向蚌娘袭击。
刹那间,神龙张简直惊得呆住了。
“娘子小心——”
但迟了。
高大名的信仓刀,已无情地砍在蚌娘的小腹上。
(二)
吕祥虽然咽喉中了一剑,还没有立刻咽气。
当他看见信仓刀飞起的时候,他居然笑了。
他在狞笑。
高大名也在狞笑。
直到这一刹那间,神龙张终于知道高大名为什么不杀吕祥,却把这桩事让给自己去做。
好狠毒的吕祥。
好奸险的高大名。
血已染红了蚌娘的小腹,也染红了神龙张的眼睛。
蚌娘是黑龙谷的“女剑王”。
便她被高大名突袭的时候,她的剑却在丈夫的手里,而剑尖还刚刚刺入吕祥的咽喉。
“女剑王”手中无剑,怎么挡得了此一刀?
即使她手中有剑,也同样挡不了这一刀。
她没有埋怨神龙张。
直到咽气的一刹那都没有埋怨。
她只是关心他和她俩的孩子。
她没有说什么!
她要说的一切,却已在眼神中表露无遗。
(三)
已是黄昏,雨后黄昏。
夕阳斜照,大地一片萧杀。
天上仿佛只有血一般的夕阳,地上仿佛只有永远无法冲洗得干净的血。
神龙张的眼睛里也只有血。
血里仿佛有点浮幻的光影,那是不是泪?
是血中有泪?还是泪中有血?
没有人能分得清,就像是爱和恨一样,往往也是混杂在人们的心里,直到生命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还是分辨不出哪些是爱,哪些是恨?
信仓刀,刀锋长三尺,刀柄也是长三尺。
这是一把来自东瀛岛国的刀。
这把刀的主人,本是东瀛名伶信仓之介的。
三十五年前,信仓之介来中土,凭这六尺长刀,连败中原数十高手。
这是一把曾经显赫一时的名刀。
这是一件杀人如麻的凶器。
但它却并不是杀人不沾血的刀。
——吕祥以此刀砍了十条腿之后,曾以雨水洗刀,刀上已无血。
但现在,刀锋上又沾满血迹,那是蚌娘的血。
高大名的眼神,充满了凶暴而愉快的表情。
而神龙张的脸却已变得比死人还难看。
他把蚌娘的剑,放在蚌娘的身边。
他紧握双拳,好像恨不得把高大名放在手掌里完全捏碎、毁灭。
他的血仿佛已结成冰,又仿佛已变成可以摧毁一切生命的烈焰。
他额上每一条青筋都已暴起。
他的“逆水游龙十六掌”,必将倾尽全力使出,为蚌娘伸冤雪恨。
高大名早已有了准备。
他知道神龙张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必然是绝对可以致命的重击。
就在这扣人心弦的时候,不远处忽然响起了一阵凄冷悲哀的箫声。
箫声听来空洞而单调,既没有特殊的节奏,也没有高低抑扬的转变。
它一直都是那么凄冷平淡,但在平淡中却又是那么令人心碎。
箫声一响,神龙张的脸色就已变了。
他的愤怒已渐渐化为犹豫,更渐渐化为惊疑、恐惧。
高大名脸上的表情,却变得更残酷、更愉快。
“神龙张,你现在想走,恐怕已来不及了。”
他忽然用一种深沉的声调缓缓地说。
神龙张脸色渐渐变成一片苍白。
他很想出掌,一掌杀了高大名。
但那箫声,那凄冷得令人心寒的箫声,却使他的愤怒冻结下来,甚至连“逆水游龙十六掌”也一起冻结着,使不出来。
这诡秘、怪异的箫声,竟似已将神龙张和高大名这一战的战局完全扭转。
在一株枯树下,忽然出现了一条朦胧的人影。
这人衣白、发白、胡子也白。
唯有手中一箫,漆黑如墨。
这是什么箫?
他是什么人?
箫声不是那么单调,但这人站立的位置却又忽然转变了。
他刚才还是站在那株枯树下的,但忽然间又已在茶馆那辆木头车旁。
神龙张连呼吸都似已停顿。
倏地,箫声一转,从单调化为复杂,从平淡化为多姿多采,从凄冷化为轻快热闹。
那不单是箫声,还有琴声和琵琶声。
在那简陋的茶馆子两旁,不知何时又来了两条幽魂般的人影。
左一人抱琵琶,右一人奏弦琴。
神龙张的眼睛好像开始模糊了。
依稀间,他只能分辨出,手抱琵琶的是个女人,奏弦琴的则是脸色苍白的汉子。
天色渐暗了。
神龙张竟然看不清他们的面貌。
这究竟是因为天色黯淡,还是神龙张的视觉已越来越模糊?
乐声更急促。
不知如何,神龙张竟已汗流浃背,身子更不住的颤抖起来。
高大名已远远站开去,但他却没有追前。
手抱琵琶的女人,渐渐移近到神龙张的背后。
她移动的并不快,但神龙张却似已怃所觉。
乐声仍然继续响在他的耳朵边,除了乐声之外,还有掌风声。
这抱琵琶的女人,竟然从神龙张背后拍出了一掌。
神龙张的眼睛,就在这一刹那间最少睁大三倍。
也在同一刹那间,他已急速的转身,挥掌相迎。
抱琵琶的女人好像有点吃惊了,她这一掌才拍出一半,就已立即收了回来。
她的反应极快,掌势一收,人又已飘然在远处之外。
神龙张一掌劈空,木然卓立。
那脸色苍白的汉子,却在这时候唱起了一曲悲歌。
悲歌一起,箫音、琵琶音和琴音,全都变了,又从轻快热闹,变成凄怨萧杀。
那汉子在唱:
“凄凉宝剑,夕夕悲鸣;
关月冷冷,芳草已暮;
鸿雁愁云,天涯无觅;
夜魂空归,化作一梦。”
悲歌,这一阕令人心碎的悲歌,在暮色中唱起,天地更见苍凉。
歌至一半,歌声已不像是歌声,而像是一种摄人魂魄的魔咒。
神龙张的魂魄,似已被这魔咒摄去。
他的人虽然还站得很稳,但却只剩下了一具没有魂魄的空壳。
当白衣汉子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人已站在神龙张面前不足一丈。
琴下藏着一把锋利的匕首,这匕首已渐渐指在神龙张的咽喉上。
歌者还在歌,听者还在听,箫声、琵琶声和琴声还在继续。
神龙张却似已浑然忘我。
他不但已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妻子的血仇,也忘记了匕首是可杀人的。
锋利的匕首,已刺破了他咽喉上的皮肤。
再刺深两寸,神龙张立刻就是个死人。
生死俄顷,间不容发。
就在这一刹那间,暮色中忽然响起了一声巨吼。
(四)
吼声响起,匕首忽然跌在地上。
吼声响起,箫声、琴声、琵琶声猝然中断。
神龙张瞳孔暴张,失声道:“佛门狮子吼!”
他这五个字还没说完,脸色苍白的汉子走了,手抱琵琶的女人也走了。
只有高大名,和那白发白衣的老人,仍然在茶馆外的官道上,静静的瞧着神龙张。
其实瞧的并不是神龙张,而是从神龙张后面出现的一个人。
那也是一个老人。
无论是谁都很难想象得到,这一个老得牙齿都没剩下几枚的人,刚才竟然能发出那一声如雷般的巨吼。
神龙张没有转过脸。
但他早已知道这人是谁。
“老不死,俺欠你一条性命。”
老人一笑!
神龙张又叹了口气道:“想不到你连佛门的狮子吼神功也练成了,中原七条龙,恐怕该数你最厉害。”
老人仍然一笑。
却没有说半句话。
那白发白衣的老人突然长叹:“龙在田,我们都老了,又何必争锋头呢?”
大吼一声的,正是南三龙之首的龙在田!
龙在田淡淡一笑,终于道:“我若要跟你争锋头,早在二十年前便已和你决一死战,又何必等到今时今日?”
白衣老人又叹了口气:“不错,你毕竟还是我的好师弟。”
这个白衣老人,原来竟然是龙在田的师兄。
龙在田淡淡的说道:“昔年旧事,不必提了,师父的武功秘笈,你我各占其三,我们谁也没有吃亏。”
白衣老人忽然笑了笑。
“不错,我们谁也没有吃亏,二十年前我向你挑战,你也避而不战,可见你还是很尊敬我这位师兄。”
龙在田忽然变得很冷漠。
他说道:“可惜你我虽同出一门,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白衣老人道:“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从我们分占六本秘笈那时开始,咱们兄弟之感情,已经完结。”
龙在田沉默了半晌。
他才道:“咱们分道扬镳,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白衣人缓缓道:“但我们现在又碰头了!”
龙在田吸了一口气。良久才缓缓的说道:“听说你已成为天绝教中身份极为尊崇的大法师了是么?”
白衣老人点头。
“我现在是教中祭坛三大法师之一的地劫法师。”
龙在田道:“还有两大法师又怎样称呼?”
地劫法师道:“在我之下的是人灭法师。”
龙在田道:“在你之上的又是什么法师?”
地劫法师道:“那是天绝法师。”
“天绝、地劫、人灭!”
“正是如此。”
“好邪异的天绝教!
地劫法师得意的说道:“天地合一,唯吾独尊,师弟若投顺我教,助教主完成空前霸业,将来——”
“不必再说将来。”龙在田截然道:“你我俱已行将就木,将来一旦归去,能避过地狱下三界诸般灾劫,已是万幸。”
地劫法师喟然长叹:“一别二十年,你还是没有改变。”
“青山可改,沧海桑田可易,唯我为人之道,绝不敢改。”
“师弟何固执于此?”
“师兄比起我来,又何尝不是固执得无以复加?”
地劫法师叹道:“难道咱们师兄弟,真的无缘共襄大事?”
龙在田沉默下来。
他不再说话。
地劫法师沉吟片刻,终于道:“既然如此,本座亦不便强人之难,只是日后再次相逢,休怪本座不念同门之谊。”
语毕,人已消失在暮色中。
神龙张突然狂呼:“高大名,高大名!你躲到哪儿去?高大名……”
他不住的狂喊。
几至力歇声嘶。
但高大名早已不知去向。
地下只留下蚌娘的遗体……
星疏云淡,龙在田想生一点火。
但雨后的树枝被雨水湿透,根本就燃点不起来。
神龙张已疲倦了。
他毕竟是血肉之躯!
就算体力还没消耗殆尽,精神也已很疲倦。
“高大名!”
这是一个神龙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名字。
若不是龙在田及时赶到,以巨吼之声救了神龙张一命,神龙张现在已是个死人了!
那一声巨吼,其实并不是佛门狮子吼的功夫。
但以龙在田数十年的内力修为,这一吼之威,也绝不比狮子吼差得太远。
“你打算把蚌娘葬在什么地方?”
“黑龙谷。”
“你什么时候回去?”
“先去藏龙坳一转,倘若没事的话,马上就回去。”
“不必去了。”
“为什么不必去?”
神龙张的眼中寒光暴射:“藏龙坳里发生了什么事?”
龙在田叹了口气。
神龙张急追问道:“你已去过了藏龙坳?”
龙在田点头。
“七郎呢?”
神龙张一口气的问下去:“他是不是在藏龙坳里?还有北三龙、花雨傲、潘若侯,他们是不是也在藏龙坳里?”
龙在田摇摇头。
“藏龙坳里没有人,连一个人都没有了。”
“死人和活人都没有?”
“都没有,老夫看见的,只是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
龙在田叹了口气,很久之后才说出了一个字。
这个字是:“血!”
(五)
——龙在田曾到藏龙坳。
——他在藏龙坳没有看见任何人。
他看见的只是藏龙坳中景象一片凌乱,血渍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