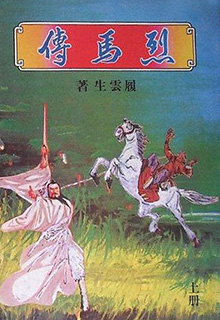夏芸以过人的机智,骗过了骄狂自大的苍玄,苍荆,逃出武当山。
她内伤尚未痊愈,胸腹之间一阵阵地觉得无比的疼痛。
但是她一刻也不敢休息,拼命地在深夜黝黑的山道上奔驰着,因为她知道,此刻她还没有真正逃出武当派的掌握,而她这次若被武当派里的人再捉回去,只怕要受到更大的屈辱。
四野虫声啾然,松涛被山风吹得籁然发出一种呜咽般的声音,一阵风吹来,夏芸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心里觉得有些害怕。
好容易,逃到山下,经过这一番勉强的奔驰,胸口疼得更是难受,夜露沾到衣上,她觉得有些冷,腹中空空,又觉得有些饿。
但是此地荒野寂然,哪里找得到任何一种他所需要的东西,她只得又勉强地挣扎着朝前面走,希望能找到一个山脚下住的好心人家。
头也开始一阵阵地晕暗起来了,她几乎再也支持不住。
猛一抬头,忽然看到前面居然有灯光,这一丝新生的希望,立刻使她增加了不少力气,居然施展开轻功,朝前面掠去。
远远地就听到那间有灯光的小屋里,发出一阵阵推动石磨的声音,原来那是间山路边的豆浆店,专门做浸晨上山的香客的生意的。
又饥,又寒,又渴的夏芸,想到滚热的豆浆被喝进嘴里的那种舒适的感觉,精神更是大振,三步并做两步,走了过去。
磨豆浆的是一个睡眼惺忪的老头子,白发蟠然,身体虽然还很硬朗,但是再是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消失所带给他的苍老了。
还有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老婆,正脚步蹒跚地在帮着忙。
为着生活,这一对本应休养的老年人,仍辛苦地在做着工,忍受着深夜的寒露和浸晨的晓风,所求的只是一日的温饱而已,生命中许多美好的事,在他们仅仅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
夏芸心中恻然,悄悄地走了上去,那老头子抬头看到一个头发蓬松,衣履不整的妙龄少女,深夜突然在他面前出现,吓得惊呼了出来。
夏芸连忙说:“老爷子不要怕,我只是来讨碗豆浆喝的。”
她温柔的声调语为平静了那老头子的惊惧,他惊疑地望着夏芸。
老太婆也蹒跚地走了过来,灯光下看到夏芸气喘吁吁,脸色也苍白得可怕,忙道:“姑娘,你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吗。”
老年人永远有一份慈善的心肠,也许他是为自己将要逝去的生命,做一首美丽的轻歌吧。
夏芸编了个并不十分动听的谎言,在这两个好心的老年人家里住了五天,身上所受的伤,经过熊倜真气的治疗,又休养了这么多天,渐渐已完全痊愈了,精神也大为松焕。
武当山上发生的事她一点儿也不知道。
熊倜和尚未明两次从这小屋前走过,谁也没有朝里看一眼。
这就是造化的弄人。
五天之后,夏芸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两个好心的老年人,在囊空如洗,无以为报的情况下,她解下了颈子上的金链子。
于是她开始感到一种空前的恐惧,在人们囊空如洗时所发生的那种恐惧的感觉,有时几乎和“死”一样强烈。
夏芸盘算她该走的路。
“离开家这么久,也该回家了。”她暗忖:“爹爹看到我回去,一定高兴得了。妈妈对我虽然总是那么冷冷淡淡的,可是这次我想她也会高兴的。”
她微一皱眉,另一个人更强烈的占据了她的心。
“可是我怎么能就这么回去呢,倜哥哥,你有没有在想我呀,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是多么想你呀。”
“回到那家胖子开的估衣铺去吧。”她暗忖:“在那里一定有倜哥哥的消息。”
“倜哥哥知道我被劫,一定会出来找我的。”她心中甜甜地,对熊倜,她实在有太深的情感。
“但是我一文钱都没有,怎么办呢。”她低头看到自己的脚,原来她那天自床上被劫走,脚上穿的只是一对睡鞋。
经过这么多天,那对鞋已经是既肮脏,又破烂了,身上的衣服,已脏得变了味,夏芸苦笑,她本来是个最爱干净的人,自小娇生惯养,几时吃过像这种样子的苦头。
突然,她哭了,她想起采石矶旁看到熊倜的那付样子,心想:“现在我不是已经和他那时候完全一样了吗。”转念又想道:“那时他说:‘既不能偷,也不能抢,只有这样了。’我还说:‘要是我呀,我就去抢了。’可是现在,现在我也不敢去抢呀。”不禁又觉得好笑,笑容甚至都泛了起来。
但是,现实的问题,瞬即又使她一丝欢乐消失了。
“假如有一个很有钱的人经过,我抢他一些银子,也不算是什么太大的坏事吧。”沿着荒寂的路走着,她不禁泛起这种想法,忖道:“最多我问清他的姓名,以后再还他就是了。”
可是这条通往小城的路上,荒荒凉凉,别说有钱的人没有,就连乞丐都没有半个。
夏芸叹了一口气,暗忖:“只有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了。”
忽然,远处竟有蹄声传来,夏芸心头一阵猛跳,叫她做强盗,她胆子虽然大,可还是有点不敢,可是她一想到以后可以还钱给人家,心里就舒泰了一些,这就是大小姐一厢情愿的脾气,永远只替自己着想。别人的想法,根本没有放在她心上。
她远远看到过来的两匹马,暗忖:“这两人都骑着马,而且看这两匹马行路的样子,都还不错,看样子这两人准穷不了。”
她两只眼睛紧紧瞪着那两匹马,拳头握得也是紧紧的,掌心都淌出冷汗来了,心头砰砰地跳,到底还是紧张得很。
那两匹马走得很慢,又走近了一点,夏芸看到马上坐的是一男一女,身上穿得花团锦绣,讲究得很,人也像都很漂亮。
马上那女的一路指点着向那男的说笑,不时还伸出手去打那男的的肩头,显得甚是亲热。
夏芸见了不禁一阵心酸,想起自己和熊倜马上邀游,并肩驰骤的情况,历历如在目前,但是此刻自己却是孤伶的。
她在路中央踽踽独行,马上的一男一女,都用奇怪的目光望着她。
她低着头,等到那两匹马堪堪走到自己身侧,突地双手疾伸,在那两匹马身上点了两下。
那两匹马一声长嘶,人立了来,立即动也不动。
这又是她在苏州街头制住孤峰一剑边浩的坐骑时所用的手法。
原来如她自幼在马场中长大,马场中有一位马师傅,原先本是马贼,不知怎的,却将这种关外马贼的绝技,教给了夏芸。
可是马上的那两个人,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马鞍上,像是钉在上面似的,神色虽然微微露出惊愕的表情,但仍是从容的,仿佛夏芸这种中原武林罕见的制马手法,并未引起他们太大的惊异。
若然夏芸稍为更具有一些江湖上的历练,她立刻便可以知道此两人必非常人,须知以孤峰一剑那样的声名地位,尚且对她的制马手法大表惊异,那么这两人岂非又比孤峰一剑高了一筹。
马上的男女微一错愕之后,相视一笑,似乎觉得很有趣。
那女的笑得又俏又娇,夏芸暗忖:“这女的好美。”自顾自己褴褛的外表,不禁有一些自卑的感觉,她向来自诩美貌,这种感觉在她心中,尚是第一次发生,当然,她衣衫的不整,也是使她生出这种对她而言是新奇的感觉的主要原因。
她微一迟疑,猛想起她对人家的存心,脸不觉有些红,想说出自己的目的,想来想去,却不知道该如何搭词。
马上的男女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她,这眼光中包括着的大多是嘲弄的意味,虽然没有说话,但是这种意味已很明显地表露了出来。
于是素性骄傲的夏芸,开始生气,而生气又使她忘记了自己对人家的存心是极端不正的,竟然毫不考虑地说出了自己的企图。
“你们——”她瞬即想起了另两个更适于此时情况的字句,立刻改口道:“朋友——”但是下面的话她依然不知该怎么说。
心一横,她索性开门见山,道:“把身上的银子分一半出来,姑娘要用。”
马上的男女,“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那男的目光中嘲弄的意味,变得更浓了些,忍住笑道:“大王——”
“大王”这两个字一出口,旁边那女子笑得如百合初放。
这种笑声和这种称呼,使得夏芸的脸更红得好像熟透了的苹果。
“大王敢情是要银子,我身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银子,怎么办呢。”那男的极力忍住嘲笑,一本正经的说道。
夏芸暗忖:“他们大概不知道我身怀武功,是以才会的这种表情。”
“你们不要笑,要知道姑娘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你们不拿出来吗——”
夏芸自以为非常得体地说了这几句话以后,身形突然窜了起来。
她武功不弱,这一窜少说也有二丈五六,在武林中已可算是难见的身手了,然后身形飘飘落了下来,依然站在原地。
她以为她所露出的这一手上乘轻功,一定可以震住这两个男女。
哪知道那男的突然仰天长笑,笑声清朗高亢,震得耳鼓嗡嗡作响。
夏芸虽然对江湖门槛一无所知,但听了这男的笑声,心中也大吃一惊,知道这男子的内功,必定在自己之上。
她不禁连连叫苦,暗忖:“我真倒霉,一出手便碰到这种人。”
但是事已至此,她在是骑虎难下,站在那里,脸上已有窘急的神色,本来已红着的脸,现在也红得更厉害了。
长笑顿住,那男的突然面孔一板,道:“你真的想拦路截财?”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倔强,好胜而又骄傲的夏芸,到了此刻,话虽然说得仍很硬,但内在却已有些发软了。
“就凭你身上的那点武功,和这点从关外马贼那里学来的偷马手法,想拦路劫财,只怕还差着一些呢!”
原来这男的见多识广,一眼便认出夏芸制马手法的来历。
夏芸“哼”了一声,又激起她好胜的心理,暗忖:“你内功虽好,姑娘也不见得怕你。”遂道:“那么你试试看。”
那男的又长笑道:“好,好,我知道你一定不服气,这样好了,你从一数到三,我们还不能让你躺下,就将身上的银子全部送给你。”随手将挂在马鞍上的包袱解下,打开来,突见光华瞭目,包袱里竟然全是价值不菲的珍宝。
那男的非但衣着华贵,人也潇洒英俊得很,随手将那包袱朝地上一丢,直像将这些珠宝,看成一文不值似的。
夏芸虽然也是出身豪富,但见了这人的态度,也有些吃惊。
却听那华服男子道:“你开始数吧。”
夏芸嘴一嘟,暗忖:“你是什么东西,我就不相信数到三时你就能怎么样我。”
“一”夏芸开口叫道,身形一掠,双掌抢出,向马上的男子攻去。
那男子又是一声长笑,手中马鞭“制”地飞出,像一条飞舞着的灵蛇似的,鞭梢微抖点,点向夏芸“肩井”、“肩贞”、“玄关”、“太白”四处大穴。
夏芸一惊,口中喊出“二”。
双腿一蹬,身躯一扭,努力地避开了这凌厉的一招。
她口中才想喊“三”,哪知鞭梢如附骨之蛆,又跟了上来。
她再向左一扭,哪知胁下突然一麻,一件暗器无声无嗅地击在胁下的“将台”穴,像是早就在那里等着,而她自己将身子送上却被击似的,口中的“三”尚未及喊出,身子已经倒下了。
这时她心中的感觉,真不是任何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
她生长关外,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从少就是“雪地飘风”的美誉,那时来到江南,第一次受挫于四仪剑客凌云子的剑下,虽然不出二十招,但究竟还算交过了手。
哪知此刻遇见这一对奇怪的男女,一招尚未进出,就已经被人家点中穴道了。
那女的似乎心肠很软,柔声向那华服男子道:“你去将这个姑娘的穴道解开吧,我方才出手重了些,不要伤着了人家。”
夏芸虽然浑身不能动弹,但这个女子所说的话,她却听得清清楚楚,心中不知是惭愧?是感激?抑或是生气。
“你点了人家的穴道,现在又装什么好人。”她没有想到此事的发生,完全是由于自己的不对,反而在怪着人家。
她这么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脾气,已经使她吃过不少苦头,但是她生性如此,正是所谓:“江山好改,禀性难移”,虽然连番吃亏,这种脾气还是一点儿也没有改过来。
那男的带着笑说道:“你的脾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以前不是动不动就要杀人吗?”
“死鬼。”那女的娇笑着骂着,心情像是高兴已极。
华服男子也未见如何作势,身形飘然自马鞍上飞起,衣袂微荡,笑声未绝,落在夏芸身旁,极快地在她身上拍了一掌。
夏芸甚至还没有感觉到他这一掌的拍下,但是她体内真气又猛然恢复了正常的运行,手一动,穴道已经被人家解开来了。
她双肘一支,跳了起来,站直身子,却见那男的正笑嘻嘻地望着自己。
她越想越气,觉得自己受那么多委屈,而且人家双双对对,自己却是形单影孤,感怀身世,不禁悲从中来,竟放声哭了起来。
她本是不懂世事,倔强任性的女孩子,想笑的时候就笑,想哭的时候就哭,丝毫不会做作,也一点不避忌任何事。
那男的见她突然哭了起来,倒真的觉得有些意外和惊措了。
他暗忖:“这个小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到自己的太太,也是这种说笑就笑,说哭就哭的性子,心中不觉对夏芸起了好感。
马上的少女见夏芸哭了起来,心中也泛起同情的感觉,忘却了夏芸方才的想拦路劫财的行为。
原来这马上的少女最近解开了心上的死结,对世事看得都是那么乐观和可爱,对世上的人们也起了很大的同情心。
于是她也飘身下了马,眼前微花,她已站在夏芸的身侧,身法的曼妙,速度的惊人,更是令人不期然而觉得神妙。
“小姑娘,你有什么难受的事,只管对我讲好了。”她抚着夏芸的肩,柔声说道:“只要我能做倒的,我一定帮忙。”
她不但语意善良,说话的声音,更是那么甜蜜,俏娇。
但是夏芸却是倔强而好胜的,人家越是对她表示怜悯,她越是觉得难受,肩头一摇,摇开了那女子的手,恨声道:“不要你管。”
她这种毫不领情的口吻,不但没有激怒那女子,反而引起那女子的同情。
“这个小女子一定有很大的委屈,但是她一定也是个倔强的女子,心中有苦痛,却不愿意告诉人家知道。”马上的女子叹气着忖道:“唉,她这种脾气,倒真是和我有些相像。”
原来这少女也是这种个性,是以她对夏芸除了同情之外,还有一层深深的了解。
“小姑娘,你听我说。”那女子以更温柔的语声道:“无论有什么事,你都告诉我好了,我替你作主,出气。”
她说得那么武断,仿佛真的将天下人都没有放在心里。
但是夏芸仍然抱着头哭着,没有回答这女子好心的问道。
路的那一头,突然蹄声零乱。
恍眼,飞快地奔过来几匹健马,马蹄翻飞,带起一片尘土。
马上的是四个衣穿蓝袍的道人,看到路上有两女一男站着,其中有一个少女像是在哭,不禁都觉得诧异得很。
夏芸听到马蹄声,下意地抬起头来。
其中有一个道人正好回过头来,和夏芸的目光碰个正着。
他心中一动,突然高喝道:“停下来。”
其余的三匹马便一齐勒住马缰,飞奔着的马骤然停下,前蹄揭起,嘶然长鸣,但是,马上的道人个个身手了得,双腿紧紧地扶着马鞍,一点也没有慌张失措的样子。
其中一人“咦”了一声,两眼盯在那两匹被夏芸制住的马上。
但是那一个看来气度最从容,丰神最冲夷的道人,眼光却是瞪在夏芸脸上。
那华服女子冷冷哼了一声,暗忖:“这个道士两只眼睛看起人来贼兮兮的,一定不是好人,我真想教训教他……”
念头尚未转周,却见那道人翻身跳下马来,身手的矫健,迥异凡俗。
那华服男子见了这四个道人的装束,和他们背上斜挂着的带着杏黄色穗子的长剑,眉头一皱,暗忖:“武当派的。”
那道人果然就是武当派的第二代弟子中的佼佼者,武当掌教关山门的弟子,初下武当,步入江湖的飞鹤道人。
飞鹤子看到夏芸,心中一动,暗忖:“这女子不就是那自藏经阁逃出的少女吗。”马缰一勒,闪道:“叫她转告熊倜最好。”
原来熊倜,尚未明乘隙遁去,天阴教主也随即下了山。
临行时,他们还再三地道着歉,飞鹤子想着:“这些天阴教徒,倒没有传说中那么坏。”
哪知当天晚上,一向静寂安祥的武当山,突然发现了数十条夜行人的影子。
这是数十年来,被武林中尊为圣地的武当山,所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那数十条的人影,身法都迅速得很,像都是武林中的能手。
武当派数十年来,被武林视为泰山北斗,当然不会想到此番有人敢来武当山侵犯,更没有想到会聚集了这么多武林高手。
但是武当道人毕竟个个都是训练有素,有些武功虽不甚高,但对道家的“九宫八卦剑阵”,都配合的非常纯熟。
这种严密配合的剑阵,此时发挥了最大的威力,来犯武当山的数十高手,一时也不能将这种道家无上的剑阵破去。
飞鹤子剑影翻飞,突然瞥见这些夜行人其中数人的面容,心中大怒:“原来这些都是天阴教徒。”刷刷数剑,手底更不容情。
武当掌教妙一真人武功深湛,甚至还在江湖中的传说之上。
此时他动了真怒,持剑却敌。
一场大战,天阴教徒虽然伤之不少,但武当派的弟子亦是大有亏损。
这还是天阴教中最辣手的两个人物——铁面黄衫客仇不可和九天玄女缪天雯留守太行山总坛,没有随同前来,不然武当山就更危险了。
焦异行想得到那本内功秘笈的心,是那么深切,是以不惜倾师而出,更不惜树此强敌,不择手段的,居然夜入武当想以强力取得此书。
他原以为武当道人猝不及防,怎能抵敌得住自己和教下如许多高手。
哪知道武当派潜在的实力,竟出乎他想象之外,他久战不下,妙一真人掌中青萍剑出神入化,施展开武当镇山剑法——九宫连环剑,剑扣连环,如抽茧剥丝,层层不绝。
他当机立断,立刻发现如果这样相持下去必定是落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须知他此次夜入武当山的,几乎是天阴教下大半的高手,全部出动,虽然他渴切的希望能占有那部奇书,但是若然为此而伤折自己天阴教的主力,他还是不会愿意的。
于是他一声长啸。
黑衣摩勒一窜冲天,掏出金锣来敲了几下,清朗的锣声,传出很远。
天阴教下的数十高手,来如潮水之涨,去也如潮水之退。
片刻之间,连未受伤的带受伤的,都走得干干净净了。
明月像往前一样,照得这海内名山的外表,泛起迷蒙的银色。
玄真观大殿前后的院子里,倒卧着十数具尸体,其中有武当派的弟子,也有天阴教下的舵主。
为着一个人的野心,这么多无辜的生命死亡了。
妙一真人这才震怒,确定以自己在武林中的地位,遍撒英雄帖,想动员所有江湖中的精锐,再次消灭天阴教的势力。
于是飞鹤子衔命下山,负起通知武林各门各派豪士的使务。
他在路上看到夏芸,想到熊倜和尚未明的武功,也想到他们必定乐于参加这一个行动,于是他勒住马,想将这消息告诉夏芸,让她转告熊倜。
夏芸望见他,惊惶地想起他是谁:“哎呀,武当派的道士追下来了。”她以为飞鹤子和另外三个武当派的第二代弟子,来捉她回山的。
哪知飞鹤子的态度,绝不是她所想象的凶恶,客气地说出了来意。
那两个华服的男女,听到熊倜的名字时,双目一张,紧紧盯在夏芸脸上,暗忖:“原来这个姑娘就是熊老弟的爱侣。”
不问可知,这两个华服男女,就是避居“甜甜谷”里的点苍大侠,玉面神剑常漫天和他幸得回复原貌的娇妻散花仙子田敏敏。
他两人静极思动,略为收拾了一下,仗着山壁的机关巧妙,也不怕有人会发现那稀世的宝窟,便连袂出山了。
他们首先关心到的就是熊倜,田敏敏对熊倜更是感激,因为他使她重得了她最珍惜的东西。
于是他们第一个目的地,便是想到武当山去看看熊倜的结果。
哪知无意之中,却遇见了夏芸。
飞鹤子侃侃而说,常漫天不禁诧异:“怎地天阴教又死灰复燃了。”他隐在深山几有十载,天阴教的重起,他根本一点也不知道。
但是他并没有将心中的怀疑问出来,他根本一言未发,因为他此时还不想将自己的身份说出来。
飞鹤子再三嘱咐着夏芸,见到夏芸点首后便上马走了。
他也曾向常漫天夫妇微一颔首,但是他却绝未想到这个儒雅英俊的华服文士,就是当年名震天下的点苍掌门玉面神剑常漫天。
四匹健马,又带起尘土绝尘而去。
站在上午温熙阳光下,夏芸愕了许久。
田敏敏一连串娇俏的笑声声,使得她自迷惘的忆念中回到现实里来。
她所忆念的,自然只有熊倜,方才她听了飞鹤子的话,知道熊倜果然冒着万难,赶到武当山去援救她,心中的悲痛,霎时之间,就被甜密的温馨所替代,熊倜的一言一笑,冉冉自心底升起。
田敏敏察微知著,见她嘴角泛起的甜意,笑道:“姑娘在想着我们那位熊老弟吧。”
夏芸一惊,起先她惊的是被人说中了心事,后来她却是奇怪这个武功高绝的美貌女子,何以会称呼熊倜为“老弟”。
她暗忖:“难道她也认得熊倜。”心里竟微微泛起一阵醋意,眼光射到田敏敏身上,却见田敏敏的手被握在常漫天的手里,心中立刻坦然,反而有点好笑:“我怎么这么多疑。”
女孩子的心理,永远是最难猜测的,对于她们所喜爱的东西,她们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不允许任何人分享一点。
阳光从东面照过来,照在夏芸左面的脸颊上,夏芸脸红红的,显得那么美丽而可爱。
田敏敏温柔地反握住常漫天的手掌,笑道:“难怿熊老弟这么想你,就是我见了,心里也喜欢的不得了,何况他呢。”
夏芸脸更红,心中却又那么舒服,低首含羞:“你也认得倜……”她终究不好意思说出“哥哥”两字,顿住了话。
田敏敏朝她一夹眼,娇笑着道:“是呀,我也认得你的倜哥哥。”
常漫天微笑地望着娇妻和这个天真美貌的少女打趣,心里觉得那么幸福。
因为已经得到了爱的人,也总是希望别人也得到幸福。
夏芸不安的忸怩着,害着羞,然而她对这一双本是她打劫的对象,却泛起了亲切之感,尤其是在她几乎已是山穷水尽的时候,这种亲切的感觉更是强烈而浓厚,因为她觉得只要是熊倜的朋友,不也就等于自己的朋友一样吗。
她低着头,留心地倾听着不忍见她太窘的常漫天说着他们和熊倜相识的经过。
那些事是那么的新奇而有趣,她抬头望了田敏敏一眼,心里在想着:“难道这么漂亮的人以前真会那么丑吗?如此说来,那种神秘的易容术又是多么奇妙呀。”
田敏敏像是永远都能看透她少女纯洁而多变的心,笑道:“我以前真的那么丑,你相不相信呀。”
夏芸低头一笑,暗忖:“怎么我的心事老是被她说中呢。”
“姑娘是不是想找熊老弟。”常漫天问道。
夏芸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于是常漫天慨然道:“我们也想找熊老弟,姑娘不如就和我们一齐走吧。”
这当然是夏芸求之不得的。
田敏敏娇笑着指着那两匹马说:“不过你可得先将这两匹马弄好。”
想起方才她对人家的举动和对人家所说的话,夏芸刚刚回复正常的脸色,又红了起来,讪讪地走了过去,伸手在马腹背上拍了两下。
那两匹马被制了那么久,但是立刻便又神骏异常,夏芸暗忖:“果然是两匹好马。”又想到自己的那匹“大白”,现在不知下落,心中又不禁恻然。
须知爱马的人,往往将自己的坐骑看得异常珍贵,何况那匹“大白”的确是名驹,夏芸“雪地飘风”的外号,也是因此而来呢。
“姑娘可是在关外长大的吗。”常漫天被她这种纯熟的制马手法,也微觉奇怪,于是试探着问道。
夏芸笑着点了点头,道:“我家在关外有个马场……”她话中含意,自是告诉常漫天她不是马贼,常漫天一笑了然。
他再次探询,在哪里最可能找到熊倜,夏芸毫不考虑地说:“鄂城。”
因为在夏芸的心目中,鄂城那间有古钱为记的估衣铺,是唯一能够知道熊倜下落的地方。
于足他们又渡南河,经襄阳,鄂城,沿着汉水南下。
在绕过大洪山脉的时候,常漫天夫妇便问夏芸要不要到那藏宝山窟中去看一看,好奇的夏芸何尝不愿意,只是却有一种更强烈的欲望使她断然放弃了一看那神秘洞窟的机会。
“我知道我们这位大妹子急着要去见她那个‘倜哥哥’,怎么会去看那个破山洞。”田敏敏甜笑着,又一次猜着了这少女的心事。
一路上夏芸对这位心思七窍玲珑,武功又神奇莫测的田敏敏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三磨着田敏敏,要她教自己。
田敏敏被磨得无法,也只有教她,但是夏芸却一直不满意,她恨不得田敏敏将看家的本事都掏出来,教给自己才对心意。
因为田敏敏那种神奇的暗器手法,奇妙的轻功,和她自父亲万相真人那里学会的一些易容之术,对夏芸的诱惑太大了。
他们只有两匹马,后来虽然凑了一匹,却不是名种,再加上田敏敏和夏芸一路上说说笑笑,不时又教些武功,是以他们走得很慢。
几天之后,他们到了孝感,距离武汉,已经并不太远了。
常漫天自然举止阔绰,将孝感城里最大一间客栈的西面一个大院子全包了下来,店小二像是见了活财神,送茶送水送饭送菜送酒,招呼得无微不至,只希望多得几个赏钱。
吃过了饭,他们在厅里闲聊着,夏芸又道:“敏姐姐,今天你还得教我几套武功才行。”
田敏敏笑着“嗯”了一声,说:“你们看,哪里有这么烦人的姑娘,人家压箱底的功夫都被她迫去了,她还要人家教。”
“不行,”夏芸摇着田敏敏的臂膀,撒着娇道:“你骗我,把功夫藏起来,也不肯教给人家。”她索性坐到田敏敏的腿上撒赖,不依着说:“今天你要是不教给我,你就别想睡觉。”
田敏敏被缠得无法,她也实在喜欢这天真的少女,笑骂着说:“你真是我的魔星,好好,你站起来,我教给你。”
夏芸高兴得一跃而起。
田敏敏说:“不过你可先要做一件事,我才教给你。”
“什么事呀。”夏姑娘着急地问道。
“我坐在这里,你如果有办法将我弄得站起来,我就教你。”
夏芸道:“好。”转了两转,转到窗口,突然叫了起来:“敏姐姐,你快来看,外面有个三条腿的胖娃娃,好看极了。”
田敏敏笑道:“我不看。”
夏芸赌气道:“你不看就算了。”又转到微笑着的常漫天面前,扬起手道:“你再不站起来,我就要用力打他了。”
“我不管,”田敏敏笑道:“何况你那双娇嫩的小手,怎么打得痛他。”
夏芸跺着脚,嘟着嘴道:“敏姐姐最坏了,用这个法子来赖。”突然心中一动,眼珠一转,道:“你坐着,我可骗不起来。”她得意地接着说:“不过你要是站着,我一定可以将你骗得坐下去。”
田敏敏笑道:“你这小妮子好笨,那还不是一样吗?”
夏芸道:“试试看。”
“好好,就让你试试看。”田敏敏说着话,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哈,你被我骗得站起来了。”夏芸拍手笑道:“这回可赖不掉吧,快教我武功。”
常漫天噗地笑出声来,暗忖:“我原以为敏妹妹已经够鬼了,哪知道还有比她更鬼的。”
田敏敏瞪了他一眼,道:“你笑什么。”转脸向夏芸笑骂:“被你这鬼丫头骗了去,来吧,再过几天,我就要拜你做老师了。”
这样一路到了武汉,夏芸想尽各种方法,将散花仙子的轻功,暗器学去了不少,连万相真人的不传之秘易容术,也被她磨着学会很多,常漫天暗笑:“这样一位诡计多端的姑娘,我那个忠厚老实的熊老弟怎么吃得消。”
他却不知道诡计刁蛮的夏芸,在见着熊倜时都时温柔体贴呢。
由武汉到鄂城,即使走得太慢,也只有一天的路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