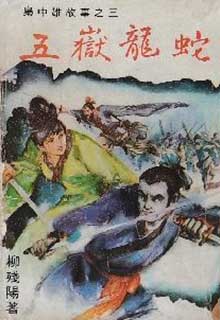上回谈到心灯看完了池佛英丢给他的小纸团,正在低头痴想,突听身后有一苍老的口音笑道:“小和尚,放不下情,你怎能成佛?”
心灯无防之下不由大吃一惊,连忙蓄掌回身,向后望去,只见风扫树梢,衰草迎拂,月光之下竟无半个人影,心中不由更为惊讶,当时朗声道:“老前辈有何指教?请一现侠踪。”
话才说完,便听得树后一阵低哑的笑声,那人笑了好一阵才道:“跟你们喇嘛可开不得玩笑,不然回去念个牙疼咒,我可就受不了了。”
话音甫落,由树后转出一人,心灯见是一年过七旬的枯瘦老头,光秃秃的脑袋,颔下无须,他似乎过于苍老,连眉毛都脱落得一根不剩。
他面色苍白,身材伛偻,似乎是一个重病的老人,一双眸子黯然无色,嗓音沙哑得几乎让人听不清,根本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啊!
心灯见他一步一晃地向前走来,并且不停地咳嗽,不禁由心底油然兴出一股怜悯之情,赶上两步扶着他。那老人已然咳得直不起腰来,用一双枯瘦如柴的手,紧紧的抓着心灯道:“小和尚……咳!……心不坏……咳……”
心灯见他咳得如此厉害,不由大为害怕,连忙道:“老先生,你快坐下来歇歇,不要说话了。”
那老人闻言一阵急咳,顺势坐在地上,心灯心中不忍,便蹲在地上,轻轻地为他捶起背来,并且腾出一只手来,与老人顺气,这样果然好了一些,那老人咳了一阵,渐渐的停止下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道:“没……没关系,我这是老毛病,死不了!”
心灯见他停止了咳嗽,这才稍微放心,问道:“老先生,你这么高的功力,怎么会有病呢?”
那病老人闻言,把一双亳无光泽的病眼翻了翻道:“谁说我会功夫?你怎么知道我有功夫?”
心灯闻言笑道:“老先生,你刚才在我背后说话,我一回头你已出去了一丈之外,我连影子都没看见,怎么能说没功夫呢?我看你功夫还高得很呢!”
老人闻言哑笑了几声道:“就算我有功夫好了。小和尚,你的功夫也不错,你是哪个师父教出来的?”
心灯闻言笑道:“老先生,我师父是枯竹老人,也许你认得呢?”
老人闻言面色突变,急喘了好一阵才道:“啊!你师父是冷古!我是他手下败将呢。可是我如果没有这身病,也未必不能胜他,咳咳!……”
说着他又轻轻地咳嗽起来,两只手紧紧的抚着胸口,心灯在旁看得极为难受,见他咳了好一阵,连眼泪都咳出来了,最后吐出了一口浓痰,才算停了下来,把背靠在树上,不住地喘息。心灯关切地问道:“老先生,你家住哪里?我送你回去吧!”
老人摇头不答,反问道:“冷古教你武艺以前,是否要你答应他什么条件?”
心灯略微思索道:“没有呀!他只说学成之后要我为他办件事。”
老人闻言点点道,面上带着冷笑道:“这就是了,还有两年时间,这两年谁都会着急的,不然卢妪不会出山,我也更不会拖着病出来,再说和尚庙也不会这么乱了!”
心灯听他说话,似乎含有什么深意,连忙问道:“老先生,你都在说些什么呀?”
老人这时突然挺了一下腰,坐直了一点,两眼紧紧地盯着心灯,看了半晌才道:“小和尚,你可愿意跟我学功夫?”
心灯闻言一惊,当下不知如何回答好。老人见状不由大为生气,一瞪眼道:“我生平未收徒,想拜我为师的,在我面前长跪不起,结果我连口痰都不赏他,你以为冷古便真是天下奇人吗?哼,要是我没病……咳……咳……”
老人说着又咳嗽起来,他枯瘦短小的手指,指着心灯不住地发抖,好似气到极点。这一来可把心灯吓坏了,连忙捶着老人的背道:“老先生,你不要生气,我答应你。”
片刻之后,老人停止了咳嗽,用袖角抹了抹额上的汗,说道:“你既然做我徒弟,还不跪下与我磕头?”
心灯当时只好跪在老人面前,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磕完正要起来,又听老人道:“跪着,细听师训。”
心灯只好跪着不动,只见老人枯瘦的面颊上,似乎露出了点笑容,但这笑容很快就被他收了回去,正色道:“我姓骆,名江元,三十年前江湖称我‘病侠’,你也不妨这样称呼。我收你为徒,要在半年之中,传你一种功夫,绝不多传,不过在传艺之前,你也要答应为我办一件事,你可愿意?……”
心灯听罢暗惊,心道:“这个老家伙,又是要我答应他一件事。”
心灯虽然有些为难,却不敢犹豫,当下答道:“什么事情?是否可以告诉弟子?……”
病侠摇手道:“你现在不必问,反正不是坏事,在你们佛家来讲,还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咳!你先答应吧。”
心灯虽然狐疑,可是知道不答应也不成,只好道:“好!病师父我答应你。”
病侠闻言似乎高兴异常,哑声笑了几声,心灯听他声音几乎低哑得听不见,不由大为担心,忙道:“病师父,你不舒服,我送你回去休息吧?”
病侠把头猛摇不答,喘息了一阵道:“你起来吧,明天二更到这里来找我,你可以回去了。”
心灯闻言站起,他实在不放心这个重病的老人,正要劝他让自己送回去,突听病侠又道:“我忘了,你叫什么名字我还不知道。”
心灯连忙答道:“我叫心灯,心腹的心,灯火的灯。”
病侠闻言,低声重复一遍,扬起了脸又道:“心灯!这大概是你的法名,你俗家姓名呢?”
心灯听他问到自己俗家之事,不由有些茫然。他只听老喇嘛说过一次,但那名字对自己太陌生了!当时低声答道:“我的俗家名字叫萧正庸,庸俗得很。”
病侠闻言,突然哑着嗓子大笑,使得他又咳嗽起来,半晌平静过来,对心灯道:“正庸!这也是个出家人的名字,你这辈子是注定当和尚了。这名字很好,一点也不庸俗。”
心灯听他说自己是和尚命,心中反而觉得舒服,实在他早入空门,一旦要他还俗,反是一大苦恼呢。
这时病侠连催他回去,心灯只好作别而去,一路不住的思索,这接二连三的怪事,真把他弄昏了。
心灯回到了布达拉宫,他脑中涌集着过多的思维,一向心如止水的他,竟有华怅然若失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是很轻微的,但他却无法排遣。
夜风吹来,天已三鼓,天边的寒星还在闪烁,月亮已不知何时隐去,心灯这时才觉察到自己的存在。
心灯回到了禅房,他似乎意识到,他的生命要开始转变了,或者说已经在转变了。已经确定了的,是他即将脱离拂门;然而还有没有确定的是,他如何去寻找他的爹娘和送他入寺为僧的人?他的师父要他去办些什么事?病侠又为何要传他武艺?他以后到何处安身?在江湖上又要做些什么?这些都是他深感迷惑,而无法解答的。
心灯痴想了片刻,他突然想起了一事,暗道:“现在天色尚早,我何不到藏塔禅房去看看,也许他正在练‘蚕桑口诀’呢。”
心灯想到这里,再也捺不下心,轻轻的推开了房门。寒月在空,轻风惊树,显得静寂和凄凉,正殿里飘出了袅袅的香烟,想是守夜的喇嘛才换了香烛。
心灯出了房,几个纵身已然到了正殿之后,绕过正殿藏经楼,心灯已可以看见藏塔的禅房了,这时虽已子夜,可是藏塔的禅房仍然燃着灯火,在以往,心灯见了这种情形,心定会想到:“主持大师真是用功啊!”
可是现在他不会这样想了,他已经开始对这位苦修的高僧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他道貌岸然的外貌了。
藏塔的禅房是在第二层,虽然离地甚髙,可是心灯点脚之间,已是十余丈,轻飘飘的落在窗台上。他真轻,连一点声息也没有。
心灯脚才落定,便听一声低沉忧虑的长叹,由窗内传出,心灯听罢不由一惊,心道:“这声音是多么悲惨啊!”
随又听得藏塔沙哑的嗓子,喃喃地自语着道:“从佛不学佛,自作孽。当初一念之恶,今日果得恶果,因果循环,不是佛门弟子,又焉能得知?……”
心灯听罢心中暗惊,思道:“这老喇嘛果然六根不净,不知道他在俗世种些什么恶因?他现在又收到了什么恶果?”
心灯想到这里,又听藏塔喟叹道:“武能防身,武也能害命。早知如此,我又何必苦心孤诣的去学武呢?……”
心灯听到这里,稍微移动了一下身子,由窗缝中向内望去只见明亮的灯光下,藏塔背着手,正在斗室中来回地踱着步,桌案上尚有一卷未曾读完的经卷,和一个红漆的小木鱼。
那藏塔喇嘛双目紧皱,面色甚是愁苦,一反平日安祥神态,他似乎在痛苦和悔恨的煎熬中,愈发显得苍老和沉暮。心灯正在看着,突听藏塔自语道:“依克为贪丧命,我也为贪断指,可是那为凶的人,又何尝能够幸免呢?”
心灯听罢不由大惊,暗道:“原来依克不是他打死的,那两节手指竟是他的!那这又是谁行的凶?”
心灯想到这里,脑中顿时闪过了一个影子,他想道:“莫非是卢妪?别人是不会有这么高的功力的。”
心灯正在惊疏猜度之时,突然见藏塔抬起了双目,精光闪闪地对着窗户道:“‘蚕桑口诀’已然落入别人手中,施主!你还纠缠我和尚做甚?”
心灯知道自己形迹已然被藏塔发觉,不由一惊,才要移动,又听藏塔朗声道:“施主!你既来,又何必走得这么快?我和尚倒想交个方外之交呢。”
心灯听罢不能接喳儿,也不敢再事停留,一翻身扑下了地,向卧房如飞扑去,那藏塔喇嘛并未追来,他连窗户都未开一下,显然是灰心透了。
心灯扑回了卧房,往榻上一躺,他活到现在,简直就没遇见过这么多怪事,他不停地想:“也许我真的该还俗了,不然再在布达拉宫住下去,怪事会越来越多的。”
直过了半个更次,心灯才沉沉睡去。这个出家人,所遭到的事,比普通的人还要多了,可是他同室的七个小喇嘛,却是糊里糊涂的,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何来学佛,他们又能得到些什么,单看他们现在鼾声如雷的睡相,便知在他们信的不是佛,而是魔了。
翌晨,早斋才达,心灯被藏塔召见了,他心中有些慌,想道:“会不会他昨天发现是我?所以今天才找我去?”
心灯在禅房拜见了藏塔,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手中拿着佛珠,而把双手套在肥大的袍袖里了。
灯一个多月未见他,见藏塔面色不佳,似乎消瘦了很多,神态也不如以前那么安祥了。
藏塔容心灯坐好,喟叹一声道:“心灯!你明年中秋还俗,也许……我已经等不及了。你看见我面前这个包袱吗?那是你被凌施主送来时,所留的布施,你现在把它拿回去罢,免得以后我不能亲手交给你……”
藏塔说着,似乎想伸手拿来递给心灯,但他手才略为一动,立刻又收了回去道:“你自己来拿罢!这些大概都是你俗家的东西,十几年来一直放在我这里,我连动都没有动一下,这个小一点的包袱,是你来的时候穿的衣服,你一并拿了去吧!以后,不要再想着回来了,有些人是不适合出家的,我……”
藏塔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心灯惊痴地望着那一大一小的两个包袱,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耳中又听藏塔道:“回去罢,把东西带走,我很累,需要休息一下……”
心灯痴痴然的,把那两个包袱捧起,觉得极为沉重,他痴痴然的转身走去,才走到门口,突听藏塔用着发拌的声音道:“心灯!你回来,我还有话说……”
心灯慢慢地转过了身子,藏塔上下仔细的把他看了一阵,问道:“心灯,你学过武功没有?”
心灯闻言一惊,忙答道:“师父,弟子从哪里去学武功呢?”
藏塔闻言似乎有些失望,他点点头,自语道:“是的,如果现在……唉!太晚了,我当初真没料到……”
藏塔说到这里,才发现心灯还在等自己的话,当时望着心灯,无限惋惜地摇摇头道:“是我糟塌了你这身骨格了,没事了,你走吧!”
心灯双手捧着包袱,心中感到有些莫名的悲伤,他根本就没听见藏塔说些什么,痴痴的奔到了“钟楼”,这是座清静的小石楼,心灯坐在那座庞大的铁钟下,畏畏缩缩的打开那个小包袱。
只见里面包着两件奇小的短衣,全由纯丝所制,触手又软又滑,心灯不由想道:“啊!这就是我来的时候穿的衣服,十八年了,看样子我的家境是不错的,可是他们为什么要送我到这里来呢?”
心灯第一次产生一种被遗弃的伤感,他又慢慢地把那只大包袱打开了,只见里面金光闪闪,大约有上千两的黄金,心灯不由一皱眉,心道:“给我留这么多的钱干什么?……”
再看包袱有一枚月形的石钱,此外别无一物。那枚古钱用极细纫的真丝穿好了,心灯见那枚古钱甚是别致,便拿在手中细看,只见上面浮雕着一付山水画,青葱茂密,甚是精致,反面用篆字刻着“缘生”两个字,此外便没什么了。
心灯见那古钱甚是别致可爱,当下便套在头上,他不禁对那一大堆金子发起愁来,想道:“这些金子怎么办呢?我还是先放起来,也许以后离开这里会用得上呢……”
心灯想着便把包袱系好,捧着回到了禅房,一古脑儿全放在床下,众喇嘛这时早已上课去了,心灯独自一人,坐在床上思前想后,心情好不紊乱。
好容易到了晚上,心灯候到二更,立刻扑出寺来,尚未到达,老远便听见有人咳嗽,心灯连忙加快脚步,心中想道:“病侠倒早来了,他病得可真不轻呢!”
心灯想着已然扑到,只见病侠依然靠在昨日那株大树下,一个劲的轻咳,好似痛苦已极,见心灯来到,他举起了一只手,连连的指着,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心灯见状连忙奔了过去,便要给病侠捶背,谁知他才走到,手还没捶下去,病侠突然一把把他推开,咳着叫道:“滚!咳咳……你不要管我……”
心灯觉得病侠这一掌,力道奇大,自己若非拿势定身,早被他打翻一个跟斗了,但他却不知道病侠对自己为何如此愤怒,惊骇之下,呆呆的站在病侠面前,一言不发。
病侠好似在拼命运气,来阻止他的咳嗽,半晌之后他咳声果然停住了,一面喘着气对心灯道:“记住,以后我咳嗽的时候,你不要再管我,现在你跟我走。”
说罢他摇摇欲坠地扶着树,把身子站起来,心灯见他痛苦模样,心中老大不忍,想上去扶他,又怕他生气,只好站在旁边看着。
病侠站好了身子,用手轻轻弹了弹屁股上的灰,这才对心灯露出了一丝慈祥的笑容道:“有时候我脾气是很燥的,你不要在意,现在跟着我走吧!”
病侠说完话,转身顺着大树向后走去,心灯连忙跟在后面,见病侠步履蹒跚,一步三摇,心灯益发生出怜悯之心,自己若非昨日被他戏弄,简直不敢相信,这奄奄一息,即将垂死的老人,竟然会身怀绝技。
病侠此刻一言不发,默默地在前走着。心灯跟在后面更是无话可说,心中狐疑不定。
那病侠在前,走得又慢又笨,简直不像一个会武功的人,心灯虽然心急,也不好催,他实在为病侠担心,怕他在月夜之下偶一失足,以他年迈病重,只怕有性命之忧了。
又走了好一阵,心灯见已绕到布达拉宫之后,地点更为隐僻,随见病侠用手一指左方道:“以后你每天便到这里来找我,练功夫也在这里……”
说到这里,想是他又快咳嗽了,赶快停止了话,用力的运气蹩着。心灯顺着他手指处看去,在这小丘的左侧,有一个极深的山洞,里面黑黝黝,阴森森的,甚是恐怖,不禁说道:“病师父,这里面这么黑……”
话未说完,病侠已然不悦,把一双怪眼一翻道:“黑?黑怕什么?难道你出家人还怕鬼魔不成?现在跟我进去,沿途不准说话,咳咳……”
说着又咳了两声,一摇一晃地走入了山洞。心灯无奈,只好在后面跟着,心中想道:“怎么人一老就变成怪物了?师父,卢婆婆,还有这个病师父都是这个样子,我将来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大概不会罢。”
心灯心中一直想着,不觉已随着病侠进去了四五丈,洞内奇黑,并且阴湿不堪,心灯用尽目力,也不过只能看出二尺远,黑暗中只听得病侠沉浊的呼吸,和二人的脚步声,竟连一声虫叫都没有。
再往里走,心灯觉得病侠向左拐去,连忙跟了过去,这一拐连洞口唯一的一点月光的反映都没有了,真个是伸手不辨五指。脚下又是崎岖不平,寸步难移。
心灯此刻如在鬼域,两手本能的向前空摸,脚下拖着地,半步半步地向前移动,耳中听得病侠的喘息声,越来显得越小,到后来竟连一点也听不见了,心灯不由一惊,连忙停了脚步,细心听去,不但病侠的喘息声没有,就连他的脚步声也没有了。
心灯这时不由大惊,连忙叫道:“病师父!你在哪里?”
心灯叫罢只听病侠在远处骂道:“我在这呢,你怕?怕什么?走得这么慢,真没出息……”
心灯听罢不由一惊,原来病侠的声音,已在三丈以外,中好生惊异,暗道:“这老怪物怎么突然走快了?他怎么会看得见呢?真怪!他也不咳嗽了。”
心灯想着,听他骂自己没出息,不由得甚是惭愧,勉强地笑了一声道:“病师父,我不是怕,只是……太黑了。”
心灯说完,便听病侠摇首道:“太黑了?你不会慢慢走呀?”
心灯听他声音又远了两丈,当下好不惊异,尤其是他低哑的嗓子,似乎较在外面响亮多了,引起了洞内的回音,嗡嗡不绝,心道:“怪了!怪了!莫非这老怪物,要到黑的地方才有精神?怪不得他有病,原来住在这种地方。”
心灯这时便不再听见病侠声息,一任自己问什么话,他总是不答,当时一睹气也就不再问了,往旁边靠了靠,黑乎乎地往内摸着走。
心灯右手所触之处,只觉水湿异常,并不时碰着软软的虫类,心灯怕是蝎子,蜈蚣之类,吓得把手收了回来,一步一停地往前走着。
心灯右手估计着,已然走了好几丈,可是始终不得病侠声息,心中不由狐疑起来,想道:“不要是病侠死掉了!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
心灯想到这里,不由得害怕起来,立刻放大了嗓子,连叫了好几声病师父,可是依然一点回音也没有,不由把心灯吓慌了,不住地想道:“莫非他真的死了?他要是不理我,怎么连咳嗽声音都听不见?……”
心灯疑神疑鬼地,向前摸着走,又走了约一丈光景,地势渐低,向下倾斜,那病侠始终就没有出过声。心灯这时可沉不住气了,他连脚都不敢抬,就怕自己一脚踩下去,软乎乎的,要是病侠的尸体哪还得了?
灯正在惊恐无状之际,突然听远处似乎有点声息,不由得疑虑全消,暗骂道:“这个老怪物,倒装死来吓唬我呢。”
这时心灯放下了心,继续向前走去,那地势越来越向下,耳中并听得殷殷隆隆之声,心中不由大奇,又想道:“莫非这老怪物把我带到地心不成?”
心灯想到这里,回头向后望了望,深觉回途艰难,突然他脑际,闪电般掠过一个念头,吓得他不敢举步了,他想道:“恐怕他不怀好意吧?要不然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恐怕依克就是他杀死的,藏塔的手指也是他砍断的……”
心灯想到这里,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他这一多心,怪想法越来越多,他又想到:“说不定他是个鬼呢!我佛不是说过,世上是有鬼魔的!”
心灯想到此处,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恰好不知由哪里吹来一阵阴风,水湿湿,冰凉凉的,把心灯吹得一个机伶,吓得几乎叫出声来,他立刻双手捏佛,心里默默念起“金刚经”来了。
他默念了好一阵,始终未见其它异状,也不知是没有鬼,还是被自己念经给驱跑了,这才稍微的安了心,继续向前走去。
又走了片刻,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弯,那病侠好像真是鬼一样,连个影子都没有,心灯这时真是又急又气,想回去也不容易,想着不由愤怒地叫了几声病师父。
山洞空空,回音盘绕,没有一点声音来回答他,这时心灯不由发了小孩脾气,暗道:“我就不相信我走不完这个黑洞。”
此刻的心灯是满腹盛怒,他再也不用手摸,不管死活向前硬闯,这一来果然迅速多了。
心灯正在走时,突听身侧发出低哑的声音道:“好了,徒弟,今天就走到这罢!”
心灯听罢知道是病侠,由于刚才他被他捉弄,满腹怒气未消,当下虽然停止了前进,可是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耳中又听得病侠干笑一声道:“坐下来。”
心灯闻言仍是不动。病侠笑骂道:“你那像个出家人,脾气这么坏……”
心灯被他说得不好意思,只好一屁股坐下,只觉地上泥土又湿又凉,僧衣立刻潮了一大块,不由得更是气上加气。
心灯坐下之后,用手往旁边一摸,只觉手触处冰凉,不由一惊,再一细摸摸,竟是一堆枯骨,自己摸着的正是一个骷髅头,不由吓得惊叫一声,“忽!”的一声站起来。
心灯惊魂未定,耳中又听得病侠不悦地道:“你真是胆小如鼠,不要怕!这是我老伴,她叫吉文瑶,死了十年了!”
心灯听病侠说到后来,声音非常悲凉,似乎在追忆他逝去的妻子,当下说道:“病师父!你为什么不把她埋了?”
话未说完,突听病侠一声怪叫道:“我的事不用你管,坐下。”
心灯虽然觉得病侠脾气古怪,不可理喻,但怪的是他的话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得每一个和他相处的人,都会服从他。
心灯无奈地坐下,把身子稍微向左移动了一下,耳中听得病侠道:“你……就算你是个和尚罢!你给我的老伴念一段超生经。”
心灯听他语音低沉,声调凄惨,不由得受了感动,在黑暗中把头连点道:“好!我为病师母念一段经。”
心灯说罢,顺手摸了一块小石头,在地上轻轻的敲打起来,只听得他“吗迷奄达”地低声念起来。
洞深音长,回声缭绕,僧人梵唱本有一种空灵飘逸的韵味,比较接近悲调,这时心灯情发于中,唱念之间益发觉得悲怆哀婉,令人沾襟。
病侠闭着眼,一颗苍老脆软的心,随着心灯悲怆低沉的调子,在他亡妻的朽骨间低迥萦绕,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他似乎已将人鬼融为一体了。
少时,心灯念完了一段经,突觉两只枯瘦冰凉的手,和一个颤抖的头,扒在自己的肩膀上,发出了一阵凄惨、低沉、断肠、惊魂的哭声,一颗颗湿热的眼泪,滴在他的脖子上。
心灯此刻是又惊又痛,回手扶着病侠道:“病师父,你不要哭,你自己身体不好……”
可是病侠哪里停得住?他的哭声越来越大,可是越来越沙哑,心灯听得鼻头酸酸,几乎也流下泪来,心内暗惊,想道:“这哪里是人的声音?太悲惨了!”
那病侠伏在心灯的肩上哭了半天,突然呼吸又急促起来,想是又要咳嗽了,他突然停住了哭声,心灯只听得一阵急促的抽噎和呼吸之声,但是奇怪的是,他竟没有咳嗽一声。
病侠这时不再说话,似乎在调息,过了半晌,心灯才听得他呼吸变成正常,不由问道:“病师父,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过了一会才听病侠道:“不要再谈这些事了,你是来学功夫的,不是来说闲话的。”
心灯听罢心中好怪,暗道:“来了!他老毛病又犯了。”
心灯想到这里,又听病侠道:“我刚才沿途故意试探你,真亏你还是自幼出家,学过念经坐禅,定力怎么会这么差?”
心灯听到这里,不觉红透了脸,好在是在黑暗里,当下一句话也不敢接。病侠又道:“刚才我虽然不知你心中想些什么,可是我猜也猜得出来,第一,你一定嫌这里黑暗,是不是?”
心灯听病侠问自己,不好不答,只得道:“是的。”
病侠听罢,微微哼了一声,又道:“这就是你生了‘怯’心。第二,你一定嫌这条路太长,是不是?”
心灯无奈,只得又答了声“是。”
病侠接道:‘这又是你生了‘畏缩’和‘厌烦’之心。第三你叫我不应,一定是以为我死了,是不是?”
心灯闻言心内一惊,暗道:“这老怪物莫非会算,怎么也猜得这么准?”
当下只好答应了一声,病侠停了一下接道:“这是你不能信任别人,犯了“疑’心。第四,你在拐角处嘴皮子乱动,一定把我当成鬼了,在那里念经是不是?”
心灯听罢益发惊异,暗道:“他在这么黑的地方,居然看得这么清楚,并且猜得这么准,真是聪明绝顶……”
心灯虽然惭愧,但又不能不承认,病侠又道:“这是你胡思乱想,拿人当鬼,犯了‘欺’心。第五,你在拐角处频频回首,定是想回头,是不是?”
心灯无话可说,点头答是,病侠仍然滔滔不绝说下去道:“这是你存了‘侥幸’之心。第六,你最后大声乱叫,定是生了气,愤怒之下,不管东南西北地往前闯,是不是?”
心灯被病侠一连串问得羞惭万分,病侠冷笑两声道:“这是你犯了“嗔’心。唉呀!我看你这个和尚也真是白当了,武艺也白学了,干脆回去娶老婆抱孩子去吧!冷古也不知怎么找的?……”
心灯被他损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偏是自己无话可说,只得苦笑道:“弟子太无能了,还请师父多多栽培……”
话未说完,病侠打断他的话道:“你不要灰心,我刚才如此骂你,并不是说你不可造就,事实上你的骨格、天赋都是天下罕见,否则我也不会传你功夫了。”
心灯闻言心下略安,连口称是。病侠老气横秋的哼了一声道:“心灯,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传你功大?再者传你什么功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