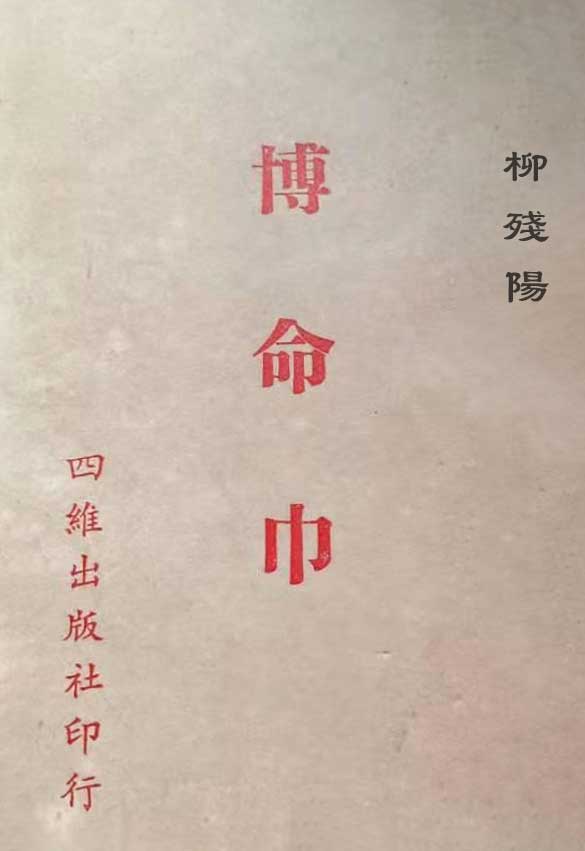暴客嘿嘿冷笑数声,不躲不避也不回抗,动也不动。
“小伙子,你这算什么?”
怪人够怪,也竟然倏地收势,似乎不愿意去打一个并不还手的人,并且极不高兴的质问蒙面暴客。
暴客冷笑声停,却仍不开口说话。
“回答与否,是你的事,傻老太爷并不生气,只是你要再拦阻我的去路,我可真的恼了。”
暴客冷嗤一声,指指地上的独孤令,又指指自己,再指指身后。
“你改变了主意,不杀小令儿啦,想带他走?”
怪人懂得暴客手式,出言相问,暴客点了点头。
“刚才傻老太爷就说过,小令儿留给你杀,谁知你举了半天手,却莫名其妙的叹息一声跑,现在又想带他走,好,过来带他走吧。”
暴客又摇了摇头,大概又变了主意。
“傻老太爷没功夫和你耗,你要……
暴客未容他把话说完,手指指他,又向远处一指,最后挥了挥手。
“哈哈!你是要我傻老太爷扔下小令儿一个人走?”
这次猜对了,暴客点头不迭。
“小子,天下没那么好的事,要人,你过来当着傻老太爷的面带走,要打,你小子就先动手,什么都不要的语,你就给我快点滚。”
“嘿嘿……哼哼……”暴客轻蔑冷酷地冷哼不绝,就是不说一句话。
“小子你听着,傻老太爷已经不耐烦了,我不愿意和不回手的人打斗,你再拦路胡闹,可别说我下手狠毒。”
说着他回身探手抓向独孤令,暴客突然无故大喝一声,此时怪人右手业已伸到了独孤令的腰际,闻声不由微停。
那知就在这略以停顿的刹那时刻,先机已失,右手腕间“脉腕”大穴,突然一麻,右臂连肩立失作用。
怪人一声怒吼,左掌疾若石火电闪般,劈向地上倚树而坐曾被点中穴道无法挪动的独孤令而去。
谁料独孤令倏地滚出丈外,挺身而起,飞越白衫暴客身后,忙似丧家之犬,逃之夭夭。
这时白衫暴客陡地扬臂对怪人大喝一声“看掌”!双掌随声凌虚打下,力道强极,风劲势猛,怪人右臂失灵,被迫纵避。
暴客得势不让,一连攻打四掌,怪人已退后了十丈。
此时独孤令,已逃出数十丈外,仅剩了一个极淡的影子。
怪人右臂肩膀一时无法复元,手指白衫暴客怒声叱道:“傻老太爷一时仁慈,又因为独孤令作恶太多,错认你是他的仇家前来报复,不忍伤你,谁知竟然被你所骗,假言必欲杀他,虚抬掌指,实在却是解了他的穴道。仍恐时间不久,他无法逃遁,再次转回诱我上当,我老头子六十年未在江湖走动,谁知再出江湖就为人所算,此耻难忘。看你一身功力,胜过独孤令多多,竟然是非不分,我老头子为你悲痛,目下右臂虽伤,仍能一搏,但那独孤令既已远逃,我老头子今夜认输,小子你走吧,咱们总有再见的时候。”
白衫暴客听怪人说完,一言未发,却蓦地扑俯于地向怪人施一重礼,随即飞身而起,疾若电掣向独孤令逃路追去,一闪而逝。
怪人为暴客的骇人举止所惊,一时不知如何才好,直待白衫暴客身影消失暗中之后,方始啊吁一声惆怅而去。
独孤令自西园寺中被怪人所擒,自忖此去后果不堪想象,那知救星天降,穴道自解,乘怪客不备,点其“脉腕”大穴而逃。
当他逃时经过暴客身旁,曾施展“冥目”神功,透视这人的面貌,可惜这人披头的银纱为特织之物,无法看清。
但他却已知道这人发长二尺,发际并透传一股奇特的幽香,故此独孤令暗中断定这人当系女子。
虽说这人嘿嘿冷笑声音阴森,独孤令却认为江湖多诈。凭自己的阅历和经验来说,这人故意矫作的成份极大。
他要仔细地思考一下,这人突如其来救他的因由。
白衫蒙面之人,向怪客突地跪拜之时,藏身较远暗处的独孤令看的非常清楚,他心头一动,似生警兆,想要远遁却又甚感犹豫,是故踌躇了片刻,这时白衫蒙面之人,已电射而至。
恰在这个当空,独孤令方才恍然有悟,暗忖要糟,必须远逃,无奈时间已晚,暴客电掣追到。他内心忐忑难安,料到虽脱虎口,恐将陷身龙潭,不由暗中提聚全身真力,以备万一打算。
那知暴客自他藏身之地经过,停都未停,若一片白云般飘飞远下,眨眼越出枯木树林,隐于黑暗之中。独孤令暗中嗟吁一声,悄然回顾白发黑髯的怪人,谁知就这刹那之间,怪人业已走得无踪无影。
他深为自己庆幸,但并不立刻登程出林,大约又隔了顿饭光景,方始断定自己平安无事,这才闪身出林,飞纵前行。
出林之后,即为农家稻田,时值严冬,今朝虽未降雪,但前数日连天大雪纷飞,故而大地仍是一片银白。
独孤令飞驰于坚冰之上,迅捷至极,行已里路,蓦地止步。
前面数十丈外,枯叶三五,其间似乎站着一人。
当他仔细端详半晌之后,不由暗哼一声惭愧,这般时候怎会有人?不过是农家为惊禽鸟所扎放田间的稻草人罢了,自己乍脱敌手,竟成惊弓之鸟,疑神疑鬼,想来怎不惭愧。
再次举步,十丈距离转瞬已到,他心中虽已无疑,却仍然止不住双目瞟向那个稻草人看去……
稻草人身上并无半丝雪迹,但却浑身雪也似的白。
他惊凛地一声呼叫,倏地止步才待后退,稻草人却横移了一丈,站在他的面前,嘿嘿地不停冷笑。
独孤令猛的一个寒颤,退了三步。
“你刚来?我候你多时啦。”
稻草人怎能说话?又怎能纵飞横飘,是人,是个活人,正是适才解开自己穴道的那个白衫蒙面暴客。
独孤令惊退三步,当时竟然木怔在那儿,讷讷不能接话。
“怎么?我站在此处相待,太也出乎你的意料了对么?”
白衫暴客语调冷凛,一个字一个字,就象是被人捏着脖颈硬挤出来的一样,生冷地丝毫不带活人口气。
“在下不能对恩者说谎,阁下站立于此,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在下却非常高兴,因为……
“因为什么等会再说吧,你可知道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等你?”
“实难猜测。”
“很简单,这里数里之内,一片冰雪,你无法躲避我。”
“这个……”
“这只是原因之一,再者,此乃你必经之路。”
“是在下必经之路不假,但我却不想躲避阁下。”
“你这是真心话?”
“阁下对我曾有救命之恩,我怎会……
“说的好听。”
“阁下不信我又能奈何。”
“你怎能令我相信?”
“这一点请恕在下,确实无法证明。”
“嘿嘿嘿嘿嘿嘿,我却能够证明你是有心躲避。”
“阁下要这样说,叫我有口难辩。”
“当真如此,适才在枯柳林内,我驰过你身旁之时,你怎地一言不发,故作未见呢?”
独孤令梦想不到白衫暴突出此言,竟无法回答。
“哈哈哈哈,这一点事情我并不挂在心上。”
“阁下必须宽恕我当时不能出声呼唤的罪过,那时候怪人尚在,在下已成惊弓之鸟,万不得……”
“我刚才说过,那是小事情,过去就算,你不必解释。”
“如此在下多谢……”
“这‘谢’字你说早了些,独孤令,你可能猜得到,我今夜为什么不惜犯险而救你脱身吗?”
“阁下知道我的名姓?不能不使人惊奇。”
“别打岔,我知道你的事情太多了,现在先答我所问。”
“独孤令一向笨,实不知阁下为何救我。”
“哼!令兄独孤大侠,昨日饶你不死,故此我才出手。”
“阁下怎的无事不知?家兄……”
“最大的原因,却是为了圣心大师夫妇,和那两个可怜的孩子。”
“噢!阁下都是认识他们?”
“问这些无用的话作甚?走,现在你跟我走!”
“走?请问阁下要带独孤令到什么地方?”独孤令一边回答,一边又退了两步。
“怎么?你不想去?”
“独孤令尚有要事……
“哈哈哈哈哈哈,尚有要事?今夜若是没有我犯险出手,此时你必然已经高吊在巨干枝头,供冷嫱祖孙戏谑讥讽,就有十万火急的要事,你又能如何?干脆点说,你愿意不愿意去吧?”
“阁下施人重恩,今又强人所难,似乎有些……”
“独孤令你仔细点听着,救你之事,出我自愿,既非你所告求,因此咱们无‘恩’可言。”
“设若阁下准我如此放肆,独孤令可以立即回答阁下,我不愿意跟你去。”
“我却一定要你跟我去。”
“那还是挟恩以……”
“不!适才我已说过,咱们无恩可言、”
“果如阁下之言,你我彼此不欠恩情的话,独孤令立即告辞。”
“慢!你决定不跟我去了?”
“早已决定。”
“你不愿去我却一定要你去,独孤令,咱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请恕独孤令狂妄,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你似乎已经知道这将如何解决……”
“不错,独孤令已经料到阁下要用的办法了。”
“因此你敢坚决的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独孤令适才被擒,只因事出突然,否则那银发长髯的怪叟也许……”
“也许早已惨死在你那‘血印’禅手之下了,对吗?”
独孤令闻言再次悚然后退,惊凛惧骇地看着这位白衫蒙面暴客。
“怎吗?你在惊骇诧疑我无所不知是不?”
独孤令并未答话,双眉紧锁似在思索一件重大的事情。
“独孤令,以你平素行事的狠毒来说,适才枯柳林中,逃出怪人掌握之后,必然立刻报复雪恨,为什么却一言未发飞纵远逃呢?”
独孤令冷冷哼了一声,目射凶光,仍然没有说话。
“知已知彼百战百胜,独孤令,这就是你聪明的地方。”
“莫非阁下认为独孤令的‘血印’禅手,还敌不过那长髯怪人吗?”
这次独孤令在忿怒之下,冷冷地接口反问暴客:“独孤令,‘血印’禅手,乃人间第一奇功,若能练到上乘‘百虚’绝顶,天下无人能敌。”
“哼哼!那阁下所说‘知已知彼’之言,又当何解?”
“很简单,你应该比任何人更明白这个道理!”
“恰恰相反,独孤令不明阁下所指之事。”
“你这‘血印’禅手,如今已有几成火候?”
独孤令暗吸一口冷气,没有回答。
“你只有三成功力,能够对付那位怪人吗?”
“阁下怎敢妄批我这‘血印’禅手,仅具三成功力呢?”
“千人石上留有你的血手印,难道你忘记了?”
“你是谁,你自始至终暗地里跟踪着我独孤令,所为何事?”
独孤令十分惊骇,突然疑心到一个人,故而沉声追问。
“独孤令,你告诉过我你是谁来没有?”
“没有!”
“我问你没有?”
“没有!”
“那你问我是谁,岂非聪智不足?”
“独孤令不愿和阁下争论不休,若无他事,我要走了。”
“你不想替我解决那个问题?”
“那一个问题?”
“我要你跟我去,而你偏偏不愿意去的问题呀”
“阁下再若苦苦相逼,独孤令可要被迫动手……”
“这倒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不管阁下说些什么,独孤令总是蒙受过……
“没用的话少说几句,独孤令,咱们立即动手一搏,尔胜,走你阳关大路,败时,只好跟我去了。”
“你认定非此不可?”
白衫蒙面的暴客嘿嘿一笑,似乎不肖答复。
“阁下认为战有必胜之券?”
“也许?”
“阁下与圣心大师等人,有何渊源?”
“等人二字包括太广。”
“我是指着与圣心之死有关系的人物说的。”
“独孤令,你不也是关系人物之一吗?”
“阁下怎地顾左言右,独孤令要明白阁下是敌是友?”
“非敌非友,专管闲事的朋友。”
“阁下救我……
“那是我的事情。”
“话固然是对的,但事实却不容两件事情分开来讲,独孤令虽不敢自言乃道义之士,但忘恩……”
“越说越多,独孤令,你可知道我为什么救你?”
“阁下似乎曾经说过,这是为了圣心夫妇及那两个娃儿。”
“不错,所以你必须跟我去一个地方。”
“在下实在不懂,阁下坚持要独孤令相随远行之事,和圣心夫妇及两个娃儿有什么关联?”
“告诉你也无妨,这两件事……噢,还是不说的好。”
“独孤令不敢强求阁下一定要说,不过我确实还有十万火急的事情待办,阁下能否谅及我的苦衷……”
“可以,但是却要答应我一个交换的条件。”
“也好,请讲当面。”
“你要不跟我去,那就必须在我两个原则中选一个。”
“阁下不是说一个条件吗?如今……”
“两个原则之中,任择其一,岂不更方便些?”
“方便与否,必须阁下说出来才知道。”
“你要不要听吧?”
“好好好,洗耳恭听。”
“第一个原则是,你我一搏,你胜,尽管请走……”
“请讲第二原则。”
独孤令此时已经有些恼了,因之声调沉重。
“第二个原则是……唉,人言独孤令聪慧过人,今日一见……”
“阁下能否专说正题,其余闲话尽多空暇……”
“这不是闲话,和正题关系……”
“请问第二原则。”
独孤令突然接口,一个字一个字沉重锵然。
“哼,第二个原则,要你猜猜我是何人。”
独孤令闻言煞眉紧皱,沉思不答,半晌之后,他突然扬声哈哈大笑,手指着白衫暴客那蒙面的纱巾,倏地白衫蒙面的暴客,未等独孤令狡谋发动,冷酷而怪异地霍霍干笑了数声,缓缓将蒙面的纱巾取了下来。
这个行动,出乎独孤令的意料,他不禁呆在当场。
蒙面暴客纱巾虽然取下,但却黑发披散,根本不见面目。
“独孤令,我不会取巧,纱巾已经摘下,你要是选择了第二个原则的话,别再延迟,开始猜吧。”
“奇怪?真奇怪,令人百思不解。”独孤令注目暴客良久,喃喃自语,连道奇怪。
“取巧无用,独孤令,你说是选择那个原则?”
“满头黑发,长有三尺,柔软细松不类……阁下到底是……”
独孤令猜了半天,突然心中一动,刚刚说出“阁下到底是”五个字来之后,却又无故停顿了话锋。
“独孤令,再不声明选择那个原则,我可……”
“慢着!唉,看来咱们只好一搏而定去留了。”
独孤令本来仍然想选择第二原则,但他几经思索之后,认定毫无把握,故而吁叹一声,选了搏战一途。
白衫暴客冷笑一声,缓缓重新披好银纱,才待开口……
“我想起来了,阁下这个办法极不公平!”
“独孤令此言怎讲?”
“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呢?”
“听我的有你的好处。”
“利害我自己知晓。”
“依你说,要怎么办才公平呢?”
“我也提两个原则,也任凭阁下选择其一。”
“真称得起狡猾难缠,好!不过原则之中,不能有两可之事。”
“那是当然。”
“说吧,这次轮到我洗耳恭听了。”
“第一,适才独孤令曾经说过,有十万火急之事待办,阁下猜测一试,独孤令待办之事为何?”
“第二呢?”
“请先试猜第一,阁下若能言中,岂不省去不少……”
“独孤令,你这个办法公平吗?”
“第二,你我皆知圣心夫妇已在千人古上自了,家兄独孤占,曾经蚀石为柩,掩葬他们,如今尸首突然失踪,阁下可能猜到内中的原故?”
“这一件事……”
“阁下莫急,独孤令言尚未尽,关于第二原则,必须要使我亲眼目睹才行,否则空口白话,岂不人人会说。”
“猜中如何?”
“阁下若能猜中,独孤令决无异说,相随阁下而去,任是虎穴龙潭刀山油锅,死而无憾。”
“独孤令,你是不是已经放弃了我所……”
“不错,对阁下所提出的两个原则,独孤令自愿全部认负,不过阁下要是无法猜到我这两件事情的话……
“任你自去。”
“君子之言?”
“虽死不毁。”
“阁下猜吧。”
“假若我能够猜到你这两件事情的话,独孤令,那时候又当如何?”
“得一,今夜之行由你分派,二者俱中,要怎样你说吧。”
“二十年内,你不得违抗我的命令。”
“哈哈哈哈哈哈,阁下原来另有居心?”
“没有用的话少说,你肯不肯吧。”
“独孤令是否能够再活二十年,自己真没把握,俗语说得好,舍不得孩子捉不到狼,咱们就这么办!”
“独孤令,大丈夫一言……?”
“如帛染皂。”
“好,你可有引火之物?”
“阁下之言令人费解,猜测事端要什么引火之物?”
“我自然有用。”
“引火之物……巧极啦,独孤令身旁正带着引火的硫磺弹……”
“嘿嘿嘿嘿嘿,独孤令,冷嫱那‘九迥火弹’你还是少动为妙。”
独孤令闻言面色一变,不由暗中惊凛不已,自己囊中之物,和心头所想之事,这怪异的人物竟能知晓,他焉得不怕。
“你左袖之中,有个火摺,何不取出一用?”
独孤令越法震惊,无可奈何的取出火摺,抖手扔给了蒙面暴客。
蒙面人嗤笑一声,接到火摺,从囊中取出来了一段细枯松枝,幌动火摺,将枯枝点燃。
枯枝烧到寸许之时,蒙面人“噗”的一口劲气,将火全部吹熄,所烧那部分,化为乌黑的木炭。
他抖手将火摺扔还给独孤令,又自袖中取出来了一张淡黄色的极薄羊皮,羊皮叠成小方,抖开大有尺半。
“阁下一应俱全,独孤令能拜问一句,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么?”
“有,非它不可。”
“请教请教。”
“我没有用处,这是给你预备的东西。”
“阁下之言,使独孤令莫测高深?”
“独孤令,我要猜你所出的两个问题。”
“猜尽管猜就是了,和这些东西……”
“你所出的问题,第二项用不着这些东西,但是第一项却少它们不得。”
“请接着说下去,如今独孤令自觉已成了丈八的佛爷,无法摸到头脑了。”
“你不是要我先猜你要办的事情吗?”
“不错。”
“假若我猜对了,你偏说不是的话,我怎么办?”
“阁下怎能这般轻蔑我独孤令?”
“独孤占老英雄,乃是你胞兄,你尚能暗施诡谋以九迥火弹悄下毒手,我焉能不多存一分戒心?”
“好,算是阁下有理,那和这……”
独孤令刚要说出,那和这些东西也没有关系的话来,突然心中一动,脑海内掠过一个意念,面色倏变苍煞,止住了话锋。
“独孤令,你已经明白这些东西的用处了,不必再要我解释了吧。”
“阁下是要我将待办急事,写在这张羊皮之上留为凭证?”
“不错。”
“你这枯枝,羊皮,是专为和独孤令打赌而备?”
“不错。”白衫蒙面之人,冷冷地淡然回答。
“你怎能预先知道,我独孤令会答应你赌猜问题呢?”
“这一点恕不作答。”
独孤令惊骇至极,设若果如这人所说,一切早已料到,二十年……
他想到这里,暗中摇头自觉好笑,世无神仙,那能前知,又将悬心放下。
“请将你待办之事,简略写明于羊皮之上吧。”
“恭敬而从命,独孤令倒不信这个邪。”
说着,他接过了炭枝和那张羊皮。
“独孤令,稍停在我猜完之后,取出羊皮对照,上面假若并无字迹,或文不成句模棱两可的话,那……”
“那就算我输了。”
“如此请写。”
独孤令微闪身形,飘出两丈以外,蒙面人动也不动,视若无睹。
独孤令略加思索,即用炭枝在羊皮之上写了,刹时完毕。
“君子不处嫌疑之间,独孤令,你接着这块纱巾,将羊皮上的字迹,反折于内,然后卷成一卷,再用纱巾包好给我。”
“什么?这羊皮给你,那……”
“莫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我若妄自窥视,即算是输。”
“阁下难道不能张袖相接?”
“正合吾意。”
独孤令这才点头应诺,蒙面之人早将另一条纱巾取出,远隔两丈有余,蒙面人二指微曲一弹,纱巾竟若疾箭般射向独孤令的前胸。
独孤令心头一颤,暗吸一口冷气,自忖绝无如此身手。
接过纱巾,裹好羊皮,他一言不发,悄没声地抖手打向蒙面人的小腹。
蒙面之人一声冷笑,右臂伸甩,纱影微闪,已被收进袖中。
“阁下好身手,独孤令自叹弗如。”
“何必自谦忒煞。”
“敢请即猜在下欲办之十万火急大事如何?”
“不,我要先猜第二个问题。”
“任凭阁下。”
“第二个问题,你曾说过要目睹而证实才算?”
“说过。”
“我知道圣心夫妇现在何处……”
“阁下是说知道圣心夫妇现在何处?”
“是呀?”
“不是圣心夫妇的尸体?”
“谁说不是?”
“那,阁下所说‘圣心夫妇’现在何处一言,是说他夫妇的尸体了?”
“独孤令,死人能活?”
“自然不能。”
“那你何必多提这些题外的文章?”
“算我多口,阁下请继续前言。”
“稍待在我猜完全部问题之后,带你去亲眼看看。”
“自千人石上,掘出他俩尸骨另外觅地掩葬之人,莫非就是阁下?”
“不是,大概是你。”
“阁下怎地笑谈起来,独孤令没干此事。”
“那你怎知是我所为?”
“阁下声言知道运葬之地,设若并非阁下所为,那又是何人……”
“这个不在题目之内。”
“在!独孤令问得是‘内中原故’!”
“果有‘内中原故’之言,好,我答覆你这句问话,圣心夫妇运葬之事,我曾亲眼目睹。”
“独孤令问得是那人……”
“抱歉之至,你问得是内中原故,原故已如上述,至于是谁所为,恕我眼拙,不认识他们。”
“他们?听阁下之言,对方是……”
“两个人。”
“噢,这就难了,要是只有一个,我是能猜到是谁。”
独孤令闻言之后,不禁自语喃喃。
“我也知道你会猜他是谁。”
“阁下似乎有些仙气。”独孤令愤念不服,有意讥讽。
“世无神仙,不过我却一猜必中。”
“哼!大言不惭。”
“也许,你猜那个人应该是令兄对不?”
独孤令这次却未接话,他只紧皱着眉头。
“你料错了,令兄彼时并未在场。”
“阁下由何得知我要猜的那个人就是家兄呢?”
“难道不对?”
“对否无关紧要,阁下曾经说过,莫论闲事,怎地却又谈起来没完没结了呢?”
独孤令无言可答,迫而夹缠放赖。
“是你问我,否则我又何必多费唇舌?”蒙面之人一句不让,沉声质问独孤令。
“这仍然是闲话,请继续说第二个问题的下文吧。”
“没啦。”
“什么,没有下文了?”
“下文虽有,那是我带你目睹才行,所以用不着多说空话。”
独孤令想了一下,果然再无话说,不由摇了摇头,暗中佩服蒙面之人的机警和聪智。
“你摇头作甚?”
“阁下管得真多,第二个问题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那第一个问题,阁下却还只字片言未发呢?”
“着急什么?”
蒙面之人说到这里话锋一顿,左手隔衣服捏了捏那卷羊皮。
“喂喂喂!阁下动它可就算输了。”
“独孤令,这是羊皮,不是竹简,你能隔着袖子摸出\字来?”
“阁下善于狡辩,独孤令自愧不如。”
“好说好说,难得难得。”
“阁下何必调侃于我,难道第一个问题猜不出来?”
“恰恰相反,和我早就准备妥羊皮枯枝一样,早已知晓。”
“说出来听听才能证明。”
“独孤令,你要不要先看看圣心夫妇?”
“当然要,哦!不不不,阁下还是先猜问题的好。”
“你听着,你那第一个问题,是……”
白衫蒙面之人,话锋突然无故自停,独孤令冷冷笑出声。
“你笑什么?”
“阁下不必管我是哭是笑,请猜问题。”
“独孤令,你认为我遭遇到了困难?”
“阁下聪慧无伦,言必有中,独孤令不敢轻视。”
他趁机回敬一句讥讽的话语,随即更得意的哈哈大笑。
“唉!可怜可叹。”蒙面之人在独孤令笑声乍停之时,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那个可怜,谁又可叹?”
“自然是你。”
“原来阁下生具菩萨心肠。”
“试想,你就要二十年……”
“独孤令虽然自认曾受阁下之恩,但却断难永远忍耐阁下无尽的侮辱和冷蔑,敢请莫使在下极端为难。”
“独孤令,你还有什么必须要办的事情吗?”
蒙面之人不理他的这番言语,反而再次郑重地这样问他。
“只要阁下猜中羊皮上所写……”
“我必须声明,我并非要猜羊皮上写的什么,而是猜测你口口声声所谓十万火急待办的大事。”
“两者有何分别?”
“有如天地云泥之别。”
“独孤令不懂。”
“设若你故弄狡狯,在羊皮上书个圈圈,或者点些点点,而要我按照羊皮上面的东西去猜,我岂不是输得冤枉?”
“我说不过你,但是羊皮上独孤令明明是写……哈哈,阁下真叫厉害,原来你在试探我是否真的写……”
“不错,如今我已经知道,你果然守信。”
“独孤令不须再耗时光,阁下要猜请快,否则作罢。”
独孤令处处跌落蒙面之人的计谋之中,不由有些恼羞成怒了。
“你要办的十万火急之事,乃寻索圣心大师同另外一个乳娃儿的下落。”
独孤令连退了三步,痴呆呆怔在一旁。
“你目睹令兄独孤占老英雄,仅仅携走一个娃儿,是故动了寻找另外那个娃儿的念头,适才你我在此相逢之后,你无心中由我蒙面的银纱之上,霍然记起来了圣心大师幼年间的那位乳母,你巧而又巧,前数月发现那位乳母,居住苏州城内,你判断另外一个娃儿,必然寄养……”
“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圣心幼有乳母之事,乃我……乃我故友家中私事,你却仍然知道,这……”
“这第一个问题我猜得可对?”
“对,独孤令绝不狡赖,不过你却必须赐下名姓……”
“抱歉,这一点并无约定。”
“否则独孤令宁落毁约背信之名,立即告辞。”
“这个也任凭自己,只要你能够走得了。”
“阁下功力虽然胜我不少,但我自信仍然能够逃出你的手中。”
“未见得吧。”
“天光将现,旭日即升,我逃你追,天亮以前你绝难擒我,我往苏州城跑,青天白日之下,看你怎样……”
“好主意,其实想错了事情,打错了算盘。”
“未见得吧?”
独孤令竟然也用“未见得吧”这四个字,来回敬蒙面之人。
“你没有机会了,独孤令!”
“哼哼!笑话。”
说着他身形倏地飘起,又退后了两丈多些,蒙面之人竟未追赶。
“独孤令你逃必死,我决不追赶。”
“大言恐哧无用,我……”
“我那张羊皮上涂着奇毒的药物,不信你尽管走吧。”
蒙面之人说完这句话之后,竟然不再闻问独孤令去留,反而转身走去。
独孤令大吃一惊,扬喝一声暴然扑到。
独孤令闻知已中暗算,自是恨怒至极,以十成劲力发掌,直袭蒙面人的后心,并且是身手俱到,迅捷无伦。
白衫蒙面之人,此时已经走出丈远,闻声并未停步,也不躲闪,仍然是缓慢地迈着步子。劲掌挟风而来,他却视若无觉。
独孤仅狞笑一声,掌化为指,点向“脊心”。
蒙面之人一声轻笑,身形倏忽飘前丈余。
独孤令一招走空,冷哼一声,如影随形再次扑到。
蒙面之人突然上身一挺,未见用力,已滑出三丈以外。
独孤令目露煞火,右臂轻抖,若闪电般追上。
右臂适时,已高高扬起,动作缓慢,不知因何如此。
阡陌尽为雪掩,一片冰莹,蒙面之人脚步未举,却滑行不已。
追逃十数丈后,独孤令已到对方身后。
首尾相连,他才再次暴喝一声,高扬着的左臂,斜劈而下。
这一掌竟无风力,因此蒙面之人似乎尚未发觉。
独孤令目睹对方根本未防,料难逃脱,不由桀桀狂笑。
谁料奇变陡生,事出意外。
独孤令只觉得对方在自己掌力下压的刹那,白衫轻摆,面前雪影微闪,突然消失无踪。
掌力击空,冰雪田间却平添了一个丈大的手印,深有一尺,清晰至极。
独孤令倏地暴转身形,他不必多想,蒙面之人既在身前失踪,自然是施展绝顶的轻功避向自己身后。
那知回顾之下,身后竟也空无人在。
“刚刚我料错了一事,如今应该补充说明。”
蒙面之人这时却又在他身后发话,独孤令霍地旋身转面。
谁说不是?对方正站在他那丈大的手印旁边,俯身静观。
独孤令心中一凛,暗地惊骇蒙面之人卓绝高超的武技和造诣不已。
“独孤令,适才我曾说过,你这‘血印’禅手仅具三成火候,如今我必须补充声明,你已练到四成。”
“管它三成四成,你再吃一掌。”
左臂暴抖,右掌斜甩,独孤令声言一掌,但却双掌齐下。
蒙面之人倏地抬头,嘿嘿冷笑两声。
独孤令这次全神贯注,他不信对方还能一闪无踪。
“虽然我曾说过对你无恩,但却更无怨恨,你竟施出这种无敌的内功,一再暴下毒手,饶你不得。”
蒙面之人竟不闪避“血印”禅手,反而沉声训叱不休。
独孤令一向心狠意毒,既与为敌,莫不心存致敌必死。因此他耳闻蒙面人喋喋不休,暗中甚喜。
那知事与愿违,独孤令全付真力所发之两掌,非但未将蒙面之人震死当地,竟若石沉大海,渺无消息。
独孤令这一惊如同危岸失足,江心崩舟,全身蓦地一阵寒凛。
“哈哈,嘿嘿嘿嘿嘿,你要不要再发一掌试试?”
独孤令那里还敢迟延,他一言不发,霍地转身飞逃。
“慢着点,前面有人!”雪影一闪,蒙面之人已经站立身前。
“唉!独孤令认输。”
他一声嗟叹,自认败北。
“如此请直向左方前进。”
独孤令点了点头,一言不发俯首疾走。
“你既自认败北,设或中途再生异意,休怪我……”
“阁下不必逼人太甚,独孤令求生之念无法……”
“随你,只要你舍得这一身功力就行。”
“阁下竟然如此狠毒?”
“也许,但愿你不会舍身相试。”
独孤令不再开口,他正沉思脱身毒谋。
飞纵迅捷至极,独孤令霍地停步不前。
“目的地未到,停步作甚?”
“前面已是西园寺,阁下要……”
“走你的,不必管前面是个什么地方。”
“再要照直前行,必须……”
“独孤令,难道我还要听你的?”
“话不是这样说。”
“要怎样说才对?”
“独孤令虽然认败,但是阁下也应该说出个地方来,否则……”
“现在还早,你走就是。”
“好,独孤令早将生死置诸度外,没什么再怕的了。”
“这样再好没有。”
“不过再有半里路就到西园寺墙了,阁下总不能半点道理不讲,一定要令硬碰红墙吧?”
“你不会越墙而过?”
“算我自找难堪。”他恨恨地答覆蒙面之人这句话后,双足用力电掣般驰下。
蒙面之人暗中窥笑,可惜独孤令无法察知。
此时他也正中暗笑,欣慰脱身在际。
眨眼之时,红墙前迎,独孤令回顾了蒙面之人一眼,指指墙内的偏殿。
蒙面之人点了点头。
独孤令暗提真气,拧身越墙直上殿头。
蒙面之人已飘身墙上。
独孤令单足微沾瓦面,越过偏殿,纵临大殿屋脊右侧。
蒙面之人这时立在偏殿顶端。
独孤令倏地全力前纵,斜奔大殿后进。那是大悲方丈静修之地。
蒙面之人恰好已经飘身大殿顶头。两人相距,约有十丈左右。
独孤令暗中回顾蒙面人,脸上掠过一丝阴险狡诈的笑容。
他顿足停身,正纵在大悲方丈静修的禅堂上面。
停身回顾,静立不去,似在等待蒙面之人。果然,蒙面之人已自大殿脊上,高拔斜飞而起,向他存身之地纵来。
他低沉地冷哼一声,顿足飞起,左手暴然后甩。
山崩地裂般一声爆响,禅堂瓦面俱被震碎,断瓦残木四处横飞。
“什么人这般大胆?”大悲方丈已被惊醒纵出,疾身半空,扬声追问。
“当!当!当!当!”西园寺钟,连声震鸣。
各殿倏地灯火齐亮。十数条灰色人影,已纷纷由四方飞登各殿顶上。
大宏掌教这时腾身正殿脊前。
西园寺僧群被巨响惊醒,已将蒙面之人困在当央。
纷乱中,独孤令沉雷般已潜泻地面,隐于暗处。巧用一石二鸟之计,他已脱身事外。
蒙面之人目睹斯情,沉哼一声,高纵半空的身形,猛地停住,随即缓缓飘落在大殿右端。少林掌教大宏,正和他站了个对面。
蒙面之人不言不语,大悲方丈及各堂大师,亦已来到。
西园寺僧分为地面和殿顶两队,将蒙面之人团围正中
“施主夜入古刹,毁我禅堂何为?”
“你看明白了震碎屋瓦的是我?”
“此间并无他人,施主狡辩何用?”
“那是你瞎了眼!”蒙面之人毫不客气的回答大宏。
大宏闻言,双眉暴飞,想是怒极。
“施主,老衲闻声出现之时,施主故然尚在半空,但……”
“那就是了,你有眼睛总比没有眼睛的看得明白。”
大悲方丈有心借机暗示掌教,震碎殿堂屋顶的不是对面这个人。
那知蒙面人却恰好借话挖苦大宏掌教一句。
“难道那人不是施主的同伴?”大悲诚恐掌教震怒,故而出言质问蒙面之人。
“一块来的不错,但却不是同伴。”
“鬼话!”罗汉禅堂的主持大慈禅师,沉声接上这两个字。
“像你这种无知的蠢材,怎配当这罗汉殿堂的大师?”蒙面之人轻蔑的讽刺大慈禅师。
“狂徒你大胆。”大慈恼羞之下,厉声叱叫。
“嘿嘿嘿嘿嘿嘿,在下确实大胆,蠢奴你又当如何?”
“掌教,方丈,弟子已不能耐,伏祈恩准弟子与这狂徒一搏。”
大慈禅师气怒至极,不禁当面向大宏大悲请谕。
大悲方丈双眉紧锁,并未示谕,却注视着蒙面之人。
“嘿嘿嘿嘿,差些差些,动手你还差一大些。”
蒙面之人阴沉地冷笑着,淡然答话。
“施主,请问夜闯古刹何干?”
大宏已知震碎禅堂室顶,并非蒙面人所为,故而接口追问来意。
“和尚这个‘闯’字令人费解。”蒙面之人若无其事的反问一句。
“老衲欲知施主来意?”
“不便相告。”蒙面之人硬生生地说出这四个字来。
“施主这就不对了,敞派掌教是善意相询。”大悲方丈闻言不由寒着脸责问蒙面之人。
“不便相告四字,也非恶意。”
“施主夜入敝寺,总有原因吧?”大悲再次和气地询问。
“这是当然。”蒙面之人仍然毫不在乎地答话。
“原因何在?”大宏掌教叮问一句。
“不便相告。”他还是斩铁断钉般用这四个字来回答。
“这……”群僧一时语塞,真不知应该如何了断。
“你说震碎我们方丈禅堂室顶的那个人,并非你的同伴?”
大慈禅师久未开口,此时突然转换话题发言。
“不错。”
“你却又曾承认那人是和你一块来的。”
“也不错。”
“那人是谁?现在何处?”
“这个我倒可以回答,只是必须有交换条件。”
说到“条件”大慈不敢接话了,他只好看着掌教和方丈。
“不知什么条件?”大悲方丈只好接话询问。
“条件简单,我要借居静楼三天。”
此言一出,群僧俱皆失色震惊。
“施主贵姓?”大悲和大宏交换了一下眼色,大悲始问及蒙面人的姓名。
“不便相告。”蒙面之人,似乎对这四个字特别喜欢。
“哼!问东,你东一个不便相告,问西,你西一个不便相告,不知你愿意而无不便相告的事情,都有些什么?”
“多的很。”
“说说看?”大慈禅师冷言相询。
“譬如震毁瓦面的人是谁?他现在藏身何处?第一次借居静楼的驼背老人是谁等等。”
“等等二字包括些什么?”
“包括除‘不便相告’者以外的一切事情。”
“那么是谁震碎我们方丈禅堂的?”
“你问这话还早了一天。”
“此言怎讲?”
“你这罗汉殿堂的主持大师,有权承诺我静楼暂居三日吗?”
“有无此权,知早了一天毫无关系呀?”
“我适才说你是个蠢材,你还很不高兴,就凭你这种记性,不是蠢材又是什么?难道你忘记了晨课之时,大悲方丈当众言明,这……”
“施主,老衲实言,此时极为惊骇,敢请施主殿中小坐如何?”
大悲方丈的是十分震惊,他传谕令大慈暂代方丈之事,除寺僧外决无人知,蒙面人却能知晓,他骇异至极。
“不必,我就要走了。”
“施主不是要暂借静楼居住么?”
“方丈可愿承诺此事?”
“甚愿诺承,但是老衲另有交换的事务。”
“我向来言出必践,恕我不能接纳方丈的条件。”
大悲闻言略停片刻,示意大宏掌教。
“方丈有话尽说无妨,不必请教他人。”蒙面之人似乎无所不知。
“老衲有两件事拜问,愿意接纳施主对这两件事所要的条件。”
“也许我会不索代价。”
“老衲恭请施主殿中一谈。”
“这里好,我要监视着一个人。”
“施主可是指那震碎禅堂室顶的同伴?”
“是他,但却非我同伴,已声明过多次了。”
“老衲失言。”
“没有关系,方丈说那两件事吧。”
“晨间老衲大典宣谕门下之事,施主怎能知晓?”
“这一件我可以毫无条件地答覆,请问第二件呢?”
“老衲可能先听施主关于第一件事情的指示?”
“指示二字却不敢当,此事说来不值一笑,当方丈传谕寺僧之时,我恰好就在大殿之中。”
此言出口,寺僧齐声惊咦出声。
“老衲也是如此料想。”
“方丈智慧过人,请说第二件事?”
“那时罗汉殿堂之中,发生一事,施主可能教我?”大悲方丈言语含混,有心如此。
“不知道。”蒙面之人语调冷沉。
“施主在大殿之中作甚?”大悲方丈无可奈何之下,转变话题,但他已经料到对方的答覆,必然还是‘不便相告’四字。
那知大出意外,蒙面之人并未开口。
“是否施主觉得不便相告于老衲呀?”
“不是。”
“那刚刚施主……”
“我在查听藏身暗处的那个人,又躲向那里。”
“施主可曾察得?”
蒙面之人并未回答,只点了点头。
大宏掌教却在暗惊不已,蒙面之人竟能一心二用,功力高得惊人。
“可否现在示知老衲,施主晨间在大殿……”
“搜索一物。”
“施主是说,那时恰在大殿搜索一件东西?”
“不错。”
“什么物件?”
“不便相告。”
“是施主的东西?”
蒙面之人没有答话,却微然俯首,似在沉思。
“是敝寺之物?”大悲方丈逼上一句。
“不,应该说是寺僧之物。”
“施主的意思是说,那件东西纯为私人所有对吗?”
“方丈圣明。”
“物属那个人所有?”
“圣心大师!”
圣心大师四个字说出口来,竟令寺僧齐声惊呼,大悲方丈已经觉得事态严重,彼物紧要了,他正想接着询问,蒙面之人突然一声冷哼,蓦地嘿嘿大笑起来。
事出突然,僧众不禁俱皆诧愕难安。
“施主突然狂笑,莫非老衲言语有失……”
“我笑那个暗中捣鬼的人物,与方丈无关。”白衫蒙面之人,冷冷地答覆了大悲方丈。
“寺僧身许我佛,故无私有物件,因此施主你所取圣心大师之遗物,应该现在交于敝寺方丈。”大慈禅师再次接话。
“嘿嘿!”蒙面之人竟用冷笑当作回答。
“有何可笑之处?”大慈早已恼羞,沉声叱问。
“难道和尚你不说话,别人就会把你当作哑巴不成?’蒙面之人极端轻蔑地这样反问。
“狂徒,老衲迟早……”
“嘿嘿!大慈,动手怕你更要丢人,最好你还是紧闭着嘴巴,乖乖站在那里少开口。”
“施主,大慈乃我西园寺中首座大师,老衲不容有人这般侮辱……”
“方丈何须动怒,大慈他是自取其辱。”
“老衲不懂施主之言,大慈声明僧无私物一节,并无过错。”
“诚如方丈所说,他这句话不错。”
“既然施主也知道他话未说错,却怎又……”
“方丈莫急,他自然有不当之处,我才……”
一旁久未开口的少林掌教,这时突然高唱一声佛号,接过话锋沉声说道:“大慈即便真有不当之处,自有寺规教法处治,施主出言猖狂,目无少林僧众而侮我门下,老衲必须讨个公道。”
“哈哈哈哈哈哈!”
蒙面之人,闻言非但不惧,反而哈哈狂笑不已。
“老衲愿在这大殿之上,领教施主的罕绝功力。”大宏掌教扬声讨战。
“弟子俯请掌教慈谕,愿意首先向此狂徒一搏。”大慈禅师立即接话请谕,他早已准备动手了。
“身为少林一派宗主,难道就如此不讲道理?”
白衫蒙面之人,突然厉声喝问。
“施主侮我佛门弟子,老衲已经让之再三……”
“设若我像‘幽冥帝君’钟灵父子一样,掌教是否也要讨个公道?”
蒙面之人竟然指着少林前耻,反问大宏掌教。
大宏和大悲不由语塞,讷讷难辩。
“何况大慈禅师首先出言辱及在下……”
“施主善辩,老衲自始至终未离寸步,大慈绝无侮谩施主之言。”
“掌教向我讨要公道,在下本无所惧,但搏战事小是非事大,敢问掌教,可愿先将是非分清之后,再论其他。”
蒙面之人话锋犀利,大宏掌教不能立即应允。
“请问掌教和方丈,大慈禅师可曾说过‘要在下将所取圣心大师遗物,交还方丈’之言?”
“说过,施主理应交……”
“说过就好,掌教请先听我解释如何?”
“施主请讲。”
“在下曾言,晨间在贵寺大殿之中‘搜索一物’,对不?”
“不错,施主说过这句话。”
“在下是否也说过‘已将此物得到手中’的话呢?”
“这个……没有,施主没有说过。”
大宏掌教和大悲方丈互望一眼之后,才这样回答。
“在下既然没有说过‘得物’之言,而大慈禅师却令在下将所得之物交出,请问此言存何居心?”
大宏和大悲,无言可答。
“在下虽非佛门中人,然知‘佛无诳语’,僧戒‘嗔’‘妄’,大慈身为西园寺中首座大师,竟然故违戒法,若非‘蠢’极,又怎会如此口不择言,又怎能怪罪在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
白衫蒙面之人,得理不让,佩侃而言。
寺僧俱皆无法分辩,大慈禅师尤觉羞愧。
“在下偶尔夜登寺殿,佛家弟子,竟然如临大敌,圈围质问,说什么夜闯清静佛门,又问什么意图何为,那个不知,庵、观、寺、院,乃十方施主布施之地,莫非在下就来不得?可笑大宏掌教,身为一派宗主,竟然轻而言战,胜故不言,万一不幸败北,少林一派的颜面何存?在下适才声言借居静楼三日,实在说,那是存心讽刺少林无能,耻笑前次应诺驼背朋友居住之事……”
“施主住口!”大悲方丈沉声喝止对方。
蒙面之人却突然嘿嘿冷笑。
“施主,大慈前言失误,今向施主致歉。”大慈禅师一旁接话,并合十为礼。
“在下怎敢当得首座大师之礼。”白衫蒙面之人冷冷地答话。
“大慈乍睹施主,即知必系武林奇客,愿以一身浅薄微技,敬向施主领些教益,施主肯否?”原来大慈致歉是假,挑战是真。
“在下敢问方丈,贵寺之中何物最重?”
蒙面之人不接大慈所问之言,反而向大悲方丈询及寺中沉重之物。
“以这大殿之下,紫铜狮最重。”
大悲虽然不知蒙面人的用意,但他仍然回答了这个问题。
“好,方丈可知重量若干?”
“每只约在千斤以上。”
“在下就用一只紫铜狮子,与大慈禅师一搏。”
他说完这句话后,大慈禅师尚未接口,他却倏地电射而下,落足殿前紫铜狮子身旁。
大悲方丈自是不容他另有蠢动,故而紧随,在他的身后也飘然坠地上。
谁料白衫蒙面之人,却在大悲方丈足踏平地的刹那,单臂高举着殿门外左旁的那只千斤紫铜狮子,腾身而起又回转殿顶之上。
这种罕绝人寰惊骇武林的神力,和无与伦比的绝顶功夫,已经震哧住了西园寺僧。僧众张口咋舌,却都寂然无声。
大悲方丈沉吁一声,懒散的纵回殿顶,大宏掌教暗诵“善哉”不已。大慈禅师面色苍然一言不发。
此时,一片悄静,众目凝视着蒙面之人,一瞬不瞬。
蓦地!蒙面之人抖臂将千斤铜狮抛上了半空,寺僧暴声惊呼,纷纷作鸟兽奔散。
大宏掌教肃然合十。大悲方丈俯首穆然。大慈禅师以下各堂主持,无不傍徨忐忑。
紫铜狮子,已自上空沉雷般飞射而下。
少林掌教霍地高唱一声佛号,音悲调哀。
目下无人能够接住这只铜狮,大殿必被砸塌。
大宏和大悲二人,身为寺主、掌教,已到殉身之日。
是故毫不闪避,只在喃喃诚祝。
一声长啸,划破静空。发自蒙面之人。
千斤紫铜狮子,距离殿脊已经不足一丈。
九尺!七尺!五尺!此物疾投而到。
散乱在各处的西园寺僧,这时大半紧闭双目。
白衫蒙面之人,蓦地嘿嘿一笑,右臂倏然平伸,掌心向上,凌虚对这千斤紫铜狮子一托,一送。惊凛人胆的怪事!铜狮似具灵性,它竟轻飘飘地落在了殿脊上面,连一块瓦都没有压碎。
“啊!”寺僧不禁齐声惊呼。
“哈哈哈哈哈哈。”蒙面之人仰头大笑。
大宏、大悲、大慈等人,老脸飞红,若涂脂粉。
“在下微薄之技,不值识者一笑,只因尚须追索隐身暗处之人,故望大慈禅师多谅,恕我不战而退之罪。”
白衫蒙面之人,突然发话,“之罪”二字刚刚吐口,人已电射而去,待大宏掌教举目看时,他已远在十丈以外。
大宏掌教摇头喟吁,蒙面之人形影已渺。
他固然早已远去,大殿脊上,却留下了个极大的难题。
那只千斤重量的紫铜狮子,无论如何,也不能任它傲居殿顶。
谁能够搬它回到原处呢?
大宏掌教和大悲方丈,心里明白,这件事没人能够办到。
除非斜着建造一座板桥,并且必须大宏和大悲亲自动手,才能够使这千斤铜狮,复归原位。但是大殿高有五丈,造桥决非当夜可成。
此事却又不容明朝料理,否则怪事外泄,无可交待。
大宏掌教沉思有顷,低声和大悲商量了刹那,大悲方丈传谕寺僧,各自归房,然后立即吩咐各堂大师,相随进入大殿之中。
各堂大师料知掌教必有训示,个个肃色静听。
“你们俱已目睹蒙面人物之事,铜狮必须今夜取下殿脊,此时既非你们所能,说不得只有老与掌教拚力为之……”
“弟子斗胆进言,掌教及方丈是否真能胜任?”大慈禅师不能放心,低声相询。
“大慈,事到如今,不问胜任与否,也必须去作了。”
大宏掌教语调悲涩地这样说。
“弟子有个拙见。”
“说说看。”
“铜狮高大宽阔,四周可供抓扶地方不少,若由掌教和方丈分力举其首尾,弟子及各堂师弟,分列两旁握其四肢,当可平安抬下殿脊。”。
大慈禅师话罢,各堂大师俱皆认为可行。
大宏掌教却幽幽地长叹一声,摇头无言。
“掌教认为不甚妥当?”经堂大师大慧禅师,接口发问。
“大慧,你可知道铜狮的重量若干?”
“弟子听说大约在千斤左右。”
“它有一千三百六十斤的重量。”
大悲方丈说出铜狮的实在重量,各堂大师不由咋舌。
“殿脊相距地面,五丈六尺,大慈的办法本来最最恰当,可惜没有将这五丈六尺计算在内。”
“方丈,大慈不懂为何要计算这五丈六尺?”
“物高一丈,下坠之时,其重量约增五分之一。”
“啊?那……”
“铜狮自五丈六尺地方坠落,全重约为二千八百斤至三千斤之间。”
“方丈,就算它有三千斤的重量,弟子等皆有举五百斤的膂力,算来应该不会发生其他问题。”
“大慈,你话是不错,不过力举五百斤和五百斤压砸而下,却相差太远。”
“弟子仍然认为可行。”
“你的心意,老衲尽知,但此事不容老衲等偷安,还是按照……”
“方丈,合数人之力,总比方丈和掌教双双涉险强些!”
大慧禅师毅然抗言,大悲方丈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没有接话。
“你们若能听命行事,本掌教作主就试上一试。”
大宏掌教突然郑重其事的谕示各堂大师。
“当遵谕令。”众大师齐声应诺。
“当本掌教喝令你们松手退下的时候,不得疑迟。”
“弟子等遵谕。”各堂大师再次一齐答言。
“好,师弟认为如何,要不咱们就试它一试吧。”
大宏掌教说了一声好,然后向大悲方丈征询可否。
大悲方丈点了点头,无可奈何的走向殿外。众大师自是相随其后,鱼贯而出。
谁料乍出大殿,大宏和大悲竟然倏地止步,同声惊咦。
那只紫铜狮子,已经好端端地蹲踞在原处。
是谁所为?谁有这高的功力?
“方丈,您瞧右边这只狮子背上。”
大慈禅师突然惊呼着要方丈注意另外那只狮子。
“呀!大慈和大慧火速将铜狮背上的施主,抱入殿中。”
原来在另外那只狮子背上,卧伏一人,大悲立令门下将此人掺扶殿内。
斋堂主持大悟禅师,已在地上平铺了四个很大的蒲团,当作卧榻,大慈和大悲非常小心地将这人抬放在上面。
殿内烛明灯亮,这人虽然昏沉未醒,但面目无伤。
“方丈,这不就是早半夜冒充驼背施主的那个人吗?”
大悲方丈点了点头,因他另有所思,故而没有开口。
原来这个卧伏铜狮背上之人,正是那独孤令。
不知何故,却突然昏睡在狮背之上,当然,这绝对不是独孤令自己所为。
大宏掌教抓起独孤令的左腕,三指扣在脉门之上。
片刻之后,他一声惊咦,随即却又长长地嗟吁叹息出声。
“师弟,你试一下看。”
大悲闻言接过手来,也扣指在独孤令的脉门上面。
“善哉!好毒辣的手段。”
当他诊断清楚,独孤令为何昏睡不醒之后,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师弟,你看拍醒他可好?”
“是否掌教有话问他?”
“此人落得如此下场,已然惨极,我怎忍心还问他一切。”
“掌教慈悲,这人即将自醒,不如守他片刻。”
“也好。”
大悟听出方丈和掌教言下之意,立即又搬来两个蒲团,放于独孤令的身旁。
大宏掌教含笑点了点头,跌坐下来。
“你们各自回堂去吧,大慈速将‘枯圣神丹’取来三粒。”
众大师应诺一声,合十为礼而退。
“大慈,顺便带来茶具,令斋堂预备浓粥。”
大慈遵谕而去,刹那返回。大悲方丈所嘱应用之物,皆为现成东西,是故往返绝速,大慈料有变故,一切东西都是亲自携来。
这时,独孤令伸腰醒转,双目微启,蓦地惊咦一声,倏然坐起,愣怔地看着大宏等人,满面疑骇。
“施主仍请睡卧,老衲等已代施主备妥药物……”
“药物?和尚,我……”独孤令听大悲之言,越法奇怪,接口询问。
“施主莫悲、莫急,提提真气看……”
独孤令闻言大惊,猛提真力,面色突变,稍停刹那,他蓦地暴然跳起,狂吼悲叫不止。
大宏掌教不禁摇头一声悲唷,舒手已将独孤令按坐在蒲团之上,独孤令挣扎数次,竟然未能挪动分毫。
“施主真力已失,如今已和普通之人一样,最好大悲方丈之言未毕,独孤令陡地狂笑起来,声调悲凉哀凄,久久不停。
大宏掌教善目圆睁,高唱一声佛号,沉声喝道:“施主莫非已失心志,忘记恩怨不成?”
这句话震醒了独孤令,笑声顿止。
“老衲等不问施主往事,赠此三粒神丸,此间茶饭已备,施主食用之后,可以离寺而去。”
大悲方丈语罢,独孤令凄然一笑,他突地接过三粒神丸,吞入腹中,挣扎站起,双手只对大宏大悲一拱,转身而去。
“大慈,开放山门送这位施主离寺。”
大慈奉遵抢先出殿,打开山门。
独孤令面如秋月,身躯摇摆着走出西园寺来。
风冷、雪寒、夜深、人静,他那长瘦的影子,孤独地似幽灵般,缓慢地消失在黝深的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