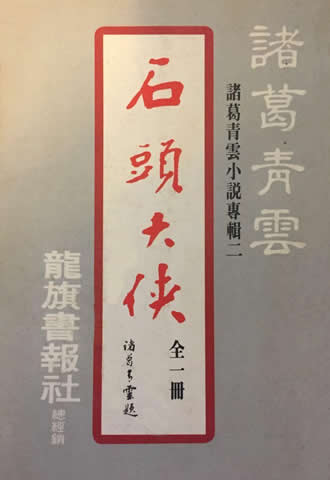他要走了。
十九年前,他就就已打定了这个主意;十九年中,他一直没有忘记,也从未告诉任何人。
十九年了,他终于要走了。他说不出自己的心情是轻松还是沉重,也不知道应该喜悦还是哀伤。
十九年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十九年前,他正是十九岁,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是鲜花怒马、丰神如玉的翩翩佳公子,是热血沸腾、喜好结客的少年,是叱咤风云的英雄……
现在,他的儿子竟也已十九岁了。
他不禁苦笑了一下,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跟“十九”这个数字如此有缘。
十九年前,他万念俱灰,几乎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可现在,他并没有万念俱灰的感觉,因为他心中还有一个念头,而且也只有一个念头——
离开这里的一切,到他自己该去的地方方去。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好收拾。
几套粗布衣衫已经很旧,快二十年没穿过了,他居然翻了出来,抖了抖,折好,放进极旧的柳条箱中。
一百两黄金锻成的金叶子,也放了进去。
有了钱,其他什么东西都会有的。一百两黄金,并不是个小数目。
但对于他的家业来说,一百两黄金太不起眼了,简直不过是九牛一毛。
他是这里的主人,他是一个巨大财团的唯一主人。
这里的一切都是他的:精美的花园,幽雅的庭院,堂皇的楼阁台榭,来来往往的男仆女仆……
而他却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一切。
他才不过三十八岁,正是年富力强、应该锐意进取的时候。他是个生意人,现在正是赚大钱的好时光。
可他居然要出走。
他的确是这里的主人,没有人敢否认。可他却总是感到不自在,好像这里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的。
他不过是借住在这里的客人。
一个客人在主人家住了十九年,当然该走了,早就该走了。
他收拾好柳条箱子,轻轻口于了口气,有些茫然的坐了下来。藤椅发出吱呀声,仿佛是在向他证实他躯体的存在。
“鬼是没有重量的。”他想着这句话,面带着淡淡的微笑。
于是他感觉到了一种轻松,那种轻松又渐渐变成酣畅淋漓的痛快。
他坐在椅中,闭目微笑着,倾听着窗外的春雨。
雨声像什么?像是有人在行走吗?
即使是,那也绝对是女人——年轻、温驯、文静的女人。
一股清爽而孕满生机的气息从窗纱慢慢渗入,他深深呼吸着,似已陶醉。
那其中有春雨的清新之气,有丁香花的郁香和木槿花的清香。
他甚至能够闻到远处一树辛夷的淡淡的幽香,能到花在雨中绽开的声音。
这种美妙的感觉,他已许久许久未曾体会到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悄然叹了一口气,走进了自己的书房里。
书房很大,也很宽敞。正中央放着梨花大案,案上却只有一个笔筒,几支鼠毫,一只端砚、一方墨和几张宣纸、一块汉白玉镇纸、一盏明亮的纱灯。
书房的四周,靠墙放着一排排的书橱,整整齐齐的排满了各式各样的典籍。
东面墙壁上,挂着一柄宝剑,装饰极其华美。
单看这书房,你绝对不会想到,他竟会是一个商人。
这个书房是他独有的天地,他从未让任何一个人进来过,包括他的妻儿。
十九年来的绝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老爷爱看书。”——这就是仆人们对他的评价。
至于老爷为什么爱看书,知道的人就少了。在这个巨大的庄园里,知道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她——他的妻子。
他在大案前坐下,沉默了半响,才伸手在案上搜索了一会儿,大案上居然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洞口,扁扁的,方方的,很浅。
他伸出了手,他的手竟然在微微颤抖。
他的脸色已很苍白,他的眼睛,也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奇异神情,似乎有屈辱,有痛苦,有欢欣,也有温柔。
他摸出了一个由丝巾裹着的扁扁的小包。
如果有人看见了这个小包里的东西,一定会十分惊讶。
包里有一条艳红的腰带,系着两个泥娃娃,一男,一女。
男的憨厚,女的娇媚。泥娃娃的背上还刻着极小的字,他们被面对着面栓在一起,撅起的嘴唇紧紧贴着。
包里还有一束长长的秀发。秀发由淡蓝的丝带系着,丝带上有两朵小小的茉莉花,绢制的茉莉花……
他怔怔地流下了泪。
十九年了,绢花已老,丝带已旧,秀发也已失去了那美丽的光泽。
可十九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一如昨日。
春雨潇潇。
春夜里的一切都似乎都已沉睡,但花却在悄悄绽开,草在悄悄拔节,树在悄悄滋长。
在春夜,人们的心田里,悄悄生长的究竟是什么呢?
他一听到那轻快敏捷的脚步声,就知道是谁来了。
他悻悻地按按已放在心口的小包,皱了皱眉头,沉重地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