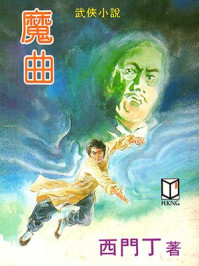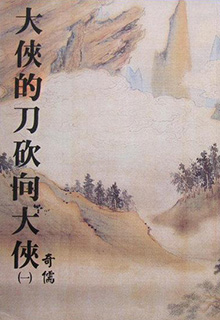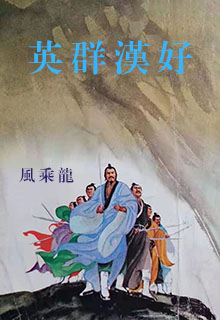全祖望跟着又拍手,这一次是连续两下。
这一次应声来到他面前的却是两个四十左右的中年魁梧大汉,一上前躬身齐声道,“庄主有何吩咐?”
全祖望脸容一肃,吩咐道,“你们两个立即给我准备兵器,这三日,休离我左右!”
“是!”两个中年大汉应声退下,面上都出现诧异之色。
这种吩咐,他们也不知道已有多久没有听到。
一用到兵器,就是全祖望不说,他们都已知道事态严重。
全祖望也的确很久没有用到兵器。
江湖的朋友也只知道花花太岁全祖望拳脚功夫了得,真正见过他动用兵器的人实在少之又少。
要动用到两个大汉,花花太岁那兵器的分量是必相当惊人。
那到底又是什么兵器?
张猛也并不怎样乐观。
一回到外廊,他一知道沈胜衣,练真真已不在大堂那边,他就想到任少卿在大堂并不怎样顺利。
他实在不想见到沈胜衣,只可惜他一抬头,就看见沈胜衣站在听松院那座小楼之上。
沈胜衣正在吹着笛子。
练真真一旁倚栏而立,似已沉醉在笛声之中。
笛声相当悦耳。
张猛听到耳里,心头却乱得好比一丛乱草般。
笛声的确悦耳,练真真的确沉醉在笛声之中。
听松院不单只有松,还有竹还有梅。
松竹梅并称岁寒三友,虽冬不凋,虽冬不折,却折在沈胜衣的手中。
沈胜衣一剑砍下一根竹子,就拿那根竹子造了一管笛。
用竹造一管笛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将那管笛子吹得令人沉醉,却就大有学问了。
练真真实在有些佩服沈胜衣。
笛子吹得是落梅花。
梅花还未落,笛声已落下,沈胜衣忽的放下了笛子,卧栏下望。
两个丫鬟已奔到小楼之上,仰首呼道,“沈大侠!”
沈胜衣应声道,“什么事?”
“天刀已到,庄主着令通知你们,小心防范!”
“天刀已到?”练真真如梦初觉,急问道,“现在在什么地方?”
丫环道,“听说顺长街那边,还杀了我们八个人!”
练真真柳眉一剔,说道,“我这就去会会他。”
语声未落,她的人已翻过栏杆,落在两个丫环身旁。
那身形陡落又起,飞向院外。
两个丫环吃惊都还来不及,又是一条人影从她们身旁掠过。
沈胜衣。
张猛一直在愁眉苦脸,这下却大喜。
沈胜衣练真真两人已先后翻过外院,越墙而出。
望着沈胜衣,练真真两个背影的消失,张猛实在有些佩服任少卿了。
“好小子,一张嘴果然了得。”
“张猛摸了摸下巴,忽一声暗号。”
十八个箭手应声,一旁闪出,一行十九人,迅速绕过听松院,赶往假山的那边。
日已过中午,阳光却依然绚烂。
凋尽的花木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又有了生气。
寒梅在阳光之下显得更娇。
第一波第二批的九个箭手阳光下逡巡在假山周围的花径上,花丛之中。
九个箭手一下子忽然变了二十八个。
张猛带领的十八个箭手已然来到。
一来到,张猛的脸就沉下。
一个人正坐在假山之上可月亭之中,却并不是张猛要见的任少卿。
这个人是大名府的总捕头查四。
张梦不知道查四为什么在可月亭,只知道这个查四来得实在不是时候。
在他身旁原来附近逡巡的一个箭手即时靠近来,悄声道,“老大,可是时机到了?”
张猛一点头,反问道,“那个当差的什么时候来到这里?”
“怕有半个时辰了。”
“他来这里干什么?”
“不知道,一来到就绕着那座假山打圈,之后便上了那座亭子坐在那儿,呆到现在。”
“那是神差鬼使要他的性命,我们成全他好了!”张猛的语声放得更低。
“你暗中传话出去,一见我发出暗号,只管乱箭将那个小子射倒!”
那个箭手应声正待走开去,张猛又叫住,问道,“你们可曾见过任少卿。”
“老大那是说方才?”
张猛颌首作应。
“没有见过。”
“哦?应该是时候的了。”
说话间,两人已来到假山之前,语声当然亦随着越放越低。
查四一直背坐在可月亭中,似乎并未觉察张猛的来到,但这下却忽的将头回过来,那视线正好与张猛的碰在一起。
“张兄么?”查四连随一声招呼。
张猛忙张开笑脸,一面挥手叫身旁的那个箭手退开,一面应道,“正是小弟。”
查四目光一扫诧异的道,“张兄的人似乎都集中在这里,外面莫非发生了什么?”
“查捕头敢情未知,是天刀来了。”
“天刀?”查四一惊而起,连忙问道,“人在那儿?”
“在街上,还杀了我们八个弟兄。”有这种事情?查四更惊讶。
张猛连忙道,“沈大侠他们已经赶去,我们自问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集中全力守在这里,也尽些心力。”
查四沉默了下去。
“查捕头可要赶去?”
“我?”查四一怔,道,“有沈大侠出手,那还用得着我,我就留在这儿好了。”
“也好。”张猛面上陪笑,心里却在暗骂,“你小子,这是自己找死,可怪不得我。”
查四当然听不到张猛心里的说话,负手在亭中一再徘徊,又沉默了下去。
张猛也懒得理会,一旁亦自踱开。
一踱开,他眼角就瞥见一个人正在那边的花丛中向他招手。
任少卿。
“这小子又在弄什么玄虚?”张猛满腹疑惑,加快脚步,赶紧走了过去。
任少卿一见到张猛向自己走来,反而向外走了出去。
张猛想叫住,又怕惊动了查四,只好忍着一肚子闷气,跟在任少卿身后。
出了月洞门,任少卿才收住了脚步。
张猛三两步走上前去,忙问道,“到底怎么样?”
任少卿反问道,“怎么那个姓查的在可月亭那儿?”
“哪管他,只要我一声暗号,管教他变个刺猬。”
任少卿大惊道,“万不能这样!”
张猛大感诧异道,“你那边事情,莫非有变?”
任少卿叹息一声。
“怎么?”张猛更是诧异,“方才我分明看到两个丫环入去听松院通知沈胜衣。”
任少卿道,“老家伙只是叫丫环通知他们小心防范。”
“但我见他们两个立即离开听松院,越墙而出,所以我才率领其他兄弟赶来这里。”
“我也是因为在外院不见你们,找到来这里。”
“你如果有些办法,这就溜掉了。”
“我是给撵出来的。”任少卿苦笑。
“老家伙要我回去待日堂那边给他守着,想不溜掉也不成。”
“那么沈胜衣,练真真两个又是什么回事?”张猛一面的疑惑。
任少卿又一声叹息,“他们两个也许是例外,但如论如何,老家伙这下必在潇湘馆,我方才走过落花厅,凌风榭,亦见消愁解语全义他们三个都已在盯紧这儿,查四更就在假山之上,因此我才来的这样子闪缩。”
唉,你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到此为止的了。
张猛这才叹气起来。
任少卿忙道,“不过不必灰心,机会以后还有。”
张猛苦笑道,“莫要到时候就只剩下你和我,想找个帮忙搬运珠宝玉石的弟兄都没有。”
“怎会?我们以后袖手旁观不就成了。”任少卿一拍张猛肩膀。
“要拼,由得老家伙他们去拼。”
“好。”张猛无可奈何的点头。
任少卿转问道,“沈胜衣还有那个姓练的女娃子果真去了?”
张猛微愠道,“难道我骗你不成?”
任少卿连忙赔上笑脸,道,“那现在他们跟那两个相信已碰上。”
“想必有一番好斗,不过,热闹不去趁一下,未免对不起自己的眼睛。”
张猛摸着下巴,已经意动。
“我也是这个意思。”
任少卿同样意动,半眯着眼睛,忽的这样说道,“最好就见到沈胜衣两人给他们打跑,再见到他们杀入缠住老家伙那几个来一场混战,好教你我来一个浑水摸鱼!”
“少废话,走!”
张猛拨开任少卿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当先走了出去。
任少卿忙亦举步。
阳光仍照在长街的青石板上。
青石板上的鲜血却仍未凝结。
沈胜衣练真真的目光先后在人头上掠过,练真真随即将脸偏开。
沈胜衣也跟着偏开脸。
死人绝不会好看,砍掉头的死人更是恶心。
他们要看,只是要看刀口。
刀口上亦可以看出那一刀的快慢。
“好快的一刀,好狠的一刀。”
这是沈胜衣下的评语。
练真真亦有同感,一点头,却问道,“哪里去了?”
沈胜衣一笑。
“你问我,我问谁?”
练真真的面上却没有笑容,道,“他是扬刀立威,未达目的一定不会罢休的,好,回头再会他也是一样!”沈胜衣一怔,忽问道,“你一定要跟他见一个高下。”
练真真颌首。
沈胜衣叹息一声。
“你叹息什么?”
练真真奇怪的望着沈胜衣。
沈胜衣叹息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以前也是你这种思想。”
“我才没有你这种思想。”
练真真噗哧一笑。
沈胜衣又是一怔。
“那为了什么?”
练真真好像没有听到,抬起头只顾望天。
长天还是那么晴朗,只是天边不知何时,已涌起了乌云。
“现在天气虽然好,黄昏只怕有雨。”练真真正好转过话题。
“哦!”
沈胜衣没有再问,居然抬高头,也望那边天打量起来。
天有不测风云,黄昏时真的有雨亦未可知。
天难测,人心更难测。
黄昏时并没有雨,雨,黄昏后才来到。
雨不大,也不小,不大不小的雨只能算作细雨。
突来的暴雨往往短暂,细雨持续的时间却往往悠长。
初更。
雨仍在下。
全祖望一伞在手,雨中穿过了花径,走上了假山之上的可月亭。
全祖望并不喜欢雨,在他这庄院之中也就只有可月亭,没有可雨亭。
今夜却没有月,只有雨。
全祖望只有叹气。
这种天气,这个时候,他实在不想停在这个地方。
亭中有张阔大的石桌,周围有五张石凳。
石凳可以移动,石桌却与石亭地面相连,桌面之下周围在往内凹下了半尺,那半尺之后就是通风的桌台,桌台与桌面亦是一体。
全祖望合起了伞子,往桌面一放,自己亦在一张石凳上坐下。
一坐下,他的一条手臂就搁上桌面,头却低垂,似在沉思,又似在倾听什么。
可月亭的四条柱子上都挂着一盏风灯,灯光照亮了全祖望的脸。
那张脸忽然泛起了笑容,全祖望笑着忽然开口轻呼,“小雪,雪!”
亭中只有他一个人,他这两声小雪又是呼喝什么呢?
“谁?”
有应声,女人的声音。
小雪原来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闻声不见人,这个女人莫非是一女鬼?
全祖望连随道,“除了我还有谁?”
小雪却问道,“初更了?”
全祖望笑道,“当然初更了,要不,我怎会在可月亭上?”
“你在亭上到快活?”
声音原来是从桌面下通的桌台中传出来,原来是雪夫人的声音。
小雪,雪夫人就是小雪!
这桌台也就是可月亭,假山下之中的那个石室的通风所在。
既然可以通风,当然,也就是可以通得说话。
“上面风又大又冷,还在下着雨,哪来的快活。”
全祖望应声连忙叮嘱道,“你听着,一过了初更,我离开之后,不管听到什么,你也不要再开口,要不给天刀听到,知道这是通风的地方,就不能用刀,找两条长虫放下石室,那你就糟了。”
通花的石台立时传出雪夫人的惊呼声,“你明知我胆小,还要吓我?”
“这不是吓你的,只是提醒你小心!”
“我这还不够小心。”
“能够再小心最好再小心。”
全祖望转问道,“方才,下面叮叮当当的尽响,你在干什么?”
“我不过将箱子里头的珍珠全都拿出来,给你好好的计算一下。”
“原来是在数珍珠。”
“我刚好数到一百,还有一大堆,你就是这么富有。”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全祖望的语声是轻快,面上却非独没有笑意,而且是一面感慨之色。
他的确早就跟雪夫人说了。
早在追求雪夫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像大多数的男人一样,为了要博取所爱的女人的欢心,将自己所有的优点,包括容貌,风度,才学,金钱,权势,地位,名誉都一齐表露出来。
就正如雄的孔雀,为了要诱惑雌的,倾全力将自己美丽的羽毛尽开。
他也早就看清楚,雪夫人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如果将金钱比作火,雪夫人便是灯蛾。
那儿有火,灯蛾便飞到哪儿去,火一灭,她便会飞到另一处去的了。
火始终会有熄灭的一天。
天下间本来就没有永恒的火焰,金钱燃烧起来的火焰更短促。
石室中本来有三十六口箱子,现在却只剩下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又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
全祖望叹息于风中,狂雨中。
马嘶在雨中,狂风中。
三匹马,三个人。
紫鸽凌羽,粉豹姚滔,花鸡向一啼!
粉豹一身衣白如粉,面庞也是一样苍白,混身却透出一股难以言喻的野性,一股难以言喻的活力。
豹向称凶狠,向称彪悍!
他就像是一条豹,野豹!
马鞍旁挂着一对锁心环,马在奔动,环在响动,粉豹残忍的语声,突然在风雨中响起。
“什么时候才到?”
“明天鸡啼的时候可到!”
花鸡向一啼尖声啼了起来。
“那么现在是到了。”
紫鸽望着花鸡,放声大笑。
“只可惜这只鸡不是那种鸡!”
花鸡却就笑不出来了。
鸡啼的时候也就是天亮的时候!
一啼天下白。
天才开始白,全家庄那只白毛大公鸡就跳上了后花园的竹篱笆,扯开了嗓子。鸡啼声啼破了长空的寂静,啼破了花径的冷雾。
沈胜衣,练真真正穿过冷雾,穿过花径,走向可月亭假山那边。
现在是轮到他们值夜,轮到他们值夜的时候,夜却已经过去。
今早的雾比昨日更浓,花径上迷蒙一片。
练真真走在前头,一穿过月洞门,几乎就撞在站在那边转角的一个人身上,好在她及时收住脚步。
“谁?”
这一声出口,练真真那双眼就睁大。
站在哪里的赫然是雪夫人。
纤细的腰肢,丰满的胸膛,修长均匀的小腿,羊脂白玉似地肌肤。
雪夫人混身赤裸!
“又是你!”
练真真随即一皱鼻子,哼一声。
一道血口由眉心直裂至胸膛,人还是直立在那里,这原来又是雪夫人那个蜡像。
“这个蜡像怎么在这个地方?”沈胜衣惊讶并不比练真真小。
“谁知道?”或者是跟你有缘。练真真噗哧的又一笑。
沈胜衣却皱起了眉头,那目光正落在蜡像的脚下。
练真真随着望去,面色不由得一变。
蜡像本来是赤足的,现在脚上却穿了一双鞋子。
“是她的鞋子。”
练真真惊呼失声。
沈胜衣忙问,“那个她?”
“雪夫人。”
“你怎知道是她的鞋子?”
“那个女人就好像只怕人家瞧不到她的脚,一双手不时将裙子拉下,别说鞋子了,小腿都露出了,难道昨日你没有看到?”
“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听,我还记得孔老二这几句说话。”
“你真的那么君子。”
练真真好像有些不信。
沈胜衣叹了一口气。
“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练真真只好信了。
“我信你,你也得信我,昨天她穿的的确是这双鞋子。”
“昨天她在进入那座石室之前,好像没有换过鞋子。”
“她一直走在那个查四身旁,何来时间换鞋子。”
“那是说,蜡人脚上的这双鞋子如果不是另一对同样一样的鞋子,现在就应该与雪夫人锁在那石室之中同一对的。”
练真真点头。
“也就是说,这双鞋子如果只得这一对,必然是自石室之中,取自雪夫人脚下。”
“那么雪夫人现在。。。。。。”沈胜衣再要说什么,那张脸不由的发了白。
全祖望的脸色更白的怕人。
一接到消息,他就仓惶离开潇湘馆,比奔马还快,到了好一会,那奉令不离他左右的两个大汉才赶到。
两个大汉合力扛着一双大铁椎,看样子怕有百多斤重。
秦始皇当年在博浪沙险些挨上的那一椎大概也不外如是,怪不得要动用两个大汉来侍候了。那在全祖望手中使来,是必有一番惊人的威势。
堂堂花花太岁用的竟是这种粗重兵器,未免出人意外。
那两个大汉未到,要到的人全都已到了。
第一个到来的当然是正在可月亭中值夜的查四。,他到了全祖望才道,跟着消愁,解语全义,最后一个是任少卿。
看到蜡像脚下的鞋子,女人不用说,所有的男人的面色都无不大变,分明都知道那双鞋子是应该穿在雪夫人的脚上。
好像沈胜衣这种君子,真的还很少。
练真真所以开心得很,频频望向沈胜衣。
全祖望就不开心了,上下打量那个白蜡像,双眉已紧缩,喃喃自语道,“蜡像一直是放在堂中的八仙桌上,现在却来了这里,鞋子应该在石室之中,现在却穿在蜡像脚下。。。。。。”
语声未落,全祖望霍的抱起那个白蜡像,大踏步奔向假山那边。
假山那边也并不安静,张猛已听到消息,带领那二十七个弟兄急赶到,却是站在一旁。
无须任少卿开口,张猛也不会动手。
水并不混,这个时候插手,摸着的一定不是什么金鱼银鱼,是鲨鱼。
全祖望也没有理会那许多,一直奔到石室之前才停下脚步,一双手马上往那凸岩一拍。
喀的一声凸岩下陷,匙洞所在的石板之上的那件石块移过一旁。
全祖望随即探手怀中,才探到一半便怔住在当场。
他总算没有忘记石室的两套钥匙都交给了雪夫人。
没有了钥匙,们无论如何是打不开的了,他却伸手扳住门上的几块凸岩,用力的一阵摇撼。
门纹风不动,他这是白费气力,却反而呼了一口气,好像放下了老大的一重心事。
“门关着。”他回头望了一眼,面色已没有那么难看。
原来他这只是想知道门到底有没有关上。
门只要关上,里面的雪夫人就安全。
两套钥匙都在雪夫人手中,门还是关着的,里面的雪夫人就应该还是活着。
全祖望随即凑近匙洞,放声呼叫到,“小雪,小雪!”
一连好几声,都没有回应,全祖望开展的双眉不觉又锁合,他偏过半脸,耳贴过匙洞,听了好一会,忽的放步绕着那座假山急急的走了一圈。
谁都不知道他那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无不诧异的瞪大了眼睛。
那一圈绕过,全祖望的眼神也满是诧异之色,忽的举步奔上假山旁边的石级,奔向假山上面的可月亭。
两个大汉扛着大铁椎亦步亦趋,中人亦不觉随后跟了上去。
一入可月亭,全祖望便在桌旁蹲下,又是好几声小雪。
这一次一样没有应声。
练真真一旁看着,实在觉得奇怪,张口正要问,全祖望又已回过头来,道,“这石桌下面的通花石台就是下面石室的通风所在,我在这里大声呼叫,下面的人,绝对没有理由听不到。”
“哦?”
练真真这才明白,转口道,“这么看来石室下面莫非发生了什么变故?”
“是亦未可知!”全祖望脸色凝重,突的一长身,一伸手!谁都不知道这又是表示什么,那两个大汉都会意,马上将扛着的大铁椎卸下,送上。
全祖望右手接过铁椎,左手往外一挥,道,“你们都退出亭外!”
看样子,他似乎就要动用铁椎,将那个亭子拆掉。
君子不立危亭之下,沈胜衣第一个推出,练真真是第二个。
全祖望只等各人都退出亭外,左手便搭上椎柄,要背一弓,双手挥椎,大喝一声,一椎横扫而出!
轰的半天猛一个霹雳,亭中的那张石桌的桌面五裂四分,漫天乱飞,飞出亭外,山外!
碎的只是桌面,不是桌台。
好厉害的一椎。
好准确的一椎。
桌面一砸掉,亭中就只剩下通花的石台,石台正中,赫然是一条三尺方圆的管子。
这条管子不单只通的气,还通的人,全祖望一纵身,就连人带椎投向那条管子!
喀勒的又一声。
那条管子与石台相连,管子之下是必就是石室之顶,石室之顶那张着通花承尘,那喀勒一声是必就是全祖望踩碎承尘之声。
那一声之后,管子之中突然传出了全祖望撕心裂肺的一声狂吼!
一时间人皆变色,沈胜衣第一个飞身而入,飞入亭中,飞入管中。
练真真又是第二个。
石管对下果然是石室通花承尘所在!
承尘已碎开老大的一个缺口,沈胜衣,练真真从容落在石室的地毯之上。
全祖望这下正在绣塌之前,呆呆的支椎而立。
绣塌之上躺着雪夫人。
被翻红浪,肉白羊脂,雪夫人混身赤裸,仰卧在绣塌之上,一身美丽衣裳尽散在床边1
一道血口自雪夫人的眉心直裂到胸膛。
这一次不再是蜡像,是人!
人已成死人!
死人的脸庞绝不会好看,裂开两边的死人脸庞更令人鼻酸。
练真真皱着鼻子,走过去拿起散落在床边的衣服,盖住了雪夫人赤裸的身子。
那刹那,她亦看清楚了雪夫人的脸庞,不由得面都白了。
雪夫人的脸庞实在恐怖,虽然裂开了两边,那一脸的惊恐不单止没有裂散,反而更显得强烈!
谁都看得出,雪夫人临死之前是怎样的恐慌,是怎样的惊惧。
这张脸现在哪里还象天仙,简直就是魔鬼的脸谱。
练真真看着脚都软了,她几乎是跳着回到沈胜衣的身旁。
这片刻,消愁,解语,全义,任少卿,查四亦已纷纷穿过管子,跃下了石室。
没有一个人不是当场呆住。
全祖望更就像已变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蜡像,周围发生了什么他都似乎并无感觉,甚至练真真在他身旁一来一去,他的眼睛也不会一眨。
今日正是十二月二十日,正是天刀三日限期的第二日。
天刀果然言出必行,果然就在今日刀斩雪夫人。
石室的门关着,钥匙都在雪夫人的手中,通风的管子刚才才砸开,在未砸开之前,这座石室是一座坚固的密室,连天都见不到,即使真的是天刀,亦不能进入室中!
雪夫人却死在刀下!
刀从何来?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想到,一种难堪的死寂充斥着整座石室。
“好一个南宫平,好一张天刀!”第一个打破这种死寂的却是全祖望。
这句话出口,就有人应道,“杀人的也许是南宫平,却不是天刀。”
全祖望应声回头,散涣的目光落在练真真的脸上,哽声道,“你再说什么?”
这片刻,他竟像老了十年,不单只说话神态,就连挺直的要背也已佝偻。
练真真摇头轻叹,重覆道,“我说凶手可能是南宫平,却并非是天刀。”
全祖望一怔,说道,“南宫平,不就是天刀?”
练真真一再摇头道,“南宫平是南宫平,天刀是天刀,天刀,南宫平根本是两个人!”
全祖望又是一怔,道,“那么天刀又是那一个?”
练真真正色道,“我!”
这一次就连沈胜衣都怔住,其他的人更就是目定口呆。
练真真叹了一口气,接又道,“家父就是天龙神刀练飞云,当年夜劫天龙坊,并非阎坤一个人,还有卜啸虎,箫师亮,他们三个人结成一颗也许巧合,夜劫天龙坊却是阎坤早有预谋,远在那之前,阎坤一次在陕北作案碰上家父,给家父教训了一顿,便已怀恨在心,屡思报复,单打独斗,他们无一是家父对手,但三人联手,再加上阴谋暗算,家父却终于死在他们手上,父仇女报,所以我练成了家传刀法之后,走马江湖,遍访仇人,杀卜啸虎,杀阎坤,杀箫师亮!”
众人不由的齐地呵的一声。
练真真接道,“家传刀法即为天龙神刀,人称家父天龙神刀总不成我又自称天龙神刀,所以我只自称天刀,至于杀人的三日限期,无疑是有些取巧,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家父死在那一年那一月的二十日!”
众人又是呵的一声。
全祖望随即问道,“那么南宫平为什么要冒充你天刀的名字?”
“我怎么知道?”
练真真沉吟着道,“最初我还以为名有相同,你们弄错对象,可是后来见他的行事作风,完全跟我一样,才晓得那个南宫平存心冒充,所以就答应留下,只道到时将他揭发,问他一个究竟!”
沈胜衣这才明白她为什么对天刀那么紧张,听到丫环报说天刀在街上杀人就立即赶去。
他也在沉吟,沉吟着忽道,“南宫平那样做对他到底有什么好处?如果他的武功比你高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如果不及你,这一来,别人严加防范,岂非是弄巧成拙。”
“不管怎么样,他现在已经得手,”是查四的声音,他听到这下,终于开口。
他说着走到绣塌之前,视线落在雪夫人的面上,眼瞳中突然闪出了一股异样的光辉,嘴角突然泛起了一丝异样的笑容。
这位大捕头似乎已有所发现。
全祖望的目光正好落在查四面上,一见有异,不觉脱口问道,“查捕头发现什么?”
查四目光再周围一扫,道,“雪夫人不是死在刀下!”
这句话入耳,中人不由得一齐举起脚步,走到榻前,全祖望更就连声追问道,“不是死在刀下,那是何以致死的?”
查四目光又回到雪夫人面上,道,“你们看她的头!”
雪夫人的粉颈上赫然透着青紫色的淡淡地几条指印!
“她是给人用手扼死的。”
查四语声一沉,接道,“我早就奇怪,既然是一刀致命,脸上的神色为什么那么可怕,待走近一看,原来那不是致命的死因。”
众人的目光下意识又落在雪夫人的面上,不由得又齐地打从心底一寒。
查四的目光却始终稳重。
时常有机会跟死人打交道的除了仵作之外,只怕就轮到做捕快的了。
这年头天下并不怎样太平。
盗贼一多,自然死得人多,一有人死,坐捕快的便不免要大显身手。
身为名捕,经验是必更就特别丰富。
死人见得多了,又怎会再当一回事。
何况雪夫人事实也不算死得太难看,何况,跟死人打交道,事实也不算一件怎样可怕的事情。
站在死人身旁最低限度没有站在活人身旁那么危险。
死人只有一种,活人却有多种,有种活人最喜欢就是乘人不备,抽冷子一刀!
死人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做。
查四所以很安心地站在雪夫人的死尸旁边,那眼中闪烁着智慧的神采,一闪,再闪,又道,“那一刀不单只是在死后才加上去,而且可能是在死后很久,你们都看到,那一刀劈的很深,很用力,刀口的鲜血已凝结,刀口旁边却没有鲜血,衣服之上,被褥之上,秀塌之上,甚至地毯之上同样没有鲜血。”
听到这里,众人不禁有些佩服。
名捕明察秋毫,的确名不虚传。
查四继续道,“脸上的鲜血可以抹掉,衣服,被褥,绣塌,地毯上面的鲜血无论如何是抹不掉的,刀既然劈得那么深,那么用力,也没有可能没有鲜血溅开,那只有再两种情形之下,才会有现在这种情形出现,一是雪夫人死后很久很久,血液都几乎凝结,那一刀才砍到她面上,不过时间上,这似乎不足,除非雪夫人一入石室便已死亡!”
“没有这种事!”全祖望立即插口。
“初更我值夜的时候,我还籍着亭上的通风管子跟她说话。”
“那就只有一种情形了。”
查四语声一顿,缓缓的道,“那一刀并不是在这里砍在雪夫人的面上。”
全祖望脱口道,“你是说她是死在石室之外?”
查四点头。
“怎会有这个可能?”
全祖望回身指着石室那扇石门,道,“这门一关上,谁都打不开,钥匙又全都在她手上,她当然不会开门外出,假山后面不错种满了花木,假山前面却一览无遗,门在假山的前面,就算她开门外出,监视在可月亭中的人一定发现!”
查四截口转问道,“各位昨夜可曾见过雪夫人外出?”
没有人点头。
全祖望接道,“再讲,就凭她也没有足够的气力打开那扇石门。”
众人的目光一齐落在那扇石门之上,一齐点头。
查四道,“只要她将锁打开,外面的人便不难替她将门拉开,她气力不足,外面的人气力未必不足!”
全祖望瞪着查四,道,“那是说,她是给人从外面将门骗开的了?”
“这难道没有可能?”
“好,就算有这个人骗她将门打开,把她掐死后再加一刀,然后送返这石室,他没有钥匙,离开之后他怎能将门关上?”
“人给他骗了出去,钥匙还愁不到手?”
“钥匙可能在这里?”
查四反问道,“在哪儿?”
全祖望应声一指榻上那一对相思无患枕。
枕下露着一角钥匙,全祖望随手将那一对相思无患枕翻开,脸色当场一变!
枕下只得两把钥匙,只有一套。
“还有一套,还有两柄钥匙在什么地方?”全祖望张目四顾。
其他的人下意识亦四顾起来。
查四张望着忽的左下半身,控手从榻旁下面的地毯上拾起了一样东西,道,“可是这两条?”
正是两条钥匙。
全祖望接在手中,道,“就这这两条,大概是她一时不小心,所以掉到床边的地毯上去了。”
“钥匙都在石室之中,石室的门又给锁上,人却死在石室内的床上,这-------”就这连查四这个名捕也束手无策,呆住在当场。
全祖望看着手中的两套四条钥匙,又看看查四,苦笑道,“这除非死人还会将门锁上,否则这石室只怕有鬼!”
那几个女的立时面都青了。
任少卿耸着肩膀,面色也不见得好到那里去,全义却是在强笑。
沈胜衣亦是在笑,淡笑道,“我这个人可不信有鬼,这其中是必另有蹊跷。”
“沈大侠说的不错。”
查四点点头,忽问道,“全庄主,石室的钥匙可是只得两套?”
全祖望微愠道,“查捕头意下是指老夫说谎?”
查四道,“不敢,查某只是想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全祖望断然道,“只有两套就只有两套!”
查四接问道,“除了那扇门,那通风管子之外,这石室可还有其他可供出入的地方?”
全祖望不假思索的,应声答道,“还有一个!”
“在那?”
“这边!”
全祖望三两步越过绣塌,走到那扇石门的对壁,嘶的拉开了悬在那儿幔幕。
幔幕的后面正是石室的墙壁,墙壁偏右,嵌着一个大铁轮。
全祖望右手往轮上轻轻地一推,墙壁正中,三尺宽阔,七尺高下,与那扇石门同样大小的一副墙壁便自缓缓移开。
一片花木同时映入眼内。
全祖望道,“这出口是通往假山的后面,但这扇门却只能在室内开关,我方才在假山外面绕圈,目的就是想知道这扇门到底有没有开启,事实证明并没有,门现在才由我打开,那也就是说,凶手并非由此离开,查捕头如果不信,不妨就现在实验一下。”
“好!”
查四几部走过全祖望的身旁,走出门外,练真真亦跟着跃出。
这个女孩子的好奇心就是这么重。
全祖望随即回手一推铁轮,那面石壁也就缓慢的关上。
也就在那刹那,全祖望振吭道,“两位现在不妨试试能否在外面将这块石壁退开?”
语声一落,全祖望亦松手,那刹那整块石壁已回返远处,紧紧地关上。
全祖望随即回头说道,“我们也回到亭上去!”
这句话出口,全祖望手中四柄钥匙怀中一塞,一纵身,就穿向那个通风管子。
消愁解语随后,全义也不慢,任少卿只好亦跟着,最后的一个是沈胜衣。
沈胜衣上得那座亭子,全祖望已将查四,练真真招呼到亭上,问道,“你们试过认为那块石壁是否有可能从外面打开?”
练真真第一个应道,“我认为就没有可能了。”
查四亦自点头道,“我也是这意思。”
全祖望目光转向那条通风的管子,道,“整间石室也就是现在这个情形,石桌不砸掉,只有雪夫人一个可以出入,雪夫人却并没有出入,就现在这个情形之下死在石室之中,凶手何来,凶手何去?”
全祖望仰天长叹,一再喃喃自语道,“凶手何来?凶手何去?
没有人应声。
查四不禁亦叹了一口气,道,“无论如何雪夫人的死是出于人为,只要有凶手,就可以找出凶手,杀人的方法虽然诡异,也并非毫无迹象可寻,在我的心中,有好些疑点,只可惜我现在的心头,就像是一团乱丝,抽不出头绪来。”
所有的目光一时都落在查四面上。
查四又叹了一口气,继续未完的说话。
“受托而有负所托,未能防患于未然,让凶手成功杀人,查某我实在深感惭愧,是以,不管怎样,我查某非要找出事实真相,找出凶手不可。
全祖望长叹道,“事情到这个地步,实在在意料之外,怪的谁来,死者已矣,我现在就只求找出凶手,将他碎尸万段!”
说到最后那一句,全祖望的牙齿直咬的吱吱作响。
众人只听的心头发寒。
查四亦打了一个寒噤,应声道,“给我时间,让我好好推敲一下。”
“有劳捕头费心。”
“应该应该。”查四应声负手走下了假山,就绕着假山,缓步踱起来。
全祖望的目光就随着查四移动,查四眯眼,他亦眯眼,查四皱眉,他亦皱眉,整副心神都似已为查四所夺。
其他人的目光亦结集在查四的身上。
无人能进入的密室,密室中的杀人事件,凶手何来?凶手何去?这就连沈胜衣也无头绪,这就连沈胜衣也感到兴趣。
朝雾已散尽。
昨夜虽然雨下不停,今日天色又见清朗,远山的那边阳光如锦,想必今日又是好天气。
绕着假山踱了好几圈,查四倏的停下了脚步。
全祖望双眉一展,正要问,那边花径突然奔来了一个家人。
人未到,声已到。
“庄主!”
这一声庄主,正好截住了全祖望的说话。
全祖望当场一声闷哼,喝问道,“什么事大惊小怪?”
“门外来了三个人,说要见庄主!”
“我今天不见客!”全祖望一挥手。
“叫他们滚。”
“他们一定要进来。”
“那乱棍把他们打出去!”全祖望的心情似乎相当恶劣,语气相当暴躁。
“小人等也是这个意思,可是一上手,所有的棍子都给他们一把抄住,拗了两截。”
“没用的东西。”
全祖望暴喝道,“人现在又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
三个人应声由那边月洞门一闪而入。
左花右紫中粉白,三个人衣服颜色不同,相貌不同,胖瘦不同,所用的兵器亦是各异。
一看到这三个人出现,张猛,任少卿的面色就一变。
“昨日在街上斩杀我们八个弟兄的就是他们!”张猛更就高声嚷了起来。
“只是我!”
紫鸽连忙纠正张猛的说话。
张猛应声手指着紫鸽,急呼道,“他就是那个天刀!”
不等他再开口,聚在那边的那二十七个箭手已搭箭弯弓,蓄势待发。
张猛并没有份儿进入石室,难怪并不知道练真真已表明身份,表明她才是天刀。
任少卿却是知道的,只可惜他虽想叫住,张猛的说话已经出口。
全祖望听说,双眉一轩,厉声喝道,“住口!”
张猛当场怔住。
全祖望接又一声断喝,“退下!”
张猛这才真的怔住。
像他张猛堂堂楚西三十六友的老大,几曾给人这样子呼来喝去,一股怒火不由的就从心底烧上,但很快便自压下。
他到底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强忍住心头怒火,一声不发的退开。
全祖望的目光早已转回紫鸽那边,厉声喝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紫鸽并不动气,柔声道,“十二连环坞的人!”
“十二连环坞。”
沈胜衣目光一寒,面色一寒!
紫鸽接着来一个自我介绍。
“我紫鸽凌羽。”
“我粉豹姚滔。”
“我花鸡向一啼。”
全祖望并未动容,接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紫鸽反问道,“阁下莫非就是全庄主?”
“正是全某,回我说话。”
紫鸽笑应道,“日前我接获消息,得知天刀寻仇全家庄,所以会同一鸡一豹,匆匆赶到来这里。”
全祖望一声冷笑。
“这件事与你们有何关系?”
“关系可就大了。”
全祖望冷笑连声。
“天刀找的是我全祖望,不是你们鸡豹鸽,我与你们鸡豹鸽亦是素未谋面,有什么关系可言?”
紫鸽不以为意,笑道,“我们十二连环坞的白虎坞主卜啸虎是死在天刀下,因为这件事,江湖朋友不少引为笑柄,这口气我们无论如何是咽不下的了,却是这个仇我们非报不可,这你说,天刀的下落,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而天刀现在是找你麻烦,正所谓同仇敌忾,这你说,你跟我们又有没有关系?”
全祖望奇怪的说道,“谁说我与天刀有仇的?”
紫鸽一愕。
全祖望接道,“天刀若是与我有仇,我又怎会让她站在自己身旁。”
紫鸽,花鸡,粉豹三个人的目光立时全都射向全祖望左右各人的面上。
全祖望看在眼内,忽问道,“你们可是并不认识天刀?”
紫鸽傻了脸。
全祖望不由大笑。
粉豹一瞪眼,闷哼道,“这有何可笑?”
全祖望大笑道,“寻仇寻到我这儿,却连那一个是仇人也不知道,天下间有比这更好笑的事情?”
粉豹一对锁心环立时一翻一合,呛啷的震断了全祖望的笑声,厉声喝道,“哪一个是天刀?”
练真真噗哧一笑,道,“你这只豹在穷吼什么?”
粉豹一番眼。
“女娃子滚开,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怎么?你们不是要找我?”
练真真是几乎笑弯了腰。
这次到粉豹傻了脸。
花鸡看见两个兄弟尽在闹笑话,实在有些生气,抢上前一步,盯着练真真,怒声道,“你就是天刀?”
练真真反问道,“我难道不是?”
花鸡厉声喝问道,“杀死卜啸虎的也就是你?”
“不是我又是那一个?”
花鸡脖子都粗了,厉声道,“下来,这次非要让你知道十二连环坞的厉害不可!”
练真真正想下去,旁边的沈胜衣突的一伸手,道,“你先别下去,他们是准备三个人同时出手!”
练真真再望那边,果然就见花鸡向一啼虽然没动,紫鸽凌羽,粉豹姚滔已左右向前移开,三个人隐约组成一个品字!
花鸡亦同时看见沈胜衣截下练真真,脖子当场又粗了,嘶声叫道,“你小子又是什么东西?”
沈胜衣没有理会,接又道,“十二连环坞人最不讲江湖道义,还得防他们突施暗算。”
“这在与卜啸虎交手的时候我已有经验。”练真真颌首微笑。
“沈大哥,我懂得小心的了。”
沈胜衣正想再说什么,花鸡那边又已尖声叫了起来,“你小子尽在啰唆什么,要就跟她一起上,我们一并招呼你!”
沈胜衣反而笑了。
“我正有此意,两个对三个虽然仍是吃亏。。。。。。。。”
话才说到一半,一旁全祖望已截口道,“三个对三个就不吃亏的了!”
说话出口,全祖望便长身而起。
花鸡那边瞥见,叫了起来。
“姓全的,你莫要不知好歹!”
全祖望笑道,“他们住在我这里,好歹总算是我的客人,我这个做主人的总不能让客人吃亏,只好凑上一份了!”
花鸡还未接得上说话,全祖望已又转过头来,道,“便宜不妨多占,亏却最好少吃,你们年青人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
沈胜衣,练真真淡笑不答,那边紫鸽却即时冷笑道,“你这个老家伙也不见得就懂,这件事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用得着你卖着力气?”
全祖望大笑,道,”不是我不懂,只不过我现在一肚子闷气,正想找机会发泄,你们来得又正是时候!”
“那么我这张刀就成全你!”
紫鸽大笑拔刀!
练真真的刀同时出鞘,道,“你用刀,我陪你!”
全祖望捋须笑道,“好,用刀的给你,那条豹年纪较大,我就捡那条豹,也省得那只鸡说我以长欺幼,以大欺小!”
那只鸡立时望着沈胜衣,叫了起来,“由我来教训你这小子最好不过!”
沈胜衣冷笑。
花鸡双手一翻,背插那一对金爪撤在左右双手。
那一对金爪金光灿灿,爪缝间却一片暗红的血色,也不知染过多少鲜血!
粉豹一对锁心环的锋缘亦是暗红一片,紫鸽那张刀更是血迹未消。
沈胜衣目光一闪,说道,“你们三个杀的人倒也不少!”
“也不多,”紫鸽一振刀。
“昨天我才杀了八个!”
粉豹一瞥紫鸽,一声叹息。
“紫鸽杀人最亏本,我最低限度留起一颗心送酒。”
花鸡一翻手中双爪,亦叹了一口气。
“只可惜人眼总是特别脆弱,我虽然一心要留下来享用,这只爪子抓下去,十有八九都是碎的一塌糊涂,难得有一顿丰富。”
这一鸡一豹说的若无其事,在场的除了那只紫鸽之外,其他的人听说都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张猛随即亦叹了一口气,一向他就自夸心狠手辣,但比起眼前一鸡一豹一鸽,他忽然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一个吃长斋的老和尚。
沈胜衣也再叹息,道,“心狠手辣的人我自问已见过不少,像你们这样辣手狠心的却还是第一次遇上,也亏你们还沾沾自喜。”
花鸡失笑道,“那本来就是赏心乐事。”
“哦?”
沈胜衣面色一寒,忽问道,“对我你又打算怎样?”
花鸡大笑道,“你若是现在跪地求饶,我或者考虑饶你一条狗命,不过你那一对眼珠子,无论如何我是要定了。”
沈胜衣面色更寒,还未答话,旁边练真真已道,“沈大哥,这种人何必跟他多作说话,他既然打定那个主意,你也就不必对他手下留情!”
“嗯!”沈胜衣淡笑。
“我并不是哪种婆婆妈妈的男人。”
练真真噗哧笑道,“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江湖中人都是这样的说你,我想大概错不了。”
沈胜衣一笑拔剑。
他剑拔在左手就剑握左手!
一剑在手,他的眼瞳便似在结冰。
冰冷的目光落在花鸡向一啼的脸上。
花鸡一脸的笑意立时冰封,他怔怔地盯着沈胜衣握剑左手,忽问道,“你用左手剑?”
沈胜衣左手靠唇,剑压眉心,道,“左右都无妨,不过左手比右手来得迅速,我向来也是喜欢速战速决!”
“你可是姓沈?”
“是姓沈。”
花鸡接问道,“沈胜衣就是你?”
“就是我。”
花鸡虽然已猜到了几分,还是不由得面色一变。
全祖望一旁即时大笑道,“也不打听一下就打来,这莫非就是你们十二连环坞的行事作风?”
花鸡冷笑一声,道,“我们早知道沈胜衣在这里!”“哦?”
全祖望一怔。
花鸡冷笑接口道,“沈胜衣在这里又怎样?”
“又怎样?”全祖望一再大笑。
“问得好,难怪江湖上的朋友都说十二连环坞睥睨天下,目中无人!”
花鸡也懒得在理会全祖望,转问沈胜衣,“这之前路经襄阳,你可是杀了我们黑鲨坞的好几个弟兄?”
“你是说钱起,崔浩,归十八他们?”
“正是说他们。”
“他们杀了我一个朋友!”沈胜衣冰冷的眼瞳刹那仿佛燃起了火焰。
“你那个朋友犯在我们手上,死了也是活该。”
“那是说,犯在我手上,亦是他们自寻死路。”
花鸡连声冷笑道,“我们现在也是自寻死路的了?”
沈胜衣语声陡沉,说道,“我并不喜欢杀人,但对你们这种人,却相反,绝不会轻易放过!”
花鸡冷笑作答,斜瞟一眼粉豹紫鸽,传音入密道,“点子硬,你们看怎样?”
紫鸽也自用上传音入密的内功,道,“江湖传言不能作备,凭我们三个人的身份,也不能就此一走了之,贻笑江湖,且试他们几招,要是实在难以应付,再行定夺!”花鸡微颌首,道,“就这个办法,凭我们的身手,即使打不过他们,要脱身应该也不是一件难事!”
“这个倒不必!”
粉豹倏的插口道,“我吃定了那个花花太岁,一上我就放狠,几下子尽快将他解决,然后转与紫鸽联手,合两人之力,结果那个女娃子应该轻而易举,剩下一个沈胜衣,凭我们三人是必游刃有余!”
花鸡一瞟那边花花太岁道,“我也知道他能征惯战,可是那回事!”
这句话出口,三人相望一眼,一齐放声笑了起来。
全祖望这边鉴貌辨色,也猜到一鸡一鸽一豹是在说自己,冷笑道,“你看他们又在打什么主意?”
“依我看是有意算计你!”沈胜衣应声回头。
“等一会儿动手,我们尽量将他们分开,只要不给他们有机会聚在一起,大概还是不成问题!”
说话间,紫鸽那边已一正脸容,道,“不过据我所知,那个太岁拳脚实在不错!”
粉豹左右双手锁心环一翻。
“我不会陪他拳脚上见高低,如果对我,他还是不用兵刃,三招之内管教他横尸地上!”
紫鸽微微点头,转问花鸡,“你自问可以支持多久?”
花鸡不假思索道,“姓沈的虽然名满江湖,未必传言中那么厉害,一两柱香的时间之内,谅他也奈何不了我!”
“有一两柱香的时间总够了,粉豹那就先助我解决天刀,再对付沈胜衣!”
粉豹应声一撇嘴。
“你这只鸽子几时学得那么谦虚,说不定我还未得手,你早已将那个女娃子力劈刀下!”
紫鸽反而皱起了眉头。
“卜啸虎的武功你我是知道的,血手阎坤,还有箫师亮,都不是无名之辈,那个女娃子杀的他们,那张天刀只怕还不是容易应付得了!”
花鸡道,“那你到底打什么主意?”
“粉豹的说话亦不无道理,这一次我们就依他,拼了!”
紫鸽左手刀脊上一掠,右手把刀一挥!
沈胜衣那边看在眼内,道,“他们准备动手了!”
语声方落,花鸡那边已然尖声高呼,“姓沈的,你还等什么?下来!”
那“来”字还在半空摇曳,沈胜衣人亦已在半空,凌空一个风车大转身,头上脚下,连人带剑,离弦箭一样飞射花鸡!
那种迅速,那种声威,简直就像是闪电奔雷!
剑未到,森寒的剑气已然迫人眉睫!
花鸡混身都几乎起了鸡皮疙瘩,尖叫一声,整个身子往后一缩,一下子倒退丈外!
沈胜衣那一剑虽然凌厉,一样是收发由心,花鸡一退一开,剑势亦收回,人同时落地!
花鸡亦同时扑返,双爪齐出,左取沈胜衣双眼,右夺沈胜衣左手长剑。
沈胜衣不退不避,剑一挑一抹,震开攻来双爪,咧嘴猛一声咆哮!
咆哮雷霆,剑光雷霆之中暴盛,一剑突化千锋,暴雨一样洒向花鸡!
花鸡急忙招架,一对金爪舞的风雨不透。
只可惜他这一次遇上的是剑雨!
剑雨暴洒,花鸡那一对金爪守得虽然严密,片刻便已给剑雨击破。
花鸡当场变了落汤鸡。
好在那剑雨击开了金爪,所余的力量已有限,花鸡的双袖虽然多了好几个口子,两条手臂总算平安无事。
剑雨并未竭,就好像那夏日突来的暴雨,一阵之后又是一阵。
花鸡仓皇后退,一退最少退出了两丈多三丈!
这只鸡,虽然没有羽毛,退起来,也并不慢!
沈胜衣亦不慢,如影随形。
粉豹,紫鸽一旁看着不由的齐都心头一凛,紫鸽意念一动,正想从沈胜衣背后掩上,眼旁已瞥见人影一闪,一道刀光凌空向自己飞来!
那一刀迅速绝不在沈胜衣的一剑之下!
紫鸽到底也是用刀的行家,刀光一入眼,便知道厉害,一偏身,手中刀“举火燎天”,忙挡向来刀!
这一刀才起,那一刀便已落下!
呛啷的一声巨震,两刀一合一分,火星四闪!
练真真连人带刀借力使刀,立时又飞入半空,那纤腰一折,人刀又凌空落下!紫鸽一口气都还未吁过,又已见刀光临头,忙再举刀挡去!
又是呛啷的一声。
练真真又再凌空,一折腰,人刀又再向紫鸽当头劈落!
她的身子似比棉花还要轻盈,燕子还要矫活,刀势却是犀利无比!
一时间,呛啷呛啷的刀击之声不绝,紫鸽一连封挡十八刀,练真真一连凌空十八个翻滚,紫鸽刀上越用力,练真真便越凌厉!
十八刀挡过,紫鸽的脖子虽然还没有疲倦,眼睛却已开始发花了!
练真真就像是一只大蝴蝶,半空中高高下下,人刀滚花飞舞炫目,紫鸽仰着头应付,实在吃力的很。
十八刀给撞开后,练真真凌空又是一个翻滚。
人翻身,刀滚花,人刀又是凌空击下!
好一个天刀,好一张天刀!
不单只紫鸽,粉豹就旁边看着,眼睛开始有些发花。
好在他眼睛只是有些发花,全祖望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总算还能够立即察觉。
全祖望并没有像沈胜衣和练真真那样子半空中飞来飞去,他只是缓步走下假山,缓步走到粉豹面前。
这倒不是他轻功不够高明,不过他手上握着一柄百多斤重的大铁椎!
他若是也来一个凌空飞身,只怕,身子还未飞到一半就这连人带椎“通”的直落地面!
走到了粉豹面前,他才收住脚步,面上居然还有笑容,笑着说道,“你不是看的已觉手痒!”
“嗯!”
粉豹虚应一声,一对锁心环已蓄势大发。
“我也一样的感到手痒!”
全祖望笑容可掬。
“哦?”粉豹只管虚应,脸上一些笑容也没有。
全祖望不以为意,接又道,“看着你我这个样子,我忽然想起了两句说话。”
“那句话?”
“以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粉豹的肚子里居然也有几两墨汁,居然也晓全祖望说话中的含意,冷笑道,“你我也应该动手的了!”
“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全祖望的左手随即搭上椎柄。
粉豹的目光不其而落在那个大铁椎之上,当场一怔,脱口问道,“你不是用拳脚?”
“今日用拳脚又怎消我一肚子的郁气?”
粉豹揶揄道,“你使得动那大的铁椎?”
“使得动使不动,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最好就上来亲身试试!”
“我可以不试?”
“不可以,来,先吃我一椎。”
全祖望猛可一声暴喝,一椎向粉豹拦腰扫去!
椎动风声,椎未到,风已将粉豹的衣袂头巾激荡的猎猎纷飞!
椎走“玉带围腰”,全祖望用在那一柄大铁椎之上的赫然是剑上的招式。
就是武功不好的人现在也应该说看得出全祖望不单只使得动那一柄大铁椎,而且还可以将那一柄大铁椎随意运用!
粉豹这一惊非同小可,慌忙往后退!
全祖望大笑追上,第一椎去势未尽,那双手一翻,椎一挑一落,第二椎已然杀出!
“力劈华山!”
第二椎走的却是刀势!
这一椎声势更见凌厉,更难抵挡,粉豹只好再退。
他到底没有忘记手上的一对锁心环并非重兵器,若是硬碰硬,难保一个照面就给砸掉!
全祖望得势不饶人,步步紧迫,第三椎,第四椎,左一椎,右一椎,“狂风扫落叶”,“乱雨打芭蕉”,连环三十六椎,猛向粉豹砸去!
一椎一咆哮,声势夺人!
那一肚闷气全祖望似乎真的要发在粉豹身上。
粉豹一退再退,不知不觉退到花径,一旁的一座比较细小假山面前。
粉豹并未发觉,全祖望的咆哮虽未震聋他的耳朵,大铁椎激荡起的劲风已几乎令他窒息,眼神虽还未眩,心神却已被夺!
他整副心神就落在全祖望那飞舞的大铁椎之上,寻隙抵瑕,只等全祖望那大铁椎一露出破绽,锁心环便双双抢入!一近身,大铁椎便无用武之地,就轮到他的一对锁心环大显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