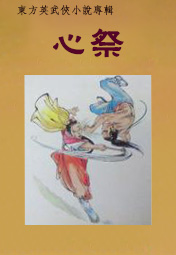马蹄声引得天宝赌坊台阶上三人注目望来,其中一人早哈哈笑起来,高声道:“好家伙,才几个时辰没见着,竟然骑上马了。”另一个也叫道:“那不是伍偷儿吗?过年他还输了个鸟蛋精光的垂头丧气走了呢,只一转眼间竟然阔气了,这算什么古景。”“伍兄,我三人也才刚来到,今见伍兄前来,正好一齐进去一战,如何?”
伍大海摇摇头,道:“我还有正事待办,约莫着我会因为办了这件事多少会捞上几个,你们且等着吧!”
三人一听,全围上来,早听其中一人道:“伍兄,你别坏了我们规矩,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约定,见面赌三把呀!”
另一人起哄的笑道:“对,见面赌三把,快下来吧,即算事情再急,先玩上三把也不迟呀!”
一手摸着怀中十两银子,伍大海道:“也只有十两银子,还得替人办事呢,如果输了,我拿什么替人买衣衫的?”
早又听得另一人笑道:“哈哈,你别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吃的,弄几件衣衫还难不倒伍兄吧!”
伍大海一想也是,自己如果输了,干脆找家大户进去摸上几件衣衫去。
心念间,他仰面望望“天宝赌坊”那盏西瓜大灯笼,嘴角一咧,大龅牙全露了出来,笑道:“好!大老爷坐大堂——吆五喝六去。”
三人帮着他把马拴在天宝赌坊门口,簇拥着短小的伍大海,一窝蜂似的挤进了天宝赌坊。
可也真是玄。
玄当然是伍大海的十两银子才在天门下了一把便被庄家扫去。
这地方可是不讲交情的,腰里没铜不敢横行,如果这时候有人要加以援手的借你几个,大概这人又在打你什么主意了。
拍拍腰间,伍大海长身而起,苦笑道:“没了,我该去办正事了。”
这时早有几个人把伍大海按住,道:“慌什么嘛,门口你不是还有匹枣骝马嘛!”猛的一阵摇头,伍大海道:“那马不是我的,我也不会有马骑的,各位,且等一天吧,天宝赌坊是我的家呀,哈……”就在这时,远处走来个大个子,他一手端着水烟袋,笑问道:“怎的这般高兴,赢了?”
伍大海一看,全身一哆嗦,因为这人是驻马镇上的地头蛇,天宝赌坊可是他开的,那驻马镇北面五里地的尚武山庄上,“铁壁熊”字文山还是他的磕头兄弟呢。人称“灰面太岁”蓝风便是此仁兄。
涎脸一声哈哈,伍大海道:“蓝爷,十两银子全输光了,我这就走人呢,可是他们却仍拉着我不放人呀!”
“灰面太岁”蓝风“哦”了一声,斗鸡眼一瞪,雷公嘴一紧,道:“这证明你伍偷儿尚有信誉,他们愿意你欠帐嘛!”伍大海道:“就算欠帐也得等我先办完事情。”说着他一矮身子,匆匆自桌下面钻出去,一路到了天宝赌坊外。
大门外,他喘了一口气,心中着实一紧张,因为蓝风已知道劳爱同宇文山两家之间的事情,他曾听蓝风大骂劳爱不识抬举,早晚要替兄弟出口怨气呢。
如果劳爱在伍家祠堂的这码子事被他知道了,又不知要弄出什么事非出来,一旦到了那时候,只怕连劳爱也不会轻易饶过自己了。
拉马走在街道上,伍大海心中琢磨,绸缎行自己是进不去了,得找家大户弄几件衣衫出来,伍家祠堂里,劳当家还在等着呢!
突然间,附近有家大门打开来——从里面正嘻嘻哈哈的走出几个人来,伍大海望去,只见是两个老夫妻在送客人呢。
只听那灰髯老者抱拳笑道:“烦请禀告亲家翁,三天回门三天住,明日一早就送她回去了。”
伍大海隔着马腹瞧过去,早见大门内的正厅廊下有个女子站在那儿,一身衣衫可着实美,灯光下还亮闪闪的,显然是绸缎制做的。
伍大海一笑望望这家大门,当即拉马走去。
附近有棵老榕树,伍大海把马拴在树下面,自己蹲坐在马旁边,而驻马镇已在慢慢沉静下来了。
约莫着半个时辰过去了,伍大海这才站起身来,缓缓走近那家大门口。
附近他只是稍一打量,腾身已翻过大门里。
伍大海是个矮个子,武功虽然平平,但他的轻功了得,只在屋脊上几个腾跃,早已摸近一处楼阁前。隔着屋脊望过去,只见这座大楼十分豪华,廊下面只挂了个玻璃宫灯,似是照路的,那些廊柱与门窗,全是盘龙雕花,净光闪亮,二楼上天热还开着几扇窗子。伍大海施展夜鸟投林身法,毫无声息的进了楼内。说多巧便有他娘的多巧,这间楼内的大床上面,正躺着两个人,二人的衣衫就脱挂在帐外面。
均匀的鼻息声传来,伍大海凑近床前望去,不由得想笑又未敢笑的伸手捂住自己嘴巴。
原来那床上正睡着一男一女,女的一头秀发正把个男的一张脸遮掩了一大半,二人头顶头宛似斗绵羊。轻轻伸手取出女的衣衫,伍大海连女的内衣也一齐扫数包起来。
匆匆的跃出这家大宅子,伍大海这才坐上枣骝马吹着口哨拍马直驰伍家祠堂。
已经是四更将尽了,伍大海才赶到了伍家祠堂里,早见劳爱已走出院子来,道:“怎的去了这么久?”
伍大海抹去额上汗,道:“现成的新衣没买到,只得买来这几件,劳当家的你快穿上看看合不合身呀!”
劳爱见了衣衫,也不再多言,立刻拿了就走,一径到了祠堂里,灯光下她看了一遍,不由赞道:“这还是新的嘛!”
伍大海可不敢走进祠堂里,他站在院子里问:“劳当家,可适合?”
劳爱边穿边应道:“不错,还算适合,只是稍见小身了些。”
劳爱绝对想不到她现在穿的这身衣衫是何人的,当然,伍大海更是不会去管这衣衫是谁的,他只要能交差便阿弥陀佛了。
上身也是粉红绣花的,下面是长裙子,劳爱一向是穿长裤,这时她穿上裙子,更见她妩媚动人一面。款款走出祠堂,劳爱来到自己马边,笑对伍大海道:“今夜你做的这两件事令我心存感激,但却想不到给你什么样的报答……”伍大海忙摇手,道:“劳当家的,你这就见外了,上回替你跑一趟西凉,你大方的给了我五十两金字,这次只是碰得巧,顺手劳罢了,你就别放在心上了。”
东方已在发白,高原上又见晨风开始吹刮,祠堂四周的树叶已抖动,劳爱伸手入袋,狠狠抓出几锭银子,道:“这些你先收下来用……”他一顿又笑笑,道:“我很清楚你的毛病,没有赌你会活不下去的,我也不勉强你去戒,但能尽量少赌就少去赌。”
伍大海捧着一把银子,那大概足有七八十两,心中正自高兴呢,早听劳爱又道:“真要混不下去,青龙会欢迎你去,不过夜里这码子事你最好把它忘掉。”
伍大海忙点头,道:“我会的,我会的!”
劳爱腾身上马,调转马头没往六盘山方向去,而是赶往附近的驻马镇,伍大海忙高声叫道:“劳当家的,你这是走错方向了吧,那是往驻马镇去的这一条才是回六盘山的呢!”
劳爱回头道:“我知道,但我得先我家客店洗去这一身霉气呀!”劳爱说的当然是端木良在她身上一阵啃咬与抓舐。伍大海却担起心事来了。
因为劳爱那身衣衫,如果被正主儿碰上,我的儿,这可有得戏唱了。
伍大海搓手直跳脚,眼睁睁望着劳爱拍马直驰驻马镇,心情恶劣得大骂“天宝赌坊”三位赌友害人精!劳爱一马进了驻马镇时候,驻马镇的街上已见行人,不少人望着策马而来的劳爱,投以奇异眼神。
马上劳爱也直拿手拢那散乱后被自己又扎起来的长发,匆匆的策马到了“驼铃居客店”外。
这时从店内走出个小二,几天前他侍候过劳爱,那时还有个背剑大汉跟着,今见她一人前来,早迎上去笑道:“姑娘这是赶夜路了,快请进店坐。”
劳爱翻身下马,立刻对店小二吩咐,道:“别管吃的,先弄一大桶热水送进客房里,快!”小二知道赶夜路的客人多半进得客店来就是先洗个澡清爽清爽自己,然后吃顿饭睡上一觉。
闻言忙点头道:“姑娘跟我来!”
就在数天前她住过的那间大客房里,劳爱好生的把自己泡在个大木桶里,口中哈着大气的撩水洗着,她这时在想,如果不是伍大海及时冒出来,只怕自己现在已血溅伍家祠堂了,因为端木良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
劳爱又望望床上堆的衣衫,不由一笑自语,道:“这伍偷儿可真会办事,这套衣衫也不知他是打从哪儿弄来的,倒也十分相衬呢!”
洗过澡,劳爱又吃了早饭,立刻付帐走出“驼铃居客店”来,只见街上已是车水马龙一片热闹景象了。驼铃居走出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美娇娘,早引起一阵骚动,人们谁不投以惊奇眼光直望着劳爱骑马而去!蹄声得得中,前面正有棵大榕树,附近有家大户,门口又是轿又是马,七八个家丁正忙进忙出呢。不料这时有个年轻人走出来,正看到马上的劳爱,一怔之下,他横身拦住劳爱:“总算我们第二次又碰面了。”
劳爱见是尚武山庄少庄主,自己解除婚约的未婚夫婿宇文长江,先也是一愣,旋即冷冷道:“有事?”
宇文长江道:“当然有事。”
劳爱俏嘴一掀,道:“与我有关?”
宇文长江已是肝火直冒地道:“我问你,长青门少门主‘青衫羽士’南宫兆呢?他是被你杀了?还是被你抓去六盘山了?你快说!”沉声一哼,劳爱道:“你以为他是被我所杀?”
宇文长江道:“总是八九不离十。”
劳爱道:“可是谁见着了?”
宇文长江大怒,道:“劳爱,你以为自己真的了不起呀!那日你不请自来,表现得目空一切,你几曾把尚武山庄看在你眼中?”他一横身踏前几步,又道:“那‘青衫羽士’南宫兆便是看不顺眼你这种长辈面前卖老大的一马追你去,怎么的,你不敢承认了?”
劳爱冷笑一声,道:“宇文长江,你真的以为那日我是专程去向你道贺?嘿嘿,我只不过是借机会归还一件东西罢了,如今劳家与你宇文家情断义绝,两不相干,再要在本姑娘面前吹胡子瞪眼睛,小心本姑娘翻脸不认人。”
宇文长江仰天一声哈哈,道:“你能对本少爷怎样,尚武山庄可并不把你青龙会看在眼里呢!你少在驻马镇上耍威风?”
一听马上女子是六盘山青龙会的人,刚走出门来的一对老夫妇忙拉住宇文长江,道:“孩子,你就少说一句吧,别惹事,青龙会我们惹不起呀!”宇文长江戟指着马上劳爱,道:“岳父呀!你知道这女子何人?她便是我订过婚的未过门老婆,她下海当强盗,你想想我宇文长江会娶个强盗婆?真是笑话!”
劳爱气得脸发青,一按剑就要翻身下马来呢,早被那老夫妻二人施礼不迭地道:“姑娘你快走吧,我女婿定是酒吃多了。”
就在这时候,大门口红影一闪,宁文长江的新婚妻子走出来了。
劳爱马上望去,心中也是一惊,这女子生得好美!宇文长江见妻子走来,早上前一把搂住,故作亲昵状的高声对劳爱道:“多谢你让位才使我得到如此美貌的娇妻,她才是个真正的女人,哈……”劳爱气得全身颤抖不已中,突见宇文长江怀中的娇妻一指自己,尖叫道:“我的衣裙,你怎么穿我的衣裙?啊!原来是你把我的衣裙偷去的呀!”
劳爱惊怒交迸中,低头一看自己穿的衣衫,不由面色由青转红,望望四周围观的人群,咬牙粗声,道:“笑话,你我穿的这种衣裙那是极为平常的衣衫,你再要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小心我劈了你!”
那女的父母早上前拦住自己女儿,道:“小玖,你千万别胡说,你知道她是谁?”小玖正是宇文长江的新婚妻子,闻言早又反指着马上的劳爱,道:“我是不认识她的人,但她穿在身上的衣裙我认识,你们看上衣领口绣的两只蝴蝶,那是我亲手绣上去的,还有她穿的裙子上面配的两条彩带……”灰发老者早拦住女儿小玖,急急道:“别再说了,你能绣别人也能,快回屋里再说。”宇文长江仰天打个哈哈,道:“这年头强盗与小偷本就没什么区别嘛,连别人身上穿的衣衫也会动心的下手偷,哼!”
劳爱一听大怒,戟指宇文长江道:“你敢侮辱本姑娘?”
宁文长江道:“证物尚在你身上穿着,难道你能否认?”
劳爱心中在想,自己明明给了伍大海十两银子要他买的,自己又如何知道这偷儿是在这里偷来的?可恶的伍大海,他怎的不明说,否则自己也不会来这驻马镇了。双目发呆,劳爱咬牙“格格”响中,突听得宇文长江又道:“堂堂青龙会当家的,原来也是个手脚不干净人物,青龙会的……”宇文长江话未说完,突然一团彩影当头罩下来,他尚未及出手,已听得“吧吧”两声脆响,那彩影半空中一个平旋,又飞回马背上。只听得马上的劳爱怒喝道:“这只是个小小教训,下次遇上,必取你性命!”紧接着,她力夹马腹,直往驻马镇外冲去。
宇文长江挨了两记耳刮子,直不愣的呆若木鸡,他实在难以相信劳爱的本领如此了得,竟然面对面的自己没有还手机会,这个人可真丢大了,那么“青衫羽士”南宫兆只怕真的要倒大霉了。
围观的人群,听说马上的美娇娃竟是六盘山青龙会的当家,一大半还不相信呢,不料劳爱露了一手“云里摘月”,还真令人咋舌不已,这时除了惊异之外,谁还敢上前去拦她的。
劳爱一怒出了驻马镇,拍马疾驰直冲高原而来。她心中可在怒骂着伍大海,谁的衣裙不能偷,却偏偏偷宇文长江新娶的老婆,阴错阳差的弄得自己当街出丑。
只不过一个多时辰光景,劳爱已到了伍家祠堂,翻身下马,她提剑直入院门,边高声道:“伍大海,伍大海,快出来!”
祠堂廊上转出个人来,只是这人并非是伍大海。劳爱一怔,问道:“你是谁?
伍大海呢?”
那人摇摇头,道:“姑娘,只怕你要找的人已经死了!”
劳爱一惊,只见这人衣衫破烂,手臂与腿上尽是鲜血,一把青钢剑拄着地。
再看这人,还真令劳爱怦然心动,只见这人年不过二十余岁,剑眉星目,胆鼻阔口,稀疏的几根胡子外,木讷中带着忠厚,只是一根蓝布带子已不能把头上的乱发扎住而使得他看来有些狼狈。
劳爱走近这人,边问道:“你说伍大海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在哪儿?”那年轻人摇头一叹,道:“他死的可惨啊!只怕已辨认不出他的模样了。”劳爱惊异地道:“可是死在祠堂中?”
那年轻人道:“祠堂内有血,但人是死在祠堂外的。”说着伸手一指,道:“呶,就在那处墙外面。”
劳爱指着年轻人,道:“你的这身伤……”一声浩叹,年轻人道:“我这是五更天尚未到路过这里的,听得群狼争食,掩过去一瞧,只见少说也有三十头恶狼在啃食一个人,我以为那人尚有救呢,就挥剑杀入狼群,不想这群恶狼见我一入,早蜂拥着围上我,所幸我距离围墙近,就在一阵砍杀中,虽被我杀死几头狼,自己也被咬得几处伤口,不得已只好跃上墙头。”
他一顿又道:“天亮了,我才看清那被咬死的人竟早已四肢不全,血肉模糊一片了。”劳爱忽然想起端木良来,这人可能把端木良的尸体当成了伍大海的了。
心念及此,劳爱早走至墙边腾身而上了墙头,往外看去,立刻便知道那尸体并不是伍大海的。
冷冷一笑,劳爱正要返身呢,不料那年轻人竟然也跃上围墙来,道:“就是他。”
劳爱惊奇的望着身边年轻人,道:“他不是我要找的人。”
年轻人,“氨了一声,见劳爱跃下墙头,也立刻跟着下来,边又叹惜地道:“这人死的可真惨!”
劳爱一声冷笑,心中暗想,这年轻人自是不会知道端木良是如何死的。
就在祠堂外,劳爱望望四周,知道自己走后,伍大海必然也跟着走了。
当然,八成那伍大海又去赌坊了。
劳爱已坐上枣骝马,她低头望望一身破烂的年轻人,只见他身上几处尚在流血,不由自怀中摸出些伤药抛向年轻人手上,道:“快把药涂上去,也可以减轻痛苦的。”
年轻人接过药来,抱拳道:“谢谢姑娘!”
边调转马头,劳爱又道:“你得去买两件衣衫换上了,手头可方便?”年轻人一笑,道:“银子我还有,我这是一路赶回西凉去的,省着花用,尚能拿几个去买衣衫的。”
劳爱听说这年轻人是回转西凉,不由得下马来,仔细的望了这年轻人几眼,道:“你是西凉人?”
那年轻人点点头,道:“在下西凉槐山人。”
劳爱一听又道:“你是槐山人?”她看了年轻人一阵,又道:“请教公子贵姓大名。”
年轻人道:“在下方敬玉。”
劳爱点着头,道:“那地方的人多都把自己名字带个‘玉’字,正说明槐山出宝玉。”
年轻人一喜,道:“原来姑娘也知道槐山出宝玉呀!”
双手抱拳,又道:“请问姑娘芳名高姓。”
劳爱道:“我姓劳,劳力的劳。”
年轻人笑笑道:“劳姑娘……”他突然一怔,又自语地道:“劳力的劳,劳……”劳爱立刻问道:“怎么啦?”
年轻人忙笑道:“没什么,没什么!”
但劳爱已从方敬玉的眼神中发现了什么,她缓缓的又拉马走入祠堂围墙内,道:“有件事情,我想顺便向方仁兄打听。”
方敬玉道:“劳姑娘尽管问。”
劳爱突然满面冷峻地道:“两年多前,槐山发生一桩武林凶杀奇案,不知方仁兄可曾听过?”
方敬玉一愣又惊地道:“姑娘可是说那有关于天下之最的‘玉王玉后’之事?”劳爱精神一紧,点头道:“不错,正是有关‘玉王玉后’之事。”
方敬玉道:“本来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不在槐山,我是事后才听长辈说的。”
他一顿又道:“不过事情发生的经过应该没有多大出入。”
伸手在鞍袋中又取了些吃的,劳爱把东西送到方敬玉的手上,笑笑道:“该吃些东西了,你先吃些,完了我再听听两年多前的那档子事情。”
方敬玉也不客气,因为他也真的需要些吃的。劳爱又把马匹拴在祠堂廊下,自己也取了些水来喝着。年轻人吃过东西,又把伤处敷药包扎起来,这才拉过一张蒲团面对劳爱,道:“劳姑娘,你也坐下来吧!”
心情有着激动,劳爱道:“我站着也是一样,你快说吧!”
年轻人看了劳爱一眼,缓缓地道:“有位被人杀得血肉模糊年约五十左右汉子,听说这人也是姓劳,姑娘既如此关心此事,则必然与那位被杀的人有关系吧?”
劳爱点点头,却未开口。
方敬玉道:“槐山出宝玉,但宝玉以龙舌沟为最,两年多前,盛传有玉王玉后已被人取得,那是两块浑圆如鹅蛋大小的两块精玉,通体不见一丝杂色,托在掌上迎向日头,但见通体透着乳白,毫光四射,美丽极了,似这种只有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多见的宝玉,论时价只怕无价。”
劳爱道:“这些我已知道,我所要想知道的,是你们槐山地方的人们,有谁知道那七个蒙面凶手的!”
摇摇头,方敬玉道:“没人知道,即算是看到他们的人,只怕一个也不认识,因为当时是在黑夜,但有一件事情,不知在下当不当在姑娘面前讲?”
劳爱一笑,道:“你应该说。”
方敬玉道:“但我必须先知道那位被杀死的姓劳的又是你的什么人?”
劳爱道:“我爹。”她语气平静中含着悲痛。
方敬玉当然看得出来,这时听说那姓劳的竟是这位姑娘的爹,不由一叹,摇头道:“那在下还是不说的好。”
劳爱道:“不论是褒眨,兄台尽管说来。”
方敬玉思忖一下,才道:“在下事前说过,这些只是在下听得来的,当然不一定真实了,还望姑娘听了千万别放在心上。”
劳爱知道方敬玉在安慰自己,当即淡然地道:“事隔两年多,我也只是想知道得更明确一些罢了,方仁兄不必有所顾及。”
方敬玉道:“好吧,那在下便直说了。”他抹抹嘴巴,缓缓道:“槐山出了玉王与玉后,这在地方上是件大事,地方上设礼祭天,击鼓鸣锣的用大红绒布包起一顶大花盘子,抬着那两颗宝玉在地方上游行,准备七天以后呈送西凉王做为大王爷的寿礼呢,当然地方上也加派人员防守着,却不料第三日晌晚,游行刚完,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红面大汉,这大汉手施一柄劈山大头刀,腾空而起中早跃近抬宝玉人的近前——”年轻人望望劳爱,见劳爱神情似在激动呢!
劳爱见方敬玉忽然不言,低头道:“怎不说了?”
方敬玉道:“那个虬髯红面大汉,后来有人说他是青龙会当家的。”劳爱道:“你应该接下去说的。”
方敬玉道:“如果这红面虬髯大汉真是你爹,那他就太过于残忍了,因为……”劳爱道:“我只想听当时事情经过。”
方敬玉道:“这红面大汉只一落地,他竟在一招之间斩去三个人的脑袋,同时奋起一脚,把个老者踢在房顶上当场呕血而死,而他却双手握刀一阵劈杀,光景是挡者披靡,宛如虎落羊圈,就在他一阵疯狂砍杀中,突又见他凌空而起,空中大旋身,而绒盘子上的两颗宝玉已被他揣入怀里,也只是几个起落,便走的无影无踪……”劳爱忙追问,道:“可是他怎会被人杀呢?”
方敬玉道:“就在红面大汉刚走没多久,槐山地方正在一阵慌乱呢,突又见七个劲装人跑来,他们在听了众人的话后,立刻又追去了。”
劳爱道:“七个人?这七个人会是谁?”
方敬玉道:“那七个人什么来路就没人知道了,不过他们七个人还真够快捷的,竟然把红面大汉堵在龙舌沟中,但他们在一阵围杀中伤了红面人,却未曾在红面人身人搜出宝玉,所以才动刀尽往红面人身上砍,当然是逼红面人说出把宝玉藏在何处了,只可惜……”劳爱道:“只可惜我爹死也不说出藏玉地点来。”
方敬玉点头,道:“后来你爹留下一口气,槐山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只能说是七个蒙面人向他下的手,依在下推测,这七个人必然认识你爹,否则他们又何须蒙面?”
劳爱点头,道:“这么说来,宝玉仍然被我爹藏在槐山的龙舌沟了。”
方敬玉点头,道:“不错,虽知道宝玉仍在龙舌沟,但槐山人几乎掀翻龙舌沟,就是没有再发现宝玉。”
劳爱突然一声冷笑,道:“我爹临断气的时候也叫我别为他的死去找仇家。”
点头木然的样子,方敬玉道:“不错,人们也是这么说的。”
劳爱道:“方仁兄,你今就要回西凉了?”
方敬玉点头道:“离家一年了,回去家乡看看。”
劳爱道:“有件事情相托,只是我们萍水相逢……”方敬玉忙笑道:“在下乐意为姑娘效力。”
劳爱道:“方仁兄真愿帮我?”
方敬玉道:“当然。”
劳爱心存感激,目芒中隐隐然已表现出来,她拢一拢鬓发,道:“替我打听那七个蒙面人用的何种兵刃。”
方敬玉点头道:“在下尽力而为。”
劳爱抱拳施礼,道:“谢谢方仁兄相助,六盘山青龙会总堂口,劳爱摆酒恭迎大驾了。”
方敬玉心中琢磨,原来她叫劳爱,连忙称谢道:“不敢,只一有了消息,在下立刻赴来六盘山相告。”
望望方敬玉身上的伤,劳爱道:“何不找匹马来代路?”
苦涩一笑,方敬玉道:“实不相瞒,在下一直跟着师父在江湖上走动,我师父‘苦行僧’了了大师,现在正住在天王庙,我这才先行赶回西凉探亲的,哪会有马可乘。”
伸手取出几锭银子,劳爱道:“收下吧,赶着到镇上买匹马代步,这样便走得快些。”
方敬玉还想推辞,劳爱已笑道:“你我江湖中人,何必在银子上拘礼的。”
方敬玉接过银子,道:“姑娘准备往哪道而去?
劳爱道:“我回六盘山,就等你的消息了。”说完跃身上马,朝着另一方向疾驰而去!澳欠骄从褚采允滦ⅲ呕夯鹤叱鑫榧异籼贸ぢ碚蛏献呷ァ?
就在这时候,伍家祠堂正门里,那块巨大的匾额后面,“唿”的一声跃下个人来。
不错,他正是龅牙外露的矮子,“八爪神偷”伍大海。
原来伍大海见劳爱骑马直驰驻马镇,心中立刻嘀咕起来,因为他偷的那衣衫万一被正主儿遇上,劳爱必然会当面出丑,其结果可想而知。
但伍大海已是两夜未合眼,只得找个地方睡一觉,他知道自己家门的祠堂没地方躲,只得跃上这块尘土半寸厚的匾额上睡下来。
他说睡便睡,甚至连方敬玉墙外斗群狼也未把他吵醒,也就在日出一竿高,劳爱的马蹄声才把他惊醒,他听劳爱的呼叫声,知道真的被自己料中,再大的胆子他也不敢爬出来,只得屏息的听着他们的对话。
如今,他却相当得意的抬头望望那块大匾额,黑漆的底面已剥蚀,四个大金字已蜕变成暗灰色,但仍可以看见四个金刚苍劲大字:“佑我子孙。”
伍大海耸肩一笑,自语道:“祖宗们,谢谢啦,哈……”
伍大海走了。
他当然是走向驻马镇的。
因为“天宝赌坊”才是他认为的快乐之地呢!劳爱一马驰回六盘山,把马留在前山的大茅屋,早听得前山发出一支响箭直冲云汉。
劳爱人尚未走近吊桥呢,吊桥的另一边石总管与祈老八、余唐、韩彪等,正率领着近百名青龙会兄弟,分排两边在迎接了。
劳爱端正一下衣裙,赧赧然的走上吊桥直往对岸走去。
石总管等见当家的突然穿着裙子,这可就透着新鲜,因为劳爱一向皆以长裤加上薄底快靴,而今脚上仍是靴子而下身却穿着裙子。
劳爱过得吊桥,大元已忙着上前接过长剑。
祈老八已当先施礼,道:“当家的好!”
紧接着所有迎接的人皆高声问安——劳爱点点头,高声道:“兄弟们大家好。”说完大步自中间走过,直往山道上走去。
这时石总管上前紧跟着,低声道:“当家的,南宫兆那小子这几日似是憋不住的嚷嚷着要见你呢!”
劳爱“氨了一声,道:“他要见我?”
石总管道:“这两天送去的饭还被他摔出洞外呢!”
劳爱冷然一哼,道:“那就饿他三天不给饭。”
就在这时候,迎面有个小孩子跑来,边高声道:“姐姐,姐姐,你回来了,我的糖葫芦呢?”是的,来的正是劳正。
劳爱还真的一怔,因为他就是忘了给小弟买上几串糖葫芦带回来了。
忙伸手入怀摸出一块银子,劳爱笑对小弟道:“且等等,我要他们下山给你买去,姐姐办事忘了给你买了。”
劳正挣脱姐姐双手,退了一步,小嘴一翘,道:“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吃了,你看你尽给自己买新衣服穿,哪会管我呀!”说完回头跑回后寨去了。“劳爱心中一痛,小弟又如何知道这身衣裙的来路?是的,这是回门新娘子的衣裙,当然是新的,偏偏就是被伍大海这偷儿弄来,自己一肚子委屈尚未找地方出呢,却又被小弟这么一叫,心中大是不对劲!
劳爱伸手却未开口,她摇摇头,一叹——余唐早笑道:“想吃糖葫芦还不容易,着人下山去买上个三五十串回来,准叫少爷啃个三天也啃不完。”
劳爱突然回身,道:“你们堂上等我,我去换件衣衫就来。”
石总管道:“当家的刚回来,今日该先歇一宿,明日再说吧!”劳爱道:“不,你们等我去。”
于是,劳爱大步走向青龙会总堂后面的大楼阁内,而楼上已是劳正的哭声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