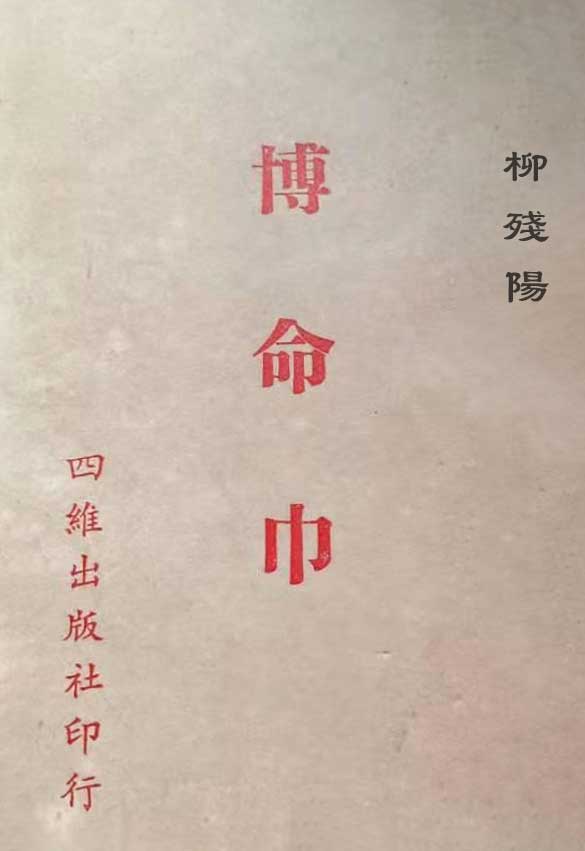从昨夜到天明,如今已过了中午,青龙会的正厅上余唐几个仍然守在那张长方桌四周,几个人连水也未进,因为劳爱还躺在那儿双目紧闭,一动未动呢!
钱大夫又看过劳爱几次,觉得劳爱在一阵挣扎过后,如今正是熟睡的时候。
当然,恢复体力的最佳途径便是睡。
又是掌灯时候了,青龙会的正厅上,劳爱先是蠕动一下,紧接着“氨的一声睁开眼来。
石冲等立刻围上前去,只见劳爱眨着一双无力眼神尽向围着她的人望!钡剿吹搅朔骄聪掠褚院笳獠怕冻龈銎嗔沟男σ狻?
方敬玉忙低声问:“当家的,你感觉如何?”
劳爱只是一个苦笑,道:“肩上有些痛,也很饿!”
余唐早叫道:“好了,好了!快叫灶房弄吃的送来!”
这时钱大夫一捋灰髯,道:“弄碗蛋花面汤,可不能多吃,且容我再看看她的伤口再说。”
方敬玉石冲二人帮着把劳爱扶好,钱大夫解开布袋,只见那布带已黑了一块,而伤口已见到红嘟嘟的血肉。
钱大夫笑道:“行了,我这里再替她换上生肌长肉的药,三五天便没事了。”
劳爱再看几人一眼,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石冲忙道:“当家的,这是正厅呀!”
劳爱欲撑身而起地道:“送我回后楼去,怎好睡在这里。”
石冲几人这才想起来,当家的是应该在后面楼阁养息,只因为几人一见当家的昏迷,全没有注意的才临时把劳爱放在这青龙会的议事正厅上。
如今经劳爱一说,石冲立刻命人抬来一张架床,匆匆把劳爱送到后楼去。
钱大夫把劳爱的伤处又洗后敷了药,且又仔细的包扎好,这才对守在一旁的石冲,道:“石爷,你们当家的已无大碍,她烧已退,只需休养三五日便没事了,我这里再留下些补身子的药丸,早晚服下便行了。”
石冲接过钱大夫的药,道:“怎么,你要走?”
点点头,钱大夫道:“你们当家的已经好了,我已尤必要留下来,还是早些回平原。”
余唐大怒,道:“混帐东西,才来一天便要走呀!”
韩彪也怒喝道:“他娘的,老子最是清楚你们这些江湖郎中,一个个见钱眼开,没本事医,便说什么病入膏盲,遇人小病却又夸大其词的猛敲竹杠,说穿了一句话,得要钱处且要钱,没得银子翻白眼,是吧?”
钱大夫哪见过这几个大毛汉发火,如今经余唐韩彪一吼,早吓得一哆嗦,道:“二位爷误会了。”边指着石冲忙又道:“不信二位可以问这位石爷,压根我就是不要银子的,这时便更是不会向你们要了。”
祈老八一听,一个箭步冲上前,簸箕般的大巴掌扬在半空中,左手已提起钱大夫,吼道:“好哇,你这老奸巨猾的即中,你原是怕爷们银子脏又硬的不敢拿了,所以你才要急急的离去是吧?祈大爷一巴掌劈了你这身老骨头,看你还要走不走!”
锦罗绣帐内,劳爱吃力地道:“你们在干什么?怎可以对大夫如此无礼?”
祈老八回来道:“当家的,你说这老小子可不可恶,他要溜了呢!”
方敬玉忙走到床前,道:“当家的,你歇着别再多说话了。”
劳爱望了方敬玉一眼,道:“方兄,谢谢你了!”
方敬玉道:“属下分内事。”说着走近祈老八,道:“祈兄且放下钱大夫,由我来说如何?”
祈老八冷的放下钱大夫,道:“你给我安心住下来,我们当家的哪天下得床来,你哪天才能离去。”
钱大夫吓的直点头不已!
其实昨日劳爱那种模样,青龙会上之下之全吓呆了,好不容易请来个大夫,而劳爱才见起色,他们如何会放钱大夫走的。
这时方敬玉轻拍着钱大夫笑笑,道:“钱大夫,害你受惊了!”
钱大夫忙期期艾艾地道:“没……没什么!”
方敬玉道:“其实你还清楚,他们几位全是刀子嘴豆腐心,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天下最热心的人了,你别怕,只等我们当家的有了起色下得床,我这里亲送大夫回家,且少不了你的出诊费,如何?”
钱大夫道:“石爷曾说过,只要你们当家病好,平凉地方的安全就由贵会担待了,所以,这诊费我是分文不能收的。”
余唐哈哈大笑,道:“我操,这原是小事一桩,放心吧大夫,往后有谁再敢动一动平凉一草一木,只管着来人说一声,青龙会准会连本带利的替你们找回来。”
看到这种情形,钱大夫知道一时间是不能走了,遂点点头,道:“也好,各位能拍胸脯为平凉地方安危保证下来,我钱通自应感思图报把你们当家的伤治好,我住下了!”
韩彪早哧哧笑道:“这才象话!”
其实钱大夫只在青龙会多住了一日,因为第二天劳爱便能起身下床了。
劳爱除了伤口尚有一点痛之外,精神已好多了。
她本来身体好,一个练武的人底子硬朗,只要烧退,身体便立刻恢复过来了。
这天过午,劳爱便着人封了银送那钱大夫回平凉去了,临行,钱大夫又留下许多治毒药丸。
又一日过去了!
一早起来,劳爱便立刻来到青龙会那间议事正厅上。
劳爱带伤坐在那长方桌一端,她先是望望方敬玉,这才对祈老八等五人道:“这次同风雷老儿决斗,我才发现他们连手时候的威力,怪不得我爹连脱身机会也没有!”
石冲道:“当家的这次实在太冒险了!”
劳爱道:“当初我的用意便是要一试他们的手段,我原以为应有四到五个,不料三个便令我难以应付了,所幸……”她望向方敬玉又接道:“所幸方兄及时赶到,总算是化险为夷了。”
方敬玉一笑,道:“属下绝对想不到当家的是中了姓沈的毒刀,还以为当家的受了伤呢!”
劳爱笑中带羞地道:“还是多亏方兄沿途照顾,不然那晚我已遭他们毒手了呢!”
祈老八五人忙一齐站起身来向方敬玉抱拳,那祈老八且正言伟举地道:“方兄弟,青龙会都感谢你了!”
方敬玉忙起身还礼,道:“一家人还言什么谢,青龙会容我方敬玉加入,我总得有所表现吧!”
也就在这时候,早有人走进正厅向劳爱禀报:“禀报当家的。有个叫伍大海的人要见石爷呢!”
石冲一笑,对劳爱道:“我去见见这老偷儿去。”
劳爱道:“带他进来吧!”
石冲一招手,那人早又走进大寨门口来到正厅上,伍大海正在翘首往里面看呢。
跟着那汉子,伍大海匆匆走入青龙会正厅上,只见地上那张老虎皮,虎头冲着正厅的门,虎牙暴出,比之自己的大龇牙更厉烈可怕。
哈腰走近长桌边,伍大海忙对劳爱施礼,笑道:“劳当家的,金安,各位爷们可好!”
劳爱一笑,道:“可是缺少赌本了?”
伍大海忙摇手道:“不,不,不,自从石爷一句话,伍大海便决心戒赌了,而且我连天宝赌坊大门口也不经过了。”
劳爱一笑,道:“你真的能悔改?”
石冲早笑道:“属下告戒他,在为我办事期间不许进赌场,至于以后嘛,谁又能管得了的。反正狗改不了吃屎,这辈子他是难以悔改的了。”
伍大海相当哭丧地道:“石爷呀!我伍大海已是悬崖勒马,浪子回头!”边入怀掏出些银子,又道:“石爷给的银子我还有呢!”
劳爱道:“说吧,你匆匆赶来六盘山干什么?”
伍大海道:“我伍大海受石爷之托,自然是要忠于石爷之事,这些天我尽是在大散关附近遛马腿,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算是把主儿碰上了。”
石冲道:“可是那匹‘一条鞭’吗?”
伍大海道:“是、是!”
石冲一笑,道:“我们已经知道那匹马的主子了!”
伍大海有些惊讶与泄气——劳爱却笑问伍大海,道:“说说看你所遇见的?”
伍大海道:“那日渭水河岸我同石爷还有个贝老九三个在柳林下,贝老九把我支走以后,我便又骑马往大散关去了,后来一连两三日也没有看到那匹马,不料昨日却被我碰个正着,各位猜那骑马的是何人?”
石冲道:“风雷!”
不料伍大海摇头道:“不是风雷,是个女的。”
劳爱一愣,急问:“怎会是个女的,她长的什么模样?”
伍大海道:“这女的四十上下,却长了一副娃娃面,那双眸子似会说话,骑在马上直转动,她身后面还有个年轻女子,那女子长得很俏,野店打尘,那俏女子向那另一女子叫娘,我才分清楚原来是母女二人。”
劳爱道:“她们往哪儿去了?”
伍大海道:“驻马镇北五里的尚武山庄。”
劳爱冷笑,道:“如果我猜得不错,这女人必是风雷老婆,人称‘狐仙’贺三娘便是她。”
石冲沉声又问伍大海道:“现在呢?”
伍大海忙道:“我来此报信时候,她们尚在驻马镇呢!”
石冲怒道:“快去盯着她们呀!”
伍大海正要告退,劳爱早又把他叫住,道:“伍大海你等等。”
伍大海道:“当家的还有吩咐?”
劳爱一笑,遂命石冲取出五十两银子交给伍大海,道:“伍大海,你不是我青龙会人,但你却在为青龙会做事,我们当然不会叫你白忙一场,这些银子你收下,别再往赌坊跑了。”伍大海一怔,道:“当家的意思是……”劳爱道:“别再去盯那匹马了。”
伍大海怔怔地道:“当家的可是嫌伍大海办事不力了?”
摇头笑笑,劳爱道:“不是,我要你暗中去盯住另外一个人。”
伍大海精神一振,忙又趋前笑哈哈地道:“只要有事忙,我伍大海便不会去想那三十二张,当家的,伍大海在伺候你了!”
劳爱道:“打从今日起,青龙会月支你五十两银子,直到我告诉你停止盯那人。”
在场诸人全都不知当家的要伍大海去盯什么人,一个个目瞪口呆的直视着劳爱……轻声一笑,旋即满面寒霜,劳爱沉声道:“这件事你们全得要口风紧,只当没有这么回事。”
祈老八等六人,彼此互相看着。
劳爱对伍大海也厉言疾色地道:“我只要你暗中盯人,绝不能被他发现你伍大海在盯他,只等我找你去问,你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伍大海忙点头,道:“是,是,伍大海记住了。”
劳爱这才道:“给我盯牢‘包打听’贝老九。”
此言一出,一室惊呼,连伍大海也愣愣地道:“贝老九还用人盯他呀!”
劳爱道:“我只问你,对于我托你的这件事你可愿意做?”
伍大海连忙点头,道:“没问题,劳当家的只管放一百二十个心,我伍大海准能把贝老九每日吃的什么饭,何时睡的觉,拉的什么屎全替当家的摸他个一清二楚。”
劳爱一笑,道:“去吧!支五十两银子你便立刻上路。”
石冲闻听劳爱如是说,当即起身对伍大海道:“跟我来吧,伍偷儿,这可是我们当家的对你恩典,往后只要你能好好干,青龙会吃香喝辣便少不了你一份。”
伍大海忙向劳爱施礼告退,跟在石冲身后,低声:“石总管你这就放心吧,伍大海这是心甘情愿的为劳当家办事,虽说青龙会在道上人的眼里是狠了些,但却狠得令我伍大海拍手,叫我佩服,没话说,我是决心替劳当家把这件事办好的。”
石冲低头望了伍大海一眼,笑笑道:“我今领你去帐房支五十两银子,你小子可别有了银子忘了人,双手捧迸天宝赌坊哟!”
伍大海道:“石总管怎么又来了,天宝赌坊我是不会去了,你尽管放心吧!”
突然,他又呵呵一笑,道:“石总管你知不知道那天宝赌坊这几天关上门在演丧戏呀!”
石冲道:“还有演丧戏的?”
伍大海道:“怎么没有,演的全是哭丧戏,像是李陵碑、哭墓、大报丧、五阎殿喊冤,他娘的单就是一支喇叭口就吵得天宝赌坊那条街上三天不太平,那个蓝风的老婆还直拍棺木痛哭死去活来十几次呢!”
石冲早已不耐地道:“赌坊正开演的什么戏,蓝风死了?”
伍大海笑了,道:“不是‘灰面太岁’蓝风死人,而是他那个独生子蓝大少爷,不知怎的被人杀死在我们伍家祠堂里,娘的老皮,害得我这些天就是不敢回祠堂向我的列祖列宗报个到。”
石冲闻言惊异地道:“那蓝风可是同尚武山庄有勾通,谁敢惹他们?”
伍大海哼了一声,道:“什么勾通呀,我看他们就是一家亲。”
这时石冲已把伍大海领到一处三间房屋门口,那石冲走进去叫道:“帐房在吗?”
里面已有人应道:“石爷来了,石爷,当家的好些了吗?”
石冲在里面应道:“好了,当家的叫支五十两银子,这是送给伍大海的,帐上你记明白就成了。”
不旋踵间,有个老者把石冲送到门口,伍大海望去,只见这老者是个小个子,身材比自己高不了半尺,却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露出一脸精明,这种人在商场上定是管帐能手。
伍大海接过五十两银子,笑道:“石总管,你替我上去谢谢劳当家的。”
石冲道:“记住,可要盯牢那贝老九呀!”
就在吊桥边,石冲送走了伍大海,但他却满肚子狐疑的匆匆回到了正厅来。
正厅上,劳爱缓缓的对几人道:“有许多事情,必须假手他人才能办得圆满,像是我们所须的几处地方之情况,那得去叫贝老九打探,如今再由人盯上贝老九,伍大海就是适当人选,如果我们的人去办,便不容易了。”
石冲正走进去,闻言笑道:“不知当家的为何要伍偷儿盯上贝老九的……”
劳爱道:“因为我渐渐发觉贝老九不简单,有必要派人盯住他,当然,我不希望贝老九有什么事情被我料中,因为当年老当家的对他十分信任,应该不会……”
余唐道:“如果贝老九是个奸诈小人,当家的一声吩咐,我便把这包打听的头提回来。”
劳爱轻声一笑,道:“暂不去理那贝老九的事吧。”
石冲这时又道:“当家的,另外有件消息顺便向当家的报告。”
劳爱道:“是听伍大海说的?”
点点头,石冲道:“伍偷儿说驻马镇上天宝赌坊这几日大唱哭丧戏,是蓝风为他的儿子办的。”
劳爱一笑,望望一旁的方敬玉,因为劳爱曾对贝老九言及,蓝大少几人是她干的。
这时听得石冲提起,早又嘻嘻笑道:“这件事我早知道的,因为蓝大少几人是我杀的。”
此语一出,石冲几人一愣——劳爱便把那晚伍家祠堂的事述一遍……祈老人一听骂道:“他妈的这叫捞不到回头咬,明着赌不赢,暗里要人命,姓蓝的这叫活该,遇上当家也算他小子恶贯满盈,痛快!痛快!”
劳爱这时才对众人道:“本来我在飞鼠崖时候便要逼问那老回子风雷的,因为我们已知道了那匹马是他风家寨的,可是当时的情形对我不利,一旦说出来,必然会令风雷老儿惊异,如此一来,他便会以此为由,重施故技的把当年那些人的力量集中起来,这是我所不愿意见到的。”
余唐道:“就算那些人重聚一起,青龙会也不怕他们!”
劳爱摇头,道:“不,我要各个击破他们,如果任由他们组合,那会造成我青龙会太大的损失了。”
方敬玉这时轻声道:“当家之言极是,已知姓风的是七人中一份子,事情便由姓风的身上开始着手才对。”
劳爱点点头,对方敬玉道:“本来原是要方兄暂去长安展堂主的第一分堂,但眼前形势有变,暂时就不派你去了。”
方敬玉道:“方敬玉但听当家的调派。”
劳爱露出满意的笑容,道:“我十分想见见那位‘鉴玉老祖’玉匠水连天,我想还是方兄再辛苦一趟如何?”
方敬玉面有难色地道:“当家的吩咐,方敬玉自当从命,只是这水连天十分怪僻,一生从未离开槐山一步,而且大半生都是在龙舌沟活动,他就曾戏称自己是个玉石精,要他离开槐山,只怕不太容易。”
劳爱道:“如果许以重金呢?”
方敬玉摇头道:“一个年逾八十的老人,银子只怕对他不太起什么诱惑的了。”
这时石冲道:“当家的这时去找那水老头做甚?”
劳爱道:“目前尚未成熟,但我觉得有去见这水老丈一面的必要,如方兄之言,我考虑自己去找他。”
方敬玉道:“如果当家的要找水连天老人家,方敬玉自当为当家的马前卒。”
劳爱俏目望了方敬玉一眼,道:“看来只有麻烦方兄了。”
余唐一边也道:“狼山风家寨呢?”
劳爱冷冷一笑,道:“我不会叫风家寨过太平日子的。”
石冲道:“何时行动?”
劳爱道:“我早已想妥了,余唐兄先领五十骑快马,三更天便在风家寨附近一阵鼓噪,三更天便回程,然后在第二夜同样时间,韩彪兄也领五十骑快马驰往风家寨,同样的三更天退回来,第三日再由祈老八的五十骑快马去骚扰!”
她冷笑一声,又道:“先叫这群家伙不得安宁,等到第四日,你三人都在正午时候,一齐围向风家寨,但要记住,如果风家寨出寨迎战,你们便立刻回马远去,但在夜间再一次的骚扰之后,便领着人马回山寨来。”
祈老八道:“单单骚扰不攻击呀!”
劳爱道:“这叫先击溃他们的人心士气,以后如何决战,便全操之在我了!”
韩彪道:“风家寨距我们这儿不过百六七十里地,只是对这群家伙闹得心慌慌,好办!好办!”
余唐也道:“何时开始呀!”
“明日你们便开始。”
石冲道:“我这就去叫马房把马匹备妥。”
劳爱点点头道:石冲立刻走出正厅往前山去了。
这时劳爱问大元,道:“你选的人够了吗?”
原来劳爱的卫士二十人已伤亡十人,她已命大元在六七百名青龙会兄弟中再选十名。
这时大元闻说,立刻向劳爱禀道:“已经选就了,只是几日正在练他们轻功呢!”
劳爱点点头,这才对方敬玉道:“我叫人替方兄叨拾了一间房子,只等我的伤愈,倒想知道方兄的那式剑法呢!”
方敬玉忙笑道:“当家可是说的那晚飞鼠崖属下一剑震慑住风雷的那招‘魔鹰扑击’?”
劳爱道:“那晚见你出招,就知风雷难以抵挡,果然,一招之间伤了那老家伙。”
方敬玉笑道:“师父临行交给我的这册《降魔剑法》,如果当家的与属下共研,彼此必然大有进境。”
劳爱本也是练剑的,而且剑上修为也已是高手之列,那峨嵋龙师太当年行侠江湖,便是以“追魂十八式”击败不少武林恶魔,如果再参研这《降魔剑法》,自然是容易融会贯通而水到渠成了。
这时候劳爱点点头,笑道:“对于方兄这番感情,我先谢了,要知武学一途武林中人视如心宝,谁不存私,而方兄竟对我如此厚爱,真令人雀跃……”她自觉有些说漏嘴,面色含羞的忙又道:“也许有一日面对七魔的时候,我二人便以这‘降魔追魂’两套剑法,痛歼那七个恶鬼。”
方敬玉点头,道:“只等当家的身子复元,属下便与当家的共研这套《降魔剑法》吧!”
这时劳爱已有些疲累,见石冲又走回来,便立刻起身走回后楼去了。
方敬玉早由石总管带到正厅右面一间干净房中。
石冲笑指房中陈设,道:“方老弟看这室中陈设如何?”
方敬玉见这房间除了光亮鉴人的桌椅床帐之外,尚有个书柜上摆了些玩物玉器之类,一座乌脚铜灯宛似黄金般闪着亮光,床头上的枕头上还铺了一张狐皮,这一切酷似有钱人家的爷们的书斋。
哈哈一笑,方敬玉道:“山里还有这种派头,倒是出人意料呢!”
石冲笑道:“只方兄弟满意便成了,我得去分派人手喂马匹了。”
石冲原是去前山马厩叫人准备的,只是一下子要出动一百五十匹马,管马的五人一时来不及,他才又匆匆回后山总堂来派人手。
方敬玉见石冲忙碌,就把石冲送出门外,他就着那张红木桌子坐下来。
双目立刻呆视着前方——不!前方原是窗子,但似乎有个人影在晃动……啊!
是劳爱,是的,是劳爱。
方敬玉几乎伸手去推窗户了,但他却又缩回手来,因为他在一怔之下,知道劳爱这时候不会来。
啊!是自己在虚无飘渺的幻想了。
而劳爱呢?劳爱她回到了后楼——后楼原住着妈与阿正弟,但现在除了自己已无他人了。
望着二楼阁房中,珠帘银灯,锦衾绣榻,独自孤眠,连个细诉衷肠的人也没有,长夜绵绵中除了想及老父身中三十八刀惨事之外,那种情意绵绵,儿女情长的意境,似是与自己脱了关系!
如今,方敬玉的出现,自己心中明白,那正是搅乱了她的一池春水生波浪。
躺在床上,劳爱想及自己脱衣由方敬玉替自己裹伤的情景,不由面上一热又笑—
—还有——还有二人共乘一骑,自己斜倚在方敬玉那有力的怀中,耳边所得他有力的紧张呼吸,啊!
人之千里有缘来相会,难道这方敬玉便是同自己有缘?看他的人木讷却颇具丈夫风范,这是青龙会中难以找到的人材,但不知——劳爱心中想着,面上也不时起着变化,因为她总是把事情想到好的地方以后,便立刻又思及槐山来——槐山是老父丧命地方,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解决,那又何必谈什么儿女情长呢!
又是一个响晴天,万里无云——天上无云,但地面上却现出一溜灰云激荡飞旋着腾跃上半天空,半晌未被风吹散,却又是一阵阵的连续着飞扬,飞扬在蹄声的震动里,也激荡在人们的心头!
是的,青龙会的五十铁骑出动了。
余唐一马奔驰在最前面,五十名黑中包头大汉,各背着牛皮套砍刀,飞马紧跟着冲下了六盘山。
当然,余唐是领着这些兄弟们赶往狼山的。
不只是余唐,再等六个时辰,韩彪也会率领五十人赶往狼山。
而祈老八的五十骑,那得等到第二天早上了。
狼山,大散关南面的终南山里。
这儿原来住了一帮远自西北边迁徙来的回子,他们原本是在西北贩马的,道上人全知道狼山风家寨的人十分排外,想在狼山生根住下来,先决条件便是这人必须是回子,否则有时即使想进风家寨找口水喝也不容易。风家寨就在大散关西北方三十里处,附近有个大草坡像是半个扣在地上的西瓜皮般墨绿一片,当年风雷便是看中这一大片青草山坡,才决定在这儿定住下来。
原来回子们牧牛放羊,很注重草地,当然风家寨也养了不少牛羊。
越过这足有一里长的草坡,隔条小河,对面高山下面便见一大排巨木拦起的栅,那即是风家寨。
风家寨寨主老回子风雷领着风家寨的子弟在道上混生活,平日老一辈看起来以畜牧为生,实际上却暗中贩盐与毛皮,遇到有利可图,自然也会干上一票。
由于银钱上的往来,风雷与尚武山庄也拉上了关系。
自然飞鼠崖一战,风雷不敢多在外逗留,匆匆的赶回风家寨,正遇上老婆要出门。
那风雷老婆“仙狐‘贺三娘见当家的回来,立刻迎上前去,但见风雷右臂一条血槽,大惊之下忙问:”你的坐骑呢?怎的走回来了,这伤……“风雷边往寨中走,边道:“老婆子,大事有些不妙了!”
贺三娘愣然,道:“你们没有撂倒姓劳的女子?”
风雷一叹,道:“本来是要得手的,谁他娘会知道半道上还真有那么个程咬金冒出来,硬生生的把人救走了。”
贺三娘一惊,道:“你怎么任其被救走呀!”
风雷已进了正门,更有不少风家寨的弟兄也围到风雷住的那个大院来。
走入屋子里,风雷喘气坐下来。道:“那人剑法犀利,为我生平仅见,我不放人成吗?这臂上的伤就是那王八蛋留下来的!”
贺三娘忙亲自为丈夫敷药,边又问:“淡云成浩他们呢?”
风雷道:“他们去尚武山庄了,两个人也伤得不轻,淡云若非机警,只怕早被姓劳的女子开了膛,成浩更惨,被捅了一剑,差一点没要了老命。”
贺三娘缠着布袋,边急急道:“这么说来,姓劳的只怕不会就此罢休了!”
风雷道:“老淡在姓劳的女子身上也砍了一刀,十天半月的她不见得会好过……”说着他又冷冷一笑,道:”你是知道的,老淡的那把刀可是浸过毒的,不定姓劳的女子已伤重毒发而死,也说不定!哈……”贺三娘道:“姓劳的真要死掉,青龙会不定会大举找来狼山为他们的当家报仇呢!”
风雷道:“这便是我最担心的事,因为青龙会有几个狠角色,全是杀人不眨眼的厉鬼。”
贺三娘道:“眼下我们必须全寨戒备,另外我同女儿走一趟万宝山去把兄弟请来助阵,顺道也把‘一条鞭’骑回来。”
风雷道:“骑马以后,绕道尚武山庄,看看那边情形如何,若得宇文兄大力相助,便不怕六盘山的青龙会了。”
于是,贺三娘匆匆与女儿风萍离开了风家寨。
这件事看来紧张,贺三娘路上自然也不敢多耽搁,却不料回程时被伍大海遇上,立刻把骑“一条鞭‘的人是谁,一口气送上了六盘山的青龙会去了。
夕阳已落山,风家寨前面的那座大草坡上,大群大群的老绵羊刚刚被赶过小河,有一半尚在寨门外呢,远处已听得如雷轰声。
似打雷,但天上无云,风家寨的人忙着寨门边挤着往那大草坡上望去——早听得寨楼上有人高声道:“不好了,是青龙会的人马呀!”
风家寨中也有几个狠角色,除了风雷以外,二寨主风雹是风雷堂弟,这人当年在西北也是个横字辈人物,一把三尺尖刀杀人也宰牛。
另外那大力士段宏能把一头牛弄翻在地。
风雷站在寨门边叫道:“先关起寨门来,快把羊全赶进寨里。”
一旁风雹早狂叫道:“哥,你我也是横吃一方的,怎的让青龙会这些王八蛋耀武扬威到我们寨门口来了。”
大力士段宏也抡拳,道:“且让我出去会会这些狗操杂种!”
风雷抚抚臂伤,道:“你们懂什么?青龙会又岂是易与的,快关起寨门再说。”
这时羊群全进了寨,高大寨门也关起来,风雷刚往高处望去,那段宏已叫道:“寨主你看,他们只不过数十骑嘛!”
风雷冷笑道:“姓劳的丫头可恶,她这种诱敌之计也想在老夫面前卖弄,门都没有。”边哈哈一笑,道:“寨上多备弓箭,余下的人尽去安歇,别理这群东西。”说着,他竟也回寨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