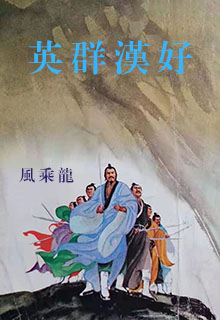熊道元“唔”了一声,道:“这叫‘识时务’,大郎中,你早点听话,不是皆大欢喜么?”
柯乃禾瑟缩着磨磨蹭蹭地往里走,熊道元立即来到门口,同鞍上的燕铁衣躬身道:“魁首,请进屋问话。”
燕铁衣飘然落地,皱眉道:“你怎么搅了这么久?”
熊道元笑道:“这老小子好痞!”
燕铁衣昂然进门,来到堂屋门前的柯乃禾转身回视,吃惊地道:“呃……你又……是谁?”
一眼看见跟在燕铁衣身边的熊道元与崔厚德,柯乃禾更是胆战心惊:“你们……是一伙的么?”
燕铁衣微笑道:“是一伙的,大郎中,请。”
进了这间陈设简陋,到处堆置着草药、干果及兽皮、骨骼的前堂,一股腥味掺和着特异的苦艾味熏人欲呕,燕铁衣又皱了皱眉头,然后,他反客为主地拖了一把竹椅叫柯乃禾坐下,他自己也在另一张椅子落座,熊道元及崔厚德二人,则分左右当门而立——那模样,活像两尊门神!
抖索索的,柯乃禾开口道:“到底……是什么事?”
燕铁衣目光在房中四扫,笑了笑,答非所问地道:“唔,像是个郎中的家,老柯这些兽皮、兽骨头,好像都是鹿麝及牛羊一类的兽畜,你是拿来作钻研之用的么?”
柯乃禾讷讷地道:“行医之人,不可自满于既知之学……仍须勤奋的研读,广习博览,始免于蹈故落际,无以为进……”
燕铁衣点点头,道:“听你所说,倒颇有一番大道理,不错,在求知技艺上来讲,应该如此,但一个人不能只靠了某一项常识或技艺的渊博,便可算个完美的人,最重要的,这人还须有崇高无疵的品格德行节操才行,老柯你说是么?”
柯乃禾迟疑不安地道:“你这话的意思是……?”
燕铁衣和善地笑道:“老柯你不妨扪心自问,近几个月来有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内疚神明之事?”
风干橘皮似的脸上突然起了一阵痉挛,柯乃禾惶急地道:“没有,绝对没有……”
燕铁衣平静地道:“这是出自内心的回答么?”
胡乱点头,柯乃禾惊悚地道:“是的,当然是的……”
燕铁衣道:“你不骗我?”
柯乃禾慌张地叫了起来:“骗你?我凭什么要骗你?我是个正当而善良的郎中,我除了救人活命,又何曾做过什么伤天害理,内疚神明之事来?你你,你……你这家伙不要含血喷人,随意诬蔑毁谤于我!”
轻轻抚着下颌,燕铁衣轻轻地道:“胡绚,你认识么?”
显然,这位大郎中并不是一个善于掩饰内心感触的人,他一听到“胡绚”两个字,顿时面色大变,皱散叠布的老脸一下子绷紧了,黄白的气色里又透出一阵暗青,他唇角微微牵动着,惶恐又惊惧地喊:“不不,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个什么胡绚……”
笑了笑,燕铁衣道:“那么,裴咏你应该认识了?你曾用你秘法特制的‘羊筋肉线’,一针一针缝合了他的嘴巴,令他自一个有嘴巴的常人变成了一个无嘴的怪人,你还曾在他左腮上开了那一个小孔,因为你慈悲的不愿叫他就那么死去,要让他用那腮前小孔摄取饮食,以便再苟延残喘下去,他的一只手也是你切除的吧?他身上生了那么多的毒疮癞斑,是因为在某个极为污秽阴暗的地方耽久的结果,那个地方,大约也是你所选择的了。老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以为你做的恶,犯的奸,便永不会有人晓得么?不,你错了,冥冥中是有只眼睛的啊,那只眼无时无刻不在注意我们,不在监察我们的。你清醒的时候,他在你的身边,你入睡的时候他就在你的心里,没有任何人的任何作为可以瞒过他。老柯,告诉我你受了多久的良心折磨了?内疚了多少日子了?你独自而处之际,你安心么?你数着你大堆财宝之际,你平静么?你过得幸福么?恬适么?你果真问心无愧?”
柯乃禾挣扎着站起,枯瘦的双肩乱挥,像是挥掉沾上身的一些什么,他双目乱翻,汗下如雨,嘶哑号叫:“不是我……那不是我啊……你不能冤枉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是在胡乱诬陷……”
燕铁衣深沉地道:“我知道是你,老柯,因为裴咏已经告诉我了——他不能说,不能写,但他有一只脚可以在地下划字,而你的姓名字划并不太多,他可以划得十分清楚,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他本人带来了,如今,他就在坡下相候,虽然他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奄奄一息,但是,我们相信,他仍会很肯定地认出你来,你要知道,一个受了如许凌虐的人,他是永不会忘记那凌虐他的仇人的!”
柯乃禾一下子僵窒了,他全身不停地栗栗颤抖,嘴巴里居然淌出了白涎,他哆嗦着连连摇头:“不……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
燕铁衣安详地道:“等你两人面对面的亮上相,老柯,你就知道可能——熊道元,下去把裴咏裴爷扶上来!”
轰隆一声,熊道元煞有介事的转身便待往门外走,这时,柯乃禾双手乱摇,其声如号:“不……不要……千万不要……我不能见他……我不能再见他……皇天啊……”
熊道元在门口询视燕铁衣,燕铁衣点点头,于是,他又垂手退回一旁,燕铁衣眯着眼,缓缓道:“你还是爽快承认了吧,老柯,罪证确凿,岂容狡赖?而且,我不妨老实告诉你,关于如何逼出一个人说真话,我们有十分丰富的经验,你是乖乖的自行招认呢,还是要我们动手逼你招认?两种方式结果一样,其感受却完全迥异,老柯,你琢磨琢磨着吧。”
柯乃禾喘息着,不住用衣袖抹汗,他颤抖地道:“这……这……这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燕铁衣叹了口气,道:“熊道元,你去扶裴咏上来对证,崔厚德,你准备用刑!”
熊道元与崔厚德立即回应,两个人马上便分开采取行动!
柯乃禾尖叫着——活像有人正在剥他的皮一样,踉跄倒退,一边干号:“我说……我说……我承认……我承认……”
燕铁衣微微举手,熊道元与崔厚德两人随即停止了动作,燕铁衣轻描淡写地道:“坐着吧,老柯,只要你能与我们好好合作,对你来说,乃是有着意想不到的好处的——我们一向都优待合作的人!”
柯乃禾畏畏瑟瑟的,磨蹭着走回来坐下,他在脸上抹了一把汗水,加上惊惧而流出的泪涕,涩涩怯怯地道:“这位……小哥,如果我……我照直说,你不会泄漏出去,告诉别人是我讲的吧?”
燕铁衣摇摇头,冷冷道道:“当然不会。”
柯乃禾又唠唠叨叨地道:“你真的不会吧?须知这和我的性命有关啊!如果那胡绚得到了我告密的消息,他……会要我这条老命的……”
燕铁衣冷冷地道:“我说不会便不会,而你也不用再含糊那姓胡的了,等我们离开这里,他的性命便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柯乃禾问:“小哥……你们与裴咏……有什么渊源么?”
燕铁衣悠悠地道:“是的,有很深的渊源……”
柯乃禾的脸色是越发青白了,他嗫嗫嚅嚅地道:“啊,有……很深……很深的渊源吗?……”
刚刚阴冷下去的脸色,忽然又幻为一片和煦的微笑,燕铁衣道道:“不谈这些——老柯,告诉我,你是怎么迫害他,折磨他的?”
柯乃禾双手急摇,紧张地叫了起来:“黄天在上……这绝不是我迫害他的……”
燕铁衣低沉地道:“没有用的,用不着这么尖喊,老柯,快点,把事情从头到尾说出来!”
柯乃禾咽了口唾液,苦着脸道:“我当然说,但你……”
不等他说完,燕铁衣已烦躁地道:“我会为你保密!”
这位大郎中连连点头,又畏缩地道:“还有……小哥,你要谅解……我在这件惨事里乃身不由己……说真的……哎呀,其实连我也是受迫害的人,我,我绝不是帮凶……”
燕铁衣缓缓道:“这要我来判断,老柯,你慢慢地讲,仔细地说,不许有一字虚假编造,否则,你就大大地得不偿失了!”
柯乃禾眼皮子又开始跳动起来,惶恐地道:“是,是,我一定从实陈述,绝不增删或虚报……”
又干咳了几声,他开始极其小心,又极其局促地叙说起来:“事情是这样的……呃,约摸在三个多月……不,四个月以前吧,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深夜,外面还落着雨,我业已收拾好熬制的药膏,准备入睡了,哪里知道就在我刚刚坐到床沿的当口,我寝室的那扇窗户竟然无风自开,一个脸色苍白,颧骨高耸又下巴尖削的瘦长个子,便站到了我的面前,我这一惊非同小可,正待呼救,天爷,他的一柄牛角弯刀已指向了我的喉咙……我好不容易镇静下来以后,他才告诉我去做一件事,一件极其可怕又残酷的事……”
燕铁衣道:“大约,就是叫你去缝合裴咏的嘴巴了?”
柯乃禾慌张地点点头,道:“小哥,你是知道的,我们以行医为业的人,讲求的乃是救人治人,怎……怎么可以反去害人……我当场严加拒绝,但,唉,他的短刀却紧抵着我的喉咙,同时威胁我说:如果不依他的话做,他就马上要我的老命……小哥,我是个人哟,我还不想这么横死哪,所以……所以我在尖刀的恫吓下,只好随他出去,就在我们村子的上坡后面一间废弃的茅屋里,我看到了那人,虽然他浑身被捆绑得异常结实,而且还挨过毒打,但我仍然看得出这是个英俊小伙子;在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业已伤痕累累,非常孱弱了。那逼我的人领我抵达茅屋之后,立即令我动手缝合他的嘴巴。我……我只稍一迟疑,便吃他搂头盖脸一顿狠揍……我,我老了,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毒打?实在没有法子,我只好……只好……照他的话做啦……”
燕铁衣平静地道:“听说,要使上下嘴唇那样的胶合生长起来,非得将原先完好的唇片割裂削开才能令生血互混,达到封合的目的,什么?”
柯乃禾脱口道:“是的——”
两个字出口,他又顿悔失言,急忙掩住嘴,以几声干咳,作为掩饰……
燕铁衣淡淡一笑,道:“而这个常识,只怕胡绚不会有吧?是你自作主张?你原可以草草缝合,表面上敷衍胡绚便行,过些日子裴咏的嘴巴只要不会长死,便仍有办法还原,但你却这么彻底地将裴咏的嘴缝合了,使他永不能再还原。老柯,你是为了什么?怕裴咏将来找你报仇?或者怕他告诉什么人?”
柯乃禾惊恐的连连摇头,急道:“不,不是,小哥,因为……因为是胡绚逼我这样做的,我虽有心敷衍,但又怕被他看出,只要一旦被他看破,我的命也没有了。因为,你也知道,他是那种冷酷毒辣的人,他真的说得出,做得到的。”
燕铁衣安闲地道:“即是如此,胡绚又何须告诉你他的名姓?如果你们不是同谋的话?”
柯乃禾忙道:“不是他告诉我的,小哥,是在给裴咏缝合嘴唇前吐露的——我们才一进茅屋。被捆绑在地下的裴咏,即已在昏暗灯光里看见了我们,他用那双眼……老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么一双怨恨仇毒的眼,像蛇似的……他就用那双眼死盯着逼我前来的那人,同时沙沙哑哑地骂:‘胡绚你个猪狗不如的畜生……’那时,我才知道他叫胡绚……姓胡的上前去用力踢他、蹴他,好多的血喷了出来……血都成浆了,那位裴咏也真有种,直叫他踢昏了也没吭一声……姓胡的冷笑着,然后,命我马上施术——”
燕铁衣一撇嘴唇,道:“施术?这也叫施术?昏你娘的狗头!”
柯乃禾吓得一哆嗦,惶恐地道:“不,不是我,我可以起誓,可以赌咒。小哥,是那胡绚砍的,他就当着我的面砍的。一面砍,一边咆哮着骂:‘畜生,你看谁会是畜生吧,你这不开眼的野种,千刀杀的混账,你抢老子的女人,老子就叫你生死不能,叫你在老子的“临波轩”后为你特设的猪圈里过一辈子,叫你真正像畜生一样在那贱妇眼前过一辈子……’他一面砍,一面尖叫狂喊,老天,他红着眼,咬牙切齿,口沫四飞,血喷溅得他一头一脸都是,他——胡绚……像是疯了……”
燕铁衣闭闭眼,没有说话,但是,他的额门上青筋暴浮,两边太阳穴“突”、“突”跳动,牙齿也深深陷入了下唇内!
门边,熊道元与崔厚德也不禁兴起了一股作呕的感觉,他们仿佛看见了那一幕惨厉的,不公平的杀戮,也仿佛闻到了那股子血腥味道,他们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宛如那种粘粘的,热热的血,也喷溅到他们头脸上来了……
燕铁衣嘘了口气,沉沉地道:“真是胡绚下的毒手么?”
柯乃禾像要剜出心来表白似的道:“千真万确,小哥,千真万确……我若非也是听到胡绚在咆哮吼骂中带出裴咏这两个字的话,我简直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我与他毫无仇隙怨恨可言,又怎会迫害他一指头?小哥,我是个和善正当的行医人,我是救人的,怎会杀人啊?”
燕铁衣童稚未泯的面庞上浮漾着一抹难以言喻的怪异表情,他这抹表情成熟世故得与他的形容绝不相称。因此,便好像他那张脸是两个人的面庞叠印在一起了,予人一种极其惊悸玄诞的感受,而这样感受却仿佛是血淋淋的那样带着不祥的意味……
柯乃禾骇惧的,几乎窒息般叫:“小哥……你得相信,相信我啊……”
燕铁衣低沉地唔了一声,道:“后来呢?”
柯乃禾皇惶道:“后来,我做完被迫所做的事以后,胡绚便叫我出去,凶狠地告诉我不得将那晚的事泄漏一个字出去,否则,他会立即前来取我的性命,他的表情显露着他说的话是绝对认真的,我又有什么法子不答应?所以,我便只好保持缄默,直到如今。”
燕铁衣冷冷地道:“就是这么简单?”
柯乃禾急道:“这全是事实,小哥,我没有讲半句假话。”
燕铁衣摸摸下巴,道:“我认为,恐怕你还遗漏了点什么没有说。”
柯乃禾恐惧地道:“不,我全说了,小哥你不能冤枉我,我所知道的都向你剖白了,绝无丝毫隐讳,我起誓……”
燕铁衣摇摇头,道:“你一定还隐瞒了些什么?”
柯乃禾叫:“我真没有,小哥,我真没……”
燕铁衣突然一句话迸出:“胡绚为何不杀你灭口?”
柯乃禾猛地一愣,挣得满面褚赤,结结巴巴:“他他他……我答答应他……答应他为他守口如瓶……我我向他赌过咒,不将此事宣泄出去……”
燕铁衣沉沉地道:“胡绚号称‘粉面狼君’,是个出了名的狠毒之徒,如果,他只是素不相识的前来胁迫你做这件事,事成之后,他也不会留下你来让他在异日承担风险。老柯,胡绚不是那种慈心柔肠的人,你光答应他保守秘密是不够的,他更无须这般麻烦,只要宰掉你,岂不一了百了,永绝后患?他做得出如此残酷的事,便不会在乎多杀一个,设若是我也会这样办!”
柯乃禾惊恐地道:“我不晓得其他的事,我也没与他有另外的暗盘,小哥,我……”
燕铁衣慢慢地道:“你是不见棺材不说真话,老柯。”
柯乃禾挣扎着想站起来,抖凛凛地道:“你不能这样武断,不能这样冤屈我,你不能……”
寒光在一刹那间闪动,当这位大郎中眼中还眩迷于那精芒的映泛时,他的一只干瘪的左耳业已血糊糊的掉落地下!
“哇……”柯乃禾颤抖的惊叫着,痛彻心肺地伸手摸向伤处,那一手的殷红血渍却令他连心肺都紧抽了!
燕铁衣稳坐不动,甚至连眼皮子也不眨一下,他毫无表情地道:“你是否还要等到另外一只耳朵削下来才说?”
柯乃禾痛得一张脸全扭歪了,他心胆俱裂,惊恐至极的大口喘着粗气,老半天没回一句话来。
燕铁衣冷冷地道:“你和胡绚是怎么勾搭的?”
柯乃禾嘴唇瘪动着,一个“不”字尚未出口,光芒骤晃,他的右耳业已一弹向空,洒出滴滴血水!“哟……”这一次,他惨叫得更凄厉,整个人瘫在椅上,口角流出白沫,连一双鼠眼也开始往上翻个不停,四肢却急速痉挛。那模样,像是随时随地都有断气的可能!
一整壶冷茶带着茶叶,全扬向柯乃禾的面空上——熊道元顺手又在他的面颊上批掴几记,然后退下,柯乃禾急促地喘息着,一边机灵灵地打了个寒战,终于又缓过一口气苏醒回来!
燕铁衣平静地注视着这张血糊糊的,黄汁与残茶沾染得狼狈不堪的丑陋面孔,低缓地问:“你和胡绚是怎么勾搭的?”
柯乃禾痛苦地抽了口气,像要哭出来般喑哑地道:“好,好,我说……我说……”
燕铁衣冷酷地道:“这一次,你要再不说实话,老柯,你就会十分痛苦地死亡!记住‘十分痛苦’这几个字,老柯,令一个人死亡有许多种方法,我们知道其中哪一种最不易消受的,如果你希望享用一次,我们便会彻底地满足你!”
柯乃禾呜咽着道:“我说真话就是了……你们不能在折磨我……”
燕铁衣道:“现在!”
柯乃禾鼻子里唏呼响动着,颤颤地道:“胡绚是由他一个姓林的朋友介绍我认识的……姓林的……带着他来到我这里,我们、我们谈妥了这桩交易,由他付我四千两纹银为代价……事实就是这样,其他我告诉你的情形也是真的……那晚上他们两人一起来,在坡后面的破茅屋里,以及胡绚动手砍杀裴咏的经过……我除了替他施术之外,并未伤害他一丁一点……那姓林的,在以前即与我熟稔,他曾替我拉拢过一些不太正当的生意,我们是三七折账……这人如今便在胡绚那里担任管事之职……”
燕铁衣木然问道:“叫林什么。”
柯乃禾哆哆嗦嗦地道:“姓林的叫林宏礼,他本来是江湖上的‘走腿子’,胡绚一向认得他……这件事之后,胡绚便用他做了宅里的管事以为报酬。林宏礼有个外号,人称‘快腿’。”
燕铁衣冷冷地道:“胡绚住在那什么‘临波轩’里?”
柯乃禾挤满点头道:“是……的。”
燕铁衣又问:“在什么地方?”
柯乃禾抽噎一声,道:“豫皖交界的‘大悠河’……”
燕铁衣道:“什么位置?”
燕铁衣目光是沉蔽又冷木地,道:“裴咏的妻子,沈娟,是这桩惨事的起因,为了什么?”
柯乃禾痉挛了一下,呢讷地道:“这……我不太清楚,只是听林宏礼在事后大约提过一些……”
燕铁衣没有表情地道:“就说你知道的这一些。”
柯乃禾艰辛的吞了一口唾液,涩涩地道:“裴咏的老婆……沈娟,是‘锡塘镇’的一个贫家女,生得……十分标致,她是靠着替人刺绣些女红为生的,亦借以供养寡母弱妹,胡绚在以前偶然去‘锡塘镇’发现了她,便惊为天人,非常爱慕,日后曾多次专程前往‘锡塘镇’,希望能接近沈娟,但是姓沈的丫头对他却不热心,甚至次次有意回避他……时间一久,胡绚急了,他亲自找上门去,要求娶那沈娟,但却被那丫头所拒,胡绚碰了个钉子仍不死心,更加以厚礼金银为攻势冀图换回女心,也全无效,送去的东西亦被屡次退回。胡绚又曾托了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前往提媒,同样没有结果,原来沈娟心里早有了人,那人,就是裴咏……沈娟在她十七岁的那年,在镇后的河里洗衣不慎落水几乎溺死,恰好被裴咏路过救起,从那时这丫头即已暗中认定了裴咏为她终生所托……当胡绚求媒不遂之后,他未免老羞成怒,十分气愤,便扬言要在下次再来‘锡塘镇’时将以暴力劫夺,并恫吓沈娟在这期间做最后考虑。沈娟怕了,就不顾一切地奔往裴咏处哭诉,坦陈心意……裴咏也是个有骨气,讲道义的血性男儿,当下便慨允相,并以闪电手法与沈娟成了亲,定了名分……”
燕铁衣垂目闭嘴,不发一言,柯乃禾哆嗦一下,又接着说下去:“事后胡绚来到‘锡塘镇’,发现了这种情形,自是愤恨莫名,暴跳如雷,将一腔怒火全发泄在裴咏身上,他约人在夜里包围了裴家,在一场激战以后打伤裴咏,并劫走了沈娟,但他对裴咏的仇恨并不因此稍竭,便更进一步地做下了这件事……”
燕铁衣长长吁了口气,道:“就是这样了?”
柯乃禾颤抖道:“小哥,你饶了我吧……我是被逼……才做出这等违背心愿之事来的……我业已向你和盘托出……小哥,我知错啦……”
燕铁衣平静地道:“老柯,裴咏是我多年挚交好友,他也是一个磊落豪爽又善良仁慈的人。此外,他曾在以前救过我一次生命;;这样的一个人,却如此悲惨地遭到横死,而且,死在我的臂弯里。老柯,你若是我,你怎么办?”
柯乃禾一下子睁大了眼,讷讷地道:“他……死了?他……没在坡下?”
燕铁衣道:“是的,他死了,那么悲惨的死了,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
柯乃禾血糊糊脸孔扭着,痛苦地道:“方才……你骗我呀……”
燕铁衣缓缓地道:“一个人受了那么多的折磨,你是学医的人,应该知道他活不长久,你之所以会相信我的话,只是因为你心里有鬼,连正常的判断力也削弱了。老柯,他本来可以不死,可以活得很爽快,但他却那样可怜又那样不甘的死了。倒是你们这些该死的,犹尚活在世上继续害人!”
柯乃禾骇然道:“不死我杀害他的……小哥,冤有头债有主,你该找那始作俑者,不能把我一起算在里面……我是被迫的,我也是冤枉的呀……”
燕铁衣低沉地道:“你太邪恶,太贪婪,也太狠毒。老柯,一个郎中,不去救人却去害人,这个郎中还算是什么东西呢?凡是为了利欲而能做出一切恶行来的人,早也失德失格,不能算一个好人,留在世上便是祸害!”
柯乃禾惊恐欲绝地尖叫着,双手挥拒,挣扎着站起,口中狂乱地大喊:“不……你不能杀我……不能杀我……”
燕铁衣坐着不动,生硬地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若是无道而取,往往便也遭到杀身之祸,老柯!”
柯乃禾干号一声,撞翻了桌椅,夺门便往内奔,脚步踉跄,却形同亡命!
燕铁衣轻轻颔首,熊道元飞身追进,只是俄顷之间,一声惨怖的惨叫突起又止,像猛然噎窒住似的变成一声呻吟断寂,于是,人影微闪,熊道元又掠了出来,右手那柄灿亮银枪枪尖血渍殷赤!
熊道元插枪回腰,低声道:“解决了,魁首。”
燕铁衣站了起来,沉重地道:“这是很不值的——天下有许多赚钱的法子,为什么却偏偏有人喜欢采用这最愚蠢,最下三滥的一种?”
熊道元咧着嘴,道:“或许他们认为这才是最方便的发财捷径吧?”
燕铁衣摇摇头,道:“这件事,我到现在才放下心里一块石头。”
熊道元愕然道:“魁首是指……”
燕铁衣道:“幸亏是胡绚霸占了裴咏的妻子,而非裴咏的妻子与胡绚私通合谋,这令我十分庆幸,为我,也为裴咏,否则,事情办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熊道元只笑不答,他知道,他们这位权隆势雄,威凌天下的魁首口中所说的“麻烦”是指的什么,那不仅是字面上的意义,那实则包括了一连串不敢令人想像的残酷手段在内!
燕铁衣有些疲乏地嘘了口气,又道:“好了,我们走吧。”
熊道元道:“‘大悠河’去?”
笑笑——却笑得冷冰冰的,燕铁衣道:“你说吧?莫非是找个地方去睡大觉?”
熊道元忙道:“是,是,我这就去备马。”
肃立旁边的崔厚德不禁暗自为胡绚祈告,他祈告那姓胡的还是早早挖个坑自行跳下去了结,免得被他们魁首找到,对方就会彻底体验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