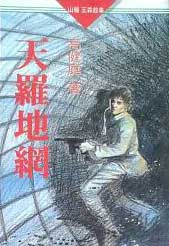第二日,阮伟与公孙兰共骑“白蹄马”直往看龙山,本要三天的路程,但他们翌日午前便抵达看龙山麓。
公孙兰本要急求其父恢复阮伟耗损的功力,故而驮着阮伟,策马甚急,哪知到了看龙山麓,阮伟却已自动运功恢复全部功力。
看龙山山势不太高,虽在冬季,气候不见特别寒冷,但因道路曲折,高地湖泊太多,行走不便,所以牧人很少来此。
他俩爱惜“白蹄马”,下马登山,公孙兰熟悉山路,看来无路可登,她却能曲曲折折、东转西弯,找出羊肠小径。
他俩一路谈笑,走到山脊上回转而上的山道,这山道十分狭窄,仅容一马来往,公孙兰在前带路,阮伟牵马跟在后面。
走了一段,前面转弯处,山石突出,形成一块丈余见方的岩石空地,空地上站着五位星冠羽衣的黑髯道士。
公孙兰暗道,哪来的道士,莫非是爹的访客?
她走近前,见那五位道士只是看着,却不说话,但又并列挡在路中,阻断他俩上山的通路。
公孙兰笑道:“请问大叔们,来看龙山作甚?”
一位面目白净、身材中等的道士道:“两位上山作甚?”
公孙兰被反问,微微一怔,阮伟即道:“我们上山去游玩。”其实他并不知上山作甚,只是随口帮助公孙兰回答而已。
道士道:“山上有什么好玩?依贫道之劝,两位还是下山去罢!”
公孙兰道:“大叔怎知山上不好玩?”
白面道士一句话被问住,好半晌,才迟迟道:“这……这山地处荒僻,行路艰险,若是好玩,自有游客,没有游客自是不好玩了。”
公孙兰道:“大叔可曾上过山吗?”
出家人不打诳语,白面道士即刻回道:“没上去过。”
公孙兰道:“大叔错矣!这山上好玩的地方可多啦,若说没有游客,五位大叔不就是游客吗?”
白面道士道:“姑娘怎知山上好玩的地方很多?”
公孙兰笑道:“我曾在山上住过,自然知道得清楚,五位大叔若不识路,我可带五位上山一游。”
另一位面目漆黑的道士大声道:“公孙求剑是姑娘何人?”
公孙兰正色道:“是家父!”
五位道士脸色齐变,白面道士道:“原来是公孙姑娘,失敬!失敬!”
公孙兰笑道:“大叔可要上山去玩玩吗?”
白面道士讷讷道:“家师……命贫道们守在此地……不得命令,贫道们不敢上山。”
公孙兰道:“令师在山上吗?”
白面道士道:“正是!”
公孙兰笑道:“那失陪了。”说着牵起阮伟,向白面道上面前走去。
白面道士被公孙兰喊了几声大叔,不好意思再阻拦,侧身让过。
又一位面目苍黄的道士举步拦住公孙兰,厉声道:“请公孙姑娘下山!”
公孙兰脸色微变,不悦道:“为什么?”
黄面道士道:“不为什么,就是请两位下山去!”
阮伟脸色勃然大变,忿然道:“天下哪有这种道理,这山难道是你们自家的吗?”他一口气说完这句话,声调苍劲,入耳震颤。
五位道士听他随口露出一股气功,霍然惊动,“哐郎”数声,一一拔出背上宝剑。
但见五把宝剑,光芒不一,白、黑、黄、青、红,分作五种颜色。
一位红面道士手持红芒宝剑上前道:“就是没有道理,今天也只有委屈阁下!”
阮伟失去往事记忆,火气很大,就要给他迎面一拳,公孙兰见机甚快,一把握住阮伟的手,和颜笑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上山?”
白面道士很是过意不去,连忙道:“师父有令下来,贫道就会让姑娘上山。”
公孙兰道:“假若令师一月不下命令呢?”
未曾开口的青面道士生得脸色幽青怕人,他忽然道:“那两位就是一月不能上山!”
阮伟气得大声道:“假若一年不下命令呢?”
红面道士嘿嘿笑道:“也只有请两位一年不能上山!”
阮伟霍然大怒,举起另一只手要向红面道士打去,公孙兰急忙拦住,柔声道:“你不要生气。”
阮伟放下手,忍住怒气,默默不言。
公孙兰神色一变,严肃道:“风闻武当清规甚严,门下弟子行道江湖,莫不是侠义为怀的人物!”
五位道士当面被捧,本是紧张的神色,不由齐都放了下来,白面道士更觉过意不去,脸色微微透出红色。
公孙兰又道:“尤其是五色道士,五色剑法令人可佩,其行径更是可佩可赞!”
白面道士脸红得如柿子一般,低声道:“姑娘不要说了,今天五色道士天大的胆子,也不会让你们上山,请两位下山去罢!”
公孙兰急道:“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让上山呢?”
黑面道士道:“贫道们也不知道,只是师父命令不让外人上山,就不能上山。”
公孙兰闻言,冷言道:“如我们定要上山呢?”
红面道士怒道:“那就看你有没有能耐了。”
公孙兰道:“你的意思是要凭武功才能闯过此关?”
黄、青、红三位道士宝剑横在胸前,大声回道:“正是如此!”
公孙兰牵着阮伟退回来路,远离五色道士十丈后,柔声向着阮伟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听我的话……”
公孙兰以为阮伟功力给自己疗伤时耗损,还没有恢复,才不敢要他随同自己闯关,阮伟点点头,很听公孙兰的吩咐。
公孙兰从鞍旁拔出新购的宝剑,两个箭步,掠到五色道士丈外,停身站住。
五色道士皆知公孙求剑之能耐,想他的女儿定也不是泛泛之辈,五人不敢托大,严阵以待。
公孙兰恳切道:“还清五位大叔让道吧!”
五色道士不敢答话,个个板着脸孔,生怕稍一失神,被公孙兰乘隙而入。
公孙兰在中原曾听传说,武当派一年无意中得到五把白、黑、黄、青、红色的宝剑,并有一本五色剑谱,尔后武当派调教出五位师兄弟使这五把剑,专练五色剑法。
那五位弟子本来面孔都很正常,就因常使色剑,被剑光映照,大弟子脸色变得苍白,二弟子变得漆黑,三弟子变得蜡黄,四弟子变得幽青,五弟子变得血红,武当派的长辈也不知是何原因,脸色会变,但江湖上却说,因那五位师兄弟日夜勤练剑法,才被剑光所染。
因有这种神秘的事实,江湖上称那五位师兄弟为五色道士,武林中只要一提起五色道士,莫不畏他们的五色剑法,恐有怪异。
其实五色道士脸色虽怪,行径却是正大光明,江湖上不少恶徒强盗,死在五色剑下。
但因五色剑法太过厉害,凡是十恶不赦的歹徒,碰到五色道士,无一能够逃得性命,传到后来,江湖上都以为五色剑法,果真是诡异无比,凡是与其为敌者,无不丧命。
公孙兰心中也怕那五色剑法,未斗之前,先已胆怯,迟疑甚久,不敢轻易下手攻击。
忽听山上传下一声长啸,啸声如龙长吟,久久不断,而且越来越是高亢,好像在招唤人似的。
过一会儿,又有一啸声在远处响起,回答先前啸声的招唤,公孙兰听出后来啸声是父亲所发,心中一急,一剑急快刺去。
虽是一剑,却分五个方位刺出,五色道士剑花轻挽,一一拦过,公孙兰急欲知道山上的变故,志在速战速决,剑不收回,手腕随着腰力,圈起一个大剑花,击向五色道士,要想把那五把色剑击落。
她却不知五色道士何等功力,凭她剑不收、不接新力的剑势哪能圈住五色道士的宝剑,反因力道不够,差点被对方扯落宝剑。
公孙兰大惊之下,一记绝招,滑出五色道士的剑力范围,若是稍慢一点,这一招便要败了。
她这一刺一击,攻入五色道士的剑阵中,但见五把宝剑布成五种颜色的光幕,罩住公孙兰全身,稍一不慎,便要遭害。
公孙兰已知功力不如五色道士,不敢硬拼,仅以高妙的剑法,一一拆解。
数十招后,公孙兰摸熟五色剑法的攻势,心想:不过如此,当下一变剑法,由守势转成攻势,她守势放轻,着重在攻势方面,顿时剑光如匹白练,飞快缠向五色道士。
五色道士剑阵不变,仿佛并不把公孙兰的攻势放在眼里。
公孙兰用尽各种凌厉的攻势,转眼一百多招过去,依然攻不出五色道士的剑阵外,这时公孙兰才了解到五色剑法的厉害,原来这五色剑法的守势,五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只要敌人一落入剑阵中,他五人不撤阵,敌人便不能逃出,直缠得敌人失却勇气,一个疏神,便要受害。
要知公孙兰的剑法非比寻常,要论个人独斗,五色道士没有一个是她的对手。她心中一定明白,急也逃不出剑阵外,不如从容应付,她心念一定,剑法挥洒自如,毫不费力,五色道士要想缠败她,却也不能。
五色道士一面和公孙兰游斗,一面暗中注视十丈外的阮伟,由阮伟的眼神及他说话露出的气功,五色道士心中害怕阮伟冲来,阻挡不住,被他闯上山去。
看看对方斗了两百余招,五色道士见阮伟牵马走来,心中一急,互相低啸一声,剑法一紧,飞快转动起来。
他五人这一转动,才现出五色剑法的真正厉害,公孙兰身在其中,即刻便被五把快剑交互穿插带起的彩色剑芒,迷乱了眼神。
这五柄剑所以有色,有它的作用,原来五剑在五色剑法的配合下,一快攻起来,幻成的奇异彩色,可以使敌人产生错觉。
公孙兰慢慢已不能确定敌人的位置,有时根本看不到敌人,五个道士已变成数十个。
这样一来,看不到敌人,公孙兰等于盲目使剑,她剑法再高也不是对手了。
二十招不到,公孙兰惊险万分,五色道士只要一狠心,公孙兰的性命便要不保。
五色道士一快攻,全神贯注在剑上,忘了再去监视阮伟的行动。
突听蹄声急响,五色道士心神一惊,剑法稍稍一慢,阮伟骑着“白蹄马”如飞袭到,手中飞龙剑圈身一转,闪电刺去。五色道士各各觉得剑风刺腕,他五人是剑术行家,知道剑一刺实,便要断腕。
五人大惊之下,尽力举剑挡去,立时“”数声,皆感到手臂酸麻,差点要丢剑,五色道士关心宝剑,一齐举剑细察。
顿时“白蹄马”飞快掠过五色道士身前,阮伟眼明手快,一把抱起公孙兰。
等五色道士看到剑上各各缺了米粒大的口子,悲痛的抬起头来,“白蹄马”已走出十余丈。
五色道士坚守岗位,不敢轻易迫赶,眼看阮伟左手举剑,右手抱着公孙兰,那高举之剑在阳光下闪闪生出金色光芒。
五色道上不由齐声大呼道:“啊!是飞龙剑!”
那“白蹄马”确实不凡,虽在狭窄的山道上,仍能奔驰如飞,毫不胆怯,不多时便奔上看龙山顶。
阮伟放下公孙兰,公孙兰对他甜蜜一笑,这一笑道尽心中的感激情意。阮伟不识方向,让公孙兰带着自己,策马飞驰。
这看龙山顶范围广大,并无山尖,山顶的面积小不了山底多少,故而攀登甚难,但若登上山顶,风景十分优美,湖泊丛林处处皆是。
“白蹄马”奔到一处丛林,这丛林很大很密,日光不易照进,奔了盏茶时间,越入越深,不辨东西南北。
再走一刻,只见树木长在湖泊中,一眼看去,水中插满林木,看不见路在何处。
公孙兰轻唤阮伟下马,将马丢下,任它在林中寻食,阮伟走时依依不舍,连连轻抚它的长颈,低声道:“白蹄马!白蹄马!乖乖在这里玩,等我回来知道吗?”
“白蹄马”甚有灵性,长颈直推阮伟,仿佛在说,“主人去吧!我知道啦!”
公孙兰带着阮伟从水中踏去,原来离水寸许处,暗埋木桩,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两人竟能踏水而行呢!
木桩因水中林木的关系,钉得曲曲折折,若是不会武功的人要从桩上走过,真要睁着大眼,看准木桩的所在,才敢下足。
但他两人如覆平地,不一会,重又走到陆地上,行了一刻,阮伟觉得地势渐高,好像在登一座坡度甚陡的山头。
渐渐阳光明亮,就要走出丛林了,哪知走到林边,才发觉仅是走到丛林的中央空地。
那空地面积甚广,有小湖,有花草,并有人工栽培的树木及亭舍建筑。
公孙兰飞快奔到她爹爹居住的精舍内,找了一遍,没有看到“飞龙剑客”的踪影,阮伟跟在她身后,被这小小的世外桃源惊呆住了,一面行走,一面心中不住赞赏。
这时看到此地盖有一栋精美的木屋,心下大是羡慕那屋主享尽清福。公孙兰找不到爹爹,急向他道:“我们到观象台去找爹爹!”
走过几排树行,已可看到前面的地势高处,有一平台,平台一侧高筑一亭,亭内坐着四位老者,两位是星目羽衣的自髯老者,和另一位鹑衣百给的中年乞丐坐在一侧,另一侧是一蓝袍老者,脸部轮廓与公孙兰十分相像,一看便知是公孙兰的爹爹了。
蓝袍老者面向公孙兰的来路,公孙兰看到爹爹正要大声唤叫。忽见爹爹微微摇首,公孙兰就知爹爹不要自己上去打扰他,便拉着阮伟坐在山坡的草地上。
忽然上面话声传下,一位坐着比其他三人高出一头的白髯老道苍声道:“公孙施主,二十一年前那段血债,该当如何?”
公孙求剑道:“武当掌门千里远来,公孙求剑尽地主之谊,且请饮盏香茶,当年的仇怨,慢慢再谈如何?”
另一位白髯老道,红光满面,暴声道:“公孙老儿,我大师兄含恨泉下二十一年,哪有时间和你消遣,元智恨不得马上取你性命,替大师兄报那杀身之仇!”
公孙求剑笑道:“曾闻武当元字辈中,元智性格粗放,闻名不如见面,今日一见,果真不错。”
元智怒道:“你可是讽刺贫道修养不够吗?”
公孙求剑道:“求剑不敢!”
元智冷笑道:“贫道纵然修养不够,总比那盗剑杀人的贼子要好得多!”
公孙求剑变颜道:“阁下骂谁?”
元智霍然站起身来,大声道:“贫道骂的就是你!”
元智神情激动,大有一言不合、马上拳脚相见之势。
武当掌门站起身来,高出元智一个头以上,他手轻按在元智肩上,慈颜道:“师弟坐下。”
元智不敢违抗掌门命令,忍着气静静坐下。
武当掌门走到中年乞丐身前一揖,中年乞丐慌忙站起,公孙求剑不识中年乞丐,不知武当掌门怎会对他如此恭敬?
但听武当掌门道:“今日有劳丐帮帮主,为双方评个是非曲直。”
中年乞丐道:“元清道长请坐。”
武当掌门元清坐下后,中年乞丐向着公孙求剑抱拳道。
“在下丐帮第二十一代帮主高瘦蒲,久仰公孙大侠,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公孙求剑起立回礼道:“原来是侠义可见的丐帮帮主,能请到帮主做公证人,求剑敢不从命。”
高瘦蒲笑道:“瘦蒲能得两方信任,感激莫名,在下洗耳恭听,还请双方捐弃前嫌是最好的了。”
元清道:“公孙施主,二十一年前施主谐同公孙夫人来武当山,重伤本派前任掌门师兄元明一事,施主可承认吗?”
公孙求剑道:“求剑失手伤人,迄今思来,犹愧于心!”
元智怒吼道:“你当然惭愧啦!你乘武当山无人,合二人之力杀害大师兄,就是临死,你也要内心不安……”
元清摆手阻止元智,叹道:“施主可知家师兄因那一剑重创,第二日便伤重而死了吗?”
公孙求剑想到往事,含泪点头,承认已知当年之事。
元清颔首道:“那就好说了,杀人者死,高帮主请评个理罢!”
高瘦蒲道:“不知公孙大侠对这件事,作何解释?”
公孙求剑用袖拭泪,好半晌,才道:“当年求剑确实不该伤害元明道长,以致伤重而死!”
元智突然鸣咽道:“杀人抵命,公孙老儿,你要是个汉子,就该自刎谢罪!”
公孙求剑苦笑道:“求剑若是偿还元明道长一命,那谁来偿还贤内一命?你们武当山哪一个可以抵她的命?”
说到后来,公孙求剑竟然声色俱厉,显是十分悲痛。
元清惊道:“公孙夫人已去世了吗?”
公孙求剑大叹道:“去世了!去世了!已去世将近二十一年了!”
高瘦蒲道:“久闻公孙夫人‘追命女侠’芮镜花武功了得,一手‘追命刀’闻名武林,不知是如何去世的?”
公孙求剑老泪纵横道:“贤内的死因,与元明道长相同,是死在他那致命一剑之下……”
元清、元智同时惊道:“我师兄当真重创‘追命女侠’?”
公孙求剑悲怒道:“怎么不是!难道求剑凭空捏造事实吗?当年若非元明道长先刺贤内一剑,求剑怎会刺他一剑?”
元清不服道:“大师兄为护剑而战,才失手伤了追命女侠,怎能怪得了大师兄!”
公孙求剑思起妻子死亡,就悲痛万分,大怒道:“怎怪不得他,二十年来求剑没有向武当山素命追仇已是好的了,想不到今日反被你们欺上门来!”
元清缓和道:“但是二十一年前,公孙施主上武当山为的何事?”
元智急遽道:“你要是正当上山,我大师兄怎会伤了‘追命女侠’?”
公孙求剑悲愤道:“这样说来,贤内是该死的了!”
元智冷笑道:“只怪堂堂一位大侠,心怀不正的结果。”
他这一句话激怒公孙求剑,霍然站起,元智不甘示弱,跟着站起,两相对峙,大有马上动手之意。
高瘦蒲忽道:“两位请坐下。”
公孙求剑、元智见公证人说话,不能输了一个“理”字,又默默入座。
高瘦蒲正色道:“可否请公孙大侠将二十一年前之情况一叙。以便在下了解!”
公孙求剑点点头,大叹道:“二十一年前,求剑确是心怀不正,夜上武当山……”
元智大笑道:“你倒是承认了!“
公孙求剑怒道:“阁下可是手痒,一定要动手才能心安?”
元清道:“师弟不要插口,听公孙施主慢慢道来,当日之事你我不在现场,孰是孰非,还请高帮主评正。”
这一番话,表现出名侠的风度,高瘦蒲听得暗暗赞佩。元智天不怕地不怕,却不敢违背掌门师兄的命令,住口不语。
停了一下,公孙求剑续道:“求剑一生好剑如命,天下名剑未曾一一见过,那年闻听武当山得到一套五色剑,其中还伴着一柄母剑,五剑倒还罢了,求剑却被那柄母剑吸引住了,心想去见识一下,以满足求剑好剑之癖性。
“但一经打听,已有甚多人上山求取五色剑一阅,都未得到武当允许,求剑暗道:五色剑都不得一见,那母剑更不要谈了。
“果然二十一年前那天白日,偕同贤内拜山求赐一阅,不得武当山允许,内心甚是不悦,心道:那套剑既不是武当山代代相传之宝,不过是无意中寻得,为何不准别人观赏!”
元清叹道:“那五色剑上刻着五色剑谱,大师兄怕江湖得知觊觎而起争夺之心,故而绝不让外人借阅,岂知因此惹下不少仇家!”
元智忍不住道:“再说那套剑并非无意得来的,早在二百年前便是武当之宝,先辈埋藏地下,二十二年前才发现而已。”
公孙求剑听元清、元智说完,才又道:“只怪求剑一生好剑太甚,那时终日不乐,贤内见我不悦,便提议晚上盗回来,好好看它三日三夜,再送还武当山。
“求剑心想,武当山不给面子,只有盗它回来看看再说,那天晚上便与贤内连袂上山,哪知为了一己私欲,竟害得贤内丧失性命。二十年来,求剑无一日不为当年之事,深悔于心。那天晚上,武当山虽然守备森严,却被我夫妇俩轻而易举闯进藏珍阁,那藏珍阁十分广大,当下两人分头寻找,求剑去找的方向尽是经典,毫无所见,却被贤内找着了,贤内正拿着那把珍贵无比的母剑,忽然惊动守剑的武当掌门元明道长……”
元清道:“这守剑之责是我师兄弟三人轮流看守,那天贫道与师弟元智出外办事,只剩前任掌门师兄一人。”
公孙求剑苦笑道:“那天纵然你们师兄弟三人全在,既是刺伤贤内一剑,求剑就是拼命也要在你们三人身上各刺一剑!
“贤内本不会被元明道长一剑刺伤,只因寻到母剑后,高兴之下,没有防范,到元明道长暗中一剑刺来,伤中要害!”
元清道:“第二日贫道与元智回山,师兄已在弥留状态,但他临去世时,曾说到了为护剑伤害一人,却未说出是谁,仅呼出公孙两字便溘然长逝,尔后打听才知是施主夫妇二人,倘若家师兄真是刺了‘追命女侠’一剑,想来他并不知‘追命女侠’得到母剑,竟不会还手!”
公孙求剑流泪道:“求剑陡闻贤内一声惨呼,五内如焚,飞快冲去,但见元明持剑呆立,贤内已倒卧血泊之中,急怒之下,我奋力一剑刺去,哪知元明道长应剑而倒,那一剑,求剑迄今思来,犹愧于心,我实在不知元明道长不会抵挡。
“当下我抱起贤内飞掠而去,到了山下旅店中,只见贤内虽已昏迷,却仍紧握着那把母剑。
“我救醒她之后,她第一件事不是顾自己的伤势,却是把那剑含笑递到我手中,仿佛只要为我达到目的,天下任何事都不重要了!尔后数月,求剑千辛万苦费尽人力,求得灵丹,才止住贤内的伤势,但那一剑伤到肺腑,已非药物所能治疗,她还是怀孕之身,当生下爱女时,触动旧创,便吐血而亡!”
公孙求剑说到此处,那么有名望的人物,竟如婴儿一般呜咽哭起,哭声悲切,听得元智都忍不住唉声低叹!
坡上阮伟在回忆往事,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听到公孙求剑的哭声倒不怎样,但公孙兰早已成了个泪人儿.因她直到此时才知母亲的死因。
公孙求剑尽情哭了一阵,才又道:“而后我也得知元明道长第二日去世,怪不得人家,在伤心之下,抱着爱女,远来此处,养心韬晦,二十年来未曾至中原一步,哪知今日武当掌门亲来此地,重提当年旧事,孰是孰非,求剑任凭高帮主裁决!”
元清低念一声“无量寿佛”后,道:“师兄未说明当日情况便惊鹤西天,武当山久经打听知道公孙施主隐居此地,为遵先辈遗命,新任掌门二十年已届,才率师弟来到此地,既已了解当日情况,武当山也不是不讲理之人,愿遵高帮主裁夺。”
高瘦蒲沉思一会道:“当年之事,两方那一剑都不知对方无心还手,这段仇怨既已造成两人死亡,事隔二十一年了,以在下之见,双方不如和好,捐弃前仇。”
公孙求剑叹道:“事情早已过去了,武当掌门若无意见,求剑不作他词。”
元清道:“想大师兄那一剑刺去,心中十分懊悔,才会忘了抵挡公孙施主那一剑,师兄英灵有知也不愿再事寻仇,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贫道甘愿接受高帮主的调解。”
高瘦蒲笑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在下有此荣幸能够为双方调解,实为生平一大乐事,愿把盏三杯,以示祝贺。”
公孙求剑道:“高帮主若要喝酒,求剑备有上等好酒,埋藏地下十余年了,待会吩咐下人在客室奉上。”
高瘦蒲大笑道:“瘦蒲平生好酒,正如公孙大侠平生好剑,有此好酒,瘦蒲倒要叨扰了,不知元清道长可有兴致否?”
元清笑道:“贫道数十年未沾滴酒,高帮主有此兴致,不妨多留几日,贫道与师弟就要告辞!”
元智突道:“仇恨既然已解,那柄剑应该还我们了罢?”
公孙求剑蹩眉道:“什么剑?”
元智冷笑道:“施主窃占武当之宝——飞龙剑,仗以成名,难道会忘了吗?”
元清低叹道:“‘追命女侠’拿去那把母剑,确非敝派无意中得来,二百年前已是武当掌门信物,敬请公孙施主赐还!”
公孙求剑脸色不悦道:“贤内为此剑丧命,求剑睹剑如见人,这剑凭何种理由,亦非武当之物!”
元智怒声道:“不是武当之物,难道是阁下之物?阁下仗剑不到一年成名江湖,还想再次下山,仗剑扬威吗?”
公孙求剑忍住气道:“求剑二十年不用剑了,早忘了‘用剑’两字,飞龙剑确不是求剑之物,求剑根本不应该窃占它。”
元清缓和道:“那请施主归还武当,贫道感激不尽!”
公孙求剑一字一字地道:“那也非武当之物!”
元智一怒立起,大声道:“飞龙剑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丐帮帮主眼见一场仇怨已成过眼云烟,想不到争端又起,当下沉痛道:“承蒙武当掌门看得起高某,在西藏途中邀来此地,高某但愿两方平安和事,若有不解之事,请元智道长坐下慢慢商谈!”
元智却不过高帮主的面子,愤愤坐下。
公孙求剑平和道:“二十年前贤内去世时,求剑发誓不再用剑,以慰亡妻之魂,‘飞龙剑’是贤内用性命换来之物,自应归贤内所有!”
元智急道:“你把那剑怎么了?”
元清道:“‘飞龙剑’因故失传二百年,既已重获,就是武当的掌门信物,不可外失,万请看在武林道义份上,祈请赐还!”
公孙求剑心中很佩服元清的修养功夫,不愧武当掌门,见他祈求,一时颇感为难,道:“爱女酷似亡妻,求剑已将飞龙剑送给爱女,就等于归还亡妻,飞龙剑已不属求剑所有,自是不能作主。”
元清道:“施主可否劝请令爱赐还?”
公孙求剑摇头道:“‘飞龙剑’已成爱女性命之物,若无他故,爱女绝不会放手。”
元智冷笑道:“你怎知她不肯放手,莫非是你自己不肯放手?”
公孙求剑深恶元智的为人,不由微怒道:“凭道长狂傲的性格,飞龙剑就是在求剑手中,也不会给你!”
元智大怒道:“要怎样才给?”
公孙求剑冷笑道:“道长有本事尽管放肆施为!”
元智大声道:“你的意思,贫道胜了,剑便属于武当?”
公孙求剑冷笑不语,显是不答应给剑。
元智又道:“贫道来时,便知阁下无心还剑,当年阁下以二人之力夺得飞龙剑,今日贫道与师兄也以二人之力夺回!”
公孙求剑不信武当竟会以二敌一,落人笑柄,向元清道:“他说的可是真话?”
主元清心知公孙求剑武功非同小可,而飞龙剑是武当必得之物,当下只有硬着头皮点点头。
元智冷冷道:“以二敌一,高帮主不会介意罢?”
高瘦蒲道:“既是当年公孙大侠夫妇两人上山夺剑,现今贵派再次夺回,高某自是没有话说。”
元智狂笑道:“此山已被贫道门下五色剑法封住,虫蚁难过,莫说是人了,公孙老儿,今天你只有一人抵挡了。”
言下甚为得意,满以为五色剑法守关,天下无人能过。
高瘦蒲缓缓道:“道长之言,却不见得!山坡上早已来了两人。”
元智不信道:“谁来得了?”
公孙兰牵着阮伟,飞身掠上,娇声道:“公孙兰就来得了!”
元智大惊失色,脸上尴尬万分。
公孙求剑暗佩高瘦蒲的听力,连元清也不禁耸然动客,因他也未听出山坡上已来两人。
元智老着脸道:“一定是公孙老儿的女儿!”
公孙兰转头望他,不闻不理,一副不屑神色!
元智恼羞成怒道:“你可听到贫道说话?”
公孙兰傲然道:“姑娘向不理对家父无礼之人。”
她这种回话,阮伟听得有趣,不禁微微一笑。
元清道:“尚请姑娘将飞龙剑归还武当。”
公孙兰笑向无清道:“这是家母遗物,怎能归还武当?”
元智怒吼道:“你刚才没有听我们说话吗?”
公孙兰根本不望元智,向阮伟道:“我的耳朵可是好的?”
阮伟笑道:“大姐的听力一向是很好。”
公孙兰白了阮伟一眼,好像不高兴阮伟喊她大姐。
元智被气得七窍生烟,愤怒道:“丫头,你要怎样才还飞龙剑?”
公孙兰霍然生威道:“家母以一命换得飞龙剑,臭老道要剑就拿命来换!”
公孙求剑十分疼爱独生爱女,但见她骂到元清道长,慈声道:“兰儿,不要无礼!”
公孙兰唤声“爹”!扑到父亲的怀内,娇声道:“爹!他们好不要脸,想要两个打一个。”
公孙求剑拍拍她肩膀道:“兰儿听话,到一旁去,让爹来处理此事。”
元智本想硬从公孙兰身上夺下剑,但见她所背之剑,并非飞龙剑的样式,急怒道:“丫头,飞龙剑到底在哪里?”
公孙兰气他道:“你管不着。”
元智大吼道:“若不交出,莫怪贫道无礼!”
公孙求剑不悦道:“你先向求剑招呼,如赢得求剑,再向爱女讨剑;否则,还请乖乖下山去吧!”
元智道声“好”!拔剑出鞘,招呼元清道:“师兄,我们上!”
元清见势,只有硬夺,乃向高瘦蒲稽首道,
“贫道有负高帮主的厚望。”说罢,拔剑而出。
高瘦蒲长声一叹,争斗在所难免,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自己调解不成,心中似是大为难过!
元清与元智持剑走出亭宇,来到平台中央,并肩而立。
阮伟从平台退到一侧,公孙兰也偕同公孙求剑走下亭字,高瘦蒲也摇着头跟了出来。
公孙求剑吩咐公孙兰站到一侧,公孙兰相信其父之能,但仍依依不舍的退到阮伟身旁。
公孙求剑缓步走到元清两人身前一丈,定身站住。
元清道:“请公孙施主拔剑,贫道师兄要领教了。”。
公孙求剑道:“求剑早已说过,发誓不再用剑,何来拔剑?”
元智怒声道:“你不用剑,怎么斗法!”
公孙求剑微笑道:
剑是何物,无剑即是有剑,有剑等于无剑,求剑双手便是双剑。”
阮伟忽然大声道:“何谓无剑即是有剑,有剑等于无剑?”
公孙求剑望了阮伟身背之剑一眼,大笑道:“技艺不娴熟,持剑若持废物:技艺娴熟,何物不可当剑?”
阮伟道:“这等说来,只要是物,皆可为剑?”
元智狂笑道:“阁下真是不用剑?”
公孙求剑微笑不语。
元清道:“施主悟得最高的用剑之道,尚请手下留情。”
说罢脚踏丁字,凝神持剑,如临大敌。
元智暗怪师兄灭了自己的威风,哪有未斗之前,便请手下留情,气愤之下,一剑迅快刺出。
公孙求剑身形不动,左掌突起,骈指如剑,轻轻一拍,拍在元智剑上,元智陡觉剑上传来一阵潜力,大惊之下,翻腕削去。
其变招之快已甚惊人,然则公孙求剑手中无剑,变招更快,“啪”的一掌,又拍在元智剑上。
元智倏然抽剑,突又向对方胸口疾刺。
公孙求剑反应更快,手掌如剑刺出,后发先到,“啪”的一掌,拍在元智剑底,剑身一歪,元智一剑刺空。
公孙求剑顺势滑下,刺向元智腹部。
元智晓得让他手指刺中,必然如剑穿腹,左掌急忙拍出,挡住那剑势,身形飞快后掠。
公孙求剑未刺到元智的腹部,却刺到他的掌心上。
元智但觉掌心一阵剧痛,举手一看,左掌已被公孙求剑中指刺穿一个孔,其利如剑一般。
这时,元智才知他那无剑胜似有剑之言不虚,心下惊骇不已。
元清沉声道:“师弟无妨吗?”
元智咬牙道:“无妨!”
这下,他不敢再大意,脚踏丁字,用起玄门正宗剑法。
公孙求剑面对两大武林高手,更不敢大意,神态凝重,但他双目却不望着敌人,垂眼低望,如观鼻心。
武当剑法本是以静制动,却见公孙求剑那样子,绝不会先攻,
当下两人暗道,自己有剑,怕他做什么?
两人心意一通,霍然举剑,交互挥出。
武当“飞龙剑法”以轻灵见重,元清、元智皆有数十年人候,轻灵之处更加稳重,剑剑刺出,风声飒飒。
公孙求剑既言双手便是双剑,自有惊人之处,数十招下来,他那两掌尽量不与真剑正面相碰,攻势凌厉之下偶然相碰,却能够即时借力使力带剑而过。
百招以后,丐帮帮主暗叹公孙求剑的剑法已然神通,时间一长,元清、元智绝非敌手。
忽见山坡上走来几个白衣仆人,公孙兰轻声道:“爹要施展神威了。”
阮伟正看得目驰神摇,见到白衣仆人,问道:“他们来做什么?”
公孙兰笑道:“不要多问,仔细看着。”
那几个白衣仆人排列坐下,各从怀中掏出古形乐器,只见他们并不管场上主人的拼斗,悠闲的吹奏起来。
那乐声一听竟是唐朝时代的一种古典舞乐,名叫桑林,混合着尧那时的一种音乐,名叫经首。
这混合乐声乍经奏出,但见公孙求剑忽然神态十分洒脱,脚下的步法,和桑林的音节配合,手上的剑法和经首的节奏相合,如此一来,步法配合着剑法,妙到极顶,仿佛公孙求剑闭着眼睛也可以打败元清、元智。
不数招,元清的剑法已显然杂乱,元智早已乱不成章,危殆万分。
阮伟记忆丧失大半,脑筋空白,却对这种高深武学领悟甚强,剑法是他所长,看到后来,他不由大叫道:“好个无剑即是有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