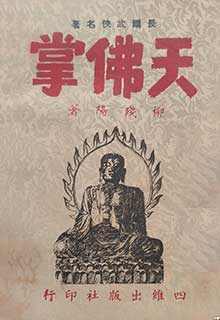孙垂玉的面孔扬起,两腿叉开,事到如今,他仍还没有忘记先摆出一副“泰山石敢当”的傲态,败军之将,大概也只能拿这一点虚无的尊严来告慰自己了。
靳百器目光炯亮的注视着孙垂玉,声音放得极低,但却非常清楚:“请告诉我们,‘大龙会’的头子赵若予如今人在何处?”
喉结上下移动了一会,孙垂玉显得有些吃力的道:“在‘血魂山’……”
怔窒了半晌,靳百器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血魂山’?你是说,赵若予人在‘血魂山’?”
孙垂玉不高兴的道:“我是这样说的,前些日临别之前,老赵曾当面向我哥俩提过,他要移师到‘血魂山’,至于是不是真的去那里,就看老赵本人说话实不实在了,我乃照本宣科,却无从查证!”
靳百器谨慎的道:“孙垂玉,‘血魂山’的范围很大,姓赵的曾否说过他们要去‘血魂山’的什么所在?”
孙垂玉道:“还会有什么所在?当然就是你们原来的寨子,‘鹰堡’的老窝!”
与对面的端木英秀交换了一个眼神,靳百器努力摒除情绪上的反应,专注的道:“‘鹰堡’早已付之一炬,被烧得七零八落,他们重回该地,面临的只是一片废墟,莫不成其中尚另有计较?”
孙垂玉面色僵硬的道:“堡子是人盖的,烧了还可以重新再起,老赵有钱有人,何愁不能恢愎旧貌?至于他们为何弃置自己的基业,欲跑到‘血魂山’一座废寨去另起炉灶,据岑玉龙说,主要为的是战防观点,他说‘血魂山’‘鹰堡’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同‘栖凤坡’这边的堂口过于参差暴露,据守维艰,另外,这样的转移亦可收至飘忽无常、出人意表之妙……”
靳百器喃喃的道:“不错,赵若予玩的这一手,确然是出人意表——”
“跟姓赵的在一起的约模尚有多少人?”
想了想,孙垂玉道:“四百多五百人吧,本来人数还会更多,只是这段日子来和贵帮口杀来杀去,折损了不少,里外里就都缩了水啦。”
靳百器接过来道:“跟在赵若予身边的,都是哪些人,我是指有份量的角色而言。”
孙垂玉一面计算,一面慢吞吞的道:“有‘大龙会’的二龙头史道全、总管司事岑玉龙、右司事陈翔、‘四龙卫’之一鹿佩文、以及二名把头,另加刑堂的大掌法勾顺德,带着一名‘先斩手’,大概就是这么些了。”
端木英秀又冒出了一句:“‘大龙会’能上盘的角儿就这几个?”
孙垂玉半侧过脸道:“原是不止,其余的除开留守堂口的田宝贵及童少安,都死净了……”
靳百器紧接着问:“不久之前,我们曾有一支人马远赴‘近安城’对‘大龙会’盘据的几个点实施狙袭,但这支人马一去以后,就再无消息,孙垂玉,你知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孙垂玉不假思索的道:“你说的那支人马,领队的可是姓孟?身份好像是你们‘鹰堡’的什么总提调——”
心腔子猛收缩起来,靳百器噪哑的道:“不错,负责指挥那次行动的人,正是我方总提调孟君冠,孙垂玉,请告诉我,他们是否出了纰漏?”
孙垂玉点头道:“纰漏当然是出了,要不怎么会讯息全无?但纰漏不是他们捅的,乃是‘大龙会’事先安排下陷阱,人马早已布妥,姓孟的那二十来个人不辨风色、晕天黑桶一头冲将进去,如何还有侥幸之理?听说不到半个时辰,就已全军尽没了!”
靳百器生涩的道:“你是说,我的人全战死了?”
孙垂玉的眼睛,在夜暗里泛着一抹亮光:“似乎并没有完全折损,那姓孟的伤重被俘,另外被俘的,像是还有个姓胡的,其余的就一个不剩,通通挺尸啦……”
靳百器急切的道:“孟君冠和胡甲还活着,你能确定?”
孙垂玉道:“我是听‘大龙会’的人这么说,能否确定,我不敢担保,但是,‘大龙会’的人该不会故意在我面前扯淡,他们骗我干什么?”
靳百器忙道:“这两个人现在何处?”
摊摊手,孙垂玉道:“他们人在哪里,我就不清楚了,事不关己,我当时哪有兴趣去打听这些零碎?”
靳百器闻言之下,不觉有了怒意:“孙垂玉,这不是些零碎,尤其对‘鹰堡’的兄弟而言,意义更为重大!”
叹了口气,孙垂玉道:“我只是直话直说,你也犯不着发火,如果早知道有今天这道关口搁着,又何妨顺势多问几句?至少眼下亦讨你个欢喜,不过你不用急,依我看,他两个一时半时,还不至有性命之危……”
靳百器道:“怎么讲?”
孙垂玉道:“理由很简单,假如老赵不想留他们的活口,当场就不令干掉了,还俘虏他们做什?更亦不会留到事后另耗精神啦!”
靳百器咬牙道:“‘近安城’设下的陷阱,是哪一个参予主事的?”
孙垂玉道:“史道全史老二,而且,从头至尾,‘大龙会’的人就只有他一个在现场。”
靳百器神情萧索的道:“你的意思是‘近安城’那一仗,‘大龙会’用的是庸兵,本身并未加入厮杀?”
孙垂玉道:“对了,甚至连到场监战的史道全都没露面,他只是负责督导协调,隔山观虎斗而已,实际动手的乃另外一批伙计!”
靳百器沉住气问:“哪一批伙计?”
孙垂玉似是豁开了,毫不迟疑的道:“你听过‘西河大坝’的‘黑巾党’?就是他们那一伙熊人!”
靳百器冷冷的道:“‘西河大坝’‘黑巾党’活动的范围从来不出坝区左近那一亩三分地,他们不侵犯人家,亦不容人家入侵地盘之内,算是相当守得住原则的一帮人,如今却甘愿为虎作伥,替‘大龙会’当打手,莫非又是赵若予拿银子买通的?”
孙垂玉表情尴尬道:“这也无可厚非,有钱可使鬼推磨,老古人都这样说的嘛……”
靳百器阴沉的道:“赵若予不但心肠狠、犹且看得透人性的弱点,了解物欲的诱惑力,将金钱的运用之妙发挥到了极致——一个人能够拿钱来买别人的命了,财富在他手上就不止财富,其利其锐,更同锋刃……”
耸耸肩,孙垂玉道:“金子银子总是好的,人生一世,时时刻刻缺不了这玩意。”
靳百器僵硬的道:“还有一件事,孙垂玉,庄婕这个女人,你一定不会陌生吧?”
孙垂玉颔首道:“认得,还见过几面,说是你们‘鹰堡’瓢把子的原来压寨夫人。”
靳百器懒得再去纠正对方的遣词用句,只低缓的道:“她如今是否也和赵若予在一起?”
舐舐嘴唇,孙垂玉道:“这倒没听说,但依我的看法,恐怕十有八成他们搅合在一起。”
靳百器道:“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孙垂玉坦白的道:“我这个人虽然粗浑了点,好歹也活了几十年,看人看事不敢说入木三分,大概是个什么光景多少亦离不了谱,他们两个的模样,瞧着就有些夹缠不清,尽管表面上他们装得规规矩矩,暗底下却眉来眼去,搓搓捏捏,显见关系不同一般,而我们都知道,那姓庄的娘们原本是有主的,原主和老赵是不共戴天的血仇……”
靳百器道:“听你的说词,好像也不以为然?”
孙垂玉又叹了口气:“老实讲,人与人之间,因为立场的迥异、利害的冲突,渊源的牵引,常有敌对的情形发生,谁有理,谁无理,往往各执一词,且不去说它,可是这伦常纲纪却永远只有一个定规,那是决不会混淆改变的,无论你是好人也摆、坏人也罢,无论你站在哪一条阵线,这伦理就是伦理,却不作兴叫一个婆娘去和杀夫的仇家不干不净……”
靳百器沉沉的道:“你看到他们不干不净的事实了?”
孙垂玉正色道:“有些事,用不着亲眼目睹,光看某些迹象即可预知端倪,况且,我听到了不少闲言闲语,这全是由他们内部的人传出来的,无风不起浪,如果没有丝毫根据,何来谣传?为什么不曾有人说我老孙和那娘们有勾搭?”
靳百器手抚额角,显得虚乏的道:“最后一个问题,孙垂玉,小杰现在怎么样了?”
怔了怔,孙垂玉道:“谁是小杰?”
靳百器苦笑道:“小杰就是耿杰的小名,我们当家的独生子,我曾在破堡之夜携他突出重围,也为他做了栖身的安排,岂知仍不免被‘大龙会’查获劫走,据最后的消息指出,小杰已被带到他母亲身边——”
长长“哦”了一声,孙垂玉寻思着道:“不错,我看过那个小小子,约摸五六岁大,生得乖巧可爱,就只不大说话,这么小的年纪,脸上便似挂着一层愁苦,活像个小老头……”
靳百器心痛的道:“那是小杰,他,他已回到母亲身旁,难道仍然不觉快乐?”
孙垂玉鄙夷的道:“有这种娘,做儿子的但凡稍具心思,又如何快乐得起来?别看五六岁的小孩子,也分得清好歹是非了!”
靳百器形容悒惨的道:“孩子一直跟着他娘?”
孙垂玉道:“这还用说?其实不跟也不行,小小子到底还是小小子,凡事容不得他做主,那庄婕早已不在‘大龙会’的堂口内,孩子也一定跟她走了!”
靳百器喃喃的道:“可怜的小杰,都怪我照顾不力,却要孩子来受这等折腾……”
孙垂玉受到靳百器情绪的感染,一时之间,竟忘了敌我的分歧:“老靳,你也不必难过,孩子他娘虽然不是个东西,但对她自己的骨肉却十分疼爱,母子之情毫未疏减,不只她,老赵待那孩子亦出奇的好,要不是孩子的态度倔拒,看上去挺像一家子人哩……”
靳百器十分注意的道:“赵若予对小杰也很好?”
孙垂玉道:“我亲眼看到,若不是早知其中有这么一段曲折,还以为孩子是老赵生的,呃,有句话,叫什么‘视同己出’,就是这么一码事!”
沉默了片竭,靳百器道:“谢谢你,我没有问题了。”
孙垂玉尚不及回话,在他背后,端木英秀已接上口道:“你问完了?好,我还有个问题,得请教请教我们的孙朋友。”
听到端木英秀尚待再出“题目”,孙垂玉就不禁头皮发炸,他偏过面孔向后瞧,堆起一抹实在不像是笑的笑颜,腔调喑哑的道:“有话请说,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过呢,既蒙二位高抬贵手,刀下超生,尚请快马加鞭,直截了当的出题,我个人是没有关系,怕只怕我这位老伙计受伤太重,挺不住了……”
蹲在地下的袁小泉倒还活道,似乎亦还耳清目明,因为孙垂玉的话刚说到这里,他便及时如斯响应,发出一声塞痰般的呻吟。
端木英秀冷冷一笑,老藤杖虚虚作势,朝着袁小泉的头顶点了点:“你不用哼唧,给我好好窝在那里少出些怪声怪调,等问完了话,自会放你们上路!”
说着,他又转向孙垂玉:“我的问题很简单,姓孙的,先前你已报过跟在赵若予身边的都是哪些人了,然则那一干子人全是‘大龙会’自己的班底,我要问你的是,赵若予身边,除开他的班底外,有没有他在别处另请的帮手?”
孙垂玉想了一会,道:“我只听说他已派人兼程赶往西疆‘大哈班’盆地‘青玉朝’拜菩萨去了——”
顿了顿,又接着道:“至于骨子里是个什么拜法,却不大清楚……”
端木英秀目光投向靳百器,靳百器立刻扼要的将他与西疆“青玉庙”派来的“座前三使”那场厮杀经过讲述了一遍;端木英秀脸上表情木然,语气却带着滞重:“原来其中尚有这么一段纠葛,难怪‘大龙会’有此一举,那赵若予算得上是会利用形势、制造机运的能手,他八成是想拿这件事,挑起‘青玉庙’的公愤,从而翻云覆雨,借机得利——”
靳百器道:“前辈想亦知晓西疆‘哈班番妖’这干异种的来龙去脉?”
端木英秀点点头,看了孙垂玉一眼,却没有多说什么,靳百器会意,立时向孙垂玉拱了拱手,态度恳切的道:“多谢尊驾各般指点,令拜兄伤重在身,不宜耽搁过久,尚请自便。”
孙垂玉无精打采的道:“不要紧,早走晚走,反正都得走,‘大龙会’这里,是待不下去了,虽说形势逼人,并非有意出卖朋友,到底不是那么回子事——”
端木英秀冷漠的道:“二位也不是毫无所获,那一头得了银子,这一头保住性命,此等好事,又到哪里去找?你们应该满足了!”
孙垂玉苦笑一声,指了指仍还躺在地下的田宝贵,迟疑的道:“这一位,我们能不能带他一起走?”
靳百器断然相拒:“不能,此时此地,尊驾还是先求自保为要,身外之事,就无庸操心了!”
讪讪的扶起呻吟不绝的袁小泉,孙垂玉挪步之前,犹不忘回头朝着躺在那边的田宝贵提高嗓门招呼,尽管语声里充满了憾疚与无奈:“我说老田,人到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是我兄弟不想救你,实在是无力相助,万一你因而有了个长短,可不能怨我兄弟不帮忙,冤有头,债有主,谁要了你的命,你务必认清主儿啊……”
嘴里吆喝,腿也不闲着,孙垂玉搀扶着袁小泉,就这么一路发话一路走远。
从“栖凤坡”“大龙会”的垛子窑赶返“回雁坪”,田宝贵沿途上受的罪可大了,端木英秀和靳百器两个轮流讯问,交相印证,不管在马背上、林野间,甚至任何一处休息打尖的地方,他们找到机会就将得自孙垂玉处的消息加以反复套询,两个人都是老江湖,伺起话来不但技巧纯熟、言词尖利,逼供的花招更是又狠又辣,田宝贵只是血肉之躯,恁情他是铁铸的吧,被这么一折腾,就不溶也溶了;这位“四龙卫”之首便学了孙垂玉的样子,真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肚里的那些隐密全吐露了出来,端木英秀与靳百器背后检讨,倒和孙垂玉所说大同小异,差不了多少,由此可见,姓孙的并没有诓言欺瞒一本三皇五帝,该表的确已表过了。
心中存着惶恐,脑筋里再三忖度着自己的命运会如何,田宝贵同靳百器合乘一骑,几天来那样的惊惧便一直攫抓着他的形魂,鞍上的颠簸,不止是摇撼着他的躯体,尤其把他的精神都震晃得快崩溃了。
“回雁坪”已在不远,但是,田宝贵却永远看不到“回雁坪”,就在山前,由靳百器动手处决了他,尸体便就地挖坑掩埋—一这样做,靳百器虽感遗憾,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在他们目前的环境之下,留人或放人都有实际上的碍难,纵敌如同纵虎、囚敌则无异倍增累赘,灭口不算是一种好方法,但势态如此,亦就别无选择,用解嘲的话说,武林凶险,草莽风凄,姓田的出来道上厮混,原该有这个心理准备才对。
牟长山父子得到传报,早在石阶之前降阶相迎,彼此见面,不得寒暄,立时登楼密谈,沿途的仆仆风尘,权且化在那一杯热茶之中了。
专注的听完靳百器的述说,牟长山目光投向端木英秀,淡淡笑道:“秀老对于西疆‘大哈班盆地’那些个番妖,似乎相当在意?”
端木英秀啜了口茶,缓慢的道:“不止是在意,而且还十分戒惕,长山,你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不明白这些家伙的厉害,靳老弟经验过,你问问他,‘青玉庙’的来人,岂是轻忽得的?”
点点头,靳百器道:“这些所谓的‘大尊’,武功怪异,招术奇诡,和我们优越传统的技击之道完全不同,其凶悍暴戾之气,亦属罕见,确然不易相与,以我同那‘座前三使’铁氏兄弟的较手经验而言,真是打到筋疲力竭,肝肠寸断,虽说后来侥幸获胜,整个人也差不多虚脱了……”
牟长山道:“我也知道这拨子人妖怪诞难缠,却不知竟有这么个凶狠法,秀老,听你口气,莫非也曾经和他们冲突过?”
端木英秀枯乾的面庞上凝起一抹阴影,语调便显得更幽沉了:“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九江派’掌门人花雄为了庆祝立派三十年正日,特别请来西疆‘青玉庙’的一位‘首座大尊’为贵宾,花雄原来的意思,是想借此炫耀他交游广阔,缘至疆垂,不料这位来自边野的‘首座大尊’却不识抬举,非但言词放肆,行止乖张,更且目中无人,毫不知谦怀为何物,尤其三杯黄汤下肚,当场就拿话轻蔑起中土武林来,是我一时气不过,也顾不得花雄的面子,即席便和对方起了争执,争执的结果,自然就由文斗演变成武斗了……”
牟长山笑道:“素仰秀老涵养甚深,不沾烟火,怎么那一次也沉不住气啦?”
哼了一声,端木英秀道:“什么涵养甚深、不沾烟火?长山,你休要用这些虚言来拘我,凡事只在一个该为与不该为,该为之事,虽千万人吾往矣,否则,泰山便崩于前,又与我何干?维护中土武林的声誉,替千万同源争尊严,自属该为之事,当仁不让,我何须客气?”
牟长山忙道:“是,是,秀老之言有理,只不知下情如何?秀老英武无双,想必赢了?”
端木英秀有些悻悻然的表情:“也不知道那算不算是赢,双方打了三百多个回合,有来有往,到了最后都搞得疲累不堪,结局是那什么‘首座大尊’使剑在我衣袖上戳了个窟窿,我在他腿弯部位赏了一记老腾杖,这才叫大伙儿拉开一一”
一拍手,牟长山笑道:“衣袖上虽然戳开窟窿,却未伤及皮肉,秀老那一杖总归打得结实,痛在那王八蛋的身上,算起来,自属秀老占足上风。”
端木英秀却了无喜色,他严肃的道:“你也用不着往我这张老脸上贴金,是好是歹,我自己心里有数;靳老弟说得对,‘青山庙’那般人委实不易相与,功夫怪,招式奇,反应又特别灵敏,个个都有一身了不起的提纵术,假如他们受了赵若予的蛊惑,倾力而来和我们作对,长山,漏子可就大了!”
牟长山皱着眉道:“形势会坏到那步田地么,秀老?‘青玉庙’方面之所以替‘大龙会’帮场,着眼点全看在钱上,姓赵的想诱说‘青山庙’再出大力,得准备多少银子才够?他们有几个底帐是不错,但我怀疑他们是否有如此雄厚的资财?”
端木英秀冷冷的道:“人急上梁,狗急跳墙,设若‘大龙会’认为决战之日,非有‘青山庙’的助力不能致胜,他们想尽办法也会凑出银子,做孤注一掷!”
靳百器颔首道:“我同意端木前辈的见解,赵若予是个非常懂得利用金钱诱人卖命的主儿!”
牟长山也开始忧虑了,他凝重的道:“二位的结论如何?”
端木英秀瞪眼道:“什么结论?”
牟长山赶紧道:“依二位的看法,西疆‘青玉庙’的那干番妖,会不会大举而至?”
看了看靳百器,端木英秀喝了口茶,大概茶水不够热,他脸上的皮肉更绷紧了:“目前还很难说,靳老弟,你认为呢?”
靳百器沉吟着道:“赵若予既已派了专人兼程赶往西疆,决不会带条件空手而去,他所出的条件,就算不能使‘青山庙’那边完全满意,相信差距也不会离谱,因为姓赵的决不是一个脱离现实,寡情憧憬的人,他派出人去,便多少有几分把握,加上‘青山庙’‘座前三使’的毙命往事,更有可能勾起对方敌忾同仇的心绪,基于这种心绪影响,说不定宁肯降低要求,遣兵上阵——”
深深点头,端木英秀道:“分析得极有道理,长山,你刚才问到结论,现在已经有结论给你了!”
牟长山端起几上的茶杯,又心不在焉的放了回去,先前的开朗与乐观,显然也已消失无踪,他吸了口气,像在自言自语:“天操他的血亲,这档子事,莫不成还真个遇上难题了?”
端木英秀唇角泛起一丝几乎看不到的笑意,带三分捉狭的道:“长山,你素有‘黑大户’之称,大半辈子来顺当日子过惯了,如今你才知道,这江湖生涯,不似你想像中那样太平安稳吧?”
烦恼的敲了敲自家脑门,牟长山两眼大睁,恶狠狠的道:“他娘,我硬是不信就没有法子应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得有个计较才是,难道说‘青山庙’的人一现身,我们便成了缩头的王八?”
端木英秀板起面孔道:“任是哪一个都可以扮缩头的王八,我可决不做这种事,哪怕豁上这副臭皮囊,我也要与他们撑持到底,宁死不怨!”
牟长山大声道:“秀老,你别低看了我,你待同他们撑持到底,我就会敲退堂鼓不成?你豁得出去,莫非我就豁不出去?要是缩头缩尾,靳兄的麻烦,我早他娘不沾手了!”
端木英秀微笑道:“不须多做解释,长山,想想看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你用尽法子拖我下水,我当然相信你不会踏着我的脑袋脱身!”
牟长山咧开大嘴道:“还是你了解我,秀老。”
说到这里,他又似想起了什么,嗓门变粗了:“除开‘青玉庙’那些个番妖,秀老,方才靳兄还提到‘西河大坝’‘黑巾党’的一伙人也在帮着‘大龙会’撒野,不知道‘黑巾党’只是参予偶一行动抑或和‘大龙会’拧成了股?若是拧成了股,我们的阻力就又加大了!”
端木英秀道:“对于敌人实力的估算,我们宁可高估,切勿低估,有关‘黑巾党’的动向,我认为还是把他们算进‘大龙会’的阵营内比较适当;长山,江湖帮口的来往关系,变数极大,利害当前,便可万众一心,眼下,‘大龙会’和‘黑巾党’可不正朝这条路上走?”
“咯噔”咬牙,牟长山恨恨的道:“管他什么虾兵蟹将,邪魔鬼崇,我们拼了!”
端木英秀道:“原就是要拼的,长山,在知己知彼之后,还得拿出一套拼的办法来才行,徒逞匹夫之勇,固可一表个人格节,却与大局无补,我们求的乃是全盘胜算,不只为了争那高节义气。”
牟长山目光移注向靳百器,却见靳百器神色晦涩,面带重忧,双手紧握,怔怔的不知在寻思什么;他忍不住提高声音道:“靳兄,你怎么不说话?别犯愁,且把心胸放开,是好是歹,我们全与你甘苦与共,福祸同当,死活都在一起!”
凄楚的一笑,靳百器沉重的道:“就是为了二位的豪义,我才深觉心里的负荷太重,俗语说,唯生死可见交情,将来与敌决战,生死虽难预卜,但二位却已有此准备,‘鹰堡’何德,我又何能,竟使二位助之以力、悬之以命?人活百载,莫非虚空,单只领受这等恩义,便不枉来过一趟人世间了……”
牟长山忙欠身道:“靳兄言重,靳兄言重,这点小事,万勿挂怀,你再要客气,倒叫我和秀老难安啦……”
端木英秀也正色道:“我说过,凡事只在一个该为与不该为,该为之事,虽千万人吾往矣,以靳老弟你目前的遭遇和境况,拔刀相助乃义不容辞,否则,弱肉强食,横吞暴饮之风何得消弥?更休提此中牵扯的纲常及渊源了,江湖纷争,不管怎么纠缠,总也有个义理存在,我老眼不曾昏花,看得出义理是在哪一边,所以,靳老弟就生受我们一臂之助吧!”
靳百器没有说话,他只感到眼眶发热,喉头哽塞,体内的血液在沸腾,在翻涌,世上有怎样悲惨的遭遇,便也有怎样温馨的回馈,有血刃相向、斩尽杀绝的死仇,亦有拿骨肉维护,以性命顶抗的朋友,德义的赐予,仿佛一把烈火,能把人自沮丧中烧得亢奋,从凄晦里烧向昂扬,不错,前途仍然坎坷多难,但是,现在看过去,却已不觉得那么阴暗崎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