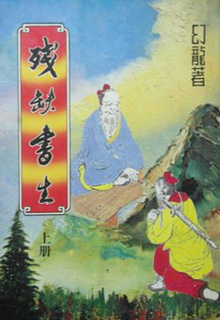黄君稚腼腆的笑笑道:“我听说,两个本领强,才识好,又都个性倔强的人是难得相处在一起的,因为双方全是恃才傲物,崖岸自高的个性,在观点作为上就不易协调一致了,这便会影响进一步的友谊发展……”
申昌玉颔首:“好,说得对,但我与厉绝铃不同。”
黄君稚问:“怎么不同呢?”
申昌玉深沉的道:“因为我与厉绝铃相识于患难,建交在并肩生死之中,我们彼此有过性命的连系,有着超越人类本性以上的谅解,所以,我们已经突破了人与人之间狭义的自我观念,所以,我们是肝胆相照,交逾刎颈的。”
厉绝铃完全同意的道:“你说得对,昌玉。”
黄君稚了悟到什么似的点点头道:“这,可叫惺惺相惜呀!”
申昌玉微笑道:“我们已不止是‘惺惺相惜’了,我们彼此更是福祸相连,生死与共!”
黄君稚沉思的道:“在你们所生活的圈子里,我已多少领悟了一些你们所尊重的传统,那是一种凛然的忠与义的组合,而这样的实质,便反映在你们二位壮士的友谊上,我相信,你所说的生死与共,便完全是不掺喧染的、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至高升华了……”
厉绝铃道:“黄姑娘,你是个可以贴切感受事与物的女孩子!”
黄君稚苦笑道:“有时,我却非常天真可笑。”
厉绝铃道:“这是谁都避免不了的,人活着,便该有点天真,否则,严肃和拘谨得过份,就是残酷……”
想着什么事,黄君稚问:“厉壮士,你先前曾告诉过我,说有一拨非常凶狠的人在背后追迫你们,是不是就是方才你们所谈的‘黑楼’呢?”
目光注视着前面的道路,厉绝铃低沉沉的道:“是他们——”黄君稚忧虑的道:“那些人,真的很凶狠?”
厉绝铃点点头道:“不错。”
迷惑的眨眨眼,黄君稚又道:“但是,我怎么听到那几个什么‘十全派’的人说,申壮士也是那‘黑楼’所属的人呢?”
笑了笑,申昌玉道:“我的确是。”
惊愕的看着申昌玉,黄君稚道:“申壮士是那什么‘黑楼’一帮的人,而‘黑楼’又千方百计的要追逐你们,而你们二位又是这么要好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把我弄糊涂了……”
厉绝铃一笑道:“非常容易解释,黄姑娘,我与‘黑楼’有仇,‘黑楼’便派人来不利于我,而昌玉是‘黑楼’的重要份子,也被派来对付我,昌玉一听到他们要对付的是我,马上便反过头来帮我对抗‘黑楼’,更冒着天大的危险来助我摆脱他们,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黄君稚道:“那么,起初‘黑楼’的人难道不晓得你们有旧?”
厉绝铃笑道:“当然不晓得,否则,他们岂会派昌玉出来自找麻烦!”
“哦”了一声,黄君稚道:“这样一来,‘黑楼’的那帮人一定对申壮士恨之切骨了?”
申昌玉淡淡的道:“这是无庸置疑的。”
黄君稚道:“一路上我已听到你们在讨论这件事,以你们二位壮士这么高强的武功来说,却好像仍旧十分担心似的!”
吁了口气,申昌玉道:“我们是在担心,因为我们的力量仍不够强——就眼前要对付的‘黑楼’来说,你不清楚他们,在他们那批人之中,有些人的武功不比我们两个人差,主要的,是他们人多,而一旦人多,势便大了!”
黄君稚急道:“真正的武士是要讲义气,他们应该一对一——”吃吃的笑了,厉绝铃道:“有时候,你的确很天真,黄姑娘,问题是,他们不是真正的武士,也就不会讲什么道义,一旦相遇,他们十有十成是恃众凌寡的!”
黄君稚不平的道:“既是这么不讲道义,这帮人怎能在你们的圈子里拥有这么巨大的势力?”
苦笑一声,厉绝铃道:“这就是人间世上千百种矛盾的一种了,黄姑娘。”
于是,黄君稚沉默下来,是的,因为暴力或诡诈,再加上点机运,多少歹人恶棍不也生存了下来?而且,其中有些甚至比一干善良的人更生活得惬意与倨傲,因为他们持有恶毒伎俩!便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邪异的势力圈子,照说,这是不该有的,但事实上却存在着,是人类容易受胁受欺的弱点所至么?这就是世界上的矛盾。
厉绝铃与白莲萍所约的日子是六月十六,时间是起更的当儿,这约期就在眼前了,所以他们一路上赶得相当仓促、急迫,当然,比较吃苦受累的是黄君稚,但她是个知道轻重、明白大体的女孩子,一路上她全咬紧了牙关,强忍着马行的颠簸与震荡,和厉绝铃、申昌玉一样,顶着火毒的日头和苦热的天气,兼程赶向目的地。
这一天,六月十六,下午,他们赶到‘清沟甸’,在厉绝铃的引导下,直奔向那片松林子。
这是一片方圆有五十余丈的松林,好像大自然中有这么一种惯性,有林子的地方便会有风,他们三人三骑尚未进入林中之前,耳中已听到松涛簌簌,针叶如浪起伏,进入林里,更是凉风习习,一片翠绿,映得人身心俱爽,说不出有多么个舒泰与熨贴。
那间凉亭,便在林子深处,亭角有些坍颓了,现出破旧而古老的,但是,却不可否认的仍带有一股清新飘逸的韵味;不管是谁,不管亭子盖在这里多么久远,那个有心在此处造这间凉亭的人,亦必是位懂得享受自然之美的人。
黄君稚以她的水湖色丝绢轻拭着额角鼻端的细碎汗珠,心旷神怡的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啊,好凉快,好舒服哟……”
厉绝铃翻身下马,微微笑道:“这里比起途中的如火日头,连眼尘沙来,自是要清爽安逸得多——”他扶着黄君稚下了鞍,与申昌玉一起步入凉亭之内,黄君稚仰起脸来深深吸了一口飘散在四周的带着淡雅松子芬芳的空气,然后,她赞美道:“这里真好!”
申昌玉靠在石栏边的长条石凳上坐下,半闭起眼道:“还有时间睡个午觉……”
厉绝铃笑道:“请便。”
黄君稚嫣然一笑,道:“申壮士说得我也突然困倦起来了!”
解下颈项中的汗巾,厉绝铃草草揩着脸上的油汗,边道:“你也可以歇上一阵,时间还早。”
摇摇头,黄君稚腼腆的道:“不了,这……这不大好看……”
厉绝铃笑道:“老实说,这一路上来,每逢晚上露宿之际,你全躲得远远的,就像生怕我们吃了你一样,却害得我们替你担着老大心事,一夜里得起来探视你好几遍,生恐你被什么蛇虫惊着,这种天气,你知道,郊野露宿多少得防着点。”
黄君稚脸儿红红的道:“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只是不习惯……”
笑了笑,厉绝铃道:“当然,我完全了解,闺阁淑女,自是深受礼教熏陶,一旦与两个并不熟悉的大男人野地共歇,心理上那种窘迫惶惶之情乃是可以想见的,不过,时值非常,事贵从权,只要我们本身光明磊落,行为不苟,也就无须太过拘束了!”
黄君稚羞涩的道:“你这样一说,我更觉得不好意思了——”申昌玉接口道:“喂,你二位若是不歇着,我是要先睡上一觉啦!”
厉绝铃道:“你睡你的,也没有人拦着你!”
刚刚依着石栏干才闭上眼,申昌玉又忽然睁了开眼来,他上下左右一溜睃,若有所思的道:“老友,我们赌个东道,怎么样?”
厉绝铃有兴趣的道:“好呀,赌个什么东道?用什么事来赌?”
申昌玉笑道:“我找你藏着的东西,若是我找着了,你给我一颗‘猫眼玉’,找不着我输你十两金子!”
豁然大笑,厉绝铃道:“娘的,你倒会占便宜,我那箱猫眼玉每一颗至少值得上百两金子,你却只用十两之数来对赌——好吧,我便自认吃亏,只收你十两金子好了。”
申昌玉道:“只收我十两金子好了?老友,你的口气相当自信,莫非你认为我一定找不着那箱玩意?”
点点头,厉绝铃道:“我是这么以为!”
一搓手,申昌玉站了起来,他道:“我就不信邪,非给你找出来不可!”
微微躬身,厉绝铃道:“欢迎尝试。”
目光迅速在凉亭子四周游动,申昌玉道:“绝铃,首先我们得把话说明白——那箱‘猫眼玉’你是藏在这亭子之内,是不是?”
点点头,厉绝铃道:“不错,包括整个凉亭上下里外,全是你想要寻找的范围,但,却绝对不在这凉亭之外的地方。”
申昌玉道:“好,我找。”
厉绝铃笑道:“说定了?”
申昌玉笑道:“当然。”
于是,厉绝铃坐到方才申昌玉坐过的地方,他二郎腿一架,悠闲的道:“开始吧,我这里先打个盹,东西只要找着了,叫我一声便行,届时箱里的‘猫眼玉’便任由你挑拣一颗!”
申昌玉颇有把握的道:“你恐怕输定了,老友,这座凉亭一共只有这么丁点地方,而且建造简单,一目了然,喏,一个亭顶,角檐四翘,不,只有三翘,有处翘角已经断落下来了,再就是四根木桩,一圈石栏加上四条石凳,一张石桌,如此而已,实在没有什么隐秘之处供你藏物,我很快即可找出东西来!”
厉绝铃笑道:“先别大言不惭,东西找出来后你再得意不迟。”
注视着厉绝铃,申昌玉忽然道:“好,首先,请你站起来。”
怔了怔,厉绝铃迷惘的站立起来:“干什么,东西也不在我身上——”突然,他颖悟的大笑:“好家伙,申昌玉,你真鬼灵精呀,我一坐到你方才坐过的位置上,你就怀疑我是故意掩饰那个地方的什么东西了——”
申昌玉急步上前,就在厉绝铃坐过的石凳部位上敲打找寻,可是,他却失望了,那条石凳是整块青斑石打磨成的,实心实质,根本没有什么间隙或伪装的洞缝。
他耸耸肩,又开始在其他三条石凳上下搜查起来,厉绝铃又坐回原来位置,好整以暇的看着他行动。
长条的石凳他搜查完了,接着又是石桌、石栏干、石柱子,申昌玉几乎是一寸一寸的在寻找查看……
黄君稚也趣味十足随着申昌玉的移动而目光紧跟不缀,她轻笑道:“申壮士真仔细啊……”
一面找寻,申昌玉边道:“一颗价值百金的‘猫眼玉’为酬呢,当然得仔细……”
厉绝铃道:“我看你那十两金是输定给我了。”
擦着汗,申昌玉又仰头察看亭顶——那是用浆灰与石粉嵌合成的里层,多半也剥脱了,他说道:“不见得。”
说话中,他的身形倏起,快速得无可言喻的双手飞闪,只听得“嗒”、“嗒”、“嗒”的碰触声连串密响,灰粉飘舞里,他已在眨眼间似乎试遍了亭顶里侧的各个部位。
微微皱着眉,他喃喃的道:“也没有……”
厉绝铃笑道:“有这么容易的事呀?”
突然,申昌玉斜掠出亭,凌空的身子一个倒翻,极其美妙又极其俐落的上了亭顶,他在上面往返搜寻,却听不到丝毫声息!
半晌,他又掠回亭里,双手空空。寻思着,他目光四转:“怪了……”
厉绝铃道:“可要我揭穿谜底?”
摇摇头,申昌玉道:“等一下。”
接着,他笑出声来:“你是怕我找着东西,由此可见,我已快要接近那箱宝贝了,只要将范围再缩小,删除我找过的地方,嗯,剩下的空间便有限了,那箱东西便必在其中的某一处——”
厉绝铃笑笑道:“别太相信你自己的推理。”
申昌玉注视地面,地面却全是大麻石铺成的,也已经残凹斑斑了,他拔出他的月刃斧,异常仔细的逐块敲打审视,耳目并用,试图听出点有异的回声,或者看出某些被移动过的蛛丝马迹来,好一阵子之后,他又失望了。
静静想了一会,他又突然奔至亭外,运力搬动那两级石阶,于是,他发觉那两级石阶也是整块青斑石嵌建在地下亭基上的,没有藏物的空间。
背着手来回踱步,他自言自语的道:“绝铃来藏这箱东西的时候,一定也是很仓促的,他匆匆来了,四顾无人,便立即匆匆找个地方藏好,他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筹思选择……奇怪,在匆促里所藏的东西应该不会太隐秘,应该在很容易找的地方……假如我是他,我会藏在哪里?我进来凉亭,石桌底下?不行,那是实心牢结的,没有空隙,石凳里?也不行,也是整条石块嵌合的……石柱?石栏干?没有足够的空间。亭顶里层?那只是一层石胶板而已,不可能,亭顶面上?没有檐角里外也找不着,亦没有拆下重装过的痕迹,事实上那檐角若拆下来便接装不上去了……奇怪,他会把东西放到哪里去呢?铺石的地面上,也一样没有丝毫可疑之处呀……。”
厉绝铃笑道:“怎么样?认输了吧?”
申昌玉苦思着道:“等等,我再想想。”
伸了伸懒腰,厉绝铃道:“不急,你尽管想。”
一边,黄君稚却掩着嘴笑了……
沉吟又沉吟,寻思复寻思,良久,申昌玉又朝凉亭四周各处打量了几遍,最后,他终于摇头苦笑:“恐怕我输了……”
厉绝铃笑道:“你输了,昌玉。”
申昌玉无精打采的道:“好吧,老友,告诉我,东西你藏在哪里?”
厉绝铃道:“说真话,昌玉,你输是输了,但不是输给我,乃是输给你自己,输给你自己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上——”睁大了眼,申昌玉迷惘的道:“你是指——?”
厉绝铃低沉的道:“很简单,你脑子里尽是想着一‘箱’的‘猫眼玉’,因此一心要找的也是一‘箱’‘猫眼玉’,你总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容纳得下那只木箱的地方,一直在找一处可以藏得下一只木箱的空间,所以,因为你有这种的想法,便自己指引自己走向歧途去了——”脑海里立即迷茫转为清晰,好像刚由浓雾里走出来一样,申昌玉失声道:“没有木箱——那么你是把那些‘猫眼玉’分散开隐藏的了?”
点点头,厉绝铃道:“正是。”
猛的敲了自己脑门一下,申昌玉跺脚道:“嗳,怎么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站了起来,厉绝铃笑道:“叫你想到,我还去赢谁的十两金?”
申昌玉忙道:“那么,你藏在哪里呢?我什么地方全找过了呀!就算东西的体积小了,也总应该有点端倪……”
厉绝铃慢条斯理的道:“老实说,那地方你已经找过了。”
怔了怔,申昌玉叫:“什么?我已经找过了?”
厉绝铃笑吟吟的走到对面那条石凳之下,蹲下来,开始用双手在铺地的大麻石石块的间隙中挖掘,他先将上面一层浮土拂开,又伸出指头挖挖抛起一些业已变硬了的泥灰,然后,一颗颗虽然沾着泥污,却仍难掩其闪耀异彩的八角形‘猫眼玉’便被他逐粒取出,堆积在他平展地面的汗巾上!
申昌玉痛悔的道:“唉,我可上了你的老当——”
厉绝铃道:“你只是想到那箱东西有没有埋在铺地的石块底下,所以逐块敲打,听其回音是否有异,更审视其是否有被搬动的痕迹,当然都没有,因为我根本便没有移动过这些石块,我只是将这些铺地石块中间的隙缝挖开,再把‘猫眼玉’一颗一颗塞进去覆掩以泥土而已,上面略略一扫,便完全没有痕迹了;你又敲又打,自然不会发觉异处,这个法子,既简便又可靠……”
申昌玉笑着摇头道:“我说你鬼名堂多,可是也没说错,绝铃,今番我算是叫你摆得四平八稳啦……”
厉绝铃笑道:“好说好说。”
接着,他一伸手:“十两金。”
叹了口气,申昌玉探怀摸出一只小金锭丢了过去:“唉,好不心痛哉,你这拥有巨额珠玉的富翁犹剥削我这穷措大,岂不太也心狠了?”
厉绝铃一面迅速挖取石隙中的‘猫眼玉’,边将金锭纳入腰带中,眉开眼笑的道:“财不嫌多,多多益善嘛……”
申昌玉也走过来,蹲下身帮着他挖,顷刻间,那张铺在地上的汗巾上已堆积了一大撮闪灿耀亮的“猫眼玉”了。
一侧的黄君稚轻声道:“厉壮士,可要我帮忙?”
厉绝铃笑道:“这是粗活,玉指纤纤,可别弄得粗糙了,不劳黄姑娘动手。”
申昌玉急道:“我该想起来的——”
厉绝铃问:“想起什么来?”
申昌玉道:“你不是说过在进‘丹冠门’会见娄子硕之前,已把那只木箱中的‘猫眼玉’取出换成满箱的碎砖烂瓦了么?这表示你已没有原来的那只木箱了,按当时的情形判断,你势不可能再去另买或订制一只箱子,我却老是一心一意在找寻凉亭中可以隐藏的地方,唉,真是窝囊!”
厉绝铃道:“这是人类的通性——自以为是。”
微微一笑,申昌玉道:“你也不要得意,下一次,我们再找机会赌——”他眨眨眼,又道:“至少,我说对了一点,你藏东西的地方是很简便又不费事的处所!”
点点头,厉绝铃双手不停:“这个,我承认你的判断很有道理,我当时的确很忙,也没有太多的闲暇来挖空心思找寻藏物之处。”
申昌玉道:“你这样一说,我颇觉安慰,这总证明我还多少有点头脑!”
已将石隙中的‘猫眼玉’全部挖出,厉绝铃将汗巾包扎后,朝石桌上一摆,拍拍手道:“好了,只等起更,白莲萍一来,我和她对分完了以后,这桩心事便已了结!”
申昌玉道:“这桩买卖亦就皆大欢喜了。”
厉绝铃道:“等我和她分过了,昌玉,你再随便挑拣吧,要几颗都行!”
“啧”了一声,申昌玉笑道:“喝,怎么忽然大方起来了?”
厉绝铃笑道:“我这半辈子从来就没小气过,和你赌东道是有赌注的,赌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心眼!”
申昌玉搓搓手,道:“正如你所说,我只是输给了我自己那先入为主的观念,尚堪可原谅自己,绝铃,下一次,你就没有这样的好运道了。”
哈哈一笑,厉绝铃坐回石凳上,道:“不用嘴硬,等你下次赢了我再说!”
接着,他转朝黄君稚道:“黄姑娘,这些‘猫眼玉’你如喜欢,我也可以送你几颗。”
连忙道谢,黄君稚道:“多谢厉壮士的盛情,这么珍贵的珠玉,我怎敢随便接受?还是请你留着移作他用吧……”
厉绝铃也不勉强,他微微一笑:“也有人不在乎这些东西的,黄姑娘,你与那白莲萍一比,她就不知差到哪里的了。”
黄君稚娇羞地一笑道:“我也没有这么脱俗——只是这些珍贵珠宝,如今于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用途……”
朝石凳上一靠,申昌玉道:“天色近晚了呢……”
可不是,就这一会,四周的光线业已有些黯淡下来,落日残照,已将大地抹上一片郁红灰紫。
松林林梢上的青绿,被这抹凄艳的晚霞一映,也就变幻得那样的意韵苍凉了,林中的光线更暗,隐隐里,有一片如云似雾的烟氲已在其中浮沉飘动;黄昏了,千万个黄昏,却仍然有着千万种迥异的情调……
厉绝铃喃喃的道:“可不是,天色近晚了——”申昌玉显得有些疲倦的瞌上眼睛,他低沉的说道:“待这件事一办完,我们就得快马加鞭往回赶。”
他的话才只说到这里,简直连一点征候都没有,凉亭外,一溜尖锐的破空啸声猝起,才听着啸声,一条细长的白影已怪蛇也似将石桌上包扎着满满“猫眼玉”的汗巾卷起来,快不可言的往外缩回!
叱声如雷,申昌玉的月刃斧寒光闪掣,却稍差一线的落了空,厉绝铃的动作更要快,“生死桥”“削”声横截,但也只割破了汗巾一角,那包“猫眼玉”仍被卷缠着飞向凉亭右侧!
申昌玉面色铁青,倏射亭外,身形之快之疾,直如石火一闪!
厉绝铃却斜着穿越三丈,在空中一个侧旋,业已来到了凉亭右边,而且刚好阻在那条沿林而出的小径前!
那个人刚刚手中抓住了那包“猫眼玉”,才一转身,厉绝铃已到了他的后面,几乎在同一时间,申昌玉也已来到!
目光冷锐的注视对方,厉绝铃的神色是严酷的——那个六尺怪客,身材瘦小,四脚又细又干,活像四根枯枝一样,但却顶了一个奇大的脑袋,乱蓬蓬的头发下是一个突出的额角,细眼,眼角黏糊糊的堆积眼屎,朝天鼻,黑黑的孔往上翘起,有如两条烟筒的黑洞,鼻毛耸耸,厚嘴唇正咧开,露出满口参差不齐的黄板大牙来。
他穿着一袭长只至膝的布衫——看不出是什么颜色来,因为腰衫上的油垢污腻至少有半分厚,足下是一双破烂布鞋,衣间扎着一根粗如儿臂的脏草绳——就是这么一号人物,现在,他左手上抓着那包“猫眼玉”,右手上是一条丈许长短、后粗前细且弹性颇强的怪异白色的鞭形物体。
一看对方这个模样打扮,厉绝铃与申昌玉立即明白来人的身份——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他们虽未唔过面,但传闻中的印象却是太深刻了!
固然,他们很快的明白了对方是谁,但人家却也同样知道他们的身份,这位形似叫花子般的怪客其声有如狼嗥般桀桀笑道:“厉绝铃,申昌玉,呵呵呵,咱们是神交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