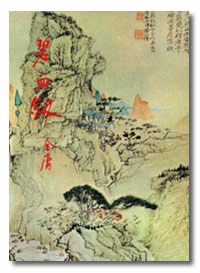于是我用极快的速度说了一句:“应该是卫斯理复制人的脑部!”
杜良哼了一声:“没有分别--你复制人脑部结构和你的完全一样,连脑细胞的数字都一样。”
虽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可是我坚持:“在你叙述的时候,最好还是分清楚。”
杜良没有再说什么,考虑了一会,改了口:“卫斯理复制人的脑部结构特殊,与众不同,最容易接受转移进入的知识,本来最适合的了,可是他复制人的脑部太特殊、太与众不同了,天生有一种特别的功能--”
他说到这里,我已经讶异之极,几次想要说话,都被白素紧握我的手阻止。
杜良瞪了我一眼:“--这种特别的功能,使他能够拒绝他不想接受的知识!我毕生从事人类脑部功能的研究,这种情况,是首度发现。”
白素也望了我一眼,道:“这种特点,反映在行为上,会形成什么的行为?”
杜良回答得很快,也很肯定,显然那是他经过详细研究之后的结论。他道:“是主观特别强,强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他会抗拒一切他不想接收的知识,具体地说,是别人的话,如果不合他的主观愿望,他绝对不会接受!”
白素听到了一半就笑了笑,道:“阁下真了不起,这正是卫斯理!”
我道:“这说明我判断是非的能力特别强--是『是』就接受,是『非』就拒绝,绝对不会听人摆布,任凭你说得天花乱,也休想我同意!”
杜良吸了一口气:“我不反对你的说法,可是这种特点,在复制人身上展现,就变成了复制人拒绝一切知识进入他的脑部!”
我立刻道:“这证明了我的复制人,并不适宜作为知识转移的对象--所有的问题那解决了,阁下『另请高明』吧!”
那时候我真的感到很轻松--既然我的复制人拒绝接受任何知识,所有的事情不就都过去了吗?
后来白素笑我:“看你当时的情形,象是真的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了,真不明白你怎么就忘了几分钟之前,杜良还说过,需要借重你脑部运作了?”
想起当时的情形,我还不免有些震荡--当时我们虽然身体上没有任何大动作,可是思想的起伏,心灵的矛盾,得失的衡量,形成的冲突和激荡,当真是难以形容--这种内心的斗争,是用思想来进行,比用身体来打斗,还要惊险。
尤其当时需要我下决定的事情,关系是如此重大,我的决定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进展,这样重大的责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却像万斤重担一样,压在心头。而在这样情形下,忽然有了可以放下重担的机会,当然会自然而然感到高兴。
至于在几分钟之后又发生的事情,当时我绝对绝对料想不到,后来事情发生了,由于事情相当怪异,所以连在场的白素也不知道,到了事情过去之后,我才告诉白素的。
当时我在真正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甚至于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杜良的话,是紧接着我的话而说的,他道:“的确要请高明,不过不必『另请』,这高明就是阁下,卫斯理先生!”
我摊了摊手:“我已经完全同意使用我的复制人--不管复制人有多少个,我都没有意见,我所能够做的,就是这样,已经做到了!”
那时候,我以为杜良既然在我的复制人身上转移知识失败,我乐得说风凉话,反正我这样表示了,他的研究工程也无法进行下去,对我来说,一点损失也没有,是典型的空头人情。
可是杜良和亮声对我的空头人情,却显出很感激的神情来,亮声甚至于兴奋得很,连连搓手。
杜良也很高兴,道:“能得到阁下再一次道样确实的保证:真是太好了。”
我做了一个“不必多谢”的手势。
然而接下来杜良所说的话,却将我轻松的心情一扫而空,他道:“经过了反覆研究,我已经找到了扫除障碍、使复制人可以接受知识转移的方法。”
刹那之间,我僵在那里,还维持着做那个手势时候的姿态,看起来一定非常滑稽,不然杜良望着我的样子,为什么如此愉快?
杜良继续这:“你不恭喜我?不恭喜全人类?”
我渐渐地恢复了活动能力,像傻瓜一样地问:“你找到了扫除障碍的方法?”
杜良大点其头,我又问道:“那就是说……知识转移,已经终于成功了?”
杜良却又摇头:“还没有,不过一定可以成功,卫斯理,关键就在你的身上,正确地说,关键在你的脑部。”
他在说的时候,手指一直指着我的脑部,情形相当怪异,使我有如同脑中有什么虫在爬行一样。
我甚至于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神情戒备,这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杜良的意图,可是既然他说了事情和我的脑部有关,对我来说,就是有关生命的大事,那和使用我的复制人不同,是切实要用到我的脑部,谁知道他要想对我的脑部动什么手脚!
电光石火之间,我已经有了一连串的决定:拒绝他对我脑部动手脚的任何要求--如果他软求不成要硬来,那就必须动武--动武一开始,在现在的情形下,必须一出手就有成果--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其不意将杜良和亮声制住,作为人质,使我们可以安全离开勒曼医院。
我也已经想到,行动必须迅雷不及掩耳,同时制服两个人,需要我和白素同时出手。
所以我立刻望向白素,示意她留意我的行动,和我配合。然而在这样我认为极其严重的时刻,白素却向我微笑,摇了摇头,表示我不必紧张--事情和真正的我的脑部有关,我能够不紧张吗?
杜良缓缓地道:“经过研究之后,唯一的方法,是解除复制人脑部抗拒知识进入的障碍,而能够解除这种障碍的,只有卫斯理,因为复制人是卫斯理的化身。”
在这时候,我还是不能完全明白杜良下一步会做些什么,白素的态度给了我可以听他说下去的镇定,所以我暂时没有任何行动。
杜良继续道:“没有找出原因之前,事情非常复杂,复杂到了令人想自杀,可是找出原因之后,事情就非常简单。只要卫斯理,你向复制人的脑部下一个指令,告诉复制人,接收转移给他的任何知识,这重障碍就可以消除了。”
听了这番话,我张大了口,却说不出话来,心中的惊讶,难以形容。
虽然我还不知道如何通过我向复制人下达指令,也还不能说事情都已经水落石出,可是把事情发展到现在的经过,把杜良和亮声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想一想,就可以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情是:杜良早已对我的复制人进行知识转移,可是却失败了。在失败之后,找出了原因,也找到了补救的方法。
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我向我的复制人下指令,指令他不要抗拒转移给他的知识。
只有我可以下达这个指令,因为那是我的复制人,我和他的脑部结构一样,一定有可以互通之处--我想的,等于他想的。
我更进一步想到,下达指令这个行动,必须出于我完全的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不然连我都不愿意,传达出去的讯息,也必然是不愿意,复制人接收了这样的讯息,当然不能够改变不接受知识转移的原则。
这就是杜良和亮声为什么要设计将我骗到勒曼医院来的原因。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经过的情形告诉我,向我说了那么多鼓动的话的原因。
他们必须我完完全全同意他们的行动,必须我百分之百愿意,才能将解除障碍的指令有效地傅送出去,使得知识转移工程能够成功。
他们当然知道,我,卫斯理,脑部特殊,有拒绝接受自已不想接受的知识的能力--我认为那是一种能使人保持自已独立的思想、不受蛊惑的能力,每个人脑部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道种能力我认为天生的成份少,后天训练所得的成份多。
他们一定针对我脑部对于事情的是非,有非常强烈的分辨能力,而定下了对付我的详细计划。
他们逐步实现计划,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我在完全自愿的情形下,向我的复制人下指令。
我从一开始起,就一直隐隐约约感到有一个阴谋存在,现在证明这个感觉完全正确,阴谋就是他们针对我的计划。
而他们的计划,在逐步实行中,可以说每一步都很成功:他们将我骗到了勒曼医院,使我在听到了他们叙述研究工程的远景之后,热血沸腾,他们鼓动了我的情绪,使我觉得能够参加这样的工程是极大的荣幸,他们使我同意了在工程研究中,无数量限制地利用我的复制人。
直到最后一步:要我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向复制人下达指令。
他们确然十分成功,因为到现在,我已经洞悉了他们的计划(阴谋),可是我却完全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事情发展下来,到了最后一步,知道工程进行可以给人类文明进展带来这样巨大的好处,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
我不但不能拒绝,而且还要说服自己:必须这样做,必须百分之百感到要这样做!
在听了杜良的话之后,我迅速转念,想到了许多,可是时间却极短,至多只是杜良微笑了几下的时间而已,事实上他几乎没有停过说话。
我在明白了这些之后,立刻向白素示意我想到了许多,白素却还我以她早知道了的表情。
杜良继续说的是:“这个下达指令的过程,非常简单:通过仪器,联结卫斯理脑部和复制人脑部,卫斯理只要将指令想一想,就成功了!”
杜良说到这里,摊了摊手,道:“看,就是那样简单,伟大的事业,从最简单的行动开始!”
我吸了一口气,向自己头上指了一指:“如何联结?插一些针进去?”
杜良和亮声听了,都哈哈大笑,在知道了一切都是他们计划中的行动之后,我只觉得他们的笑声之中,充满了虚情假意。
这时候我的心情其实并不矛盾,我虽然对他们的这种阴谋非常不满意,可是没有拒绝的理由,我准备接受他们的要求,各复制人下指令,使知识转移工程能够进行,并且还确然以这样伟大的工程能够从我开始而感到光荣。
也就是说,我准备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按照他们的计划去行动。
然而我也决定了,在行动之前,我要揭穿他们的“阴谋”,表示我知道了一切,才自愿进行,就非在他们的欺骗之下才进行的,好让他们知道,想要从头到尾欺骗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准备在揭穿他们的时候,大大奚落他们一番,尤其是亮声,不会轻易放过他--我和他相交一场,算是朋友,他却伙同杜良来骗我,太可恶了!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自然而然想起和亮声交往的经过,想起难怪亮声会给我陌生的感觉,原来是他心中有鬼的缘故。
(当时我确然如此以为。)
我在这时候,脑中所想的一定全都是,或者大部份是亮声--这一点非常重要,立刻发生的事情,后来证明和我当时脑部活动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就在我准备开口,开始揭穿他们,令他们大大狼狈,然后才答应去向复制人下达指令时候,我忽然听到有人在叫我:“卫斯理!卫斯理!”
若不是那叫我的声音非常特别,我一定以为不是杜良就是亮声在叫我,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
然而那叫我的声音,听来焦切之极,很是绝望,象是已经叫了几千几万声,我都没有听到,他在濒临绝望之前,还是不肯放弃,还在继续,却又没有使我必然听到的可能,带者很深的痛苦。
我怔了一怔,向杜良和亮声看去,只见他们都笑嘻嘻地望着我,带着计划接近完成的喜悦。
那在叫我的,并不是他们,当然也不会是白素,而且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其它人都并无所觉。
若不是这时候,那声音继续在叫我,我一定以为刚才是错觉了。而正由于在继续,我立刻明白实际上并没有声音--我听到,是我脑部感觉到而已。
这种情形在我身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可以说相当熟悉,那是有力量在影向我的脑部活动,使我“听到”。
一般来说,要做到这一点,绝不容易,而这时候,对方的“声音”听来如此焦切,必然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进行沟通。
我向杜良和亮声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我要想一想,然后我走向一角,面对墙,集中精神,作出响应:谁在叫我?
这时候我隐约听到白素和杜良在交谈,象是在问杜良一些问题,我由于要集中精神和那叫我的人联络,所以听不真切,然而我却可以知道,白素向杜良说话,目的是要稳住他们,好让我不受到打扰。
我一作了响应,立刻听到那声音发出了一下呻吟:谢天谢地,你终于听到了我的叫唤,卫斯理,我,我是亮声!
刹那之间我的惊讶,到了极点--那人若是自称他是玉皇大帝,我也不会再惊讶的了!
当时我的脑中轰轰作响,自然而然向亮声看去,只见亮声正在和白素说话,完全没有注意我。
而通过我脑部活动和我沟通的人,却自称是亮声!
那人在继续:“我是亮声,卫斯理,我是亮声,你的朋友亮声,绝对不会欺骗你的亮声,请相信,请相信!事情非常严重,请相信我是亮声!”
我脑中陡然灵光一闪,他那句“绝对不会欺骗你的亮声”打动了我,确然,亮声应该绝对不会欺骗我,那么就可以非常直接地得出结论:欺骗我的,就不是亮声!
刹那之间我想到许多在这以前不可解的现象,从老蔡对诡声的态度,从他对我的告诫开始想起,许多使我对亮声产生陌生感觉的事情,都集中说明了一件事情:目前在我视线范围内的亮声,绝不是我的朋友亮声!
而他外形和亮声一样,道理也简单之极--本来就是借用地球人的身体,要找一个同样的身体,对勒曼医院来说,是容易到了极点的事情。
事情竟然要出动到假冒亮声,可知其严重程度,必然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我立刻响应:我相信,朋友,我相信!发生了什么事情?
亮声(我相信了那是真正的亮声)在喘气--我真的感到他在喘气,后来知道亮声当时的情形,如道亮声不可能有喘气的行动,可是当时我确然有这样的感觉。
亮声道:“日后再告诉你,现在你千万记得两件事:一、不论你被要求做什么事情,都绝对不能答应,绝对不能答应!二、你要设法尽快安全离开勒曼医院,并且在没有再次见到我之前,千万别再来!那杜良不是好东西,勒曼医院之中,也有败类,情形非常严重!”
听了这样的话,我心中混乱之极,立刻感到的是,亮声这样紧急的吩咐,极端矛盾。
他说的话,告诉了我,勒曼医院中有了败类,杜良也不是好东西,显然两者勾结,不知道要进行什么阴谋,所以他要我绝对不能答应他们的任何要求。
然而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为了阴谋的实现,必然不择手段来应付,我和白素又如何能够尽快又安全地离开?
我知道亮声对我下了这样的警告,事情一定严重到了极点,亮声本身,可能也出了问题,会不会遭到了囚禁?所以才要用这种直接影响我脑部活动的方法来和我联络,刚才一定是我在偶然之间,脑中想起了亮声,这才和他发给我的能量接上了头,使我可以收到他的警告。
这种联络方式随时可能中断,我必须向他请教,如何才能解决我拒绝要求、又能离开的矛盾。
我还没有发出问题,亮声的话,在感觉上更是焦急:“照我的话做,别犹豫了!”
他一定是感应到了我的思绪,我立刻问:“拒绝容易,可是如何在拒绝之后离开呢?”
亮声的响应,令我啼笑皆非:“你想办法!你会有办法的,你是卫斯理啊!”
我自然而然骂了他一句--完全是正常的和熟朋友的应对方式,亮声立刻有反应:“别骂我!现在不能多说了,多说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日后我会将情形详细告诉你。”
我觉得他的处境可能很不妙,才想起关心他,他就有了表示:“我很好--清除败类的努力,正在进行--”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杜良和假亮声都发出了响亮的笑声,我还想和亮声联络,却已经没有了音讯。
我转过身来,眼前的情景,可以用他们三人“相谈甚欢”来形容。
后来我问白素,问她和杜良以及假亮声说了些什么--白素在那关键时刻,将两人对我的注意转移,使得我能够和亮声通消息,白素的行动,非常重要。
白素笑道:“那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只知道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发生,既然你的行动表示了你需要思索,我就当然要替你营造不受打扰的环境,只有没话找话说。”
我好奇:“究竟说了些什么内容?”
白素若无其事地回答:“也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是说起了一些历年来有关卫斯理的糗事而已!”
我哼了一声,想起当时他们笑得欢畅的情形,非常之后悔多此一问。
白素当然注意到了我脸色难看,她道:“我故意将过去的事情拿出来说,有特别用意--我很早就觉得亮声不对劲,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所以特地试他一试,果然很多事情,他早就应该知道,甚至于有的事情,他曾经参加过,可是听我说来,他还是很有兴趣,显然是第一次知道,更证明了他非常有问题,正想告诉你我的发现,你已经向我说这亮声是假的了。”
当时我转过身来,和白素四目交投,我立刻感到白素有话要对我说,可是我觉得我要说的话更加重要,所以立刻用唇语告诉她:“这亮声是假的!”
白素立刻略点了点头,对这个讯息,毫无保留地接受--当时我并不知道,白素不但早已起了怀疑,而且已经证实。
那时候,杜良和假亮声还在笑,笑得非常不怀好意,我也不去追究他们笑的是什么,杜良先停住了笑,向我道:“考虑的结果怎么样?”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大声说出我拒绝他们要求的决定。可是有时候事情的变化,非常奇怪,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当时的而且确,我是准备拒绝的,因为我接受了亮声的警告,我必须拒绝,这是亮声千叮万嘱的事情。
然而突然之间,早一秒钟的决定,会突然改变,我一开口,说出来的话竟然是:“好,我们什么时候进行?”
从要拒绝,到答应,是完全相反的决定,这种回答,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白素立刻扬了扬眉,表示疑惑。而杜良和假亮声则兴奋之极,杜良叫道:“马上开始!”
我吸了一口气,装成很轻松的问:“不必在我头上钻孔?”
杜良走过来,亲热的搭住了我的肩:“当然不用,只需要戴上联结的设备就行,保证不会有任何伤害,也不会有任何痛苦。”
我又提出要求:“我不想和我的复制人见面,是不是可以作特别的安排?”
杜良立刻道:“当然可以!”
这时候我故意提出一些要求来,目的是为了使杜良相信,我是真正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准备向复制人下达接受一切转移知识的指令。
我提出的要求多,就表示我真的要那样做。
杜良对我所有的要求,都一口答应,我也表现出适当程度的兴奋,道:“能够参与这样伟大的工程,真是令人难忘。”
杜良很是自负:“可以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工程了。”
在说话之中,我们离开了原来的房间,进入另外一间房间,那房间中有更多的仪器,有两具设备,特别引人注目。
那两具设备,无以名之,只好形容一下它们的形状。那东西家极了放木乃伊的棺木,中间有一个人形凹槽,大小可以躺下一个人,两具设备,相隔人约一公尺,有许多线联结。
我可以想象这两具设备的用途,我向它们指了一指,杜良点头:“要请你躺进去。”
我看到那设备有盖子,刹那之间不禁有一些犹豫,问道:“躺进去之后,要盖上盖子?”
杜良显出很轻松的神情,道:“是啊,刚才你说不想看到你的复制人,所以你应该先躺进去。”
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似笑非笑,很有挑战的神情,象是在说:你卫斯理不会是没有这个胆量吧!
我笑道:“既然答应,就要做到,躺就躺吧。”
我向那设备走去,杜良紧跟在我的身边,我向白素望了一眼,看到她很有担心的神情,我就给她鼓励的眼色,告诉她我有准备,不必担心。
其实这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躺进那设备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感觉上来说,被放人像棺材一样的容器之中,绝对不是愉快的事情。
然而我这时候却又非如此不可--谁叫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呢?
白素向我点了点头,我吸了一口气,杜良可恶地在我背上拍了一下,道:“不必吸气--会有足够的氧气供应。”
我哼了一声:“多谢照应。”
杜良立刻向我深深鞠躬,表示歉意,看来他为了要我照他的意思行事,对我非常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