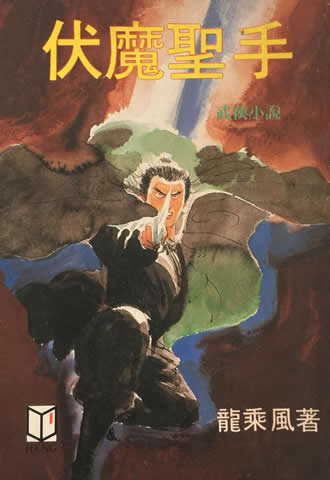白素顺手把皮包抛在地上,她知道日本人很有拾遗不贪的习惯,拾到了之后,会交给警方去处理。她心中这时很有点后悔,因为她根本不相信这两个人真是什么蛾类研究所的人。
她觉得自己应该继续跟踪下去,了解这两个人的真正身分才是。
于是她又追上去,可是一直追到刚才的街道,又在附近找了好久,花了大半小时的时间,也没有再看到那两个人。他们显然是截到了计程车离去了。
白素感到相当懊丧,恰好有一辆空的计程车经过,白素决定回尾杉家去看看,所以她上了车。在车中,她取出了那个纸袋来,打开,纸袋里面的,并不是她想像中的盒式录音带,但是也相当接近。
说“相当接近”,是因为白素一看,就可以看出,那是一卷磁带,可是却有着特别的装裹方法,外壳是十分坚固的金属盒,比普通的盒式录音带来得扁,比较大一些。
磁带用来记录信号,一定要有一种特定的仪器,才能使磁带上的信号还原。白素相信那仪器,一定在尾杉的家中。
反正尾杉的家里没有人,她倒很有信心把那个仪器找出来。
车子到了附近,白素下了车,这一次,她从正门推门进去,从大堂开始寻找起。照她的推测,那两个人鬼头鬼脑,深宵送“资料”来,那份“资料”,尾杉一定十分重视。从“资料”的形状来看,那很像是一具种型电脑的软件,小型电脑再小,也有一定的体积,应该不会很难找。
可是,白素虽然在尾杉的书房中,发现了一具小型电脑,却发觉那两个人拿来的资料,全然不适用,在书房中,白素花去了不少时间,一无所获,她又搜寻其他的地方。
时间迅速地过去,已经是凌晨五时了,白素仍然一无所获。虽然她沉得住气,这时也未免有点焦急,几乎想放弃了,因为那卷资料既然在她手中,一定可以有办法令该带上的讯号显示出来的。
就在她准备离去,经过大堂之际,她忽然看到,大堂的一边,是一列架子,架子上所放着的,全是高级的音响器材、唱片和录音带。
有一个时期,白素和我,都沉迷于音响,也有着相当程度的音响器材的知识,叫得出各种各样古怪器材的名称和用途。
白素在一瞥之下,停了下来,因为她看到,在一架十段均衡器之旁,有一样东西,她不认识。那当然是一种仪器,有着十公分地萤幕,看来像是一具示波器。但是却又有着可以放进盒式录音带的装置。
白素走过去,把手中的那盒资料,凑了一凑,恰好可以放进去。
白素的心中不禁暗骂尾杉狡滑,尾杉故意把十分重要的东西,放在当眼处,和类同的器材放在一起,那的确可以骗到人。
白素放进了那金属盒,略为观察了一下,发现有一副耳筒,联结着那具仪器,她开启了电源掣,感到十分兴奋,尾杉获得的,究竟是什么资料,看来可以有答案。
那仪器上有许多掣钮,有的标明用途,例如电源开关、磁带运转的方向、停止、微伏的调整等等。但是还有许多掣,却并没标明用途。
白素先令磁带运动,不一会,在萤光屏上,就出现了许多看来是全然没意义的、杂乱无章的闪动的线条。
白素又将耳筒带上,希望可以听到一些声音,可是却什么也听不到,她又随意按动几个用途不明的掣钮,结果仍是一样。
在这具仪器之前,白素不知不觉,又花了将近一小时,这时,天已开始亮了。
白素心想,天亮了,要是有人发觉尾杉的住所之中有人,那可不容易解释,而且张强也可能等得很急,不如把东西拿回去,慢慢研究。
白素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就把那具仪器,自架上搬了下来,连着那副耳筒──这时她也发现,那副耳筒的构造,十分特别,与普通的音响用的耳筒,大不相同。
白素随便找了一个纸盒,把那具仪器放了进去,事情很顺利,并没有给人发觉她自尾杉的家中搬走了一样东西。在街口叫了计程车,回到了酒店,那是六时四十三分,白素先打电话到张强的房间,告诉他,有了重要的发现。
然后,白素就搭乘电梯,上楼,张强已打开房门在等她,一见面就问:“发现了什么?”
白素十分简洁地叙述了经过,一面说,一面替那具仪器插上电源:“你看,这是什么意思?”
萤光屏上显示的凌乱的波纹,一点意思也没有。张强拿起耳筒来,戴上,整理了一下,抬起头来道:“这不是普通的耳筒,你看,这里有两个有吸力的软盘,紧贴在头上,倒像是做脑电图时用的接触装置。”
白素早已发现了这一点,她只是问:“你可听到了什么声音?”
张强一面摇着头,一面不断随意扳动着那具仪器上的掣钮,突然之间,他出现了怪异莫名的神情。
由于接下来的一切,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以致反应敏捷如白素,也不知所措,只好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
张强的神情,陡然之间变得怪异莫名,白素想问他怎么了,可是还未曾出声,张强已经发出了一下惊呼声。
(就是两个清洁女工听到的那一下。)
张强一面惊呼着,一面陡然除下了戴在他头上的耳筒,抓着耳筒,用力挥动。
由于耳筒的一端,有联结线的插掣,插在那具仪器上,他一挥动,连带着把那具仪器也挥了起来,插掣松脱,仪器向着墙角飞过去。
在那一霎间,白素犯了一个错误──其实,不能说是白素的错误,任何人在这样的情形下,都会这样做。因为以后接下来发生的事,全然出人意表,谁也无法料到。
白素一看到了张强有这样反常的动作,只当是他从耳筒中听到了什么怪异的声音。
接下来,那具仪器向墙角直飞了过去。它一撞在墙上,必定损坏,是以白素也立时发出了一声惊呼声。
(两个酒店清洁女工听到女子惊呼声。)
她立刻抓起沙发上的椅垫,向那具仪器抛过去,希望挡在仪器之前,由于她的动作太急骤,带倒了一张椅子。
(两个女工听到重物坠地声。)
白素只是注意那具仪器是否会损坏,一抛出垫子,立时扑了过去,在床上弹一下,再落下地来。
那个被她抛出的垫子,起了预期的作用。
她将那具仪器接住,看出仪器完好无损,十分高兴,立时把仪器放在床上。
这时,她在床边,张强在窗前,如果不是距离远,张强坠楼的惨剧或者可以阻止。
白素才放下了那仪器,站起身来,她看到房门打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工进来,同时,张强一个转身,冲向窗子。
张强冲向窗子的冲力极强,看起来他简直像是一头野牛。
白素自然看得出这样一下冲击的结果会怎样,所以她立时向前奔来。
白素还没有来到张强的身边,事情已经发生了。
张强的头先碰到玻璃,这一下,远不足以令得玻璃破裂,但是紧接着,他的肩头也撞到了玻璃。这一下,玻璃经不起撞击,破裂了。而张强向前冲的力道,还未曾中止,他整个人,就从被撞裂的玻璃之中,飞了出去。
白素完全被这意外震呆了,所以,那个管事,宝田满来到她身前,她的声音失常,只说了一句:“他──跳下去了。”
可是,宝田满和那两个女工,却异口同声,说张强是白素推下去的。他们的指证,高田警官向我详细地叙述过。
白素知道她根本什么也没有做,但是却有三个人指证她,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越快离去越好,宝田满当然抓她不住,她溜走了。
她在离开酒店之际,张强坠楼已被发现,大堂中十分乱,没有人注意她。
我紧握着白素的手,激动他说道:“你当然不会将张强推下楼去!”
白素望着我,神情像是在等待着我的发问。我陡然想了起来:“对,那副耳筒,那具仪器呢?为什么报上没有提起,连高田警官也完全不知道有这两样东西?”
白素道:“这是问题的重要关键,在我离开时,十分慌乱,静下来之后,立即想起,张强戴上了耳筒,就举止失常,当然和那具仪器有关,我非将那具仪器找回来不可。”
我吸了一口气:“你不是又回到现场去了吧?”
白素笑了一下:“正是,我略为化装了一下,又回到了现场,冒充记者,看到宝田管事正对高田警官指手画脚,在讲述我推张强下楼的事,可是仪器和耳筒却不在,我以为警方收起来了,可是稍一打听,就知道警方也没有发现。”
我道:“在你离开之后,警方到达之前,被人取走了。”
白素道:“当然是这样,这个人是谁?”
我连想也没想:“尾杉三郎。”
白素“嗯”地一声:“当时我也这样想,所以我才去见尾杉的情妇,想知道尾杉究竟在哪里,不得要领之后,我想尾杉可能在精神病院,于是──”
我笑了起来,在她脸上亲了一下:“于是你大闹银座,装疯入院。”
白素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是的,我在把那个护士长注射了麻醉针之后,就进入了尾杉的房间──”
白素轻而易举地弄开了病房的锁,她注意到,门上的小监视窗,从里面被遮住,看不到里面情形,所以她十分小心,一拉开门,立时闪身进去,作了应付突袭的准备。
可是病房内却没有什么异动,她看到有一个人,背向着外,躺在床上。白素向前走去,故意弄出脚步声来,床上那个人一动也不动。白素一直来到床边,定了定神:“尾杉先生,你好。”
床上那个人略为震动了一下,缓缓转过身来。白素看过尾杉三郎的相片,她一看就可以肯定,床上那人正是他,只不过看来比较瘦削。
尾杉看到白素,现出一个十分诡异的笑容,慢慢坐起身来:“你来得真快。”
他恶狠狠盯着白素,转过身去,一下子将一张毛毯拉开,毛毯下正是那具仪器。
她料得没有错,那具仪器到了尾杉的手中,那自然是白素逃走时,他趁人不觉,在混乱中取回来的。
张强坠楼时,尾杉一定也在酒店中。那么,张强的发生意外,是不是和他有关?
白素一想到这里,一股怒意陡然升起,她踏前一步,已经准备把尾杉拉过来,先给他吃一点小苦头,再逼问他究竟是在捣什么鬼。
可是,就在这时,尾杉已迅速地按下或转动那具仪器上的一些掣钮。白素也看到,那具仪器接上了电源,白素略停了一停,想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
然而,就在那一停之间,白素已经觉得事情不对头了。
白素说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喘起气来。
我忙问道:“怎么样?什么不对头?”
白素蹩着眉:“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当时的经历,我却记得十分清楚,就像那是真事。”
我呆了一呆:“你的意思是,突然之间,产生了幻觉?”
白素道:“我不能肯定,你听我说。”
她在讲了这句话之后,又顿了一顿,才道:“当时,突然之间,我的眼睛,就出现了一大片怪异之极的色彩。那色彩,绝不是实际上所能看到的,我像是一下子跌进了一个包罗了世界上所有颜色的万花筒之中,同时,我还感到那万花筒在旋转。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叫喊了起来。”
我忙道:“那一定是尾杉这家伙,趁你不觉,向你喷射了强烈的麻醉剂。”
白素道:“当然不是,有麻醉剂喷向我,我事先应该有感觉,但这种情形,突如其来,当时,我双手挥舞着,只想把那团色彩挥开,可是色彩却还在迅速地变幻,接着,色彩破裂了,自破裂的色彩之中,冒出了一个极可怕的怪物。”
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心中在想:这种情形,倒像是和吸了大麻,或是吞食了迷幻药之后的情形相类似。
白素的气息变得急促:“那怪物的样子,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是……那是一只似蛾非蛾的东西,可是所有花纹斑点,全是一个人的脸,是尾杉的脸,在狞笑,再接着,所有的脸都向我飞过来,我赶不开它们,它们把我包围住了。”
我大声道:“那当然是幻觉!”
白素闭上眼一会,又睁了开来,现出惊怖的神情──要白素现出这样的神情,那绝不是简单的事。
我伸手在她的手背上轻拍了两下,白素道:“事后,我也想到,那可能是幻觉,但是幻觉怎会那么实在?我甚至可以感到,那些脸撞在我的身上,有一种冰冷之感。”
我道:“你并没有受伤,是不是?”
白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突然一下子什么都不见了,我还在病房之中,但是病房中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自己,不,当我挥动着手的时候,低下头来的时候,我绝对看不到自己的身子,这只是一霎间的事,然后,你出现了,你奔过来,尾杉也突然出现了,我看到尾杉在逃,你把他抓起来。”
我闷哼了一声:“绝对是幻觉,那时候,我多半在飞机上。”
白素望了我一会,才沉声道:“我真的看到的,看得清清楚楚,你把尾杉抓起来,再摔下去,然后,用重手法砍他的后颈,他中了你一掌的神情,清楚得就在眼前,我真是看到的。”她一再强调:“真是看到的”,那使我感到一股寒意。
我心跳不由自主加剧:“那情形,就像酒店管事和两个女工,看到你推张强下去一样。”
白素隔了片刻,才道:“其实,尾杉也有他取死之道。”
我几乎直跳了起来:“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和白素在一起多年,我几乎从来也没有对她这样嚷叫过,但这时,我却忍不住大声叫嚷,因为看她的样子,像是真以为我打死了尾杉三郎!
白素对我的嚷叫,沉默了片刻,才现出十分苦涩的神情,缓缓地道:“你不能怪我,任何人,对于……亲眼看到的事,又清楚知道不是在做梦,总……总以为那是事实!”
我握着拳,又放了开来,再握上,尽量使自己心平气和:“可是其间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在。那三个酒店员工,亲眼看到你推张强下楼,但事实上,你并没有那样做。”
白素呆了片刻,才叹了一声:“那么,尾杉三郎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我又吃了一惊:“什么?你没有继续追踪他?”
白素向我望了一下,神情更加苦涩:“你听我说下去,当时,我看到你一掌砍在他颈骨之上,我还听得他颈骨折断的声音,我看到他的头,软垂了下来,你转过身,向我望来,我忙道:“你快走,这里的事,让我来处理好了。”你答应了一声,就离开了病房。”
我也只好苦笑着:“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怎么会离开。”
白素没有表示什么,只是挥了挥手,示意我不要打断她的话头:“你走了之后,我把尾杉搬上了床,拉起毯子来盖住他,他显然已经死了。我转身,再去找那副仪器时,却已经不见,我只好也离开了医院。”
我十分肯定地道:“这一切,实际上,都未曾发生过,只不过是你以为发生过。”
白素抿着嘴,不出声。她十分理智,可是这时,也显然受着极度困扰,不是身受者,实在是很难了解:连亲眼看到、亲身经历过的事,如果都“未曾发生过”,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发生过的?
这样的疑问,两千两百多年之前,庄周先生就曾不止一次提出,他甚至问到了他的一生,究竟是一只蝴蝶的幻觉呢?还是蝴蝶的一生,是他幻觉,他终于未能肯定。
为什么庄子不用其他的生命来怀疑,而用了蝴蝶?蝴蝶和蛾,不正是同类的生命么?
我越想越乱,我知道,这时候,我的思绪乱不要紧,但是决不能让白素的思绪乱下去。
所以我用十分肯定的声音道:“你一定要弄清楚,那一段经历,是你的脑部受了某种干扰之后的结果,是一场太过真实的梦。”
白素又呆了片刻:“太真实了,真是太真实了。”
我苦笑着,又发急:“你可以当作这是你在被催眠下发生的事。”
白素道:“不对,那是真正发生过的。”
我叹了一声,不知道该如何进一步说明,急得满头是汗,白素反倒安静了下来:“我知道自从我眼前看到奇异的色彩,一直到后来发觉我自己在街头上,其间一切,我以为发生过的事,全是幻觉。”
我松了一口气:“对。”
白素睁大了眼睛:“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内,实在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道:“那要问尾杉三郎这……家伙才知道。你说什么?后来你发觉自己在街上?
”
白素缓缓地道:“是的,我记得在病房之中,找了又找,找不到那具仪器,心想不如把你找来,我们一起寻找,就离开了医院。那一段时间,我记忆之中,比较模糊。等有记忆时,我在街头,有两个警员,正以十分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我失声道:“天,你是受通缉的啊!”
白素摊了摊手:“是啊,所以我一看到警员注意我,立即转身就走。我没有地方好去,想起曾在芳子的记事簿中,看到过一个地址,我找来,就是弥子的住所。我不知道如何和你联络,就只好仍然打电话回去,希望你听到。”
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安慰着她,因为白素从来也未曾如此慌乱过:“好了,一切全过去了。”
白素也吁了一口气:“不,尾杉还在,还有他的那个仪器,还有我的凶嫌,还有许多事。”
我“哼”地一声:“凭我们两个人的本事,那怕尾杉躲到天上去,也可以把他找出来。”
白素却仍然叹着:“找出他来之后──”
我知道白素的心意,是说就算我们找到了尾杉,如果再发生如同在精神病院病房中的情形,那只有使得事情更混乱。
所以,我想了一想:“尾杉未必见得有什么特别,我看一切全是那具仪器在作怪,只要我们把他和那具仪器隔离──”
白素一扬手:“对。”
她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突然蹙住了眉,不再说下去。
我道:“我们已经有了对付尾杉的方法,还有什么担心的?”
白素仍在想着,过了一会,她才道:“我不是担心,我是在想一些事……我感到所有……不可解释的事,都可以用一条线穿起来。”
白素的话,深得我心,我也已经有了这样的感觉,可是感觉却还十分模糊,我正在思索着,所以我对白素的回答,只是点了点头,同时作了一个手势,表示我也想到了一些头绪,正在作进一步的思索。
白素没有再说什么,我们两人,各想各的,过了大约三五分钟,我和她陡然异口同声,叫了起来:“那个蛾类研究所。”
我和白素,都想到了安普蛾类研究所。
我抢着说:“安普蛾类研究所,看起来和所有的事全没关连,但是事实上,却正是问题的中心。”
白素立时道:“是,一切全从那里开始。”
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让我先来归纳一下,你来作补充。”
白素一面答应着,一面拿过了纸和笔来。我道:“第一件事,研究所中,有一个姓洪的人,他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一只飞蛾。”
白素记了下来。我又道:“第二,陈岛是研究所的主持人,他和尾杉是中学同学,曾在好几年之前,和尾杉提及过他所作的研究,告诉尾杉,在理论上,要知道他人在想什么,是有可能的。”
白素“嗯”地一声,补充道:“对陈岛而言,这是他作为科学家的假设,他正朝着这个方向作研究。可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尾杉听了之后,一直在想着可以知道他人思想的好处,于是他就展开了行动。他十分卑鄙,而且他的知识,也不足以从事那么复杂的科学研究,所以他就──”
我立时接了上去,和白素一起思索复杂的问题,真是无上的乐趣,我想到什么,她也想到什么,配合得再好也没有。
我道:“所以他就采用了最直接的方法,花钱向研究所的人员,购买研究的成果。”
白素点头,一面记着,一面道:“我在尾杉住所见到的那两个人,就是被尾杉收卖的人,他们送资料来给尾杉,已不止一次。”
我道:“还有那具仪器,一定也从那两个人手中来的,尾杉自己造不出这样的东西,外间也未必见得有得卖这样的东西。”
白素把我的话写了下来之后,眉心打着结:“我们的推测,到这里要触礁了。”
我不服气:“触什么礁?”
白素道:“如果再分析下去,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尾杉在有了那些资料之后,通过那具仪器,他似乎掌握了一种力量,真的可以知道他人在想些什么。”
我苦笑了一下:“听起来全然不之后理,可是……可是……事实就是这样。而且…
…我们的礁石,好像还不止这一块?”
白素道:“是啊,尾杉不但有知道他人想什么的力量,而且还明显地可以用那具仪器,去干扰他人脑部活动──”
白素讲到这里,我陡地闪过了一个想法,忙叫道:“等一等。”
白素不再出声,我不由自主,敲着自己的头,想把刹那间捕捉到的想法具体化起来,我只花了短短的时间,就高兴地叫了起来:“那具仪器!不是尾杉利用了那具仪器,而是那具仪器本身。”
白素一时之间,未能明白我的意思,我急急解释着“你和张强,研究那具仪器,发生了什么事?”
白素道:“张强穿破了窗子跳下去,而另外有三个人,却“看”到他是被我推下去的。”
我大声道:“那时,尾杉可能也在酒店,但是他绝未操纵那仪器!那仪器有一种力量,能使人产生幻觉,如果配上耳筒,直接刺激脑部,幻觉就可能更加强烈,张强就是因为产生了极度的幻觉,才有反常行动。而三个酒店职工,也因为脑部活动受干扰,所以才“看”到了你在推张强。”
白素默然片刻,从她的神情上,我知道她已经同意了我的分析。
但是,她却极度茫然:“张强在那一霎间,产生了什么幻觉呢?”
我苦笑了一下:“张强已经死了,不会再有人知道。或许,他感到自己会飞了,可以穿窗而出,在空中自由飞翔,所以才……”想起了张强的死,我心中一阵难过,停了一下,才又道:“这种情形,曾在服食过量的迷幻药的人身上发生过。”
白素苦笑了一下:“我忽然有一个极其怪异的想法──真是太怪异了。”
我摊手:“怪异到了什么程度?”
白素望着我:“我想,张强可能觉得自己是一只蛾,蛾喜欢向着光亮飞扑,所以,他就扑向窗子,结果他就──他就──”
白素没有再说下去,她的想法,真是怪异透顶,但是谁又能肯定那不是事实?
我和白素都静了片刻,我才道:“总之,那具仪器和尾杉获得的资料,有一定的神异力量,可以干涉人类脑部活动。”
白素“嗯”地一声:“我们可以继续下去:这种力量,有时帮助了尾杉在棋赛中获胜。”
我用力挥了一下手:“所以,尾杉把这种力量,我相信他其实也不是太能顺利地掌握这种力量,当作自己最大的秘密,而倒霉的时造旨人,却开玩笑地把它写了出来。”
白素苦笑:“真是倒霉,时造全然不知道这些事,尾杉一发急,就要杀时造,逼得时造离开日本,时造不能在镜中看到自己,自然也是脑部活动受干扰的结果,干扰的来源相同。”
我接着道:“时造倒也十分聪明,他由尾杉的行动上,联想到尾杉真可能有妖异的力量,所以他把这一切,告诉了张强──”
讲到这里,我陡然停止,白素也没有接口,因为张强在知道之后,就来找我,以后的事,都已经发生过了。
我叹了一声:“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何以那具仪器,会有这样的力量。”
白素沉声道:“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可以回答──”
我陡地叫了起来:“陈岛。”
陈岛是研究所的主持人,只要我们的推测不错,那具仪器来自研究所,那么,这个问题也只有陈岛可以回答。
而且,在飞机上,和陈岛交谈,他一直要我到他的研究所去看看,看什么呢?他又说不上来。是不是在他的研究所中,正有着一些连他也不知道的事情发生?
想到这里,我不禁大是懊丧,陈岛在东京,可是他在东京哪里呢?他当然会住酒店,但是会在哪一家?我竟然没有问他要联络的方法,就和他分了手。
白素看出了我的懊丧,她道:“不要紧,就算在这里找不到陈岛,他不是还要去接那个姓洪的研究员出院么?我们可以立即和梁医生联络,叫她留住陈岛,我们赶回去见他。”
我连连点头,伸手去拿电话,我的手还未曾碰到电话,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我呆了一呆,这里是弥子的住所,电话不知是谁打来的,要是她的男朋友打来的话,我接听电话,可能会引起误会。
所以我侧了侧身,让白素去接电话,白素拿起了电话来,才“喂”了一声,对方讲话十分大声,连在旁边的我,也可以听到,话筒中传出了一个女的声音:“是白小姐吗?我是弥子啊。”
白素答应了一声,弥子的声音继续传来:“你有没有听收音机?”
白素呆了一下,显然不知道弥子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她回答:“没有啊,什么事?
”
弥子道:“我刚才听收音机的新闻报告,说是在东京北部五十公里处的茨城县,筑波郡,山中的一个溪涧间,发现了一具男子的尸体,已经证实那是你曾经提及过的,九段棋手尾杉三郎。”
我和白素,在刹那之间,神情都变得极其紧张,白素忙道:“弥子,请你再说一遍。”
弥子又重复了一遍:“这样的新闻,电视一定会报导的,你可以看看电视。”
白素向她道了谢,放下了电话,我们互望着,神情都十分疑惑。
尾杉三郎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才分析过,所有的事,全是由他而起的,他怎么会死了?
白素扭开了电视,还没有到新闻播映的时间,白素打电话去问,要二十多分钟之后,我就趁这个时间,用电话找到了梁若水。
梁若水的声音,在长途电话中听来,也是那样充满磁性,十分动听,我道:“梁医生,还记得那个叫陈岛的人?”
梁若水的回答很令我惊讶,她道:“本来可能不记得了,但现在一定记得,因为在半小时之前,他才和我通过了电话。”
我“哦”地一声,梁若水又道:“他告诉我,他抽空到日本去看一个朋友,但是找不到,他决定立刻回来,要我准备好手续,他一到,就要把他的朋友带走。”
我忙道:“我有极重要的事要找他。梁医生,所有怪异的事,已经渐的眉目,其中的关键问题,只有他可以解答。所以你见了他之后,无论如何你要留住他,等我回来见他。”
梁若水停了片刻,我可以想像得出她蹙着眉的那种神情,她道:“我尽力而为,但如果他一定要离去,我也没有法子。”
我道:“至少你可以运用你的权力,不让那病人出院,那他就非留下来和你办交涉不可。”
梁若水的声音之中,充满了不以为然,但是她却道:“这是好办法,卫先生。”
我苦笑了一下:“谢谢你,我和他同机到东京来的,可是却不他知道在哪里,真是糟糕透了。”
梁若水的声音听来很低:“好吧,我尽力。”
我松了一口气,这样,我和陈岛的联系,就不至于中断了。
放下电话之后不久,电视上就开始播映新闻,果然,第一宗就是尾杉九段陈尸山涧的新闻。日本的新闻工作者,有着超水准的工作成绩,他们总是第一时间赶到新闻发生的现场,所以,连尸体被抬上黑箱车的镜头,都出现在萤光屏上。
新闻十分详尽,不断打出尾杉生前的相片,并且还特地提到了大黑英子,说是尸体运到了东京之后,一位叫高田的警官,认出那可能是尾杉九段,所以就请尾杉生前的女友大黑英子来辩认,大黑英子认出那是尾杉三郎,而且,精神病院方面,也因为尾杉突然失踪,早已向警方报了案。
至于尾杉三郎何以会死在山洞中,可能是由于失足之故,因为现场的山势十分险峻──
萤光幕上,出现了现场的情景,那道山涧,简直像是瀑布,水势十分湍急,水中有许多巨大的石块,涧水流过,溅起老高的水花。
一个记者指着涧中突起的两块大石:“尸体就在这里发现,可能由上流冲下来。如果不是这里有两块大石阻止,可能会随着急流,不知被冲到什么地方去。”
那记者继续报导着:“警方人员循着涧流,向上面搜索,希望发现一些尾杉三郎跌入山涧前的遗物,但是还没有发现。”
涧流附近,全是树木和石块,野草长得极高,要找东西,确非易事。
然后,萤光幕上,又出现了殓房门口的情形,说是消息传出之后,有不少棋迷,在殓房前徘徊凭吊云云。等到新闻播完,我闷哼了一声:“尾杉真的死了?我不相信。我要到殓房去看看。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离开日本。”
白素说得十分正经:“我不想变成通缉犯。”
我苦笑了一下,白素的这个麻烦问题我想了很久,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来。我们要偷离日本,当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绝不是一走可以就此了事。
她是一个有着确凿证据的谋杀疑犯,这一类的刑事疑犯,通过引渡,一样逃不掉,除非白素从此不再露面,但是那又绝无可能。
虽然我们对于一切事,已经有了一个系统的解释,我们可以接受这个解释,甚至,我可以说服高田警官相信这个解释。但是……
或者再进一步说,可以令得主控官或是主审法官在私下也相信。但是,我却绝对无法令得他们在法庭上接受这个解释,不但我不能,连白素也不能。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几乎可以做任何事,但无法使白素无罪。
我眉心打着结,一时之间,想不出办法,只好安慰白素:“反正你暂时在这里,相当安全,我看,慢慢总可以想出办法来的。”
白素瞪了我一眼,撇了撇嘴:“神通广大的卫斯理。”
我实在啼笑皆非,说道:“彼此彼此,谁又不知道神通广大的白素。”
白素叹了一口气,她显然没有心情笑话,我又说了几句“一定有办法”之类的说话,可是办法在哪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我知道白素自己会小心,不必叮嘱,先打开门来看了看,看到走廊里没有人,才闪身走了出去。在街上召了一辆计程车,告诉司机去殓房去。不巧,那位司机是个棋迷,一听我要去殓房,就猜中我是为了尾杉三郎去的,滔滔不绝和我谈起他的棋艺,令得我昏然欲睡。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殓房外的人还真不少,我一下车,就看到高田警官正指挥着几个警员在维持秩序,大声在嚷着:“各位,等出殡的时候,去瞻仰尾杉先生的遗容。
各位请回去,请回去。”
他的声音已经有点发哑,在他身边,又有好几个记者围着,趁机在提出问题。高田虽然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可是也不敢得罪新闻界,还是敷衍着他们。
我向他走去,挤过了人丛,在隔他还有几个人时,就叫:“高田先生。”
高田抬起头来,一看到我,陡然呆了一呆,忙向我招了招手,我来到了他的身边,他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来,进去再说。”
我和他一起走了进去,有几个人想跟进来,被警员阻在外面,我和高田,一进了殓房,高田立时道:“尾杉死了。”
我道:“就是为看他的尸体而来的,这个人的花样极多,他真的死了?”
高田神情凝重,点了点头:“虽然没有人知道他怎样死的,可是尊夫人的嫌疑,又多了一重。”
我一怔,要想一想才明白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他竟然在怀疑尾杉三郎被白素杀死,难怪他看到我的时候,神情那么古怪,我一句“放你妈的春秋大屁”已经几乎要骂出口来了,后来转念一想,日本人根本不懂得复杂的骂人话。一句“农协”已经可以令得两个日本人大打出手,高田听了不懂,我还得向他解释,不如不骂算了。
高田望着我,我改口道:“你少胡说八道。”
高田叹了一声:“尊夫人装疯,我也瞒不过去了,而且,有人看到她扮了护士长,在尾杉的病房出入,接着,她和尾杉一起失踪,再接着,尾杉的尸体就在茨城县的山涧中被发现。”
我苦笑:“事情的复杂,超乎你的想像之外,我要看尸体。”
高田愕然:“尾杉生前,你见过他?”
我道:“没有,但是我看过他生前很多相片,对于认人的特徵,有一定的本领。”
高田摇着头:“其实大可不必了,连指纹都已经经过了鉴定,已经肯定了。”
我固执地道:“我还是要去看一看。”
高田扭不过我,只好叹了一口气,带着我向前走去,进了殓房中放尸体的冷藏室,一股寒意,令人有说不出来的不舒服。
一个职员和高田交谈了几句,又向我望了一眼,拉开了一个铁箱。一点也不错,那是尾杉三朗,看起来,他真的是死了。
尾杉三郎是整组怪事的中心人物,他怎么会死,真叫人猜不透。我看了一回,转过身来问高田:“听说警方在搜索他的遗物,可有什么发现?”
高田皱着眉,道:“事情有点不可思议,在那山洞的上游,一块大石上,发现了一具被砸碎了的小型电视机,已经残缺不全,但经过辨认,还可以知道那是一具小型电视机。”
我立即知道,那被砸碎了的,不是小型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