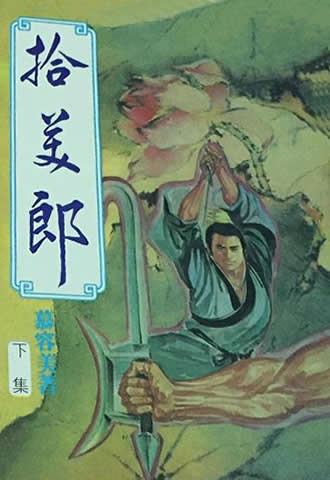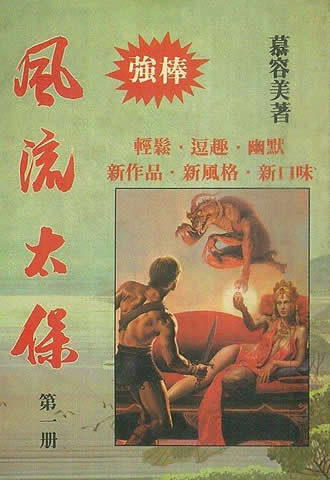我定了定神,开始看那册子上所记载的一切。那的确是一本日记,记载着大约三个月之间的事。等到我看完了这本册子之后,已经是将近午夜时分,我合上册子,将手放在册子上,呆呆地坐着,心头的骇异,难以形容。
就算我能够将心头的骇异形容出来,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倒不如将那本册子的内容介绍出来的好。
册子中所写的字极多,超过二十万字,最好,当然是原原本本将之抄下来,但是有许多,是和这个故事没关系的,而且,记载的人,也写得十分凌乱,还夹杂着许多时事,用的又是很多年前,半文不白的那种文体,看起来相当吃力。
所以,我整理一遍,将其中主要的部分,介绍出来,其它的略而不提。而且,一些专门名词,我也用现代人所能了解的名词来替代,以求容易阅读。
写日记的人,名字叫林玉声。我相信这位林玉声先生,一定是林子渊的祖先,可能是他的祖父,或者曾祖父,等等。
林玉声是太平军的一个高级军官,在日记中看来,他的职位,相当于如今军队中的一个师的参谋长。他的军队,隶属于忠王李秀成的部下。日记开始,是公元一八六○年(清咸丰十年),三月。这时,已经是太平天国步向灭亡的开始了。
三月,曾国藩的湘军,已经收复武汉、九江。向北进兵的太平军,又被僧格林沁打得大败,但是太平军还保有南京,在江苏、安徽一带,还全是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军队的数量也不少。
当时的形势是,清廷在南京附近屯兵,由向荣指挥,称江南大营,在扬州附近屯兵,由琦善指挥,称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的战斗对象是太平军的李秀成,江北大营的敌对方面,是太平军的陈玉成。
林玉声,就是李秀成麾下的一名高级军官,他的日记,也就是在如何与向荣的江南大营血战开始,其中的经过,写得十分详尽,两军的进退、攻击,甚至每一个小战役,都有详尽的记载。这些,当然是研究太平军和清军末期交战的好资料,但是对本篇故事,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只是约略一提就算。
真正有关系的是在四月初八那一天开始。那一天,林玉声的日记中记着如下的事件(我将之翻译成白话文,仍保留林玉声的第一人称)!
忠王召见,召见的地点在军中大帐,当时我军在萧县以北,连胜数仗,俘向荣部下多人,有降者,已编入部队,其中满籍军官三十七人,被铁炼锁在一起,扣在军中,拟一起斩首,忠王召见,想来是为了此事。
及至进帐,忠王屏退左右,神情似颇为难,徘徊踱步良久,才问道:“你看天国的前途如何?”我答道:“击破江北大营,可以趁机北上,与北面被围困的部队会合,打开新局面。”
忠王苦笑:“怕只怕南京城里不稳!”我闻言默然。天王在南京,日渐不得人心,虽在军中,也有所闻,但不便置喙。
忠王又问:“如果兵败,又当如何?”我答道:“当率死士,保护忠王安全!”忠王长叹:“但愿兵荒马乱之后,可以作一富家翁,于愿足矣!”我不作答,因不知忠王心意究竟如何。
忠王又徘徊良久,才道:“玉声,你可能为我做一件事?”
我答:“愿意效劳!”
忠王凝视我半晌,突然大声叫道:“来人!”一名小队长,带领十六名士兵进帐来,我认得这十七人,是忠王的近身侍卫,全是极善斗之人。忠王等他们进来之后,指着我道:“自现在起,你们拨归玉声指挥,任何命令,不得有误!”
全体十七人都答应着,忠王又挥手令他们出去,然后取出一幅地图来,摊开,置于案上,指着地图一处:“这里叫做猫爪坳,离我们扎营处,只有四里,翻过两座山头可到!”
我细审地圃,心中疑惑,因为这小山坳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于行军决战,毫无用处,不知忠王何以提及。
忠王直视我,目光炯炯。忠王每当有大事决定,皆有这种神情,我心中为之一凛,心知忠王适才要我为他办的事,决非寻常。
忠王视我良久,才道:“玉声,你是我唯一可以信托之人。”
我忙道:“不论事情何等艰难,当尽力而为。”
忠王道:“好。”随即转身,在一木柜之中,取出一件东西,那是一只径可五寸,长约三尺的圆筒,两端密封,筒为铁铸。
我看了不禁大奇,因从未在军中得睹此物,于是问:“这是什么?洋鬼子的新武器?”
因为这时,有洋鬼子助清廷,与我军对抗,是以才有此一问。
忠王笑道:“不是,这铁筒内,全是我历年来,在戎马之中所得的财宝。”
我闻言,大吃一惊。忠王戎马已久,转战南北,率军所过之处,皆东南富庶之地。
军中将领,莫不趁机劫掠,贤者不免。为讨好上峰,颇多择其中精良罕见的宝物,价值连城者,奉献上峰。忠王位高,又素得部下爱戴,可知此一圆筒之中,所藏的宝物,一定价值连城,非同小可。
我面上色变,忠王已洞察:“玉声,这筒中,有珍珠、翡翠、金刚钻,颇多稀世之宝,我曾粗略估计,约值银三百万两之谱!”
我不禁吸气:“如此,则兵荒马乱之后,岂止一富家翁而已!”
忠王笑,神情苦涩。我道:“若是要我找人妥为保管这批宝物--”
忠王挥手,截断我话头:“不然,我已找到一妥善地方,收藏此物!”
我恍然大悟:“在猫爪坳?”
忠王点头道:“是。月前我巡视地形,经过该处,发现某地甚为隐秘,古木参天,我已想好收藏这批宝物的方法,找其中一株大树,以极精巧之方法,将树心挖空,然后将圆筒插入树心之内,再将挖伤之处,填以他株树上剖下之树干,用水苔、泥土包扎--”
忠王讲到此处,我已明白,击案道:“好方法,不消一年,填补上去的树干,会和原干生长吻合,外观决不能觉察!”
忠王笑道:“是,而原树一直长大,宝物在树心之内,绝无人知!”
忠王讲到“绝无人知”之际,我心中已暗觉不妙。此事,他知、我知,而且非一人可办,何得谓绝无人知?然而当时又未暇细想。
忠王又道:“玉声,我派你带适才一队士兵前往,不可告知任何人,去办此事。办完之后,更不可对任何人提及。不幸兵败,取宝藏,远走高飞,当与你分享!”
忠王语意诚恳,我听了不胜感动惶惑,忙答道:“愿侍候王爷一生!”
忠王笑拍我肩,将有关猫爪坳之地形图交予,嘱明日一早行事,出发之前,先到他帐中,取收储宝物之圆筒。忠王虽曾一再叮嘱,不可将此事与任何人提及,但我向有日记之习惯,是以归营之后,将与忠王之对话,详细记载,或有后人观之,我固未曾与任何人提及也。
(才在册子上看到这一段记载,我心中已经骇然。原来林子渊的上代,在太平军的地位相当高,而且,曾替忠王李秀成进行这样一件秘密的藏宝任务!)
(林玉声在日记中提到的那个圆筒中宝物,忠王自己的估计,是“约值三百万两”
,这真是骇人听闻。当年约三百万两,是如今的多少?而且,近一百年来,稀有珍宝的价值飞涨,这批宝藏,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财富!)
(我想,林子渊一定为了这批珍宝,所以才动身到萧县去的。)
(我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是当我再向下看那本册子中所记载的事情时,我发现,这种想法,就算是对的,也不过对了一部分。)
(林子渊到萧县去,那批珍宝,只是原因之一,因为后来事情发展下去,有更怪诞而不可思议的事在!)
(让我们再来看林玉声当年的日记。那是他和忠王对话之后第二天记下的。)
昨宵,一夜未眠,转辗思量,深觉我军前途黯淡,连忠王也预作退计,我该当如何,实令人浩叹。
往忠王帐,兵士与小队长均在帐外,进帐,忠王将圆筒交予,在铁筒外,裹以黄旗一面。我接过,忠王又郑重付托,说道:“玉声,此事,你知、我知而已。”
我道:“帐外十七人--”
我语未毕,忠王已作手势,语言极低:“帐外十七人,我自有裁处,你可不必过问。”
我听忠王如此言,心中一凉,已知忠王有灭口之意,但骇然之情,不敢外露,免遭忠王之疑,只是随口答应:“如此最好。”
忠王送出帐来,队长已牵马相候,我与队长骑马,十六名士兵,八人一队,列两队前进。
一路上,我和队长闲谈,得知队长张姓,江苏高邮人,沉默寡言,外貌恭顺,但我察知其人阴骘深沉。然此际共同进退,绝未料到会巨变陡生。
自军营行出里许,略歇,停息于山脚下一处空地之中,士兵略进乾粮,我不觉饥饿,但饮清水。于其时,我问队长:“忠王所委的事,你必已经知道?”
出乎预料之外,队长答:“不知,王爷吩咐,只听林六爷令。”
我不禁略怔,由此看来,忠王真是诚心托忖,当我是亲信。当时,知遇之感,油然而生。队长也不再问,我道:“到达目的地之后,自当告知!”
休息片刻,继续前进,进入地图所载之猫爪坳之范围,且已圈中其中一株树木,按图索骥,来至树前,随行士兵,多带利器,剖树挖孔,甚易进行。
至天将黑,树心已挖空,我抖开黄旗,将圆筒取出,置于树心之中,再在它树剖取一截树干,填入空隙,裹以湿泥,明月当空。
队长及众士兵,在工作期间,一言未发,当我后退几步,观察该树,发现已不负所托之际,长吁道:“总算完成了!”
队长面上,略现讶异之色:“没有别事?”
我道:“是,这事,王爷郑重托付,不可对任何人提及,你要小心!”
队长道:“是,是,我知道这事,一定极其隐秘--”
队长说到此际,月色之下,隐见他眉心跳动,神情极度有异,我忙道:“王爷派你跟我来办事,足见信任,要好自为之。”
队长答应一声:“林公,我蒙王爷不次提拔,始有今日,王爷若有任何命令,自当一体遵行!”
我尚不以为意:“自然应当加此!”
我话才出口,队长陡地霍然拔刀出鞘。月色之下钢刀精光耀目,我见刀刃向我,不禁大惊,竟张口无声,队长疾声道:“林公,此是忠王密令,你在九泉之下,可别怪我!”
队长疾喝甫毕,刀风霍然,精光耀目,我急忙转身,待要逃避,但背上已经一阵剧痛,我在剧痛之中,扑向树身,双臂紧抱树干,身子也紧贴在树干上,但觉得背上剧痛,身子像已裂成两半,眼前发黑,耳际轰鸣。所想到唯一之事,是我命休矣!忠王竟先杀我灭口,枭雄行事,果异于常人!
我一想到此际,已然全无知觉,但奇在倏忽之间,眼前光明,痛苦全消,身轻如无物,心静若悟禅。最奇者,眼前景物,历历在目,但竟不知由何而视。耳畔声响,一一可闻,但也不知是何而闻。首先看到者,是我自己,仍紧抱于树干之上,背后血如泉涌,神情痛苦莫名,其时,我只觉得心中好笑,根本无痛苦,何必如此神情痛楚?
继而,听到惨呼声不绝,旋又看到,十六名士兵,八人一队,正在呼喝惨斗,其中八名,旋即倒地,有扭曲者,有负伤爬行者,血及污泥交染,可怖之极,无异阿修罗地狱,惨叫之声,惊心动魄。
尚余之士兵,仍在狠斗,长刀飞舞,不片刻,一一倒地,只余队长一人,持刀挺立。
我看到队长来到众士兵之前,一一检视,见尚有余气未断者,立时补戮一刀,直至十六名士兵尽皆伏尸地上,队长向我抱在树上的身体走来,扬刀作势欲砍,但扬起刀后,神情犹豫,终于长叹一声,垂下刀来,喃喃道:“上命若此,林公莫怪!”
我听得他如此说,又见他转身,在鞋底抹拭刀上之血迹,心知他回营之后,必遭忠王灭口,想出言警告,但竟有口不能言,而直到此际,我才发现自己,有口乎?无口乎?不但无言,亦且无身,我自己之身,犹紧抱在树干之上,但我此际,分明已超然于身躯之外,与身躯已一无关系可言,直到此时,我方明白:我已死!我已死!魂魄已离躯壳,我已死!
(当我看林玉声的日记,看到这里之际,实在骇异莫名。说不定是心理作用,我竟觉得酒店房中的灯光,也黯淡了许多!)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第一个直接的反应,是逻辑性的:林玉声既然“已经死了”,如何还会将他的经历写下来?在册子上所写的文字来看,笔迹一致,分明是一个人所写的。如果说他死了之后还会执笔写字,当然不可能。)
(其次,我感到震惊的是,林玉声在记述他“已死了”的情形时,用的字句,十分玄妙,他说自己没有口,没有眼,没有耳,连身子也没有,但是,他却一样可以听,可以看,而且还可以想!)
(我的手心不由自主在冒汗,我看到这里,将手按在册子上,由于所出的手汗实在太多,所以,当我的手提起来之际,册子上竟出现一个湿的手印!)
(我定了定神,我知道再看下去,一定还可以接触到最玄妙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真要好好镇定一下,才能继续看下去。)
(林玉声写在册子上的“日记”,继续记述着以后所发生的事。)
我已死!魂魄已离体,想大叫,但无声。目睹队长离去,欲追队长,但发现不能移动。也非绝不能移动,我自觉可以动,可以上升,可以下沉。
可以左、右横移,但移动不能超越大树树枝的范围。
可以一直移至大树最高的树梢之上,望到远处,望见队长在离去之际,开始尚一步一回头,神情极痛苦茫然,但随即走出山坳之外。
我又下沉,沉到自己的身体之前,犹可见自己痛苦扭曲之脸,紧贴于树干之上。
至此,我更恍然大悟,我之魄魂,离开身躯之后,已进入大树之中,依附于大树,不能离开大树范围之外,我在大树之中!
我实在不愿在大树之中,更不知此事如何了局,我竭力想叫唤,但自己也听不见自己发出之声音,我竭力挣扎,想脱出大树之范围。
我无法记忆挣扎了多久,事后,一再追忆,恍然若噩梦,只有片段感觉,清楚在忆,其余,散乱不堪。我只忆及在挣扎之间,陡然眼前剧黑,背部又是阵阵剧痛,张口大叫,已可闻自己之声,背部剧痛攻心,令我全身发抖,张眼,见树皮在眼前,低头,见双手紧抱树身,我竟又回到了自己躯壳之内!
背后之剧痛,实难忍受,我大声呻吟,甚盼再如刚才之解脱,但已不可得,剧痛继续。幸久历军伍,知伤残急救之法,勉力撕开衣服,喘息如牛,汗出如浆,待至紧扎住背后的伤口,已倒地不起,气若游丝。
当时,唯一愿望,是再度死亡,即使魂魄未能自由,千年万年,在所不计,适在片刻之间,眼前光明,痛苦全消之境地,犹如亲历,较诸如今,满身血汗,痛苦呻吟,不可同日而语。虽夭死可怨,我宁死勿生,生而痛苦,何如死而解脱!
我已知人死之后,确有魂魄可离体而存,又何吝一死?但此际,求死而不可得,痛苦昏绝,及至再醒,星月在目,已至深夜。
我不知何以会死而复苏,想是张队长下手之际,不够狠重,一刀之后,猝然而亡,魂魄离躯,但心肺要脉未绝,又至重生。或是由于我当时竭力想挣扎离开树中,以致重又进入躯壳之中,是则真多此一举矣。
醒转之后,难忍痛楚,重又昏绝,昏后又醒,醒后又昏,一日夜之中,昏绝数次,每当醒转之际,剧痛攻心,口乾舌燥,痛苦莫名,直至次日黄昏时分,在大声呻吟之中,才挣扎站起,倚树喘息。
我魂魄何以会进入大树之中,真正难明,其时,只盼魂魄能再离躯,思索若其伤重不治,又可解脱,内心稍觉安慰,但当日中午,适有樵夫经过,骤见遍地尸体,大惊失色,继闻我呻吟声,将我扶住,又召来同伴,将我抬出三里之外。
十日之后,伤已大有起色,可以步行,削树为杖,持杖告别樵民,回至营地,大军已拔营而起,唯我所住的营帐还在,想是忠王心有所愧,未敢擅动。进帐之后坐定,帐内物件,一一还在,无一或缺,人言“恍若隔世”,我是真如隔世矣!
大军虽起行,但尚留下不少食物,在帐中,独自又过一月有余,伤已痊愈,背镜自顾,背后伤痕,长达尺许,可怕之极。
帐中养伤,早已想定,一旦伤愈,自然不能再从行伍,当急流勇退,而忠王对我不仁,我也对他不义,树中宝藏,自当据为己有!
伤痊愈之后,再依图前往猫爪坳,十六名士兵尸体,已成白骨,大树兀立,拆开包裹之湿泥,补上之树干,已与被挖处略见吻合,正以随身小刀,待将填补之树身取出来之际,奇事又生!
小刀才插入隙缝之中,身子突向前倾,撞于树干之上,俄顷之间,又重睹自身,满面贪欲,油汗涔涔,正在缓缓下倒。
于此一刹那间,我明白自己重又离魂,但我固未受任何袭击,身躯虽在向下倒去,绝无伤痕。如今情形,正是我一月余前,伤重痛苦、呻吟转辗之间想求而不可得之境地,今又突然得之,一时之间,真不知是喜是悲,不知是留于树中,还是挣扎回身躯之内。
也就在此时电光石火,一刹那之间,我已明白,不禁大笑,虽未能闻自己笑声,但内心欢愉,莫可名状,古人有霎时悟道者,心境当与我此时相同。
我已明白,魂魄在树,魂魄在身,实是一而二,二而一,并无不同。魂魄在树,可见可闻,魂魄在身,情形一致无二,何必拘泥不化,只要魂魄常存,树干即身躯,身躯即树干。
我内心平静欢愉,活泼宁谧之间,忽又觉山风急疾,倒地之身,又重挺立,眼前已是树而不是身,开口闻声,则魂灵归来,重复我身。
有适才之悟,财宝于我,已如浮云,满眼白骨,一地落叶,无一不是我躯,又何必拘泥?肉躯多不过百年,古树多不过千年,何物依附,才至于万万年不绝?世上无物可致永恒,永恒在于无形,得悟此理,已至于不灭之境矣!
飘然而离,于我而言,已无可眷恋之物!
林玉声的“日记”,最主要的部分,如上述。
而当我看到了他在日记中记载的一切之后,心中的感觉,真是难以形容。
林玉声在由死到生,由生到死之中,悟透了人生不能永恒,躯体不能长生存的道理。任何人,在经历过巨大的剧变之后,多少可以悟点道理,何况是生死大关!但是,他记载着,他的“魂魄”,曾两度进入大树之中,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魂魄”是林玉声日记中用的原文,这是中国传统的说法。较现代的说法,是“灵魂”。
从林玉声的记载中看来,他肯定了人有灵魂的存在。灵魂离体之后:“有口乎?无口乎?”或者说:“有形乎?无形乎?”根本已无形无体,但是,为什么会进入树中呢?
林玉声记载中,有不明不白的地力,就是,在进入树干之后的他的灵魂,照他记载的,是可以在树内自由活动,上至树梢,下至树根,但是脱不出树伸展的范围之外。
这样说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树,就是他的身体。那么,是不是这时候若有人伐树,他会感到疼痛?
林玉声没有说及这一点,当然,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当时只有他一人,并没有人在这时在树上砍一刀或是折断一根树枝,使他可以“有感觉”。
还有我不明白的是,当时,一起死去的,除了林玉声之外,还有十六名士兵。
这十六名士兵的情形,又如何呢?他们的灵魂又到哪里去了?是进入了附近的树中,还是进入了其它什么东西之中?
何以灵魂可以进入其它东西之中?中国古时的传说,虽然常有“孤魂野鬼,依附草木”之说,但是林玉声的记载中那样具体的,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
我呆呆地想着,心里难怪计四叔看了之后,除了“我不相信”、“我不明白”之外,根本没有别的话可说。这时,如果有人问我,我的感想怎样,相信除了这八个字外,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呆了很久,林玉声的日记还没有完,我再继续向下面看去。
以后的一切,全是说他如何定居之后的情形,都十分简单,显然是他已真正感到,人生百年,如过眼烟云,连他自己的婚事,也只有六个字的记载:“娶妻,未能免俗。
”
一直到最后一部分,看来好像是另外加上去的,纸质略有不同。
这几页之中,记载着林玉声一生之中,最后几天的事情,我再将之介绍出来:“年事已老,体力日衰,躯壳可用之日无多矣。近半年来,用尽方法,想使魂魄离体,但并不能成功,曾试独自静坐四日夜,饿至只存一息,腹部痛如刀割,全身虚浮,但总不能如愿。
曾想自尽,自尽在我而言,轻而易举,绝无留恋残躯之意。但弃却残躯之后,是否魂魄可以自由?若万一不能,又当如何?思之再三,唯一办法,是再赴旧地。
我魂魄曾两度进入一株大树,在大树之中留存。当时情景,回想之际,虽不如意,但树龄千年,胜于残躯,或可逐渐悟出自由来去,永存不灭之道。
世事无可牵挂,未来至不可测,究竟如何,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最后一段相当短。
想来,林玉声其时,年纪已老,他写下了那一段文字之后,就离开了家,再到猫爪坳去。
在林玉声这段记载之下,另外夹着一张纸,是用钢笔写的,是林子渊看了他祖上的日记后所写下来的,我将之一并转述出来。
记载可能是分几次写下来的,其间很清楚表现了林子渊的思索过程,每一段,我都用符号将之分开来。
这种事,实在是不可信的,只好当是“聊斋志异”或“子不语”的外一章。
(这是林子渊最早的反应,不信,很自然。)
再细看了一遍,心中犹豫难决,玉声公的记载,如此详细,又将这本册子,放在这样隐蔽的一个所在,决不会是一种无意识的行动。
“发现此册之后,祸福难料。”是什么意思?是肯定看到册子中记载的人,会像他一样,也到那株大树旁去求躯体的解脱?
玉声公不知成功了没有?算来只有百年,对于一株大树而言,百年不算什么,玉声公当年若成功,他的魂魄,至今还在树中?是则真正不可思议之极矣!
(这是林子渊第二个反应,从他写下来的看来,他已经经过一定程度的思索,开始想到了一点新的问题,并不像才开始那样,抱着根本不信的态度。他至少已经想到,人有灵魂,也怀疑到了灵魂和身躯脱离的可能性。)
连日难眠,神思恍惚,愈想愈觉得事情奇怪。魂魄若能依附一株大树而存在,可见可闻,那么,灵魂是一种“活”的状态存在着。是不是一定要有生命的物体,才可以使灵魂有这种形式的存在呢?
如果只有有生命的物体才有这个力量,是不是只限于植物?如果灵魂进入一株大树,情形就如同玉声公记载的那样。如果进入一株弱草呢!又如果,动物也有这种力量,灵魂进入了一条狗、一只蚱蜢之后,情形又如何?
再如果,没有生命的物体,也可供灵魂进入的话,那么情形又如何?设想灵魂如果进入了一粒尘埃之中,随风飘荡,那岂不是无所不在?
愈想愈使人觉得迷惘,这是人类知识范围之外的事。
(这是林子渊第三阶段的思索了,一连串的“如果”,表示他在那几天之中真是神思恍惚,不断在想着这个问题。从林子渊的记载,结合林老太太的叙述来看,林老太太的叙述很真实,林子渊在发现了那小册子之后的几天之中,一直思索着这个人类生命秘奥的大问题,他自然无法和妻子讨论。)
(从林子渊这一段记载来看,他已经有点渐渐“入魔”了!)
我有了决定,决定到那个有着那株大树的猫爪坳去。我要去见那株大树。如果玉声公的灵魂在那株大树之中,他自然可以知道我去,我是不是可以和他交谈呢?灵魂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以看到他?或者是感觉到他?
要是灵魂真能离开躯壳的话,我也愿意这样做。
退一步而言,就算我此行,完全不能解决有关灵魂的秘奥,至少,我也可以得到忠王的那一批珍宝,价值连城,哈哈!
(这是林子渊第四段记载。直到这时,他才提到忠王的那批珍藏,而且,还在最后,加上了“哈哈”两字。我很可以明白他的心情。人喜欢财富,在没有比较的情形之下,会孜孜不倦,不择手段追求财富,以求躯体在数十年之间尽量舒服。但如果一旦明白了躯体的短短一生,实在并不足恋,有永恒的灵魂存在,那就再也不会着眼于财富的追寻了。)
(林子渊这时,显然在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一定要到猫爪坳去,见那株大树。忠王的珍藏,实在算不了什么,如果灵魂可以脱离躯体,那岂不是“成仙”了?
这是极大的诱惑,玉声公说:“福祸难料”,我认为只有福,没有祸。不论怎样,我都要使自己的魂魄,像玉声公一样,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就算要使身躯损毁,我也在所不惜。
我深信,只要我有这个信念,而又有玉声公的例子在前,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不论是一株树、一块石头、一根草,或是随便什么,我都要使灵魂附上去,我相信这是第一步,人的灵魂,必须脱离了原来的躯体之后,才能有第二步的进境。第二步是什么呢?我盼望是自由来去,永恒长存。
我不惜死,死只不过是一种解脱的方式!
我决定要去做,会发生什么后果,我不知道,但即使死了,一定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留下来的东西,必然是我的生命的第二形式。
我要留几句话给伯骏,当他长大之后,他应该知道这些,至于他是不是也想学我和玉声公一样,当然由他自己决定。
我走了。
(这是林子渊最后一段记载。)
(在这段记载之中,他说得如此之肯定,这一点令人吃惊。虽然我这时和他一样,读过了林玉声的记载,也经过了一番思索,但是却不会导致我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或许,是因为林玉声是林子渊的祖先,这其中,还有着十分玄妙不可解的遗传因素在内之故。)
在林子渊的记载之后,还有计四叔的几句话写着。计四叔写道:“林子渊先生已死,死于炭帮炭窑,炭窑中有何物留下?是否真如林先生所言,他生命的第二阶段,由此开始,实不可解。”
“不论如何,余决定冒不祥之险,进入曾经喷窑之炭窑中,察看究竟。若有发现,当告知林氏母子。但事情究属怪诞,不论找到何物,林氏孤子,有权知道一切,知道之后,真是祸福难料,当使他不能轻易得知,除非林氏孤子,极渴望知道一切秘奥,不然,不知反好。至于何法才能令林氏孤子在极希望擭知情形下才能得知,当容后思。”
计四叔当时说:“当容后思。”后来,他想到了这样的办法。
他进入秋字号炭窑,发现炭窑之中,除了灰之外,只有一块木炭。从林玉声、林子渊的记载来看,这块木炭,自然是林子渊坚信他生命的“第二形式”了!
一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战!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林子渊的灵魂,在那块木炭之中!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盛载那块木炭的盒子,就在我面前,不到一公尺处,我曾经不知多少次,仔细审察过这块木炭,但是这时,我却没有勇气打开盖来看一看!
木炭里面,有着林子渊的灵魂!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说,林子渊一直在木炭之中,可见、可闻、可以有感觉、可以有思想?木炭几乎可以永远保存下去,难道他就以这样的形式,永久存在?
当我用小刀,将木炭刮下少许来之际,他是不是会感到痛楚?当我棒着木炭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看到我?
就这样依附一个物体而存在的“第二阶段”生命形式,是可怕的痛苦,还是一种幸福?
我心中的迷惘,实在是到了极点。
这时,我倒很佩服四叔想出来的办法,他要相等体积的黄金来交换这块木炭,就是想要林伯骏在看了册子上的记载之后,对所有不可思议的事确信不疑,有决心要得到这块木炭。只要林伯骏的信心稍不足,他决不肯来交换。至于林伯骏根本没有兴趣,连那本册子都不屑一顾,这一点,四叔自然始料不及。
我又想到,林伯骏曾说过一句极其决绝的话:“即使你带来的是我父亲的遗体,我也不会有兴趣!”
如果我告诉他,我带来的,不是他父亲的遗体,而有可能是他父亲的灵魂,不知他会怎样回答?
我苦笑了起来,我当然不准备这样告诉他。正如四叔所说:“林氏孤子”如果不是极其热切地想知道事情的始末,可以根本不必让他知道。四叔要同样体积的金子换这块木炭,就是这个原因。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盯着那只木盒,思绪极其紊乱。我首先要令自己镇定下来,我喝了一杯酒,才慢慢走向那木盒,将盒盖打开来。
木炭就在木盒之中,看来完全是一块普通的木炭。
我立时想到,当年,当林玉声的魂魄,忽然进入了那株大树,那大树,在外表上看来,自然也只不过是一株普通的大树,决计不会有任何异状。那么,如今这块木炭看来没有异状,并不能证明其中,没有林子渊的灵魂在木炭之中!
我有点像是服了过量的迷幻药品一样,连我自己也有点不明白,何以我忽然会对那块木炭,讲起话来。我道:“林先生,根据你祖上的记载,你如果在木炭之中,你应该可以看到我,听到我的话?”
木炭没有反应,仍然静静躺在盒中。
我觉得我的鼻尖有汗沁出来,我又道:“我要用什么法子,才能确实知道你的存在?如果在木炭之中,如你所说,是生命的“第二阶段形式”,那么我相信这个“第二阶段”一定不是终极阶段,因为虽然无痛苦,但长年累月在木炭中,又有什么意思?”
讲到这里,我又发觉,我虽然是在对着木炭讲话,但事实上,我是在自言自语,将心中的疑惑讲出来,自己问自己,没有答案。
我像是梦呓一样,又说了许多,当然,木炭仍静静的躺在盒中,没有反应。
林子渊当年动身到“猫爪坳”去,到了目的地之后,发现他要找的那株大树,已经砍伐下来,作为烧炭的原料,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边五和祁三已经对我说得十分详细。
林子渊最初做了什么,何以他会毫不犹豫跳进炭窑去?看他如此不顾自己的身躯,这种行动,似乎不是单凭他思索得来的信念可以支持,其中一定还另外有着新的遭遇,使他的信念,更加坚定!
那么,最初他到了目的地之后,曾有什么遭遇呢?
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的,大约只有林子渊本人了!所以,我在一连串无意义的话之后,又对着木炭,连连问了十七八遍。
这时,还好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不然,有任何其他人在,都必会将我当作最无可药救的疯子!
不知什么时候,天亮了。我叹了一声,合上木盒的盖子,略为收拾一下,也不及通知陶启泉和林伯骏,就离开了汶莱。
白素在机场接我,她一看到了我,就吃了一惊:“你怎么了啦?脸色这样苍白!”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脸色苍白到什么程度,但可想而知,我的脸色绝不会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