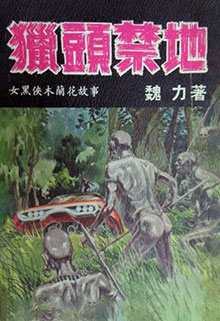当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别紧张,年轻人,别紧张!”
“老”仆张大了口,急速地喘起气来,我知道,在我识穿了他这一点之后,他决不会再有反抗的能力,所以我松开了手。
果然,我松开了手,他呆呆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动也不动,我又道:“怎么样,我想我们应该好好地谈一谈!”
他口唇又动了片刻,才道:“卫先生,我实在很佩服你,我……我知道很多……你的事,我……也知道你的为人……”
他显然仍然在极度惊骇的状态之中,所以讲话,有点语无伦次,我将手按在他的肩上:“别惊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他语带哭音:“可是,死了一个人!”
我直视着他:“是你杀死他的?”
他骇然之极地摇着头,又摇着手,我道:“既然不是你杀他的,那你怕什么?”
他道:“我……实在害怕,我求求你,你先离去,我会和你见面,让我先静一静,好不好?求求你。今天天黑之前,我一定会和你联络!”
我不禁踌躇起来,他的这个要求,实在很难令人接受。
他说要我离去,他会和我联络,如果他不遵守诺言呢?现在,他是我唯一的线索,最重要的线索,我怎样可以让他离去?
他哀求我时的声音和神态,都叫人同情,但是,我硬着心肠,摇了摇头:“不行,现在就谈,或者,随你高兴,我们一起到警局去。”
他一听到“到警局去”这四个字:“腾”地后退了一步,喃喃地道:“何必要这样?何必要这样?”
我不理会他在说什么,用相当严厉的声音逼问道:“王直义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他不同答。
我又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他仍然不同答。
我提高了声音:“你刚才手中拿的是什么?”
他仍然不回答,但是这一个问题,是不需要他回答我才能得到答案的,他不出声,我疾伸出手来,抓向他的手臂。
他的手臂向后一缩,但是我还是抓住了他的衣袖,双方的力道都很大,他的衣袖:“嗤”地一声,扯了开来,那支金属管落了下来。
我连忙俯身去拾这枚金属管,可是我绝没有料到,已经震骇到如此程度,一面流着汗,一面向我哀鸣的人,竟然会向我反击!
这自然是我的错误,我没有想到,将任何人逼得太急了,逼得他除了反抗之外,什么也没有法子的时候,他就只好反抗了!
就在我弯身下去捡拾那金属管的时候,我的后脑上,陡地受了重重的一击。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东西打我,但是那一击的力道是如此之重,可以肯定决不是徒手。
我立时仆倒,天旋地转,我在向下倒地的时候,还来得及伸手向他的足踝拉了一下,我好像感到,我那一拉,也令得他仆倒在地,但是我却无法再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因为那一击实在太沉重,以致我在倒地之后,立时昏了过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后脑之上,好像有一块烧红了的铁在炙着,睁开眼来,眼前一片漆黑。睁开眼来而眼前一片漆黑,那种漆黑,和身在黑暗之中,全然不同,那是一种极其可怕的。前所未有的感觉,我变得看不见东西了,我瞎了!
我忍不住大叫起来,一面叫,一面直坐起来。
我立时感到,有人按住了我的肩,我拚命挣扎,那人用力按住我。
同时,我也听到了杰克上校的声音:“镇定点,镇定点!”
我急速地喘着气:“我怎样了?我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杰克上校仍然按着我的肩,可是他却没有立时回答我,他在我叫了几声之后,才道:“是的,医生已预测你会看不见东西,你后脑受伤,影响到了视觉神经,不过,那可能是暂时性的!”
我尖声叫了起来:“要是长期失明呢?”
杰克上校又没有出声,我突然变得狂乱起来,不由分说,一拳就挥了出来。
我不知道我这一拳击中了上校的何处,但是这一拳,是我用足了力道挥击出去的,从中拳的声音,上校后退的脚步声,以及一连串东西被撞的声音听来,上校中了拳之后,一定跌得相当远。
也就在这时,我觉得突然有人抱住了我,同时,听到了白素的声音:“你怎么可以打人?”
我立时紧握住白素的手,颤声道:“你……来了,你看看,我是不是睁着眼?”
我听得出,白素在竭力抑制着激动,她道:“是的,你双眼睁得很大!”
我叫起来:“那么,我为什么看不见东西?”
白素道:“医生说,你有很大的复原机会!”
我将她的手握得更紧:“多少?”
白素道:“你脑后受了重击,伤得很重,发现得又迟,有一小块瘀血团,压住了视觉总神经。有两个方法,可以消除这个瘀血块,一是动脑部手术,一是利用雷射光束消除它,有办法的!”
经过白素这样一解释,我安心了许多,又躺了下来:“上校!”
杰克上校的声音很古怪,他立时回答:“算了,不必道歉,我不怪你就是!”
我道:“我应该怪你,为什么你自顾自离去,将我一个人留在觉非园?”
我等了很久,没有听到上校的回答,想来杰克上校对他当时的盛怒,理也不理我就走,多少感到内疚。我只听到白素轻轻的叹息声:“算了,事情已经发生,怪谁都没有用了!”
在白素安慰我之外,我才又听到了上校的声音,他道:“你在觉非园中,究竟遇到了什么了?是谁袭击你?我们曾找过那老仆,可是他却失了踪,我们也和在槟城的王直义联络过,他说,他会设法尽快赶同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杰克不停地说着,他一定未曾发觉,我越听越是恼怒,不然,他一定不会再继续不断地说下去的,我好不容易,耐着性子等他说完,我还想再忍耐的,但是,我却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我的怒意突然发作,我用尽气力吼叫起来,叫道:“你关心的究竟是什么,是案情的发展,还是我盲了双目?”
上校的声音有点尴尬:“你不必发怒
”
这一次,我没有再容他讲完,就又叫了起来,我大喝道:“滚出去,滚出去,走!
”
我一面叫,一面伸手指向前直指着,我觉察着我的手指在剧烈地发着抖,我喘着气,只听得上校苦笑着:“好,我走,你冷静些!”
他略顿了一顿,接着,又自以为幽默地道:“不过,我无法照你所指的方向走出去,那里是墙!”
若不是白素用力按着我,我一定跳起来,向他直扑过去,接着,我听得一阵脚步声,想来,离开病房的人相当多,而我的后脑,也在这时,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刺痛,使我颓然睡倒在床上。
我还是睁大着眼,希望能见到一丝光芒,然而,我什么也看不见,一片黑暗。
白素轻柔的声音,又在我耳际响起,她道:“你不能发怒,必须静养,要等你脑后的伤势有了转机,医生才能替你动进一步的手术,要是你再这样暴躁下去,你永远没有复明的希望!”
我苦笑着,紧握着她的手,她喂我服药,大概是由于药物的作用,我睡着了。
在沉睡中,我做了许多古怪、纷乱的梦。在梦中,我居然可以看到许多东西,当我又蒙矓醒来时,我不禁怀疑,一个生来就看不见东西的人,是不是也会有梦?如果也有梦的话,那么,出现在他梦境中的东西,又是什么形状的?
接下来两天,我一直昏睡,白素二十四小时在我身边,当我醒来的时候,她告诉我,杰克上校来过好几次,看来他很急于想和我交谈,但是又不敢启齿。
白素又告诉我,警方正倾全力在找寻那个“老仆”,可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
那自然不会有结果,在击倒了我之后,那“老仆”一定早已洗去了化装,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发现那“老仆”的秘密的经过向上校说一说。可是,即使我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我记得,我发现那“老仆”的秘密,是由于我突然的转身,而看到他手中握着一根奇异的金属管。
直到现在,我还可以肯定,那金属管,是高度机械文明的产品,和连电灯也没有的觉非园,完全不相称。虽然,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以及为什么那“老仆”要用这东西对准了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便是:觉非园古色古香到了连电灯也没有,那完全是一种掩饰,一种伪装!
需要掩饰的是什么呢?这一点,我不知道,而且,除了王直义之外,只怕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解答,而王直义却离开了本地,虽然那天晚上,我明明在九月咖啡室,曾经见到他!
而那根小金属管呢?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倒下去昏过去之前,还曾将那“老仆”拉跌,接着,我也仆倒在地,将那金属管,压在身体之下,而那“老仆”仓惶逃走。
那金属管是压在我身子下面的,如果不是那“老仆”去而复转,那么,警方发现我时应该发现那个金属管。
可是,为什么杰克上校未曾向我提及呢?
我伸手向床追摸索着,白素立时问:“你要什么?”
我道:“我的东西呢?我是说,我被送到医院来之前,不是穿这衣服的,我的衣服,我的东西呢?”
白素道:“全在,我已经整理过了,我发现有一样东西,不属于你。”
我吸了一口气,同时点头:“一根圆形的金属管?”
白素道:“对,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知道那东西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一发现它,就收了起来,而且,这两天我详细研究过这东西。”
我的呼吸有点急促:“那是什么?”
白素的回答令我失望:“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它的构造很复杂。”
我又道:“至少,看来像什么?当时,持着这金署管的人,正将它有玻璃的那一部分,对准了我的背部,那是什么秘密武器?”
白素道:“不是,它看来好像是摄影机,或者类似的东西!”
我沉默了一会,才道:“将它藏好,别让任何人知道你有这东西,等我恢复了视力再说。”
白素答应着,这时,传来叩门声,白素走过去开门,我立时道:“上校,你好。”
我自然看不见进来的是谁,但是上校的那种皮鞋谷谷声,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
我叫了他一声之后,上校呆了片刻,才道:“我才同医生谈过,他说你的情形,大好转!”
我苦笑着:“这情形,只怕就像你应付新闻记者的问题一样,是例行公事。”
上校来到了我床边,又停了片刻,才道:“王直义从槟城回来了!”
我觉得有点紧张,这种情形,当我失去我的视力之际,是从来也未曾发生过的!
我之所以觉得紧张,是因为我已经可以肯定,王直义是一切不可思议的事的幕后主持人,也就是说,他是最主要的敌人。
我喜欢有他这样的劲敌,如果我像往常一样,我自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和他周旋到底。
可是,现在我是一个瞎子,而王直义又是掩饰得如此之好,隐藏得如此周密的劲敌!
杰克上校接下来所说的话,令得我更加紧张,使我手心隐隐在冒着汗。
他道:“王直义和我会见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他要见你!”
心里越是紧张,表面上就越要装得平淡无事,这本来就是处世的不二法门,尤其在我这种情形之下,更加应该如此。
我装着若无其事地道:“他要见我作什么?表示歉意?”
上校的声音,有点无可奈何:“我不知道,他从机场直接来,现在就等在病房之外,我想他一定有极其重要的事!”
我又吃了一惊,上校道:“你见不见他?”
我心念电转,是不是见他?我还有什么法子,可以避免在失明的时候,再对劲敌?
我考虑的结果是,我没有别的法子!
所以我道:“好的,请他进来!”
上校的脚步声传开去,接着是开门声,又是脚步声,然后,我可以感到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在紧张,因为我觉出王直义已来到了我的身边,王直义的声音,听来很平静,和我上次去见他的时候,完全一样,也和在九月咖啡室中,他说话的声音,完全一样。
他道:“我听得上校提及了你的不幸,心里很难过,希望你很快就能复原!”
我也竭力使我的声音镇定:“谢谢你来探望我。”
王直义静了下来,病房中也静了下来,像是在那一刹间,人人都不知道这应该如何开口才好。
过了好一会,杰克上校才道:“王先生希望和你单独谈话,不想有任何人在旁,你肯答应么?”
我早已料到,王直义来见我,大有目的,也料到他会提出这一点来。
白素立时道:“不行,他需要我的照顾,不论在什么情形之下,我都不会离开他半步!”
我点了点头:“是的,而且,我和我的妻子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秘密,如果有人需要离开的话,只有上校,或者,王先生。”
我的意思再明白也没有了,只有白素在,我才肯和王直义谈论,不然,王直义大可离去!
病房中又静了下来,我猜想在那一刹间,杰克上校一定是在望向王直义,在徵询他的同意。
而在那一刹间,我自己心中在想:上校和王直义之间,究竟有着什么默契?我们两人,一定是不可能有什么合作的,上校之所以代王直义提出这一点来,无非是为了尊重王直义是一个大财主而已!
病房中的沉静,又持续了一会,才听得王直义道:“好的,上校,请你暂时离开一会。”
我又猜想,上校的神情一定相当尴尬,但他的脚步,立时传开去,接着,便是房门关上的声音。
我判断病房之中,已经只有我们三个人,我首先发动“攻势”:“王先生,你有什么话说,可以放心说,因为凡是我知道的事,我太太也全都知道!”
我本来是不想这样说的,而且,事实上,我也未曾将一切的经过,全告诉白素,白素也没有问过我。
而我决定了那样说,也有道理,我不知道王直义在做些什么,但至少知道,他在做的一切,绝不想被外人知道。
而我,对他来说,已经成为“知道得太多的人”,如果他不想被别人知道的话,他就会设法将我除去。
而我这样说,也并不走想拖白素落水,而是给王直义知道,他要对付的话,必须同时对付我们两个人,他应该知道,那并不是容易的事。
本来,我在外面一切古怪的遭遇,是我独立应付的多,中间也有和白素合作的。但是现在,我必须白素的帮助,因为我看不见任何东西。
白素一定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她才坚持要留在我的身边。我的话出口之后,听到了王直义深深的吸气声,接着,他道:“卫先生,原来你第一次来见我,就是为了郭先生失踪的事。”
我也立时道:“不错,所谓房屋经纪,只不过是一个藉口而已!”
王直义乾笑了两声,从他那种乾笑声判断,他并不是感到什么,而只是感到无可奈何。
接着,他又道:“卫先生,现在,你已经知道得不少了?”
我冷笑着,道:“那要看以什么标准来定,在我自己的标准而言,我应该说,知道得太少了!”
王直义道:“你至少知道,所有的事情,和我有关!”
我故意笑起来:“若是连这一点也不知道,那么,我不是知道得太少,而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王直义跟着笑了几声,他果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因为他竟立时开门见山地问我:“要什么条件,你才肯完全罢手,让我维持原状?”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咄咄逼人,很厉害的问题,这是一个逼着人立时摊牌,毫无转圜余地的一个问题!
我的回答来得十分快,我猜想,王直义一定也感到我很难应付。
我立时道:“让我知道一切情形,然后,我再作判断,是不是应该罢手!”
我自然看不到王直义的神情,但是从听觉上,我可以辨出,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了,那表示他十分愤怒,几乎不能控制自己了!
我不出声,等着他的反应,过了好一会,他才道:“你所知道的一切,其实并不构成任何证据,要知道,我根本不在本市!”
我道:“是的,我也无意将一切事告诉上校,你也决不会上法庭,不过,我不会罢手,你要明白这一点,我不会罢手,即使我现在瞎得像一头蝙蝠!”
王直义又急速地喘了一回气,才道:“卫先生!”
他先叫了我一声,然后,显然敛去了怒意,声音变得平静了许多:“你不会明白我在做什么的,你不会明白,没有人会明白
”
他讲到这里,又顿了一顿,然后,从他的语调听来,他像是感到了深切的悲哀:“郭先生的失踪,完全是一个意外。”
我立时道:“那么,陈毛的死呢?”
王直义苦笑着:“更是意外!”
我再问道:“罗定的失踪呢?”
王直义没出声,我再道:“我的受狙击呢?”
王直义仍然不出声,我的声音提高:“王先生,你是一个犯罪者,虽然法律不能将你怎样,但是我不会放过你!”
我听到王直义指节骨发出“格格”的声响,我想他一定是因为受了我的指责,在愤怒地捏着手指。
过了好一会,白素才道:“对不起,王先生,如果你的话说完了,他需要休息!”
我没有再听到王直义讲任何的话,只听到了他代表愤怒的脚步声,走了出去。
接着,便是杰克上校走了进来,向我提出了许多无聊幼稚的问题,好不容易,我用极不耐烦的语气,将他打发走了,白素才在我的耳际道:“既然你刚才那么说了,我想知道一切事情的经过!”
我点着头,将我所经历的一切,和我所猜想的一切,全都告诉了她。
白素一声不响地听着,直到我讲完,才道:“刚才,王直义一度神情非常无可奈何,像是想取得你的同情和谅解,但是终于又愤怒地走了!”
我道:“要看他是不是我所指责的那样,是一个犯罪者,只要看是不是有人来对付我们就行了,我想,得加倍小心!”
白素有点忧虑,因为我究竟是一个失明的人,她道:“是不是要通知杰克,叫他多派点人来保护?”
我摇头道:“不要,与其应付他查根问底的追问,不如应付暗中的袭击者了!”
白素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握紧我的手。
可能是我的估计错误了,接下来的三天,平静得出奇,杰克来看我的次数减少,我在医院中,未曾受到任何骚扰。
医生说我的伤势很有好转,快可以消除瘀血口,恢复我的视力。
而了实上,这几天之中,我虽然身在病房,一样做了许多事,小郭事务所中的职员,不断来探望我,我也对他们作了不少指示,小郭仍然踪影全无,也未曾再有不可思议的电话打回来,而罗定的情形也一样。
我仍然不放弃对王直义的监视,但是那几位负贵监视的职员说,自从进了觉非园之后,王直义根本没有再出来过,他们简直无法想像,他一个人在觉非园之中,如何生活。
一直到了我要进行雷射消除瘀血团的那一天,事情仍然没有变化,而我的心情,仍然很紧张,我不知道手术是不是会成功,要是成功的话,自然最好,要不然,我还会有希望么?
我被抬上手术台,固定头部,我听得在我的身边,有许多医生,在低声交谈,这种手术的例子并不多见,我这时,颇有身为白老鼠的感觉。
我被局部麻醉,事实上,也和完全麻醉差不多,我不知道手术的过程,经过不多久,但是突然间,我见到光亮了!真的,那是切切实实,由我双眼所见到的光亮,而不是梦境中的光亮。
然后,我辨别得出,那是一个圆形的光,就在我的头前,接着,这团圆形的光亮,在渐渐升高,而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不少人影。
我听到医生的声音:“如果你现在已能看到一点东西,请你闭上眼睛一会!”
我听得出,医生在这样说的时候,语调紧张得出奇。自然,他们无法知道我已经可以看到东西,我行动如何,便是手术是否成功的回答!
我本来是应该立时闭上眼睛的,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听到一阵欢呼声。
然而,就在我快要闭上眼睛的那一刹间,我脑中突然电光石火也似,兴起了一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