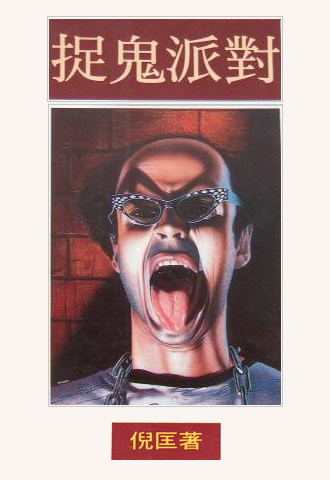江南地面,原本文风极盛,武风不昌,但如今却因有“关家堡”和“江家堡”两大势力,竞相对峙,互为雄长,便也经常刀光剑影地,显得十分热闹!
“关家堡”的堡主,叫关承祥,生有二子,长子“长风”、次子“少风”,姿质均相当不错,被誉为江湖中的后起祥麟,兄弟之间,尤以大哥关长风无论在武功品貌方面,都比乃弟关少风,秀拔不少!
“江家堡”的堡主,叫江奔涛,膝下有一子一女,子名“穿云”,女名“留云”,姿质也算尚佳,但和关长风、关少风兄弟,比较起来,便显得有点不是正派路数。
“关”、“江”两堡,均设有不少外围镖局,一来经营商业,开辟财源,二来也便于结交江湖中的奇技异能之士!
但近一段时间以来,江湖道上,居然风波不靖?!
不论是“关家堡”或“江家堡”的外围镖局之中,近来都屡屡出事!
消息传来,震动本堡,关承祥和江奔涛,都久已不曾亲涉江湖的了,于是,相当惊怒之下,派出了关长风和江穿云,查询各镖车出事究竟?
下面,又有事了!
好威风,好漂亮,好巨大的旗帜!
紫红色的绒质,杏黄色的缎边,和猎猎的飘带,寻丈的旗杆,的确是够威风,够漂亮了,但更威风,更漂亮的,却是紫红绒旗中央那个斗大的黑色“关”字!
另外一杆肃有白色虎头的镖旗,代表:“白虎镖局”,本在南七省地面也有相当声誉,威震三江(江苏、浙江、江西),但如今插在比它大了倍许的“关”字旗边,却立刻见绌,失了颜色!
“关”字旗的少主人,太湖“关家堡”的大少堡主关长风,突然一勒跨下“五花骢”的缰绳,目光微扫四外静悄悄的青山绿水,向他身旁并辔同行的陈通镖头,抱拳笑道:“陈镖头,一过前面的‘落魂坡’,就到达交镖地了,我想先行告辞,因为还要赶去‘金牛镖局’,看看蔡镖头方面,有无甚么突发情况,需要特别援助!”
这位关少堡主,只有二十上下年纪,貌相极为英俊风神也极为潇洒,但身着青衫之上,却满布风尘,眉目间,也微有疲倦之态,显得他连日以来,奔涉长途,极为忙碌,没有好好地休息盥洗。
镖头陈通听得关长风要走,在马上抱拳,含笑说道:“少堡主慢走,多谢少堡主一路护送,回堡以后,请替陈通叱名代候堡主金安。”
关长风一面勒缰回马,一面正色嘱道:“近来,江南道上,怪事迭传,风险特多,陈镖头一切都请多加谨慎!”
话完,手中轻抖,缰绳一松,“五花骢”双耳微耸,四蹄扬处,便往来路驰去。
陈通目送关长风人马背影杳后,方转身挥手发话:“兄弟们,赶一程吧,过了七八里外的‘落魂坡’,就算平安无事的到地头了。”
另外两名镖师,和趟子手,暨车夫们,齐声暴喏,喊起了“威……武……”之声,不再歇息,准备立即赶路。
就在此时,一声霹雳,陡响当头!
此处乃是山道,所谓“霹雳”,只是左道旁削壁半腰,有人发出了威势颇严,“慢走”二字的一声断喝!
随着这声断喝,一条白色人影,垂空疾落,穿过了随风飘拂的紫红“关”字旗影,在陈通马头的七八尺前,飘然落地。
那是个头戴绝大箬笠的白衣人,背对陈通等一行人马,手按腰间剑柄,像座冰山般,卓立不动!
既见有人拦道,镖师、趟子手等,自然立刻防变地,各亮兵刃,把镖车圈了起来。
镖头陈通勃然震怒,伸手摘下挂在鞍边的得意兵刃“软索九芒锤”,向那背对自己的白衣人,沉声喝道:“朋友是哪条道上的?莫非不知道这是‘太湖关家堡’旗下,十二地支镖局中的‘白虎镖局’镖车?”
白衣人手按腰间剑柄,徐徐转身,虽面对陈通,仍未除掉头上所戴的绝大箬笠,从鼻中“哼”了一声,冷冷说道:“哼!还要打甚么‘关家’旗号?狗仗人势的东西,怎不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关家’的门户垮了……”
经白衣人这样一说,陈通与两名镖师暨趟子手等,方对那杆威风无比的紫红巨大“关”字旗,加以注目,不禁齐都心弦猛紧,倒抽一口冷气!
原来那杆“关”字旗如今业已变成了“丝”字旗,“丝”外之“门”,竟被人于不知不觉间,用剑挖去!
这显然是白衣人适才由峭壁飘落,身形穿过紫红旗影时所为,但未见剑花舞,未见剑光腾,一刹那间,便神鬼不觉的,毁了“关”字之“门”,乃是何等手法?何等功力?
陈通等相顾失色之际,白影又飘!
白影当然便是那头戴绝大箬笠的白衣人,他长剑仍未离鞘,就在白衣一飘,飚轮电转之间,便以腰间剑柄,把“白虎镖局”的镖头陈通,和另外两位镖师,一齐点了穴道。
然后,这白衣人并举步走向镖车,但却不劫镖,只伸手拔起了插在镖车上的“白虎镖旗”!
可怜,趟子手暨车夫等,眼见连镖头、镖师们都一合未交,便告被制,他们哪个还敢作死多事?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神秘白衣人,拔了镖旗,狂笑扬长而去!
另外一处山道。
也有镖车,镖车上插的是象征“流水”图样的“洪流镖局”镖旗。
“洪流镖旗”旁边,也有一杆寻丈巨旗,但巨旗中央,不是“关”字,却是一个斗大“江”字。
因为“洪流”字号,是属于“江家堡”的外围镖局。
四名镖师,暨众趟子手,个个都趾高气扬,镖车旁,另有一辆囚车,车中囚的,是位白衣客,打扮和关家“白虎镖局”在“落魂坡”前所遇之人,差不许多,只是头上少了顶绝大箬笠而已。
一名冯姓镖师,眉飞色舞地,向另一名丘姓镖师,狂笑说道:“丘镖师,这一下,关家堡可没有脸再和我们互争谁是‘江南第一堡’了……”
丘姓镖师轩眉狂笑:“当然,当然,关家堡的镖车,遇上神秘客,不单镖旗被拔,连‘关’字旗,都被人家整垮门户,而我们江家堡也遇上了神秘客,却把他擒禁在囚车之内!”
神秘白衣客在囚车中,冷笑接口道:“别不要脸了,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关家’的‘门’虽垮掉,‘江’家的‘水’也干了!呸……呸……呸……”
这神秘白衣客,已具内家咳唾伤人之上乘功力,每“呸”一声,即以“唾痰”,把“江”字的三点之中的一点,击成一个空洞。
三声“呸”罢,“江”字大旗上,果然点水皆无,只留下一个“工”字。
四镖师、众趟子手一个个目瞪口呆,相顾失色间,神秘白衣客继续冷笑:“你家太爷,不过因连日奔波太累,才乐得稍作歇息,让你们像孝子贤孙般,用车辆送我一程,如今我是想来便来,想走便走,还要拔杆‘洪流镖旗’,带回去作纪念品呢!”
说至此处,囚车突然摧枯拉朽般,呈现四分五裂之状,神秘白衣客则须发猬张,像只发怒公鸡般,从囚车中,冲天飞起,威猛无比!
丘、马等四镖师,见势不妙,赶紧各抄兵刃,但眼前暗处,劲风狂拂,全都在一刹那间,被人用极高明的隔空手法,制了穴道!
神秘白衣客虽轻易制住镖师,镇住趟子手等,却仍不取分毫镖银,只拔了那杆“洪流镖旗”,满面哂薄不屑神色,仰天狂笑而去!
这是一家酒店。
酒旗在店外飘扬,酒客在店内喧哗……
相当敞宽的大厅,几乎挤得满满,因为除了酒客,还有镖车。
有“关家堡”的“金牛镇局”镖旗,也有“江家堡”的“五湖镖局”镖旗,当然更有那比镖旗更威风,更神气的“关”字“江”字大旗。
“关”“江”两家的镖师、趟子手们,壁垒分明,两堆吃喝,神采飞扬,语声十分嘈杂。
酒店门外,慢慢走进一个头戴绝大箬笠,身披渔夫簑衣之人。(校对按:“簔簑”同“蓑”。)
“江”家“五湖镖局”的镖师们,一向比较来得自大骄狂,哪里会把一个孤身渔夫,看在眼中,主持一行的苏镖头,举杯在手,皱眉说道:“‘洪流镖局’怎会遇上这等怪事?是谁敢捋‘江家堡’旗下的虎髭?莫非他吃了熊心……”
邻桌“金牛镖局”的蔡镖头,恰巧也在发狂卖味,有语音传来:“是谁敢动‘关家堡’的镖车,莫非他吃了豹胆……”
天下事往往真叫无巧不成书,就在“关”“江”两家镖头这“熊心豹胆”之语,刚刚出口之际,便有两只巨大酒篓,不知从何处咕噜噜地滚了进来,而一只酒篓上赫然写着“熊心”两字,另一只酒篓上则赫然写着“豹胆”两字!
“金牛镖局”的蔡镖头怪叫一声道:“真邪门儿!怎么刚说到‘熊心豹胆’,就有这‘豹胆熊心’出现?……”
“五湖镖局”的苏镖头,狞笑道:“先下手为强,我要看看这两只巨大酒篓之中,会不会藏着一个‘熊心豹胆’的神秘白衣客?……”
这一回,“关”家“江”家的镖头镖师们,居然敌忾同仇,相当齐心,分别以兵刃暗器,同时电击出手!
江家的镖师们,是发暗器,把上写“熊心”的酒篓,射穿了无数孔穴。
关家的镖师们,是拔兵刃,把上写“豹胆”的酒篓,砍劈成破损不堪。
但酒篓之中,别无异状,所流出的,只是奇香美酒而已!
那簑衣渔人静等关、江两家镖师们,抖足威风,方从容脱掉簑衣,现出了神秘白衣客的打扮!
这时,酒店门外的东西两方,都有急骤马蹄声息,远远传来。
神秘白衣客目光如鹰地,一扫那些业已惊得发怔的关、江两家镖师,嘴角微披,冷然地说道:“你们的靠山,也赶的来了,莫怪我狠,我非赶在他到此之前,下快手,和下重手不可!”
随着话声,一式“冷送春烟”,身形转若飚轮,以快得令人难信,奇得令人咋舌的身法手法,竟把“金牛镖局”、“五湖镖局”等关、江两家镖师,一齐击倒在地!
神秘白衣客一举制敌,嘴角微披,哂然说了声:“酒囊饭袋!”便伸手欲拔“江”家镖车上所插的“五湖镖旗”。
陡然一声沉叱:“住手,‘江家堡’的旗号,不许你碰,江穿云在此!”
随着这声沉叱,一条极雄健的年轻阴鸷汉子,出现在酒店门外,怒视神秘白衣客,双目中似要喷出火来!
神秘白衣客闻言,改变目标,方自转身欲拔“金牛镖旗”,店门外又是一声轻叱:“朋友,有分寸些,关长风在此,我‘关家堡’属下的镖旗,更岂是外人能动?”
果然,英俊、潇洒,但却满身风尘的关长风,也出现了,在店门外,与江穿云一左一右,并肩而立。
神秘白衣客纵声狂笑:“两位少堡主也只是两块嫩姜而已,你们纵比这群酒囊饭袋强些,又能接我几招?”
江穿云勃然道:“自以为了不起的狂妄东西,出来试试!”
一面发话,一面向左闪身,关长风也微侧身躯,表示让神秘白衣客出店。
神秘白衣客毫无怯色地,扬长举步,冷冷说道:“好,我们到外面比划,让你们这两个公子哥儿,知道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江湖中有多少远出你们意料,高明厉害的能人奇士!”
到了酒店门外的空地广场,神秘白衣客傲立如山?目光微扫关长风、江穿云二人,轩眉笑道:“‘东江’、‘西关’,往日是冤家,今天却敌忾同仇,成了朋友,两位少堡主,一齐上吧!”
江穿云怒道:“狂妄匹夫,本少堡主既然亲自出手,怎会倚多为胜?就凭我江穿云的家传‘奔雷重手’,和出剑追魂的‘奔涛快剑’,你就吃不消兜着走了!”
神秘白衣客不屑笑道:“一个一个的来也好,我和江奔涛略有渊源,暂时还不想要他儿子这条小命,故而,‘奔涛快剑’免了,就试试你的家传‘奔雷手’吧!”
江穿云一再被人藐视,心中委实恼怒已极,闻言之下,“天门擂鼓”、“紫电抓魂”、“奔雷夺命”等,带有隐隐风雷声息,增强了不少威势!
神秘白衣客白衣一飘,竟以一种极神奇的身形步法,使江穿云的“奔雷三式”,完全打空,口中并冷笑说道:“江穿云,‘奔雷手’虽是‘东江绝艺’,但你却只得了你爹爹的七成传授,火候还差得远呢!”
这情况,把一旁观战的关长风,看得慄然一惊!
因为,他深知这神秘白衣客既能轻易应付“东江”绝学,则自己少时出手,多半也难占上风,不如趁此机会,未虑胜先虑败地,作些防范准备?……
心意阮动,他立刻为自己作了一些未雨绸缪的防御工作,就在关长风戒意已生,正自暗作准备之间,神秘白衣客与江穿云身形已合,对拆数招,蓦然间江穿云,似乎中了一掌,足下跄踉后退,神秘白衣客并狂笑说道:“回去告诉江奔涛,就凭他儿子尚未成材,少在江湖丢脸!”
江穿云羞愤欲绝,但知对方功力太高,对于自己,确已手下留情,不敢多言自讨没趣,只得一挫钢牙,认蹬搬鞍,上马疾遁!
神秘白衣客见江穿云已走,回过头来,向关长风问道:‘关少堡主,我们是否也应应景儿?还是不必多此一举?”
关长风缓步而前,神色相当稳重,毫不轻狂,一抱双拳,含笑说道:“江湖访艺,难遇高明,关长风不愿错过这种‘他山借石’的大好机会,请朋友指教几手罕世绝学……”
神秘白衣客闻言,对关长风上下细一打量,点头笑道:“岳峙渊停,神凝气稳,你这位关少堡主,似乎要比刚刚先走的那位江少堡主,强得多了。”
关长风依然不亢不卑,面带微笑说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江湖好走,关山难越,朋友,请……”
神秘白衣客“咦”了一声道:“你真沉得住气,不想先问问我这神秘白衣客的来历姓名?”
关长风淡然摇头答道:“朋友一不劫镖,二不杀人,却到处生事,专拔‘关’‘江’两家属下镖旗,用意显然便在扬名立万!我若不能于艺业上有所承让,除非你自动报名,又何必多此一问?”
神秘白衣客闻言,点了点头,向关长风再一打量,扬眉说道:“论神气,你比江穿云来得沉稳,论见识,也远为高明,看来,你确是关承祥的跨灶佳儿,在我手下,大概接得了三十照面……”
关长风尽量按捺心神,免得被对方狂傲言词,激起怒火,只是抱元守一地,向神秘白衣客亮开了门户,足下活开步眼。
但神秘白衣客居然确有实学,说的并非狂言!
两人对掌过招,三十合内,龙拿虎攫,秋色平分,果然是个旗鼓相当的平衡局面。
但一出三十合后,神秘白衣客绝学突施,连环进手,关长风便应付为难地,在胁下中了一掌!
不过,关长风虽足下跄踉,退出几步,神秘白衣客却也身形微震,伸手从所着白衣的腰上,起下一只关家的独门暗器“如意镖”来,掂了一掂,向关长风点头笑道:“好,我打了你一掌,掌下曾略为留情,你打了我一镖,镖上也避免带血,足见‘关家堡’的少堡主,着实不差,但在未能把你父亲的‘天风七式’,练得火候圆融之前,要想胜我,简直白日作梦……”
语音至此略顿,向关长风看了一眼,狂笑又道:“看在你的面子,‘金牛镖旗’,我不拔了,但‘五湖镖旗’,仍要带走,让那在‘江家堡’中,养尊处优已久的江奔涛,丢点面子,生生闲气!”
话完,重又走进酒店大厅,拔了江家“五湖镖旗”,意气轩昂,扬长而去。
关长风看着他狂,看着他走,不便拦,也知道不必拦,英俊脸庞上所展现的,是惭愧,是惊讶,和无奈的交织神色!
这里是名震江南实力超越其他武林门派的两大堡之一的“关家堡”。
另一大堡,是“江家堡”,以地缘而论,“江家堡”在东,遂简称“东江”,“关家堡”在西,遂简称“西关”。
“关家堡”的堡主,叫关承祥,老伴早亡,膝下二子,长子长风,次子少风,关承祥本人,晚年腰腿有疾,不良于行,遂特制一“椅轿”代步。
如今,关承祥坐在“关家堡”议事厅上,手执“班竹旱烟袋”,面有忧容,不住抽烟沉思。
次子关少风,侍立身右,身左站的,则是关承祥的多年江湖老友,也成了他“关家堡”内外一把抓的心腹总管骆驼。
关承祥喷出了一口浓烟,侧顾骆驼,发话问道:“骆二弟,外面的事,当真有这么严重?”
骆驼神色恭谨地,垂手答话:“回堡主,十二地支镖局中,有‘青龙’‘黑马’‘白虎’‘金牛’等四家镖局,全出了事,但镖银分文未失,趟子手等,也无人丧命,只是负责押镖的镖头镖师,都成为残疾,被对方废了武功!”
关承祥重重团了团在手中玩弄的两粒“鸳鸯铁胆”,皱眉问道:“对方历次出手的,共有几人?”
关少风一旁接口:“孩儿问过今天特地赶来报讯的‘灰鼠镖局’崔镖头了,他说根据一致报告,每次出事,都是位神秘白衣客,一人生事!”
关承祥把手中“鸳鸯铁胆”,重重放在身旁几上,“哼”了一声,眉锁重忧说道:“这神秘白衣客如此大显威风,一再故意生事,分明是冲着我‘关家堡’的威望来的,我只怕……”
骆驼见关承祥语音忽顿,便恭身接口问道:“堡主是不是担心大少堡主巡察十二地支镖局之行,可能也会遇上甚么神秘白衣客?……”
话方至此,一名庄丁,匆匆进入议事大厅,向关承祥行礼报道:“启禀堡主,大少堡主回庄,有重要事件,立即请见堡主。”
关承祥正是为关长风有所悬忧,闻得爱子回堡,脸上立现宽容,方含笑点头,一个“好”字,刚刚出口,骆驼与关少风,业已双双抢步飞迎。
而关长风那满身风尘的挺拔俊影,也已出现在大厅门口。
骆驼上前,正为关长风拂尘,关少风已伸出手儿笑道:“大哥,你这次定然玩得过瘾,可带回甚么希罕东西给我?”
关长风拉着关少风的手儿,苦笑说道:“还玩得过瘾呢?我差点儿把条小命,都给玩掉!希罕东西是有,但要等我向爹禀过重大事儿之后,再拿给你。”
关长风是边说边行,到了厅中,行礼参见关承祥后,躬身禀道:“启禀爹爹,十二地支镖局中……”
关承祥摆手道:“‘青龙’‘黑马’‘白虎’‘金牛’等四家镖局所出岔事,已由‘灰鼠镖局’的崔镖头,赶来报告过了。”
关长风躬身抱拳:“爹爹可知孩儿业已见着神秘白衣客,并和他互相过手,对了一阵?”
关承祥闻言动容,立向关长风仔细打量地,展露了关切神色……
关长风当然知晓关承祥有询问胜负之意,遂俊脸微红说道:“此人所学,渊不可测,孩儿已竭全力,不过勉强应付了三十照面,终于在‘期门穴’上,中他一掌!”
关承祥神情一震道:“‘期门’乃是重穴……”
两字才出,关长风便接口说道:“请爹爹望安,―来对方发掌时,手下留了分寸,二来孩儿在见那神秘白衣客,谈笑挫败江穿云时,自知不敌,已暗把爹爹所赐的‘风铜护心甲’,佩以护身,故而,‘期门穴’上,虽中敌掌,却未重伤,孩儿受人恩惠,当场酬情,遂在趁势打了他一只‘如意镖’时,也使镖上未曾见血!”
关承祥听得连连点头,似对爱子“以镖酬情”的仁厚光明胸襟,相当满意,口中只轻轻“哦”了一声道:“哦?挫败了江穿云?连‘江家堡’的镖旗,他也动么?”
关长风应声答道:“只拔镖旗,不劫镖银,但那神秘白衣客对付‘江家堡’,比对‘关家堡’,还要残酷一些?‘江家堡’下的出群好手,至少已有三人,死在他的‘吴钩剑’,和‘五行轮’下!”
当啷……
这是关承祥听得“吴钩剑”和“五行轮”等两般兵器名称后,震惊得使手中旱烟袋落地之声!
关长风听得关承祥拾起烟袋,关承祥又向他皱眉问道:“那神秘白衣客所用的兵器,竟……竟是吴钩剑,和五行轮么?他……他的年貌如何?”
关长风道:“中年虬髯,但显曾经过易容,不是他本来面目!”
关承祥又装了一袋旱烟,并喃喃自语道:“吴钩剑……五行轮……会是二十年前的那……那笔债么?‘关家堡’不……不会平安……要……要多事了……”
自语略顿,目中神光电闪,一扫关长风、关少风兄弟,沉声又道:“长风、少风你两兄弟,从现在起,你们要对关家的几桩绝艺,痛下苦功,说不定,我还会找我方外老友,讨个大大人情,把你们送进‘少林’,修炼修炼‘痛禅八法’和‘十八罗汉手’呢!”
关长风有点惊……关少风则有点喜,兄弟两人心情虽略不同,却一齐抱拳躬身!
骆驼的江湖火候,与遇事经验,却似炉火纯青,脸上没有喜怒,没有惊奇,只是令人莫测高深的一片宁静!
议事厅,这仍是议事大厅,但却不是关家堡的议事厅了。
也不是“江家堡”的议事厅,这是明朝中季以后,不论在庙堂上,或江湖间,均极具威势,炙手可热的锦衣卫都指挥使府第的议事大厅。
被昵称为“大档头”的锦衣卫都指挥使梁芳,大马金刀地,高坐厅中太师椅上,脸色不悦,似乎在发脾气!
四五名锦衣卫服色壮汉,神色惶恐,大气都不敢出的,静静垂手,侍立在梁芳面前。
梁芳身后,也有一男两女,身左男孩,是名垂髫剑童,手中捧着梁芳平素惯用不知杀过多少文武官员,和江湖好汉,特宽特长的“血河巨剑”。
身右是一名青衣俏婢,为他伺候烟茶。
背后,则是一名更美更媚的红衣艳婢,在为他捏肩捶背。
梁芳从青衣俏婢手中,接过一只江西细磁盖碗,才喝了两口茶儿,突然发起脾气,戟指众锦衣卫,怒声问道:“你们这群猴儿崽子,办起事来,真笨得让我生气,‘江家堡’的那根毒刺,替我扎好了没有?”
一名年龄稍长的锦衣卫,赶紧躬身抱拳:“回大档头的话,刺儿已扎好了。”
梁芳“哼”了一声,目光微注众锦衣卫中,一个身材特瘦,面容如鼠之人,冷冷的又问道:“‘关家堡’呢,那根钉子,替我栽稳了么?”
另一名面容如鼠的锦衣卫,应声谄媚接口道:“大档头,您望安,对于‘关家堡’,属下可煞费苦心,把那根钉子,栽得毫无痕迹,包管安而又安,稳而又稳!”
梁芳冷笑道:“办得稳妥,是你们份所当为,办得不妥,小心脑袋搬家……”
语音略顿,伸手环指众锦衣卫:“还有更重大的事儿,我要的‘吉祥如意印’,和‘富贵荣华印’呢?”
众锦衣卫面面相觑,那容貌如鼠的瘦削之人,似乎比较得宠,上前半步,哈着腰儿陪笑低声说道:“回大档头,‘吉祥如意印’虽还查不出下落,但‘富贵荣华印’却已稍有迹象,并派人去下手了!”
这名锦衣卫是边自回话,边自暗向正替梁芳捏肩捶背红衣艳婢,递过了一瞥眼色。
那红衣艳婢,果极玲珑识趣,立即手中加劲,把梁芳按摩得十分舒泰,并撒娇笑道:“大档头,您这锦衣卫都指挥使的府第之中,金印、玉印,堆积如山,真所谓不尽‘吉祥如意’,无边‘富贵荣华’,还急于要甚么……”
梁芳“哈哈”一笑,伸手捏了捏这骚媚入骨,红衣艳婢的小腮帮子,向她说道:“芳红,你这丫头,哪里知道,‘吉祥如意印’和‘富贵荣华印’,比甚么‘金印’、‘玉印’都重要万倍,它们和‘星星、月亮、太阳’的关系大得很哪!”
艳婢芳红“哟”了一声笑道:“可热闹了,这里面边有甚么‘星星、月亮、太阳’?……”
垂髫剑童也涎着一张天真无邪小脸,在梁芳身左笑道:“大档头,把这‘星星、月亮、太阳’,和甚么‘吉祥如意印’、‘富贵荣华印’的热闹故事,说给我们听听好么?……”
梁芳似乎对这两婢一童,均极喜爱,点了点头,缓缓说道:“‘太阳’是‘赤阳辟邪剑’,‘月亮’是‘冷月夺魂刀’,‘星星’是‘金星宝藏’!能够把这一刀一剑,和‘金星宝藏’,弄到手中,不单天下无敌,也有吃不尽,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否则,我这威力虽强的‘血河巨剑’,总有一天,会在‘赤阳辟邪剑’,或‘冷月夺魂刀’下,受到克制,故而非要找‘吉祥如意印’,非要夺‘富贵荣华印’不可,你们这群猴崽子,要替我快……快……快……”
梁芳似乎真是情急欲得“吉祥如意”“富贵荣华”双印,每说一个“快”字,便“吧”的一掌,拍在身旁几上。
大厅!
这不是议事厅了,但比“议事厅”更为热闹,这是“四海居”的大厅。
“四海居”是茶馆,是酒馆,也是南来北往等行旅人士所乐于投宿的老字号招商客栈。
大厅中热闹非常的原因,除了有茶客,有酒客,有旅客以外,还有“书客”。
所谓“书客”,是在厅中搭起“说书台”,“四海居”大厅门外,也竖起海报书牌,上写“本店特请评书泰丁老爹,即日开讲三国故事‘火烧连环船’”。
于是,这“四海居”的大厅中,够热闹了,客人的成份也相当复杂!
有土著,有街坊,有行旅,有商贾,有江湖人,甚至还有出家人……
土著、街坊、行旅、商贾,以及江湖人等,可能是茶客,酒客,至于那四位齿白唇红的年轻小和尚,则散站各处,并未就座,连茶都没有泡上一壶,酒更不敢轻易沾唇,他们大概是被书牌海报吸引,想来听段白书,比较比较诸葛先生协助小周郎,火烧赤壁的热闹历史故事,和甚么金刚法偈,佛理禅机,究竟哪一种较有趣味?
江湖人,成份更杂,说书台右前方,坐的便是英姿俊挺,“关家堡”的大少堡主关长风。
说书台左前方,坐的是“江家堡”慓鸷雄壮的少堡主江穿云,和他那相当美艳,但鼻子太尖,尖端微钩,以致显得有点阴刁的妹子江留云。
正面人多,其中最少有四名换了便装的锦衣卫好手,而四名小和尚中,就有两名,站在这群身份最杂的江湖客座位之间。
陡然间,满厅宾客,眼前一亮。
这不是甚么“评书泰斗”丁老爹,开台出场,灯光大明,而是从“四海居”门外,走进了一位光彩照人的特殊人物!
那是一位装束相当神秘,大帽长衫的白衣客,但决非一再拔取“关”“江”两家镖旗的神秘白衣客,而是一位风华高得不能再高,容貌美得不能再美的白衣女郎。
白衣女郎进入大厅,目光四下一扫,见已无空座,遂婷婷袅袅地,走到独据一席的关长风身旁,向他嫣然一笑。
关长风是位倜傥英雄,也明白白衣女郎这一笑之意,更颇为对方的容光所夺,遂相当潇洒的起立侧身,伸手笑道:“姑娘请坐,一切茶资、酒菜,包括书赏,都由关长风作个小东如何?”
白衣女郎更倜傥,更大方,毫不客气地,点头一笑,便由店家加位,在关长风的身旁,坐了下去。
这时,“四海居”的金掌柜走上说书台,清清喉咙,先行举起双手,再抱拳环揖,高声笑道:“诸位贵客,本店为了仰酬诸位的惠顾厚意,特以重金礼聘,评书界的泰山北斗丁老爹,开讲‘三国故事’,今天讲的是‘火烧连环船’!……”
台下的茶客,酒客,以及书客,响起一片热烈掌声!
金掌柜见反应热烈,相当高兴地,转身掀开了后台布帘。
一位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唇有微髭之人,手持摺扇,从后台缓步而出,另外有位极美、极俏,年约十七八岁的短衣女郎,则站在讲台的后角把场。
假若目力稍好,可以在明亮灯光之下看出,这长袍马褂之人头上瓜皮小帽中央,嵌了一面玉牌,玉牌上用篆书镌了“富贵荣华”四字。
慢说阅历丰富的江湖人,就是普通商贾,也一看便知这说书人年龄甚轻,最多只有十六七岁,上下唇间的那点短髭,显然是用化装药物,粘上去的。
故而,他才一出场,台下立起了嗡嗡议论。
一名酒客,愤然于色,不悦说道:“这是什么丁老爹?是丁老爹那个一向极为调皮捣蛋的徒弟海小天嘛!”
坐在他身边的另一名酒客,到神色和缓地,含笑说道:“徒弟替师傅上场,也没甚么不可以,常言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又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我们反正来捧场了,就让海小天显点本领,看他是不是‘后生可畏’?能不能‘长江后浪推前浪’吧?……”
话方至此,海小天已走到台前,朗声说道:“天降吉祥如意,人争富贵荣华,该是你的不会归他,何必你奸我诈?……”
念完这半阕“西江月”,海小天从长袍大袖之中,取出一块相当巨大的紫红“惊堂木”来,“拍”的一声,重重击在书桌上道:“我师傅丁老爹,昨夜喝多了几杯夜酒,又稍得风寒,不太舒坦!今天,请他老人家歇着,换上学徒海小天我来,伺候众位大哥、大姐、二大爷、二大奶奶们,一段三国故事‘火烧连环船’……”
语音顿处,又举起他那块色呈紫红,特巨特大的“惊堂木”来,拍在说书桌上。
在他二度击桌之际,因举木稍高,有眼尖之人,又瞥见这块特别巨大的“惊堂木”上,有“富贵荣华”字样。
海小天惊堂既毕,清嗽一声,正色朗声:“话说魏蜀吴三国年间,孟德曹操带领三十八万大军,亲下江南……”
江穿云性情毛躁,一闻此言,立即停杯摆手,高声怒叫:“胡说,曹孟德下江南时,带的是八十三万大军,你怎么颠倒过来,成了三十八万?”
众酒客哗然大笑,左台角为海小天押阵的短衣俏丽女郎,不禁掩口情急!
海小天到不慌不忙,打开洒金摺扇,摇了两摇,向江穿云抱拳笑道:“请教江少堡主,曹操是忠臣?还是奸臣?”
江穿云双眉一挑,正待答话,他妹子江留云已抢先说道:“那还要问,挟天子以令诸侯,史书上早留骂名,自然是大大的奸臣!”
海小天双手一摊,耸肩笑道:“这不结了,自古奸臣无不贪!那年头,没有回扣可拿,想贪污,只好‘吃空缺’呀,大奸臣吃了大空缺,号称‘八十三万大军’,其中有‘四十五万’的‘空缺’,中饱了曹操私囊,实足人数,就是学徒刚才所说的‘三十八万’!”
台下又是一阵大笑,跟着便掌声如雷!
这时,关长风经过请教,已知同座这美得出奇的白衣女郎,名叫段天心,遂含笑说道:“怎么样?蛮有意思?”
段天心秋波微流:“强词夺理而已,但临机应变,蛮够聪明,可说‘辩才无碍’!”
这时,海小天应付过一次质询,神情更加稳定,继续说道:“曹操这个事过方知的聪明笨蛋,一到江南,先中周瑜的借刀计,杀了惯习水战的蔡瑁张允,又中庞统的连环计,把战船锁成一排,再中诸葛先生的草船计,被借走了二十四万三千七百单八根狼牙箭……”
江穿云上次被海小天巧言饰辩,顶了回来,这次好不容易又抓住对方的错处,便立即大叫道:“又在胡说,无论是蒋干向曹操报告,或鲁肃向周瑜报告,都说孔明草船借箭,十万有余,你怎么……”
海小天向江穿云一摇摺扇,扬眉笑道:“江少堡主,你听我说,蒋干以多报少,是施展清客手段,替曹操稍留脸面,鲁肃向周瑜以多报少,是本忠厚心肠,替孔明略敛锋芒,古往今来,除了我这学有专长,经过苦心考证的海小天外,还有谁能说得出如此精准的二十四万三千七百单八箭之数?”
台下着实对海小天的伶牙利齿,十分喜爱,笑声、掌声、赞美声,响成一片!
一名便装饮酒的锦衣卫刁昌,却突出冷笑高呼:“甚么二十四万三千七百单八箭?我看我该给你三根‘夺魂箭’……”
随着话声,右手一扬,三缕寒光,便向海小天电射而去。
海小天想不到大庭广众,有人行凶,百忙中,一举“惊堂木”,见“叮叮叮”地,木上连中三箭,不禁大惊问道:“这位客官为何好端端的,向我突下辣手?”
刁昌狞笑道:“这就叫‘人争富贵荣华’嘛,你若不把‘富贵荣华印’给我,我就要你这条小命!”
段天心见地下恰有一只乌龟爬过,遂嘴角微披,低声自语道:“要争富贵,我给你来只乌龟!”
脚尖微挑,乌龟凌空飞过,恰好打在刁昌的脑门子上,形状可笑已极!
一位法号“大空”的小和尚,也先合掌念了声“阿弥陀佛”,然后,低低自语说道:“要争荣华,我给你来个嘴吧!”
僧袍拂处,果然向刁昌脸上,一记耳光掴去。
刁昌身手,并不太弱,居然用尽身法,仍未闪开,被这脆生生的一记耳光,掴得身形倒栽,嘴角流血。
刁昌又惊又怒,爬起身来,勃然叫道:“佛掌降魔,是‘十八罗汉手’中招术,你……你……你是少林小僧?”
另一名法名“大慧”的小和尚,从僧袍大袖中,摸出些刀、镖、针、箭、暗器,放在刁昌桌上,合掌说道:“阿弥陀佛,这是你身上所带的一些零碎,件件都喂奇毒,见血封喉,可见得不是好人,一记‘罗汉手’,是我‘大空’师兄,心存慈悲,换了我这嫉恶如仇的小和尚,就毫不客气地,要超度你一记‘开碑手’了!”
刁昌见有少林僧人卫护海小天,自知不敌,立即脸色大变,发出一声胡哨。
其他几名便服锦衣卫,以及与他们蛇鼠一窝的江湖人,立即纷掣兵刃,推翻桌椅!
“四海居”中,当然乱成一团。
海小天作了个调皮表情,咋舌说道:“乖乘,有人行凶,想抢夺甚么‘富贵荣华印’,‘火烧连环船’既说不成,我只好逃命去了。”
转身拉着尚在台角为他押阵,但已被意外变化吓得有点发呆的师姐丁香,双双闪入后台。
先追海小天的,居然是江穿云、江留云兄妹,江穿云并毫无顾忌地,高声喝道:“海小天,把你手中那颗‘富贵荣华印’,留下再走!”
段天心见状,微扬双眉,看着关长风道:“关少堡主,这群东西,简直目无王法,仗势欺人,你管不管这种不平之事?”
关长风毫不迟疑,应声答道:“身在江湖,虽不可以武犯禁,却应匡国法之不逮,这就叫‘每见人间不平事,胸中常作不平鸣’嘛……”
他答得既快,走得也快,随在江氏兄妹后,人化轻烟,飘然出店!
段天心目送关长风英挺背影,满面佩服嘉许神色,一挑拇指,含情自语说道:“俏侠士,好男儿,要管不平,就大家一齐管吧!”
白衣飘处,也紧随在关长风之后,出了“四海居”。
这是一处静僻山野,海小天喘气跑来,神情狼狈,和他一同逃离“四海居”的师姐丁香,业已不知何往,不在他的身边。
海小天扶着一株大树,上气不接下气地,自语说道:“哎哟我的妈呀,我可跑不动了,这一帮人,怎么个个如狼似虎,这样凶法?……”
江留云突然出人意料地,从树后闪出,向海小天笑道:“海小天,你跑不动么?我有办法。”
由于江留云貌相尚美,不太凶恶,海小天遂不太怕她地,拱手说道:“江姑娘,请教高明,我实在跑得太累怎么办呢?”
江留云指着山壁下的一块大石笑道:“累了,你就坐下。”
海小天委实太累,乘乖如言坐下后,抚掌笑道:“江姑娘确实高明,坐着比跑着舒服……”
江留云不理会他这卖傻装痴的讽刺之语,只是看着海小天,冷冷说道:“可惜你舒服不了好久,大批追兵,马上就到,他们有‘天目三霸’、‘浙东双绝’,和东厂锦衣卫等,一般凶神恶煞!”
海小天似乎有点不服气地,一挑双眉道:“我也有朋友,朋友们会帮忙呀!”
江留云点头笑道:“我知道,那几个小和尚,似乎是你朋友?但一来他们共仅四个,人数太少,二来少林僧规律极严,他们定是私自下山,不敢轻易犯戒,又怎样应付抵挡得了那些无所不为的凶神恶煞?”
海小天站起身形,向江留云深深一揖:“江姑娘,海小天急难无计,再度请教高明!”
江留云笑道:“凡事要溯本追源,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场祸变,既从‘富贵荣华印’而起,你不如把它丢掉,或是索性送给别人,两手一空,就可以轻轻松松,脱身事外的了!”
海小天一摊双手,苦笑说道:“江姑娘说的虽是高明治本之策,但我身边既不‘富贵’,又无‘荣华’,哪里来的甚么‘印’啊?”
江留云闻言失笑,目注海小天道:“你自己当真不知道么?就是你在‘四海居’中,开讲‘火烧连环船’,所用那块镌有‘富贵荣华’字样,紫红色的惊堂木呀!”
海小天不以为然地,嘴角一撇说道:“一块烂木头嘛,又有这么多麻烦,送给谁会要呢?……”
江留云伸手笑道:“送给我吧,因为我的武功还好,又仗着‘江家堡’在大江南北的多年威望,还可以勉为其难,帮帮你的忙儿,替你抵挡一阵!”
海小天满面感激神色,伸手入怀,看着江留云道:“好吧……”
这“好吧”两字,刚刚出唇,就有人接口说了“不好”两字。
接口之人,居然是比江留云更美,而美得脱俗,美得出尘的白衣女郎段天心。
段天心飘然现身,伸手拦住海小天道:“海小兄弟,你不要把那惊堂木送她,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江留云事败垂成,勃然大怒,向段天心那身神秘装束,恶狠狠地盯了几眼,冷笑说道:“我是黄鼠狼,你是甚么狼?瞧你这一身白,大概是只想来白捡便宜的白眼狼吧?”
海小天听得有趣,竟忘了害怕,抚掌笑道:“有趣,有趣,一个黄鼠狼,一个白鼠狼,两个都是又勾勾,又丢丢,花不溜丢的大姑娘……”
话方至此,“天目三霸”,刁昌以及其他形相凶恶之四五名江湖人物,已把海小天退路封住。
海小天耸肩摊手,苦笑说道:“这些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大野狼嘛!我海小天,身陷狼群,恐怕要龙归沧海,玩儿完大吉……”
段天心生恐海小天突然中人毒手,遂挺身挡在海小天之前,笑道:“海小兄弟,你这句‘龙归沧海’,提醒我了,一群狼,也斗不过半条龙,我替你找条龙来,救救命吧!”
语音一落,剑光立闪,逼开首先接近海小天的锦衣卫刁昌,口中漫声高吟:“龙……在……江……湖……”
一条极潇洒的英挺人影,宛若游龙,在段天心的漫声长吟中,飘然而至,赫然正是关长风。
段天心向关长风一挑拇指笑道:“关少堡主英风侠胆,真不愧是条‘江湖之龙’,但你这儿,是否来得太慢一点?”
关长风向段天心拱手拱手,摇头苦笑道:“不是我来得慢,是必须先救丁老爹,有不肖之徒,偷袭丁家,丁老爹已受重伤,连丁香姑娘都差点儿遭了毒手!”
海小天闻言,不禁顿足大哭道:“哎哟,我的师傅……我的丁香姐呀……”
关长风正向海小天劝慰间,“天目三霸天”中,最阴险狠毒的“蛇霸天”,已以“蛇形毒剑”,悄无声息地,向关长风后腰,挺臂飞刺!
关长风勃然大怒,长剑出鞘,一式“龙战四野”,便把对方那柄“蛇形毒剑”,震得裂碎几段,连“蛇霸天”的右手虎口,也告涔涔出血!
“蛇霸天”骇然大叫:“点子扎手,并肩子上!”
“天目三霸天”中其余的“虎霸天”和“金镖黄霸天”,立即出手,刁昌见有便宜,也加入战斗,向关长风发动围袭。
江留云似乎对段天心特别看不顺眼,扬眉冷笑说道:“他们在男斗男,我们也来个女斗女吧!”
段天心也讨厌江留云神情刁媚,秀眉微挑,“哼”了一声道:“要斗就斗,我又不会怕你,‘江家堡’的那点势力,已渐衰微,也欺压不到我的头上!”
语音落处,两条窈窕人影,便自凤翥龙翔,斗在一起!
海小天一见群雄混战已起,便拔脚悄悄开溜,心中暗暗祝道:“老天爷请多多保佑关少堡主和江姑娘吧!我海小天不是不够义气,自己单独开溜,是太关心我师傅和丁香姐了,想去看看他们,有没有甚么急难灾厄,需人帮助?”
关长风动手不久,发觉情况不对!
围攻他的“天目三霸天”,和锦衣卫刁昌,倒并不对他构成严重威胁,但段天心、海小天二人,却告失去踪迹!
关长风看出段天心是巾帼奇英,身手不弱,倒并不十分担心,只觉得海小天不会无故失踪,多半是落入魔掌!
义愤一动,肝火立腾,青钢剑“天台觅路”,转化“笑指天南”,先把“蛇霸天”的胁下,划了半尺长的一条血口!
踉着左掌掌演“推山震虎”,“斜划鸿沟”,飞切在“虎霸天”左大腿近胯之间,硬把这雄壮凶人,击得发出一声惨嚎,身形仰跌出四五步去。
就在剑刺“蛇霸天”,掌震“虎霸天”之际,关家独门秘传的“如意神镖”,也招呼了“飞镖黄霸天”!
黄霸天本以“飞镖”成名,却偏偏逃不出关长风的“如意镖”下!
关家的“如意镖法”,难怪威震大江南北,关长风不单仅仅掌握了独斗四名武林豪客,好容易觅出的一刹那空隙,并是在绝不可能的诡异角度下,奇妙出手,使那一向惯于用镖伤人的黄霸天,左右双肋,各挨了一枚“如意神镖”。
“天目三霸天”劲敌一败,关长风神威陡发,龙吟起处,一式“武行者醉踢蒋门神”,双足起处,便把那满面凶光的锦衣卫刁昌,踢得跌了个黄狗吃屎!
关长风虽胜不骄,连讽刺对方的话儿,都未说上半句,便急闪身形,飘然离去。
他当然不是胆怯,只是心急,急于尚有其他觊觎甚么“富贵荣华印”的豺狼虎豹,莫要使那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而又十分调皮可爱的海小天遭人毒手,有甚不测?!
但才转过那角山壁,走未多远,关长风便剑眉双蹙地,止了脚步!
他不是发现海小天已遭祸事,而是发现段天心倚壁而立,手抚右肩,白衣上一片殷然血渍!
关长风失惊道:“段姑娘,你……你……你……你……”
段天心不等关长风发问,便苦笑说道:“我和江留云倒是斗得胜负难分,但见海小天先走,怕他独自遭人算计,遂随后欲加防护,谁知江留云刁狡异常,竟追来造一谣言,说关少堡主已遭群凶合力所伤,我闻言之下,心惊失防,反而中了江留云的暗算!……”
关长风接口道:“甚么暗算?不会是她江氏家传的‘蝴蝶镖’吧?”
段天心点头道:“正是……”
“正是……”二字,才一出口,手儿松开,右肩头的白衣血渍之中,果然有只五色斑烂的展翅彩蝶!
“江……江留云呢?……”
段天心道:“去追海小天了,关少堡主找她则甚?……”
“江家的‘蝴蝶镖’,和我关家的‘如意镖’不同,恐怕镖上有毒……”
段天心凄然一笑,点头接道:“不单有毒,而且是极厉害的独门剧毒,我虽然已服了自己的一些护心药物,但仍知药不对症,恐怕活不到明日此刻!”
关长风“唉”了一声,顿足道:“事不宜迟,我得赶紧去找江氏兄妹,只要能找到江留云,或是江穿云,便有可能弄上一些‘蝴蝶镖’的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