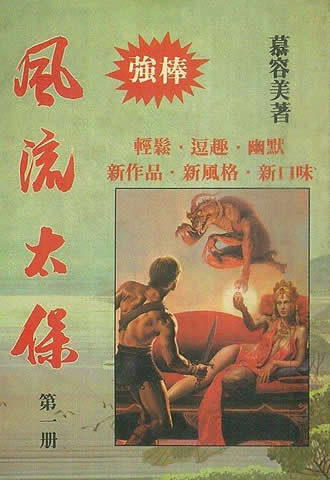茂兴绸缎庄门面高大,里外都装修得很富丽很有气派,所以除非是大客户,普通人若是打算只买几尺花绸,还真不敢踏进大门。
林掌柜大概五十来岁,面上总是挂着和霭的笑容。从他举止及不时命令其他掌柜伙计做这做那的派头看来,他就算不是老板,也一定是全权替老板看守荷包的人物。
他把那个抱着一岁婴儿的少妇请到一间华丽会客室,他注意到这位打扮朴素的少妇对绸庄堂皇气派以及华丽陈设布置都毫不惊讶畏惧。她走动或坐下一切举止都很娴雅大方,全无丝毫侷促之态。
林掌柜拿着一封信,那是她特地来交给他的,但林掌柜却没有拆开,并且请她到会客厅,显然有机密话要说。
林掌柜道:“这封信暂时会耽搁一下,相反的我这儿也有一封紧急密函要给沈神通,可是他已不在杭州,所以我没有法子把这封信交到他手中。”
那少妇迷惑地道:“这是怎么回事?”
林掌柜再打量她一会,才谨慎地问道:“你是沈神通的女人?你贵姓名?”
那少妇点点头道:“我叫马玉仪。”
林掌柜道:“这孩子也是他的?叫甚么名字?”
马玉仪答道:“是他的孩子,叫做沈辛,辛酸的辛。”
林掌柜皱眉摇头道:“就算你们经历过辛酸辛苦的日子,也不必在孩子身上留下痕迹。”
马玉仪道:“也许不应该,但这却是事实。我们不必把悲惨的事实用美丽的绫罗绸缎遮掩起来,对么?”
林掌柜叹口气,道:“你一定有过很可怕的悲惨遭遇,人往往在苦难中才会成熟。”他同情地望住马玉仪,又道:“如果我这封密函托你带给沈神通,他会很快收到么?”
马玉仪道:“不知道,可能很快收到,也可能永远收不到。”
林掌柜道:“我明白,干他们这一行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他几时回来。唉,沈夫人既然你抚育他的孩子,我只想知道他临走时留下多少钱给你?如果他很久才回来,你母子的生活能支持到甚么时候?”
马玉仪没有直接回答,只微笑一下,但笑容中却含有无尽辛酸凄凉,甚至惊惧。她道:“那已经不是重要问题了。”
林掌柜柔声道:“比起一个人的生死,钱财固然是不重要,但问题是你和小儿子沈辛还要活下去。”
马玉仪道:“三五年之内不成问题。”
林掌柜道:“那么我替你安排一下,希望一二十年之内都没有问题。你顺便把密函带去,也希望你很快很快就交到他的手中。”
如果她能够很快见到沈神通把密函交给他,那就等于说沈神通已经无恙已经安全。当然这是人人都愿意为她祝福、愿意看到的结果。
但沈神通已经到了镇江,也已经入了虎穴。他究竟要干甚么?究竟能不能回来呢?
×
×
×
破旧狭窄的房间,一灯如豆闪动着昏黄光芒,臭虫联群结队在墙壁床铺间游行示威。
这种第三流的旅馆,谁也不相信浙江省总捕头会落脚居住,而且一住就三天之久。
不过沈神通安慰自己又安慰得力助手“笑面虎”何同说:“爬险峻的高山,开始时步伐必须缓慢(注)。”
“笑面虎”何同只有廿余岁,外表像个白面书生,永远带着微笑,完全不似公门捕快。但事实上他嘴巴很牢,武功很好,为人机警又不贪酒色钱财,所以沈神通近两年一直带他在身边一直训练他,因此何同已经成为沈神通的衣钵弟子,成为浙省公门第二把高手。
何同连一句都不问为何要等候这么久还不动手缉拿严温?就算不久会被臭虫蚊虫吮干了全身血液,他也绝对不会多嘴询问。
当然沈神通并非故意隐瞒,并非对何同有提防之心,只不过时机未到,所以懒得提起,懒得谈论。关于“公事”方面,他们照例不肯多讲一句废话。
第四天早上他们跑到菜市场吃过牛肉油豆腐细粉,一路走回客栈,路上何同曾经掏一把铜钱施给一个乞丐。
他们没有回房间,却在客栈附近一间茶馆各泡了一壶龙井。茶客已经不少,其中有很多托住鸟笼,神色悠闲。
沈神通羡慕地叹口气,道:“他们并非有钱人,他们等一会就要开始做事,但他们日子过得优游自在,工作时也许很辛劳,但一个鸟笼,一杯龙井,或者加上几盆花草,便足以使他们的人生另辟境界,使他们内心没有煎熬没有烦躁。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熬过艰苦年头,不但不被生活重担折磨成神经病,反而还能从恬澹中享受到一些乐趣。”
何同的微笑消失一下,就像把面具暂时收起来,然后又挂上了。说道:“但我们决不可能过他们那种生活。沈公你办得到么?”
沈神通道:“我从前不行,但现在却可以了。我可以在长江边那座房子过隐居生活。我可以一年足不出户……”
何同当然知道南京靠江边那座房屋就是马玉仪和小儿子沈辛的居处。那儿已离开城市,但屋后不到一里就有村庄,那儿也就是沈神通另外一个家。看来沈神通的“心”已经放在这个家,而不是放在杭州的家了。
也许过一二十年之后,何同也可以收敛隐退,但现在却绝对不行,现在还不能接受不能欣赏那种清淡生活。所以他说:“沈公,请振作起来,等完成这次任务才考虑别的问题。”
沈神通点点头,道:“你接到甚么消息?”
何同只怔一下就笑道:“没有事情能瞒过你的眼睛么?”
沈神通道:“希望没有。你这一次好像比以前沉默,你的招牌(笑容)也常常消失不见,你有心事?”
何同想了一下,忽然道:“沈公,我们能不能放弃这一次任务?反正不是在我们辖区,而且我们有很多时间,我们可以设下罗网耐心等待,等到‘他’自投罗网那一天。‘他’一定会到杭州,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沈神通道:“这就是你的心事?”
何同道:“我们在这儿势孤力弱,你又不肯叫这边的人帮忙。但‘他’却正好相反,此地是老巢穴老根据地,精锐尽聚于此,我觉得好像以卵击石,我们是鸡蛋,他们是石头,您认为如何?”
沈神通道:“你到底得到甚么消息?”
何同道:“只知道‘他’还在家里,三天以来,未出过门口一步。”
沈神通道:“那乞丐很年轻,眉清目秀,脚下也有点功夫。他是你布置此地的眼线?”
何同道:“是的,已经一年多,但从未动用过。”
沈神通慢慢地站起身。何同深深叹口气道:“我们不能张设罗网?我们非去不可?”
沈神通声音很轻很低,有如耳语却十分清晰,道:“对,因为有一个鸟笼告诉我,马上就有一辆马车会驶入一条地道。我们必须乘搭这辆马车,这是唯一的空隙,也是‘他’身边最少人护卫之时。”
何同目光扫过桌子上七个鸟笼,但看不出任何一个有甚么异状。他颤栗一下,似乎忽然掉在冰窖。这个“老总”永远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奇妙布置奇妙手法,而且他几时在镇江埋下了“线人”呢?
踏出茶馆时,何同居然还提到“罗网”的事。他道:“沈公,我们还是回杭州张设罗网的好。‘他’不是简单之辈,而且他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我们真能够顺顺当当入虎穴探虎子么?”
(注:语出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
×
×
×
马车在黝黑地道缓缓驶行,车伕一手拉住嚼环徒步带路,所以马匹不必用眼睛,亦不会惊慌乱发脾气。
车里有两个乘客,本来是两个妙龄美丽的少女,但现在已换上沈神通和何同。
马车忽然停住不动,在黑漆的车厢里沈神通伸手拍拍何同肩膀,接着互相摸到对方的手,互相紧紧握一下,这一握当然表示了很多意思。
沈神通感到何同的手掌十分冰冷,而且也有冷汗,因此他再拍拍何同肩膀,示意他安慰他不要太紧张。
马车其实已经停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内,车伕走到角落扯动一条红色绸带。
车帘深垂,沈神通稍稍弄开一点缝隙,车厢内立刻明亮得可以看手相看掌纹。
平滑墙壁上忽然轧轧微响,露出一道门户。
沈神通很希望门口出现的人是严温,但他不能不微感失望,因为出现的是一个卅岁左右的女人。
这个女人面貌五官只能形容为端正而已,美丽谈不上,但她却有一股能溶化男人的热力四射。这是因为她身上只穿一件薄如蝉翼简直透明的外衣,而外衣之内显然并无其他衣物。
所以那对高耸震荡的乳房,小腹下面隐秘地带,都能大致看得见。
“大致”的意思是看得见却并非纤毫毕露。这女人身裁之佳美性感,恐怕一万个女人也选不出一个。所以她能使男人觉得像是掉在铸铁炼钢的火炉一样,炽热得使人受不了。
马车伕面向屋角,变成一个木人似的,没有回头瞧看。
那个性感女人根本不是走路,而是滑行于坚冰上,一下子就滑到马车前。
她伸手撩开车门厚厚的帘幕,忽然睁大双眼,满面俱是惊诧之色,但她居然不叫喊,也不会逃走。这是因为她一来已经哑了,根本发不出声音,二来她雪白的颈子上已被一条金色链子缠住,就算能够叫喊也叫不出声音,当然更不能退后逃走了。
缠住她脖子那条金链形状正如公门捕快所用的锁链。天下能使用这种兵器只有一家──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所以沈神通是孟知秋的嫡系弟子绝无疑问。而金锁链套住那哑女人颈项那种无声无影的手法,真是叫人叹为观止。
沈神通柔声道:“你不必着急,也不要挣扎,我知道你是谁。”
哑女人身子靠倚车门边,既无力移动全身任何一部份,同时亦发不出声音(假设她不是哑巴的话),只有眼睛还能转动,骨碌碌瞧看车厢内两个男人。
沈神通又道:“如果严温在书房里,我想见见他,但我并没有暗杀他的意思。我们是执行法律的人,如果他的确有犯罪,那也是法曹的事。又如果我们跟他有私怨,亦不会做出公报私仇的事,希望你肯相信我。”
哑女人用眼睛表示相信。她只用眼珠转动的动作,就居然使两个男人十分明白。
沈神通又柔声道:“现在我们去跟严温见面谈一谈好不好?”
哑女人居然表示“不好”。
沈神通坚持道:“不行,我们非见他不可。告诉我,他就在那边书房里?有没有别人?”
哑女人眼珠竟然能表示不少奇怪意思,其中包括“严温在书房”、“不要进去,请不要进去”、“危险,快离开此地”等等。
沈神通心灵上忽然发生感应,情况似乎奇怪而且不妙。为甚么?莫非严温已有准备?已经布置足够人手?但严温怎能知道?是谁泄漏了秘密?
何同的微笑招牌老早已经消失。他一定也觉得情况不妥,所以轻轻说道:“沈公,等有机会才卷土重来好么?”
沈神通叹口气,道:“你和我一样心里很清楚,如果真有问题,回头之路也绝对走不通。”
何同喃喃道:“是的,是的。如果有问题,大江堂精锐伏兵一定早已堵死回头之路。”
沈神通潇洒笑一下,柔声道:“你且在马车内歇一歇,女孩子看见凶杀场面到底不大好。”
哑女人当然没有反抗或抗议余地,她躺在马车内之时,已经被点了穴道昏睡过去。
沈神通当先下了马车。何同眼光在哑女人丰满得极能诱惑男人的身体上巡梭一会,才跟着下车,并且拔出长刀。
这两个公门“强人”终于走过那道门户,置身于一个比厅堂还宽大的“书房”内。
对面角落有一张铺着虎皮的太师椅,俊秀白净的严温坐得四平八稳,一点也不因为沈何二人出现而惊讶。
沈神通大步走过去,距他寻丈才停步。说道:“我看我只怕今天无法离开贵府了。你就是严温?你的确长得很漂亮,很俊秀!”
严温懒洋洋指指墙边的靠背椅,道:“请坐。老实说,公门中人也只有你们两位能踏入我的书房,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
两张交椅当中的紫檀木茶几,已经放着两杯香茗。
沈神通居然坐下,何同自然也跟他一样落坐,并且还拿起茶杯啜饮。
沈神通忽然提出比利刀还锋利的问题:“严温,你已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大人物,你为何还要强奸女孩子?而且强奸了很多个?”
严温轻轻皱起眉头,道:“现在恐怕只有我问你而不是你问我,你说对么?”
沈神通冷笑一声,道:“不对,因为如果你的回答我认为满意,又如果有我满意的保证,我很可能跟你和解。有我点点头,至少有六省吃公事饭的人不会找你的麻烦。”
严温愣一下,才道:“你?沈神通也会跟我这种人打交道谈条件?”
沈神通道:“当然不会,但我真想不到棋差一着,所以我也不得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了!我仍然希望你回答我的问题。你肯不肯回答呢?”
严温沉吟一下,缓缓道:“本来你说得不错,对于女人我严温何求而不得?但我却觉得不够刺激……”
沈神通严厉批评道:“你心理有问题。你狂妄自大惯了,所以根本不曾替别人想过。难道这世界上只有你最重要?”
严温泛起苦笑,道:“别这么凶好吗?如果不是六省公门不找麻烦这种巨大诱惑,我理睬你才怪!”
沈神通又冷笑道:“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不管你大江堂已调集了多少精锐高手在此,就算他们能把我剁成肉酱,可是现在我一出手,仍然能够早一步杀死你。因为你剑法虽然不错,却只不过得到‘血剑’严北的三四成真传。你最好相信这一点。”
严温面色变得很苍白,道:“我相信。”
任何人只要看见沈神通烱烱目光以及无限自信的神情,绝对不能亦不敢不相信他的话。
严温又道:“你到底想怎么样?难道想把我抓回去审讯定罪?”
沈神通道:“原来是这个意思,不过现在……”
他眼睛转向窗外,外面数株参天古树映眼一片苍翠。“绿色”的确能使人有宁静之感,也使人想到广阔无垠、无拘无束的大自然。但沈神通却从清凉碧绿中看见马玉仪,也看见小儿子沈辛胖嘟嘟的面庞。
他知道目下尚有一线机会,所谓机会只是指公事而言──因为他可以突然出手,与严温拚个同归于尽。但这世间的一切,尤其是马玉仪和小儿子,却是永远永远也不能再见了!
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你是沈神通,你会怎样做呢?
×
×
×
马玉仪把屋子里外都打扫抹拭得纤尘不染,屋里家俬固然干净不过,但她却变成有点蓬首垢面了。
“忙碌”通常能使人没有时间流泪,尤其是等待着未可知却可怕命运揭晓的人,忙碌是消磨时间最好的方法。
所以马玉仪把几件衣服放在竹篮里,又把新铺好的床单换下来放入篮子,另一手抓起捣衣的木杵,匆匆走出家门。
园子里菊花开得正盛,空气中浮动桂花馥郁香味,秋日温暖阳光使万里晴空更显得旷朗蔚蓝。
可惜马玉仪甚至不敢在园子里多停留一阵,因为在这儿她会听到沈神通的笑语,会看见他充满欢笑活力的面庞。所以她走到江边,沿着一道伸入江水的石阶下去。
紧接水面的几层白色石阶特别宽阔些,以便于几个人同时洗涤衣裳,甚至可以几个人坐在阶上眺望着亘古东流滔滔茫茫的江水。
马玉仪忽然大吃一惊,因为她看见左面峭直江岸边,有一个白色的人躲在树丛里。
假如不是相距只有六七尺,又假如她不是从侧面缝隙望入去,绝对不会发现丛生灌木里面竟然有一个男人,而且这个男人居然没穿衣服,白皙皮肤也使他更为触目。
马玉仪跟着又知道这个裸体男人已经对她不构成威胁,因为他显然已经昏迷,只靠双手环扣丛树根部,所以虽然下半截身子还泡在水里,还随着江浪飘摆,却不曾随波逐流而去,不曾葬身江流鱼腹中。
她刚得到一个印象,这个裸体年轻男人长得很俊秀,就已经无暇视察他了,因为一艘顺流而下的巨舶向她驶来,相距虽然尚有数十丈之遥,但马玉仪却感觉到那艘巨舶是向她驶来,而且一定跟裸体男人有关。
马玉仪开始不慌不忙拿出床单衣物泡在水里。她知道就算巨船来到两三丈之内,但由于角度关系,决计瞧不见那裸体男人。
巨舶不一会就到了三十步之内,篙师设法把船停在那儿。船头上一个女郎长得很美,一身雪白雁衣在江风中飘拂。而马玉仪却注意到她鬓边插着一朵白绒花,因此她那一身飘逸衣装便变成惨淡丧服了。
那美丽的白衣女郎声音不高,却能透过江风,透过江浪呜咽声,很清楚传入马玉仪耳中。她道:“你常常在这儿洗衣服么?”
马玉仪装出惊讶神色,大声道:“是的,洗了很多年啦!”
船上女郎又问道:“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一个没穿衣服的男人?”
马玉仪道:“你说甚?我听不懂?”
有人说一个好的男人每天说谎十次,好的女人却每天说谎廿次。可见得“说谎”乃是人生日常不能不做的事情,而却以女人为甚。
马玉仪随口应答,简直不必考虑──虽然她说的都是谎话。
船上白衣女郎道:“你长得很漂亮,可惜没有梳洗而且不会打扮,你要不要跟我走?我会把你打扮得比孔雀还美丽。”
马玉仪摇摇头道:“不行,我儿子快醒啦,我儿子一醒就要吃奶,我不能够走开。”
白衣女郎道:“多可惜,我甚至看不出你已生过孩子。你儿子叫甚么名字?”
马玉仪应道:“他爸爸姓沈,我叫他小辛。”
白衣女郎道:“小辛?好怪的名字,但一定很可爱。”她从皓白如雪的手腕褪下一只金镯,又从头发上拔下一支金钗,很快地用金钗在镯上刻几个字,然后把金镯丢到马玉仪的竹篮内。马玉仪一时倒没有想到白衣女郎何以能够在三丈之远随手就把金镯丢入竹篮。
白衣女郎道:“给小辛,希望他平安长大,希望他将来变成不平凡的人。”
马玉仪不觉呆住,却发现一转眼间巨舶已经随着滔滔江水远逝,不知驶向何处。
她当然已不能安安静静洗衣服了,这一幕冲击得她紧张而又兴奋。
树丛内那个裸体男人究竟是谁?是好人抑是坏人?白衣女郎是谁?她送了一只金镯给小辛,看来好像不是坏人。但如果她不是坏人,则她追赶的人当然就是坏人了。
不过世事却又绝非如此简单,好人可以追赶坏人没错,但好人何尝不能追赶好人呢?
何况那个裸体男人瞧来一点也不似是为非作歹之徒,他究竟是不是坏人呢?
马玉仪忽然站起身,并且很快将床单撕开,联接成一条相当长的“绳索”。
她很艰苦才爬入树丛,将床单一端缚住那男人,另一端已经系在石阶(亦即是码头石级)边的树根,然后用中指勾住那男人拇指根部的“鱼际穴”,食指则勾住他拇指尖的“少商穴”。
马玉仪只用少许气力,那裸体男人双手环扣忽然松散,因此他整个人沉坠水中,接着随波逐流漂走。
但马玉仪毫不着急,慢慢爬向石阶,然后扯紧床单撕成的长索,很快就把那男人拉到石阶边了。
看见他男性的身体,马玉仪不免有点不好意思,但现在已无可选择,非赶快做下去并且把事情做妥不可。
幸而附近没有人家,所以她可以把裸体男人横拖直拽,而且休息了七八次才拖回屋子。当然她已经发现这个男人右腿上有一支金色长箭,但她却不敢胡乱动手拔下来。
用一碗热腾腾的红糖姜汤灌下去,那裸体男人不久就悠悠回醒,于是马玉仪知道他姓雷名不群。
雷不群虽然文秀白皙,但身体很好,回醒之后除了皱眉忍住箭伤的疼痛之外,竟也可以述说他的遭遇。
马玉仪说道:“你所讲的人,甚么桃花溪宋家,甚么血剑严北,甚么海龙王雷傲侯我都从未听过。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法子把腿上的箭拔出来?”
雷不群尽量小心揭开被子,以免身体裸露得太多。他仔细看过那只金箭,叹口气道:“想不到‘射潮弓’竟是在她手中。这一支是沉鱼落雁箭之中的‘沉鱼神箭’,怪不得我在水里仍逃不了一箭之厄。”
马玉仪只问道:“现在怎么办?”
雷不群寻思半晌,才道:“此箭已贯穿我右腿,如果直接硬拔的话,箭镞会造成更大的伤口,但此箭杆却又是五金之精铸成,没有可能拗断。”
马玉仪讶道:“莫非永远任得此箭插在腿上?那多不方便?何况还会痛?”
雷不群道:“箭翎是羽毛,可以割掉或烧掉。这样箭杆大小一样,就可以从另一头拔出来了。”
马玉仪立刻找出剪刀,将两片美观的箭翎剪掉,一面道:“很简单不是么?为何你不早说出来呢?”
雷不群苦笑一下,突然手起掌落,拍在箭杆末端,又从另一端两指箝住箭镞,一下子就将金箭拔出。
他大腿两个伤口都流出鲜血,大腿里面当然更痛,因为任何人在腿肉上开一条通道岂有不痛个半死之理?
他包扎好了之后,只淡淡的好像谈论别人事情一样告诉马玉仪说:“这个拔箭方法很不妙,因为箭翎有毒,我这条腿已经残废,终身都变成跛子了,所以我没有早说。”
马玉仪不觉獃住,她早已感到世上很多事情表面看来简单,其实不然。现在这个感觉更强烈更鲜明。她问道:“你早已知道?”
雷不群道:“是的。”
马玉仪道:“你怎会知道的?”
雷不群叹口气,道:“因为我父亲是‘海龙王’雷傲侯,所以总比别人多知道些。这支箭上面镌着‘沉鱼’两个字,如果是‘落雁’那就是银色的。”
隔壁传来小儿啼哭声音。马玉仪轻轻道:“是我的儿子,他叫沈辛。我希望他长大之后能有你的学问,能有你的勇气,还有能有你的潇洒风度。”
雷不群道:“他一定会,而且比我好得多,因为你先生不是普通人,而你也不是凡俗的女孩子,所以你们的孩子也一定不平凡。”
马玉仪不禁变色道:“你知道沈辛的爸爸是谁?你见过他吗?”
雷不群俊秀的面庞上居然有汗珠。这种天气只盖一条薄被绝对不应该热得流汗。所以马玉仪更狐疑更担心了。他流汗,是不是表示心中有愧呢?
“你是不是曾经在附近窥伺过,所以知道我先生是谁?”
雷不群微笑道:“没有,我为甚么要窥伺你们呢?只不过有些事情可以用脑子想出来的。你年轻而又美丽,你先生不在家,但你却敢把一个负伤男人带回家(他虽然不提裸体这件事,其实口气中已包含此意),而且你似乎不怕你先生突然回来,不怕他看见我这副样子。你为何不怕他误会呢?还有就是你先生是甚么职业呢?我看不见任何可以推测他职业的线索,就算做木匠,也应该有些工具。既然没有一点线索,反而证明他不是普通人,当然你也不是普通女孩子,所以才配得上他。”
马玉仪讶道:“你说得头头是道,说得很有道理,但你为何流汗呢?”
雷不群道:“那是因为我腿上箭伤毒力发作之故,我想现在我还是快点告诉你为妙,我很可能会疼得昏迷不醒,我会发烧发冷,但只要多喝白开水,不必吃药,熬过三天后就会痊愈。有时候有些毒药药性很奇怪,你既不能也不必使用其他药物,只靠本身的抵抗力熬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了(感冒的过滤产病毒便是如此)。”
马玉仪忙道:“我很抱歉,我居然没有想到你流汗是因为伤痛之故。但请你再支持一会,请暂时不要昏迷,我想知道我要不要通知甚么人?那个穿白衣服美貌新寡的宋夫人会不会再到这儿来找你?如果她来,我该怎样做?难道把你交给她?”
雷不群道:“对,如果她能够找上门来,你一定要将我交给她。”
他想起黄莲的倩影,也想像得出她用恨恨神情盯住他与及恨恨地扼住他脖子的样子。唉,你为何不把我一箭射死呢?我跛了一条腿,终身成了残废,活下去又有何意思?
他觉得自己疼痛得快要昏迷,所以赶快又道:“如果可以的话,我最好在这儿躺三天。请切勿通知任何人,因为你一定找不到家父,只徒然走漏消息反而替你惹来麻烦。”
马玉仪疑惑不解,道:“我进城一趟,去见你父亲并不是难事。他不肯见我?他不会相信我?”
雷不群道:“家父将宋去非的尸体送回船上,虽说已经侦查出,也已经得知我的情况,所以利用‘棺木传香’使我恢复行动之能,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要离开南京,要我隐姓埋名。如果我不改名换姓不离开南京,别人不说,单单是黄莲为了报杀夫之仇,就决不肯罢休。你想想看,她丈夫已死于家父手中,我就算有能力,我能杀她么?如果不杀她,事情又会变成怎样呢?”
马玉仪叹口气,道:“我总算明白了。”
雷不群竟然还未昏迷,所以能感觉得到她替他拭汗时温柔动作,显示她的善良仁慈天性。如此美丽如此年轻,又如此善良的女孩子,何以居住于如此偏僻地方?何以害怕有人窥伺他们?
可惜现在他已经毫无能力帮助她照顾她。所以他叹口气,道:“希望你先生赶快回来,我一定劝他带你搬到别的地方居住。此地太荒僻了,附近周围都没有人家的。”
马玉仪道:“如果真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就算附近有很多人家也没有用。”
雷不群道:“对的。”
马玉仪说道:“何况我们不想被人知道。但如果住在城里,那里的公人都认得他……”她忽然发觉这些话会泄露身份,所以立刻闭上嘴巴。
她的警觉很有道理,因为雷不群一听见“公人”两个字,马上就联想起公门中赫赫有名的沈神通。
马玉仪深深喟叹一声,道:“我也希望他早点回来,如果他不回来,那就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她的话既惨澹不祥而又不大合逻辑,但女人往往用这种方法表达内心意思,她们脑筋里向来不大理会逻辑不逻辑的。
雷不群一直痛得流汗,他很想昏过去,但现在却不行,因为马玉仪显然怀着无限沉重的心事。如果他不能使她宽慰,至少他也应该为她做一点事。他道:“如果沈辛的爸爸就是沈神通,如果连沈神通也必须将女人孩子安置于这种地方,事情一定非常严重非常可怕。”
马玉仪忽然流下明珠般的泪水。她太想听见“沈神通”这个名字,只要有人跟她提起跟她谈论,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既然雷不群已经猜到也已经提到,她当然情不自禁,也不必隐瞒了。她道:“你认识他?事情的确很严重可怕!天啊,你怎会猜到是他呢?”
雷不群极力装出微笑,道:“你一定还不知道沈神通名气有多大?也不知道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而他为人公正廉洁也是天下着名的。他是真正的英雄人物!”
马玉仪的眼泪像泉水涌出,喉咙也发出呜咽声。能听到别人这样赞美沈神通,使她感激之情飞腾汹涌。
她抓住雷不群的手臂,雷不群居然还不昏迷,居然还能用另一只手轻柔抚拍她肩头。
雷不群知道自己最多只能替她做这么多事──设法使她哭出来,以便用泪水冲去大部份无补于事的焦虑。纵然马玉仪是他嫡亲妹子,他能做的事也只有这么多,况且这种事连金钱也完全失去效用。而雷不群目前只有“金钱”(他一个签押就可提取用不尽的银子),别的甚么都没有,连身份名字都没有……
小沈辛传来呀呀哭啼声,马玉仪忽然停止哭泣,眼睛恢复清澈神采。她道:“你现在可以昏迷了,我会照顾你,我会把你当作亲哥哥一样。”
雷不群果然很听话,马上就昏过去。在这世界上人类的灾难以及人生的悲剧何时才会终止?
×
×
×
这间练武厅前面有座大庭园,园中假山亭阁,花木扶疏,池中残荷摇曳。厅前的百年梧桐三二枯叶飘落地下,已是秋天了。
雷傲侯道:“我们其实跟落叶没有分别。我们这些人虽然个个都很不凡,但时间一到,却也跟落叶一样枯萎,也一样变成尘土。”
厅堂内有“风鬟雨鬓”南飞燕(她刚刚到的),“大自在天医”李继华,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等人,连“海龙王”雷傲侯在内一共四人,人人各有惊世绝学,所以的确可以形容为“不凡”。
李继华道:“秋天的味道很特别,的确可以使人回忆很多往事,使人感到去日苦多的季节。”
南飞燕道:“我以为你脑袋里只有医书和药材,那知你居然也会像别人一样悲秋?”
李继华道:“我不是石头,像你这种女人站在我面前,我仍然看得出你很漂亮,我决不会把你看作丑八怪母夜叉的。”
南飞燕笑得很娇媚很美丽,道:“哟,那我真的应该向你道歉,因为我一直以为你是既没有眼睛也没有感情的人。”
李继华道:“孟老总,你也在这儿观赏秋天景色么?你想起甚么人?”
他声音中显然含有讽刺意思,所以孟知秋皱起眉目,使得那张平凡的脸孔有了表情有了生气。
孟知秋道:“难道我就不可以悲秋怀人?我又不是石头。”
李继华道:“人人都可以,你却不行。因为我记得你答应过要替老雷挡去两路人马,现下连南姑娘都闻风赶来,说不定她也会帮忙打发一两个。但我眼睛却告诉我,你老兄仍然坐在椅上,而且坐得很稳。莫非你坐着就可以忽然到了他们面前?”
南飞燕插嘴声明道:“我只是来看热闹,不是来帮忙打架的。”
李继华道:“你可以,因为你是女人。”
南飞燕马上反驳,声音也有点不高兴:“你的意思是说女人不会打架,不会打赢?”
李继华道:“我意思是说女人脾气不易捉摸,明明应该帮的人她会不帮,而不该帮的人她却偏偏要帮。”
孟知秋道:“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正在等一个人。”
李继华讶然道:“等人?谁?”
孟知秋道:“严北。”
李继华道:“他马上就会从房间出来,也马上会到另一间练武厅。你知不知道他拿着剑去那边干甚么?”
孟知秋道:“我当然知道。淮扬大侠‘风云一条鞭’应无求正在等候雷老板,却万万想不到出现的人竟是血剑严北。”
李继华道:“既然如此,严北兄那有时间跟你聊天?莫非你又来那一套反对私斗要公平执法的大道理?你想阻止严北兄出手?”
孟知秋道:“都不是。”
南飞燕不甘寂寞插嘴道:“你认识应无求?你们是朋友?”
孟知秋道:“我刚才已声明过我不是石头。其实可能是秋天的缘故,使我记起廿七八年前一个人和一件事。”
南飞燕仍不放松,钉着问道:“你识得应无求?你们是朋友?”
孟知秋叹口气,道:“廿七八年以来我都没有再见过他。那时我才出道不久,才只是廿二三岁小伙子,但他已经威名四播,已经是卅多岁壮盛之年,而且主持全国最大的镖行,由江南到关外都可以看见大汉镖局的镖旗。那时候大汉镖局势力之大,局子里高手之多,你们恐怕都不晓得,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
我在总局的内厅第一次见到淮扬大侠风云一条鞭应无求。所谓内厅就是镖局的心脏,由大门到内厅有八重警卫,因为藏放无价珍宝的地库只有一个入口,入口就在内厅。不过我当然不是为了他们保镖的无价珍宝而去,我只是为了一名镖师李谦而去。事实上李谦已经离开大汉镖局,已经不是大汉的人,同时他为人一点也不谦,脾气简直坏极了,所以外号叫做霹雳火,刀法极佳。”
人人都不作声听他讲故事。
“霹雳火李谦在苏州犯了事,跑来南京就住在大汉镖局里。府衙出公事要人,大汉镖局推得一干二净。如果硬闯抓人,则不免做成死伤,何况大汉镖局朝廷中有人撑腰,硬干是一定不行的。”
这时南飞燕插口问道:“究竟李谦犯了甚么事?”
孟知秋道:“很小的事,只不过酒后斗殴打伤十几个人而已。”
南飞燕道:“这等小事值得你伤这许多脑筋么?”
孟知秋苦笑道:“我那时可能太傻了,我只知道公事公办而且一定要办好,所以我调查了七日之久。那天假扮附近饭庄的伙计,居然瞒过八重警卫直入内厅,见到应无求和李谦。”
谁都知道孟知秋那时处境万分危险,因为他只是孤身一人,却是深入人家重地,陷入无数高手重围之中。
不过人人也知道危险情势突然消失,因为最怕是见不到主持人应无求。既然已经见到,同时李谦也在场,应无求除非决定杀死孟知秋并且毁尸灭迹,否则只好让孟知秋抓人。由于李谦犯的不是甚么大罪,就算抓了去也不过罚赔汤药费,最多是关上三五天,所以凡是主持大局的人绝对不肯为此杀死公人。何况应无求侠名已着,更不肯做此种事。
孟知秋说道:“我和应无求就只见过这一面,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应无求很尊敬地送我出去,他说以我的耐心智慧胆色,就算武功不怎么样,将来也必能扬名天下,也必能替很多老百姓主持公道。”
雷傲侯道:“这些你果然都做到了。”
李继华道:“你答应过帮老雷的话,现在总不能反转来去帮应无求对付严北或老雷吧?”
南飞燕道:“他除了跟应无求联手之外,我看不出有甚么其他法子可以帮助应无求。”
孟知秋问道:“严北呢?”
这话自然是向雷傲侯询问。雷傲侯忽然惊道:“他现在一定已经找上应无求。他杀人时不喜欢有人在旁边瞧看,所以故意不经过此厅,也故意不跟我们打招呼。”
南飞燕道:“现在赶去恐怕已太迟。这两人一出手,谁能阻止得了?”
其实她是一边说一边走,其他的人也都跟着。走过一条长廊,虽然廊边种着各式各样美丽花卉,还不时可以看见挂着精致鸟笼,笼里都是名禽异鸟,却居然不能吸引任何人看一眼。
他们虽然没有奔跑,但一步步行去的速度却居然比普通人急跑还快,所以他们很快就来到练武厅。厅门没有关闭,但门内却有一块屏风挡住望入厅去的视线。
人人一齐停住在大门口。他们虽然看不见里面情景,也听不到兵刃或叱喝声,但却可以感觉得到森厉寒劲的杀气透出来。
这时候当然谁也不可冒失踏入,并非因为危险,而是由于误会所产生的仇恨。
南飞燕的笑声不但娇媚悦耳,而且保证能传出数里之远,所以厅内的人只要不是聋子,也保证必能听得十分清楚。她笑着说道:“孟知秋,你号称天下第一神探,据说对任何人望一眼,就能知道他擅长甚么武功,也知道他功力造诣深浅。又据说你耳朵一听鼻子一闻,就能知道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请告诉我,现下厅堂里是怎生情况?”
孟知秋的种种神奇传说早已脍炙人口,所以他现身说法的吸引力,当然强大无比。南飞燕这一招乃是针对严北施展,只不知她这回有没有摸准“男人”心理?
孟知秋道:“此地每一位都是当代无双之士,所以我平常使用和观察的方法全不适用。现在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风云一条鞭’应大侠已经真正了解真正承认‘血剑’严北是当世最可怕最冷静的杀人专家。”
南飞燕道:“难道应无求从前不知道严北是甚么人物?”
孟知秋道:“当然知道,但现在才真正亲自体会到。这里面大有分别。”
南飞燕道:“你怎知道应无求的感觉以及他的想法?”
人人都想问这一句,所以人人都不觉竖起耳朵等候答案。
孟知秋道:“应大侠退休十二年,日日优游林间享受满堂儿孙之乐。他年纪也届望七之年,任何人处于他的地位,决不会闻讯就挟鞭孤身登门。但偏偏他就会,因为他向来重义轻生,所以他是淮扬大侠而我不是。此所以他自知面对血剑严北(真正要报仇的对象)时,已经具足壮烈威猛气势,但何以应大侠凭恃这股气势而居然迟迟不能出手?”
南飞燕道:“很有趣很有意思,请快说下去。”
孟知秋道:“因为血剑严北虽然亦一时不能出手,但他的可怕杀气,他无上精湛剑道却也是足以使应大侠出不了鞭。应大侠深知自己年岁已老,体力和雄心都非复当年,继续僵持下去大是不利,也知道严北正是此意,更知道严北不到溅血五步那血剑决不出鞘。”
一方是剑拔弩张,一方是剑仍在鞘,一方是急图决战,一方是静候良机。整个画面呈显出严北已经控制大局。
孟知秋又道:“南姑娘,如果你是严北,如果应大侠答允你有生之年不再找你,当然连雷老板在内,你答案是不肯抑是转身走开?”
南飞燕也不觉一怔,道:“应无求此来既然不把生死放在心上,你竟然能劝他认输?他肯在垂暮之年自毁英名?”
孟知秋道:“好,我不妨试试看。”
他居然不走进练武厅,仍然在门口说道:“应大侠,我希望你还记得廿八年前,花了七天时间调查观察,终于在大汉镖局内厅见到你一面的小小捕快。”
厅内传出宏亮哈哈大笑声,说道:“我当然记得。廿年来我一直猜想当年那位捕头是不是你。”
孟知秋道:“你的答案呢?”
应无求道:“那还用说?如果严北不反对,我马上回家抱孙子。”
厅内传出的阵阵杀气忽然消失。
孟知秋道:“应大侠,我有事先走一步,希望将来能够拜访你,能够见你第二面。”
应无求雄壮宏亮声音传出来,道:“严北已经走了。孟兄,我一定等着见你第二面。”
南飞燕忍不住道:“孟知秋也走了。应无求,我真想不通你何以肯答应孟知秋?”
应无求道:“难道有人居然敢认为逮捕严北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飞燕讶道:“逮捕严北?疯子才认为是容易的事。”
应无求道:“所以孟知秋兄很耐心等候,十年廿年卅年都不要紧。我当然也在等候。”
等到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当然就是表示严北已经被捕已经依法律惩处。但“血剑”严北是天下无双的杀手,他会被捕么?
×
×
×
孟知秋还未走出雷府,在一个幽静宽敞的院落停住脚步。
他并不是不想走出雷府,而是因为有一枚黑色“人”钉以及一地鲜血阻住他去路。
黑色人钉自然就是血剑严北,一地鲜血却是从一颗头颅流洒出来。
严北浑身散射出鬼魅似的阴森杀气,严峻冷酷眼光盯住孟知秋。他声音也冷峭得很可怕,说道:“你知不知道地上这颗人头本来长在谁的身上?”
孟知秋颔首道:“我当然知道。他本来叫做赵老甫,外号‘阴风’,但现在人头和身体分了家,赵老甫这个名字可就不知道要给人头好或者给身体好?”
严北道:“赵老甫名列‘恶人谱’上,总算也是个名人,只不知道他这种下场在你看来应不应该?”
孟知秋道:“如果他这一类人全都得到这种下场,天下立刻太平无事。我意思就是说应该之至。”
严北道:“假如死于我剑下都是这种人,你有何评论?”
孟知秋脸孔平凡得近乎愚蠢,但眼光忽然变得锐利坚决,面孔也就跟着不平凡了。他道:“我的评论是‘干得好’,但可惜死于血剑之人并非个个歹恶。何况以个人私见执行惩罚,从人群长远的观点看为害甚大。”
举例说明已无必要,因为就算举例精当正确,只怕也不能说服严北。何况那时司法权并非超然独立?审判权力操于行政官吏手中,人们当然会怀疑法律的公正性。
严北的杀气的确使人不寒而栗,尤其是瞬息间就能杀死“阴风”赵老甫还割下人头,因此连震慑天下黑道顶尖人物神探孟知秋心里也为之波澜起伏。严北的剑术究竟高明到何等地步?他的杀人技巧难道当真妙到呼吸间就能杀死赵老甫?
严北冷冷道:“我承认曾经杀死过一些不算坏的人。”
孟知秋叹口气,道:“我也曾经抓过不该抓的人。只要你杀人,并且继续杀,不管你存心为了除去奸狡宄邪恶,但你一定不免要杀死一些好人。我也一样,虽然事后我还可以想点办法,但一定还有些被冤枉。”
严北不以为然道:“你也会犯这种错误?”
孟知秋说道:“我只是人而不是神,况且‘对’与‘错’时时很难确定,我们评估一个人却常常因时因地不同而改变。北方的大车因十几头牛骡拽拉,可载四五千斤货物,架车只有车主和助手两人。你看见他们终夜劳苦,简直不是人,尤其是霜雪泥泞时更惨更苦。你必定心生怜悯,人活得如此悲惨怎能算是人呢?”
严北道:“我见过,的确很可悲。但你的话是甚么意思?”
孟知秋道:“当你忽然又看见他们喝着酒带着妓女,就躺在车厢底的地上,然后又吵闹叫嚣甚是无赖恶劣,你又会觉得他们压根儿不值得怜悯。由此可知我们对人的评估判断常常很有问题常常无法确定。”
严北道:“你脑子里这些问题,使你不像传说中老练狠辣的神探。”
孟知秋道:“你也不像外表冷酷无情。我奉告你一句话,说完我就走,因为我答应过雷傲侯替他挡退两路人马。”
其实谁都听得出,孟知秋的“赠言”等于买路钱一样。有些人不一定要钱,严北就是。有些人的话可能比钱宝贵得多,孟知秋就是。
严北道:“请说。”
孟知秋道:“假如有人能够杀死你,那一定是因为你的心不够黑,你的血不够冷。”
“谢谢,请走。”
孟知秋走出院门,却仍然禁不住回首向地上人头望了一眼。严北真的能在指顾呼吸之剎那间杀死赵老甫?如果能够,他的剑道造诣高明精妙到何等地步?能不能描述形容?
雷府由内而外全无异状,门房老头殷勤行礼送出大门。
孟知秋站在台阶上,站了好一会,忽然发现了门房老头还陪笑着站在旁边。
孟知秋道:“世事便是如此,结局都很简单很悲哀──分离,不论是生离或死别,都是一样。”
门房老头陪笑道:“是,孟老爷。”
孟知秋道:“我虽然没有送你主人走,但却知道他已经走了,也许要等很多很多年后他才会回来。你心中的悲伤是不是怕年纪太大,恐怕等不到他回来那一天?”
门房老头笑容消失,黯然点头。
孟知秋叹口气,喃喃道:“我为甚么要讲这么多话?唉,我也要走了,但奇怪小沈何以还没有消息?我是不是太担心因而不觉踌躇徘徊,希望在拔脚离开最后一剎那竟能等到他的消息?”
这个小沈就是沈神通。他应该两天前就会在雷府大门外留下记号,表示已接到密函,这样孟知秋就可以安心前赴巫山神女峰,因为沈神通一定可以把“悲魔之刀”安全送到呼延逐客的儿子手中。
其实孟知秋也认为没有替沈神通担心的理由。沈神通是他最得意的门人,连武功也已经跟他差不多,谁想杀死沈神通的话,一定发现是非常错误的决定。何况沈神通现任浙江总捕头?
南飞燕严北等人已经出发,大家已经约定时间地点会合。如果孟知秋还不赶快办妥挡退两路人马之事,还不赶快去会合的话,他就会错过刀王血剑两大高手的决斗了。
但他拔步离开时,仍然禁不住望一眼没有暗记的墙壁。沈神通为何没有及时赶到呢?
×
×
×
答案除了沈神通本人之外,还有副手何同以及“空前绝后”严温回答得出。
书房外清凉绿荫并不能使任何人沸腾的内心宁谥下来。
严温面色变得很苍白,眼中显然流露出恐惧。
他根本不必等沈神通说出来,就知道沈神通一定不肯妥协。
沈神通一定会出手。也必定是蕴集全力的一击。如果躲不过而丧命,那时就算大江堂如云高手能把沈神通剁成肉酱,但对于严温已经全无意义了。严温的恐惧便是由此而生。
沈神通眼光从窗外婆裟绿荫收回,马玉仪的娇艳,小沈辛的胖胖面庞都消失不见,心中一片出奇平静,但话声却铿锵有力,道:“如果不能活捉,死的也好。”
何同应一声“是”,身子已像弹簧蹦起疾扑严温,在空中那一瞬间亦已掣出长刀,闪耀出一溜精虹。
但人影飘闪从何同身边掠过。沈神通居然比他更快,后发先至,一伸手已经搭在严温肩上。他五指齐张有如龙爪,指尖都嵌入严温骨头。
这时严温当然绝对无力反抗也无力逃跑,他甚至不知道这种功夫就是中原绝艺“天龙爪”。沈神通如果要取他性命,当时五指只要换个部位就可以了。
大局已经底定,因为严温活捉到手,等于是一张通行证,一定可以安然离开大江堂势力范围了。
然而沈神通却忽然面色大变,五指松开从严温肩头滑下。
那是因为他胁下突然一阵剧痛,一把锋快长刀深深刺入。
长刀刀柄已经没有人握持,因为本来握刀之人,弃刀疾退了七八步之多。
沈神通眼光既迷惑又悲伤,道:“何同,怎会是你?”
何同面色非常难看,甚至好像也有点悲伤之意。
他亲自出手暗杀沈神通,还有甚么好悲伤的呢?
“你当然想不到,我本来就不是何同,只不过两年多以前杀了何同,冒充他的身份成为你的手下。”
沈神通说道:“你究竟是谁?”
“我的姓名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但我义父伊贺川你一定知道。他几天前已经死在你的师父孟知秋手中,所以我一定要完成他的付托一定要杀死你。”
沈神通虽然是在极大痛苦中,仍然能露出惊讶神色,道:“啊,暗杀道第一杀手伊贺川。他终于被家师除去?真不容易,听到这个消息我更感惭愧。我不但不能逮捕严温归案,还死在我最亲信的人的刀下。”
他话声虽然不响亮,却也居然并不衰弱无力,所以“笑面虎”何同惊惧地又退开六七步。因为如果沈神通竟然还能够出手一击的话,这一击定是非同小可。而严温肩骨尽碎,已经不能动手帮忙。
不过沈神通仍然屹立不动,假如他还有最后一击的力量,对象当然最好是抵抗力已不强的严温,而不是生龙活虎的何同。
故此沈神通寸步不移很有道理,而严温那清秀俊俏面庞也因痛苦和恐惧而肌肉抽搐皱缩,变得很难看很丑陋。
沈神通又道:“虽然你是伊贺川义子,虽然你用尽方法投入公门变成我手下,但你和严温怎会搭上关系?”
别人可能不明白沈神通何以会有此一问,但何同却极了解极清楚。那是因为一年来沈神通下了不少功夫侦查严温,这个侦查网当然万分严密,甚至严密得连何同暗中与严温勾结私通的话,也不可能瞒得过沈神通。
但事实上何同居然与严温搭上,而沈神通居然丝毫不知,所以他要问。显然这个问题在沈神通来说,是个死不瞑目的疑问。
何同道:“有一个年青人叫做陶正直,你有没有印象?”
沈神通道:“我知道,听说他武功很不错,身兼数家之长,但为人十分卑鄙,外号称为‘人面兽心’。是不是他?”
何同道:“就是他。我跟他认识很久,所以他知道我本来是谁,所以我有时也不得不听他的话。而他跟严温关系密切非常,所以如果这次严温发生事故,我一定没有好日子过,况且我义父已死,我也不能再不出手了。”
严温第三次从剧痛昏迷中回醒,发出呻吟之声。
何同皱眉望他,道:“严公子,你就算肩骨被捏碎也不应该这样呀。你一向很怕痛?”
严温乏力地道:“如果内伤未愈,忽然加上一记硬伤,你受得住么?”
何同道:“我也受不了。我这儿有药,你吃了一定很有帮助。”
严温道:“我不吃你的药。”
何同道:“别害怕,如果你死了,我就收不到一万两黄金。我绝对不想损失一万两黄金,所以也不想你死。”
严温面色非常苍白,冷汗布满额头,看来随时随地都会再昏迷,所以他不再拒绝何同的药。事实上服药后他立刻精神振作,显然何同的药很有效真能止痛。
但沈神通却道:“严温,如果我是你,我绝对不吃他的药。”
严温讶道:“你还未死?照我看何同那一刀已经刺入你心脏,你何以还不曾死?”
沈神通苦笑道:“生命力太强也不是好事,我现在就是在活受罪。我一时三刻还死不了,除非你拔出这把刀。”
何同道:“沈公(他仍然如此尊称),你的遗体将会连同这把刀一齐送回公衙。”
沈神通道:“无怪你这一刀用的是少林刀法。不过若是孟老总看见,一定看得出破绽,一定知道不是真正少林刀法。”
何同道:“陶正直说孟老总绝对不可能回到杭州或南京。他意思说孟老总永远留在阴间,不会回到人世。”
沈神通叹口气道:“这话以前我绝不相信,但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陶正直的确是很可怕的人物,尤其是他年轻又没有名气。”
何同道:“对,他很厉害。”
严温道:“我为何不该吃他的药?”
沈神通道:“唉,你只会记挂自己,别的事一概没有兴趣?”
严温道:“我是的。”
沈神通道:“何同是伊贺川义子,伊贺川是东瀛忍术大家,天知道伊贺川有多少古怪离奇本领。所以你吃了药,可能永远受制于何同,永远要听他命令。不过既然你已经吃了药,这些话不说也罢。”
严温道:“何同,沈神通的话你不至于听不见吧?”
何同道:“的确不至于。”
严温道:“如果我不听你的话,有何后果?难道会死不成?”
何同道:“好像是的。”他那张白净斯文脸庞上挂着温和笑容,使得这句话回答不但毫无杀气,甚至像是说笑而已。
严温道:“你其实不必这么做,这样使我们关系变得很恶劣,必要时我甚至不惜先杀死你才想法子找解药。大自在天医李继华肯替我医治很严重的内伤,当然也肯替我解毒。”
何同道:“李继华也和孟老总一样永远不会回到人间,所以你最好还是另外找一个名医。老实说,我就是想活着出去想活着拿到黄金才用这种手段。你最好考虑一下,因为你的命比我的值钱得多了。”
严温道:“你出去之后仍然回到公衙?仍然当你的副总捕头?”
何同道:“我为了私怨私欲害死沈公,我唯一能稍报答他的方法,就是用他教我的本事,继续尽力维持治安。反正我黄金已经多得用不完,我不必枉法徇私求取钱财。而你的大江堂,只要你严公子一日当权,我也可以限制你们的活动不准太过份。”
沈神通忽然叹口气,眼光转到窗外。在那充满盎然生气的清凉绿荫中,浮现出马玉仪婷婷盈盈倩影,小沈辛胖嘟嘟红扑扑脸庞。我本来还可以提聚内力作最后一击,但我横竖已经活不成,而这两个人活着却各有用处(对社会而言)。我这一击的目标应该是谁?
──唉,玉仪小辛再见了。唉,我甚至在尚有能力之时也不能出手报仇……
──为何当此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瞬间,我仍然想起浩淼长江边小小家园?玉仪可是在临水石阶洗濯衣服?她洗濯是假,遥望等候归帆才是真的。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她将遥望等候到何年何月才肯罢休?她本是命运坎坷的弱者,所以生命乐章总是沉郁悲哀。但我呢?我曾是“强人”,然而命运却更强,所以我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