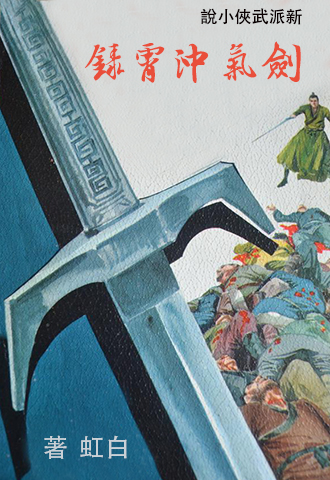阿烈在柜台前静静的站着,又过了一会,那老人停下来,并且抬头,可就望见了前面的人。
他眨眨眼睛,才道:“你想买什么?”
阿烈内心大为震惊,忖道:“怎么啦?他不是粱大叔啊?”
但他面上不动声色,道:“借问老伯一声,这儿可有一个姓梁的梁大叔?”
那老人皱眉道:“谁呀?”
阿烈又说了一遍,那老人道:“没有,这儿没有姓梁的人。”
阿烈如是当年,一定刺刺追问,并且会说很多话,但现在可不同了,他只点点头,歉然道:
“那么是我弄错了,或者还有一定也叫恒昌的杂货铺吧,我且去找找看,如果找不到,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他转身行去、走了几步,突然回头,道:
“有人托我传个口讯,要不要告诉你?”
那老人摇头道:“不,不,你再去找一找吧。”
阿烈道:
“也好,我猜这个口讯根本是玩笑的,也许是她临死之时,神知已经不清之故,但无论如何,那些银子却不是假的。”
那人眼中亮了一下,似是内心震惊之故。
阿烈想道:
“我这一番话之中,只有一个死字,可使他注意,因为如果他乃是假装不识梁大叔的话,则他一旦听到有什么死讯,当然会吃惊啦!”
又转身走去,堪堪要跨出店门,那老人叫道:“喂!你刚才说什么?”
阿烈停下脚步,回头大声道:
“你可是想知道那个口讯?若是要听,我就告诉你。”
老人招他过去,道:“你小点声音,告诉我吧!”
阿烈道:“是一个女人,嘱我来找一个梁大叔的。”
老人道:“口讯是什么?”
阿烈道:“听起来你的好像识得梁大叔呢,是不?”
老人道:“你似乎太聪明,与你的外表不符。”
阿烈微微一知道:“是的,因为我和你都是一样。”
老人又皱起眉头,道:“什么一样?”
阿烈道:
“说穿了不值一钱,咱们皆是伪装的,你就是梁大叔,而我呢,也非是传口讯之人。”
老人反而笑起来,道:“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阿烈迫近一点,与他相距不及两尺,他双眼之中,射出足以震撼对方心弦的光芒,坚定地道:“你是梁大叔?”
老人道:“你一定要找到他么?”
阿烈道:
“当然啦!而我细心多看几眼之后,已认出你的轮廓,不错,你就是我小时候叫做爸爸的人,”
老人身子震动一下,徐徐道:“你叫什么名字?”
阿烈道:“我叫阿烈,姓查,名思烈。”
老人叹;口气,道:
“我活了这把年纪,还是头一次碰上这等怪事,你走吧,我完全听不懂你的话。”
阿烈一怔,闭嘴不言,他本来深信自己一说出姓名,这个老人必定马上改变了态度,甚至立即带他到后面去,讲出真话,然而这个老人的反应,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同时还叫他走,口气十坚决。
这是什么回事?莫非他不是梁大叔?但他明明已认出他就是梁大叔,虽然他多了一头白发,以及面上的皱纹等,但仍然可以认得出来,而他的记忆力却是最好的,小时候的事,无不记得清清楚楚。
他想了一下,才道:
“我虽然是想不通这道理,但我仍然要试一试,我告诉你,我妈已经被害去世了。”
他一提到母亲,顿时泪水急涌而出,这是无法可以假装的一种孺慕的悲痛,而那老人问道:“她遇害了?”
阿烈点点头,道:“是的,为的是血羽檄之事。”
那个老人道:“我虽然听不懂,但我瞧你却不是讲假话。”
他起身走出柜台,步履蹒跚地走到门口,细细看过街上的情形,这才回转过身来,道:
“你跟我来。”
阿烈随他转入铺后,走进一个宽大房间内。
老人让他坐下,并且斟了一杯热茶给他,道:
“我姓梁是不错的,但你要找之人,却是我的弟弟,如果你有话告诉他,只好由我转告。”
阿烈道:“这话虽然似有道理,但我却认得你就是梁大叔。”
老人熟视他—会,嘴角泛起一丝朦胧的,难测其意的笑容,道:
“好吧,就算我是梁大叔,你有什么话说?”
阿烈道:
“如果你是梁大叔,那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不该这么冷漠的对待我。”
他面上犹有泪痕,使得他的话更充满了感情,更为真挚动人老人沉吟了—会才道:
“奇怪,我本是很工心计,善于自制之人,但见了你的神情和说话,居然禁不住相信了,唉!这真是不可理解之事。”
阿烈:
“梁大叔,我当真是阿烈,如果在半年前来看人看你一定毫不疑惑,因为半年前我仍是又矮小又瘦弱,但近半年当中,发生了巨变,使我变成这等样子,也迫得前来找你。”
老人道:“一个人可以变得这么厉害么?”
阿烈道:
“让我扼要把内情告诉你,我不能耽搁太久,因为我现下跟冀北欧阳家的小姐在一起,当然她不知道我的来历,而她事实上以前在开封见过我,但她也认不出我呢!”
老人道:“你越解释,我越糊涂,难道我已老得这般可怕了?”
阿烈不觉微微一笑。
他立即扼要的把“血羽檄”案说出,一路叙述到他得服“仙昙花露”,换筋易骨之后,又卷入丐帮及太白山魔女剑派的宿怨旋涡,而日后碰上了这神秘无比的“极乐教”
为止。
他虽是扼要而言,却也费了不少时间,而当他重提及母亲惨遭幸之时,简直是声随泣下。
老人听他叙述之时。面上没有一点表情,使人摸不透他到底听得懂听不懂,如果听得懂的话,是不是完全不予相信?
最后,房中静寂无声。阿烈沉声道:“梁大叙,你敢是还不相信我的话?”
老人身子一震,道:
“唉!你的容貌,绝似公于当年,这还不说,连刚才最后一活,说得那神情声音亦全无二致。”
阿烈眼睛睁得大大的,道:“那一个公子?是不是我父亲?”
老人没有回答,抬头望着黝暗的屋瓦。
阿烈突然间惕然而惊,忖道:
“如果这老人乃是别的武林人物,加害了真的粱大叔,以便等侯有关化血门查家之人前来,则我旭今已是陷入罗网了。”
想是这么想,其实他心中可不相信这等事会有发生的可能性。
不过无论如何,他已暗暗戒备,略一定神,丹田中涌起了真气,遍布全身,现在他不但可以抵御住任何袭击,亦能随时出手攻击,甚且能听得见四周数丈方圆之内的任何声息。
那老人冗自望着屋瓦,然而阿烈却已看见他双目闪闪生光,敢情是涌满了泪水,以他这么大岁数之人,居然热泪潮涌,那自然是情绪非常激荡的了。
阿烈一方面松了口气,一方面也十分感动,柔声道:“梁大叔,人怎么啦?”
老人站起来,突然双膝跪下,道:“小人梁忠山,参见查公子。”
阿烈为之手忙脚乱,要去掺他,但一时拉不起他,只好也自双膝跪倒,道:
“梁大叔不可如此。”
梁忠山挥泪道:
“公子有所不知,小人实是感到非常愧疚,因为你们化血查家,只有人这一点血脉,而小人却贪生怕死,竟然不把你们查家的绝技传授给你,任得你们母于饱受贫寒之苦,而主母最后更遭了不测,唉!小人罪大如天。”
他的眼泪直滴下来,阿烈道:
“梁大叔不必过于自责,你这样做法,一定有你的理由。”
梁忠山道:
“小人敢夸自已实是老谋深算,当日曾苦思了三日夜,才决定从此退出江湖,只求保存查家一点血脉,因此,小人从开始之时,就首先从湮没一切证扰痕迹着手,主母所过的贫寒日子,亦是我计划中的主要部份。”
阿烈插口道:
“是啊!他们一查之下,认为我家一直穷困贫苦,不可能是化血门查家之人。”他说话之时,把对方扯起身,分别落坐。
梁忠山道:
“幸而我这番布置末落空,终于收到奇效,不然的话,你们就白白吃苦了,此外,小人的不把化血门根基功夫传与你,以及把你的岁数改变等,也都是为了湮没证据。”
他目下说来容易,其实当初稍一大意,就未必会考虑及此,因此阿烈露出佩服之色。
梁忠山又道:
“少爷你目下的容貌,与昔年主公很相肖,小人一眼看见就证了一下,但正因如此,我才不敢轻信。因为如果是仇家有意查探秘密,哄我相信的话,自然会找一个与主公相肖的人,不过主人的神情和声音,那当然模仿不来,所以最后你的一句话,使小人完全相信不疑便是此故。”
他向房中四面扫瞥一眼,又道:
“少爷可晓得么?小人此房之内,埋藏了足够的火药,如果你是假的,小人举手之间,就可与你同归于尽。”
阿烈笑一笑,道:
“但梁大叔你不一定抓得住机会,因为你必定想等仇家越多人在此越好,这一贪得等侯的话,可能就错过机会了。”
梁忠山讶道:
“少爷这话真有见地,唉!你才智英发,举世罕有,小人尚复何忧。”
他歇一下,又道:
“不过少爷却忘了一点,那就是小人乃是比血门下之人,虽然功夫有限,但化血门的武功,天下无双,小人只练了一点皮手功夫,亦可与世上任何名家高手,走上三五十招而不致落败呢!”
阿烈大喜道:
“这样说来,我就不必访寻名师啦!我使用家传武功,名正言顺,真是最好不过之事。你几时可以教我?”
梁忠山道:
“这事容小人考虑一下,因为少爷与常人不同的是,你一旦使出化剑门绝艺,就必须有胜无败,换言之,你必须自问能打编天下无有敌手,方可使用家传武功,对不对?”
阿烈点头道:“是的,如果艺业不精,却把消息传了出去,那真是惹祸上身。”
梁忠山道:
“化血门的武功可说是天下无双,而奥妙精华全在内功上,人称化血神功,必须练在了这根基功夫,方始有用,上阵动手之时,全看内功造诣如何。功力随之作强弱之分。
叫做所积者厚,其力越大。像小人只练到第三层,拳掌的力道只有三层的强弱。如果像老主公已练到最高的七层,即化血真经所云的七重天境界,所以他一出手,即有无穷无尽之力.宛如宇宙中大自然的力量,如海啸山崩,飓风雷电,试问还有什么人能抵挡?”
阿烈顿时大悟于心,道:
“这便是与天地融合的无上境界,只不知先父昔年练到什么境界?”
梁忠山道:
“小人不敢相瞒,主公的武功比主公差得太远了,据说这是受累于美色,据小人想来,主公大概只有五层的造诣。”
阿烈道:
“这就怪不得咱们查家会遭覆灭之祸了。若果他已练到爷爷一般,到了七重天的境界,天下无人可敌,焉能覆灭?”
梁忠山点点头,他对死去主公,忠心耿耿,实在不愿再谈他的短处。
阿烈又道:“先父的遭遇,是我前车之鉴,我往后也不可近女人了。”
梁忠山忙道:
“少爷万万不可矫任过正,主公只不过是过于沉迷美色,生荒了功夫,如果是有限度的亲近女人,并不妨事,像老主公,他亦从不忌女色,府中有三房姬妾,但他还是天下武功最高之人。”
他觉得问题太严重,如果不讲清楚,阿烈可能为了武功之故,不近女人,以致绝了子嗣,所以他再也顾不得是不是攻讦公的短处了。
他又道:
“主公自小履丰席厚,娇生惯养,十分任性,练武之事从来就不专心,加上他长得漂亮潇洒,有财有势,可以说没有一个美貌女子,碰上他能不入迷的,因此之故,主公的一生,根本就在酒色中过日子,少爷只要不过份,即使偶然留情,逢场作戏,也不要紧。”
阿烈道:
“原米这就是孔夫子说的‘中庸’之道了,凡事总是过犹不及,太多了不行,完全戒绝,亦与天道有悖,可是这样?”
梁忠山忙道:“是的,是的。”
阿烈突然问道:
“据说咱们查家遭难之时,仇家们已清点过所有遗骸,连家中丫环,俱不缺少,你又如何能漏网呢?”
梁忠山道:
“这一点小人倒是可以解释,要知咱们家里做事之人甚多,上上下下,皆有一定的工作,小人是主公身边的听差,亦即是家将之意,是以学过武功,普通一点的问题,小人即可打发……”
他想了一卞,叹了一声,道:
“主公一生风流,平生所识女子,真是上千论百,由于小人计谋胜过周瑜,兼且小人又是个天阉,所以后来一切女人这事,他都交待小人去办。这一来小人就时时在外边奔走,秘密地送银子啦,安排种种琐碎之事啦!”
阿烈忽然释然了,这是因为梁大叔曾与他母亲,假装为夫妇多年,这一点他虽然不愿放在心上,可是下意识中,总是希望没有这等事故,如今既知他是天阉却是不能人道的人,则—切都没有关系了。
只听梁忠山道:
“老主公有时会诫责主公不可过于放荡,污人妻女,所以小人的行事,非得以秘密方式不可,那些女子,绝大部份都不知道主公的真正身世来历,如若有了子女,才连大带小,都收回府中。”
阿烈点点,道:“这样说来我有不少哥哥姐姐都遇害了?”
梁忠山道:
“是的,你有五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之多,都完全遇害了,小人因为时时在外,所以小人的缺,由另一个人补上,这还是刚刚补上,府中仍然保持一样多的人数,所以不知底蕴的儿根据名册,点起来,就全无遗漏了。”
阿烈道:“原来如此,那么你是不是奉命来搬我母子返府呢?”
梁忠山道:
“小人奉命暗中送钱,顺便到处看看,刚刚查出主母快要分娩之事,尚未回报,就出了大祸。”
阿烈道:
“好啦!其他的细节以后再说,目下该谈谈武功问题,我虽说已可刀枪不入,但出手时没有法度,总是不行的呀!”
梁忠山道:
“小人所识的武功,是老主公亲自选了十二招心法,恰好适合小人的资质路数,其他的小人虽也看得惯熟,可是如果没有化血真经,小人也没有法子,只能传你化血神功及这十二招手法而已。”
他停了一下,又道:
“小人晓得化血真经在什么所在,若是找到了,便还有希望。”
他的腰肢已挺得毕直,目中精光闪耀,与方才的龙钟老态,完全不同。
阿烈大喜道:
“化血真经虽是传写了七份之多,但据说只有血羽檄一章是真的,如果咱们找回真的秘笈,我就算费上二十年时间,也要练成功方肯罢休。”
梁忠山道:
“你还是先修练化血神功,否则出手之时,全无威力可言,这是因为化血门武功,出手所击的部份,尽是独门脉穴,必须练有本门神功,方能伤得敌人,而练到老主公那等境界,敌人被击伤的话,当真是五肺六腑尽皆化为血水而死呢!如果没有神功底子,纵然学会了手法,也没有用处,击中了敌人,并无化血的威力。”
阿烈点点头道:“我明白这个道理。
梁忠山道:
“天下间各家派的武功不同,便是因为所修练的内功不同,是以所取的部位及方法皆不一样,例如人身大腿外侧的‘风市’穴,只是足少阳膀经上一个极平常的穴道道任何家派都不理会的,然而咱们化血门手法中,却能使这个穴道变成‘死穴’,可是你如果没有化血神功,虽然用本门奇奥招数,击中了敌人此穴,对方至多倾侧一下,不会伤及内肺。”
阿烈如有所悟,低头沉思了一阵才道:
“这样说来,咱们本门手法,有很多是攻击人家不注意的穴道的了。”
梁忠山道:
“是的,人身上的几处重要穴道,那是天下各派都一样,必定非常重视防备,唯有一些不要紧的穴道,才是发挥独门手法的着眼处。”
阿烈道:
“反过来说,别的家派,亦有一些独门的手法,专伤别人不注意的穴道了。”
梁忠山道:
“是呀!都是一样的,分别只是在威力大小,以及难易问题,比方少林寺的一记绝招‘金丝缠腕’,这是十分普通手法,各家派皆有这一招,但少林门下使出这一招,被刁住腕脉之人,绝不是身子摇动或摔一跤就能了事的,这是因为少林的‘小天星掌力’,可以伤经侵穴,使敌人真气不调,受到内伤。”
他举这个例子,非常明白通畅,阿烈不但通通明白了,同时又悟出更多的道理来。
他问:
“那么我再问一句,如果有人受伤,行家一看,晓得了这是什么家派,那定得伤人之人,具有那种内功才行,比方说,我们用金丝腕之式,把敌人打倒,行家一瞧,就晓得不是少林门下所干,对不对?”
梁忠山道:
“对呀!但这有什么用处呢?假如你不会小天星掌力,你就不肯时时使用这一招了。”
阿烈道:
“我是在想,如果我只学会本门招式手法,但末练成化血神功,则纵然使出本门招式手法,也不会露出形迹。”
梁忠山沉吟道:
“大致说来,人家不易认得,不过碰上一流高手,他们见多识广,便会认得出来。”
阿烈道:
“然而纵然他认得,也不要紧,因为被我击中之人,伤势不呈化血神功的情状,他们这时反而认为我的手法只是无意与化血门相同而已。”
梁忠山露出既讶且佩的神情,道:
“少爷真了不起,想深一层,果然如此,这正如诸葛先生在华容道诱曹操入伏一般,怎能使人不疑。”
阿烈道:“你在武林日子很多,不知可曾听见过逍遥老人萧冷的名字没有?”
梁忠山一楞,道:
“怎么没有?他是被天下公认为唯一可与化血门查家一较长短的人,只是此老平生行迹不定,逍遥于名山大川间,不理世事。”
阿烈摇摇手,打断了他的话头,插口道:
“我要你讲老实话,这位老人与咱们查家拼过没有?”
梁忠山笑一笑,道“少爷问得好,你猜他有没有来过呢?”
阿烈道:“我猜他一定来过。”
梁忠山道:
“这是武林中无人得知的大秘密,小人虽然得知,但受过主公严嘱,从来不敢透露。”
阿烈道:“可是爷他败了一招半式?”
梁忠山道:
“是的,那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逍遥老人萧冷其实只五十岁左右,来到咱们查府,其时主公不过在襁袱之中,那时小人也只有一两岁而已,据说老主公与萧老人倾谈甚欢,大有惺惺相惜之意,一连盘桓了半个月以上,这才较量武功。”
阿烈道:
“他们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因此,他们之所以盘桓了半个月,必然别有作用在内。”
梁忠山非常佩服地道:
“唉!少爷真了不起,居然看得出其中关键,不错,他们乃是互相观察对方,从日常言谈举止,以及生活习惯等等窥测对方的性情,以便找出弱点,不过,据主公说,老主公和萧老人都非常真心的倾佩对方,历久不忘这段友情呢!”
阿烈忙道:“后来怎样了呢?”
梁忠山道:
“后来他们择日较量武功,大家都全力准备,务求到时能够有超水准的演出……
他停了一下,又道:
“这两位天下再无俦匹的高于,根本不须动手,只用口头比武就行了。”
阿烈叹一声,道:“你说爷爷居然输了,真是今人想不到的事。”
梁忠山并没有难过之色,道:
“那也没有法子啊!他们这两个盖代高手,口头比武,足足比了三日三夜,一直没有停过嘴,算将起来,起码有数千招之多。”
阿烈仰头一笑,道:
“哈!你想哄我么?第一,爷爷结果不会输。第二、他们如何斗得几千招之多,就算上天入地,加上水中打滚,也弄不出几千个姿式啊!”
梁忠山道:
‘他们虽然斗了几千招、可是由于敌方的步法姿式不同,刚才用过的一招,回来又可以再用,只不过在前后左右高下等方面,略是更改而已,所以反反覆覆的打来打去。
就有几千招之多了。”
他欢喜地笑了笑,又道:
“关于胜负问题,你为何如此猜测?”
阿烈道:
“以你这般忠心之人,如果爷爷真是输了,你怎会全不感慨,所以我认为另有内情。”
梁忠山道:
“少爷能够敏锐的观测人心,小人不但欢喜佩服,也敢说天下间没有几个人可以与你相比的了。”
他赞过之后,才转回正题,道:
‘那一次的文斗,老主公的的的确确输了一招,逍遥老人萧冷非常得意,与辞而去。”
阿烈讶道:“他当真走了?不行,他一定得回转来。”
梁忠山道:
“是的,他半个月后才回来,一见了老主公之面,立刻拱手认输。”
这时已谈论到精微高深的武功境界,阿烈本是外行,是以绕他如何聪明,也推想不出这些关键奥妙。
他问道:“只不知爷爷这回如何能赢得他?”
梁忠山道:“这—一次根本没有动手……
阿烈讶道:
“奇就奇在这里,他是一见面就认输的,可见得他离开的半个月当中。一定是发现,这一场赢得有问题,可是他们当时都没察觉。这却是何缘故?”
梁忠山道:
‘总之据小人所知,老主公当时十分客气不肯承认是赢了,但他却又是当真赢了,其中缘故。小人始终没有弄明白过。”
阿烈点点头,脑海中泛起爷爷的神威逸韵.不由得悠然神往久之。
他忽然惊觉,道:“不好了,我还得依约行事,先把那妇人劫走。”
梁忠山骇然道:“什么妇人呀?”
阿烈已经在考虑下手之法,所以没有注意到他骇然之态,道:
“是个年纪很轻,但很淫荡的女人。”
梁忠山的心直往下沉,忖道:
“不好了,他竟也和主公当年一般,爱好女色。”
阿烈又道:“还有那一大笔银子,也要劫到手中才行。”
梁忠山想道:“更糟糕,主公当年只爱女色而不爱财,但他却要财色并畜兼收。”
他深深感到失望,所以不再做声,好像失去气力般,靠坐椅上。
阿烈想了一下.觉得下手劫定李姬之举,不论是把她弄昏了也好,不弄昏也好,仍然会留下破绽。
问题乃是在如何使得极乐教派来调查之人,认为她的失踪,合情合理,并且不予追究。
他终是年轻,世故不深,因此想了一阵,仍然不得要领,但时间已不早了,使他心急起来,更加想不出办法。
他一转眼,只见老人颓然而坐,神色有异,不禁问道:“你可是不舒服么?”
梁忠山摇摇头,半响才挣出一句话,道:
“那女人是谁?一定长得很漂亮的?她很富有么?”
他如果不问,阿烈决计想不到他的心事,现下恍然大悟,晓得他想到歪路上去了,心中暗暗一笑,想道:
“这也难怪他,谁叫我父亲是个风流情种呢?”
当下他把最末一段如何碰上孙泽、李姬以及宋水胜、岑瑜两个极乐教高手之事说出来,并且说明如何设下计谋,使这宋岑二人死得有理由,不致为极乐教所疑则孙泽亦可免去后患。
梁忠山听了,这才释然,他终究是极老练的江湖,又工心计,微一寻思,便有了计谋,说道:
“劫走李姬之举。如果不着一点痕迹,不让孙家有后患的话,实在不大容易,不过小人却有一计在此。”
阿烈甚喜,问道:“你有什么妙计?”
梁忠山道:
“小人说不得也要出手才行了,这个女的交给小人处理,等欧阳姑娘把宋岑二人杀死,你可假扮那赶车的大汉,欧阳姑娘则假扮李姬。两人驱车离开许昌,好在一两天后方会事发,其时你们已到了别处,早就弃了马车。”
阿烈道:
“妙极,极乐教之人,一定以为这赶车的教中门下,趁火打劫,来个财色兼收,他们自然不肯放过这赶车的,定要分出一部份人力,力查叛徒下落,此举甚至可以使咱们便于暗中察破敌人的隐秘和身份,不过……”
他拖长声音,想了一会,才又道:
“不过问题却有两个,一是我相那赶车的完全不像,如何冒充法?阿菁混充李姬,倒是不成问题。第二,这赶车的我瞧不是易与之辈,加上李姬,你如何处置?”
梁忠山笑一笑,道:“小人说出来,会骇着你。”
阿烈道:“没关系,我胆子不算小。”
梁忠山道:
“胆子还是其次,而是你可能嫌我太毒辣,加以阻止,至于第二个问题。小人自有解决之法。”
阿烈道:“你的意思杀死他们么?”
梁忠山点点头,道:
“小人这房后有一片菜圃,而且已经挖好了四个深穴,泥土堆一边,一下子就可以填好,埋两个尸体,真是易如反掌,也永远会败露。”
阿烈道:“使得,李姬淫恶之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那赶车的既极乐教中人,杀死了也不会冤枉的”
梁忠山道:
“公子赞同就最好了,有时这些坏蛋,万万不可留情,免得反而受他们之害,关于第一个问题,小的识得易容之法,包管店中之人看不出来。”
计划就此拟定,阿烈回身出去,在一处人家,会见了欧阳菁。
她见了他,又是欢喜,又是着恼,欢喜的见到了这个英俊男儿,不用再牵挂,着恼的是他来得迟了。
她埋怨了两句,听了阿烈的计划,大为惊异,道:
“这真是妙极了,我们只等夜深,便前往那客栈,待我施展家传功夫,一下子把这男女六人全部毒死。”
事实上阿烈没有提到梁忠山,而欧阳菁竟也没有想到他会有人相助。
他们就在那人家的一间,特别借给他使用的房间中,吃过晚饭,谈了一阵,各自盘坐调息。
到了半夜,他们起身结束一下,阿烈猛可想到一事,不禁皱起了眉头,道:
“不行,不行,这个计划之中尚有大大的破绽。”
欧阳菁讶道:“什么破绽?”
阿烈道:
“你说毒死那男女六人,然而你又是打算让人家以为他们是互殴而死的,试部人家一验他们曾经中毒,焉能会看不出其中有破绽?”
欧阳菁笑道:
“放心好了,我有的毒是一个月后才验得出来的,其时早已上葬,如何还看得出来?
他们只有外伤,保证谁也瞧不破的。”
阿烈这才放心了,道:“那么快进行。”
两人一道奔了出去,街上静寂如死,也十分黑暗,千家万户,尽在睡乡了。
阿烈心中又泛起了恍如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的感觉,因此,他不禁游目四顾,好像要把周遭的景象,深深印刻在心中一般。
欧阳菁被他吓了一跳,连忙也向四下打量。但并无所见,当下问道:
“你发现什么了?”
阿烈摇头道:
“没有,我只不过感到气氛与白日行事之时,大大不同,好像踏入另一个世界中似的。只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欧阳菁道:
“我倒没有,不过你说得不错,在晚上是另一个世界、这是江湖人的世界,普通的人,纵然想进来瞧瞧,也万万办不到的。”
她笑一笑,又道:
“哈!想不到你竟是善感的人,通常练武之士。都不大有这些情绪感觉的。”
阿烈不答理她的调侃,向前奔去。才奔出数丈,欧阳菁从后面追上来,把他拦住,同时把他推到暗隅中。
阿烈讶道:“敢是发现有人么?”
欧阳菁道:
“你本是聪明多智之人,还要我解释么?似你这种行动法,别说是老江湖道,就算是凡夫俗子,也很容易瞧见你。”
阿烈微微一笑,想道;
“她不知我已有一种异常灵敏的视听神通,数丈之内,只要是有生之物,我都能够察觉,所以我不妨大摇大摆的走,如果有人,我自然来得及隐起身形。”
接着念头一转,又想道:
“我这个本事,乃是心灵中发生的一种超凡的能力,一来不易解释得清楚,二来又难使人信赖,倒不如保持缄默为佳。”
因此,他不作解释,只点点头,道:“那么我跟着你走便是了。”
欧阳菁道:
“武学之中,有几种潜踪匿迹的上乘功夫,如道家的木石潜踪、五行遁法,佛家的隐形神通皆是。此外,各家派都非常重视夜行术,讲究趋暗避光,善用地形掩蔽身形,加上种种特别的身法配合。务求夜间行动之时,不致被无心之人看见,似你这等走法,岂不是惊世骇俗则有余,潜踪隐形则不足,如何使得?”
阿烈道:
“是啦!我又没练过武功,怎知这许多秘诀呢?不过以我看来,什么遁法,隐形以及夜行术等,都没有什么用处。”
欧阳菁摇摇头,道:“我从来末听人这样谈过,你可以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也许是吧!但总而言之,这些功夫有时有用,有时却全然无用,天下之事,本来就是如此。”
他的话含蕴着极深奥的哲理,只因世上之事,原是没有“绝对”可言,不过这个理论,却太抽象了,不是人人都可领悟的,尤其是现实中,理论究竟是理论,所以欧阳菁淡淡一笑,道:
“看你扯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往前走吧!”
他们两人在黑暗中窜越过许多房屋,不久,只见前面一条街上,右方一间铺子门口,挑起一个灯笼,写着大大的“店”字。
那便是他们所欲前往的客栈了,欧阳菁晓得阿烈没有打听出那宋、岑等人,居住在那个房间内。所以她一迳绕到侧面,打算逾墙进去查个明白。
他们来到右边墙下,阿烈伸手楼住她的纤腰。
欧阳菁跃不起来,当下轻轻拧他胳臂一下。道:
“我们不是出来玩的,你这是什么意思?”
阿烈在她面颊上亲了一下,道:“啧,啧,好香。”
欧阳菁身子一顿,依偎在他怀中,道:
“唉!别闹,我们要办事啊,你敢是忘记?”
阿烈道:“我没有忘记,你想越墙而入,对不对?”
欧阳菁道:“如果不过去查看;怎知那些坏胚子住在什么处所?”
阿烈轻轻道:“不可从这边过去.不然的话,人家就要发觉了。”
欧阳菁道:“乱讲,谁发觉呢?”
阿烈沉吟一下,道:
“大概是岑瑜吧?他站在窗前,向这边直瞪眼睛,不知在等什么人。”
欧阳菁忍不住皱起眉头,道:“你别开玩笑了,好像你见到似的。”
阿烈道:“不管你的夜行术多么高妙,只要你往上一冒,就会被他发现。”
欧阳菁听他说得认真,不似是开玩笑;当下道:“好,我不妨试一试。”
他们说话之时,声音极低,虽在黑夜之中,亦传不出几尺远,所以不虞隔墙之人会听得见。
阿烈道:
“不行。你一上去,就会被人察觉。我告诉你。墙内是个露天跨院,两丈许远有一排房间,岑瑜就在房内的窗下、向外面瞧看。”
欧阳菁道:“你放手,让我瞧瞧,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服气你了。”
阿烈放开手,道:“等到被他发现、服气也没用了,是也不是?”
欧阳菁道:“我自有办法。”
她往前面再走五六步,墙头摆着几个花盆,她口中发出一声猫鸣。这才向上窜起双手搭住墙头,只冒起半个头,在花盆边,向墙望去。
阿烈暗点点,循道:“这法子真不错。”
猛然想起一事,连忙奔过去,拍拍她的小腿。
这时她挂在墙上,已看得见墙内的已切。果然已如阿烈所言、在对面的一排房间有已间灯光外泄,在窗间有一条人影站着不动。
她飘身而下,尚未开口,阿烈已拉了她向前走去,直到转个弯,这才停住了脚步。
欧阳菁问道:“又有什么事了?”
阿烈道:“他既是在等人,咱们若然仍在那儿,岂不是很容易被来人察觉?”
欧阳菁道:
“他会在等谁呢?假如是与极乐教之人联络,则我们今晚下手,或有问题。”
阿烈道:“是呀!只不知什么人要来?”
他们在黑暗中等了好一会工夫,欧阳菁时时查看四下的动静,阿烈只是不动,好像不关心此事。
又过了阵欧阳菁不耐烦起来,道:
“假如那要来之人、到天亮时才到达,我们岂不是失去下手的机会了?”
阿烈道:“不错。”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但我猜不会有人来了,你要下手,正是时机。”
欧阳菁讶道:“你这话有何根据?”
阿烈道:
“岑瑜已躺回床上,而且几乎是马上就入睡了,你现在去下手,岂不正好?从他入睡这一点看来。可见得他所等之人,约定时间已过,大概不会再来啦!”
欧阳菁如言出去,窥看一下,果然房中灯火已经熄灭,窗间似乎也看不到人站立的迹象。
她暗吃一惊,忖道:
“这家伙什么神通?居然事事前知,但目下且不理他,先去做手脚再说。”
她跃入院内,阿烈也随后进去,帮她找寻别的人所居的房间,好在都在同一跨院之内,很快就找到了。
欧阳菁施展家传绝技,只见她打量过房内的情形。外面的明间,虽有床铺,但目下人却是睡在内间。她从窗隙间先丢了一件物事进去,这才取出一个小小的钢盆,两端各有—根小管哨子。
阿烈看了此物,心下纳罕,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只见把其中一根小管拉一下,竟然拉长了许多,远一尺以上。
之后,她把小管插入窗内,咀巴凑在盆上另一很小管上,轻轻吹动。
顿时一阵香气,透入房边的阿烈的鼻中。阿烈情知自己不畏千毒,是以也不须屏住呼吸付道:
“你如果用这什物事来对付我,那就只有惨败而已。”
方转念间,欧阳菁似是不慎,在窗户上弄出了声息。”
阿烈吃了一惊,揪她一下。表示有了变故。原来在他灵敏无比的视听神经中枢,已接到警报。
他清楚地感到内间已有人起床,并且悄悄走出来。由于房内较黑,是以纵然向内窥看,也看不见他出来。
那人已走出外面,而欧阳菁只停止了吹气的动作,把头缩开,但左手仍然托住那个盆,让那长管冲入窗外。
忽听“嗤”的一声,阿烈的神目看得真切,一枚很细的,像是针状的暗器,透过窗纸,射将出来。
假如欧阳菁还在吹气,面门一定被此针射中。
阿烈迅快忖道:
“你使用毒气,仍然末把对方毒倒,这岂不是要打上一场架。”
念头方自掠过心上,但见欧阳菁收回钢盆,并且跺一下脚,发出“吟吟”的一声。
阿烈虽是聪明,但这刻也看得糊里糊涂,不知道在搞什么鬼,不过他很清楚的晓得一点,那就是欧阳菁也知道对方已经起身出来。
她既已知道这一点,阿烈便放心不少。
在阿烈的感觉中,那人已刷地跃到门边,不问可知他乃是要开门出来,找敌人的霉气。
因此,他暗暗聚集功力,准备出手。说时迟,那时快,房门还没有动静,那人却已倒了下去,发出“砰”的一声。
欧阳菁笑一笑,也不推门去看,一迳跃到邻房,又如法泡制。
然后她到第三个房间,此房是个单间,乃是宋、岑的车把式所居。这一次欧阳菁换了一个铜盆,同时事先也没有丢什么东西进去。
她迅即走回第一间房间外,阿烈自然跟着她,只见她推了推门,发觉闪住,便从袋里中拿出一件工具,插入门缝中,挑弄了几下,那门便应手而开了。
靠近房门口,有个人躺着,身上衣服相当齐整。
阿烈不必灯光,已看得清楚,发觉那人真是岑瑜,那勾勾的鼻子,以及瘦削的身材,一望而知。
此外,他还看见靠门边这一大片的地上,错落布满了形状奇异的小针,针尖尽皆向上,长约半寸。
这一点倒使他感到迷惑了,忖道:
“她利用这一片毒针,摆下陷阱,又故意弄出声响,等敌人发觉,出来查看,此计固是十分高明,因为任何人发现有人使用迷香,而又功力不高,发出声响,肯定不则一声,想悄悄出来捉住暗算之人,这么一来,绝对不会惊动别人。”
想道这里,面上开始流露出迷惑之色,继续付道:
“但问题是在她如何能使这一片面数十支小针。尽皆针尖向上,莫说隔窗丢入去,就算是一支支的摆在地了,也是十分的不容易。”
他举步跨入,欧阳菁大吃一惊,伸手挡住他,道:
“不行,等我收拾干净之后,才可进去。”
阿烈笑一笑,道:
“我已看见地上的小针了,正是要进去看看你用的什么手法,居然能得支支都向上。”
欧阳菁摇摇头,道:
“你眼力这么好,真是使人感到难以置信。”
阿烈已跨入去,脚底落地之前,先把那些小针拔开,一面应:
“据我所知,很多人都能够黑夜视物,有何奇怪?”
欧阳菁道:
“你那里知道?我这些毒针,漆上一种特别设计过的颜色,洒在地上时,白天也极难瞧得出,在黑夜中,任是最好的眼力,也无法瞧见的。”
她一面说,一面取出一块黑色石头,很快就把些小针,全部吸起,不须几下,就通通收好,放在一个很小的盒内。
阿烈还拿了一根,细细瞧着,发觉此针虽然极细,但头部粗而圆,敢情是利用“不倒翁”那种原理,使这些毒针全都能够坚立起来。说来虽是简单,但这等设想,以及制作之时,都是非常困难的。
欧阳菁警告他道:“小心,只要皮肤有一点点损伤,致命的毒力就会入侵。”
阿烈笑一笑,把毒针还给她,道:“你自家小心些才好,不必为我耽心。”
欧阳菁道:
“我手中已戴上一层药水制炼过的人皮手套,一点都不必担心,现在我去把昏迷在床上的淫娃杀死。”
阿烈点点头,看她奔入内间,心想:她说到杀人之事,口气十分轻松自然,好像是洗面吃饭一般,真是可怕得很。这大概是家世使然的吧?他想到这里,再低头瞧瞧岑瑜,僵卧的尸体,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胃中很难过。
转眼间,欧阳菁走出来,在黑暗中,她的神情显得很是颓丧。
阿烈虽然想到她下手杀人,似是不费一点事而发生了不少感想。可是今日这些人,全都有该杀之道,并不伤天害理,是以他对她并没有反感。目下一见她神情颓丧,似是碰到不如意之事,不觉一惊。
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两个侍女,必定是身无寸缕,形相猥亵,使她感到很碍眼而不高兴。
但接着就猜她一定是遭受挫折,多半是内间的床上,空空如也,是以她无法达成使命。
他连忙问道:“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欧阳菁道:“唉!说起来真不好意思,我竟然无法下手杀死她们。”
阿烈听了这话,大出意外,内心暗暗欢喜。不过他又明白一点,那就是这个恻隐仁慈的美德,目下不能加以赞扬,因为在这险恶可怕的江湖中,若是处处存有妇人之仁,定是后患无穷,终必为敌人所算。
因此他很沉着地,说道;
“那些淫娃荡妇,罪应处死。不过你既然不惯,那就待我想法子,只不知她们将于何时回醒?”
欧阳菁道:
“光是我的迷药,也须三个时辰以上,何况我已点了她们的穴道。唉!我真想不懂,为什么下不得手?但刚才撤毒针,以及最后对付那车把式时,用的有毒迷香,我却毫不迟疑,莫非我对男人便容易下手?。
阿烈道:
“老实说,我看了尸体,胃里面就直难过,生出呕吐之感,也许我去杀死那女人,便不感到难受。”
事实上他早就想到梁忠山这个老仆,所以他才胆敢一口就应承下来。
他又道:
“我自己把这些男男女女统统运走,我日间已找妥了地方,并且化装好才回来,你也找一件李姬的外衣,我们在天色破晓前,就得离开。”
他奔入内间,从床上抉起二女,但觉她身材丰满,并且由于皆是赤裸,所以感觉得出她们的体温。
他用一件外衣,把二女一齐包好,扛起来奔出去,又往邻房。
这时欧阳菁已收拾好毒针,并且把宋永胜的尸体踢开。
阿烈进去内间,揭开被盖,只见李姬昏迷似死,身上也是一丝不挂,雪白的肌肤,起伏的曲线,甚是迷人
他晓得这个李姬实际只有二十岁不到,正是鲜花一般的年纪,加以委实长得丰满迷人,肌肤白腻。
阿烈尽管心中已存杀机,可是事到临头,不禁也觉得很是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他心头鹿撞,忖道:
“这个美女,如此杀死,未免太残忍了,我岂能没有一丝一毫的惜花之念呢?但目下如何是好?放是一定不能放心是,若然交给梁大叔,他绝对不会惜得怜玉,她们有死无生。”
这念头说时费事,其实只不过是转眼工夫而已。幸而这时欧阳菁已到那边的边间,看那赶车大汉的情况,是以他的犹疑,才没被她察觉。
欧阳菁回转来,只见阿烈业已出房,肩上扛着三个叠在一起的长形物体,皆以外衣包住。
由于夜风吹拂,外衣有一截散开,顿时露出几只雪白的玉腿。
她皱起双眉,道:
“你若是在路上被人看见,一定闹出很大的事情,不出三日,天下南北十三省尽皆得知。”
阿烈看了垂在胸前的几条玉腿一言,承认道:
“这的确是非常骇人听闻的事。但办法很简单,只要不让人家看见便是了。你的路比我远,又要逐个的搬运,很费时间,何不少替我耽心,去做你自家的事?”
欧阳菁气道:“人家是好心提醒你。”
阿烈道:‘我知道,你放心去吧!”
她仍然心有不悦,一运转身奔入房内,扛了岑瑜出来。
但见阿烈已去得无影无踪,当下也跃上墙头,越出客栈,通向日间选好的城外一个极荒僻地方奔去。
阿烈已走近杂货店,突然停下脚步,忖道:
“唉!我难道当真让李姬送死么?”
转念又想道:‘她如不死,定会被极乐教之人查出底蕴,坏了大事”
此一想法,似乎还不足以使他安心送她去死,并且另一念头泛起来:
“她长得这么动人年华正青春。若然死了,正合着红颜薄命这句话了。唔!假如我不杀她,而是把她藏在一个地方,则她便是我的秘密情妇了。这个女人必是天生尤物,男人得到她,定然其乐无穷。”
他满腔绮念。如波澜起伏,此生彼长,在胸中涌激不已。
要知这本是男人的天性,尤其是当一个女人,如古道边的垂柳一般。并无定主,人人皆得而攀折,同时她又非常漂亮迷人的话,没有理由男人不会生出欲念的。除非是缺乏这等能力之八方是例外。
因此,阿烈心中有欲念和理性在交战,实在是非常合乎人情自然之事。谁也不能对他加以谴责。
至于他日后如果已信奉了某一种哲学或宗教,因而认为今晚的想法,乃是不当之举,那也当作别论,因为他目下还没有也不懂这等信仰和道理,谁又能过份严厉的怪责少年无知的本能欲念呢?
突然间一道人影,自远而近,悄悄掩到阿烈身后一丈之处。
到了这么近,阿烈方始警觉,心中怦地一惊,疾然回头望去。
黑夜中依然瞧得真切,来人鬓发泰半已白,身披长袍,腰间用一条布带束札着,腰肢挺得毕直。
这个老人敢情是梁大叔,他炯炯双目盯住阿烈,自然也看见了那几条垂下来的雪白大腿,很不雅观。
梁大叔道:“少爷,快到屋子里来。”
说罢,当先转自奔去,窜越过四五座屋字,就到了杂货店。
在后面的房间内,阿烈把三个女子放在坑上,外衣散开,赫然露出三个赤身裸体的女子,在灯光之下。呈现眩目的一片雪白。
阿烈心中叹一口气,忖道:“我这样就放弃了么?”
梁大叔深深看他一眼,接着俯身去看那三个女子,还用手拉扯拨动,以便细细端详每一个的样貌。
最后他指着当中的一个,问道:
“这一个就是李姬了,对不对?她确乎很漂亮。足以使男人动心。”
阿烈郁郁地点头,没有开口。
梁大叔这回迫近看着他,问道:“少爷,你有何心事?”
阿烈先是摇摇头,但旋即泛起欣然之色。说道:
“梁大叔,你实在已不是我的父亲了,所以我应该把心中的疑惑,请你教导。”
梁大叔肃然道:“小主请说,老奴这厢恭聆。”
阿烈道:
“我不但不忍心杀死李姬,甚至想把她藏起来,作为情妇。这个想法,岂不是很可怕么?”
梁大叔道:“这又有什么可怕呢?”
阿烈耸耸肩头,梁大叔又道:‘小主一定有所感触,才会说可怕。”
阿烈道:
“例如我这样应不应该,又例如刚才我心绪很乱,所以连你到了身后,几乎也没有发觉等等,这岂不可怕?”
梁大权道:
“女色迷人,往往如此,假如这个女人,能令你败坏大事,以致失去报复血海之仇的机会,你还要不要她?”
阿烈道:“自然不要她啦!”
梁大叔道:
“那么你得记住,此女淫荡成性,寡恩无良,出卖主人,随便与人苟合。这等女人,尤如败柳残花一般,岂值得去冒事机败露之险?老实说,单单是救她活命,危机只限于被极乐教查得真实内情而已。但如果你收她为情妇,则你身份败露,只不过是迟早之事。”
他停歇一下,又道:
“说到她使你心乱,所以不曾察觉老奴行近之事,这倒不必过虑,只因老奴出身于化血门,轻功一道,颇为高明,你能在一太的距离,便发觉我,已足见灵警过人了。”
谁知这正是阿烈最害怕之事,他原是能把十丈八丈方圆内的一切,以听觉代视觉,一切宛如目击。这是感官的功能在心灵中融合为一的境界,而达到此一境界,定须常保心灵中的宁静不可,李姬之事,使他失去此一能力,教他如何能不惊心动魄?
从这一件事中,他已得到了教训,那就是他切切不可被色欲扰乱了心灵,尤其是在要保持警觉的情况之下,情绪的波动,将使他遭遇到杀身之祸。
由于梁忠山说过番大道理,因此。阿烈虽然还有一点不舍之心,也说不出口了,只好眼睁睁看着梁忠山把三个女人挟到后园去。
梁忠山孰视过那人的面孔,便先行把他搬到后园,回转来以后,从一个大皮箱内拿出一个小小的皮包,约是一掌宽,长度加倍而已。
他松开扣子,揭开皮包,模出四五个金钱般大的薄薄圆盒,阿烈好奇地看看。
梁忠山道:
“那厮面部手脚的肌肤都比你黝黑得多,所以必须替你露出的皮肤,加上颜色才行。
这是化妆术中第一要诀。”
那些小圆盒中,敢情皆是颜色,深浅不同,也有红和黄等色泽阿烈等他用一支特制的短柄毛刷,替自己上过颜色,然后说道:
“假如要化妆为一个皮肤特别白晰之人,岂不是无法办到?”
梁忠山道:
“咱们查家乃是此道高手,别人可能被这个难题难倒,但咱们却不怕。”
他从皮包中,挖出一小叠白色之物,看来薄如蝉翼,不知是什么物事。
梁忠山指指这叠白色的物事,傲然道:
‘这是一副制作精绝的人皮面具,戴到面上,五官之形丝毫不变,可是肤色却变得极白。就算迫近注视,也很难看得出是戴上人皮面具。世间有些人皮面具,戴上之后。
面目变形而肌肉较硬,全无表情,一望而知有异。”
阿烈道:
“这真是闻所未闻之事,假如我戴了这副面具,就算很熟之人,也看不出破绽而只觉得我面色忽然变得很白么?”
梁忠山道:
“正是如此,所以当你要化妆为肤色白晰之人。但须戴上人皮面具,再动手勾眉画眼,利用阴影的强弱,使脸部某处看来突起或凹陷。”
他一面说,一面替他勾画泻染,最后,加上胡须。然后把嵌在皮包内的镜子,送上去给他自照。
阿烈看了一下,笑道:
“果然很像那车把式了。你真行,几时有空,我定要讨教这一项绝技。”
梁忠山道:
‘小人自然要把这门玩艺传给你,几天就可以做好几副人皮面具,以供应用。”
阿烈骇一跳,道:
“什么?你敢是打算用李姬她们的面皮制造?那太可怕了,我戴上的话,必定觉得非常不舒服。”
梁忠山笑一笑,道:“小主公觉得那一点可怕?。
阿烈道:
“想想看,她们本是很美的女孩子,但剥下面皮,变成一片血淋淋的,多么残忍可怕?你难道一点都不觉得么?”
梁忠山道:
“老实说,小人一点也不觉得怎样,不过小主公可以放心,因为那些材料,不是从她们的面上剥下来的。”
阿烈摇摇头,道:
“总之不大好就是啦,现在我得回去啦!咱们以后怎样见面呢?”
梁忠山道:“你们如果在一起,小人实在不便露面。”
阿烈道:“我这回出了此城,弃车之后。就与她分道扬镳。”梁忠山道:
“这敢情好,小人立刻带领小主公前去一处地方,找回化血神功的秘笈。”
他上上下下的打量阿烈一阵,才又说道:
“小人有好些问题,要跟小主公你研究,但现在已没有时间,只好等路上会合之时再说吧!”
阿烈道:
“我不忙,只要在天亮前返回客栈就行啦,首先我想知道的是,那本秘笈在什么地方?”
梁忠山道:
“这本秘笈,小人从未见过,但因主公特别信任,是以听他略略提过,得知这本秘笈,不知是什么质料所制,薄如蝉翼,虽然有很多页,但卷起来,却只有指头那般粗细,乃系塞在查家历代传家之宝‘分光剑’剑柄之中。”
阿烈道:“那这本秘笈的尺寸也很短了?”
梁忠山道:“不错,大约是四五寸见方吧,小人可不知道。”
阿烈吸以口冷气,道:“知道是什么材料?”
梁忠山讶道:“你如何晓得?”
阿烈道:“一定是人皮所制。”
梁忠山迟疑一下,笑道:
“这一猜很有道理,咱们化血门秘传制炼人皮之术。天下无双,果然可以制造这么一本册页。”
阿烈摇摇头,道:“这得用多少人皮啊?”
梁忠山道:
“人身上除了面皮之外。胸背和大腿上的人皮,都可以取用、一本秘笈,用不了几个人就够了。”
阿烈兀自摇头,忖道:
“梁大叔讲起这事,口气中轻描淡写得很,可见得他根本不把这关乎人命的事放在心上。这样说来,我查家可不能算是正派了。”
他想到这一点,顿时十分气馁,不敢再想下去,因为如果他化血门查家并不正派,杀孽甚重,并且他父亲查若云又到处拈花惹草,淫辱人家妇女,细论起来,岂不是应该得到合门被戮的惩罚?
梁忠山心中也甚是感慨,因为他感到这位小主公,虽然聪明机警之极,不愧是虎子,可是他不但没有英雄好汉的性格,甚至是胆小心软的人。以他这等性情,如何能够闯荡江湖,成就大名?
双方都没有泄露半点心中的想法。阿烈岔开话头,问道:
“分光剑是怎样子的?会什么特点?”
梁忠山道:
“据说此剑乃是天下至利的神兵,宇内已无其匹。但此剑是何形状,小人却不知道。”
阿烈讶道:“那么咱们到什么地方去找?”
梁忠山道:
“咱们查家有一座秘库,却不是在家宅之内,所以对头们一定没有找到。小主公只要打开那座秘库,顿时就是富甲一方之人,钱财可以用之不尽。自然那分光剑和神功秘笈,也在库中。”
阿烈听了这话,深为感动。道:
“你真是非常忠心的人,竟不曾把秘库财宝,据位已有。”。
梁忠山微笑道:
“小人如何有那等福份?据小人猜想。那秘库之中,必定还有很多奇怪之事,是咱们做梦也想不到的,这是小人平时偶然听见一些口风,归纳起来而得的推测。”
他突然露出兴奋之色,原来当他说这个推测时,猛可想起查家一神秘传奇药,服用之后,能使一个胆小怯懦之儿变为胆大生毛,可以杀人不眨眼。这种奇药。正好是阿烈所需要的。
他大为欣慰,忖道:
“只要小主公变得心肠狠辣,以他那种脱肌换骨了的身体。加上练成了本门神功绝艺何愁不能横行天下,重振化血门的声威?”
阿烈问他想起了什么,梁忠山却支吾以应,不肯告诉他。
阿烈也不追问,向他说道:
“我打算离开许昌几十里路之后,便弃去马车,与欧阳菁分开,我到开封去,扫祭我娘之墓,以后恐怕不易抽空回来拜祭了。”
他说到后来,触动了悲怀,眼泪都快要滴下来。
梁忠山本来感到很不安。可是件他如此伤心情挚.一时说不出阻止的话,只好点点关,道:“那么我们在何处会合呢?”
他想了想,又道:“在朱仙镇如何?欧阳菁会不会路过那儿?”
阿烈道:
“我也不知道?我看这样子,咱们在开封碰头的好,你先帮忙我办一件事。”
梁忠山心中暗暗诧异,因为阿烈本来很单纯,何以忽又有不少事要办?
阿烈把冯翠岚之事,扼要说出来、道:
“现在丐帮已布下罗网,一面发出独门飞报,通知十余个南方北上的高手,叫他们转向西行,沿途细加查看,而他们这五六个人、则向东追去,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假如能够早一步通知冯翠岚,她或可逃脱大难。”
梁忠山道:
“这位冯姑娘,对小主公有救命之恩。咱们无论如何也须尽力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