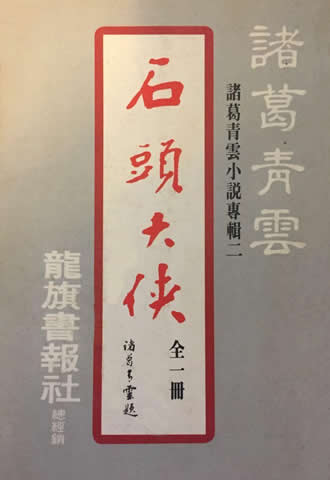纪香琼听从齐南山的话,暂时在济南隐居下来,此处且说薛陵的遭遇经过。
他出走之时,朱公明等人尚在庄内,因此他安然驰走,向东钻行。薛陵他深知朱公明精明毒辣,势力极大,因此化装为乞丐,弃马步行。一路上餐风露宿,倍加辛苦,这一日,已踏入广饶县境。
他经过两个村落,已感到有异,不久又经过一座村寨,这个村寨很大,四周有高大坚牢的寨墙,约有数千户人家。入寨之后,但见一片冷落死寂,好像是经过兵荒马乱之后的光景。
薛陵诧讶忖道:“这几处村庄,俱是如此冷落光景,不知是何缘故?我且趁买点吃食之时探询一下……”他虽是乞丐装束,但一路上总是花钱购买食物。
当下找着一户人家,屋内有个中年庄稼汉子,他才一探头,还未开口,那庄稼汉子就怒声骂道:“瞎了眼的小贼,敢是活得不耐烦了,快给我滚得远远的,不然就敲断你的狗腿!”
薛陵一怔,心想这厮火气真大,懒得与他争辩,连忙走开。说也奇怪,这一路上民俗淳厚,人人乐善好施,但此寨之内,家家户户的人,无不十分凶恶,都是未等薛陵开口,就火气冲天地把他轰走。
他连挨七八户人家臭骂之后,心中感到事出有因,决不是此地之人都用火药当饭,以致火气特大。眼光连转,发觉有一户人家之内是个老婆婆,当即掏出二三十枚铜钱,走到门前,先摊开手掌,让那老婆婆瞧见铜钱,才道:“我可不是上门乞讨,婆婆别骂我。”
老婆婆咧开没有牙齿的嘴巴,笑道:“罪过!罪过!我这么一把年纪的人,怎会张口骂你?”
薛陵问道:“婆婆这儿可有吃的东西?卖点给我行不行?”
老婆婆点点头,拿了两个馍馍给他,道:“不要钱。”
薛陵不肯,道:“我说过不是乞讨来的,请婆婆把钱收下。”
老婆婆一面摇头,一面向门外的天空望去,忽然笑容消失,叹一口气,道:“天色又快黑啦!”
薛陵不禁也转头望一望天空,发觉还只是未牌时分,离天黑还早着,登时大感胡涂,问道:“难道这儿比别处天黑得早么?”
老婆婆道:“不是天黑比别处早,而是害怕天黑,所以一过了午时,家家户户都心烦害怕。”
薛陵恍然地哦了一声,道:“那就怪不得我老是挨骂了,大家心里又烦又怕,自然脾气不好。”
老婆婆直着眼睛向外瞧看,喃喃道:“他们还不回来,待会儿要好好的嘱咐他们才行,免得明儿又给忘了。”
她转眼望住薛陵道:“我说的是两个小孙子和一个孙媳妇,他们都在庄地里干活,这时候还不回来,唉!真急死人了!”
薛陵躬身行了一礼,道:“婆婆,您老人家行个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心里蹩闷得难受,这会才未牌时分,那有庄稼人这么早就不干活的?”
老婆婆讶道:“什么!你都不晓得?我劝你快快走,赶过三十里路就不妨事啦!这几日正在闹妖怪,几十里地之内的村庄,家家户户都骇死了。”
薛陵这才明白了内中缘由,问道:“这妖怪怎样子闹法?难道还会吃人不成?”
老婆婆面色一变,低声道:“小声点,我年纪大的人不妨,但你年纪轻轻,正是那妖怪爱吃的。”
她泛起恐怖的表情,又道:“两年前已闹过一次,一共闹了一个月,周围十四个村庄,一共被妖怪吃了十六个人,那可不是真的把人吃掉,只是吸血,但被妖怪吸过血的人,有的骇得疯疯癫癫,不疯癫的也几个月不能走动,后来虽是能够行走,可是面黄肌瘦,四肢无力,都不能下田干活,你说可怕不可怕?”
薛陵道:“没有人禀告官府么?”
老婆婆道:“前年告到官里去,派来几个捕头查究,这些公人光会大吃大喝,都不办事,最后有一个被妖怪吸了血,便通通跑啦,现在是谁也不管这事,别处地方之人也不敢提起,生怕把妖怪惹到他们村里去。”
薛陵骇然道:“这还了得?只不知有没有见过妖怪的?那妖怪是怎生模样……”他略略一顿,便又压低声音道:“婆婆啊,您老人家或者不知道,有种恶毒的强徒坏得很,专会装神扮鬼,吓唬良善之人。”
他这么一说,登时搏得那老婆婆的信任,便也低声道:“也有人这么说来着,可是听那几个被妖怪吸过血而又没有死的人说,那妖怪身高体大,蓝面红须,眼如铜铃,发出的凶光可以把人骇死,黑色的嘴唇,两角突出两根獠牙,能够腾云驾雾,呼风唤雨……”
她喘一口气,才又道:“总之,这可真是个妖怪,附近的道士、和尚统统走个干净,谁也不敢惹他。”
薛陵倚在门边沉吟忖想,那老婆婆直着眼向外面张望,薛陵见了心中一阵恻然,想道:“倘使她的小孙子们遭遇不测,可真难为了这个倚闾而望的老祖母了,我可不信有什么妖怪鬼魅,好歹查究一下此事,只可惜我武艺低微,说不定会死在那恶徒手中,但这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当下向老婆婆探询妖怪出没之地,得悉那妖怪每次掳摄了人之后,翌日,村民就结伙到西北方八九里路的一座慈恩寺找寻,总是在大殿上找到,薛陵有意无意的又问出她的孙子们就在里许外的田里做活,便告辞而去。
出得寨门,放目望去,但见四下田地中杳无人迹,一片荒凉惨淡的景象,使他深深叹一口气,同时也因此而下了查个水落石出的决心。
他放步向西北方奔去,绕过一片杂林,但见数箭之遥一块靠着树林边的田地上,有三个人正在做活。
薛陵望去之时,彷佛见到一条影子在树林中闪动了一下,心中怦地一跳,忖道:“难道事情就这么巧,赶上我绕了过来,那林中本来有恶徒正要出现掳人,见到了我便缩回去?”
他心生一计,突然间,大叫一声,等田里的三个人全部望过来之时,才跌坐在地上,双手按着肚子,发出尖锐的呻吟声。
那三人是两男一女,互相商量之下,便一齐放下手中的活,举步奔来瞧看,到了切近,乃是两个壮伟的青年人和一个长得忠厚端正的小媳妇。
他们虽然见到薛陵是个乞丐,仍然露出关心的神情,过来询问何处不适。
薛陵一面呻吟,一面断续的说道:“你们……快点回家……妖怪……就要出现……把我扛起来……一道走就行啦!”
他们都现出惊愕之容,那小媳妇最先说道:“我们且照他的话做。”
原来她见薛陵虽是乞丐形状,可是剑眉虎目,她凭仗女子天生的敏锐直觉,感到可以相信这乞丐的话,所以出这个主意。
那两个壮健青年自家没有主意,便听从妇人的话,合力扛起薛陵,往回路走去。绕过杂林之后,薛陵一挺身站稳身子,挥手道:“你们快回去,你家老祖母心焦得很啦,我还要瞧瞧那妖怪是什么东西?”
他们都骇得面色发白,小媳妇道:“那物事怎生瞧看,你一个人最好别留在此地。”
薛陵微微一笑,道:“我可不信世上真有邪魔鬼怪。”
他暗中摸一摸贴肉绑在前臂上的小匕首,接着又道:“若是真有妖怪,那叫做时运不济,命该如此。”
他说得很是认真和镇定,使人一望而知不是开玩笑,也当真毫不畏惧,那小媳妇痴痴的望着他,心想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薛陵目送这三人隐没在寨门之后,才转身走出杂林,脚步飘浮,表现出病中衰弱的样子。良久才走到那一排树林旁边,忽然一阵怪异的低响,传入耳中。
薛陵已经尽其所能的收敛起眼神,面上本就已涂成黄色,所以外表倒很像扶病而行一般,他缓缓地无心地转眼向那怪异声响望去,不禁骇了一跳,原来一颗大树旁边,站着一个青面獠牙的怪物,高达八尺,常人只能齐他胸际。
他鼻孔中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宽阔的胸膛起伏不定,喷气之时,把两腮双颊上的红毛吹得乱动,形状煞是骇人,而且一望而知不是有人假扮。
这巨大怪物身上穿着衣服,可是裸露出双臂和双腿,筋肉虬突,赤毛甚长,底下登一双软底靴,这副打扮真是不伦不类。
薛陵发呆的瞧着他,那巨大怪物发出一阵震耳的咆哮声,双手捶胸蓬蓬乱响,虽是凶恶可怖,但细瞧却似是十分高兴欢愉。
那怪物跨开长脚,向前迈步,但又缩了回去,似是不敢走上来。
薛陵收摄心神,胆气更壮,开口问道:“喂!你是谁?”他还记得自己装病之举,所以声音中仍然有气无力。
那巨大怪物厉啸一声,远扬数里,薛陵装出耳朵疼痛,举手摀住两耳,啸声一歇,那怪物竟自口吐人言,道:“老天啊,你是第一个问我是谁的人,胆子可真不小,难道你竟认为我算得是人么?”
他言语流畅,口舌便给,倒是十分使薛陵惊讶之事,薛陵点点头,道:“当然是人啦,不是人是什么?”
那怪人道:“人人都叫我妖怪,只有你把我当做人看,这可真太难得啦,你不用害怕,我决不伤害你。”
薛陵微笑道:“你的外形确实有点骇人,不过我流浪天下,四海为家,奇怪事物见得多了,倒也不觉害怕。”
那怪人仰天瞧瞧天色,说道:“我虽不想伤害你,但到时候就情不自禁了,你叫什么名字?”
薛陵摇摇头,道:“你叫我一声小叫化就得啦!你贵姓大名?”
怪人道:“我现在已不能用以前的姓名啦,但你叫我什么才好呢?”他用巨大而长着锋利指甲的手,搔搔焦黄的乱发,沉吟忖想。
薛陵涌起满腔探求秘密的欲望,他想知道这怪人是谁?什么叫做“到时候”?他以前竟是另有姓名?那么是不是后来才变成这等模样?
那怪人狞笑数声,说道:“有了,我本来姓江,现在长得像山精海怪一般,就叫做山精吧!江山精,江山精,这名字倒是挺合适的。”
薛陵心中道:“我敢打赌,世上已没有比这山精两字更合适贴切的名字了,他原本姓江,只不知名字是什么?”想时,连连点头道:“就用这个名字也好,只不知山精大哥你本是何处人氏?怎会……怎会……”
江山精巨眼一瞪,凶光四射,狞声道:“怎会什么?”
薛陵本想问他怎会变成这般模样,但这刻觉得似乎不便老是触及对方心病,便改口道:“你怎会来到此地?”
江山精举手搔搔头皮,道:“我自家也不晓得,糊里胡涂就到了这处。”他的一举一动,纵是细微至说话时嘴唇的掀动,也使人觉得十分凶恶可怕。
薛陵好不容易才制止自己移开目光,事实上,眼前那张面庞太丑陋凶恶了,简直教人不愿多瞧一眼,他微笑道:“山精大哥,小弟有个疑问想请教你,只不知该说不该说?”
江山精点点头,但凶睛一转,便停住在碧朗长空之间,怔了一下,才道:“不能问啦,你快走,再说下去就来不及了。”
薛陵奇道:“什么事来不及?”
江山精厉啸一声,一晃身凌空跃到他面前,身法之快,大出薛陵意料之外,他大喝道:“快走,不然我凶性发作,便不知道你是谁啦!”
薛陵心头一凛,问道:“你的凶性几时发作?”
江山精长臂一伸,巨大如蒲扇的手掌已抓住他左臂,那五只粗大的手指,力气巨大无比,握得薛陵臂骨欲裂。他一挥手,薛陵整个人离地向前疾冲,飞出两丈有多,双脚才沾到地面。
耳听江山精咆哮叫道:“马上就要发作,快跑,不要回头。”
薛陵虽然有胆跟他一拚,只要他没有邪法,总还有一点机会。但这江山精对他毫无恶意,用尽方法使他脱离魔爪,就凭他这一份好心美德,岂忍与他决斗。
他不知不觉放步飞奔,眨眼间,已冲出老远。回头一瞥,那江山精竟像是一阵清风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薛陵大感诧异,脚步略缓,正在考虑要不要回转去查看,突然间,一阵震耳响声传来,但见那排树木内一阵骚动,许多树木折断倒下,响声不绝。
他顿时晓得那江山精业已凶性发作,正在树林中对树木发作。以这等声势瞧来,他的神力实在骇人听闻,纵是内外兼修之士,恐怕也难当得他的一击之威,而他本人身上这一点不三不四的武功,更加无法抵挡。
薛陵脚下加快,转瞬间,已达数里之外,早就瞧不见那座树林,因此也不知道江山精后来的情形。
他缓下速度,心中蓦地泛起后悔内疚之情,忖道:“我这一走了事,但江山精会不会闯入村寨之内,祸及村民?唉!我这等贪生怕死的行为,岂是侠义之士的行径,怎对得起忠义凛烈的先父英灵?”
他痛苦的长叹一声,停下脚步,忽见左方里许有座丛林古刹,心中一动,顿时打消了转回去之念,直向那座寺庙奔去。
不一会,到达庙外,但见山门上题着“慈恩寺”三个大字,这正是乡人纠众到此寻回被掳者的地方,想必就是江山精盘踞的巢穴。
当下疾步入内,放轻脚步,小心查看四下动静,踏入大雄宝殿,但见殿内方砖上犹有不少黑色的血渍。
他明知凶险万分,但心中毫无畏怯之意,一直奔入后殿,这座慈恩寺倒也不小,深达三进,第二进大殿和两侧的侧院都杳无人踪,便奔入第三进。
四下一搜,都无异状,也没有别的怪人在内,他在一处院落内凝身止步,想道:“江山精如若踞宿此地,必定有迹象可见,目下却找不出他藏身之处,倒是十分令人不解,难道他另有宿处不成?”
一面寻思,一面转眼张望,忽然见到高出院墙不少的一座钟楼,那口巨钟在最顶之处,下面乃是石砌台架,僧人如欲鸣钟,须得从石台内的梯子攀上。
他钻入钟楼内一瞧,上面还有一层木楼板,当下跃到楼上,只见两丈方圆的楼板上有许多啃过的骨头,还有半头猪,一大截牛腿,俱是鲜血淋漓。
上面巨钟吊架上一条粗索垂下来,乃是悬挂巨钟之后剩余的,不但垂到楼板上,还多余不少,堆成一个索圈。
薛陵瞧来瞧去,测度出吊架离楼板达丈半之高,那口巨钟甚是巨大,重逾千斤,当下有了计较。
他先猱升上吊架,移到巨钟顶的横木上,用匕首割断索结这一边多余的巨索,此举甚是费力,但终于被他割断了。
这口巨钟用粗索吊起之故,乃是准备铸造铜环钢链之后,才松开绳结放下巨钟,所以余下很长的一段粗索,以备吊落巨钟之用。
薛陵把粗索绕过横木,在巨钟顶端的孔洞穿过缚牢,然后垂索而下,先把这一端打个活结,摆放在楼板当中。然后又跃出钟楼之外,拣定距楼丈许的竹丛中一根长竹。
薛陵费了不少气力,才把这一株长竹扳得弯曲,竹端嵌入钟楼石缝之内,便不弹起,在长竹顶端,他使用两根后来才找到的绳索缚牢,一条用作拉出竹尖,好让长竹弹起,另一条别有作用,暂时不管。
连试三次,对这根长竹弹起的速度和强度,感到满意,这才把长竹嵌好,把第二根绳子缚在钟楼内垂下来的粗索的活结附近。
这一来若是有人踏入活结圈内,外面扯动长竹顶端的细绳,长竹从石缝内滑去,疾然弹起,使另一条细绳带动了活结,向上提起急拉,可以收紧活结。
不过此举也是徒劳无功,因为被粗索活结套住之人,最多跌上一跤,甚至被长竹的弹力拉出钟楼之外,也不致于有什么伤害,尤其是这个圈套是对付江山精之用,他身体伟巨,力大无穷,可以测度得出那根长竹之力不能把他扯跌,更无法把他拖出钟楼之外,再说即使可以拖出钟楼之外,他还不是一举手间就可以恢复自由。
当然薛陵另有安排,第一是这个打着活结的粗索虽然很长,可是他量好所需长度,割断了一部份,使得这个活结恰好是平放在楼板,不长也不短。第二是他再攀升巨钟顶端,十分小心的用匕首割划原本吊住巨钟的粗索,割断了三分之二,便停手不动。此时他满头大汗,深恐这余下的三分之一粗索承受不住巨钟的重量,巨钟因而跌坠,若是就此罢手,又怕等一会那江山精中了圈套,乱扯乱蹦之时,仍然没把这三分之一的粗索震断。
要知他布下这整个圈套,主要的得靠这口巨钟掉下来时把江山精砸死,但要巨钟砸下来,非用那活结的圈套不可,假使江山精被活结收紧,他这等凶暴,一定绷扯粗索,这时由于粗索的另一端绕过横木而系在钟顶上,他一扯起巨钟,除非不松手,松手的话,那巨钟向下沉坠,自然能把原本吊住巨钟的粗索绷断,因为这根粗索业已被薛陵割开了三分之二。
他定神想了一会,收起匕首,极其小心地离开,之后,他拿着缚着长竹尖端的细绳,一直走到另一丛修竹之中,设法爬上丈许之处,恰好瞧见钟楼上的情形。
这一番手脚,费去很长的时间和许多精力,只累得他气喘不已,四肢微感酸软。
天色已近黄昏,薛陵心中大为着急,心想:“那江山精若是等到天黑之后才回来,那时已瞧不见他的脚是否踏入活结圈中,便无从发动机关了。”
正在着急之时,突然一阵狞厉啸声传入耳中,初听那啸声好像距离很远,但转眼间,啸声再起,已到了附近,不久,一条长大人影落在院内。
薛陵凝神定虑,极力减低呼吸之声,心中紧张之极,暗呼今日是祸是福,全靠这个机关灵或不灵了。
江山精挟着一个年青村人,在院内团团直转,但见他好几次张开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要向那村人身上咬去,但堪堪咬中,便又停住。
薛陵怎样也想不通江山精这个茹毛饮血之人,为何不敢食人?尤其是分明瞧出他十分垂涎欲滴的样子,却总是不敢当真咬下。
江山精团团转了一会,突然间,嘴巴贴在那人颈侧,嘓嘓有声的吮吸起来,薛陵知道人体中以颈侧的大动脉最便于吸血,所以明白他在干什么。
他只好硬着心肠不管这村人的生死,过了一阵,江山精挟住村人一跃而去。
薛陵暗想:“他一定把那村人弃置在大殿上。”眼看天色渐暗,心中的焦急真是难以形容。
幸而片刻间,江山精就回转来,他在老远便腾身向钟楼纵去,真有点像腾云驾雾。他到了楼板上,大步走到角落,取起牛腿,张口大嚼,这一次他虽是经过中心位置,却不曾踏入活结之内。
薛陵急出一头热汗,瞪大双眼,心中直叫道:“老天爷帮帮忙,教那江山精踏入绳圈之内。”
那江山精只咬嚼了四五口生牛肉,便把牛腿丢下,举步走去。
薛陵眼睛瞪得快要突出眶外,只见他巨腿提起,跨到活结绳圈上空,接着向下踏落,这一脚可正踏在活结绳圈之内。
薛陵更不迟疑,用力一扯手中细绳,绳子把嵌入石缝内的竹尖拉出来,便迅急向上弹起。
长竹一弹起,便带动那个活结,向斜上方升起,由于江山精的粗腿被套住,活结自动收紧,便牢牢束住他的小腿。
以那根长竹弹起之势,力道甚猛,若是常人,非摔一大跤不可,但江山精力大无穷,身壮如山,站得稳如盘石,动也不动。
他口中发出咆哮之声,举脚挥甩,但活结已收紧,那里甩得掉?
他登时大大冒火,抓住粗索乱拉乱摇,他力大无穷,随手一拉,竟把上面那口千斤重的巨钟拉起数寸,接着向上松之时,那口钟便向下沉,一下子坠断了原本吊系巨钟的绳索。
那口巨钟迅急向下砸落,江山精虽是力大身重,但一则不曾防范,二则他身躯怎可与千斤重的巨钟相比,登时一跤跌倒,一条粗腿被活结粗索向上扯升。
巨钟砸下来之时,恰好江山精身躯向上升,两下一凑,碰个正着,“砰”的一声巨响,江山精被巨钟碰开,而巨钟因这一下相碰而生出的缓冲力量,使得下坠之势减慢,故此落在楼板之时,虽然又是一声巨响,整座钟楼都剧烈震动,尚幸终于不曾把钟楼砸坍。
江山精倒吊在空中,全身软垂,动也不动,好像已被砸死。
薛陵大喜过望,迅即从竹丛中跃出,奔上钟楼,但见江山精巨大的身躯在空中微微晃荡,双睛已闭,口角流涎,可是鼻中仍然有粗重的呼吸之声。
他把袖内小臂上缚着的匕首拔下来,向他胸口比划一下,作势欲刺。
但他陡然间泛起一阵痛苦和怜悯,想道:“他虽是十分凶恶,可是仍然保存得有一点人性,晓得凶性将发,劝我快走,又不忍得生噬人肉,只吸几口鲜血就把人丢弃在大殿上。由此可见得他本是性情良善之人,只不知何故变成这等骇人的模样。”
然而他的理智又告诉他,倘若不趁这刻赶快下手,让他回醒,便再也没有更好的机会了。
他咬牙举起匕首,脑海中迅快想道:“江山精虽是无心为恶,无奈凶性难以控制,若不狠心杀死他,只怕他还要害死不少善良的百姓。”
此念掠过心头,更不迟疑,手中匕首运力向他胸口刺去。
只听“啪”的一响,匕首如中败革,竟刺不进去,薛陵大惊道:“他居然刀枪不入,若不是我胡乱设计使用那口巨钟把他碰昏,谁也别想弄死他。”
当下又用匕首刺了好几处,仍然刺不透他坚厚的皮肉,薛陵心知这与自己乏力有关,但纵然一身气力俱在,可是对方皮肉如此坚厚,谅也刺不到他的心脏,因此最多令他略受皮肉之伤,决难把他弄死。
这时他心情又难过又紧张,前前后后查看了一下,好像都没有致命的部位,忽然间,见到他太阳穴上青筋突起,那是倒吊着血液集中头部之故。
他试用匕首刺向江山精的太阳穴,然而纹风不动,但由于那两条粗大的青筋触发了他的灵机,仔细瞧瞧他颈侧的动脉,但见突得更高,颜色似是比太阳穴的血脉深得多。
薛陵用匕首插向青筋侧边,用力一挑,轻响一声,一股鲜血溅射出来,腥臭无比。
他强自抑压住那股恶心之感,退开一旁,顷刻之间,江山精头面全身鲜血,楼板上已流了一地,腥气扑人。
那江山精因是倒吊之故,血液从伤口流出来,甚是急疾,过了好一会功夫,他突然间身躯一动,双睛缓缓翻开。
当他恢复知觉之后,便剧烈挣扎,但他神智未清,竟不晓得弯竖起腰身去解足上之缚,反而大声咆哮吼叫,挥拳乱舞。
他果真力大无穷,这一阵挣扎,弄得整座钟楼都摇震不休,好像就要坍倒似的,幸而那根悬吊巨钟的粗索和横梁都十分坚牢,没有断折。
薛陵已躲起来,但心中十分耽忧,一则恐怕他把钟楼弄倒脱身,二则怕伤口自合,不再流血。
天色业已全黑,江山精的咆哮声十分恐怖,夹杂着粗重的呼吸声。
薛陵心想自己反正不能再查看他的情形,便离开钟楼,走到大殿上。
他用火折点燃殿上的长明灯,荧荧灯光之下,但见一个人躺在地上,上前一看,正是早先被江山精吸了血的乡人,他设法想救醒他,以便问一问经过情形,但那农家少年一直昏迷不醒,由于这一件事,薛陵心中觉得好过一些,觉得自己弄死江山精之举,实在是义不容辞的事。
他在另一个院落的禅房内躺下,一面侧耳倾听钟楼的声响,这一夜真是漫长难渡,他在不时随风传来的咆哮声中时醒时睡。
这真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恐怖经历,但他自觉仍然有胆量可以支持承受,须知他很可能忽然惊醒之时,发觉江山精狰狞地站在床前,世间之人,无不怕死,但若是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这惧怕之心,定然减少许多。这就是说,人类都害怕不可知的事物,因此虽然是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的薛陵,仍然感到惊恐怖惧,因为他不知道江山精会不会挣脱束缚和找到此处来报仇?
天色微明之时,四下一片岑寂,薛陵经过一夜的紧张等待,这刻反而沉沉睡着。
他在梦中陡然被一阵声响惊醒,腾地跳下禅榻,揉揉双眼,定一定神,侧耳而听,分辨出这阵声响乃是从大殿那边传来。
这时红日满窗,把长夜中使人不安的黑暗完全驱散。他悄悄走出禅房,向大殿走去,在殿外便停步聆听,阵阵哀伤的哭声传入耳中,夹杂着几个男人劝慰之声。于是他稍稍放心地从门缝张望出去,但见十多名掮着锄铲的乡人,围住那个昏迷的农家少年,在少年身边有个妇人掩面大哭。
过了一阵,这些人通通走了,也把少年扛走,整座古寺又陷入寂静之中。
这些乡人们都不敢到寺内各处查看,薛陵因此想道:“那江山精如若已死,我便得想个法,告诉乡民们,否则他们还要惊恐许久,将来说不定会被奸人趁机利用他们畏惧的心理,而做出种种恶事。”
当下悄悄转身向钟楼走去,心中十分紧张。到了钟楼之下,侧耳聆听片刻,毫无声息,于是壮起胆子,从木梯轻轻爬上去。
他的头刚刚伸上来,一声惨哼传入耳中,骇得他那颗心大跳特跳,暗想:“原来江山精还未死去。”
但薛陵旋即瞧清楚江山精仍然倒吊在粗索上,两条长臂乏力地垂下,满楼板的鲜血,此刻业已凝固,呈现一种使人恶心的紫青色。他口中偶尔还发出呻吟之声,薛陵踏上去,叫道:“江兄,江兄……”
江山精似是没有听见,口中喃喃的发出一些声音。薛陵仔细一瞧,他颈上大动脉的伤口,仍然有血滴出,不禁大感骇然,忖道:“他流了一整夜的血,至今未干,若是用大水缸盛装的话,最少也可以盛满几个大水缸。”
他已听明白对方口中不断的声音是要水喝,心下大为悯然,想道:“他纵是罪大恶极,也不该受此酷刑。不管他会不会把我弄死,我仍然要把他放下来。”
此意一决,更不迟疑,纵上去抓住绳索,用匕首力割,眨眼间,“砰”的一声大响,江山精已掉落在楼板上。
薛陵很快就去提了一桶清水,用巨大的木瓢舀起,送到他嘴唇边,由于江山精无法抬起巨大沉重的头颅,所以薛陵只好托起他的头,弄得一身皆是腥黏的血。
江山精连喝了六七瓢,这才停止,巨睛缓缓睁开,瞧见了薛陵,他有气无力地道:“是你把我杀死的?”
薛陵难过地道:“不错,江兄虽是有恩于我,然而为了千百无辜良善乡民,在下不得不这么做,还望江兄能够见谅。”
他准备忍受江山精的辱骂,可是江山精却没有这样做,反而长叹一声,道:“我早该自行了断,唉!试想活得这么令人可怖,还有什么意思?更别说残害了许多良民性命。”
薛陵肃然起敬,道:“江兄有这等仁义胸怀,在下真是失敬得很。”
江山精咧一下大嘴,缓缓道:“我原本是武林豪侠之士,不幸被万孽法师选中,以致后来身败名裂,变为精怪之类,虽然命运如此,但也是我意志不坚之过。”
薛陵大惊道:“江兄,你说什么?难道你以前不是这等模样的么?”
江山精闭目良久,薛陵几乎以为他已经死了,这时却发觉他睁开眼睛,援缓地说道:“我以前不但武功过得去,人也长得不俗,加上擅于词令,所以在江湖上颇闯下一点名气,也有不少红粉垂青。但最后我仍然过不了‘色欲’之关,沦落至此。”
薛陵急急迫问道:“万孽法师是谁?”
江山精道:“他的外貌潇洒正直,有如得道真仙,然而其实他是个万恶之首,罪孽如山似海,古往今来,无人可及。”他的声音渐渐兴奋起来,又道:“我可不是身受其害才这样极力诋毁他,事实上他真是万恶之首,因为这世上的恶人,大半是由他制造出来,像我只不过是很普通平凡的例子,这万孽法师若是把他制造的怪物统统放出世间,登时可以使天下大乱。不过,他透露出这天下间还有几个人能够制他死命,所以他不敢这样做,只放出一些人面兽心的伪善之徒,这些恶人很难被人发觉,所以更无人得知他们乃是被万孽法师制造出来的。”
薛陵心中叫一声“我的老天”,饶他素常胸怀大志,气吞河岳,可是这等惊人的大秘密,却听得他暗暗胆寒。
此时,江山精庞大的身躯缩小了许多,但薛陵一点也不曾注意到。
江山精又道:“那万孽法师常说人性本恶,一个人做善事,谈仁义,都是违反本性之举。而他只不过修炼种种神通,把人类与生俱来的恶性引导出来,使他从今以后不会违反本性行事!”
薛陵万万想不到这里面还有如许道理,不禁怔住。
须知这世间不乏为非作歹之人,但这等人作下种种恶孽,却很少有理论支持他的行为。这些为恶之人,绝大多数是自私成性,贪婪无度,所以变得十分残酷无情,这些作恶之人,只不过是独行其是,不会影响到别人的想法。然而这万孽法师却有理论支持他的邪恶,以此自然有不少邪恶之徒信奉他的理论,而变成以宗教的热诚去为非作歹了。
薛陵虽然没有想得这么多,可是他深心之中隐隐觉得这万孽法师十分可怕,是个可以使天下善良之人得不到安宁的魔鬼。
他不知不觉激起胸中豪侠之气,心想:“若是能够除去这个万恶之首,那就等如做了无数的善事了。”当下问道:“万孽法师武功很高强么?”
江山精道:“高强极了,最要命的是他全身所学没有一宗不是十分诡奇恶毒的,以武功而言,他炼成许多种绝艺,都十分稀奇古怪,使敌人简直无从防备,以他的点穴手法来说,人身有几处不关重要的穴道,到了他手中,却变成了死穴,不但无法救治,而且当场狂哭或是狂笑而死,使人感到十分可怖。”
他喘息一下,又道:“他的绝学多着呢,精擅奇门遁甲阵图变化,这门绝艺使他修成玄门的五遁隐身法,那就是说他凭借阵法的奥妙,使别人瞧过去发生幻觉,瞧不见他的人,只见到树木石头或者是一堆火等等。我曾经研究过他这宗绝艺,由于我晓得他炼成一种特别强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我相信这一门五遁隐身法,还包含得有这等精神力量在内。”
薛陵讶道:“江兄胸中所学也渊博得很,在下见识浅陋,真是望尘莫及。”
江山精乏力地叹息一声,说道:“我本来饱读圣贤诗书,平生作为都无愧于心,可是不幸落在那恶魔手中,终于过不了色欲大关,被他趁机使用药物,把我变成了怪物,你大概也知道,每个人的本性中总是存留有兽性,他的药物便是利用我的兽性,压倒我学问修养之功,便变成这等茹毛饮血的妖怪。”
薛陵一方面听得毛发耸竖,一方面暗自倒抽一口冷气,忖道:“这位江兄懂得如此之多,还不免身败名裂,我这读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的人,如何能诛除那万恶之首?”
他突然间发觉江山精的身躯已缩小到像是常人一般大小,不禁惊讶的说出来。江山精泛起一丝微笑,此时,连他的面孔也恢复了人形,他道:“我深心之中的一点良知、灵光,终于战胜了兽性,在这最后关头总算恢复了人性,真是值得安慰之事。”
他的话声忽然变得十分微弱,以致后来他说些什么话,薛陵都听不清楚。
薛陵想起一事,急忙大叫道:“江兄,江兄,那万孽法师住在什么地方?”
江山精嘴巴张开,可是喉咙间格格有声,竟说不出话,薛陵急忙又问了一遍,江山精用力地吐出好些声音,可是薛陵只听明白他说什么“陵”和什么“古墓”等字。
江山精瞑目长逝,身躯很快就僵硬了,薛陵把尸体搬落钟楼之下,找个钢铲埋好尸体,然后洗干净身上血迹,这时已是午后时分,他奔到那座村寨之内,找到那位老婆婆,她的孙子们和孙媳妇都认得他,因此薛陵告诉他们说妖怪已除之事,他们也有几分相信。
薛陵晓得已不必多说,反正过一段日子之后,妖怪绝迹,他们非信不可。于是他继续自己的行程,向濒海的威海卫进发,数日之后,他已到达威海卫。那时候,此城修筑未久,城内居民还不甚多,不过由于常年有重兵驻扎,故此市面还算热闹,薛陵无暇游览,匆匆忙忙向港口海边走去。
他穿过市街之时,便已发觉许多人用惊诧的目光瞧望着他,薛陵心下微感诧异,忖道:“我装扮乞丐已有多日,没有人瞧出破绽,但此处之人都惊诧的瞧望我,不知是何缘故?”
他不时碰到一队队的官兵,在他细心察看之下,觉得这些官兵步伐不整,微有紊乱之象,可见得统带此城兵马的将官,治军不严。
明代倭寇之乱,由来已久,当元末明初之际,日本因有南北朝之争,南朝失败,遗民多避入海中,遂成海盗,到明初朱洪武统一天下,以前与他对敌过的张士诚、方国珍余党不少逃亡海上,加入倭寇,作他们的向导。
明太祖虽然运用过政治手腕,遣使日本,而日本国王良怀也奉表称臣,然而倭寇之患如故,因此,明太祖知道空言不能止祸,便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五十九城,威海卫便是其时修筑的。后来又在福建等地建十六城,籍民为兵,以资守卫。
现下正是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之势最盛,这是因为严嵩当国持政,贪墨弄权,朝政紊乱,边防不修。加上近十余年来,沿海人民被繁重的徭役所迫,多逃避入倭,去年沿海告急,严嵩派他的党羽赵文华督促海防,这赵文华不学无术,既无治寇办法,又贪污凶横,侵饷冒功,对于沿海的昌国、上海、金山诸城镇,沦失在倭寇手中之事,毫无办法,反而使诸军失去斗志,倭寇益发得势横行。当时倭寇都是阔衣宽袖,沿海之人称之为蝴蝶兵,他们的船舶多奉“八幡菩萨”,所以称为八幡船,沿海居民一见八幡船和蝴蝶兵,都很惧怕。所以往往一小群数十名蝴蝶兵,就在沿海转战千里,如入无人之境。
这便是当时倭祸的大略形势,薛陵一向很关心国事,所以以前虽然住在北方内陆,但对倭寇祸边之事,也略知梗概,他刚刚走到通向港口的城门,但见禁卫森严,城门上下内外,都有许多官兵把守。
他心中一动,忖道:“是的,我这一身装束,来到这海滨防倭重地,自然会惹人注目,试想流浪乞讨之人,怎会跑到这等地方觅食呢?”
心中忖想之际,已到了城门边,两名持戈军士拦住他,盘问姓名来历与及何事出城。
薛陵报出真实姓名,又说出要到城外寻访一位世交老丈,正在说时,一名军官过来,他长相十分精干,虽然阶级甚低,却有一股慑人的威严气概。
那两名军士似是十分畏惧这位官长,语气态度都很和霭,不敢叱叱喝喝,薛陵对这名军官登时大生好感,心想:“军中若然都是这等严明军官,定必能大得当地民心。”
他忍不住向那军官请教姓名,那军官掠过一丝讶异之色,旋即答道:“本旗何元凯,现在请你到卫所走一趟,待本旗派人查明你所言各节属实,当即放行。”
薛陵忖道:“海防重地,事关国家安危,自应严格查核出入之人。”
于是只好跟他向回路走去,不一会,只见一座府衙,旗帜飘扬,禁卫森严,衙前守着“威海卫行都司”,他们进衙之后,薛陵被安置在一间大房子内,里面官兵进进出出,还有许多人民申请各事,甚是热闹。
那旗牌官何元凯吩咐两名军士看守薛陵,自去报告及派人查问薛陵所说往访之人,薛陵已说明是广寒玉女邵玉华派他前来,心想那位欧阳元章老前辈听得邵玉华之名,定必肯为他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