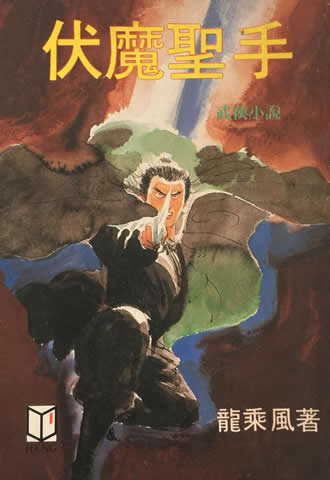正在谈论之时,女罗刹郁雅忽然在房门出现,人未到香风先送。
她娇娆的笑道:“哟,你们两位谈些什么呀。我可以听听么?”
何仲容笑了笑,道:“没有谈什么。”心中却忖想道:“女人总爱大惊小怪,又喜欢串门子东谈西论,郁姑娘虽是巾帼奇人,不比寻常的脂粉,但在这一点上,却也和普通女人一般。”
周老丈明知郁雅对何仲容有情,因心感郁雅昔日送他来扬州之恩,便打个哈哈,起身道:“老朽还有点事,去去就来。”
房中剩下这对青年男女,何仲容当然也知道郁雅的情意,可是他已把全部爱情献给成玉真,只能辜负郁雅一片柔情。
郁雅在房中坐了一会,闲谈了几句,见何仲容直打呵欠,只好怅怅回房安寝。
次日何仲容洗盥之后,便上街买了数色礼物,写了一张名帖,自个儿溜到东门,按址探询,不一会走入一条陋巷中。
只见陋巷外面只有十余间破屋,内里左边是一块旷地,右边却是一片菜园。
他走到最末的一家,柴门半掩,十分静寂。
这位俊美的少年在门外迟疑着,不敢立即叩门。心想听周老丈说,他师兄孑然一身,为人沉默寡言,对世情看得十分淡泊。虽有一身天下不测的武功,但一向以种菜为生。
当下瞧瞧那片菜园,估量大约有三亩大小,四周俱围植着荆棘,又厚又密,高达寻丈,真是老鼠也钻不进。除了从木屋的门外这一面棘墙当中开了一道门户,因此看得见园中情形之外,不论在哪一边,都不能窥望见园中。
何仲容微觉好笑,心想以申伯老人的武功,别说这么一个三亩大小的菜园,便是数十里周围,只要他留心,所有人畜经过动静,均可察知,有如目睹,因此何必弄了这么一道荆棘围墙?难道还怕人偷菜么?
菜园中除了纵横排列得齐齐整整的菜畦之外,当中有个土丘,树立着一方石碑,似是坟墓。墓上青草油绿得异常悦目,在坟墓四周,植立着二十余棵桃树,此时因在深秋,故此枝桠秃立在秋风中,显得十分凄冷。
何仲容看罢,便步到木门前,正要举手去敲,忽听屋内一阵步声出来,连忙退了几步。
却见一位大姑娘,蓬松着头发,脸上一片潮红,一面整理着衣裳出来。
何仲容冷不妨这个孤身老人的屋中,会出来这么一个大姑娘,而且又是这般模样,使人想到猥亵事情上头去。不由得在惊讶之中,加上几分分析隐情的眼光。
那位姑娘看来似是小家碧玉,此时乍见有位年轻俊美的公子,直着眼睛看她,不由得脸上一热,心儿直跳,把头一低,扭扭捏捏地走出陋巷。
何仲容怔怔地站在原处,极力要自己不要想到坏事上面去。可是他为人天生正直,竟无法以袒护的心情,硬替申伯贤老人辩解。
屋内传出一下吁气之声,甚是苍老,似乎是那老人做了一件令人疲乏的事后,舒服地坐下或卧倒时,发出的吁气声。
何仲容勃然大怒,回身便走,到了巷口,只见一个妇人在屋外晾晒衣服。当下过去,向她点点头,问道:“请问大婶,这巷子最后的一家,可是姓沈的夫妇两人住的?”
那妇人见是位公子,忙道:“啊,不是,那一家姓申,只有一位老人家,已住了几十年。”
何仲容谢她一声,便走出巷子,心中忿忿地道:“这个老家伙还能是好人么?他今年可能超过八十岁,但以他练有上乘武功的人,体力自然比常人不同,哼,居然勾引无知的女孩来泄欲,怪不得他隐姓埋名,不肯露面江湖,敢情这一手比下五门那些淫贼可要高明得多!我如不是无意撺破,只怕还认定他是个德高望重的一代高人哩!”
他口中发出“嘿嘿”笑声,折出巷子不远,只见屋檐下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长得甚是清秀,手中拿着一本书在看着。
何仲容望望手中挽着的四色礼物,余怒犹在,却又颇喜这孩子勤奋用功,便停在他面前,柔声道:“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子眼光由书本上移到何仲容面上,口齿伶俐地应道:“我姓高,名叫启福!”
何仲容勉强笑一下,道:“高小弟,你真用功,我这几包礼物送给你吧。”
高启福眼珠一转,双手缩到背后,露出拒绝之状。何仲容忙道:“我因访友而找不到地方,故此打算回去,这几包礼物带着没用……”
说到这里,门内走出一人,何仲容停口举目一瞥,微觉一惊,原来那出来的人,正是早先见到从申伯贤家中出来的大姑娘。
高启福大声道:“妹姊,他要给我礼物……”
何仲容真想拔脚走开,这是因为心中厌恶这姑娘之故。可是此时形势却不许他这样做。
他必须先解释清楚何以要送这些礼物给高启福,否则一片好心倒变成了诱拐孩子之嫌。
那姑娘直着眼睛瞪着他,何仲容苦笑一下,道:“我本来要拜访一个人,但找不到他住处,买了这些礼物,带回客店也没用。”刚刚说到此处,那姑娘嘴角一撇,大声道:“小福,回屋子里面去!”
何仲容怫然道:“难道姑娘不信,以为我故意编的谎话么?”
那位高姑娘眼睛一翻,白他一眼,道:“我又没说不信,莫不成你的话有不可信之处?”
何仲容想不到一个小家碧玉,嘴上如此厉害,自己确实无话可说。
虽然没话可说,却也不能拔脚便走,一时倒僵住在当地。
高姑娘又白他一眼,露出又怀疑又不屑的神气,并且不肯示弱,仍然站在原地。
何仲容自觉老大没趣,站了一下,心想拔脚一走,固然不大好。但老是呆站此地,人家却是住在这里的人,自没话说,但自家一个男人,竟呆立着和人家一个大姑娘对耗,更不象话!
他苦笑一下,自个儿讪讪转身走开,一面想道:“这个大姑娘这么不畏羞,哼,还算是什么好人么?”
刚走了三四步,耳中听到那姑娘咕哝道:“算你识得进退,不然姑娘非要给你好看不可!”
何仲容心中一动,突然停步,回头冷冷瞥一眼那姑娘。
他的眼光有如闪电一般,明亮锐利之极。加上他那俊美异常的面庞,越发英姿勃勃。
高姑娘不知如何,芳心一怵,竟然垂低头颅,不敢看他。
何仲容冷笑一声,心想这位姑娘原来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戮就破。
高姑娘也在心中叫声“怪”,暗想自己怎会突然不敢和他正视,当下倔强地抬起头来,凝视着那俊美公子,尖声质问道:“你冷笑什么?”
何仲容本来不会和女子斗口,但他另有企图,当下故意又冷笑一声。
高姑娘气势汹汹地冲过来,何仲容退了一步,道:“咦,你是一位大姑娘,居然也管人家冷笑。你这是要对付我么?”
她也冷笑一声,道:“对付你?哼,凭你也配?姑娘今日可要教训你这狂徒!早先在申老爹家门口,姑娘已觉得你不是东西!”
何仲容虽是有意撩拨,但好男不与女斗的观念,到底十分根深蒂固。因此不知不觉中又退了两步,道:“你不得胡说,当时我……”说到这里,猛然想起在申伯贤老人的木门前碰见她时,因她神情可异,果曾用力盯她一眼,但这等话却不便宣之于口,因此只好咽住下面的话。
她冷笑一声,追将上来,突然间玉掌已到了他颊上。
以何仲容此刻的身法眼力,居然还在对方手掌堪堪沾上自己面颊时,方始发觉,心中不由得一阵骇然,疾忙使个身法,旋将开去。
饶他闪避得快,但鬓角已被高姑娘指甲挑刮着,掌风拂面而过,劲而不猛。
何仲容更加惊讶,暗忖这姑娘的掌力,分明已练到刚柔兼济,收发自如之境。这等功力,出诸于一个容貌平常的小家碧玉身上,不免令人奇怪。
高姑娘一掌掴不到他,并无惊奇之色,身形一侧一旋,双掌一齐交叉掴出。
何仲容登时大感为难,但觉对方这两掌夹攻上来,真是妙到毫巅。自己除了使出重手法,取她胸前大穴之外,别无闪避之方。
这原是刹那间的事,何仲容不暇多想,左手压住胸前的“鸠尾穴”,以免被敌人打着时,把真气击散,右手使出一招“推窗望月”,掌上含劲蕴力,蓄而不发,是以只有极微弱的风力,铁掌直向对方左胸击去。
高姑娘面上微微变色,但其时不但自己双掌已交叉向对方面颊上击到。而对方的铁掌,也只差分寸便触及自己左胸的“膺窗穴”。
何仲容这一招发出去,非迫对方撤掌不可,否则两败俱伤。自己可以不死,对方却非当场毙命不可,是以他的招数有发无收。
“霹啪”脆响一声,何仲容面上一阵热辣辣的,但连牙齿也没动摇。这时他的铁掌也按到对方左胸上,手触处一片柔软中而又蕴有弹性。
何仲容在这刹那间,暗骂自己一声“该死”,倏然奇快地把铁掌撤回来。
高姑娘的面上泛起红潮,转眼间连耳根都红了。她左胸被何仲容摸了一下──其实是按了一下──比时尚感到一阵奇异的滋味。
何仲容骂自己该死的原因,十分简单。只因他在掌力欲吐未吐之时,蓦然醒起以自己目下的功力,击毙一个籍籍无名的姑娘,不论事情的是非曲直如何,也将遭到江湖嘲笑。而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他对一个姑娘家,居然用这一招把她击毙,明眼人一看便知,更加会被武林不齿。
高姑娘银牙一咬,沉声道:“好狂徒,你敢仗着练过几手武艺,便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姑娘今日非教你死无葬身之地不可!”
何仲容一听,敢情这个不起眼的姑娘,语气中倒真有江湖味道,正要道歉赔罪。高姑娘又道:“这儿是通冲大道,不便动手。你要是还有点男子气概,可敢跟姑娘到申老爷的菜园中比划一下么?”
何仲容极快地想了一下,还未想清楚时,一眼省见高姑娘面含鄙视之色,登时激起执拗之性,朗朗道:“姑娘先请!”
高姑娘冷笑道:“你先走,我可怕你撤腿逃跑!”
何仲容大为不悦,但此时此地,不便再斗口舌,便爽快地向那陋巷走去。
转眼间已走到菜园门口,他大踏步进去,回头一瞥,却不见了高姑娘。
正在讶异间,旁边那间木屋“呀”地开了一道后门,高姑娘自门内走出来。
何仲容明知这间木屋,便是申伯贤老人所居,心想高姑娘必定已将事情告知申伯贤,便睁大眼睛,等那申伯贤老人出来。
哪知高姑娘出来之后,那道后门静悄悄的,并无第二个人出现。
高姑娘先过去把菜园门关好,然后转身厉声道:“大胆狂徒,你既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调戏妇女,想来姑娘不会是第一个被害的人。今日姑娘要替那些被害的姊妹们,尽报仇恨!”
何仲容忍耐不住,面色一沉,严肃地道:“姑娘你不能含血喷人,适才我发的一招,便是临时醒悟,因此才不发掌力,否则你此刻还能胡乱加罪于何某人么?”
高姑娘怔一下,似乎觉得有理,何仲容又道:“何某可以向姑娘道歉赔罪,但纵使斧钺加身,决不肯承认姑娘所加的罪名!”他说得如此慷慨激昂,语气严肃,那姑娘已软了一半。
何仲容闭口静候她的回答,忽见她头颅微侧,似是凝神倾听什么。他不禁讶异起来,也自凝神查听,却听不到有什么可疑的声息。
高姑娘点点头,轻轻道:“我知道了。”何仲容还以为她对自己说的,方在揣想言中之意。又听她大声道:“你的狡辩诚然动人,但姑娘不吃这一套,除非你站着不动,让姑娘掴你几巴掌,或可饶你一趟。”
何仲容心中愠怒,便不言语。她款款走上来,又道:“一动上手,你的苦头可就吃得大啦!你不信么,看掌!”喝声中一掌飘飘拍过来,何仲容出手封闭来路。
只见她右肩一沉,便知她底下踢出左脚,连忙分一掌封住下盘。
微风拂处,她另外未动的左手,不知如何已拍到颊边。这时何仲容才知道中计,敢情对方招数奇异奥妙,出手都从意想不到之处攻到。
百忙中不暇多想,仗着内功湛深,猛可施展出“仰观天象”一招,上半身向后一仰,双掌已连续攻出,狂飊蓦起,潜力如山,果然把对方迫住。
他横跃数尺,然后仰天笑道:“想不到十步之内,竟有芳草。呔,你也接我一招!”双掌一分,欺身扑去,虚虚实实地使出劈砸拍抓四种手法。
高姑娘左手在面前划个圆圈,右掌疾然从圆圈中拍出去。
何仲容收掌不迭,退开数步,定定神想道:“她的出手奇奥无匹,轻描淡写间便把我的辛辣攻势消解。但假如她知道我这一出手,连四堡五寨那几个老头也招架维艰,而她却这么从容轻易的话,她一定不会自甘寂寞,默默无闻地住在扬州城中……哎呀,我必需找出她的弱点才行。”想得虽不少,但也不过是一刹那而已。
高姑娘移宫换位,娇喝一声“狂徒看掌”,右掌一晃,忽地踏入奇门,左掌已堪堪掴到他面上。
她每一出手,全都是掴嘴巴的绝妙手法。何仲容大大一凛,一招“星移斗转”,身形疾旋开去,他的身法已奇快绝伦,但面上仍然感觉到对方掌风刮过,只差一线便吃她纤指刮着。
当下使出“毒龙掌法”,左手半招“少阳再引”,攻取对方右臂。右手一招“急流鼓棹”,疾取对方中盘。前一招是华山派绝招,后一招是武当派煞手。两招同时使出,威力之大,一时无两。
何仲容招数出手,猛可发觉自己功力大进,对敌时已可不拘法度。这两招同时并使,正是要对付对方那一招怪异手法。而他以往一向不曾练过以左右手分使不同的招数,此时却因时随势,自然而然地便施展出来,由此可见得功力大进。
高姑娘左手又划个圆圈,右手从圆圈中击出去。这一次左手所划的圆圈较大,威力迥异。
何仲容咦一声,自动收招疾跃开去。
高姑娘冷笑道:“你就学会跳跳跃跃的本领么?姑娘至今脚下未移动过一下呢!”
何仲容无话可答,心中一味寻思破她这一手怪招之法。
高姑娘忽然退到纵横排列的菜畦中,冷笑招手道:“狂徒敢过这边来比划么?我们约定不许踏上菜畦如何?”
何仲容岂甘示弱,纵将过去。那菜畦每一行相距不过一尺,因此只能直攻直退。
她迫上来,左掌一晃,右手已拍到面门。何仲容蓦地悟出对方掌法的奥妙,全在脚下。原来当她左手虚晃时,身形忽在无声无息中移前尺许,故此她早已举起欲拍的右掌,忽然已到了他面门。当下真气一沉,力聚右脚,身形蓦然向右边欹到。
那高姑娘右掌扫空,左手一沉,便已掴到。好个何仲容,内功精纯,提住那口真气,身形倏地侧贴地上。
高姑娘两掌皆落空时,何仲容右手虚虚向地面按下,左掌力劈对方胫骨。高姑娘只好退了一步,何仲容已站将起来,朗声大笑道:“这一次姑娘可移动了吧?”
话虽如此,但何仲容心中却十分烦恼,只因对方这个姑娘,打到如今,总是那么两三招,自己却已使出好多种身法和招数,却还未赢得人家。这一来他可就想到假使是那个传授她武功的人,亲自出手的话,他如何能吃得消?
高姑娘一连掴了数次,俱告落空,已有怯战之意。何仲容蓦地大喝一声,纵身跃上半空,由空中俯攻下来。
那姑娘仰面向天,仍然以左手划圈,右手从圆圈中击出来。
何仲容但觉无懈可乘,提着那口真气,斜斜飘落左方町畦中,脚一沾地,复又腾身而起,极快地从她身边掠过,顺手攻出一招。
他明知对方只要看得见自己攻到,使出那一下怪异手法,自己便攻不进去。因此一掠即过,身形落在右边隔了一道菜畦的畔埒时,复又疾掠回来。
转眼间何仲容已化出四五个之多,四面包围急攻,这刻他尽量施展轻功,虽不能落脚在菜畦上,但菜畦不宽,四方八面尽有畔埒可供落脚。
高姑娘面上失色,一味使出那一式护身奇招,不过目下改为左右手并开,脚下直向菜园中心退去。
何仲容攻得甚急,有几次他已有取胜之机,但因必需用极霸道的招数,是以纵然胜了,对方也得立毙自己掌下。他是个侠义为怀的人,岂能无端取她性命?只好轻轻把机会放过。
不觉已移了两丈许,本来都是直着排列的菜畦,如今已变为横直相间。何仲容奇快地左起右落,每逢贴着对方身形掠过之际,便顺手攻上一招。
蓦地情势大变,原来他算好落脚之地,临到快要到达时,忽然发觉仍是菜畦。忙不迭仍然就着去势,提气一飘,果然飘前数尺,刚好踏在町畦间。
这一来攻势为之一挫,只因他一向仗着身形奇快,使得对方应付艰难。目下慢了这一线时间,那幻化出来的人影便立时消灭。
他也不急急继续攻击,徐徐转身,蓦地讶疑交集,原来高姑娘在这一瞬间,又远在八九丈以外。
“真是咄咄怪事,以她的脚程,如何能走到那么快?”何仲容想道:“莫非她从申伯贤老人处,只学到那两三招和这奇快的轻功么?”念头在心中一掠而过,自个儿仍然屹立当地,不肯追赶。
却见高姑娘回头冷笑,似是笑他毫无法子对付她。何仲容心中虽然不忿,却依然不追。
高姑娘转眼间已隐人菜园中心那二十来株树木之后,不复再现出身形。
何仲容等了一刻,本待径自走出菜园,回心一想,那申伯贤老人武功之高,如今已可窥见一斑,这等当代高人,却不能与之一见,未免是件大大的憾事。
这么一想,不知不觉恋恋不舍离开此地,同时觉得菜园中心那块墓地十分可怪,是以动了好奇之心。
当下举步向那块墓地走去,准备瞧瞧那方墓碑,究竟葬着的是什么人?如能见到高姑娘,设法把过节化解,不要再打。
晃眼间跃过菜畦,到达墓地边缘。
只见高姑娘在左面一棵树后,现出身形,严厉地道:“站住,姑娘有话交待!”
何仲容如言止步,也自沉下脸色,凝视着她。忽然发觉这个貌不惊人的姑娘,眉宇间隐泛煞气,那双眸子中,流露出聪慧过人的光芒。这一刹那间,对她的印象大为改变,已不敢过于轻视。
“姑娘先警告你,第一不得擅自踏入这片墓地,否则有死无生!”
她的话声极为坚决,一听便知绝无通融余地。何仲容正要回答,却听她又坚决地道:“其次你如无法出得此园,而又不敢妄自尊大,侵犯圣地,可跪倒向天立誓,此后不向第二人提及今日之事,便可放你逃生,你听清楚了没有?”?
何仲容抑住一肚子怒气,反而仰天朗声大笑,应道:“何某人听得清清楚楚。”
高姑娘立刻接着道:“很好,生死祸福,唯你自招,就看你自己如何决定。”说罢,复又隐入树后。
何仲容极快地想道:“她无端说这番话,决不会虚声恫吓,难道申伯贤老人已决定出手拦截?好极了,我何仲容今日得会天下第一高手,死亦何憾?”
想毕便迈步前走,刚刚走了两步,忽又想道:“这块墓地既称为圣地,一定是申伯贤老人本门中的禁区,这等情形在天下各派也不是没有,我可不能为了私忿,因而犯人大忌。”一念之转,便自回身而走,准备一径出园,堂堂正正地叩门找那申伯贤老人。或是他中途拦截,亦可一睹称绝天下的六纬神功。
走入菜畦中施展出轻身功夫,直向园门那面纵去,一掠三丈许。几个起落之后,忽然惊讶得直瞪眼睛,放情眨眼间方向全变,那道园门已移到右后方。
他觉得十分迷惑,改变方向,又是几个起落。一眨眼间,那道园门虽然仍在前面,但似乎离得越远。
他停住脚步,暗中咬咬舌尖,疼痛之感尚在,便确定没有白日见鬼,可是为何越走越远?
回头一瞥,那片墓地依然在身后,光秃秃的桃树在微风中显得十分孤零冷落。
他继续向园门跃去,奋力急纵,然而半晌仍然未曾到达门口。
这种奇异的情景,使得他觉得恍如坠入梦境中。在梦中常常会发生好些奇怪的现象,明明一件极为轻而易举的事,却变成十分艰难。譬如想走得快些,偏偏双腿沉重无比,或在高处俯瞰下面,本想站得稳些,偏偏不由自主地向下面跌坠。
何仲容此刻便是生出这等恍惚的感觉,奔跃了好一会,渐觉视线模糊,那道园门已瞧得不大真切。
何仲容又奔跃了一会,前面一片迷茫,园门已不知在何处,同时人也有点困倦欲睡的感觉。
这时他脚下越来越慢,但他自己还不知道。
过了片刻,何仲容倦眼朦胧地踉跄而行,心中迷迷忽忽,已忘了自己何故在此。
无意中一回头,只见不远处一片碧绿墓地,墓地上错落地挺立着二十余株桃树。
这景象是那么熟悉,以致何仲容不由自主地向墓地走去。
踏上墓地边缘,心头逐渐明白过来。但到他陡然想起前事,人已走进桃林之内。
这二十余株光秃秃的桃树散布在墓地四周,故此甚是疏落。
但他走进桃林之后,立刻感到好像走入重重埋伏之中。四方八面,都屯驻着坚甲精兵,生像只等他一出来,便冲杀过去。
何仲容定定神,觉得太以奇怪。穿过两株桃树,这种感觉更加深切动人心魄。
猛一回头,只见桃树上钉着一个白色的木牌,上面写着好些字。
何仲容好奇心一动,便走回去瞧着。只见那方白色的木牌上,用朱笔写着:“桃神守墓,窥秘者殛!”等八个隶书。
他悚然一惊,心想自己虽然读书不多,但这八个字,意思却甚明显。是说这个坟墓是一件秘密,故此由桃树之神守护,窥探坟墓秘密的人,桃神便要将他殛毙。
眼光一闪,又见隔邻那株桃树上,钉着同样的一方木牌。
过去一看,那牌上写着:“避劫之门,近在眼前!”等八个朱笔隶书。
这八个字他可就参详不出其中意思,楞了一会,想道:“怪不得刚才那姑娘一闪入树后,便自不见,本来这些桃树并不粗大,一个人决不可能躲在后面而不露出形迹。原来这些桃树有神,因此我在外面瞧不见她。但是不是真的有神?”当下决定不去窥看那坟墓秘密,只因自己本来不是为了刺探人家秘密而来。
转身向桃林外走出去,只见桃树一株一株不断地掠过,但走了半晌,还未走出墓地。
这次他已经留上神,因此一直保持着头脑清醒。这种奇怪的情形,他很快便已发现。但发现了也没用,他走了好久,仍然在墓地内转来兜去。
不觉已转近中心那座坟墓,只见墓碑上刻有字迹,大概是墓中人的姓名。
这时忍不住奔到墓边,那方长形的高达五尺的墓碑两边均刻着同样的字迹。
何仲容看时,只见上面刻着“天机地秘之墓”等六个斗大的字。
转过后面一看,也是刻着这么六个大字。
何仲容面上露出一片茫然之色,举手搔搔头,忖道:“天机地秘一定是两个人的名字,但这名字真怪,我从来未听说过。”举头四望,只见天色暗沉,四面都有点迷蒙灰黯。
何仲容大诧,想道:“适才分明太阳高悬,天气晴朗,嘿,这里真有点邪气。”转念又想道:“我不如跃上坟顶,加上这墓高出地面,视线自可越过桃林,看到整座菜园的一切。”想毕便做,腾身一跃,脚方离地,斜刺里突然一股吸力袭上身来,把他扯得向横边飞开。
何仲容借势飘落地上,虎目电扫四周一眼,只见一个白发龙钟的老头子,身穿蓝布大褂,足踏布鞋,径由桃树后走出来。
何仲容心知是申伯贤老人,暗忖如今已有过节,不可道出他姓名,以免吃他查问出乃是他师弟周工才泄的底。周老丈可能因此遭受师兄处罚,因为这可不同于以礼求见。当下故意朗声大笑,道:“何某还以为桃神出现哩!但桃神既会殛人,不该像老丈您这般模样,应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才对。”
那老头子身量甚是高大,但因腰弯背驼,是以看不出来。一双老眼皮浮肿,眉毛长长垂遮眼盖,没有一点神气。
何仲容如不是早得周老丈告诉他这申伯贤来历,怎样也不会想到这个糟老头子会是当今宇内武林第一位高手。即便现在已知他底蕴,但也不大相信他已承继了云溪老人的衣钵真传。
老头子眼皮抬也抬不起来似的,缓缓道:“老朽虽不是桃神,但年轻人你将不会觉得比遇到桃神好受些。年轻人你不相信么?这也难怪,你叫什么名字?何故欺负老朽义女?”
何仲容讽嘲的笑容未敛,应道:“在下何仲容,无意中遇到那姑娘,因误会而动手。在下岂能欺负于她?不信可以请她出来当面问明白。但你别误会,在下并无惧怕之意,刚才我手下留情,没有使出重手法,否则你的义女早在未进这菜园之前,便已死在我掌下。哦,老丈贵姓高名?可肯见示?”
糟老头子眼皮微微一抬,何仲容已看到一线奇亮如电的光芒,微闪即逝。
“老朽申伯贤,隐居此地数十年,从来不肯和江湖人交往,因此你不会听过老朽之名!但你不必在老朽跟前吹牛,你大概是个后起之秀,因此目空一切,以为天下人都不过如是,今日你可要碰个钉子,得到一个宝贵的教训。秀儿出来,再露两手给这个年轻人瞧瞧。”
先前那位高姑娘应声由一株桃树后转出来,何仲容大感诧异,只因那株桃树不过比碗口还粗一点,怎能掩蔽住一个人的身形而不露出来?
正在诧讶之际,却见那姑娘眉头锁起来,露出为难之色道:“义父,你老只教我几手,此刻叫我上哪儿再露两手呢?”
申伯贤道:“你这丫头真够笨的;老朽叫你出来,难道还会使你吃亏么?”
何仲容听了又在心中叫怪,同时也有点惭愧,暗想自己这回可真得到一点教训,人家一个大姑娘,内家功力分明远不如自己,轻功也不能和自己相比,但仅仅凭着一手划圈的招数,便足够将自己凌厉进攻的任何招数挡住,甚且两次三番差点儿掴到自己一个大嘴巴!由此可以想见那老人申伯贤,本身的武功将是何等厉害。
他一面想,一面向附近的桃树张望。
高姑娘嘴巴一嘟,道:“义父你先把他治住,秀儿才掴他嘴巴,同时还得把他的武功废了,免得将来又去害人。”
老头子笑一声,道:“秀儿,你看清楚这家伙不是好人么?”
她顿顿脚,道:“一定是坏人,他竟敢……”下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自家因提起而想到刚才的一幕,不由得气得粉脸涨红。
何仲容因她在一旁,不便把情形说出来然后加以解释,当下只好歉然道:“在下纵有过失,亦属无心,老丈不可尽信一面之词。”
申伯贤老人眼睛一瞪,道:“难道秀儿会哄骗我么?她还说要废你武功呢!秀儿,听我的话,过去给他一个嘴巴。”
高姑娘纵过去,大声道:“义父,这回一定要掴得到才行啊!”叫声中一掌掴去,出手奇突,来势虽不快,但何仲容因不能立刻判断她如何变化,只好挨到她手掌快要掴到脸上之时,这才倏然闪开。
申伯贤道:“秀儿,你为何不掴他嘴巴?”
高姑娘楞一下,停手道:“他不是闪开了么?”
申伯贤道:“设法别让他闪开不就行了?我教你一个法子,你一掌掴去,顺便吐口唾沫,迫他非向左右闪避不可,然后用‘左右分花’的手法,必定可以掴他一掌。这可够简单么?”
高姑娘道:“你老该暗中告诉我问啊!”
何仲容想道:“难道我不会招架么?啊,不行,老头子这些话,分明要引我出手招架。”
高姑娘娇声喝道:“狂徒小心看掌!”一掌横掴过去。
何仲容见她掌势来得奇怪,单是这么一伸手时,途中已连变了两下,生像变化太多,一时反而不曾变出来,心中不禁微凛,决定不出手封架。
高姑娘手掌堪堪击到何仲容面上时,何仲容根本不必瞧看,一双虎目,却紧紧盯在她的面上。果然瞧见她嘴巴一呶,直是要吐唾沫的样子,猛吃一惊,忙忙左闪。
高姑娘唾沫没吐出来,但手掌一翻,手背已拍到何仲容面上。
何仲容到底功力高强,就在她手掌已拍在脸上的一刹那,居然还能改左闪为直退。这一下变化得快,因此虽然到底吃高姑娘掴着面孔,却没有响声。
然而这已够何仲容羞愧交集,大吼一声,疾如奔雷闪电般反扑回去,使出毒龙掌法,双掌翻飞,宛如长江大河般绵绵力攻。
高姑娘左手划个圈,右手划个圈,神妙无伦,居然封得严严密密。可是何仲容内力太强,迫得她立足不住,直往后退。
何仲容的毒龙掌法,乃是毒丐江邛把他师父毒死之后,把他师父的一本秘籍“六纬神经”的上册取到手中。这本秘籍遍载天下各大门派的精奥武功,毒丐江邛苦练了三十年之后,攘精取华,一共选了十三招,加以细微变化,使之能贯通连接,一气呵成。
这套掌法威力不比等闲,尤其有一点妙处,你如功力越高,则这套掌法的威力越大。
何仲容以全力使出来,但见人影兔起鹘落,迅疾如风,双掌前攻后守,声东击西,忽而有雷霆万钧之成,忽而似冰雪一片。
堪堪攻了七招,高姑娘已香汗涔涔,面目失色。
要知何仲容本是侠义中人,当初虽觉得自己受了冤屈,但对方一介女流,胜之不武,更不能把她杀死,故以动手时,不曾像现在这么凶狠,目下那申伯贤既是一代高手,虎视在侧,自己又被那姑娘所辱,几方面一凑,不觉使用了全力。倒没有想到自己这么一出手,对方假如失闪一招半招,势必命丧当场!
申伯贤本来漫不经心,这俊美公子功力之深,虽然令他讶异了一下,但万万想不到他竟能溶会聚集天下各大门派的绝招于一身,是以连他师门秘传无上护身绝招“圈里乾坤”也抵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高秀的功力太差,但单单这样,也就够使这位天下无双的武林高人申伯贤为之动容。
何仲容招数使得方自顺手,猛可施展毒龙掌法中得自岳家散手的“直捣黄龙”一招,拳头上风雷迸发,刚猛绝伦地直击出去。这一招对方如仍划圈封架,非吃他震出寻丈以外不可。
高秀惊噫一声,现出慌乱之象。说时迟,那时快,何仲容的拳头已到了她胸前尺许之处,拳风有如狂飊巨浪,排空激卷。
老人申伯贤本来离开他们两丈以外之远,此时人影一闪,已到了高秀身侧,伸臂一架,何仲容的拳头恰好击在他臂上。
何仲容这一拳运足全力,又极得势,拳力之重,天下罕睹。申伯贤老人竟然视若无睹,任得他一拳击在臂上。“啪”地响处,何仲容虎吼一声,“蹬蹬蹬”退了三步之多。
却看那白发苍苍的老人时,只见他身形纹风不动,此时竟不理他,一径低头向高秀道:“秀儿,可是给骇着了么?等义父先替你掴他一个大嘴巴出出气如何?”
高秀吁口气,道:“不,我要亲手掴他!”
申伯贤老人笑道:“那也使得!”
“义父,他想逃跑呢!”
“逃跑?你放心,他逃不了……”
何仲容勃然道:“何某虽然武艺平常,但从来不曾试过临阵退缩。”
申伯贤老人笑道:“小伙子,你让我义女用话扣住啦,看来你也是个笨蛋!”
何仲容心想这位老人大概喜欢骂人家“笨”,故此早先连他的义女也挨一句“笨丫头”,现在却叫自己做“笨蛋”。不过他的话不无道理,那高姑娘的话,分明是摆个圈套。
老人道:“你把刀亮出来吧!”
何仲容哼一声,道:“除非你也用兵器!”
申伯贤白眉一皱,道:“笨蛋,凭你那点道行,也敢空手和我老人家动手么?”
何仲容道:“你爱怎样想我管不着,但我决不能用兵器对付一徒手的老人!”
老人先是摇摇头,跟着笑一下,道:“这一点执拗还算可取,碰上疑难微妙之处,也许能够执拗地非弄个明白不肯罢手!”
何仲容不明白他的说话有何含意,一径行功运气,准备应付这位天下第一的武学大师。
有一点令他大惑不解的,便是刚才使的一招“直捣黄龙”,势猛力沉,无与伦比。以他历经大小许多次厮杀的经验,知道这一拳换了四堡五寨任何一个老的主儿,纵然抵挡得住,却也比他多退一步。只因他除了如今功力更为深厚之外,还加上拳势已顺,故而拳上的力量,何止增加了一倍!这样说来,申伯贤老人功力之强,岂不是比四堡五寨如金大立成永等人要高出数倍?
当年号称天下无敌的云溪老人,听成玉真叙述,似乎并不比四堡五寨最老一辈的人物高出这么多。要是改为现在四堡五寨的九人施展出金龙八方天马阵,是不是仍然可以赢得申伯贤?
这个疑问有如电光一闪,便自掠过心头,此刻他没法子询问,也不暇询问,扬手一掌,径砸对方左胁。
申伯贤动也不动,等他手掌已堪堪砸到左胁上时,这才一吸气,身躯骤然伸长尺许,因此腰腹间最少因而幼细了大半。何仲容这一掌竟然变成击向虚空,连对方的衣服也没擦着。
何仲容暗自一惊,心想这等精纯功力,不论天孤叟瞿寒或是黄衣老人宇文飞,即是当今少林方丈梦智老禅师的师叔松雪大师的孪生兄弟,也比不上他。
这念头在心上一掠而过,心中尚不敢确定,当下使出“金指银掌”的功夫,因他如今武功已入化境,相情度势,居然不依照好友高弃所传的出手,竟是先以一招“天女散花”,双掌疾出,幻出七八只掌影,待到掌影已临敌人身上,方始化为左掌右指,招式大变。
这一下手法变得高明神妙,虽是山右老农孔廷式亲自到此,见他居然能够以昆仑派的绝招先行掩护,然后才施展出他独门“金指银掌”的功夫,也得为之心悦诚服。
申伯贤老人淡淡一笑,面上神色如故,但其实心中大震,这时才知道这个少年,竟然堪以称雄于天下高人之中。
何仲容吐气开声,嘿然一喝,宛如平地起个响雷,端的神威凛凛。
喝声中,右指左掌均已击在申伯贤老人身上。但他掌指上的功夫只用上五成不到,只因他明白像申伯贤这等不可一世的高手,一定练有特别厉害的气功。假如他这一下用足全力,而又不是击在对方畏忌的穴道上时,势必反被对方借力反击。自己用力越大,便受伤越重。
那申伯贤老人在他掌指及体的一瞬间,身形暴然缩小许多。因此何仲容本来取的是死穴部位,但在击到他身上时,却有了些微变化。
何仲容一击中对方,猛觉掌指所及之处,暗具弹性,便知不妙。申伯贤老人运动六纬神功护体,此时体内真气有如珠走玉盘,将对方力量卸开,蓦然反震出去。
何仲容站立不稳,连退四五步,不由得一阵骇然,定睛凝视着面前的老人。
申伯贤老人冷冷一笑,道:“你虽学会天下各家派的功夫,却也奈何不得老夫!”
何仲容心知自己决非其敌,但此刻绝无退走之理,蓦然灵机一动,从容笑道:
“想不到在这市廛之地,居然除有当世第一位高手!何某虽然不才,但方今敢垂手让何某一击的,只有‘六纬神功’能够抵挡得住……”
申伯贤老人蓦地神色一变,道:“何仲容,你既知道老夫来历,今日想出此园,只怕已办不到!”
何仲容讶道:“为什么呢?难道昔年威镇天下的云溪老人,有什么事不能让别人晓得,故此老丈你传承衣钵之后,也被迫隐遁于此?”
“老夫不必瞒你,这一点果然是老夫不肯露面于世的理由,但认真讲究起来,老夫淡泊断绝尘欲,却是最要紧的……今日你既不能生出此园,老夫要大展身手,教你死得心悦诚服……”
何仲容夷然不惧,道:“何某虽不想如今便死,但如死在当世第一位高人手下,却也光荣之至!”
申伯贤老人颇为惊讶,心中疑念潮生,但此时不经细想,口中喝声:“你仔细防守吧!”人随声动,迅疾如风,飊忽间已欺到何仲容身前,只见他一掌拍到,竟不知何时出手,更摸不准来路。
何仲容心中大不服气,右手一招“手挥琵琶”,欲攻还守,左手蓦然使出少林十八路无敌神刀的绝妙招数,伸掌如刀,急斫敌人腕脉。
这一掌发出之后,连何仲容自己也感到惊奇。敢情掌发如刀,又快又狠,威力之大,不可思议。
申伯贤老人微噫一声,掌势化为擒拿,扣擒他那如利刀般的左掌。
何仲容拼着左手被扣,争取一线机会,右手又化为刀势,使出无敌神刀中“夜渡关山”之式,猛可疾取对方胸腹。掌风锐烈惊人,比利刀劈风之声尚见功力。
申伯贤老人飊然退开半丈,朗声大笑道:“真有你的一手,老夫竟也差点走了眼,如今你可掣出宝刀来,且让老夫瞧瞧少林寺十八路无敌神刀,是否真个无法可破!”
这刻老人雪白的须发,无风自动,豪雄中又极是威猛,高姑娘失声道:“义父,你别太生气,提防气坏了身体……”
她哪知申伯贤老人“淡泊”二字上,下了数十年功夫,因而养成了与世不争的性情。然而他既能练到天下无双的功夫,当初必有争雄要胜之心,方克成功。是以细究起来,淡泊二字,不过是另一种境界,岂能完全泯灭了雄心?因为他之所以求淡泊,一方面是觉得尘世一切,均不值他一争。但另一方面说来,他此举是要特立独行,超乎天下武林之上。这刻却因何仲容惊世骇俗的武功,触发了他一腔豪情雄心,是以命何仲容亮出刀来。
那少林寺十八路无敌神刀,云溪老人昔年曾经加以研究,深知其中三昧,故此申伯贤老人所说的话,却是甘苦之言。
高姑娘哪能明白这等武林豪侠对武学上的感情,是以见到申伯贤老人须发俱动,便误以为他老人家十分生气。
申伯贤道:“秀儿,你站远一点,你不会明白义父的心情……可还记得义父曾对你豪气地说过,当今宇内,能够接得住你义父三招的人,不会超过七人,是以早先我先让他两招,留下一招出手。那知居然出手无功,这一来义父的话可得改七个人为八个人了。”
何仲容听了矍然动容,立刻掣下蓝电刀,抱元守一,调运好真力。
申伯贤老人拂须道:“你无庸客气,尽管动手!”
何仲容应声“好”,迎面一刀削去,化出大片刀光。